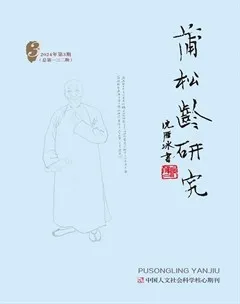震震雷霆 皆为一人
摘要:《聊斋志异》中《纫针》篇不太为人关注,但小说可读性强,故事情节复杂,人物命运曲折,倒叙、插叙天衣无缝,巧妙运用了“雷霆”天象有机串联,首尾呼应,结构精巧。小说不仅让读者领略到蒲松龄行文叙事的文字造诣,还可以通过一个弱势年轻女子逆转命运的故事,看到社会底层女性之间互助与感恩的人性之美,感受到蒲松龄在世态炎凉背景下对女性处境的平视与思考。同时,小说也成功塑造了三位有信念、有行动力的鲜活感人的市井女性形象,这是蒲松龄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也是其仁义思想的体现。
关键词:救赎;女性互助;人性之美;雷霆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
《纫针》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中并不起眼,故事的主旨是惩恶扬善,塑造了三位有别于其他篇章的市井女子形象,其命运在抗争、救赎和恩义中交织起伏,在世事冷暖中彰显了人性的良善之美。女主人公纫针非妖非仙,在一连串困境中信念坚定、有情有义,最终实现了弱势个体的人生逆袭。
纫针的故事从母亲范氏与另一位女性的对话写起。东昌府商人虞小思的妻子夏氏走娘家回来,在自家门外遇见一个老妇人带着一个少女,见两人哭得很伤心,便上前询问,“妪挥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斋,亦宦裔也” ① 。蒲松龄瞬间调转笔尖,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老翁王心斋借钱出去做买卖,中途遇盗被劫,差点丢了性命。债主黄氏追债,“计子母不下三十金,实无可以准之”,连本带利不下三十金,家里实在没什么能抵偿的,债主看上了王家姑娘纫针。“王谋诸妻:妻泣曰:‘我虽贫,固簪缨之胄。彼以执鞭发跻,何敢遂媵吾女!且纫针故有婿耳,汝乌得擅做主!’”簪缨:古代官吏的冠饰。胄:古代帝王或贵族的后裔。我们再穷也是名门之后,不给他一个驾车发家的财主做妾。一句“汝乌得擅做主!”足见老太太的坚定和见识,也引出了纫针原有婚约的信息。纫针是“褓中论婚”,和同县傅孝廉的儿子阿卯订了娃娃亲。后来傅孝廉到福建做官,不久去世,两家便断了音讯。
范氏打消了老伴的念头,但难处还在,为了保护女儿她必须付诸实际行动。范氏祖父曾是京官,给她娘家兄弟留下的家产不少。“次日,妻携女归告两弟,两弟任其涕泪,并无一词为之设处。”设处:安排、处置。这里的叙事比较有意思,是从纫针之父王心斋的角度讲述,更凸显了他在女儿命运这件事上的“缺席”。家境优渥的亲兄弟袖手旁观,希望再次破灭,范氏带着女儿一路哭着回来,半道上遇到了夏氏。亲情如此凉薄,但素不相识的夏氏动了恻隐之心,“视其女,绰约可爱,益之哀楚”。她邀请母女回家,安排她们吃喝,“慰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这边范氏还来不及谢恩,纫针“已哭伏在地”,这是蒲松龄对女主角纫针的第一次正面描写,之前她像个符号,只是在行文叙述中充当背景角色。纫针这一行动起了作用,她敏锐地把握住时机,让夏氏愈发怜惜动容,更下定决心去帮她们。三十金也不是个小数目,夏氏承诺“当典质相付”,她与纫针母女以三日为约,随后开始想办法筹措资金,甚至回娘家向母亲借钱。整个过程夏氏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虞小思,在封建社会的男权视野里,这样的女性形象超越了时代,果敢仗义,有侠气,展现了女性的力量。一如冯镇峦赞:“天下惟难能之事为可贵耳。”不承想平地起波澜,赎金凑齐的当夜,夏氏的房中进了强盗,“夏觉,睨之,见一人臂上悬短刀,状貌凶恶。大惧,不敢复作声,伪为睡者。”盗贼翻到了夏氏枕边包裹着的钱,扬长而去。面对危险,夏氏可以沉着冷静,面对陌生人的急难,她也能慷慨相助,但巨额筹款的失窃却击垮了她,绝望比困境更致命,她只得上吊自尽。“虞知,奔至,诘婢始得其由,惊涕营葬而已。”夏氏之夫虞小思正式登场,蒲松龄遣词造句精准凝练,“奔至”“惊涕”,几个字就活现了一个不狭隘的男人形象,当然这一点读者到后文会更明白。对于要褒扬的人物,蒲松龄从来不吝笔墨,总要给予他们足够神异的光环。
场景转到夏氏墓,得知消息的纫针跪在墓前哭,“暴雨忽集,霹雳大作,墓发,女亦震死。虞闻,奔验之,则棺木已启,妻呻嘶其中,抱之出。见女尸,不知其谁。夏审视始辨之,方相骇怪。”很快,范氏赶来,“见女已死,号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闻夫人自缢,日夜不绝声。’”冯镇峦评:“读至此令人目眩心惊,双瞳霍霍不定。”这段描写节奏快,信息量大,反转不断,充满了戏剧张力。一场生死交替迅雷不及掩耳,魔幻十足,细节却毫不含糊。虞小思没见过纫针,所以他不认识,刚苏醒过来的夏氏也不会第一时间认出纫针。由此,夏氏夫妇得知了纫针的情义,于是就地安葬了她。接着,剧情继续反转,“闻村北一人被雷击死于途,身有字云:‘偷夏氏金贼。’”按蒲松龄的行文节奏,当是同一场雷击,如此因果报应的氛围感更足,更符合民间信俗。冯镇峦点评:“快哉!人心天道,理实可信。”遭雷劈者是邻村一个叫马大的无赖,正是他翻墙越户偷了夏氏的三十金。原来“范以夏氏之措金赎女,对人感泣”,被他听到,便起了歹心。都说无巧不成书,但蒲松龄小说里的巧合不会强行“嫁接”,要么前有伏笔暗藏,要么后文回“扣”前情,于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带给读者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这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素养。村人报官,遭雷劈的灵异事件变成了刑事案件,追回的金钱还给了虞小思,“夏益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偿债主。”商人虞小思毫不市侩,支持妻子完成对纫针家的承诺,尽管纫针已死。蒲松龄不下定义,也无需过多解释,几个字就勾勒出这对夫妻的可贵之处。
纫针的戏份自然也不会就此“杀青”,且看蒲松龄怎么续写他的女主人公。“葬女三日,夜大雷电以风,坟复破,女亦顿苏。”又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惊雷再次打开坟墓,复活了纫针。这个桥段读者已经不意外,出人意料的是纫针重生后的选择。“不归家,往叩夏氏之门。盖认其墓,疑其复生也。”纫针再次展现出过人的心智,醒来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选择,她没有回归那个保护不了她的原生家庭,果断投奔恩人夏氏。面对夏氏的惊问,纫针很沉着:“夫人果然复生啦!我是纫针啊!”先脱口而出的是心里最重要的人,纫针这一句话,无论是求生欲强,还是情商高,都源于她的笃定。冯镇峦赞:“先此一句妙。”但明伦评:“九字中欣慰伤感之情,一时全到。”夏氏也有自身的操守,面对纫针的追随,她推却——“我出钱救你不是为了买丫鬟。”纫针继续争取,愿以夏氏为母,“夏未诺,女曰:‘儿能操作,亦不坐食’。”纫针认定了夏氏是她的贵人,决不轻言放弃。天亮,范氏赶来,愿遵从女儿的意愿,但夏氏还是坚持把纫针送回了王家。这三位女性,善良而豁达,通透且明理。蒲松龄的笔墨充满了对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敬意。
按说已经没有被逼婚之忧了,但纫针仍无意留在自家,整天哭念夏氏,父亲只好把她再次送来,“夏见之,惊问,始知其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这样我见犹怜又乖巧的姑娘谁能拒绝?况且虞小思和夏氏尚无子嗣,最终他们留下了纫针。“女纺绩缝纫,勤劳臻至”,纫针任劳任怨,努力展现自身价值,只求在这个靠得住的家庭里安身。夏氏生病,她“昼夜给役,见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时有啼痕。向人曰:‘母有万分一,我誓不复生!’”纫针心思缜密,此言当不虚,夏氏若真有个三长两短,她在这个家中的情形难免尴尬,虞小思也不过中年光景。姑娘先表明心迹,争取舆论先机,如果真到那般田地,恐怕她也说到做到。在纫针的悉心照料下,夏氏康复,至此她打心底里把纫针当做女儿了。第二年,一直不育的夏氏竟中年得子,人们都说是她行善之报,这也是《聊斋》中常见的劝善情节。
又过了两年,纫针17岁了,义父虞小思与其生父王心斋商量,纫针的婚事恐怕不能再等下去了。王翁倒很大方,把择婿事宜全权交由虞小思。这一来,“惠美无双”的纫针成了香饽饽,“问名者趾错于门,夫妻为之简对”。问名:即议婚,古时婚礼“六礼”之一。简对:选择应对。当年的债主黄氏竟然也来了,虞小思厌恶他为富不仁,极力拒绝,选了县里的名门冯家。这期间,王心斋正外出经商,糊涂亲爹再次“助燃”女儿的噩梦。不肯善罢甘休的黄氏转而“主攻”王翁,假扮商贾投其所好,两人关系逐渐密切。(黄)“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这次想让纫针做儿媳,这事任谁听到都会不齿,但“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与订盟”。这一节外生枝的细节蒲松龄构思得很巧妙,一个是龌龊可憎的财主,一个是是非不分的亲爹,增加了小说的戏剧冲突和读者的阅读感受,也为后文故事情节的“峰回路转”做足铺垫。一日之差,两桩婚约,到了纫针这里就一句话:“债主,吾仇也!以我事仇,但有一死!”黄、冯两家对簿公堂,各执一词,县官打算遵从纫针的意愿,却又被黄氏贿赂,于是案子拖了下去,一个多月都迟迟未决。纫针命运的转变由之前的孤苦无依,变成了僵持悬空,分毫之间,一脚天堂一脚地狱。
熟读《聊斋》的人想必都知道,蒲松龄笔下不会出现“无用”的角色,时机到了自会出场。“一日,孝廉入都,道过东昌,使人问王心斋。”这位孝廉除了傅阿卯还能是谁?好巧不巧,他问到的人正是虞小思,更好的消息是阿卯18岁“乡荐”,“犹以前约未婚”,傅家一直惦记着与纫针的婚约。虞小思担心真伪,阿卯出示当年的婚书,“虞招王至,验之而真,乃共喜”。结果毫无悬念,阿卯的名帖递到县衙,争婚官司不判自消。不仅纫针的婚事得偿所愿,喜报也从福建传来,“傅又捷南宫矣”。捷南宫:指考中进士。阿卯“入都观政而返”,观政,即“观政进士”,明代新科进士在正式授官前须先去部院见习政事。纫针再次作出选择,她不愿迁居福建,阿卯尊重新婚妻子的意愿,“遂独往迁父柩,载母俱归”。即便拥有了美满姻缘,纫针依旧准确把握命运,给自己安全感,也能够照顾自己关心的人;即便是现代社会的女子,远嫁他乡都可能要承受诸多不确定,何况在交通和资讯闭塞的古代。几年后,虞小思去世,幼子才七八岁,“女抚之过于其弟”。
曾经孤苦无依的弱女子最终成为人生赢家,蒲松龄在“异史氏曰”里点赞了正义神勇的雷霆霹雳,“瘅恶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钱塘破阵舞’也”。雷霆,成为小说中的神奇意象,“雷之妙用,被作者发挥到极致,这一超越现实的大胆构思,与民间传说中雷霆的刚正形象密切相关。”(赵伯陶《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版)不仅如此,蒲松龄还自问难道纫针是被谪人间的龙女?这是他关注社会和弱势群体的慈悲与幽默,也是他笔端的正气和愿景。读罢纫针的故事,不禁想起《聊斋》里的另一篇故事《妾击贼》,身藏武功的小妾却甘愿被正妻欺负,只说:“是吾分也,他何敢言。”思想观念不同,人生境界亦不同,人与人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对造化、命运以及自身的认知。纫针这个人物形象,有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意识,加之得益于其母范氏、恩人夏氏以及并未正面出场的阿卯母亲。这些身份各异的女性共同发力,选择善良,坚持做对的事,以纫针作为代表,成功走出一条逆袭之路。这是蒲松龄对社会底层普通女性的关注,是其仁义思想的体现,作家赋予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以互助与感恩的人性美,这也是小说特别动人之处。
Thunderous roars are all for one person
——Analysis of “Renzhen” in “Liaozhai Zhiyi”
Abstract: The story of “Renzhen” in “Liaozhai Zhiyi” is not very well-known,but the novel is highly readable,with a complex plot,twisted fates of characters,and seamless use of flashbacks and interludes. It skillfully uses the “thunderstorm” meteorological phenomenon to organically link the story,with a clever circular structure that echoes the beginning and end. The novel not only allows readers to appreciate the author's mastery of storytelling and writing,but also offers a glimpse into the human beauty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gratitude among lower-class women,as well as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on women's situation in a harsh world. Additionally,the novel successfully creates vivid and touching portrayal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women with beliefs and actions,reflecting the author's concern for the real world and his value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Key words: Redemption;Female Solidarity;Beauty of Humanity;Thunder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