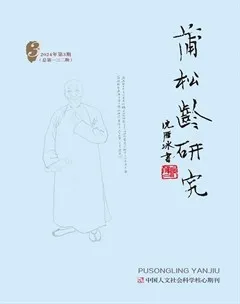文言小说中话语的双声关系
摘要:在巴赫金的思想中,语言学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对话是他对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而双声语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所提出的独特见解。而中国小说艰苦的孕育、产生、发展,完全仰仗文言小说的力量;没有文言小说的出世、成长,明清时期蔚为大观、雄踞文坛的白话小说就不可能出现,也就没有中国文学史上足以同诗、文、戏曲媲美争辉的小说的繁荣。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是一个多文体综合的作品,各类体裁在其中相互交融、对话。本文试从巴赫金的视角分析《聊斋志异》中典故运用和“异史氏曰”所体现的话语双声关系。
关键词:双声语;《聊斋志异》;作者和叙述者;典故;异史氏曰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
语言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既有广义的语言,即日常生活语言、阶级语言、社团语言等,又包含狭义的语言,即一些较小的词句,不同意义单位的文本话语等。而巴赫金所说的语言是广义的人文学科的话语,“语言的生命在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对话贯穿于文化” [1]163。因而,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我们都可以找到巴赫金语言对话性的某些特性。就文学作品来说,它是多种语体组合的一种现象,其词语是基本的构成部分,而作品中的说话人便成为语言的主体。这一语言主体和词语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风格的形成,或者表现某种立场,因为“所有的词语,无不散发着职业、体裁、流派、党派、特定作品、特定人物、某一代人、某种年龄、某日某时等等的气味。每个词都散发着它那紧张的社会生活所处的语境的气味;所有的词语和形式,全充满了各种意向” [2]74。
总体来说,文学作品的语言大抵上分为两类,即对话语和独白语。它们都是语言的独特形式。就独白的形式而论,它是一种重要的言语形式,有多种存在形式,比如集会演讲、国会咨询、总结发言、讲座、日记、自白等。就表达效果来说,“对话的对应体是独白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它同极权政治和不自由有关” [3]239。又或者说,独白总是追求完成,使生活停滞,甚至变得单一。因而,独白话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虽然我们这里谈到了独白强大的作用,但是,强调独白并不意味着完全摈弃对话。“无论是记录个人隐秘的心理活动的日记,还是有感而发的自言自语,同样都包含着对别人的行为(包括话语行为)或想象中别人的行为做出的反应。” [4]121作为文学中两种重要的言语形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与人物关系的建构问题,这种关系是话语中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具有对话关系的话语在巴赫金那里被称为“双声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各类语言纷繁复杂,且占据主要优势的就是双声语,“尤其是形成内心对话关系的折射出来的他人,即暗辩体、带辩论色彩的自白体和隐秘的对话体” [5]271。它主要包孕了对他人话语的仿效、讽拟和折射,简而言之,就是作品中的话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和音调。
文学作品中的双声性话语都具有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小说话语世界的重要体现。从一方面来说,一些国内外小说作品的名字就体现了双声性,比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同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存在着这种直接的对话性,除了名字上的双声性,文学作品中的用典“总是有古今两种甚至更多的声音和意向进行交锋” [4]127。在一些典故中,“源”作者和“现”作者相互呼应,形成双重声音的交错,或者说,某些典故的运用使得“源”内容也具有新的涵义。除了典故之外,古典小说中的词句总是会出现一些转义、引申、反用、双关等形式,这些方式“使得话语具有了双声甚至多重的情感和含义联想” [4]128,也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和情感表述。
一、巧用典故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具有士林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重品格,其主题丰富,多以劝人向善为主,此外,其中的语言运用有着深刻的涵义,特别在一些词句的运用显现了双声性,也就是说某些词句它们既有“源”作者的声音,又充斥着“新”作者的某种情感诉求。小说《聊斋志异》篇幅巨大,其中话语的双声性首先便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聊斋志异》从开篇到最终,我们总能感受到其中与古典故事的相关性,同时,这些典故的运用在不同的篇目中都有其特定的情态意义,一些极其普通的词汇在历史故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流传至今。并且,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典故是清晰直接,即正用,而有些则是比较隐晦或者是故意而为之,也就是反用。
(一)典故正用
小说《偷桃》中艺人与儿子为堂上的官员表演偷桃,在节目最后,儿子因上天偷桃惨遭横祸,艺人声称要把儿子带回家安葬,并说到:“为桃故,杀吾子矣!如怜小人而助之葬,当结草以图报耳。” [6]35蒲松龄在这里运用了“结草报恩”这一典故,即魏颗结草,该典故原出于《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一个妾,没有生孩子,武子生病的时候嘱咐自己儿子魏颗,一定要让她改嫁,在病危时,他嘱咐儿子让她殉葬。武子死后,魏颗将她改嫁。因为他认为,父亲病重时神志不清,他应当按照他清醒时的命令去办。辅氏之战时,魏颗看到一位老人结草绊倒杜回,他取得了胜利。晚上,魏颗梦到老人,他说他是被嫁之人的父亲,是来报恩的。后来的人,便以“结草”代指报恩。原本一个普通的词汇“结草”因而获得了新的含义,并历代流传。在《偷桃》中,艺人以该词作为表演的结束语,既是应语境所致,也表达了自己作为手艺人的不易,希望众人可以给些赏赐。总体而言,前面希望众人帮助自己安葬儿子,必当结草报恩,接过赏钱后,他又叫儿子出来感谢大家。让观众时而处于惊险中,时而感到惊喜,风趣而又幽默,令人回味无穷。
在小说《林四娘》中,女主人公林四娘总是在夜里与陈宝钥见面,饮酒奏曲,久而久之,陈宝钥的家人也被她悲凉的歌声所吸引,在陈宝钥的一再询问下才知她是衡王府宫女。她总是讲述往事,并与陈宝钥评论诗词,三年后,她告别陈宝钥,投生去了。离别之际林四娘送给陈宝钥一首诗,其中前两句是:“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 [6]290后两句中的“乔木”充分体现了话语的双声性,该词的原意是高大的树木,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这句话意思是,所谓的故国,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有数代功勋之臣。因此,后代便以乔木作为故国,这句诗道出了杜四娘内心的思念之情。在该小说所营造的语境下杜四娘思念故国是确切的,而从时代来看,蒲松龄所述林四娘一文,“仅是一次文人幻想中的艳遇,红袖添香夜读书,惺惺相惜中得到一种情感的满足,属于孤寂中一种自我慰藉” [7]462。
(二)典故反用
同典故正用相比,小说《聊斋志异》中典故反用的例子比比皆是。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蒲松龄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就更加清晰而独特。
在《叶生》中,淮阳叶生科举屡次落第,巧合之下结识了县令丁乘鹤,丁公很赏识他,数次鼓励叶生参加科举考试,无奈,他仍然受挫,郁郁而终。死后,他的鬼魂跟随知己回乡,教授丁公的儿子,使他最终顺利考中举人、进士。之后,叶生参加考试,考中了举人,丁公子派仆人送叶生回家,妻子见到他时,惊吓不已,因为叶生早已故去。在文末:“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 [6]91“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是蒲松龄反用典故,原出于沈约的《别范安成》诗句“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这句话说的是在梦中都不知道你在哪里,那要如何慰藉我的相思之情呢?唐李善注引的《韩非子》也对这一典故有解释,六国时,张敏与高惠是好友,当思念对方时,张敏就在梦里去找高敏,但在途中迷路了,如此者三,遂回。后人便以此形容对朋友的思念。而在《叶生》中,作者反用其意,知心的朋友,即使相隔千里,在梦里也能知道他在哪里。作家高度赞扬了丁公与叶生之间的真挚友情,但这里面却也透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感伤,正所谓“而况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 [6]91。高山流水般的友情是双方共同维系的结果,可以说他们是互相成就,但文人呕心沥血,抱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意志,却也未必尽如人意。因此,在结尾蒲松龄反用典故,颂扬了丁公与叶生之间的情谊,确也反衬出了文人志士的荆棘路途,或许,唯有这浓厚的知己情谊方能慰藉求取功名之人的悲凉命运。
小说《绛妃》中作者在毕刺史家坐馆,在梦中遇到绛妃,与她饮酒,绛妃说自己是花神,被狂风摧残,今日背城一战,让他帮忙写一篇檄文,写完后,绛妃很满意。待他醒来之后,便将梦中所写檄文补足,文中句句都在声讨风的恶行,将自己对风的愤怒和憎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篇檄文中正是反用典故,即“不奉太后之诏,欲速花开;未绝做客之缨,竟吹灯灭” [8]768。这里说的是风不执行武则天太后的诏令irncoDwg8Ifa46QodYTaaNUU4aGYrQYmDCeF1WAijzU=,催促着百花早早开放;没有扯断楚庄王群臣的帽缨,把烛火一一吹灭。后一句话出自《韩诗外传》卷七,有一次,楚庄王大宴群臣,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喝到黄昏时,众人都醉了,突然,殿内的灯火灭了,有人拉住了其王后的衣服,王后扯下那人的帽带,想要让楚庄王点亮蜡烛,将无礼之人找出来。楚庄王并未知此,他反而让所有人都把帽带去掉,让大家尽兴饮酒。后来,楚庄王因此宽容获益。在伐郑的一次战役中,有一位战将率先开路,最后战争取得胜利,论功行赏时,楚庄王才知他是当年的无礼之人。在檄文中反用典故,其一是为了让文章更加精彩丰富,其二,风虽未扯断楚庄王客人的帽带,将烛火吹灭,但这一说法却反衬了风的恶行。原典故中楚庄王的宽容忍让与小说中风的飞扬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看似是在讨伐风的种种罪行,但实则是借风讽刺世人。
除了在以上的论述中所列举的典故,小说《聊斋志异》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典故,比如《续黄粱》中“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6]550-551;《马介甫》中,“若赘外黄之家,不免奴役,拜仆仆将何求” [8]748运用了张耳入赘富人家的典故。从某种层面来说,这些典故充满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过去的那些涵义同现今这种用法形成了对话关系,这便形成了典故所具有的双声性。在《聊斋志异》中,除了典故运用所呈现的双声关系外,在“异史氏曰”中也有独特的双声关系呈现。
二、“异史氏曰”的双声话语分析
小说是各种艺术语言的组合,是个性化声音的多声部合唱。那么,小说中话语的对话关系同作品的言语建构、作家个性、文学流派的创作特点、社会性以及风格都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话语的建构实际上能反映出作者所见的大大小小的世界的复杂性,他把这些复杂性用自己的声音记录下来,而他的声音又不能不与其他声音(包括艺术世界内部的各种人物和现实生活中可能的前人、同时代人甚至后人)处于相互作用的对话关系之中” [4]128。也就是说,在审美活动中,作者声音是处于边缘上的,他的语言是针对他人而发的,换言之,“语言具有双重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这一点同一般的语言是一致的),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而发” [5]245。这种具有双重指向的语言风格有仿格体(模仿风格体)、讽拟体(讽刺性模拟体)、故事体等。
具体而言,故事体是利用他人语言,它代表特定社会阶层的声音,带来了一系列的观点和评价,而这些正是作者所需要的东西。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故事体而言,“作品结构中没有作者的语言,由叙事人代替作者。叙事人的讲述,可能采用文学的形式,可能采用文学语言的形式(如别尔金、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记事型的叙事人),或者采用口头语言的形式” [5]252。仿格体是仿效他人风格,保留他人风格自身的艺术任务。讽拟体是借助他人语言说话,“作者要赋予他人语言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隐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在里面同原来的主人相抵牾,发生了冲突,并且迫使他人语言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 [5]256。需要注意的是,讽拟体强调出自己的语气侧重,有怀疑、愤恨、讥讽、嘲笑和挖苦等等。暗辩体作为一种双声语,“是一种向敌对的他人语言察言观色的语言;它无论在实际的生活实际里,也无论在文学语言里,都极为普遍,对于体式风格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5]260。它的分类很多,有“旁敲侧击”的话语,“话里带刺”的语言,卖弄言辞的语言,极力解释的语言等等。
(一)“异史氏曰”的分类
在朱其铠主编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中,将近二百篇故事有“异史氏曰”,“从《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到《资治通鉴》的‘光(司马光)曰’,史传文体中,这种在历史叙述的同时为一己留下论说的空地的叙述传统经久未衰” [10]75。在《聊斋志异》中我们总能读到“异史氏曰”,或长或短,并达到总结全文的目的。然而,《聊斋志异》虽说其最终目的是教给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但以“异史氏曰”结尾的篇目却各有不同,按照内容大体上有三类形式。
第一,以简短的几句话作总结,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异史氏曰”中最普遍的一种类别。或歌颂人物品德的篇目,比如《于江》《商三官》《田七郎》《邢子仪》《于去恶》《小谢》等;或表达是因果报应的,比如《花姑子》《厍将军》《赌符》等;也有的写爱情、家庭和友情的,比如《夜叉国》《青梅》《江城》《娇娜》等;还有的是道德说教,劝诫世人,比如《促织》《云翠仙》《司文郎》《画壁》;也有讽刺现实,谈论为官之道,比如《潞令》《绛妃》《陆判》《阎罗》《李伯言》《潍水狐》等。
第二,在“异史氏曰”之后又加入故事。比如《霍生》中加入了一个王某与同窗妻子的故事;《狐惩淫》中加入了莲实菱藕的故事;《申氏》中加入了淄川某乙的故事;《佟客》中加入了捕快妻子的故事等。
第三,在“异史氏曰”引入其他著作中的语句或者采用其他的文体形式。比如《崔猛》中引入了《世说新语》中的“快牛必能破车”,《诗谳》引入了《易经》中的语句,诸如此类的篇目还有很多。还有在个别篇目以判词代替了“异史氏曰”这种形式,比如《黄九郎》。
(二)“异史氏曰”双声关系及表现
在以“异史氏曰”结尾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基本上都是以“故事+异史氏曰”的形式结束,并且,其中对故事的叙述都是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待故事结束之后,便以“异史氏曰”作为结尾。但在这里划分为两类声音关系,也就是说不仅有作者声音与叙述者的立场融合,也会有作者声音贯穿于叙述者的声音之中。
1.叙2HHvx44Cgzr5Bf2GCckEVA==述者的声音与作者声音融合
我们发现,《聊斋志异》中,大部分的篇目都是以叙述者之口道出了故事的道理,即行善积德,因果报应。大部分的故事结尾就有一小段的话语,这是“他者”对人的劝告,也是作者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我们一般只能感受到叙述者的声音。实际上,作者的声音早就同叙述者的声音融合,叙述者想让我们看到或听到的就是作者要给我们呈现的。因此,在《聊斋志异》中叙述者与作者声音融合的情况很多。
比如《蛇人》中:
蛇,蠢然一物耳,乃恋恋有故人之意,且其从谏也如转圜。独怪俨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数世蒙恩之主,辄思下井复投石焉;又不然,则药石相投,悍然不顾,且怒而仇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6]47
这篇小说展现了蛇与人、蛇与蛇之间的深厚情谊,在“异史氏曰”中,叙述者先论述了蛇知道留恋故人的行为,然后转入到对人的叙述,两相比较,人竟然还比不上蛇。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看到作者声音的出现,又或者说作者声音融合于叙述者的声音中,叙述者所言即为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
再如在《王六郎》:
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余乡有林下者,家綦贫。有童稚交,任肥秩,计投之必相周顾。竭力办装,奔涉千里,殊失所望。泻囊货骑,始得归。其族弟甚谐,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伞盖不张,马化为驴,靴始收声。”念此可为一笑。 [7]30
小说中讲述的是水鬼和捕鱼人之间的美好情谊,二人互敬互爱。在“异史氏曰”中,开头的“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一句点明了题旨,即人与人之间美好情谊的可贵之处在于苟富贵不相忘。接着,叙述者又举出了类似的例子,以深化主题。可以说,在这整个的叙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叙述者的话语,而作者所要传达的道理也是通过这个叙述者传达出来的。
在《聊斋志异》中,带有“异史氏曰”的篇目中,我们发现,叙述者的话语多与作者的声音融合,或者说,作者并不直接出现在小说之中,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诸如此类的篇目还有很多,比如《种梨》《娇娜》《僧孽》《鬼哭》《李伯言》《潍水狐》等等。
2.作者声音贯穿于叙述者的声音中
虽然大部分的小说中,作者与叙述者融合,然而,在某些篇目中,我们仍旧可以感受到作者的部分在场,他贯穿于叙述者声音中。比如《长清僧》:
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异之乎其再生,而异之其入纷华靡丽之乡,而能绝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6]44
这篇文章的前面部分讲的是长清僧死后,魂魄与一位乡绅的儿子结合,拒绝酒肉姬妾和家里的富贵,因为他记得自己是和尚,他坚定心性,并要回到原来的寺庙中。在结尾的“异史氏曰”中,叙述者认为,长清僧之所以能拒绝人间的富贵,是因为他内心坚定,品行高尚。而在“若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中,这里说的是现实中的一些人,只要看到了美人财富,便被迷了心智,只要能得到这些,死都不害怕,更何况一个老僧人呢!叙述者在这里看似是影射现实中那些心智不坚定的人,借助“有求死而不得者矣”的反讽意味,实际上表达了叙述者背后的作者的想法,即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在实现理想的途中,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这里,作者的声音偶然进入了叙述者的表述中,以此来凸显文章的主题。
再如《夜叉国》:
夜叉夫人,亦所罕闻,然细思之而不罕也: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 [6]348
这篇小说原讲述的是一位男子巧合之下,进入夜叉国,并与母夜叉结婚的故事。在“异史氏曰”中,叙述者赞叹夜叉夫人的神勇,之后笔锋一转,将话头代入了生活中的“母夜叉”,这反转的话头即是作者的声音。
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带有“异史氏曰”的篇目中,包括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异史氏曰”中,虽然某些内容带有议论性的总结,但一般情况下,小说中“异史氏曰”作为一个全新的形象,他是叙述者,是作者声音的传声筒,或者说是作者声音同叙述者的声音完全融合。
3.引入的他人话语
在第三类带有“异史氏曰”的小说中,情况有些不同。在这些结尾的论述中,叙述者或引入了他人的话语,或仿效他人文体,使我们总能从中听到另一层声音。我们这里所说的“引入”和“仿效”,在某种程度上与巴赫金所说的仿格体和讽拟体是一致的。
具体而言,作者会仿照先前已有的言语风格,以服务于自己的新创作。需要注意的是,模仿不是简单的摹写,也不是照本宣科式地拿来应用,真正的模仿在于“作者不让自己的态度全部沉浸在这种他人言语的意向中,而是形成一种借花献佛的视点,这是作者的意图、目的和意向与这种言语固有的意向只部分地融合在一起。” [4]130这种模仿包括仿效典故、俗语、警句等,“作者一般以此来追求特定的修辞目的,如激发读者联想到某种文风来增强叙述的表现力,模仿大家熟悉的名人话语及其风格来引发读者的某种情感反应,或者为了渲染特定的修辞色调” [4]130。我们关注到,在多个篇目的结尾处,作者都非常注重对他人话语的引入,并以此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比如,在《马介甫》中,“惧内,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间,乃有杨郎!宁非变异?余尝作妙音经之续言谨附录以博一噱” [8]718。在词句之后,便是妙音经续篇。
开始,叙述者认为,怕老婆这件事并不可怕,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后两句:“然不意天壤之间,乃有杨郎!宁非变异?”这不仅表达了叙述者的感叹,也是叙述者在与他之外的他人进行对话。再看叙述者所引述的妙音经续篇,全文一千多字,多由四六句的骈文构成。前部分历数了悍妇与妒妇的种种恶行,悍妒之妇对家庭和夫妻和睦的破坏不容小觑,因此,唯有佛法才能拯救悍妒之妇。
叙述者称为妙音经续篇,这里所说的妙音经是佛经中的《妙音菩萨品》,取自《妙法莲华经》,一共七卷二十八品,其中第二十四品便是《妙音菩萨品》,讲的是妙音菩萨曾用十万种伎乐供养云雷音王佛,因此得到神力,并能处处现身,为众生讲述法华经。显然,这篇序言是戏仿之作,它与之前的故事形成对话,作者正是在这篇“不是妙音经而胜似妙音经”的文章中道出了自己的声音,凡事有因果,妙音菩萨的大功德才得来如今的大神通和大智慧,相比之下,杨万石夫妇的矛盾在于夫妻力量的失衡,丈夫太软弱,妻子太蛮横,不懂得收敛,所以,才会有他们的悲惨结局。因此,“天香夜爇,全澄汤镬之波;花雨晨飞,尽灭剑轮之火。极乐之境,彩翼双栖;长舌之端,青莲并蒂。拔苦恼于优婆之国,立道场于爱河之滨” [8]720。悍妇敬奉神灵,修身养性才是解决夫妻矛盾、维护家庭安宁的良方。
引入他人话语的另一种形式就是讽拟体,“作者要赋予他人语言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隐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在里面同原来的主人相互抵牾,发生了冲突、并且迫使他人语言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 [5]256。需要注意的是,讽拟体强调自己的语气侧重,有怀疑、愤恨、讥讽、嘲笑和挖苦等,同时,“作者的意向和立场与被模仿的对象完全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4]132。在《聊斋志异》中引入这种相对立话语的例子并不多,其具体呈现如下。
如《陈锡九》:
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使为尚德之达人也者,即终贫,犹将取之,乌论后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娇女,付诸颁白之叟,而扬扬曰:“某贵官,吾东床也。”呜呼!宛宛婴婴者如故,而金龟婿以谕葬归,其惨已甚矣;而况以少妇从军乎? [8]1157
小说《陈锡九》讲述的是善良孝顺的书生陈锡九千里寻父,迎回父亲尸骨,获太守相助,与妻子团圆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前几句中,叙述者道出了孝道是每个人必要遵守的,而之后,叙述者将自己论述的重点转入到嫁女这一问题上,“某贵官,吾东床也”是引入的他人话语,看似是表达嫁女之父母的喜悦得意,而通过“呜呼!宛宛婴婴者如故,而金龟婿以谕葬归,其惨已甚矣;而况以少妇从军乎”展现了少妇嫁给老夫之后的惨状,我们发现,前者是作者模仿他人话语,意在讽刺那些将婚姻当作人生投资的人。
结论
我们大多数的研究基本将对话分析用于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心理小说,甚至有学者认为,“巴赫金并不正确,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复调第一人而忽视了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 [11]170-171。俄罗斯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也不能忽视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的复调性,那么,推及我国呢?作为复调小说本质特征之双声性话语在我国文学作品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因为“在非复调小说中同样可以有双声语存在,它们的话语同样可以具有内在对话性,换言之,双声语不是复调小说的充分必要条件” [4]136。因此,在小说《聊斋志异》中我们发现其中的典故就是双声语最直接的体现。
《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话语类别虽然多样,但具有双声性话语的文本并不是太多,大多数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话语都是同叙述者话语融合,也就是说叙述者代替了作者,这种写法如同屠格涅夫的故事体小说,“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去模仿他人的带个人特色或社会阶层特色的讲述格调”。换言之,我们在小说中基本上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它直接代表了作者的思想。这类话语在小说《聊斋志异》中占有绝大部分,而巴赫金所说的双声话语主要凸显的是一个声音中可以融入其他人的声音。小说中借助他人话语展现作者声音的篇目也有不少,其中我们可以明显读到仿格体话语,借助“异史氏曰”这一形式,作者仿效他人话语,即谚语、骈文、易经、檄文或者一句戏言等,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者达到戏谑的效果。相比之下,讽拟体的话语在这部小说中并不多,但这部小说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对人对事的讽刺态度非常明确。有些讽拟体话语的小说中,作者意向与模仿对象之间的意向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强烈,比如《刘姓》。
参考文献:
[1]白春仁.边缘上的话语——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辨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3).
[2][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Куралех А.В.монолог диалог молитва[J].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2012,(4).
[4]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上册)[M].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7][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卷1)[M].赵伯陶,注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8][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中册)[M].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9][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下册)[M].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0]申朝晖.《聊斋志异》叙事思想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5.
[11]Исупов К.Г.М.М.Бахтин: pro et contra: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М.Бахт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мысли:Антология.Т1[C].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
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1.
The Double-voiced Relationship of Discourse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Taking Liaozhai Zhiyi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Bakhtin’s thought,linguistic issue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his attention. Dialogue is the core of his research on linguistics,and double-voiced word is his unique insights in his research on Dostoevsky. The arduous gestation,production,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ovels completely rely on the power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without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the vernacular novels that dominated the literary worl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ould not have appeared,and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the prosperity of novels that could compete with poetry,prose,and drama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epitome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Liaozhai Zhiyi is a multi-genre comprehensive work in which various genres blend and dialogue with each oth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ouble-voiced relationship of Discourse in allusions and“Yishishi Said” from Bakhtin's perspective in Liaozhai Zhiyi.
Key words: double-voiced words;Liaozhai Zhiyi;author and narrator;allusions;Yishishi S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