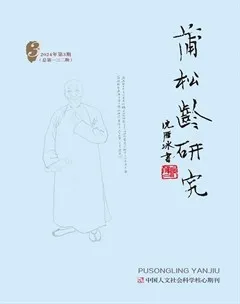蒲松龄迂道访友所去的官庄在哪里?
摘要:清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蒲松龄自青州考贡归来,曾迂道去一个叫官庄的村庄访问友人李之藻。本文考察认为,张崇琛先生提出的这个官庄在今青州市弥河镇,岳巍、李绪兰先生所说的这个官庄在今邹平市长山镇的观点都不能成立。清康熙年间地处益都县仁智乡的仇官庄(今淄博市经济开发区罗村管区东官村),才是蒲松龄自青州归来的路上,迂道访问友人李之藻所去的那个官庄。
关键词:弥河镇官庄村;长山镇官庄村;仁智乡仇官庄;罗村管区东官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
清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七十二岁的蒲松龄曾一仆一骑赴青州考选岁贡生,这也是蒲松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青州之行。
蒲松龄六日青州之行的具体情况,笔者在《蒲松龄年谱汇考》 [1]和《蒲松龄与黄叔琳——从蒲松龄的青州组诗说起》 [2]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考证。
蒲松龄的青州之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在回到淄川故里蒲家庄之前,蒲松龄归途行至青州、淄川交界之地时,曾迂道去访问侨居于此的武定州友人李之藻(字澹庵)。因为李之藻恰在此时回了武定州(即清雍正十二年武定州升为武定府后设置的武定府附郭惠民县县治)城南的老家,蒲松龄访友不遇,于是写了《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七古一首纪事。
蒲松龄迂道过访友人李之藻,他所去的这个村庄名叫官庄。这有《聊斋文集》中的《与李淡庵》一札为证:
别时相约,方期作五老之会,而竟渺然。屡向官庄问讯,则并无知行踪者,殊为怅惘……闻尊驾尚有东返之意,作大欢喜。引领翘切,不尽欲言。[3]1140-1141
李之藻虽然做过嘉善、青田两任知县,但此时还复自由之身已历十馀年之久。他在淄青之界筑屋而居的村庄并不是他的桑梓之地,可以肯定的是,若非村名官庄,蒲松龄自不会在书信中以“官庄”称之。
这个蒲松龄回到蒲家庄之后屡屡派人前往问讯的官庄,是其四海为家的友人李之藻近年来的栖止地之一。
同样是在康熙五十年,绵绵秋雨之后,李之藻曾从这个官庄出发去淄川蒲家庄造访蒲松龄,且赠以墨竹图,并以所携其小像图卷见示。蒲松龄因此写了《雨后李澹庵至》和《李澹庵小照》两首七言古诗,并亲笔将后一首诗和一篇名为《李澹庵图卷后跋》的跋文题写在了李之藻携来的图卷之上。
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之藻又曾“遥惠佳贶”,派人给蒲松龄送来了书信和赠送的礼物,所以才有了上面这篇蒲松龄《与李淡庵》的回信。
《与李淡庵》的札题见于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本《聊斋文集》,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本《聊斋文集》“李淡庵”作“李淡菴”。检国家图书馆藏耿士伟编订的《聊斋文集》钞本,此札题作《与李澹庵》,可知李淡庵、李淡菴和李澹庵为同一个人,它们都是李之藻别字的不同写法。
蒲松龄在《与李淡庵》一札中说“闻尊驾尚有东返之意,作大欢喜。引领翘切,不尽欲言”,可知蒲松龄接到书信时,李之藻正居停于他在武定州城南的老家,且有不久之后回返至淄川左近的打算。张崇琛先生考察认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东返’。所谓‘东’,是与惠民之西相对而言的。” [4]22因为武定州州治在西北方向,故回返淄青交界之地可以说是“东返”,张崇琛先生此说甚是。
一、问题的提出
康熙五十年十月,蒲松龄自青州归里途中访友所去的官庄究竟在哪里呢?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是张崇琛先生的看法。2017年,张崇琛先生在《蒲松龄与李澹庵》一文中说:
经奚林介绍,李澹庵也就知道了蒲松龄。后李澹庵在青州附近的官庄构堂暂住,遂于康熙五十年(1711)雨季的一天,就近到满井庄访问了蒲松龄……这年的初冬,七十二岁的蒲松龄在去青州考贡回来的路上,还曾迂道去官庄拜访过李澹庵,不巧因李澹庵临时回武定而未能相遇。[5]7-8
张崇琛先生此文确认了蒲松龄寻访友人李之藻所去的地方是官庄,但未指出这个官庄的具体位置。在此后发表的《蒲松龄老友李澹庵的别业究竟在何处》一文中,张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李之藻的别业在今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的看法。他说:
官庄又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青州。具体说,便是今青州市东南方15公里处的弥河镇官庄村。[4]21
其次是岳巍、李绪兰两位先生的看法。岳、李二位不同意张崇琛先生此官庄在今青州市的地理定位,他们先是在《蒲松龄研究》2020年第3期发表了《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因为蒲松龄《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诗说李之藻“年来停云淄青界”,岳、李二位据此认为:
“淄青”可以理解为淄川县,但蒲松龄在诗中写作“淄青界”,似乎说明李澹庵别业的位置在一个与淄川县交界的地方。从蒲松龄诗中提到的李澹庵别业离孝妇河西北流向河段不远的情况来看,这个交界地区应是淄川县与长山县的交界处。因为孝妇河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改道,于济南府下辖的长山县绳村流向东北方向,经过济南府下辖的新城县和青州府下辖的博兴县汇入小清河。因此,孝妇河西北流向段大约从淄川县浮山驿至长山县绳村。在目前查考不到李澹庵别业的具体位置所在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蒲松龄诗中关于孝妇河的流向进行推测,李澹庵的别业位于当时淄川县浮山驿至长山县绳村孝妇河西北流向段的范围之内,而且很可能位于长山县境内。[6]51
此后,为回应张崇琛先生提出的官庄在今青州市弥河镇一说,岳巍、李绪兰又发表《李澹庵别业位置再考兼及蒲松龄的民族思想》一文。两位作者对张先生所说李之藻侨居的官庄是今青州市弥河镇官庄村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蒲松龄在致李澹庵信中所提到的‘官庄’是当时长山县的官庄,即今天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7]6
我们认为,蒲松龄访友所去的官庄既不是今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也不是今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它就在今淄博市境内,具体位置为原属益都县仁智乡西南约的仇官庄,也即今隶淄博市经济开发区罗村管区的东官村。下面缕数我们的看法,兼向张崇琛、岳巍、李绪兰先生请教。
二、蒲松龄没有去过今益都县弥河镇的官庄村
张崇琛先生认为,今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是蒲松龄寻访友人李之藻所去的官庄。他说,这个官庄“具体说,便是今青州市东南方15公里处的弥河镇官庄村。清初,该村附近曾有古刹数区,至今村西北5公里处尚存广福寺一座。” [4]21
依照张先生提供的地理方位,我们在百度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弥河镇官庄村和坐落于该村西北方向的广福寺的具体位置。广福寺位于青州市南郊的劈山东南一公里处。按百度地图提供的标尺测量,广福寺与官庄村的距离比张先生所说的五公里要远一些,为七点五公里。
查检光绪《益都县图志》,与今广福寺、官庄村一带相对应的方位是清代益都县乐善乡南约或东南约一带的位置。但细检光绪《益都县图志》卷二乐善乡南约、东南约、西约、龙山后峪诸图,却找不到官庄这个村名。检同书卷三《道里表》所列乐善乡诸村村名,我们计数的结果是乐善乡共有村庄192个,但其中也没有出现官庄的村名。
我们还发现,在光绪《益都县图志》卷二乐善乡东南约的图上,其最南端的村庄名赤涧,由赤涧村往南便进入了临朐县境。检光绪《临朐县志》,果然其卷一《疆域》有如下记载:“北至赤涧铺交益都界,二十里。北至(直)十里至石沟河,又直十里至赤涧,一地二界:南临朐,北益都。” ① 也就是说,乐善乡东南约的赤涧村是益都县与临朐县的分界之地,这里与临朐县治的距离为二十华里。复检百度地图得知,今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在赤涧村正南一点七公里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张崇琛先生所说的这个官庄村在清光绪年间已经超出了益都县的管辖范围,它不是益都县下辖的村落,而是临朐县属下的一个村庄。
在清康熙年间,益都县与临朐县的疆界是不是与光绪年间相同呢?检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印的《益都县志》,其卷一《疆域》有云:“南界临朐县二十五里。”又卷四《市集》云:“赤涧集,在城南二十五里乐善乡。” ② 由此可以知道,作为益都县城南的集市而存在的赤涧村,其位置在益都县治以南二十五里,它在康熙年间同样是益都县和临朐县的分界之处。换言之,地处赤涧村正南三华里以外的今青州市弥河镇官庄村,在清康熙年间同样隶属于临朐县,它并不是益都县下辖的村庄。
细检光绪《益都县图志》,我们在当时的益都县乐善乡东南约还发现了一个叫刘官庄的村庄。这个村庄不仅出现在光绪《益都县图志》卷二《乐善乡》图中,也出现在同书卷三《道里表》中。《道里表·乐善》一栏记载曰:“刘官庄,东南约。” ③
以刘官庄东偏南二华里的杨家村为坐标,我们在百度地图上找到了今刘官庄的具体位置。刘官庄今名小官庄村,它正是当今青州市弥河镇政府的驻地。
那么,清康熙年间地处临朐县,今已划归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以及当年地处益都县乐善乡东南约的刘官庄,也就是今日成为青州市弥河镇政府驻地的小官庄村,有没有可能是当年蒲松龄迂道访友所去的官庄呢?
我们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可以举出五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是蒲松龄往返青州所走的道路并不经过康熙年间的益都县乐善乡,即今青州市弥河镇一带。说蒲松龄去益都县乐善乡一带探望李之藻,与蒲松龄自己所说的他在归途中“迂道”访友的事实并不相符。
蒲松龄自淄川去青州府的附郭益都县,有三条路可以到达。
第一条路是从西南方向抵达益都。咸丰《青州府志》卷三《道里表·益都县道里近表(附郭)》记载:“西南:直五里至五里堡。迂六十五里至朱崖庄。邪(斜)二十里至长秋庄交博山县界,凡九十里。” ① 其实不必经过今属青州市庙子镇的长秋村,自朱崖庄往西,经益都县附郭乡西约的黑旺、蓼坞和淄川县正东乡的寨庄(今寨里),即可到达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蒲松龄是反向而行,自蒲家庄出发,经寨庄往东进入益都县西南境,再经蓼坞、黑旺、朱崖庄、五里堡进益都西门,可以抵达青州府附郭益都县。
第二条路是从正西方向抵达益都。咸丰《青州府志》卷三《道里表·益都县道里近表(附郭)》又载:“西:直五里至五里堡。又直三十五里至郭庄。迂二十五里渡淄水至边庄。又直五里至大庙庄。邪(斜)二十里至仇家官庄交济南府淄川县界,凡九十里。” ② 边庄在光绪《益都县图志》中名“边庄河”,今名边河村,旧属益都县仁智乡东南约,今隶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大庙村在边河以西五里。仇家官庄在大庙村西偏南方向二十里。自仇家官庄往南,经淄川县东北乡的罗家庄、道口,正东乡的寨庄,同样可抵达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那么反过来,蒲松龄从蒲家庄出发,经寨庄、道口、罗家庄,在仇官庄附近进入益都县西境,再经仇官庄、大庙庄、边庄河,渡过淄河至郭庄,经五里堡进益都西门,同样可以抵达益都县。
在清代,以上两条路都是山僻小道,道路崎岖,行走十分不便。这有《聊斋文集》里的两篇修桥募序为证。一篇是《连三沟募修桥序》,其略云:
莪山一道,为淄、青通衢,然轮辕所不经也,蹄足过之。盖道通南北,而巨沟横阻之,出入地者三,乃得途里余中;沟径居其七,非按膝登则卓地降下,而中沟尤剧,去地数十武,山斗绝如石斜立,如壁半欹,即晴燥时亦滑滑有蹄痕,小雨过,则如鲇鱼上竹竿,不可复行矣。[3]1050
另一篇为《石沟河募建桥序》:
石沟河在淄、青之界,盖南北之通衢也。临崖下注,苍茫数寻,入谷仰窥,青空一线,亦途之至危者矣。而乃万蹄万趾,晨夕奔腾,九地九天,倏忽变易,喘牛汗马,覆轮踬毂,慈悲者或怜之矣。虽然,此犹未为其甚者也。迨乎秋落桑麻,野无蓑笠,深沟易蔽,遂有伏莽之虞,狭道难奔,辄罹丧资之祸。挺矛骤起,跪献鹤缠,囊笈全搜,乞怜蚁命;则是为三冬暴客设出没之窟巢,留数矢长渠作南北之陷阱。此乘人于险,为行道之所忧,而御寇无能,即维摩之所病也。然而不宁惟是:横石碍路,已忧跋履之艰,急雨倾盆,更惧怀襄之水;浑潦肆注,澎湃无休,块磊互冲,擂炮不已;期愆花烛,或阻宋子之车,目断舟梁,因下阮生之涕;即或河消浊浪,已灭夕阳,鸱叫空山,并无归路。[3]1061-1062
因为小路崎岖难行,凶险叵测,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自淄赴青一般都不履此险道,他们正常走的是驿道。所谓驿道,也即淄川通往青州府附郭益都县的大道。
由淄川去往益都县的大道是如何走的?岳巍、李绪兰认为应该走淄川城北三十里的浮山驿,其说有误。康熙《淄川县志》卷二《建置志·仓庾铺舍附》云:“总铺,十字街西。由总铺东北十里,曰十里铺。二十里,曰瓦村铺。三十里,曰旦村铺。四十里,曰昌城铺,今改为丰水铺。” ① 也就是说,去益都县走的是淄川往东北方向的驿道,具体说便是淄川→十里铺→瓦村铺→旦村铺→昌城铺后改丰水铺这条官道。
昌城铺所在的昌城村是笔者的故里,丰水铺所在的丰水今名沣水,在昌城村以南三华里处。自丰水铺继续北行六华里,经淄川东北境的昌城村、益都西北境的刘家村,可以到达地处益都县最西北角的张庄。从张庄转而东行,就进入了明清时期自济南经益都通往胶东的东西大道。沿这条东西大道行经红庙、李家庄、商家庄、上湖田、辛安店、金岭镇、五里阁、于家店、矮槐树、辛店、鞑子店(今安乐店),东渡淄河至柳店,再经牛山、淄河店、普通店、锺家井、车辕门(即古东阳城门)、青州北门,即可到达青州府治和其附郭益都县治所在的青州城。
清康熙十六年(1677),蒲松龄的乡前辈唐梦赉等有江浙之游。据唐梦赉《志壑堂集》卷七《吴越同游日记上》,其自淄川南下江浙,出游路线山东段为淄川→三里沟→昌城→金岭镇→牛山→淄河→青州→临朐→穆陵关→沂水→郯城→红花埠。其中淄川至青州段行经的就是淄川至青州的官道。
须要说明的是,蒲松龄居处的蒲家庄在淄川城东七华里处,他自然不会绕道至淄川城北的三里沟或十里铺踏上驿道。蒲松龄所走的路应是从蒲家庄北行,经北杨家庄、北沈马庄、双辛庄、小赵庄、华坞村,至瓦村铺走上驿道的一条直路。一路计数下来,自淄川蒲家庄至青州城,全程为一百四十六华里。
蒲松龄康熙五十年所写的《青州道中杂咏》七绝五首,印证了他所走的正是途经牛山、淄河的山东东西大道。
据咸丰《青州府志》卷三《道里表·益都县道里近表(附郭)》,自青州西北行,走的是“邪(斜)五里至满洲驻防城,又邪(斜)十五里至普通店,直十五里至临淄县淄河店,临淄境内迂行三十二里至五里阁,又入县境,直五里至金陵(岭)驿,又直二十八里,至红庙西济南府新城县张店东交新城县界,凡百里”的山东东西大道。① 蒲松龄往返青州所走的就是这条东西大道和淄川县的驿道。
从蒲松龄《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的诗题看,寻访友人李之藻一事发生在从青州归里的途中,而不是在踏上归途之前。如果蒲松龄去益都县乐善乡的刘官庄或隶属临朐县的官庄村,那却是与“自青州归”反方向而行的,不是出青州城北门去往蒲松龄回家的方向,而是出青州府南门去往离家更远的地方。《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诗中还说,蒲松龄访友的结果是“迂道过门失初望”。“迂道”是什么意思?同样是说向着目标而行但要绕一段路。而去这个官庄或刘官庄,则是与蒲松龄的归途南辕而北辙,这已经不是迂道、绕路,而是去往与归途完全相反的方向了。
换句话来说,假设蒲松龄去临朐县的官庄或益都县的刘官庄,此事必发生在他“自青州归”之前。他只能是先去官庄或刘官庄访友,然后回到青州城里,再从青州城启程踏上回家的路。正因为去官庄或刘官庄访友的途程并不是蒲松龄“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的同一途程,所以在归途去官庄或刘官庄寻访李之藻一事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
其次,去官庄或刘官庄访友,与蒲松龄回到家乡之后“屡向官庄问讯”的事实不符。
蒲松龄在《与李淡庵》的书札中说,因为李之藻回到武定州老家之后久未归来,他在自青州回家之后至康熙五十二年接到李之藻的书信之前,曾“屡向官庄问讯”,即派人前往官庄打听李之藻的讯息。但益都县乐善乡东南约的刘官庄距县城近二十华里,临朐县的官庄距益都县城在二十八华里以上。从淄川蒲家庄到这一地域,走大道的途程总计为一百七十华里上下,来回三百四十馀华里,即使是青壮年,步行往来起码也要四天的时间。而且,蒲松龄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岁杪自同邑西铺村撤帐回到蒲家庄之后,一家人的生活也仅可言温饱,他的家庭绝对算不上是富裕人家,并没有购买奴仆照顾起居的经济条件。他的长子蒲箬所说的“冬十月,一仆一骑,别无伴侣,奔驰青州道中”的“一仆”,实际上就是蒲松龄康熙四十九年所作《惰奴》诗中那个懒惰的奴仆,其身份实为家里雇佣的长工。这惟一的一个长工,要在蒲家里里外外干各种杂活,试问来回数百里的距离,而且是越县跨府而往,蒲松龄又如何能做到派出人手屡屡向地处临朐县的官庄问讯呢?
其三,今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与蒲松龄所去的官庄地处“淄青界”的地理位置不符。
蒲松龄《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一诗,称李之藻“年来停云淄青界”。这里所说的“淄青界”,指的是青州府附郭益都县与淄川县交界的某处地方(说见下)。而无论是地处益都县乐善乡的刘官庄,还是位于临朐县治以北的官庄村,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们都处在青州府腹地的位置。这里与淄川县界的距离接近一百华里,与“淄青界”一说并无任何关涉。
其四,这个官庄村和刘官庄以东的弥河,与“心逐河水西北流”的河道流向不符。
蒲松龄迂道寻访,却没有见到友人李之藻。失望之馀,他在《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诗中写下了“心逐河水西北流”的诗句。可以想见,心情失望的蒲松龄站在官庄的村头,眼前所见的是一条呈西北流向的河流。
张崇琛先生说:
至于“心逐河水西北流”之“河”,也显然不是孝妇河或淄河,而是弥河。因为官庄就在弥河西岸不远处,而其河水的流向也正是自东南向西北。[4]22
此河确实不是孝妇河或淄河,张崇琛先生说的没有错。但蒲松龄所见到的河流,同样不是位于官庄村和刘官庄以东,出入于临朐县北境、益都县南境的弥河。
弥河古称巨洋水,发源于临朐县沂山西麓,向北流经临朐县城以东,自益都县南部入境,由东北部出境进入寿光县。就其流向而言,弥河在临朐县北境、益都县南境为正北流向,之后在益都县变为东北流向,且两县有多条支流汇入其中。
检百度地图,今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东距弥河约三华里,地处其西北方向的小官庄村东距弥河约八华里。因为弥河的流向是东北方向,它越往北流离自益都县城南下的大道就越远。无论蒲松龄去往官庄或小官庄,他都无法亲眼看到弥河干流的流水,他也没有充裕的时间亲临弥河岸边。蒲松龄怎么会把他明知是东北流的弥河说成是“心逐河水西北流”呢?张崇琛先生说弥河“河水的流向也正是自东南向西北”,这样的说法与弥河东北流向的事实恰好相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五,临朐县的官庄村里有没有寺院,同样是检验这个官庄是不是蒲松龄所去的官庄的必要条件之一。
张崇琛先生说,这个官庄“附近曾有古刹数区”。但翻检光绪《临朐县志》,我们只在卷四《古迹》发现有“修真宫,在县北十里养老院。宋建,元时修”一条记载 ① ,而且这个修真宫的三进院落,“南为青龙白虎殿,中为三清殿,北为玉皇殿”,明显为道观而不是寺院。[8]
至于张先生所说的官庄西北方向的广福寺,则在康熙年间就已经颓圮败落了。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十三《营建志上·坛庙附寺观》:“广福寺,在城南十里劈山东麓。创始无考。寺有武定二年造像,则亦北魏建矣。隋曰胜福,唐以后始易今名。金皇统八年重修,明永乐以后迭次修葺。国朝康熙间渐次颓圮,后遂废,神像皆露处。光绪十三年,知县张承燮为葺数椽以庇之,又易其名曰兴福云。” ②
此条之下,附录蒲松龄的安丘友人张贞《游广福寺记》,记载了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重九之日,张贞与其妹婿、益都人高舜木,子张在辛来游广福寺的所见所闻。张贞写道:至广福寺,但见“旧迹久湮,所存像、殿,皆舜木先人纳言公所成。今去世已远,郡中乡先生无复好事如公者,故亦渐就倾圮矣。七十老僧,折足铛中糙米饭有时不给。山行CgBj7jh5EAxbPC4vWgfl5g==疲饥,无房可憩。于西院松下得一石案,颇可人意,据而坐焉”。① 广福寺在康熙二十八年就已经破败到如此地步,自此至光绪初的近二百年间一直无人修葺,这与蒲松龄所见到的“佛阁高敞僧舍幽”的情形怎么说都不会是同一处景致。
综上而言,蒲松龄自淄川去青州,往返都不会经过地处临朐县治以北的官庄和益都县乐善乡东南约的刘官庄。这个官庄和刘官庄,都不在蒲松龄自青州归里的途程和“迂道”行经的地域之内。这一带区域,与蒲松龄家乡的距离在一百七十华里左右,因路途遥远,蒲松龄不会屡屡派人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听李之藻的下落。这里地处青州府的腹地,距青州府附郭益都县与淄川的交界之处接近一百华里,与蒲松龄的诗所叙及的李之藻“年来停云淄青界”的地理位置不符。与这个官庄乃至刘官庄相近的弥河,先是正北流向,然后是东北流向,与蒲松龄访友所去的官庄附近“河水西北流”的情形更是大相径庭。这个官庄村里没有寺院,附近的广福寺在蒲松龄去青州考贡之前二十馀年就已经颓败不堪,与蒲松龄说的“佛阁高敞僧舍幽”不是同一景致。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清康熙年间,地处临朐县境内的官庄和益都县乐善乡东南约的刘官庄,都不是蒲松龄自青州回返淄川的途中“迂道”而去的那个官庄。
三、蒲松龄没去今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
岳巍、李绪兰不同意张崇琛先生提出的蒲松龄所去的官庄是今青州市弥河镇官庄的说法,认为蒲松龄去的官庄在淄川西北的长山县,即今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
我们以为,蒲松龄去今邹平市长山镇官庄村寻访李之藻的观点同样是难以成立的。岳、李二位之所以持这样一种看法,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相关历史地理状况的解读出现了偏差。
首先,蒲松龄去青州考贡,往来所经的河流不包括孝妇河,他也不可能经过孝妇河畔的淄川县浮山驿,即今张店区傅山镇浮山驿村。
蒲松龄《青州杂咏》七绝五首其一有句云:“满河断续水潺潺,日夜西流去不还。”赵蔚芝先生《聊斋诗集笺注》:“满河:应为‘淄河’之误。” [9]598盛伟先生编校《蒲松龄全集》本《聊斋诗集》,则径改“满河”为“淄河”。[3]1913我们以为赵蔚芝、盛伟两位先生的校说皆误,因为淄河是一条全程呈东北流向的河流,特别是蒲松龄往来青州途经的淄河鞑子店(今安乐店)一段,河床更是呈东向略偏北的走势,与蒲松龄诗中“日夜西流”的描述并不相合。
岳巍、李绪兰认为这里的“满河”指的是贯穿淄川南北境的孝妇河,原因是他们认为蒲松龄去青州的驿道要经过距孝妇河东岸只有一华里的浮山驿村。其《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云:
第一首诗(按,即《青州杂咏》七绝五首其一)中提到的河,指的应是孝妇河。当时从淄川县到益都县主要经过两条河流,即今淄博的第一大河淄河和第二大河孝妇河……孝妇河流向先自南向北,在流经浮山驿的时候又折向西流,然后折向西北,因此“日夜西流去不还”是从蒲家庄到达浮山驿时所见的情景。因此根据河水西流可以断定蒲松龄当时经过了孝妇河西流的河段,而这一河段正好位于浮山驿附近,由此可以确定蒲松龄走的是当时的驿路,这条驿路从蒲松龄家乡所在的仙人乡北上经傅山镇的浮山驿,向东入临淄即是青州府地界。[6]48
我们在上文的考察中已经说得十分明白,淄川去青州的驿道走的是淄川→十里铺→瓦村铺→旦村铺→昌城铺后改丰水铺一线。而孝妇河自淄川城西关北流,在淄川县西北界出境。蒲松龄家在淄川城东七里的蒲家庄,所去的青州又在淄川的东北方向,他为什么要越过去往青州的驿道,绕远路来到这个浮山驿村去看西流的孝妇河呢?
岳、李二位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淄川县以北三十里的浮山驿村地处淄川去往青州的驿道上。这一说法非但找不到任何文献资料的支持,反倒是存在文献的反证。明嘉靖《淄川县志》卷二《古迹》有云:“浮山驿:在县治北三十里,今废。闻故云:昔淄川为路时曾置邮,以地僻,张太师奏革之。” ① 在元代,淄川先隶济南路,后为淄州路、淄莱路、般阳路路治。也就是说,浮山驿在元代曾为驿站,但明代就已经废止了。浮山驿村在笔者故里、地处淄川县去青州驿道上的昌城村以西约十五六华里处,假设蒲松龄从这里北上去益都县,其从淄川东北驿道上的瓦村铺斜往西北到浮山驿约十二华里;从浮山驿到马尚镇以东的原大寨村进入周村镇到张店以东的东西大道,路程约八华里;从大寨村沿山东东西大道东行至当时隶属益都县仁智乡西北约、今属张店区湖田街道的张庄(即自淄川县驿道进入东西大道的地方)路程约十五华里。也就是说,走浮山驿这处不是驿道的偏路、小路去青州,蒲松龄起码要绕十多华里的远路。因为清康熙间的驿道并不经过浮山驿村,所以蒲松龄是不会走这样的冤枉路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认知偏差,除了岳、李二位不了解自淄川去青州驿道的具体位置,还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淄川境内西北流的河流只有一条孝妇河。其实,就淄川县的地形地貌而言,其东南部以及益都县的西南境多丘陵山地,淄川县东部地区的地形呈东南高而西北低的态势,孝妇河以东的河流无一例外都是呈东南至西北流向的。即以蒲松龄走驿道去青州,一路东北行到达东西大道上的张庄所经的地方为例,其所经过的暖水河、漫泗河、猪龙河、涝淄河,无一不是东南至西北流向的河流。明确了淄川去青州的驿道并不经过久废的浮山驿的历史事实,则岳、李二位所作的“根据河水西流可以断定蒲松龄当时经过了孝妇河西流的河段”的结论,无疑是存在胶柱鼓瑟之嫌了。
蒲松龄自青州归来,岳、李二位认为走的是经过边庄河、浮山驿到长山县官庄的路。他们在《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文中写道:
“日出叩禅关,出门惟僧雏”,根据《憩僧寺》一诗,蒲松龄返程途中曾到寺庙休息。从时间和沿途的情况来看,他休息的寺庙很可能是当时边庄的普济寺。边庄即现在的金山镇边河庄,村里原有一座古寺,名曰“普济寺”,大殿北侧有一棵明代古槐。20世纪八十年代,普济寺大殿被拆除,现古槐犹存。
蒲松龄返回途中还绕道去了李之藻(字澹庵)的别业……李澹庵的别业具体在什么地方呢?诗中所写河流的流向(按指蒲松龄《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诗中“心逐河水西北流”句所写)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参考。通过河水流向西北方向可以推知,诗中之河应为孝妇河无疑。孝妇河在浮山驿向西流过一小段,然后流向西北方向,因此可以推断李澹庵的别业离孝妇河流向西北方向的河段不远,李澹庵的老家似乎位于其别业的西北方向。[6]50
说蒲松龄归途经过边河村,除了这里有一座普济寺之外,找不到其他依据。检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十三《营建志上·坛庙附寺观》,并不见有这座普济寺的记载,反倒是在同卷中记载了蒲松龄自青州沿东西大道西行,一路上经过的多处寺庙,如:
白衣庵,一在白龙庙西,一在白衣庵街路北,皆明衡藩香火院也。一在城西北锺家井。
普济庵,在金岭镇东五里,俗名五里阁。明万历年建。
圆融寺,在城西北七十里金岭。旧志云明正统初建。①
在上引的《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文中,岳、李两位举出了蒲松龄归途所写的《憩僧寺》中的诗句。《憩僧寺》诗所写的,正是蒲松龄昧爽时分自青州起行,到日出时刻来到一处寺庙休息,顺便打尖吃早饭的情景。从青州城出发,经青州北门、车辕门(古东阳城门)再到锺家井,途程有七八华里,费时在一小时开外,正当冬季的日出时分。所以,我们认为蒲松龄在这里歇歇脚吃早饭是合理的。
但如果按岳、李两位所说的路线,蒲松龄自青州沿东西大道西行到达淄河西岸的鞑子店(今安乐店)后,即从这里沿淄河南下,经南仇到达边河村,那么边河村到青州城的距离已经达九十华里上下。在天不亮的时候自青州启程,走了九十馀里之后早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时分,蒲松龄竟然还能在边河村的普济寺“日出叩禅关”,试问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在《李澹庵别业位置再考兼及蒲松龄的民族思想》文中,岳、李二位又进一步确认了李澹庵的别业就在今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然而,说蒲松龄归途经边河村、浮山驿去往今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这同样是不可能的。
岳、李二位说蒲松龄自青州归来经过边河村,那么他行走路线的前一段就变成了先从山东东西大道上的鞑子店(今安乐店)沿淄河西岸南下,经南仇村到达边河村。既然说蒲松龄《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诗中“心逐河水西北流”句所写的河流“应为孝妇河无疑”,那么蒲松龄后一段的行走路线就成了自边河村到达浮山驿村,在这里看到了“心逐河水西北流”的孝妇河之后,又从浮山驿村向西北行去,直到今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
假设蒲松龄真的要在自青州归里的途中去往今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他也绝不会走这样一条中途向南绕行再回转向西北的远路。因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告诉我们,自东西大道上的鞑子店(今安乐店)继续西行到达张店之后,可以跨过猪龙河,沿着张店以西的石村、房镇、固悬、姜家铺(今大姜村)一路西北行到达长山县城。而这条自张店西北行的路,正是明末清初之前山东东西大道中段的位置,也是自张店一带去往长山县最为便捷的路线。[10]438-439
岳、李二位以为浮山驿村是淄川通往长山县驿道上的一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熙《淄川县志》卷二《建置志·仓庾铺舍附》云:“由总铺西北五里,曰夏庄铺,今改为黄家铺。十五里,曰变衣铺。三十五里,曰高唐铺。” ① 高唐铺,今为周村区南郊镇高塘村。淄川→黄家铺→变衣铺→高唐铺,是当时淄川县境内去往长山县的驿道,自高唐铺往正北方向行走十六华里为固悬村,由此进入东西大道,再经姜家铺即可到达长山县城。
如果按岳、李二位所说,蒲松龄走鞑子店(今安乐店)、南仇、边庄、浮山驿去往长山县城一带,他无疑又要多走几十里的冤枉路。
其次,说蒲松龄去今邹平市长山镇官庄寻访李之藻,与蒲松龄自青州归里的途程、时间都不相符。
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问题:一个没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百姓,一天步行下来,究竟能走多少里路?
之所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岳、李二位认为蒲松龄一仆一骑从青州归来,一天可以走二百华里以上的路程。他们说:“蒲松龄……在尚有残月的时候早行,可惜还是没有见上李澹庵,等蒲松龄回家时已经很晚了,而且天降大雪。一天行了二百多里路,尽管已经疲惫不堪,蒲松龄还是很庆幸平安归家。” [6]52
这个问题,牵涉到按照岳、李二位给出的归家路线,蒲松龄和随行的长工能不能在两天(而不是岳、李两位所说的一天)之内自青州回到淄川蒲家庄的历史事实,所以是不能忽略的。
我们知道,以当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例,部队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行军训练。他们的行军训练包括急行军,也包括常行军,就是正常速度的部队行军。急行军的时速可以达到一小时十公里,连续行军可达十二小时。常行军每小时的行军速度可以达到四至五公里,每日行军十小时,行程为四十至五十公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有幸听一位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的老兵讲起他们在广西追击败逃的国民党军队时,一昼夜行军二百四十里的传奇经历:前面的战士背上系一条毛巾,后面的战士手抓着毛巾跟着向前走。饿了,从路旁的供应点抓起馒头边吃边走;渴了,从路旁的水缸里舀半茶缸水边喝边走;困了,闭着眼跌跌撞撞地边睡边走。总之,就是走路不能耽搁,他们一直在一刻不停地赶路。一昼夜走二百四十里,可以说已经接近人类体能的极限,哪怕是四野的百战老兵,一路上掉队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么话说回来,如果是骑着马赶路的蒲松龄,特别是跟随他一路步行的长工能“一天行了二百多里路”,而且是昧爽起行,当天晚上到家,就算是按早五点到晚九点的时长,中间去除一小时吃饭、喂马的时间,一路行走十五小时,那也达到了一小时六点五公里以上的速度,已经超过了部队常行军的时速。蒲松龄这一仆一骑,岂不是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普通百姓赶路的奇迹?
实事求是地说,对没有受过行军训练的百姓而言,哪怕是壮小伙子,每小时行程八华里,每日步行十小时走八十华里的路已属十分不易。记得笔者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学校放假,几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集合到一起,从一个有钟表的同学家里看了时间出来,一路上疾走如飞,半个小时走了约五华里的小路赶到张店火车站的挂钟前,结果人人汗下如雨,个个疲惫不已。
蒲松龄赴青州考贡,路上一仆一骑,来回时长六日。从他去青州的途程接近一百五十华里来看,应该是路上用时两天,在途中休息一夜。如果硬是要一天走完近一百五十里路,那就要不眠不休地走上近十九个小时,骑牲口的“七十老翁”蒲松龄身体自然是受不了的,跟随他一路步行赶路的蒲家长工更是没有这样的体能潜质可供长途挥霍。到达之后的时间里一天考试,一天看榜,蒲松龄一行二人从青州归来也应该是用时两天,中途休息一夜。
假设蒲松龄的归途如同岳、李二位推论的那样,从青州到长山县的官庄村寻访李之藻,然后从这个官庄走长山县到淄川县的驿道回到家中,那么问题来了。
前面说过,从青州出发,到达张店以东益都县仁智乡西北约的张庄,咸丰《青州府志》记载的途程是一百华里。清乾隆时人李漋《质庵文集》卷四《济南纪程》一文,则记载了自张庄至长山县城的道里途程:
(张庄)又西北八里为张店,隶新城。西北行十里为石村。又八里为房镇。又西北二里为二十里铺。又西北五里为故县(今固悬村)。又西北十五里入长山县。①
自益都县西北鄙的张庄至长山县城,走大道的途程为四十八华里。自长山县城至其东北四里的官庄村约四华里,合计五十二华里。也就是说,自青州到长山县官庄村的距离为一百五十馀华里,比到蒲松龄家乡蒲家庄的道路里程还要长。
检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蒲松龄自青州归里的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为公元1711年12月5日至6日。两天后的十月二十九日(12月8日)即大雪节气。时近冬至,昼短夜长,一个昼夜中,白昼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一小时。按十一小时算下来,除了赶路,还要两次打尖吃饭,喂饮牲口,走路的时间最多十个小时,尽力赶路也只能走八十华里。到长山县官庄村的路程有一百五十馀里,蒲松龄一仆一骑要走整整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
然后,他们还要从长山县回淄川老家。走长山县到淄川的驿道,自长山县城到固悬,再到高唐铺、变衣铺、黄家铺、县城、蒲家庄,这一路的途程为六十二华里。前后相加,总共二百一十四华里的路程,哪怕蒲松龄和随行的长工拼了命地赶路,他们在两天之内也回不了蒲家庄。
或云,他们会不会只留出一天的时间在青州参加考试,第四天就开始往回赶呢?我们以为绝不可能。试问蒲松龄辛辛苦苦跑这么远的路到青州所为何事?来都来了,难道他会连看榜的时间都不留给自己吗?
事实其实十分清楚,蒲松龄给自己留了两天的时间自青州回归故里。如果他打算途中迂道去长山县东北郊的官庄村,两天的时间是走不完这二百一十馀华里的途程的。那么反过来说,实际情况是蒲松龄就没打算去这个长山县城附近的官庄村,或者说,他要去的那个官庄根本就不用走这么远的路。
其三,正确理解与解释“淄青”与“淄青界”的涵义,是探讨蒲松龄所去的官庄的地理位置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蒲松龄《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一诗,称他去寻访的友人李之藻“年来停云淄青界,佛阁高敞僧舍幽”。应如何理解这里的“淄青界”一词?岳、李二位在《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中说:
“淄青”一词有多种解释,较早的解释指“唐方镇名,或称淄青平卢,或称平卢”。唐代白居易有《贺平淄青表》……宋代陶榖的《清异录·青喜》有云:“李正己被囚执,梦云:‘青雀噪,即报喜也。’是旦果有群雀啁啾,色皆青苍。至今李族居淄青者,呼雀为青喜。”以上文中“淄青”皆指藩镇。
在明清时期,“淄青”也被用来指淄川及附近地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耳中人》一篇中提到了谭晋玄是“邑诸生也”。李学良在《丁耀亢全集》中查到丁耀亢曾作《送谭晋玄还淄青,谭子以修炼客张太仆家》一诗,其中提到谭晋玄在张若麒家中修道之后返回淄青,而谭晋玄是淄川县的诸生,可见淄青与淄川相关……
“淄青”可以理解为淄川县,但蒲松龄在诗中写作“淄青界”,似乎说明李澹庵别业的位置在一个与淄川县交界的地方。从蒲松龄诗中提到的李澹庵别业离孝妇河西北流向河段不远的情况来看,这个交界地区应是淄川县与长山县的交界处。[6]50-51
其实,“淄青”和“淄青界”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就“淄青”而言,先是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率军南迁青州。侯希逸旋封平卢、淄青二镇节度使,简称淄青节度使,领青、淄、齐、沂、密、海六州,驻青州。所以,在唐代,无论是平卢、淄青二镇节度使,还是淄青节度使,指的都是以青州(治今青州市)为中心,包括淄州(治今淄川区)在内的藩镇势力。
在明清时期,“淄青”一词也不是“被用来指淄川及附近地方”的,而是指淄川、青州一带地区。如果与青州无关,又何必并称为“淄青”?清顺治八年(1651),淄川县学生员谭晋玄自胶州回淄川故里,丁耀亢写《送谭晋玄还淄青,谭子以修炼客张太仆家》诗用到“淄青”一词,一是因为“淄青”二字在唐代即被连用,属于有典可依,二是因为淄川东部和青州西部区域犬牙交错,相连相接。如果仅仅是指“淄川及附近地方”,如被岳、李二位引申所指为淄川及长山县一带,丁耀亢就不会用到“淄青”一词了。
所以,岳、李二位接下来引申的“‘淄青’可以理解为淄川县”的解释,其实是存在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用“淄青”指称淄川县,指的是与青州接壤的语境里出现的淄川县,而不是与青州没有关系,只在与其他州县接壤的语境里出现的淄川县。
那么,什么是“淄青界”呢?毫无疑问,“淄青界”指的就是淄川东部与青州西部接壤的地域。这里的“淄”指淄川县,“青”指青州府,具体说来是指青州府下属的与淄川接壤的益都县。“淄青界”语境中的“淄”“青”二字分别指称的是淄川县与青州府益都县,其涵义十分清楚,与“淄青”二字连用泛指淄川、青州一带地区没有直接关联。
从上引的岳、李二位对“淄青”与“淄青界”的解释来看,两位先生先是由“淄青”一词由来的解释引申出“在明清时期,‘淄青’也被用来指淄川及附近地方”的误读误解,然后又进一步解释说,“蒲松龄在诗中写作‘淄青界’,似乎说明李澹庵别业的位置在一个与淄川县交界的地方”。这样的释读,也就把对“淄青界”的解释偏离到了一个与“淄青界”中的“青”字毫无关联的错误的方向。
我们上面的考察已经说明,蒲松龄的青州考贡之行,既不会行经淄川城北三十里的浮山驿村,也不会看到西北流向的孝妇河;他在自青州返回淄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去长山县东北郊的官庄村的打算,所以才把归里的途程定为两天。事实其实已经十分清楚,蒲松龄迂道而往的官庄并不在远离“淄青界”的长山县境,它其实就在淄川县与青州府益都县交界处的某地。
四、蒲松龄迂道而往的官庄是益都县仁智乡的仇官庄
在《李澹庵别业位置再考兼及蒲松龄的民族思想》一文中,岳、李两位先生提出了蒲松龄访友所去的官庄应该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地理位置在“淄青界”;其周围河流有西北流向段;距离蒲松龄家乡蒲家庄百里左右。
我们认为,这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第三个则非但不是必要条件,而且是与必要条件存在矛盾和抵牾的逆淘汰条件。这种不能成立的条件,是理应被摒弃在必备的基本条件之外的。
岳、李两位先生把距离蒲松龄家乡蒲家庄百里左右列为确认官庄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依据来自蒲松龄的两句诗,即“君驰百里犹庭户”和“百里奔波第此程”。
“君驰百里犹庭户”,出自蒲松龄《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一诗。赵蔚芝先生《聊斋诗集笺注》云:“百里,指从新建之舍至家。” [8]603也就是说,这里的“百里”说的是李之藻从官庄别业到其武定州老家的距离。当然,蒲松龄说这段距离为“百里”,也只是举其约数而不是细数其详细里程。
如果像岳、李二位那样,把这个“百里”解释为李之藻居处的官庄到蒲家庄的距离,有两个问题是他们无法作出解释的。第一,淄川与益都县相邻,两县交界之地从益都县仁智乡西北约的张庄(今淄博市张店区湖田街道西张村)始,到益都县附郭西约的赵家庙村(今淄川区寨里镇赵家岭村)止,南北逶迤来去达六十馀华里,但其中任何一个村庄与蒲家庄的距离都不超过五十华里。也就是说,如果把距离蒲家庄百里左右的官庄作为入选的基本条件,那么所有的地处“淄青界”也就是淄川和益都县交界地域的官庄都将被摒弃在入选条件之外。如果真正地处“淄青界”的官庄不能入选,反倒是远离“淄青界”的长山县的官庄才是李之藻“年来停云淄青界”的地方,这个条件就成了荒谬的逆向淘汰的逻辑前提。第二,如果说这个官庄与蒲家庄的距离达到了百里之遥,以蒲松龄的家庭条件而言,他并没有条件在李之藻离开官庄之后“屡向官庄问讯”,也不会不止一次地派人到这里来打听李之藻的下落。这同样可以反证这个条件从根本上是难以说通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百里奔波第此程”,出自蒲松龄的《归途》一诗。《归途》诗写的是蒲松龄一仆一骑自青州昧爽而行的情景及归途的所见所闻,故这里的“百里奔波”云云,说的是蒲松龄自青州至淄川蒲家庄近一百五十里的途程,“百里”在这里同样是约数而不是实指。这个“百里”,与官庄距蒲家庄路程多少实在是了无关涉,因为《归途》诗所叙青州到蒲家庄的距离与官庄到蒲家庄的距离本来就不是同一回事。
摒除“距离蒲松龄家乡蒲家庄有百里左右”这个条件之后,其实还应该加入另外三个基本条件。这三个基本条件是:第三,蒲松龄去李之藻居处的官庄是“迂道”而往,即离开驿道而去官庄;第四,李之藻居处的官庄附近有庙宇,有驻锡的僧人,而且这座庙宇与李之藻新建的屋宇距离甚近,所以蒲松龄才写下了亲眼所见的“年来停云淄青界,佛阁高敞僧舍幽”的诗句以纪事;第五,李之藻不会无缘无故地到这个名为官庄的村庄筑屋而居,这里要么环境优美,要么具备吸引李之藻前来的人文因素。
依据以上五个基本条件,我们先是在“淄青界”上择取了两个大致符合条件的官庄,然后用排除法排除了其中一个,最后选定这个官庄为益都县仁智乡西南约的仇官庄。
在我们初选的两个官庄里,一个是位于益都县仁智乡的官庄。这个官庄在清代属益都县仁智乡中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属淄博市张店区湖田公社,笔者高中时代一位同班同学就是这个官庄的人。因为地处张店东部化工区,此官庄于2009年开始整体搬迁。之后建成的官庄社区坐落于洪沟社区东侧,隶属于张店区湖田街道办事处。在整体搬迁之前,这个官庄位于益都县西北隅一片丘陵山地之阴,山东东西大道益都县西北段以南,北距东西大道约三华里。
在本文撰写的过程中,我们曾先后三次前往官庄村原址与今官庄社区进行调查走访。在此期间,中共官庄社区支部书记王成华同志召集了十馀位七十岁以上的社区居民与我们进行座谈,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官庄村的基本情况。这个官庄村原址距益都县西陲的刘家庄直线距离约十二华里,可谓接近“淄青界”,此其入选的基本条件之一;去往这个官庄,须从东西大道上的辛安店下驿路西南行约三华里抵达。因为其西南方向为山地丘陵地带,离开这个官庄要西北行六华里到上湖田重新回到东西大道,可见确实是迂道而往,此其基本条件之二。
在走访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这个官庄存在的与上列基本条件不相符合的地方。一是此官庄西距西北流向的涝淄河十华里上下,虽然说算是周围河流有西北流向段,但因距离太远,又有低山丘陵阻隔,村民们只是知道但却很少有机会见到十数里外的涝淄河。若蒲松龄来到这里,站在官庄的位置向西望去,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片山岭,所以难以发出“心逐河水西北流”的感叹;二是参加座谈的官庄社区老年居民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更早的年代,官庄村仅有一座北方农村普遍存在的小关帝庙,以及一座村民亡故之后供家人送浆水的土地庙,村里从来没有高敞的大庙,也没有僧人在此挂搭,与“佛阁高敞僧舍幽”的情形不符;三是村里明清时期没出过什么名人,这个村之所以叫做官庄,不是因为村里有人做过官,而是因为全村有官、毕、王、胡、刘、赵六大姓,而官姓人数一直较多的缘故。官庄村过去缺水比较严重,就自然景色和人文因素而言,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以为,由于符合蒲松龄访友所去的官庄的基本条件较少,这个官庄可以排除在蒲松龄所去的官庄之外。
第二个官庄是同样位于益都县仁智乡的仇官庄。这个仇官庄,咸丰《青州府志》卷三《道里表·益都县道里近表(附郭)》称其为“仇家官庄”,旧属益都县仁智乡西南约,曾为淄川区罗村镇下辖村,今隶淄博市经济开发区罗村管区。
今淄川区罗村镇北偏东六华里处,东南至西北向排列着东官村和西官村两个村庄。两村之间的距离本来约一华里,由于近几十年来村民在村边建房的缘故,两个村庄不断靠近,现在已经几乎连接为一个村庄了。
旧日的东官庄和西官庄哪个村又名仇官庄,光绪《益都县图志》的记载前后并不一致。光绪《益都县图志》卷二《仁智乡》图,标注的是“东官庄、仇官庄”,以西官庄为仇官庄; ① 同书卷三《道里表》,于“仁智”一栏记载的则是“仇官庄,西南约;西官庄,西南约”,以东官庄为仇官庄。② 可见光绪《益都县图志》的编纂者也没有弄明白,东、西两个官庄中的哪一个是仇官庄。
我们同样去这个东、西官庄进行了三次调查走访,之后又进行了多次电话采访。经过向原官庄学校校长、今年八十岁的袁聿萍老人和七十岁的村民仇传灵进行咨询了解,确认了今天的东官庄就是昔日的仇官庄。之所以被称为仇家官庄、仇官庄,是因为在明崇祯年间,东官庄人仇维祯曾先后出任南京户部、兵部尚书,而且仇维祯的长子慰祖还得到青州衡王的垂青,尚衡王郡主而成为衡王府的仪宾,用百姓通俗的话说,就是被选中做了衡王的女婿。此事见载于东官村仇氏的《仇氏世谱》,我们曾翻阅一过,应属确凿。仇维祯一家在当地影响很大,仇氏一族所居住的东关庄也因此而得名仇官庄、仇家官庄。袁聿萍老人告诉我们,仇维祯家的宅院原来是一片大院和几幢外砖内坯的楼房。在今日东官村里,仇家大院的位置已经被新建的农村宅院所替代,袁聿萍老人还向我们指认了大院的旧址。
与今张店区湖田街道官庄社区的前身、地处益都县仁智乡中约的官庄相比,位于益都县仁智乡西南约的仇官庄,可以说是符合蒲松龄所去官庄的全部条件的唯一一个村庄。
由光绪《益都县图志》卷二《仁智乡》图可知,仇官庄以西二百米处即淄川、益都两县的边界。仇官庄距西面隶属淄川县丰泉乡的聂村直线只有三华里,可以说它正处在“淄青界”上,此其一;漫泗河自南部山区迤逦而来,经仇官庄村西、西官庄村南和村西流向西北,此其二;如果蒲松龄是到仇官庄探望李之藻,须从淄川驿道上的丰水铺下驿道,迂道南行经田家庄、岳店到达仇官庄,然后再南行,经鲁家庄、罗家庄、牟家庄、前河庄,至蒲松龄妻子刘氏娘家所在的道口庄(今淄川区罗村镇道口村)以南折而西行,经寨庄(今寨里)、北沈家庄、北杨家庄回到蒲家庄,此其三。
其四是关于左近的庙宇的。在调查走访中,现年七十六岁的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曾任淄川区作协副主席、原中共西官村支部书记的吴传永老人告诉我们,西官庄的南面和东南方向原有三座庙宇:一是位于西关村村南的侯恺寺;二是侯恺寺东一百米处,位于东、西官庄之间的尼姑庵(百姓俗称姑子庵。后来庵里的小尼姑因事被逐,村人又在庙内东厢建起了龙王殿,此庙也因此改称龙王庙);三是位于侯恺寺以南二里,南北路以西的南冠寺。
这三座庙宇,现在只有前为尼姑庵后为龙王庙的一座遗迹尚存,原因是自1951年起,这里被改造成了官庄小学。学生先是在高约十米的大殿里上课,后来拆除了南向的大殿和其右后方的东阁、位于东厢的龙王庙和院墙,用拆下来的砖瓦木料修建了北、西、南三排平房作为教室,大殿左后方的西阁则被保留下来用作校工的住处。这所学校规模较大,除了东、西官庄,附近的南韩、北韩、罗村、聂村、岳店等村的学生也在这里上学。1993年农村学校撤并,保留了庙宇西阁的官庄学校也被闲置并保存至今。
三座庙宇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尼姑庵正西一百米、西官庄正南方向的侯恺寺。1947年出生的吴传永老人回忆,他记事的年龄侯恺寺就已经拆除了,庙宇山门的建筑也已被拆,但下面的石基仍在,村人称之为“庙台”。侯恺寺山门为南向,东西长约十几米。石基的南面,中间是九层高大的石头台阶,两边有青石板铺成的坡道。山门面向西流的漫泗河,河上的石桥正冲着庙门。
翻检光绪《益都县图志》,我们在卷十三《营建志上·坛庙附寺观》找到了这座庙宇的相关记载:
侯恺寺,在城西一百里仇家官庄。明隆庆四年,新乐王重修。碑云“晋永安二年比丘法果建”。按,晋永安无二年。晋盖魏之讹也。①
为什么叫侯恺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李森检得,青州的古代寺院,还有白苟寺、孙泰寺、杨郎寺等,他因此认为,“中国古代寺院有官寺、私寺之分。这些寺院中的白苟寺、孙泰寺、杨郎寺和侯恺寺显然都是以人名命名的佛寺,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青州古代民间营造私寺的兴盛情况”。[11]29
永安分别是晋惠帝司马衷和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年号。因为晋惠帝的永安只有元年,没有二年,所以光绪《益都县图志》的编纂者确认侯恺寺碑中的“晋永安二年”为“魏永安二年”之误。这个魏,当时的人称大魏,今人称北魏。北魏永安二年为公元529年。
这个侯恺寺建造的具体年份,使我们想到了被称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20世纪全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青州龙兴寺窖藏造像的发现和出土。青州龙兴寺这批佛教造像以“曹衣出水”的青州风格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而其中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造像,就是北魏永安二年(529)的韩小华造弥勒像。这说明侯恺寺这座私人寺院就建造于北魏时期的兴佛运动之中。如果侯恺寺的北魏佛教造像得以保存下来,它们将会为中国佛教造像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传永老人说,故老相传明代青州的衡王曾修过侯恺寺。据上引光绪《益都县图志》的记载,修葺侯恺寺的不是衡王,而是作为衡王分支的郡王新乐王。明第一代衡王朱祐楎谥曰恭,后世称衡恭王,其第三子朱厚熑被封为新乐王。朱厚熑去世后,其子朱载玺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袭封新乐王,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在隆庆四年(1570)重修侯恺寺的就是第二代新乐王朱载玺。距青州百里之遥的侯恺寺却能受到明代新乐王朱载玺的重视并予重修,足见这座寺院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其五,前面曾言及,据咸丰《青州府志》卷三《道里表·益都县道里近表(附郭)》,仇官庄正处于出益都县城西门,经五里堡、郭庄、边庄、大庙庄至其村的山径小路上。据张崇琛先生考察,李之藻其人文武兼备,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他不仅协助其堂兄、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总督浙江军务、兼理粮饷的李之芳运筹帷幄,而且曾亲自上阵,仗剑前驱,率众与叛军耿精忠部拼杀搏命于浙江衢州的坑西战场。李之藻辞官之后,长期居停于诸城县放鹤村、卧象山,琅琊台侧歇歇庵等地。[5]他从诸城一带西到益都,然后走出益都西门、经仇官庄的小路来淄川,且因喜爱仇官庄的人文和地理环境而筑屋侨居于此,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总之,仇官庄地处淄川、益都两县交界之地;漫泗河经其村西和紧邻的西官庄村南、村西流向西北;蒲松龄自青州归来,到仇官庄须偏离驿道正路“迂道”而行;仇官庄村西北、漫泗河畔有建于北魏时期的侯恺寺,且在明隆庆年间由明新乐王朱载玺重新修葺;这里又地处出益都西门前往淄川的小路上,以李之藻的性情、身份而言,他都有经过此地而喜爱此地,因而卜居于此的可能。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清康熙年间地处益都县仁智乡的仇官庄(今淄博市经济开发区罗村管区东官村)符合蒲松龄自青州归里访友经过此地的全部条件,它就是蒲松龄自青州归来的路上,迂道访问友人李之藻所去的那个官庄。
参考文献:
[1]邹宗良.蒲松龄年谱汇考[D].济南:山东大学,2015.
[2]邹宗良.蒲松龄与黄叔琳——从蒲松龄的青州组诗说起[J].蒲松龄研究,2014,(3).
[3][清]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4]张崇琛.蒲松龄老友李澹庵的别业究竟在何处[J].蒲松龄研究,2021,(2).
[5]张崇琛.蒲松龄与李澹庵[J].蒲松龄研究,2017,(2).
[6]岳巍,李绪兰.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J].蒲松龄研究,2020,(3).
[7]岳巍,李绪兰.李澹庵别业位置再考兼及蒲松龄的民族思想[J].蒲松龄研究,2022,(4).
[8]李宝垒.青州现存宗教建筑考察[M]//齐鲁文化研究(总第12辑).济南:泰山出版社,2012.
[9][清]蒲松龄.聊斋诗集笺注[M].赵蔚芝,笺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10]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视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1]李森.龙兴寺历史与窖藏佛教造像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5.
Which Village is Pu Songling’s Detour Visiting Location for a Friend?
——A Discussion with Mr. Zhang Chongzhen/Mr.Yue Wei and Mr.Li Xulan
Abstract: In October,the year of 50th in Kangxi Region(1711),Pu Songling was on the way back to Zichuan County from Qingzhou after finished his Gongsheng examination,he made a detour to visit one of his friends named Li Zhizao,and the destination named Guanzhuang. This paper argued that this location is neither Mihe County Qingzhou City proposed by Mr Zhang Chongzhen,nor the Changshan County Zouping City proposed by Yuewei and Li Xulan. The exact and correct location is Chouguan Zhuang in the Yidu County and Renzhi Town in Qing dynasty Kangxi Region. The current name of this location is the Dongguan village Luocun Precint economy development district in Zibo city.
Key words: Mihe County Guanzhuang Village;Changshan County Guanzhuang village;Renzhi Town Chouguan Zhuang;Luoguan Precinct Dongguan Vill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