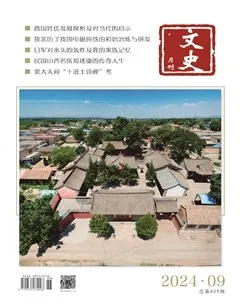康熙皇帝赐字御书的理学大家范鄗鼎
在洪洞县城中心广场上,塑立着12名洪洞历史名人,其中洪洞县曲亭镇师村就有两人,即师旷、范鄗鼎。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宫廷乐师,史称“乐圣”,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与他生活时代相差2200余年的范鄗鼎,则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大家,康熙皇帝御书赐匾“山林云鹤”。
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年初,笔者因参与师村段绪德《乐师师旷》剧本的修改、发行诸事宜,两次走进师旷和范鄗鼎的故里——师村,有了深入了解和探究师村范氏和理学大家范鄗鼎的欲望和机缘。
坚守大义与绝意仕途
范鄗鼎(1626—1705),字汉铭,又字彪西,学者称娄山先生。明末清初洪洞曲亭师村人。祖父范弘嗣,字耀昆,学者称正学先生,又称竹溪先生,明末晋南名儒。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山西按察使李维桢设局主修《山西通志》,范弘嗣受召,北上参与修撰(清雍正八年(1730年)《洪洞县志》卷之四《人物志·乡贤》)。崇祯元年(1628年),范弘嗣以贡生身份任山东德州(今山东省德州市)通判,任中革改漕弊,人称能吏。明末农民起义军兴起,社会动荡,遂辞官归里。崇祯九年(1636年),应保举赴京,但他看到明王朝大势已去,遂回归家居。范弘嗣受绛州(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辛全(字复元,号天斋,其理学思想在明末山西影响很大)理学思想影响,忧患于当时崇尚空谈的学术风气,提倡经世致用学说,认为儒者应注重修为,以个人的言行潜移默化扭转颓废的社会风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范弘嗣“闻之即焚袍笏于家庙,哭扑地,越时乃苏。后郁愤成疾,遂卒,年七十八。”(民国《洪洞县志》卷十二《人物志上·列传·范弘嗣》)范弘嗣著作有《三晋正学编》《仕国人文》《养正唾余》《南原野记》《师冈杂俎》《晋诗续雅》《毛诗补亡》《四子密藏》《聪圣志》《圣臣志》等二十余部,大多散佚。父亲范芸茂,字赞衮,号丹虹,县庠生,曾跟随祖父游学于理学家辛全之门。明亡后,杜门不出,读书著述,督课子弟。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病去世。范芸茂著作有《养正书屋集》《涧南集》《洪乘编》,不幸散佚。范鄗鼎出生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辽东建立了后金(清朝的前身),形成了与大明王朝政权并立的局面,祖、父为其立字汉铭,是否另有深意?
范鄗鼎出生于理学世家,祖父范弘嗣经世致用的理念和实践,对他影响很大。祖父坚守民族大义、笃志死节的“卫道者”行为,对他的震撼和影响根深蒂固,这也成为他后来不愿置身清代官场、一直不能与清廷积极合作的根本原因。
清顺治三年(1646年),范鄗鼎考中乡试副榜;顺治八年(1651年),考中举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会试明通;顺治十八年(1661年),会试中式,“辛丑榜未放,予抱病先归”。康熙三年(1664年),因病未赴殿试。(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二《四书反身录序》)康熙六年(1667年),参加殿试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待命。他以母老“告终养”,辞京归乡。古代的所谓“告终养”,是指为官者辞官归家,奉养父母或其他老人,以终其天年。在范鄗鼎之前,“告终养”者有例可循,如,三国时蜀国武阳(今四川彭山区)人李密,自幼由祖母刘氏抚养,曾拜师于蜀中名士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文采斐然,以文学见长。历任蜀汉益州从事、尚书郎等职。西晋灭蜀后,隐居乡里。晋武帝司马炎欲征李密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李密作为前朝遗老,不愿仕于新朝,便以九十六岁的祖母刘氏供养无主上书《陈情表》,武帝司马炎大为感动,答应了其暂缓出仕的要求。范鄗鼎刻苦攻读,二十余年寒窗,历经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激烈角逐,最终获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脱颖而出,在即将授官进入仕途的关键时期,却戛然而止决然退出,其行为非常人能所为,也非常人所能理解。范鄗鼎绝意于仕途,究竟何因?范鄗鼎父亲去世时,他年仅26岁,后来母亲一直寡居,他以奉养母亲提出“告终养”辞归请求,也是能够触动人的感情神经、让人能够接受的正当理由。但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关:祖父身为汉人政权的明朝官员,食君禄,忠王事,明清鼎革,身为满族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忠于明政权的祖父心理上难以接受,焚官服,废寝食,郁郁而终,深受震撼的范鄗鼎如若出仕为官,就是对祖父意愿的违逆,就是对祖父尽节的不孝;但范鄗鼎满腹诗书,如若归隐山林,又与文人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相悖。心里矛盾之际,进退尴尬之中,范鄗鼎选择了折中的做法,一方面寒窗苦读,积极参加科举得中进士,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使世人认可自己的学识文章;一方面辞官归隐,不违祖德,坚守了传统的忠孝道德。
潜心儒家与转向理学
范鄗鼎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酷爱儒家经典如《左传》《国语》,以及秦汉、唐宋八大家古文,不仅刻苦学习,还下苦功抄辑,“寝食俱废,十指几秃”,抄写成部,曰《古文汇编》与《续古文会编》。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博取功名期间,在家攻读上古文献及先秦诸子文章,文字也“务为奇奥”。范鄗鼎在刻苦攻读中,深得古文奥妙,不但裨益于科举应试,也铸牢了深厚的文字功底。
康熙六年(1667年)殿试考中进士以母老决辞归乡后,范鄗鼎隐居山林,授徒著述。其间,思想发生转变,逐渐对上古文献、诸子百家丧失兴趣,“厌其古怪,翻尽二酉,烂极五年,于我方寸一块,但有劳而无益”,“范无津涯,倏爱倏厌,倏取倏弃,夺吾有用之日月,而劳劳于朝华文秀之间也”,对自己过去专注于儒学的读书生活予以否定。“余三十岁时,读先聘君《三晋正学编》,知淡八股而嗜理学”。(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二《李礼山达天录序》)他认为理学乃人生正途:“嗟乎!言理学于今日,有不讥其愚且腐者乎?予谓:人不为理学,将为何如人?文不为理学,将为何如文!”(2005年《洪洞县志·卷二十三·人物》)最终,范鄗鼎思想转向了理学。
名噪当时的希贤书院
范鄗鼎绝意仕途后,隐居乡村,“一片野心,白云留住。门掩流水,户纳青山”,“足不入城市,身不谒官长”,执念于授徒著述。他把其书斋命名为“五经堂”,并订立了戒条。范鄗鼎最初创办有义学,后来求学者不断增多,义学已难以容纳,遂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用数年所积在师村村西构建书院。书院占地二亩余,门口匾曰“五经书院”,其门联曰:“读孔夫子之书或习诗或习书或习春秋或习周易礼记五经总属一贯必须身体力行方成个学,生师大夫之地也有耳也有目也有手足也有心肝肚肠七尺原兼三才岂但寻章摘句便说是聪。”山西(河东)三任巡盐御史先后为书院题写匾额:江南金坛(今江苏省常熟市金坛区)人、辛丑进士徐诰武,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题曰“学全知行”;直隶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人、己亥进士傅廷俊,康熙十七年(1678年)任,题曰“足表当世”;江西清江(今江西省樟树市)人、癸丑进士鲁寅,康熙十八年(1679年)任,题曰“理学正宗”。书院内设讲堂,南北坐向,当时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太原名士傅山为其题写“文献堂”匾额(内门),浙江上虞贡监、洪洞县令朱璘题写“善鸣远大”(外门);门联曰:“由东鲁以来暨恒讫霍学山至于山只见严严气象,自西河而后沿汾达津观水难为水且求混混本源。”(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希贤书院碑记》)书院内凡门都有匾有联,书香味浓;松柏梅竹梧桐石榴桃树银杏蔷薇等一应俱全,环境雅致。
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为了笼络山林隐逸和名儒硕彦,增开了博学鸿儒科(又称己未词科),朝廷下诏各地推举“博学鸿儒”,太常卿朱斐以博学鸿儒荐举了范鄗鼎,清廷下旨山西巡抚图克善督促范鄗3YpPmUDL1y9wJHIMAuU0PQ==鼎入京待试。起初,范鄗鼎以母老推辞。后来,巡抚衙门接连催逼十三次,范鄗鼎三上呈词,重申“既列终养,不宜出仕”,断不可“破终养之例,行欺罔之私”,以“鼎一人而玷国典”(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一《辞荐举呈词》),坚不应赴。巡抚据实上奏,朝廷只得作罢。“旨是役也,始终抱病不起者四人,鼎之外,爰有陕西李君颙,江南魏君禧,浙江应君撝(huī、wéi)谦,三人皆布衣庶人,不传质为臣礼也,独鼎叨两榜释谒候铨而病不起,既免雷霆之威,又荷雨露之仁,俾桑终养得全。”(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希贤书院碑记》)明末清初吴门(今江苏苏州昆山)人、著名思想家、“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之一的顾炎武对此评论曰:“本朝荐举大典应运而起者固不乏人,尚有烟霞之士,迫于催请,多在路途告病至,始终不起者,山西范公鄗鼎、陕西李公颙、江西魏公禧、浙江应公撝谦四人而已。商山四皓,于今复见。”(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一《辞荐举呈词》)
这次被清廷征试博学鸿儒时康熙皇帝圣旨中有“求贤”二字,范鄗鼎便将五经书院更名为希贤书院。“始五经而继希贤”。(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希贤书院碑记》)这次荐而拒赴后,范鄗鼎声名远播,朝野士子皆以名儒视之,拜其门下从教者日众。长于范鄗鼎十三岁的河津人陈大美,携《薛文清全书》四十卷,拜在门下;长于范鄗鼎十二岁的翼城人吕元音,携《朱勉斋在疚记》一卷,前来受业;垣曲人石云根,读范鄗鼎著作后,长行五百里,虔诚拜学,数年不归,受其教,读其书,效其行,为其刻书校板;绛州人闫擢,先是一人,后携两幼子常住希贤书院,历经年月,受范氏教,读范氏书,观范氏行,为其校阅文稿,参与范氏家事,犹如范氏家人。(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及门起予记其一》)陕西咸阳人吕大章,素慕范鄗鼎之教,不远千里而来执贽受业。(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二《吕伯玉问道录序》)
涵养家风与倡导义行
明朝一代,山西儒学明初首推河津薛瑄,明末当为绛州辛全。范弘嗣、范芸茂父子二人都曾拜学于辛全门下,深受辛全理学思想影响,均向心于理学。范鄗鼎出生在理学世家,幼受庭训,祖父范弘嗣为他讲授《河图》《洛书》《性理大全》,父亲范芸茂向他授予辛全的《养心灵》。范鄗鼎坚辞仕途隐居山林后,即笃志于理学。中国的传统理学,既是高深的哲学课题,又包含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成分。范鄗鼎所推崇实践的理学,不停留于晦涩难懂的理论层面,不尚空谈,注重个人修为,重视躬身实践。他的理学主张和修为践行获得了当时在朝重臣和隐逸的硕儒名贤的普遍认同。
师村范家在范弘嗣、范芸茂两代时,只有家庙,范鄗鼎于康熙五年(1666年)建成范家祠堂,制订了较为完备的家族祭祀礼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修成家谱,置祭田三十亩,“为他年祭祖宗,兼修先祠茔域之费”(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祭田碑记》),以保证祖宗祠祀绵延不绝。在家族事务中,范鄗鼎设立五经堂戒词二十则,涉及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并对每条戒词进行解释说明(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一《五经堂戒词》),作为族规,用以规范族中子弟的行为。
范鄗鼎注重孝行。他的“告终老”,是因为奉养母亲。康熙十三年(1674年),吏部行文调范鄗鼎进京,准备授予知县实缺,他辞而未受。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山西提督学政卢元培、太原府同知江南龄,请范鄗鼎参与撰修《山西通志》。范鄗鼎携子范翼、门生范尔梅赴省城,进入通志局,参与编纂,前后历时二十余日。范鄗鼎主张将稿件分四类处理,冗长者裁去,遗失者补充,可信者留存,有疑难者照实叙出,与阳曲李方蓁、闻喜温敞互相考订。其间,接到母亲郇氏来信召其归家,范鄗鼎婉拒了卢元培、江南龄的再三劝留,匆匆南归。(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修通志记》)康熙《山西通志》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才刻印成书,前后历时七年。范鄗鼎参与编纂前后仅二十余日,即以母亲来信回返,孝母之行堪为人子典范。母亲弃世后,他对自家的祖坟大加修葺,前后历时数年,把这作为文人躬行“人伦”道德的实际行为。他在祖茔牌坊上撰联:“天成象而地成形,有一念感通之天,无三旬不变之地,讲地理不如讲天理;心游虚而身游实,无百年不老之身,有千古常生之心,求心存即是求身存。”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傅山为范鄗鼎祖茔牌坊题额曰“竹策丛生”“槐栾勿拜”。(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莹域记》)
范鄗鼎倡导义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出资购地重修羊舍肸祠,撰文《重修羊舍大夫祠序》(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二《重修羊舍大夫祠序》)同年,捐资重修了春秋时晋国乐师师旷的陵园和祠宇,撰《周乐师子野墓碑记》。(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并申请府、县,请载其祀典于志书(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一《请聪圣坟制入志呈词》)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范鄗鼎倡捐百金,购置县城西辛村民田四十二亩,将田租作为县廪生和贫苦学子的生活费用。同年秋,他就江南总督于成龙入祀太原三立祠一事,两次呈书山西地方当局,终成其事。(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一《请于清端入三立祠呈词》《再请于清端入三立祠呈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修葺了皋陶祠、墓,撰《虞士师庭坚墓碑记》以记之。(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同年,范鄗鼎出银三百两,购置五十八亩水地作义田,用以赡养附近孤贫无依的老年人。设义冢,收葬贫而无力归葬之民。(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义冢碑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范鄗鼎又出资重修了曾任明朝户部尚书的韩文的坟冢,撰《韩忠定故里碑记》。(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民国《洪洞县志》卷十六《艺文志中》)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倡修了曾任明朝开封知府的卫英的坟冢,撰《卫太守故里碑记》。(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三;民国《洪洞县志》卷十六《艺文志中》)师旷、皋陶、韩文、卫英皆为洪洞历史上的名人,范鄗鼎修其坟、纪其事,旨在彰显其事迹,弘扬其精神,教化后来人。洪洞南垣靳堡里农民梁国瑞,为医母病割肋下肉;东垣里农民刘魁恩,为医父病割左膊肉,范鄗鼎听说后,详细询问,书字赠匾,并撰《刘梁两孝子传》对他们大加赞扬。(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五《刘梁两孝子传》;民国《洪洞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上》)
凡此种种,都被范鄗鼎视作发扬“道”的一种方式,是他弘扬理学学以致用、躬身实践学说思想的实际行动。深受绛州辛全和祖、父理学思想影响的范鄗鼎,以希贤书院为平台,赓续文脉,培养人才;弘扬孝行,彰扬义举,以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道民风。
师村范氏家族在明清鼎革之际,家道有所中落。进入清代,经范鄗鼎精心经营,“屡节衣食,家业渐丰”。(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四《创塑祖父像成祭文》)他整饬家风,教育子弟;设立书院,弘扬理学;倡导义举,褒扬义行,师村范家声名鹊起,虽不如当时洪洞苏堡刘家、李堡韩家、薄村王家、城内晋家等那样族大人多、影响巨大,也算远近驰名的家族了。
康熙皇帝御书“山林云鹤”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康熙皇帝从直隶保定入山西太原,南下晋南蒲州渡黄河,入陕西潼关,溯渭河而抵西安,出潼关经河南北还京师,途经四省历时68天,史称“西巡”。西巡途中,康熙皇帝于十一月初四日路过洪洞。在到洪洞前,已听闻范鄗鼎众多传闻的康熙皇帝,下旨平阳府要范鄗鼎接驾。年逾七旬的范鄗鼎在儿子范翷的陪伴下,初四大早就来到县城北北官庄桥旁恭候圣驾(康熙帝从霍县过来)。康熙帝经官庄桥入城后,传召了范鄗鼎。范鄗鼎将所撰辑的《明儒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两种理学著作进呈给康熙帝,并奏告《国朝理学备考》即将编成刻印,得到康熙帝的嘉勉。
第二天,范鄗鼎在城南恭送圣驾,康熙传召他父子随行到平阳府。入驻平阳后,康熙帝询问了范鄗鼎身体情况,御书“山林云鹤”四字匾额赐给他。(清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二八《艺文一御制·圣祖皇帝御书匾额》)康熙皇帝御书中所谓“山林”,是何意也?陕西三原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刑科给事中梁鋐在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的奏疏中曾曰:“山林者何?谓远于朝市也。隐逸者何?谓异于趋竞也。”(《清史稿·志·卷八十四·选举四·制科荐擢》)这应该是对“山林”涵义最恰当的解释了。
康熙皇帝西巡途中,在太原、西安赐予臣下大量书法作品,但大都为现任或曾任的文臣武将。范鄗鼎虽考中进士,但未曾入仕为官,身份仍为一介平民,名声和事迹能够传到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耳中,足见其社会影响之大;能够得到康熙皇帝召见,并获赠皇帝的御书匾额,又是何等的不易和殊荣!
生平著述与身后余绪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范鄗鼎病逝于师村家中,享寿八十岁,其门人私谥曰“文介”。
范鄗鼎绝仕归里后一直蛰居乡村,致力于授徒著述。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明儒理学备考》(又名《理学备考》)34卷、《广理学备考》48卷、《国朝理学备考》26卷、《三晋语录》10卷、《续垂棘编》4集35卷、《三晋诗选》14卷、《晋诗二集》2卷,另有《五经堂文集》5卷、《五经论略》等多种,也曾撰修过康熙癸卯年(1663年)《洪洞县志》(清雍正八年《洪洞县志》之《旧编纂姓氏》、民国《洪洞县志》序二)。
《三晋语录》辑录了明代至清初山西名儒、名宦的语录;《续垂棘编》收录了明清两代山西士人文章590余篇,对所录文章进行圈点并撰写评语;《三晋诗选》《晋诗二集》,辑录了明清两代及其以前山西诗人的生平介绍、诗作及出处、点评等。语录、文、诗三者并传,保存了大量文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地方文献价值。
《明儒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国朝理学备考》是范鄗鼎在理学上的代表著作。《明儒理学备考》是明代理学诸家的传记汇编,共34卷,卷一至卷六辑录辛全《理学名臣录》,卷七至卷十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传记摘编,十一卷至十六卷为范鄗鼎博采诸家传记所作续补,十七、十八卷为熊赐履《学统》,十九卷至二十九卷为张夏《雒闽渊源录》所录理学诸儒传记,三十卷至三十四卷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广明儒理学备考》为《明儒理学备考》的姊妹篇,共计48卷,辑录明代理学共80家的语录、诗文,与前书相得益彰。《国朝理学备考》录入清代理学家许三礼、熊赐履、陆陇其、魏象枢、于成龙、李颙、王士祯等26人,先为生平简历,其后附范鄗鼎按语,最后为学术资料汇编。三部理学著述可补官修史书之阙略,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五经堂文集》是范鄗鼎所撰戒词、呈词、书信、序文、记、书后、题赞、行状、志铭、表、传等的汇编,共计5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2册(清康熙间唐五经堂刻本)。其文章多属应用之文,记事详明,论述周密,语言凝练,如《重修洪洞儒学碑记》《社坛记》《后土碑记》《祭田碑记》《二弟香北像赞》等。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太原令德堂书院内设立“四徵君祠”,将洪洞范鄗鼎,太原傅山、阎若璩,蒲州吴雯四人的牌位供奉于祠内,供士子们瞻拜。清代体仁阁大学士、“一代文宗”阮元所纂的《儒林传稿》,为范鄗鼎立正传,这是山西唯一入正传的理学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刻本《山西通志》,康熙版《平阳府志》,均载有范鄗鼎传。中华民国3年(1914年),徐世昌(曾任中华民国总统)担任清史馆总纂,编纂《清儒学案》,列范鄗鼎于该书卷28,题名《娄山学案》,誉其为“清代山右儒宗”。
范鄗鼎之后的师村范氏家族,清雍正八年(1730年)《洪洞县志》、民国版《洪洞县志》有传的共五人:范凝鼎,范鄗鼎族弟,清雍正间拔贡,候选教谕,学问渊博,长期受聘于洪洞苏堡刘家做私塾先生,有《四书句读讲义》一书传世,曾参与编撰清雍正八年《洪洞县志》。范翼,范鄗鼎长子,县学生,屡试不第,精通医学,颇有医名;笃志于理学研究,三十一岁病死,有《敬天斋文稿》《敬天斋语录》刻印传世。范翷,范鄗鼎次子,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人,潜心经史,不求仕进,有《四氏心书》《正蒙摘粹》《心亨录》行世。范鹤年,范弘嗣裔孙,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任湖南衡阳县知县,才情横溢,学问宏深,著有《寸芹草》《藐雪山房集》《默账杂俎》《青影楼诗余》等。范燮,前后世系不详,清光绪时诸生,博学工诗,精通风水阴阳之学,以设塾教学为生,著有《诗韵补遗》《帝王世系图考》。再其后,未见有人出现于邑乘。
洪洞文史学者解谭之告诉笔者,2000年前后,他在洪洞县苏堡镇尹壁村工作采访时,在农户家中曾见到过范鄗鼎的著作,书中夹的纸页上记录了清朝末年范氏族人谋卖范鄗鼎著作的书板,当时主讲于运城宏运书院的陕西朝邑进士阎敬铭 闻讯,前来捐银五十两以济范氏族人生计,又捐五十两为范鄗鼎祠堂购置祀田,并将范鄗鼎书板运至宏运书院保存的事宜。
在师村实地走访时,范鄗鼎的后人范宾义引领我参谒了范鄗鼎祠堂遗址(1955年曾翻修)及室内供奉的头部残缺的范鄗鼎彩色泥质塑像。他指着祠堂内的顶部木质阁楼(民间俗称“存棚”)说,康熙皇帝御书的“山林云鹤”木匾和先祖鄗鼎公的书籍,原先都存放在上面,书籍后来渐渐散失,木匾后来也被损毁。
行走在师村,这片孕育出春秋时期晋国乐圣师旷、西汉“酷吏”郅都、明清两代三大家族(申家、理学范家、业商范家)、三位进士(明天启乙丑科进士申嘉言、清康熙丁未科进士范鄗鼎、清乾隆己酉科进士范鹤年)、曾经作为“古之遗直”叔向采邑的土地上,眺望着不远处麦田覆盖下的羊舌古城遗址,不免心生感叹:沧海桑田,时序维新,赓续绵延的唯有文化和精神!
范鄗鼎对理学发展和文化传播的贡献明载史册,于今昭昭,先生的声名和影响将是长久和深远的!他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