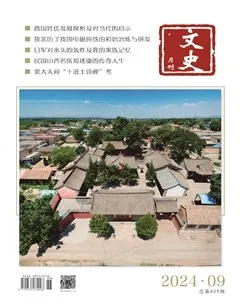“百官楷模”马丕瑶
马丕瑶(1831—1895),字玉山,号莲溪,清代河南安阳县人,同治元年进士,历任山西平陆、永济知县,解州知州,太原知府,贵州布政使,广西、广东巡抚等职。主政地方30余年,清廉正直,“勤求治理,实心爱民”,政绩卓著,被百姓称为“马青天”,被光绪皇帝称为“堪为晋省百官之楷模”。
惩恶扬善
同治元年(1862年),马丕瑶考中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到山西。先留在山西巡抚身边从事幕府工作,4年后,被派任平陆知县。平陆县地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地带,位置偏僻,人员混杂,盗匪横行,民怨沸腾,历来号称“难治”。马丕瑶到任后,走遍村寨沟垣,访贫问苦,体察民情,了解到当地百姓有“三怕”:一怕苛捐杂税,二怕盗匪横行,三怕告状打板子。
针对苛捐杂税问题,马丕瑶创办了徭役征派机构——里民局,规范徭役征派,得到百姓拥护。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马丕瑶狠下决心打击盗匪。他深入田间地头,明察暗访,每天和百姓在一起,谁贤谁不肖,都了如指掌。平陆县有个村子发生了一起杀人案,马丕瑶接到控告后,对左右说:这一定是某某所为。于是派捕快将某某缉拿到案,过堂庭审,果然如他所料。还有个村子发生了盗窃案,马丕瑶听说邻县抓获了盗窃犯的同伙,于是商请将这伙盗窃犯移交平陆,并案审讯,被拒绝了。于是,他派人到邻县,故意犯案,被关入监狱,从在押囚犯口中套出了7名盗窃同伙的姓名,随后在河南登封、渑池一带将盗窃团伙成员全部抓捕归案。马丕瑶在平陆连破几个大案,盗贼受到震慑,从此在平陆县销声匿迹,“所治无盗”。
当时平陆县有个陋习,官员在审理案件时,为了约束“刁民”,限制诉讼,不论原告被告,有理无理,先打一顿“板子”,称为“杀威棒”。马丕瑶到任后,体恤民情,废止了打板子的陋习,而是启发开导,使他们知道悔悟。他还撰写了“不爱钱,不徇情,我这里空空洞洞;凭国法,凭天理,你何须曲曲弯弯”的长联,悬挂于平陆县衙大堂。马丕瑶担任平陆知县不到三年,三害全除,“辖境大治”,被百姓称为“马青天”。
同治七年(1868年),马丕瑶调任永济知县。永济县东北乡有个小村子,名叫“过村”,距离县城50里,与临晋、荣河、猗氏、虞乡四县接壤,虽然仅有百户人家,但有一半的人以盗窃为生。其他地方的盗匪也把过村作为落脚据点,邻县邻村的盗抢案件层出不穷,失主即使拿获盗贼,也不敢过分追究,一旦告到官府,盗贼就会千方百计加以陷害,直到把失主搞得倾家荡产。这些盗贼不在永济本地行窃,永济县接到过村人所犯的盗抢案件寥寥无几,而临晋、虞乡、荣河、万泉、安邑、解州等地移交过来要求查办的案件,无不指过村为贼窝,方圆数百里的百姓不得安生。马丕瑶到任后,面对盗贼,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史书记载,但凡他得知某处有盗贼出没的警报,“即单骑往捕,虽夜中及大风雨雪不避”。马丕瑶调查清楚后,将贼首绳之以法,其他从犯见贼首伏法,都改邪归正,从事了正当营生,村风民风焕然一新,马丕瑶为该村改名为“善村”。
怀民以仁
永济县的上源与夏阳两个村子,面朝黄河,背靠中条山,上源在南,夏阳村在北,滩地彼此相连,由于黄河泛滥,滩地界碑早已不知所踪,自乾隆年间两村就为地界争讼不休,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各级衙门多次诉讼,府、道、院司、都察院都作了处理,由于始终没有令双方满意的结果,7wqftuibsqm5412s6pFFvKsiT8sFQCHkUlQc2MD0R/Q=两村械斗百年,村民死伤甚多,严重影响地方治安,两村也被拖累得贫困交加。马丕瑶上任后,查阅了有关的水文资料和以往的争讼文档,亲自前往实地勘测,对照历史记载精心测算,丈量土地面积,勘定山势走向,提出新的勘界定分解决方案,重新竖立界碑,并镌刻畔石铭,铭文称:“百年疑案,莫辨渭泾。呜呼畔石,竟尔通灵。来余梦寐,复汝原形。天圆戴笠,并锡巾青。下维坤舆,上曜文星。石乎石乎,汝其安常镇静,为翰为屏,勿得惊骇惑众,而动摇于冥冥。”当时正值初夏,马丕瑶经常暴露在太阳底下,不辞劳苦,汗流浃背,村民既服其公允,也受其感动,百年仇怨得以化解。
马丕瑶主张:“做官以教化为先。”他在平陆时,从端正士习入手,整顿风气,张贴《观风告示》,要求读书人立志要大,士习宜端,读书宜博,文体宜正。在永济时,创办了敬敷书院,力邀在河南灵宝教书的山西大儒薛于瑛(号仁斋,芮城人),担任了敬敷书院山长。马丕瑶亲自为书院撰拟了对联:“道岂求远,缅诸冯,眺首阳,教孝教忠,极千古人伦之至;文其在兹,亲百姓,逊五品,克宽克敬,括累朝圣学之全。”而且答应薛于瑛,讲实学不讲八股,以道义相交不讲官仪,敬敷书院声名鹊起,冀豫秦晋群贤毕至。
勤政爱民
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因为这两年分别为阴历丁丑、戊寅年,所以史称“丁戊奇荒”。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千余万人饿死,另有两千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晚清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山西的旱荒空前,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称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
山西解州受灾最为严重,且当地盐枭趁机作乱。工部侍郎阎敬铭作为钦差大臣到山西稽查赈灾工作,听说晋南有个“马青天”,于是专程寻访,并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推荐,任命马丕瑶为解州知州。马丕瑶临危受命,雷厉风行,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捕斩了20多个盐枭,控制住了局面。他在解州设立赈灾总局,提出“赈务六条”,全力救灾。最困难的时候,马丕瑶给赈灾总局同仁写下《即事书怀并示赈局诸公》诗,称:“七万生灵口,而今剩几何。每惊人数少,不觉泪痕多。巧妇难无米,饥民幸止戈。赈粮长弗继,日月恨蹉跎。”“赖有同舟济,官民意味亲。天恩三次泽,州属一家人。分合筹全局,城乡洽比邻。诸君须努力,散作梓桑春。”同时,他向附近绅民贷粟十余万石,全部发放给灾民,计口给粮,使得灾民免于流亡。同时彻查地亩,平均田赋。下令全州捕蝗,种桑种树,黜奢崇俭。当时山西赤地千里,死者大半,只有解州死亡最少。马丕瑶考虑到土地没有鱼鳞册,吏民会因缘为奸,于是组织清丈土地,编订鱼鳞图册。阎敬铭称赞他的救荒政绩为“山西之最”,他的“清丈地粮”同样被后任山西巡抚卫荣光称赞为“山西之最”。马丕瑶聘请在虞乡(今永济)养病的工部右侍郎阎敬铭(光绪年间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主讲解梁书院,聚所属一州(解州)五县(安邑、夏县、闻喜、平陆、芮城)士民讲学,广开教化,被赞为“兴学而人才丕变,励俗而礼让大行”。不久,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推举马丕瑶为“贤良”。光绪帝接连收到多位朝廷重臣和地方大员对马丕瑶的上奏表扬,认为马丕瑶堪当大任,钦赐“百官楷模”牌匾。
马丕瑶在广西设立官书局,倡办蚕桑,开设机坊,发展了地方经济文化。光绪二十年(1894年)出任广东巡抚时,严禁了广东赌博之风,参劾两广总督李瀚章的违法情节。去世留下《遗折》,希望皇上“励精图治”。
清廉自律
马丕瑶廉洁自律。任永济知县时,他的俸禄除了负责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开支外,还要接济穷人,加上创办书院等各种捐款,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但他“自奉俭约,恒以清慎自持。虽膺瘠苦,宴如也”。
当时永济县有个人称“不倒翁”的县吏,极善奉承。他听说马丕瑶和他的子侄都喜欢养花,便搜罗奇花异草,来献殷勤,被马丕瑶断然拒绝。马丕瑶认为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随后便派人调查,发现这个县吏是百姓痛恨的“巨蠹”,马丕瑶立即对其实行了严厉惩处。事后,马丕瑶借此事件,告诫子侄:“人之投吾所好者,必有所为而来。稍中其毒,与饮鸩等。”这句话显示了马丕瑶的慎独、自律以及严格的家风家教。
马丕瑶到永济的第四年(1871年),老父亲突然病逝。马丕瑶报请停薪,归家丁忧。可他连买棺材、雇车马回家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全家受困,竟至无米为炊。永济百姓听说后,被其廉洁奉公的事迹打动,纷纷解囊相助,捐凑银两,这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从永济丁忧回到老家后,马丕瑶遵照父亲遗命,创修家庙,在家庙旁边建立私塾,教育家族子弟,捐助田地设立义庄,用于扶助鳏寡孤独、贫困疾苦的族人。他精心修订《马氏四种条规》,教导马氏子孙要以孝悌为本,多行慈善之举。
马丕瑶综合挚友劝谏,反省自己过去,写出了对己对人都影响深远的《约斋铭》,并将其作为马氏家训,告诫子孙要日新其德、刚健笃实、正己守道、不辱门楣。《约斋铭》全文共741字,包括“戒色、功名、思虑、笔墨、言语、处家、生业、银钱、享用、应酬、读书、豪情”等12个方面。
马丕瑶经常以写诗的形式,教育子女。光绪四年(1878年)腊月,马丕瑶的次子马吉樟冒着大雪,从解州返回故乡安阳,准备到京城参加会试,马丕瑶写诗鼓励他:“才别汴梁又解梁,河东绕历递安阳。父兄师友资摩励,险阻艰难要备尝。大雪寒澄清心胆,春风和气入文章。贤豪世业无他术,澹静垂书忆武乡。”他给侄儿马吉福的诗中说:“汝曹尔为长,倡率一家人。处乡要和睦,九族本一亲。怒时须忍耐,见利防害身。作事退步想,以屈而能伸。勉之哉!读书第一传家法,教训诸弟耐苦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