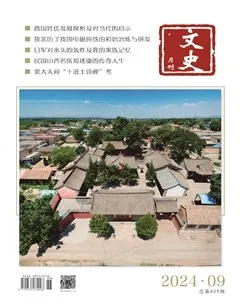窦大夫祠“十进士诗碑”考
在太原上兰村窦大夫祠中有一通“十进士诗碑”,立于山门内檐下,未具立碑年月。碑上共刻有陈璧、仲奎、廖俊、谢佑、王允、杨璿、朱忠、祝灏、□□、□□,明代十进士十首同韵诗(后两人名字局部损毁,难以确认,用□□替代),其内容为盛赞裂石(笔者注:“裂石”与“烈石”互用,文中引文不强求统一)暮春美景。碑阳碑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捐赠人名字与字号名称,但无法断定十进士诗作创作的具体背景与立碑年代,因此也成为窦大夫祠诸多碑碣中一个独特的存在。现录之于下:
明进士:陈璧
冠盖追游正暮春,马蹄蹀躞蹴香尘。
山花供翫飘红雨,芳草宜眠展绣茵。
一甃清流寒浸玉,半空飞瀑净浮银。
主宾畅咏情何极,归晚东溟起月轮。
明进士:仲奎
观风偶尔遇残春,自喜名山远市尘。
骢马似龙人似玉,林花如锦草如茵。
圣君恩重心常赤,慈母年高鬓渐银。
抚景兴怀吟眺久,夕阳西下未回轮。
明进士:廖俊
寻芳尚喜值残春,紫陌行行不动尘。
古井亭边山作画,仙人岩里石为茵。
水经滩碛轻敲玉,风送扬花碎剪银。
酒尽夕阳啼鸟散,士民簇簇迓归轮。
明进士:谢佑
群公笑语满怀春,出郭元非避俗尘。
览物郎吟行并辔,观风清话坐联茵。
云迷树色山排画,石激琴声瀑泻银。
为报豺狼须敛迹,无劳柱史更埋轮。
明进士:王允
民物熙熙四野春,风和日暖不生尘。
半空青絮飞晴雪,满路香花铺锦茵。
石罅泉流千尺练,林稍月挂一钧银。
丰年有象心皆乐,笑逐青骢拥画轮。
明进士:杨璿
暖云香雨酿芳春,骢马行春不动尘。
山色乱红花似锦,水洆柔碧草如茵。
群公报国心同赤,壮岁追欢鬓未银。
胜境良时宁易遇,独因羁绊后蹄轮。
明进士:朱忠
追游正喜属芳春,杨柳风轻不动尘。
吟看落花红作雨,坐联芳草翠为茵。
云开峻岭寒堆玉,石迸流泉色泛银。
明月照人归未稳,夜深何用促蹄轮。
明进士:祝灏
宪台宾从出行春,正喜三边净虏尘。
祈岁偶然来胜地,观风非欲醉重茵。
夕阳西下山横翠,明月东生水滉银。
豺虎潜踪民庶乐,时清不用复埋轮。
明进士:□□
骢马登临属暮春,东风吹雨净纤尘。
举杯直欲邀明月,席地何须列绣茵。
柳絮缀衣千点雪,溪鱼掷浪一梭银。
山亭底事留连久,应叹年华逐转轮。
明进士:□□
熙熙笑语满怀春,雅操水壶不受尘。
群彦总知真今器,独吾有愧接重茵。
看山到处诗成画,联辔归迟烛剪银。
游乐岂应殊赤壁,鹤来如见翅如轮。
关于斯碑,曾有当地学者以碑中陈璧为明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阳曲人作解,得出成化八年(1472年)后勒石的结论。但分析碑上十进士及其诗作,分析碑上玉工与化缘者、募捐者所属时代,乃至斯碑与周围寺庙碑文内容,“成化八年(1472年)后”的结论值得商榷,有正本清源之必要。
从“十进士诗碑”十进士及诗作分析
从“十进士诗碑”诸诗内容分析,当为同一时间雅集唱和之作。第一首中的“主宾”,第四与六首中的“群公”,第八首中的“宾从”,第十首中的“群彦”,第五首与十首中的“熙熙”,均说明是一次有人发起相邀,众人响应随行的郊外雅集;第二首、第四首与第八首的“观风”,说明出行目的“出郭元非避俗尘”;第一首与九首中的“暮春”,第二首与三首中的“残春”,说明出行的时间在春三月;第一首中的“马蹄”,第二首、第六首与第九首中的“骢马”,第五首中的“青骢”,第四首中的“并辔”,第六首中的“羁绊后蹄轮”,第十首中的“联辔”,说明出行既非乘车,也非徒步,而是众人骑行;第一首中的“归晚东溟起月轮”,第七首中的“夜深”,第八首中的“明月东生”,第十首的“归迟”,说明众人出行雅集一直到晚上才返回城中。综合分析十首同韵诗作发现,发起雅集者当为第一首诗作者陈璧,众人皆随行者,并步韵陈璧诗作唱和。
关于陈璧其人,道光《阳曲县志》卷五《选举表》进士、举人条目下均有记载。卷十三《人物传略》记曰:“陈璧,字瑞卿,成化壬辰进士,知嘉兴、武邑二县,性抗直,不折节权贵。以绩最擢监察御史,益厉风采。巡按山东,辨太保刘诩狱,进山东兵备副使,临清为漕运所经要冲之地,凡百需蛊弊。璧一切裁省。有贵珰贪餍于民,璧折以法,珰恚怒击其首,竟莫能夺寻……此尤不可及云。”卷三《建置图·乡贤祠》记载:“陈璧,明右副都御使。”曾有当地学者解读“十进士诗碑”当在成化八年(1472年)后,将“十进士诗碑”中陈璧断为阳曲陈璧(瑞卿),所据者即此。其实明末太原府太谷县也有进士名陈璧者,生于1460年,卒于1520年,字德如,号龙泉。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授行人司司副,屡次奉命出使宗藩,不受馈赠,迁刑部员外郎、郎中,出为陕西左参议,迁湖广按察副使,奉命整饬郴州等兵备,安抚荆襄等流民,剿伐边寨少数民族起义,食三品俸,以丁忧去职归乡,卒于家。“十进士诗碑”中之“陈璧”,究竟是阳曲陈瑞卿,还是太谷陈德如?笔者认为,不应局限于阳曲县或太原府出身的进士,还应当从此间出身进士的山西官员中考察是否另有陈璧其人,乃至从仲奎、廖俊、谢佑、王允、杨璿、朱忠、祝灏等十进士及其诗作入手,进而综合分析。
在明成化《山西通志》卷之八《名宦》记有陈璧其人:“直隶常熟人。由进士除江西道监察御史。天顺二年(1458年)差代。升浙江按察司佥事。致仕。”而在卷之十六《艺文·集诗》中,则收录了4首同名同韵的《游裂石》诗,其中第一首标“陈璧见巡按”,即为这位常熟陈璧之作。与“十进士诗碑”所刻诗文比照,首作陈璧诗与碑文同,次为“茂彪见巡按”,诗与碑文中仲奎诗相同;三为“孙珂见巡按”,诗与碑文中祝灏诗相同,仅诗首“宪台”为“兰台”之别;四为廖俊“江西乐安人,天顺间行人”,诗与碑文中相同。由此可见,诗碑中陈璧并非成化八年(1472年)阳曲进士陈璧,更非太谷进士陈璧,而是直隶常熟人陈璧。
此外,成化《山西通志》卷之八《名宦》对茂彪与孙珂也均有记载,“茂彪,陕西安化人。由进士除江西道监察御史,天顺二年(1458年)差清军,升山东按察司佥事。以疾致仕。”“孙珂,山东福山人。由进士除云南道监察御史,天顺三年(1459年)差代。升南京大理寺丞,改知潞州。”但志书记录与“十进士诗碑”所刻,仲奎与茂彪、孙珂与祝灏何以诗同而人异?
在《常熟志》卷四《科第》对陈璧有详细记述,明确记载其“字仲奎,号恤庵,甲戌进士”,仲奎为陈璧字,可见“十进士诗碑”中第二首诗作者应当不是仲奎(陈璧),这也反证了成化《山西通志》卷之十六《艺文·集诗》中的记述。第二首诗作“观风偶尔遇残春,自喜名山远市尘。骢马似龙人似玉,林花如锦草如茵。圣君恩重心常赤,慈母年高鬓渐银。抚景兴怀吟眺久,夕阳西下未回轮”,为茂彪之作。
至于“十进士诗碑”中第八首诗作的作者祝灏,当为祝颢之误。祝颢在山西为官时间较长,从布政司左参议拔擢为右参政,足迹遍山西,留下大量咏晋诗文,并收录于诸版《山西通志》艺文中,但不论在其诗文集《侗轩集》,还是在诸版《山西通志》艺文中,均无有该诗记载。可见成化《山西通志》卷之十六《艺文·集诗》中的记述是准确的,“十进士诗碑”中第八首诗作的真正作者并非祝颢(灏),而是孙珂。于此,后文还将提供佐证。
“十进士诗碑”中涉及的其他进士,成化《山西通志》卷之二十七《碑目·庙坛类》中记有“《烈石祠祷雨记》国朝立,萧启”,此碑至今完好保存于窦大夫祠正殿檐下。碑文中叙述了景泰乙亥(1455年)巡按御史金台李宏、古汴马文升、四明钱琎,偕三司官员烈石祠祈雨的情况,三司官员中即有“十进士诗碑”中的布政司左参议祝颢、杨璿,都司都指挥使朱忠。
“十进士诗碑”中的王允与谢佑,明成化《山西通志》卷之八《名宦》中也有明确记载:
王允,山东历城人。由进士初除监察御史。天顺元年(1457年),以温州知府升山西按察使。既而召升湖广左布政使。以忧去。成化六年(1470年),调任山西。致仕。
谢佑,直隶桐城人。由进士初以户部郎中升河南左参政。天顺六年(1462年)升山西右布政使。自乞致仕。但经与其他记载印证,谢佑升任山西右布政使并非天顺六年(1462年),而是天顺二年(1458年)。
以上说明,“十进士诗碑”中除第九、第十两首诗作者姓名漫漶不清而无法求证外,陈璧等七人均为明代景泰、天顺间同一时期山西官员,廖俊其时虽未入仕,但以进士身份行走于晋省官员文人间。十首诗作当为某一年暮春三月雅集于太原府城北窦大夫祠同题《游裂石》唱和之作。
从“十进士诗碑”与窦大夫祠内外其他碑碣关联玉工、化缘者与募捐者分析
全面分析“十进士诗碑”,碑阳十进士题名诗外,共有33行25列,涉及735个人名,21个字号,另有与勒石关系紧密者14人;碑阴涉及1395个人名,61个字号。全碑总计涉及2144个人名,82个字号。碑石上最为突出的人物即玉工王贵仓。如果能考定王贵仓其人,或可解开“十进士诗碑”勒石年代。
在北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三《石作制度》中,对于碑、碣列《赑屃鳌坐碑》与《笏头碣》,有论述,但十分简略。《笏头碣》:“造笏头碣之制:上为笏头,下为方坐。共高九尺六寸。碑身广厚并准石碑制度笏首在内。其座,每碑身高一尺,则长五寸,高二寸。坐身之内,或作方直,或作叠涩,宜雕镌华文。”这是一种没有盘龙碑首而只有碑身、碑座的石碑,而且碑座也不用鳌座而只是简单的方座或者做成有进出叠涩的须弥座形式。古时把有装饰雕刻的方形碑头的碑石称为碑,把无装饰的圆形碑头的碑石称为碣,《营造法式》也是据此原则把碑、碣加以区分,但实际上又多混用而统称为碑碣,或简称为碑。从总的造型上看,石碑确有简洁与复杂之分,其中主要区分就在于碑首与碑座的形式。清末,尽管遵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制度,但在民间,碑碣制度已不十分严格。对于石作匠人的称谓也不尽统一,如石工、石匠、良工石匠,泛指石作匠人,也特指造作、雕花、造型石匠。也有镌刻人、镌匠、镌匠人、镌玉工、玉工、石工、铁笔生、铁笔人、铁笔等,其中也包括部分文人石匠。本文对此问题不多作探讨,仅对崛围山一带碑碣中有关石作匠人简要比对,以判断“十进士诗碑”勒石年代。
关于玉工王贵仓的生活时代,窦大夫祠及崛围山周边祠庙的相关碑碣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嘉庆二十年(1815年)上兰村《关帝庙乐楼展建碑记》中有“玉工于利斌、王贵仓”,碑在上兰村五龙祠;道光五年(1825年)净因寺《重修碑记》中有“玉工王贵仓”,碑在土堂村净因寺;道光十五年(1835年)窦大夫祠《重修膳亭彩画禅院碑记》中有“铁笔石工王贵仓”。三通碑碣,王贵仓为玉工或铁笔。碑刻中留有姓名者也多有重叠,如住持僧祖琏、祖枚、祖珏,玉工于利斌,木匠常义,画工苗大、李大德,纠首李大全等。说明王贵仓其人起码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间,一直活跃在上兰村周边石匠碑刻圈。由此可以得出“十进士诗碑”当在此一时段刻成的初步结论。
关于“十进士诗碑”具体的镌刻时间,还可以从“十进士诗碑”与窦大夫祠内外其他碑碣关联玉工、化缘者与募捐者分析中求证。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六月,窦大夫祠寺宇有两通碑刻成,一是《英济侯庙碑记》,为本里学儒苗千宝抄录金代阳曲县令史纯所撰《英济侯庙碑记》前半部分,功垫主、总管钱粮、经理纠首、乡约、渠长一应俱全,时在“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夏六月谷旦”。二是《万人碑记》,为平定进士太原府儒学教授刘鸣鹤撰书,时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于“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夏六月谷旦”所指的确切日期,根据万年历推算谷旦所指黄道日,当在初三、初四、初六、十二、十五、十六与十八中之某日。下面从三个维度将此二碑与“十进士诗碑”对比研究。
首先从碑碣形制等视角分析。
通过分析表可见,三通碑尺寸与用材基本相同,仅碑首有异,但恰恰体现出三通碑勒石于同一时间,但《万人碑记》为主,是对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窦大夫祠寺宇大修完工的即时碑记,而《英济侯庙碑记》《十进士诗碑》为次,或复刻前碑或补刻前诗。
其次从碑碣的镌刻者分析。
《英济侯庙碑记》与《万人碑记》中众纠首有27人相同,前者比后者还多出连发金、赵大亮、王维新、于明、赵玉德、连秉伸、苗明望、苗绪福8人,后者比前者也多出苗明昌、赵秉源、苗维福3人。而且“十进士诗碑”中人名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英济侯庙碑记》《万人碑记》中人物,同样多有重叠。由此可见,尽管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英济侯庙碑记》中无有王贵仓其名,但与王贵仓合作刻碑的画工李大德、苗大,镐工李大全,石工于利斌,均参与了碑刻。特别是与王贵仓合作《关帝庙乐楼展建碑记》的玉工于利斌、画工李大德、苗大与李大全,还同时参与《英济侯庙碑记》与《万人碑记》两通碑的镌刻,于利斌与王贵仓又同为“十进士诗碑”施钱一千。至于王贵仓为什么未能参与《英济侯庙碑记》的镌刻,也许另有原因。
再次从碑碣的内容分析。

《万人碑记》中记述了这样的事实:“檐楹栋宇自十九年(1814年)斟工重修,于今岁已告竣勒石矣。兹复募化万缘,共得金捌佰余两。金妆大佛三尊,兼修禅室一所。立万人碑而嘱于余,余唯之。”之所以会勒石《万人碑记》,缘在窦大夫祠寺宇三年维修工竣,凿碑以记,“碑曰‘万人碑’,毋亦生万应,护万法,育万有,济万物。”《英济侯庙碑记》原本为金大定二年(1162年)阳曲县令史纯所撰书,但到元代时已碑石无存,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窦大夫祠寺宇大修完工,本里学儒苗千宝抄录上半部分复刻,而且功垫主、总管钱粮、经理纠首、乡约、渠长一应俱全,足见该碑在上兰村百姓中的地位。而“十进士诗碑”,其内容为“游裂石”唱和诗作,韵辙相同,明显为一次雅集之作。而嘉庆间之所以要将明代十进士诗作碑刻于窦大夫祠,无非是借明代十进士的一次雅集以彰显上兰村窦大夫祠一方形胜,当然客观上也保存了其中一些早已失传的诗作。至于“十进士诗碑”中十进士唱和诗作的传抄者,亦当为上兰村学儒苗千宝。由此可以推断,“十进士诗碑”当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英济侯庙碑记》《万人碑记》镌刻于同一时间,此或亦“十进士诗碑”未落碑刻时间的原因。
“十进士诗碑”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分析
上述分析说明,几百年后的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窦大夫祠寺宇大修完工,刻《万人碑记》以记。同时,为彰显窦大夫祠与烈石寒泉一方形胜,不仅复刻了毁于元代的金大定二年(1162年)阳曲县令史纯所撰书《英济侯庙碑记》,而且将明代陈璧等十进士《游裂石》雅集诗作勒石。但明代陈璧等十进士又为什么选在烈石山下窦大夫祠,而不是他处雅集?
解读上述疑问,还需从祝颢其人入手。在“十进士诗碑”中,祝颢被误为祝灏,且其名下之诗也当为孙珂之作。这其中的张冠李戴,或祝颢误为祝灏,当与民间传抄几百年有关,不足为奇。而之所以判断祝颢未曾参与“游裂石”雅集,答案就在其《博趣亭》与《书博趣亭诗后》一诗一文中。
博趣亭
观风何待出郊坰,台畔新开博趣亭。
对榻好山横几案,绕檐嘉树映帘屏。
衣冠俎豆公余会,里巷歌谣静里听。
燕喜有文千古诵,谁操掾笔插芳馨。
《书博趣亭诗后》曰,博趣亭位于其时臬司之西,冀宁道后,由按察司佥事朱瑄、吕正提议,王允、李俊、张瑄、张春、王豪、强宏诸官参与,“亭作于天顺己卯夏四月辛酉,成于是月戊寅。”“监察御史陈公过而悦之,为书‘博趣亭’三字,揭于楹间,后写‘□君子璧’,以全清玩,而亭之胜益彰。宪臬诸公从而观庆,凡遇休暇辄游于此。”
祝颢此《博趣亭》七言近体之“观风何待出郊坰,台畔新开博趣亭”,恰与茂彪《游裂石》诗中“观风偶尔遇残春,自喜名山远市尘”相关联。也说明茂彪《游裂石》诗写于《博趣亭》诗前,诗意观风要到名山,远离市尘。而祝颢之诗,恰与前诗意反。观风未必出郊坰,可以到闹市静地的博趣亭。游裂石雅集后的夏四月辛酉至戊寅日间落成博趣亭,也才有了“陈公过而悦之”,为书“博趣亭”雅事。此亦可以证明祝颢未曾参与“游裂石”雅集,十进士《游裂石》诗成于博趣亭建成之前,即天顺三年(1459年)夏四月之前,而陈璧、茂彪上一年仕晋,孙珂该年到任,廖俊行走于山西,四人《游裂石》只能作于天顺三年(1459年)春三月,即诸诗中所述“暮春”或“残春”。陈璧、茂彪、孙珂、廖俊之外,王允仕晋于天顺元年(1457年),杨璿仕晋于景泰三年(1452年),谢佑仕晋在天顺二年(1458年)前,朱忠仕晋于景泰六年(1455年)前,一起参加了此次雅集。至于后两首诗作者,因碑上作者姓名漫漶不清,无法判断,但诗作无疑为《游裂石》雅集唱和之作。
但陈璧等十进士又为什么会在天顺三年(1459年)暮春雅集于窦大夫祠,不仅仅是文人闲情逸致的抒发,其实还有着深刻的背景。《明实录》记载,景泰至天顺间山西大旱不断,祈雨成为地方官员的头等大事。景泰三年壬申(1452年)十月辛丑,山西右副都御使朱鑑被召回京,右佥都御史萧启代之。次年萧启历郡邑考察,至六月天旱不雨,回到藩城太原时天降甘露,且连雨四日,遂往城北烈石祠致祀。自此设祷雨坛于藩城外,每望烈石云起必雨。景泰六年乙亥(1455年)又至五月不雨,萧启卧病,五月乙亥日,巡按御史金台李宏、古汴马文升、四明钱琎,偕三司官率僚属列石祠祈祷,当日晚降雨,且连降三日。三司立石以记,并请萧启撰文碑记。参与烈石祠祈祷的三司人员分别是:布政司左布政使张茂、右布政使陈翌,左参政刘训、右参政王庾,左参议祝颢、杨璿、叶盛,右参议郭恕、毕鸾、魏琳;按察司按察使俞本,副使李俊、章绘、叶清、刘琚,佥事徐行、王豪、武聪、张春、张宏;都司都指挥使朱忠,同知张怀,佥事宫端、李刚、李泰、陈瑄、李端、江涌。此碑明景泰六年乙亥由太原知府孙睿勒石,至今《烈石祷雨感应记》完好立于窦大夫祠主殿檐下。
可以推想,明景泰六年乙亥五月祈雨祷雨,萧启撰文碑记,三司立石于窦大夫祠后,窦大夫祠也成为官府祈雨祷雨之地,相沿成习。几年后的天顺三年己卯(1459年)春三月,陈璧等官员步窦大夫祠祈雨祷雨后尘,邀同僚同好雅集烈石山下窦大夫祠,并以《裂石山》为题相互唱和,是窦大夫祠祈雨祷雨活动的延续,自然也成就了一段十进士题咏裂石山的佳话。以至三百余年后的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上兰村乡绅百姓与祠寺僧众仍念念不忘,并采取勒石铭记的方式,刻制成此“十进士诗碑”。
诗作明季天顺年,勒石清中嘉庆间。风风雨雨数百载,日日年年立祠前。碑碣不仅是彰显一方风土形胜的载体,其本身也作为文化与历史的一部分,而被古人誉为“贞珉”。更何况,在其镌刻因果之间,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与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