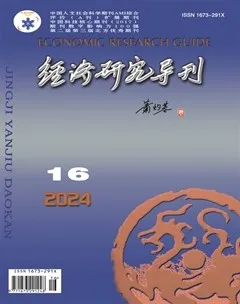“济困”还是“求精”
摘 要:养老服务设施对保证晚年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不仅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要重视实际服务需求。基于各省市2017年全要素POI数据和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匹配省份和个体层面数据,定量分析了养老服务设施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差异。结论显示,只有中等健康、中等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群体属于设施效用目标群体,且设施对农村老年人总体发挥效用较低。由此可知,现有养老服务设施福祉促进作用的发挥存在门槛和上限,即既不能“济困”也不能“求精”;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当从供需角度双管齐下,既要着力优化养老服务设施整体布局,又要强化以需求为导向的养老服务资源供给,深化新型养老观念的普及。
关键词:养老服务设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分层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4)16-0093-08
引言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焦点。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12个省份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14.0%。随社会经济水平提升,“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逐渐成为新型养老观念,老年群体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使该群体成为市场中日趋庞大的消费端,不断激发对应生产端的活跃与更新。民政部发布的信息指出,截至2022年一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总数突破36万个,养老服务供给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持续创新。
养老服务设施通常被认为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息息相关,而影响其边际效益的因素主要是养老模式和服务质量。目前有关设施建设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和实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越多、服务水平越高,老年人尤其是其中的相对弱势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就越强烈[1]。另一种观点认为,养老服务设施所构建场域极易诱发虐待老人[2]、加剧老人孤独感[3]等众多弊病,且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和设施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迎合不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因此,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整体影响方向尚不明确,从老年人本身乃至整个社会有机体来看,鲜有文献将不同层次变量进行匹配研究,这一群体是否真的从养老服务设施中获益以及设施建设是否存在外部性仍未可知。总体而言,国内外研究呈现出三大方面不足:一是忽略老年人内部分层,大多研究将老年人作为整体进行笼统研究,未将多元需求纳入考量;二是忽略设施分类及目标群体问题,缺少供需匹配相关量化研究;三是忽略机制分析,仅仅从因果角度进行验证,鲜少关注作用过程。
那么,现有养老服务设施是否能切实满足老年人差异化需求?养老服务设施更多发挥兜底作用、普惠作用还是精进作用?养老服务设施又是借助何种路径作用于老年群体福祉?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主要有以下边际贡献:首先,养老服务设施的建造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不同老年群体偏好的探查将有助于供需匹配,提高资源利用率;其次,通过对现有设施的福祉促进效用进行考察,有助于养老服务设施真正实现普惠;最后,只有明晰养老服务设施的作用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对症下药,避免服务供给鸿沟。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设
(一)养老服务设施与幸福感
从政策演变历程中来看,随着养老服务体系顶层设计的渐趋完善,配套设施的建造加快提上日程。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构建的“家庭-社区-机构”三方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基础上,首次强调了“医养结合”概念;随后于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引入“康养”理念,形成“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全新格局。从政策演变历程中不难看出,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着力点在于保障和改善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发力点在于社会网络中的多方主体支持。
从理论来看,养老服务的核心功能一般体现在精神慰藉和保健照护两大方面。研究表明,养老服务设施不仅发挥了基础的医疗照护作用[4],还充当了老年人群融入社会支持网络的媒介[5]。
相比于年轻群体,主观健康状况通常被认为是影响老年群体福祉的重要因素。首先,两者存在极强相关性,借助老年人对自身主观健康情况的评估结果能够较好预测其幸福水平[6]。其次,更高水平的健康状况往往带来更为强烈的幸福感受[7]。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对健康标准的期望会影响主观健康水平乃至与之相关的幸福感,且整体呈现与伊斯特林悖论相似特征[8]。例如,同等客观健康状况下,习惯艰苦生活条件的老年群体的主观健康评价可能更高,说明健康公平对于解释幸福公平至关重要[9]。
根据Bourdieu的定义,社会资本是基于制度化关系网络建构起来的、为社会成员提供支持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且可以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互转化[10]。进一步的,Bjornskov将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度量指标,发现其对主观幸福感具备显著积极效应。但他同时也指出应当纳入更多衡量维度[11]。个人通过建立与网络中他者的关系来获取分布于网络中的相应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福祉。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养老服务设施能够通过改善老年群体主观健康状况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H2:养老服务设施能够通过激发社会网络力量提升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
(二)社会分层与品位实践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李春玲发现,学界对社会分层理论的关注重点呈现出冲突论与功能论分层观的交替轮动现象,两种观念的代表理论分别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12]。相比于马克思,韦伯更强调阶层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权力和声望,这也为多领域分层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社会分层的测量方面,学界公认其指标包括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但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户籍对我国社会分层及流动的影响极为深远。除此之外,老年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在影响其社会分层的因素中,职业因素重要性趋向减弱,而客观健康状况发挥了更加强有力的作用[13]。
在布迪厄的阶层理论中,他认为阶层指的是社会空间中身处相似位置、具备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在同一组合中的个体拥有相似的秉性和实践[14]。由于具有不同品位,不同社会层次个体在消费选择上亦存在分层,从而导致同一性质消费发挥的具体效用也可能不同。因此,不同老年群体在养老服务设施的选择上以及相同服务的具体效用上可能存在差异。
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从供给角度看,现有养老设施到底更能满足高层次需求,还是更能发挥基础保障作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目前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依旧面临缺乏标准、服务种类不全、城乡建设进度参差不齐等现实困境,更有可能发挥局部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作用。但也正因如此,过于基础的服务可能无法满足高主观健康和社会资本需求个体。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并提出如下单边假设。
H3:在户籍层面,养老服务设施对城市老年群体的福祉增进效用更强。
H4:在收入层面,养老服务设施对低收入老年群体的福祉增进效用更强。
H5:在客观健康层面,养老服务设施对客观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群体福祉增进效用更强。
H6:在教育层面,养老服务设施对低教育水平老年群体的福祉增进效用更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涉及两个数据集,通过省份代码进行匹配,达成省份层面的宏观数据与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相结合的效果。
1.2018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本文在处理个人绝对收入指标时采用均值插补法,以避免由于个人收入过低或过高而拒绝填答所导致的结果失真。由于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总量为4 419个,样本量较大,因而上述剔除操作对研究结果并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2.2017年全要素POI数据
本文基于历史POI数据(原始数据取自谷歌地图)展开分析,每条原始POI数据都包括经度、纬度、设施名称、地址、设施类型、省市行政区等属性。考虑到CGSS问卷采集实际时间多为2017年,因此本文选取2017年6至7月的POI数据开展分析。参考《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国家标准GB 50867—2013)》《养老服务设施分类及标准》,对原始数据进行关键词筛选,①在数据清洗和筛选完毕后得到5 244、4 764条数据。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研究原始地图数据来自OpenStreetMap(OSM),并进行了投影校准处理。
(二)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见表1)
1.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重要的主体性感知,更多通过个体评价来展现。根据CGSS 2018所设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将选项“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依次赋值为1—5。
2.核心解释变量:养老设施核密度对数
本文参考汤国安和杨昕(2012)等学者研究,通过对地理信息的空间密度分析,考察不同省域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聚集特征变化。相比于点密度,核密度将三维空间因素纳入考量,设施离中心越近则权重越高,有效避免了孤立测度的问题,同时较好展现了不同性质设施间的协同效果。
借助GIS进行核密度分析、分区统计等操作,得到双变量等值区域地图。由图2报告分析结果可以得到,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半数省份(深灰色图块)趋向一致,说明两变量有较大可能存在相关关系。考虑到以宏观形式呈现变量关系忽略了个体异质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究。
3.控制变量:选取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如下
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拥有房产数量、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和社会信任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相对收入。
4.工具变量: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对数
养老服务设施密度指标存在一定内生性风险,其可能与各省份GDP有关,而各省GDP会同时影响老年群体生活水平与老年人的主观感受。因此,本文选择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对养老服务设施的建造状况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对于不从事重体力劳动且安土重迁的老年群体来说并不存在直接影响。
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不难发现,老年群体总体主观幸福感较高,均值为3.959,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标准差为0.834,说明个体间幸福程度依旧存在差异。在核密度分布方面,养老服务设施在区域内的集聚状况良好,大部分区域核密度范围在116.400—163.200之间,①但从标准差可知,部分省市数值可能存在较大范围偏移。
(三)模型设计
为研究养老服务设施核密度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并便于后续多种方式检验,本文主要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
happinessijk=β0+β1lnDensityk+β2Fj+β3Xi+ε
其中,下标i表示老年人个人,j表示家庭,k表示省份;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老年人幸福感,Density为各省养老设施的平均核密度值;X代表个人特征控制变量,F代表家庭特征控制变量,β1、β2和β3分别指代养老设施核密度以及各层次控制变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ε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分析
出于严谨性考虑,本文在OLS回归基础上加入有序Probit、有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以形成互证,详见表2。其中,(1)、(2)、(3)列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4)、(5)、(6)列增加了个人及家庭特征。研究发现,在不同模型条件下,核密度变量的系数始终为正且在统计学意义上保持显著。在控制个人与家庭特征后,整体关系并未发生改变,说明省域范围内养老服务设施密度增加有利于老年人幸福感提升。
(二)稳健性检验
主观幸福感可分为正向幸福感和负向幸福感[15]。其中负向幸福感代表老年群体对生活的消极态度。为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衡量尺度进行替换,由主观幸福评级改为感到沮丧频率,②不改变其他变量并重新进行回归处理,得到如表3所示结果。由(1)、(2)列结果可知,养老服务设施密度越大,老年群体感到沮丧或抑郁的频繁程度越低。该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照应,表明各模型结果不受度量方式影响,可信度较高。
表2所得基准回归结果能够初步展现核心变量间的潜在关系,但若直接断定养老服务设施核密度是老年人幸福感变动的影响因素则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较为庞杂,研究过程中极易发生遗漏变量问题,如经济进步在换取边际幸福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扩大养老服务设施建造规模。为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工具变量,以同时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要求。
表4展示了模型的2SLS结果,其中,列(1)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进行全样本回归操作,列(2)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列(3)控制了全部变量。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能够满足基本检验需求;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并不存在不可识别或弱工具变量问题。从整体结果来看,养老服务设施核密度与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确实存在强正向关系。
综合以上多项稳健性检验,本文认为内生性问题并未对研究结论产生根本影响。
(三)机制检验
以往文献表明,健康因素对潜在幸福至关重要,护理和助养型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老年群体(特别是失能老人)的生理健康需求。机制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主观健康状况切入,列(1)和列(2)结果显示,养老服务设施核密度值每上升1%,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评价以及生活免受健康问题指标就会在1%显著性水平上分别上升0.047%和0.132%,说明养老服务设施能够发挥健康照护作用,能够疏解老年群体病痛。
已有研究发现,家人、邻居、朋友的社会支持网络能够提升老年人自尊感和恩情感,缓解内在孤独感与被排斥感,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16]。依托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居养型和社区型养老服务设施能够增强安全感与归属感,提高老年人与周边社会的融入程度;而娱乐型养老服务设施则针对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参与需求提供沟通交流平台,解决老年人的认知以及孤独感问题。为验证其实际效用,本研究开展相应检验,结果如列(3)和列(4)所表明,交际频率以及参加文化活动频率会随养老服务设施核密度提升而增大。综上可知,养老服务设施能够依托社会网络,扩大老年群体社会资本,发挥物质支撑和精神滋养的双重效用。
由表6可知,不管控制主观健康状况还是交际频率变量都会对核密度系数产生影响;而在影响程度方面,相比于列(1)原回归结果,健康条件的作用更大,其使得原始系数下降了28.9%。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低层次需求满足优先度高于高层次需求。尽管社会资本变量与之相比更为弱势,但在控制上述所有机制情况下,系数降低了31.1%,说明两者均发挥了关键作用。综上所述,H1和H2得到印证。
四、养老服务设施福祉的异质性分层讨论
最后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是养老服务设施究竟能够“济困”还是“求精”。
(一)户籍类别异质性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依旧存在,户籍制度的遗留问题使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将总体样本按照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个子样本,①分别计算城乡养老设施核密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表7结果显示,养老服务设施核密度系数在非农户口组为0.030,并在5%水平上显著,而农村户口组未出现显著效应,由此H3得证。
(二)收入水平异质性
个人的经济状况也是影响幸福体验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收入水平划分标准,按照年人均收入将老年群体划分为“低、中、高”三类人群,并进行分类回归,得到列(3)—列(5)结果。研究显示,除中等收入群体外,低收入及高收入老年人群主观幸福感均不受养老服务设施核密度变化的影响,由此拒绝H4。
(三)客观健康状况异质性
不同阶层的客观健康状况通常存在群体异质性[17],相对应护理服务的需求及选择亦会趋向不同。因此,本文借被访者2017年前往医院次数这一客观指标,②反映老年人客观健康状况。表8结果显示,客观健康状况相对较好(未去医院)以及较差组别(3次以上)的核密度变量系数均不显著,由此拒绝H5。
(四)教育水平异质性
教育作用于老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制约或激发不同阶层趣味偏好,从而使社会网络支持力度出现差别。列(4)和列(6)显示,受教育水平处于上层和下层组别的核密度系数在1%和5%水平上显著,值分别为-0.095和0.036。该数据表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更乐意享受养老服务设施所搭建的社交平台,而高教育水平老龄群体幸福感反而会随地区养老服务设施密度增加而降低,由此H6得证。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空间地理分布视角切入,通过匹配省级层面养老服务设施核密度与个体层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指标,运用OLS回归模型检验了各省域内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对不同群体的异质性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证明,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该效应发挥主要依托主观健康和社会资本两大路径。其中,设施对农村老年人发挥效用相对较低,只有中等收入和中等客观健康水平老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能受到设施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设施对低教育水平老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作用,对高教育水平老龄群体反而发挥负向效用。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未对不同类别设施进行探究,POI数据也无法体现更为细致的设施性质相关信息。其次,本文受制于客观数据,选取时间节点为2018年前后,因此在将结论推用到当下情境时需要秉持谨慎态度。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考虑省域协同、优化养老服务设施整体布局
政策的施行并不是“铁板一块”,应在规范指引基础上适当放权,鼓励执行单位因地制宜寻找特色发展模式,实现“同路不同车”。
(二)强化以需求为导向的养老服务资源供给
为弥合供需不平衡现状,相关部门应当事先开展大规模养老需求的社会调查。
(三)强化新型养老观念普及,实现幸福公平
农村老年群体对养老设施的普遍印象大多停留在传统养老院或乡村老年活动中心,以致农村养老产业活力难以激发。只有优先创造合理需求,才能吸引资源搭建平台。政府的应急性以及先导性投入是必要的,但长期永续发展仍需要依靠社会多方资本整体统筹运转。
目前“农村老龄化”问题已随人口迁移愈演愈烈,这预示着农村地区蕴藏着海量消费潜能。政府应当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使得农村发挥承接城市养老压力作用;另一方面,加紧开拓农村养老产业“蓝海”,通过新媒体渠道加速农村老龄人口树立新型养老观念,推行居家养老、互助养老或将养老机构有机嵌入乡村等改良方式。
参考文献:
[1] Kim D,Jin J. The Impact of Welfare Facilities on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Evidence from Seoul,Korea[J].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2019:0739456X19874112.
[2] Hardin E,Khan-Hudson A.Elder Abuse—“Society's Dilemma”[J].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2005,97(1):91-94.
[3] Quan N G,Lohman M C,Resciniti N V,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Interventions for Loneliness Among Older Adults Living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J].Aging & Mental Health,2020,24(12):1945-1955.
[4] 严晓萍.美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启示[J].社会保障研究,2009(4):19-25.
[5] Lai C K Y,Leung D D M,Kwong E W Y,et al.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of Nursing Home Residents in Hong Kong[J].International Nursing Review,2015,62(1):120-129.
[6] Angner E,Ghandhi J,Williams Purvis K,et al.Daily Functioning,Health Status,and Happiness in Older Adults[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3(14):1563-1574.
[7] Allmark P.Health,Happiness and Health Promotion[J].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2005,22(1):1-15.
[8] Angner E,Ray M N,Saag K G,et al.Health and Happiness Among Older Adults:a Community-Based Study[J].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2009,14(4):503-512.
[9] Ovaska T,Takashima R.Does A Rising Tide Lift All the Boats? Explaining the National Inequality of Happiness[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10,44(1):205-224.
[10] Bourdieu P.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
[11] Bj?rnskov C.The Multiple Facets of Social Capital[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22(1):22-40.
[12] 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70 年[J].社会学研究,2019,34(6):27-40.
[13] House J S,Lepkowski J M,Kinney A M,et al.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Aging and Health[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4,35(3):213-234.
[14] Bourdieu P.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J].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32:1-17.
[15] 胡洪曙,鲁元平.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2(11):41-56.
[16] 陈立新,姚远.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5,29(4):73-78.
[17] Isaacs S L,Schroeder S A.Class-the Ignored Determinant of the Nation's Health[J].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4,351(11):1137-1142.
“Help the Poor” or “Strive for Excellence”
—Elderly Service Facilities and Stratified Well-Being
XU Ruyue, RONG Kex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old age. The construc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not only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actual service needs. Based on the 2017 total factor POI data from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2018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 the impact and differences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ifferent elderly groups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matching provincial and individual level data.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only the moderately healthy, middle-income, and low education groups belong to the target group of facility effectiveness, and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facilities on rural elderly people is relatively low.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thresholds and limits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existing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in promoting welfare,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not “help the poor” or “strive for excellence”; when formulating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 dual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focusing on optimizing the overall layou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of demand oriented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and deepen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 elderly care concepts.
Key words: Elderly service facilities;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stratification
[责任编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