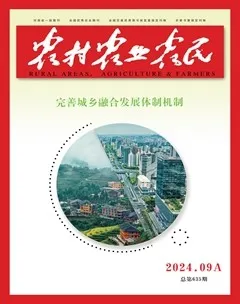传统农业与中华文明(上)
农业的出现,具有“人猿相揖别”的划时代意义,人类缘此由单纯的自然攫取者变为经济生产者。农业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是维持和延续人类生命的基础产业。人和人类的农业活动构成互为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在人类的关照下某些优质农林牧业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与利用,而人类也缘此获取了赖以生存与繁衍的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
在悠久的农业历史进程中,中国农业逐渐形成了农牧结合的产业结构,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礼乐规范的约束机制,休戚与共的群体观念,家国同构的宗法范式,循序行事的月令图式,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和谐观念,吾以观复的圜道理论,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独具特色的丝茶文化,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中国传统农业与农学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基本思想理论与指导原则,既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术体系,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精神价值取向,这些精神与物化的总体表达是谓农业文明。
农业的基本特质
农业与工业。农业是指人类利用生物的生长机能,采取人工培养和养殖的办法以取得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而工业是对自然界资源和原材料进行利用和加工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农业是人类获取衣食的产业,工业虽然可以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减轻人类的劳动强度,但是目前尚不能从根本上提供和解决人类的食物问题。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农业与工业都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农业是必需条件而工业不一定是必需条件。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生物活体,生命秩序不能超越和逆转,生命活动构成农业的基础。农业的主题词是养育,遵循生物学和生态学规律。工业生产一般是利用器械直接加工生产对象,使之变成新样态的器物。工业的主题词是制造,遵循物理学和化学规律等。农业生产以土地为平台,直接依存于自然环境,从而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和严格的地域性。工业生产大多在厂房内进行,不太受季节和地域的限制。生物及其生命形式只有在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的整体中才能存在和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力核心的生物生产力,不是以生物个体生产力的形态而是以生物群体生产力的形态出现的。农业生产讲究的是对生物及其环境条件的顺应、利用与控制。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较,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相互交织的特点。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物本身具有其自身的生长、发育和繁衍的规律,所谓的农业劳动只是对动植物的养护与关照而已,人类并不能替代动植物的生长与发育过程。天下人莫不希望自己的禾苗长得快一些,然“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苗则槁矣,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农民开辟了农田并在近便的地方建立定居村落,形成农业与农村、农民的相互依存。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相互渗透,是人的生命活动与物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融。农民生产、生活的圈子不只是村落和农田,他们还要从周围的山林、水体获取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猎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定居的农业则催生了人工生态系统。乡村人工生态系统由村落系统、农田系统和自然的山林系统、水体系统等组成,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生态,但它又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建立和运作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生产节律、生活节律和生命节律、自然节律是一致的。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商。农民是农产品的生产者,而农产品又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然而农民很少有巨富产生。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业生产的周期固定性。与古代的采集渔猎和现代工业生产的“即获”性特征相比,农业生产的由种到收呈现出明显的“断续”性特征。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畜牧产品从出生到育肥出栏等,均有相对固定的周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与管护过程,若遇天灾人祸甚至有绝收之虞。这或是古人好狩猎、今人喜进城的缘由之一,因为狩猎与打工可以马上有收益,谁会舍近求远呢!农业的断续与周期性生产,拖延了生产时间,制约了生产规模的伸缩性。当农产品偶遇较好价格,农民无法迅速扩大其生产量,常常只能望利兴叹。而非农行业则常能抓住时机,获取巨额利润。二是农产品功能的稳定性。农产品的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功能的稳定性就会使消费者抵制农产品的涨价。而工业品的功能在不断变化,随av4zZxMHqJqDzm9Y1OT9nA==着功能的变化价格也会不断提升,消费者欲享用新功能只能被动地接受涨价。三是对农产品价格的人为干预。农产品是关系人们生存的一种特殊产品,如果农产品价格暴涨,则会影响一部分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因此,当农产品价格剧烈上涨时,政府便会出面干预,通过各种措施平抑物价。四是农产品总的发展趋势是要供过于求。理想的社会发展态势是人人都要丰衣足食,而丰衣足食的前提是农产品要有少量过剩,农产品的过剩又必然导致其价格下跌。农产品的供过于求,既是农业发展的目标,也是农业经营的悲哀。五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缓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十分缓慢的,农作物在万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经人类不断优化选育,但产量的提升空间毕竟有限。猪鸡牛羊提供的肉蛋产品,几千年来的生产速率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农产品就无法像工业品一样通过薄利多销来获取较高利润。农民的比较效益较低是由农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农民的富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而政府保护农业的前提是非农行业的充分发展。只有非农行业有了充分发展,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优势份额,才可支持和保护占份额极小的农业。当农业的份额还比较高时,非农行业是无力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而,农民及农业脱贫的根本出路不在农业内部,而在农业之外的非农行业。
农业的多功能性。如果单从农业经营绩效看,古人已知“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但是人毕竟是要吃饭的,尽管当今人类的经济活动已高度非农化,人们对粮食之外的消费需求日趋增加,但粮食的不可替代性永远不会改变,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永远不会改变。这或是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类尽管遇到过诸多的艰难险阻,却不忘初心地向着认定的目标前行的基本原因。
《吕氏春秋·上农》篇曰“民农非徒为地利也”,对除经济之外的农业多样性功能的认识,或是中国传统农业思想中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农业是个政治问题。食为政首,农业出了问题就会闹乱子。农业是个社会问题,《上农》篇借中国农神后稷的口气说“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农业的社会稳定与秩序功能,因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农业具有文化传承教化功能。农业文化是民族性的特色文化,工业文化是世界性的通用文化。农业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产业,农业是民德归厚的精神家园,农业是亲近自然的绿色净土。农耕文化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体,现代化不能割断历史渊源,不可废弃优良传统。今日之忧,或在农产品需求日增而知农事者日寡。农业的教化功能,旨在鉴古知今、继承创新。在现代社会,农业的生态环境功能、休闲观光功能等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农业的多样性功能是对农业经济功能的修正与升华,农业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与利润的产业(即使亏本也要生产),这是认识论上的科学回归。
“三才”理论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见诸《吕氏春秋·审时篇》。《吕氏春秋·上农四篇》或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谈论农业问题的,但是它甫一面世即非同凡响。《上农》等四篇篇名,本身就包含了农业生产中非常重要的四大基本要素:《上农》讲的是重农思想和政策;《任地》讲追求优质高产;《辩土》讲农业要因地制宜;《审时》讲农业应趋时、顺时、得时。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诸问题,虽历数千年仍是中国农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值得重视的基本思想认识与行动准则。学术界对它们的评价是:这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完整的农业论文;这是先秦时代尤其是战国以前农业思想、文化与科技的一个光辉的总结;它所记述的精耕细作农业科技体系直接为后世所继承与发展,等等。其实最关键的是它提出的“三才”论,科学地概括了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并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对农业的自然与经济再生产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由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农业的中国传统农业科技体系。
农业生产和天地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关于天地人关系的“三才”思想,很可能是从对农业生产的理解中产生的。“三才”观念源于农业的生产实践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农业生产诸要素的整体思维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规定和影响了中国农学发展的方向。这些思想与认识后来表达为天时、地利与人和。既有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又充分表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三者各司其职,和谐共处。中国农学讲究“顺天之时,因地之宜”“盗天地之时利”,就是主张按照农作之情性,依据客观规律选择和调整它们与天时、地宜的关系以及它们自身之间的关系,使这些生态关系达到最佳,从而获得好的收成。由于把人和自然不看作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中没有犯颠覆性错误,没有发生中断,保证了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文明能存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与农业
中国古代有关天的论述,分别包含了神学天、自然天、命运天等不同内容。神学天,决定王朝更替和族姓兴废;命运天,决定死生祸福,穷富显微;自然天,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自然天的最大特征和本质内容集中表现为一定的时序。因此,我们往往把天称作天时(天道运行的时序)天气。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为最主要的社会实践,这时天时的意义主要在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我们的先贤将农作物置于宇宙大时空体系之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天时对农作物发育的影响和决定作用。要保证农业增产、丰收,最重要的事情是将时序记录准确,以便时至则作,时竭则止。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我们的祖先已十分重视季节的变化对农作物和其他人事活动的影响,并对天象和物候做了相当细致的观察和总结。关于农时方面的大量农业技术资料表现出我们民族一种十分重要的思维趋向,就是坚持把万物的运动与广大的宇宙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而且特别注重考察事物变化发展过程的时间节律,特别重视时间因素对事物的意义。元朝的王祯总结历代关于历法和授时的论述,并设计了一张《授时指掌活法之图》以指导人们适时耕作。农业最重视二十四节气,而物候历和二十四节气结合得最为紧密。
阳历与阴历。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点,决定了它与天地日月的密切关系。但是东西方却走了不同的路径,西方选择了阳历而东方选择了阴历。古埃及人由于计算尼罗河泛滥周期的需要产生了太阳历,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其优点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回归年的长度。但是以太阳视运动为依据设置的历法,不易于观测与把握。除少数天文、星相专家外,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一年365个日升日落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异。中国人按月相周期来安排历法,他QOAnykeaOXslPog/kwyd9A==们以朔(无月为朔,每月的初一)和望(满月为望,每月的十五或十六日)为基础把一年划分为12个月。以月亮的视运动规律为依据设置的历法,充分利用了月亮的盈亏周期,较之阳历更易于辨识使用。但阳历的缺憾在于无法体现月相的变化,而阴历的缺陷在于无法体现四季的变化,二十四节气的设置搭建起了阳历阴历沟通的桥梁。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的独特创造,它把地球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以相应物候体现四季变化。又通过置闰,使得阴历和阳历之间的差距得到调适。阴历加上二十四节气之后,变成了阴阳合历。《淮南子》一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记录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虽然以月相观察为主,但节气却对应了自然界的四季变化,因此在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中被普遍使用。
“夏数得天”。在中国先秦历法中,一般认为“夏数得天”。当时有所谓的夏历、殷历和周历,三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岁首的不同,又称“三正”。周历以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冬至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大寒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农历正月,雨水月)为岁首。由于三正岁首的月建不同,因此四季也不同。刘知几在《史通》中说“春秋诸国,皆用夏正”,大概是因为夏历既符合春夏秋冬阴阳始终之明又以万物之生以为四时之始,所以比较通行,盖取其易知易行也。
黄河流域与二十四节气。由于历史上中国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农业活动中心多集中在黄河流域,二十四节气应是以这一带的自然气候状态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二十四节气所反映的季节变化(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物候状况(惊蛰、清明、小满、芒种)、雨雪情形(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气温升降(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都与这一带的农事活动有着极高的契合与对应性。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认为,二十四节气很可能是“以黄河中上游(可能主要还是关中地区)气候条件为分段标准,所以根据二十四节气来安排这个地区的农事活动的年计划,是非常适合需要的”。
[责任编辑:李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