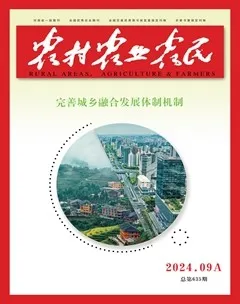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与构建
摘 要:新乡贤文化的培育和构建既需要传统乡贤文化的滋养,也需要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下作出制度安排。厘清绅士—乡绅—乡贤—新乡贤发展脉络,梳理自发性乡贤文化和制度性乡贤文化,落脚点都在构建当代“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的构建既要对新乡贤“从哪来”“怎么用”作出制度性安排,也要培育自发性“新乡贤文化”,激活新乡贤的内生动力,着力培育新乡贤文化主体、搭建新乡贤治村平台、增进新乡贤文化认同。
关键词:新乡贤;乡贤文化;历史源流;乡村振兴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包括“七个着力”的具体要求。其中“第五个着力”是指“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在纷繁浩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乡贤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乡贤对于维护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乡贤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新乡贤文化,吸引和激励新乡贤深度融入乡村建设,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梳理乡贤文化的历史源流,挖掘自发性乡贤文化传统与制度性乡贤文化传统的形成机制,或能为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提供方法借鉴。
一、乡贤文化的历史源流
王先明先生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一书,明确将“绅士”界定为一种特定的社会阶层。这种“绅士”作为阶层身份的获得必须是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等,并具有一定的特权。有的绅士居住在城市,有的则居住在乡村,故而称之为“乡绅”。因乡绅或推恩于里党,或树德于桑梓。所谓“绅而富,以财济于乡;绅而耆,以德式于乡”;故称“贤”,谓之“乡贤”。这就是“乡贤”一词的由来。
古代乡贤文化,从官方和民间不同的视角,可以分为“自发性乡贤文化”和“制度性乡贤文化”。所谓自发性乡贤文化,是站在民间的立场而言的,是乡贤自发、积极地主导、参与乡村公共事务,造福桑梓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传统。所谓制度性乡贤文化,是站在官方视角而言的,是一种推选、祭祀、书写乡贤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
(一)自发性乡贤文化传统
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发性乡贤文化传统的兴起,建立在农业经济相对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农业生产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地方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使得地方社会能够支持一定数量的非农业人口。宗族内部的经济互助和财产共有,为乡贤提供了经济支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古代“皇权不下县”,地方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乡贤能够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如管理地方公共工程、慈善事业和教育等。
梳理而言,乡贤文化的雏形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社会结构以宗族和村落为单位,村落中的长者或是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往往能在村务管理、解决纠纷、教化村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德治”理念得到推广,地方上的乡绅、儒生等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德行和学识影响和治理乡村,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乡贤文化。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许多“未能进入”或“已退出”中央或地方官府的士人回到乡村,成为乡贤的主体。明清时期,乡贤文化达到鼎盛。这一时期,乡贤不仅是乡村社会的管理者,也是乡村文化和道德的维护者。他们采取建立宗族祠堂、编纂族谱、修建学校等方式,维护和传承地方文化。传统知识分子于“得君行道”之外,另辟一条“觉民行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实现修齐治平理想的新路径。一般来说,“乡贤们”或积极兴办乡村教育,民间的义学和义塾成为乡村教育的重要力量。明代的泰州学派,更是高举“觉民行道”的大旗,要重塑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或积极参与乡村慈善事业,好善乐施、救灾赈灾,通过义庄、义仓救助百姓,在民间获得很高的声望。或通过德行、礼仪教化乡里,具有影响力的乡贤往往通过制定族规、乡约来化民成俗,一种自发性乡贤文化传统蔚然成风。
(二)制度性乡贤文化传统
从官方视角而言,对乡贤与乡贤文化作出制度性安排,代表了乡贤文化的逐渐成熟,时间不晚于汉代。汉高祖时期,就下诏推举“能帅众为善者”为“三老”。《汉书·高帝纪》记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传统中国的政治是“双轨制”——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政府的政令一旦与下层民众接触,就会落入“乡约”的特殊轨道,乡贤具有很大的效力。《汉书·高帝纪》的诏令为“三老”设置了推选标准,规定了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以及可获得的相应特权和礼遇,这可以说是“乡贤”参与治理最早的制度性安排,是制度性乡贤文化传统的开端。唐宋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加之民间书院的兴起,乡贤逐渐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唐以后中国社会是“科举社会”,宋以下甚至可以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绝大多数科举录取者是民间出生的白衣举子。白衣举子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受到皇权的重视。为优化与乡贤的权力合作,皇权为乡贤参与乡村事务作出更多的制度安排。并且,出现了“祭祀乡贤”的制度,宋代开始有专门祭祀乡贤的“乡贤祠”,刚开始还是由民间发起,到明代实现了制度化,开始由官方大力推动地方建设乡贤祠。为与“名宦祠”区分,官方甚至明确:“仕于其地,而在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乡贤的推选流程较为复杂,从推举、商议、审定、复核、批复,有一整套规范,官方和民间都非常重视,希望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达公论”。另外,“书写乡贤”的制度也值得注意,即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名录、传记、碑铭等表彰乡贤,以遗风化俗,敦厚乡里。因记录乡贤、书写乡贤,逐渐构建出对后人有极具劝勉作用的乡贤文化。被推举为乡贤、进入乡贤祠,成为许多士人终生的梦想,所谓“死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显然,制度性的乡贤文化的构建,是这种人生理想的幕后推手。
二、乡贤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2014年,《光明日报》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从此“新乡贤”这一概念被广泛讨论并接受。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传承乡贤文化传统,培育新乡贤文化。从方法论而言,自发性新乡贤文化和制度性新乡贤文化的构建缺一不可。
乡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儒家文化传统以及科举制度等紧密相关。它强调的是地方精英在地方治理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知识和道德的价值观。在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文化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价值和意义在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中仍然被重视。
(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激活自发性新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近年来,国家倡导新乡贤文化,将新乡贤视为当代乡土的守护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乡贤之“新”,首先就表现在与古代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乡贤”不同,他们既传承传统乡贤文化,造福桑梓,为民众所广泛认同,又跳出了传统乡贤由阶级和阶层意识所伴生的狭隘、闭塞、本位的思维局限,以民主和平等取代高高在上的特殊身份,放下“架子”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格局中。当代乡村社会的新乡贤,并非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更为恰当的定位应该是乡村社会的一个新群体,新乡贤自身则将其看成一种“荣誉称号”。自发性新乡贤文化的培育,需要以乡缘、血缘、业缘为纽带,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助力乡村发展的意愿,以激活新乡贤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为重点。
(二)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构建制度性新乡贤文化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阐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在之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新乡贤”的作用渗透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中。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通过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借助乡情纽带,将有情怀、有能力、有资源、有文化的“在村的”或“在外的”贤达人士整合起来,参与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构建制度性新乡贤文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重要政策背景是现代基层的自治制度,可以说“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已经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打开相应的制度空间。然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尚需准确把握。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不能“窄化”为“慈善公益”,不能“泛化”为单向付出的“好人好事”,而应建立起较为科学的治理机制。这种科学的治理机制,不是否定现有的乡村治理的组织架构并取而代之,而是为新乡贤在民主协商、经济合作、文明教化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搭建平台、提供制度保障,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打通“最后一公里”。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要继承和弘扬乡贤传统,倡导“知乡贤”“颂乡贤”“学乡贤”的文化氛围,写好新时代新乡贤的动人故事。
三、培育构建新乡贤文化的策略建议
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下,新乡贤作为自治和德治的重要力量,加之自带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技术资本等资源属性,又有城乡融合的“文化中间人”角色定位,是应对乡村的治理困境、资源匮乏、人才缺乏、文化凋敝等问题的解决思路之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的价值越发被重视,需着力培育新乡贤文化,充分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
(一)培育新乡贤文化主体
在培育新乡贤文化主体时,既要注重传统乡贤与新乡贤的内在传承,传承和发展乡贤文化自发性传统和制度性传统中合理、积极的部分,又要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新乡贤文化主体的界定,应符合最大限度发掘、整合乡村社会资源的需要。当代新乡贤的群体来源,不应过多设限,一般来说,大抵有三种方式:或经普查——筛选,或经推举——聘选,或经申请——评选。根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分类标准,规范程序流程。在新乡贤的各种分类的尝试中,按照“空间”和“价值”分类,与新乡贤的培育、使用关系最为紧密。
按照“空间”不同,新乡贤可以分为“离土”和“在土”两类。其中“在土”的新乡贤又可以细分为“本土”与“外来”两种。“在土乡贤”,因人熟、地熟、事熟的“在地化优势”,具有深度参与乡村实践的现实可能性。“离土乡贤”因长期不在乡村生活,深度参与乡村事务并不现实,更多的是在“资源下乡”“建言献策”“提供资源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对于“离土”新乡贤,一般通过家乡发展促进会等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值得注意的是,家乡发展促进会这类资源型组织,并不一定局限在资金资源,还包括政策、信息等其他形式的资源。
按照“价值”不同,新乡贤可以分为“富乡贤”“文乡贤”“德乡贤”“技乡贤”等,不同类型的新乡贤群体的推选、培育、使用应有不同的侧重。要着重引导“富乡贤”侧重经济资源导入,“文乡贤”侧重乡土文化传承,“德乡贤”侧重乡风文明涵养,“技乡贤”侧重乡村产业带动,为其助力乡村振兴搭建平台与舞台。
总而言之,新乡贤的涌现需要我们用好“乡缘、血缘、业缘”纽带,面对“离土”新乡贤回流难、“本土”新乡贤遴选难、“外来”新乡贤引进难的现实困难,要采取明确标准、盘点摸底、引流遴选、搭建平台、广泛宣传、机制保障等方式不断培育、挖掘新乡贤主体,培育新乡贤文化。
(二)搭建新乡贤治村平台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也需要制度化的途径和平台,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运作机制。古代的“三老制度”,正是乡贤治乡的一条制度化途径。当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很多,比如浙江省常山县的“归雁计划”,直接推出“贤人治乡”,推选新乡贤进入村“两委”。但毕竟“两委”人员有限,为用好乡贤资源,新乡贤各类组织的培育不可或缺。散兵游勇终究独木难成舟,搭建好组织和平台,才能更好发挥效能,促进新乡贤文化的良性发展。
鉴于“离土乡贤”和“在土乡贤”的不同情况,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也分为“强参与”“弱参与”,应有不同的组织承载。一般来说,当代新乡贤组织有家乡发展促进会、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等。家乡发展促进会属于资源型组织,侧重于在外新乡贤的资源整合,为“离土乡贤”建立回归故乡的通道。乡贤工作室则属于日常型工作平台,以半官方的形式参与各种具体乡村事务。更具复杂性或综合性的乡贤理事会等组织,既是作为乡村治理的参事、议事机构,同时又是作为新乡贤团体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组织载体。这类新乡贤组织发起和运行需由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牵头,对其规范运行给予支持与监督,使新乡贤组织在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扮演好村“两委”的“协同者”这一角色,既不至于越俎代庖,又能促进新乡贤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增进新乡贤文化认同
培育新乡贤文化的关键是如何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助力乡村发展的意愿,重点在增强新乡贤的乡缘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
增强乡缘认同是基础。不管是现在的“村BA”“村晚”还是“家乡联谊会”各类形式活泼、情感真挚的文艺活动,乡缘都在被不断创造的“共同叙事”中更加鲜活起来,以增强更深的乡缘认同。增强身份认同是路径。赋予“新乡贤”身份标签,通过美丽屋场、文化长廊、乡贤名录等平台,不断书写新乡贤故事,不断加强新乡贤的身份认同,并通过知事、理事、议事来增强参与感和认同感。增强价值认同是归宿。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多数并没有具体的经济目的,更多的是来源于内心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求。从高层次需求出发构建起的价值认同,是深层次、牢固、稳定的认同。要从高层次需求入手,进行培育和引导,加强乡村振兴与新乡贤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正向关系,激发其蓬勃动力。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59-68.
[2]钱穆.国史大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69.
[3]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9.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23-32.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2-24.
[6]游子安.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J].中国史研究,1997(4):127-133.
[7]孙敏.乡贤理事会的组织特征及其治理机制:基于清远市农村乡贤理事会的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49-55.
[责任编辑:樊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