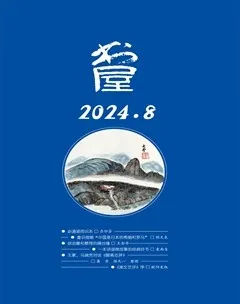侠骨柔情
一
春寒料峭的清晨,捧着热咖啡,望着窗外,风儿拂过树梢,落在花瓣紧闭的郁金香上。心中却满是失落。多么怀念从前清早起床,顾不得一切,开门飞奔出去在车道上拿起前一天的报纸,一边奔回家一边将报纸上的封套取下,进得门来,边看报边喝咖啡的愉悦。自2023年秋天起,《世界日报》取消了华府地区的办事处,送报改作邮寄。看的是一周之前的报纸不说,缺漏更是常事。新闻早已陈旧不堪,只剩了艺文版与数独,永保新鲜。
在这样令人心灰意冷的日子里,我一再重温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从私家侦探马洛那里重拾勇气与信心。这一次,我读《漫长的告别》,除了无论面对怎样的威逼利诱都不肯趋炎附势的侠义之外,还有对一个全然陌生之人的理解与同情,里面也隐含着马洛这一位硬汉内心的波澜,柔软而温暖。在寒冷时节,这本书格外迷人。
小说一开篇,我们看到虽然年轻却满头白发、半醉半醒、脸上有明显疤痕、遭人遗弃在水泥地上的特里·伦诺克斯。尽管如此狼狈,他却是马洛所见过的最客气、最有绅士风度的醉客。整本书,马洛与伦诺克斯在一次又一次的短暂相聚与告别中经历血雨腥风,经历他人的死亡,而最终永远地离别了,伦诺克斯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再不复见。“你深深打动了我,特里——凭一抹笑容、一颔首、一挥手或者在各处安静的酒吧静静喝几杯酒。别了,朋友。我不说再见。我在别有深意的诀别式中道过再见了。那时我道别,感觉很悲哀、很寂寞、很决绝。”马洛这样说。
话分两头,伦诺克斯的妻子西尔维亚是亿万富翁哈兰·波特的小女儿。将丈夫丢下,开车扬长而去的正是这位西尔维亚。马洛在西尔维亚被谋杀之后得到机会同亿万富翁见了面。哈兰·波特告诉马洛,他只想安静度日,不希望每天被纷纷来到的丑闻烦扰。不幸的是,他的两个女儿的状况都不妙,西尔维亚的婚姻只是将酒鬼伦诺克斯当作幌子,她自己实际上过着为所欲为的生活;另外一个女儿艾琳则嫁给了江郎才尽的作家韦德,另外一个酒鬼。波特不希望被丑闻包围,自然不希望马洛对西尔维亚的被谋杀穷追不休。
然而,马洛不会停手。因为他的恻隐之心推动他不惧任何威逼利诱,勇往直前。西尔维亚不但被谋杀而且被毁容。警方认为这是伦诺克斯在酒醉、意识不清的状况下造成的恶果。马洛不以为然,因为他绝对不相信伦诺克斯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伦诺克斯战战兢兢地拿着一把没有用过的枪敲开了马洛的房门,要求马洛助他逃逸,伦诺克斯坦陈自己没有杀人,而且将自己要离开的消息告诉了西尔维亚的父亲和姐姐,甚至给马洛机会报警。
在伦诺克斯登机之前,马洛说:“登机吧,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儿。”
“他强打起精神,全身变得很僵硬,慢慢转过身,回头望。他静静说:‘抱歉。这一点你错了。我要慢慢地上飞机。你有充分的时间阻止我。’”
当然,马洛有自己的见解,伦诺克斯没有遭到阻止,顺利地离开了。留下的烂摊子由马洛一手收拾。钱德勒就是会用这样传神的叙事与对话来点出危机的关键处。这也是钱德勒小说最为迷人的桥段之一。更不消说,就在那个机场,小说里另外两个人物出场了,恍然间,远远望见两个人影而已,却是重要的联结,下一起谋杀案即将揭开序幕。
马洛因为他的恻隐之心而进了牢狱,挨了重拳,却没有出卖朋友。获释的原因则是“伦诺克斯案已经结案,他在墨西哥一家旅社写了完整的自白书,并且举枪自杀”。警方这样告诉马洛,并且要他“闭紧嘴巴”。
谣言永远比一封邮寄的信来得快。马洛在他简陋的办公室外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人是特里·伦诺克斯:“……我写了一份自白,觉得有点恶心,而且害怕得很。你在书报上看过这种情况,可是书报上说的,毕竟隔了一层。事情发生在你头上,除了口袋里的枪什么都没有,你被困在异国一家肮脏的小旅馆,只有一条出路时——相信我,朋友,那可一点也不动人,一点也不精彩。只有龌龊、下流、灰暗和狰狞。所以忘了这件事也忘了我吧。不过请先替我到维多酒吧喝一杯Gimlet(吉姆雷特鸡尾酒)。下回你煮咖啡,替我倒一杯,加点波本威士忌,替我点根烟放在咖啡杯旁。然后把这件事全部忘掉。特里·伦诺克斯已成过去。再会啦。”信封里还有一张极为稀罕的“麦迪逊肖像”——一张五千美元钞票。
之后,大量的篇幅围绕着下一起谋杀案展开,凶手设计了重重叠叠的圈套。换句话说,马洛与韦德夫妇开始了相当频繁的接触,于是他们的长辈哈兰·波特约见了马洛,声明他认定是伦诺克斯杀害了妻子,并且强烈表示不希望有人继续调查。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1953年,钱德勒借波特之口谈论社会:“钱有个古怪的特性,大量的钱好像自有其生命,钱的力量变得很难掌控。人向来是一种可用钱收买的动物。人口的成长、战争的大开销、无止境的重税压力,正在使人越来越容易被钱收买。一般人疲劳又惊慌,讲究不起理想,他必须养家糊口。我们的时代公德和私德都在惊人衰退。”波特指出,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质量不会太高,商人不要好质量,嫌太耐久了,于是使用商业诈术,改变设计,造成产品过时的错觉,于是产品一年后变得不再流行,如此这般,新产品才有市场:“我们的产品包装举世无双,但里面的内容多是垃圾。”
我们读到这里如同在读近日的社会现实。何等敏锐!七十多年前,很多电子产品还没有诞生之前,钱德勒就已经精准无比地预见到今日社会的弊端。
小说继续展开,作家韦德“自杀”。没有被金钱蒙蔽眼睛的马洛继续他永不停歇的调查与思索。离开事发现场,钱德勒这样描述站在风口浪尖上的马洛:“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就像星子之间的太空。空洞又空虚。到家以后我调了一杯烈酒,站在敞开的客厅窗前,一面啜饮,一面聆听月桂峡谷大道的巨大车流,凝视大道附近山坡上空那刺眼的都市强光。远处警笛或救火车的不祥哀鸣此起彼落,难得肃静。”
世事吊诡而难解,马洛打破了波特先生的怪圈,证实了真正的凶犯正是百无聊赖的艾琳·韦德,她杀死了妹妹和丈夫,然后自杀。波特先生的家庭再无更多丑闻。
易容过后,只有眼睛的颜色还一如旧日的伦诺克斯最后一次站到了马洛面前。在伦诺克斯最终湮没于人海之前,马洛把那张巨额钞票还给了他。侠骨柔情的最后一丝痕迹也消失殆尽。
余音袅袅,时报文化在出版这本杰作之时,极为好心地附上了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长文。长文谈及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写作者对钱德勒和《漫长的告别》的观感。我站在钱德勒一边,带着挑剔的眼光阅读村上春树的“文学批评”,却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喜欢村上春树是有道理的。他的论述使得对这本书的阅读格外有趣、格外深邃,绝对可以祛寒。
二
米兰·昆德拉走了,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地点是巴黎。他离开的时候,人们认为他是法国作家,他的作品应当列入法国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当代最富于哲学思考的小说家,他始终关切着故国捷克,在六十七岁之后才开始用法文写作。
1929年,米兰·昆德拉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1967年发表小说《玩笑》,以戏谑的方式猛烈抨击专制制度,1968年参加了“布拉格之春”民主改革运动。这个运动遭到苏联的武装镇压。苏军占领布拉格之后,米兰·昆德拉上了黑名单,作品被禁。他在1975年抵达法国,并在六年之后成为法国公民。1989年,东欧剧变,跟着到来的是苏联解体。捷克需要再等待三十年,才会想到这位被迫离开捷克四十多年的伟大文学家。2019年,米兰·昆德拉在他九十岁高龄之际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身份。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法国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应当列入法国文学之林。他成为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由于其不断深入的哲学思考,他对小说艺术的见解愈见独特。
当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时候,他不是在写一位骑士的故事,而是在提出“人生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谜题。人生的帘幕在塞万提斯的笔下被掀开了,在堂吉诃德就要断气的时候,他的侄女正在忙着吃东西,女管家在喝饮料,而桑丘的心情也挺好的。这样的叙事是一种回忆、摘要、简化和抽象,而场景就在此时此刻展开了,让我们看见、听见、理解人生的真谛便是一场挫败。面对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挫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理解它。这就是小说艺术存在的理由。米兰·昆德拉这样告诉我们。塞万提斯写完《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后,数年内赞扬声四起。就在他准备好开笔写第二部之时,竟有人抢先写了续篇!塞万提斯怒不可遏,但转念一想,点子便有了。他开笔写第二部,在整本书结束前五六页的地方,堂吉诃德与桑丘遇到了一个窃贼,一个文字的剽窃者。于是,堂吉诃德面对了自己的幻影,一个不真实的存在。幻影面对本尊,瞬间裂成碎片,消失于无形。可见,塞万提斯能够让小说熔散文、滑稽剧、史诗于一炉。
米兰·昆德拉喜欢英语小说鼻祖菲尔丁(1707—1754)。菲尔丁在1749年完成他的代表作《汤姆·琼斯》,也就是拉伯雷完成《巨人传》两百年以后的事情,距离《堂吉诃德》出版也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了。毫无疑问,菲尔丁尊重并沿袭了前辈作家对小说的理解,但他的《汤姆·琼斯》却以小说来探讨小说理论,舍弃所有的学术名词,“小心翼翼”地为小说这门新艺术做出诠释。首先便是人性。小说存在的理由便是揭示人性,思考自然状态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模样。事实上,菲尔丁对人性的不可思议充满好奇,这种对发现人性之复杂的向往成为菲尔丁进行创作的唯一动力。因此小说创作成为一种认知行为,去发现人性中不为人知、被掩藏起来的那些面向,也就是“能够迅速而且智慧地洞悉作为我们冥想对象所有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作家依靠什么才能够迅速地做到这一点?直觉。那么小说的形式又是如何?“小说的形式是无人能加以限制的自由空间,它的演进发展给人的惊讶是永不停息的。”而且,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希望读者崇拜他们的美德,他们只是希望读者了解他们。米兰·昆德拉这样告诉我们。相信,很多现代小说作者根本不知道菲尔丁或者米兰·昆德拉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想一想,毕竟有益而无害。
《汤姆·琼斯》面世八十年后,巴尔扎克将读者变成了观众,其小说场景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魅力。紧跟着,小说的天空出现了灿亮的星斗,小说走进了伟大的世纪。果戈理、福楼拜、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等广受读者热烈赞叹的小说家的光辉使得拉伯雷、塞万提斯、菲尔丁们不再那么耀眼,这对于小说这一门艺术而言是吉还是凶,米兰·昆德拉颇有疑问。
“在群体意识中,小说的历史,从拉伯雷开始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就一直处于不断蜕变的状态。参与它的包括有能力的、能力不足的、聪明的、愚蠢的,但是统摄一切的,却是那片越来越大的遗忘坟场。在那些无价值的旁边还躺着被低估的价值、被误判的价值以及被遗忘的价值。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公正性使得艺术的历史深深带有‘人性’的印记。”
福楼拜让我们知道,琐细小事只有在进入小说之时,才能展示其神秘而巨大的力量。托尔斯泰则提早五十年展现乔伊斯的风格,安娜·卡列尼娜在“将脖子一缩,两手向前,跳落到车厢底下”之前,“有种感觉淹没了她,好像以前她去游泳的时候,正要下水的那一刹那……”。米兰·昆德拉赞叹道:“瞬间,严肃的气氛居然和如此平凡、轻盈、令人愉快的回忆混杂起来!安娜远远离开了古希腊悲剧,而没有离开散文那条神秘的幽径,那是美与丑并存的地方,理性让位给非逻辑的地方,谜面永远找不到谜底的地方。”那地方便是小说的领域。
无论如何,小说的载体是文字。米兰·昆德拉认为,对于世界而言,欧洲最大的价值便是它文化的多元性,能够以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大的歧异。冰岛,到目前为止,其人口最多时不会超过四十万,却在十三、十四世纪出现用古诺斯语写成的长达数千页的英雄史诗Sagas。事实上,国家的“大小”与人口数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重点在于某种更深层的存在。波兰作家忧虑“百年之后,如果我们的语言仍然健在……”,西班牙作家便没有这样的忧虑,为什么?因为曾经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把它的语言带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再比如说卡夫卡,虽然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虽然他在1918年以后成为捷克公民,但他一生用德文写作。米兰·昆德拉说:“如果卡夫卡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捷克人,今天不会有任何人认识他。”何其残酷的事实,却真实地存在着。
米兰·昆德拉走了,留下了他的小说、他的思考,将给我们启迪。将华文小说放在国家、民族的小背景、亚洲的中背景,以及世界的大背景中审视,又当如何?
三
初次读林文月教授的作品,是她翻译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翻译文学是重要的,翻译文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阅读内容。对于日本古典文学相当陌生的中文读者而言,《源氏物语》绝对是必读作品。这部写于公元十一世纪初日本平安时代的写实小说,早于但丁三百年,早于莎士比亚六百年,早于歌德八百年。我买到的译本是洪范书店2000年元月的修订版,四册,读得我如醉如痴。书本的上缘贴了无数的便签,色彩缤纷,正如同阅读时的心情。世界上还有比手中之书更丝丝入扣、更温柔婉约的文字吗?边读边去寻找林教授更多的作品,于是书架上出现了一整排的论文与散文作品,同年11月,我还得到另外一部日本古典文学《枕草子》的中译本。阅读过程中,林文月教授情之所系于我脑海中清晰浮现。
1933年,林文月生于上海彼时的日本租界,所习语言是日文。十一岁时到了台湾,开始学习闽南语和普通话。1952年,林文月进入台湾大学,1959年至1993年于台湾大学执教。在此期间,1969年秋天,林文月来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行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这就是林教授著名散文作品《京都一年》的创作背景。1993年,林教授自台湾大学退休,移居美国,成为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嘉惠无数学子,并且著述不辍。2023年5月,享寿九十岁的林文月教授驾鹤西去。我从书架上取下重温的这一本书,便是林教授名作《京都一年》的增订新版。泛黄的书页边缘满是细细的注记,带我回到多次阅读的诸般心境。
京都,自日本平安时代的794年成为日本首都,止于1869年日本迁都东京。这样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令林文月一见倾心。谈及京都市西南区的东寺,她这样说:“举首眺望,可以看见金堂东侧五重塔的尖顶,和墙外烛台型的建筑物‘京都塔’。那三百余年前匀称庄严的塔,与二十世纪流线型的塔,正代表着今日的京都——一个保留古典遗迹的骄傲,同时又慷慨地兼容今日科学文明的都市。这是一个奇妙的都市。在这儿,低矮而古老的日式木屋,可以和钢筋水泥的新型大楼比邻;在这儿,三味线的弦音,可以和爵士热门音乐并存;在这儿,梳高髻、穿和服、长带摇曳背后的祇园舞伎,可以和染红发、着露膝迷你裙的摩登少女同行。新与旧,传统与时兴,在这个都市里是如此协调交融着,散发出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这就是京都之不同于东京的地方,这就是京都之不同于奈良的地方,也正是京都之所以为京都!”
如此感性的宣言令人深深体会到林文月对京都的热爱。在新版代序中,作者谈到二十余年后的深秋再访京都时的感受,特别谈到造访古老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谈到经过平冈教授的住宅。这里曾经是她造访请益的地方。平冈教授不在了,林文月流泪鞠躬,表达她对师长最为诚挚的敬意。这是最令读者动容的地方。全书的第一篇谈的不是京都,而是奈良,是在深秋陪同平冈教授夫人到奈良参观当地博物馆所举行的年度“正仓院展”。看完展览之后,她们来到东大寺。一千二百多年前,奈良朝廷推行佛教,普设佛寺,东大寺便是在当时有计划的经营下,耗费巨资兴建的大寺院。之后,她们便来到正仓院宝库。
在这里,林文月展示出身为学者极富知性的一面。正仓院由北、中、南三仓组合而成。南、北两仓均以三棱木材纵横叠积而成,充分利用木材对自然湿度变化的反应,不但能使干燥空气流通而且能够阻止湿气侵入。而且,下承石柱,整个仓库离地九尺,得以通风,成为树屋般的“校仓”。中仓则以方形木板建成,加入南北两仓成为三仓。东洋古文物能够安然无损保存至今,实在是公元751年兴建的这座仓库的功劳。然而,彼时彼刻,仓中宝物已挪入钢筋水泥筑就的新仓库里,厥功甚伟的老三仓只是历史陈迹而已。林文月告诉我们,当时日本朝野大起怀疑,钢筋水泥真的能好过木材?林文月觉得,这座一千二百多年来避开了无数天灾人祸,鞠躬尽瘁,如今已退休的正仓院宝库像是“一个老而弥壮的人,屹立在我们眼前,令人肃然起敬”。
文章气势磅礴,结尾却说:“把平冈夫人送回家,再折回距离不到五分钟远的住宿处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走进六席的房间,有一股深秋的寒意袭人。这儿不是我的家,这里面没有亲爱的家人在微黄的灯下等待着我。我孤孤单单地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登上这二楼的小房间。但是扭开了那四十烛光的日光灯,心里却意外地有一种安慰的感觉。人总是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巢啊!”散文大家林文月游学京都一年间不断变换的心情就在这样优雅而平实的文字里与读者心灵碰撞。
欢喜、赞叹无处不在,尤其是关于日本的庭园,桂离宫的池塘,“池形曲折,饶富变化,而不见冗笔”,将野趣与优美熔于一炉,因之,林文月赞美道:“上帝创造大自然之美;而日本人则创造庭园之美。”
京都东北郊区修学院离宫附近的曼殊院有着浓郁的乡野气息,然而进到里面,却见识了日本有名的枯山水庭园。形状各异的石块是山的代表;满铺细白石,上扫出规则的波纹,便是水。这便是著名的枯山水,或曰石庭,起源于日本平安时代。幽玄的枯山枯水,白色一片,充满禅意,富于超自然主义的形式,带给观者的“与其说是眼睛的观赏,毋宁说是心灵的领悟”,石庭因其“简单而精致”遂成为林文月的最爱。
林文月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三面高山环绕的京都的庭园,在书中专辟一个章节,细细描述。十七世纪后,水尾天皇之离宫圆通寺位于大悲山之顶,苔庭、白石、枫树、茶花、老松近在眼前,中景则是林海一片,极目之处是山影,形成“山气日夕佳”的美好景致,最是迷人。
京都一年,举凡美景、建筑、书铺、寺庙、节庆、市集、茶道、服饰、食经、人情、礼仪,无不牵动林文月的情愫,林文月遂引经据典,知性与感性并存,以秋冬春夏顺序详实描摹。手边详谈都市之万千气象的书籍甚多,而拔得头筹的,便是林文月这一本情感深厚的《京都一年》,读之再三,获益匪浅。
四
2016年,台湾观众有幸沉醉在《十诫》《两生花》,以及“蓝白红三部曲”等剧情片所带来的对于戒律与人性,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等的深度思考中。2023年“金马经典影展”将波兰电影导演、剧作家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生创作的五十二部长短影片全部呈现,他们更有机会深度了解电影应当是怎样的存在,以及优秀的电影是怎样把希望留在人间的。现在,电影之外还有书,威尼斯、柏林、戛纳影展的获奖者基耶斯洛夫斯基夫子自道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将影像与文字融合,让更多的人知道,比文学原始很多的东西,原来竟然是电影。
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年出生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华沙,二十一岁毕业于华沙剧场技师学院。二十三岁到二十七岁就学于著名的洛兹电影学院。毕业后,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拍摄了一系列著名纪录片;之后,拍摄了大量剧情片,并成为波兰电影革命运动“道德焦虑电影”的重要成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基耶斯洛夫斯基已经是公认的电影大师,他最后四部作品《两生花》与“蓝白红三部曲”系与西欧影人合作拍摄完成,大获成功。根据但丁《神曲》创作的新作未能完成,1996年其人因心脏病于华沙辞世,其电影文化遗产不仅为影迷留下无尽怀想,而且被年轻一代电影工作者奉为圭臬。
从网上买到“蓝白红三部曲”,在静夜里观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杰作,面对影像、色彩、镜头、音响超凡入圣的绝佳组合,对白变得无足轻重。手里捧着的这本书,则用文字道出了电影背后的心态、思虑、煎熬与无奈。
从小,基耶斯洛夫斯基热爱读书,从书中了解到“生命中除了物质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不喜拘束,受不了行政命令。报考洛兹电影学院,有两次落榜的经验。第三次,只剩最后一个考题了,主考官问道:“什么是大众传播?”基耶斯洛夫斯基答曰:“有轨电车!”主考官大笑,基耶斯洛夫斯基跨过了数千人报考只取四五十人的那道窄门。主考官认为,那问题太蠢,此考生不屑正面回答所以有此答案。事后,两人私下交谈,基耶斯洛夫斯基告诉主考官,他确实认为有轨电车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此时主考官才了解,他录取的这个学生不同凡响。人们读到这里也就明白,波兰洛兹电影学院绝对不凡,能够容纳不同的思维与声音。果然,基耶斯洛夫斯基进入了校风开放、没有电影审查制度、为学生提供大量电影的好学校,而且从中学习到“电影是生活的一部分。电影也留在我们心中某处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内在自我的一部分”。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虽然电影是创作出来的,但电影同真实世界没有不同,“电影会留下”。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毕业作品是他踏入电影界的第一部片子,也即纪录片《洛兹小城》。他念书的这个小城“是个残酷又不寻常的地方,破败的建筑、破败的楼梯、破败的人,让那里看上去特别美。当地极为落后,老旧的纺织产业,永远有人的手脚被扯掉,也因为街道狭窄,有轨电车直接挨着建筑行驶,稍不留意,行人就在电车下面了……”,因此,“洛兹有些吓人,却也因为这样而有意思”。从摄影到拍片,真实的洛兹被影像留了下来。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电影学院教我如何看这个世界,向我展现生活真切的存在。而且这一切都能拍下来,能说出故事”。对于电影学院,他也有怨言,因为学院没有告诉他,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观点,他得在离开电影学院之后,花费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这个结论。
关心民间疾苦的纪录片,自然不是当年波兰政府电影审查制度所能够完全容忍的。虽然,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来不曾热衷于政治,他认为“政治只能定义人的身份,但从来无法解救人心”,但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他拍摄出题材敏感的《七一年的工人们》。片子被删减出一个版本,但无论是原始版本还是删减版本都从未被放映过。这使得基耶斯洛夫斯基转向剧情片,也使得他加入了“道德焦虑电影”运动,他本人不喜欢这个标签,但他确实认识到这个标签的效用。自1974到1980年,一些电影工作者对波兰人的道德困境感到焦虑,因此形成一个团体,设立一个工作室,专拍低成本剧情片。看到这不落俗套的篇章,读者会想到,真正深入人心的好电影有时是来自那样独特的工作室。
基耶斯洛夫斯基道出他的无奈与坚守:“我大概是靠着一股强烈的野心在拍电影的。电影比文学原始很多。开始的时候,有故事要讲,接着经过一两年或五年出现了最后的成果,这个成果只忠于最初的想法,和后来发生的事不太相关。角色被创造出来,动作出现了,然后是摄影机、演员、道具、灯光,还有一千件你得妥协的其他事情,你得接受一千种不便的情况。最后的成果永远不是你在写剧本构思这部电影时想象的样子。不过最初的概念真的只是某个念头或直觉的基础,把它牢记在心,能以一句话概括整部电影,是件好事。”拍电影是苦行,是彻夜不眠、六点钟起床,是烦忧发愁、担心下雨,而感到满足的片刻鲜少发生。从苦行到伟大,其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辛苦而短暂的五十四年生涯,非常电影,非常波兰,非常人性。
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波兰曾经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亡国期。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为战场遭到剧烈破坏;战后又加入苏联的“东欧阵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波兰的历史与文化所产生的向心力使得波兰人非常恋家。基耶斯洛夫斯基来到美国之时便强烈感觉到两国文化之不同,美国人动不动举家搬迁的生活形态带给他很多思考。正因如此,其最后四部大片虽然在完全不同的城市拍摄,演员、掌镜者却多是西欧影人。电影仍然非常有波兰风,带着波兰名导基耶斯洛夫斯基深刻的印记,永远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