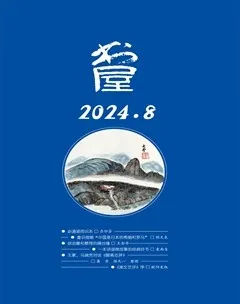王蒙、马瑞芳对谈《聊斋志异》
王蒙,当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著有二十三卷《王蒙文存》,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马瑞芳,著名作家、学者。曾出版《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等,在央视《百家讲坛》担任《马瑞芳说聊斋》系列讲座的主讲,影响巨大。2023年,在天地出版社出版了《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系列作品,同时出版的还有《马瑞芳品读西游记》三册、《马瑞芳品读红楼梦》五册,形成了古典小说名著品读系列。
马瑞芳:我的大师兄李希凡先生说过这样的话:“《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千古流传,万世流芳。”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中国古代最好的小说按文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长篇,一种是短篇;就语言形式来说,一种是白话,一种是文言。《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艺术巅峰,这是无可置疑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巅峰,也是无可置疑的。
民间对蒲松龄有一种说法,叫作“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这个说法我查了很长时间,没找到是谁提出来的,但是它相当有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蒲松龄是崇祯十三年,也就是1640年出生,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去世,活了七十五年。在他去世两百年之后,世界文学中出现了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分别是俄国的契诃夫、法国的莫泊桑与美国的欧·亨利。当我们考察这三个世界短篇小说巨匠时,会发现他们小说里面的人文关怀、艺术描写、手法、构思,可以说都是蒲松龄玩剩下的,所以蒲松龄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巨匠。我们在大学里边讲,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唐传奇,是由若干个进士——其中还有几位宰相——共同创造的;第二个更高的高峰是《聊斋志异》,而这个高峰是由一个穷秀才独力创造的,所以蒲松龄就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
王蒙:《聊斋志异》,早就闻其名,以民间故事为话题。最近一两年,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马瑞芳教授关于《聊斋志异》研究的作品,有五本——包括人的、狐的、妖的、鬼的,还有神的。我觉得《聊斋志异》非常少见,几乎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虽然蒲松龄也受到很多人的影响,这些马老师都考证过,比如《田七郎》,核心内容与《史记》中描绘吴起的篇章几乎一模一样。他极致的想象力,源于他进入了“怪力乱神”“妖魔鬼怪”的世界。《聊斋志异》中最短的故事之一是《咬鬼》,那男主人公一口就咬住了女鬼。《咬鬼》虽然大约只有二百字,却讲到了极致,我想一个人在拼死斗争中,到了用牙咬的程度,那是很难再进一步了,达到极致了。还有《野狗》中的鬼哭,人为了求活命,伪装成死尸。于是读者就想,死尸被野狗吃了怎么办呢?那些死尸哗啦啦地、成千上万地站起来,一下子就把人吓傻了,这描写简直到达了极点。
《聊斋志异》共有四百九十余篇。不光体量大,故事种类也多。有的短篇只有一二百字,但有的内容本来应该是长篇。《聂小倩》绝对应该是长篇的,要是换一个人来写起码要写五十万字。《叶生》可以分三集写。还有《娇娜》,也完全是长篇的题材。
再比如蒲松龄有的小说明显是有所攻击,有话要说,有块垒要浇。但也有的我们看完了弄不清到底说的是什么,就是一件怪事,单纯以事为纲,以故事为主题。同时,《聊斋志异》的各篇,观点也并不一样,有的篇目把狐狸写得像犬,有的篇目就明确狐狸是妖孽。文本内部的思想也非常不一样,有的篇目非常同情女子,有的篇目又显得很保守、很陈旧。故事的内容与“异史氏曰”,又是两个角度、两套语言、两种意识形态。《聊斋志异》里的一些篇章让人想到中国的神怪故事;有的感觉和世界文学里的契诃夫、莫泊桑,还有我喜欢的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契弗等的短篇小说很靠近,却都不一样。再有的甚至还会让人想到阿拉伯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段子或野史。可见中国最早对小说的理解是“段子”,是通过这个“段子”借题发挥的。
《聊斋志异》独占一座山峰,这座山峰上的景色,我们百赏不厌、百读不倦。马瑞芳教授对《聊斋志异》的研究非常深,令人受益匪浅。
马瑞芳:王老对《聊斋志异》看得非常细,琢磨得也很深。《聊斋志异》中确实有一些很奇怪的故事,像《野狗》中写到缺头断臂的尸体站起来说“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故事其实影射的是清代初年清军对山东人民的大屠杀,如果单纯就是野狗要吃人,那没什么价值。清廷入关以后,大兴“文字狱”,考官连出个“维民所止”的题目都要被杀头。所以这种屠杀只能用鬼怪的题材来写。
《聊斋志异》的故事样式太多了,构思太有意思了。我们可以发现,蒲松龄在写爱情上特别创造了一种模式,我归纳成“青龙白虎并行”,即两个女主角,如:《小谢》里“小谢”“秋容”两个人;《青梅》里青梅和她的小姐;《巧娘》中的一鬼一狐。这种写法此前从没有人尝试过或者使用过,所以蒲松龄非常不简单。
他的创作一定对王老的短篇小说创作有影响。
王蒙:我还是要好好学习。
马瑞芳:《聊斋志异》最重要的版本是存放于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手稿,我很荣幸亲自翻阅过,我看的第一篇就是《考城隍》。《考城隍》给《聊斋志异》规定了一个“善善恶恶”的观念,就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赏罚善恶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个人的动机,无意之中办了坏事是不要紧的,但有意识地去干坏事,是绝对不能原谅的。《考城隍》为《聊斋志异》规定了“惩恶扬善”的宗旨,所以《考城隍》在所有的版本当中都是第一篇。
同时,《考城隍》是蒲松龄早期的作品。他一开始认为,科举制度是按照人的真才实学来取士的。但是到了后来,就发生了改变。在他的《聊斋志异》当中,科举制度一塌糊涂,和我们所认识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不完全一样。但是如果按照他的观点,王维是唐代的状元,文天祥也是状元,唐宋八大家全是进士,他们难道不算人才?这可都是科举制度选出来的。而蒲松龄自己不适合科举制度——他用写小说的方式答论文,怎么能通过呢?
所以《考城隍》有这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确定了善恶观念,一个是表现了他最初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王蒙:我是一个热爱《聊斋志异》的读者,不是一个研究者,对版本、作者知之甚少。拿《考城隍》为例,这是不是作者自己选择放在第一篇的,我也没有特别注意。《考城隍》以一种很调和的、和解的方式来写人生的体悟——活着是一个世界,死后阴间还有一个世界;阴间世界的一切是阳间世界的模拟版,是阳间社会的投射。阴间也有科举考试,活着考不上,死后却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我很喜欢他们考试出的题目“一人二人,有心无心”,我想着我们中文系、文学院,也可以每人照着这个题目交一篇作文。《聊斋志异》里有些观点说有心做好事不是好事,无心犯罪不是罪,这种观点我们现在绝对不支持,有利和有害一定要分清。但这种说法却更容易让自己跟自己、跟社会和解。《考城隍》是一篇心平气和、诸事好说好商量的故事,甚至可以请旁人先替自个儿死掉,因为自己家中有八十岁老母。
当时小说的地位很低,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小说有别于大道。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就是茶余饭后引车卖浆之流的娱乐,写文章写诗才是高级的,小说、戏曲、歌词都是低级的,尤其小说是最低级的。所以他小说里出现了“异史氏曰”,这仿佛就是说“我和别人不一样”,仿佛是说:“各位看好了,我不只会写小说,也会写文章,写论文。”
马瑞芳:蒲松龄在最初的八卷本确实把《考城隍》选为第一篇。也确实,当时写小说的人没地位。蒲松龄非常崇拜的同时代的王渔洋,是清初大诗人,他很欣赏蒲松龄的写作,要了蒲松龄抄本来看,而且写了几十条点评。蒲松龄特别希望王渔洋写一个序,王渔洋答应了,但没写——台阁重臣、大诗人给一个小说家写序,他觉得丢面子。但是现在王渔洋最著名的诗就是写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诗。所以历史有时候也给人开开玩笑。“我是大诗人,你是小穷秀才”,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聊斋志异》。
蒲松龄的传记我写过四本。第一本是1985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近一本是参加中宣部的“组织当代一百个作家写中国古代一百位作家”项目时写的——那一次王蒙老师被邀请写“老子”。而我写蒲松龄,特别着重考察他的科举经历。蒲松龄十九岁时就是山东省第一名的秀才。清初有两个大诗人“南施北宋”——施闰章和宋琬。其中,山东学政施闰章欣赏蒲松龄,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很生动精彩,便录取他为第一名秀才,蒲松龄可能就觉着这样写就很好了。但是考官都是八股文严格训练出来的,除了施闰章以外,他们并不欣赏蒲松龄。八股写得像小说,就不能被录取。
蒲松龄到底考了多少次举人呢?据我的统计,至少考了十一次。他六十四岁时写了一首诗,称“三年复三年,所望复虚悬”。这说明他六十四岁时还没考上举人。所以在中国小说史上,谈到《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成就,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抨击往往被重点强调。蒲松龄是中国古代作家中第一个向科举制度全面开火的。他认为科举制度的命题不合理、选材不合理,认为科举制度对社会有恶劣的影响,而《叶生》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叶生》确实是他本人的经历,特别说了他无论怎样苦心经营都过不了这一关。过不了这一关怎么办呢?活着考不上,死了去考。《聊斋志异》中的鬼魂科举故事代表作实际上不是《叶生》,而是《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这几篇,这几篇写了鬼魂是怎么样考试,考试出的什么题目。正如王蒙老师所说,《叶生》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活着考不上,死了考上了,回到家后看到的是自己的棺材,这是多好的长篇小说题材,但是蒲松龄以一两千字写出来了,这就是他一辈子的深刻感受。
中国古代文学史论著无论哪个版本,都一定要讲《聊斋志异》与科举制度。关于蒲松龄与科举制度的文章非常多,很值得研究。但是我想,因为蒲松龄他自己不适合科举,所以小说里边是带有他的偏见的。
他最糟糕的一次科考经历是“闱中越幅”。蒲松龄那一次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但是他写完第一页,接着写到第三页上了,这就是“闱中越幅”。“闱中越幅”就得张榜,蒲松龄不仅没考上,考卷还被贴出公示了——这叫违规。
王蒙:我对《叶生》也非常感兴趣,因为《叶生》让人感觉非常悲哀,让人觉得科举制度非常荒谬。从考官的角度,较好的文章和很差的文章都是可以分辨出来的,而“最好的”恰恰绝对不可能是最大公约数。“最好的”挑战性相当强,“最好的”文章所具“非熟悉性”“陌生性”,必然使一部分人说好,一部分人难以接受。
科举制度在全世界得到高度评价,中国从一千多年前——特别是宋朝起,就把科举制度搞得这么完善、这么成功,打破了阶级死不相通的状况,允许不同的阶级通过自己的学习读书,有所晋升、淘汰、提拔、转化。鲁迅的《孔乙己》对科举制度抨击得也很厉害。可是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完全是靠人情、靠后门、靠背景、靠行贿升官,那样会更坏。
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天才难以被发现、被接受,那岂止是科举制度,以前的教育制度都或多或少有这个问题。比如,俄罗斯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学习阶段的评价很差。在音乐附中的时候,他就被建议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所有教授的要求;到了高等音乐学院以后,他得到的评价也是负面的。
《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叶生》,一方面,这好像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叶生》是天才,小说是天才的命运悲剧,也是智慧的悲剧、创造的悲剧。从另一方面来说,叶生的形象实际是光芒四射的,既有悲感又有壮感。
最近我在琢磨一件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战斗报》要全世界的几百个作家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铁皮鼓》的作者、德国的君特·格拉斯说:“我做不了别的,我只能写小说。”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回答,曾多次引用。这一引用,许多人对我就失望了,说:“王蒙带头贬低文学,说文学穷途末路了。”我喜欢这句话有三四十年了,最近忽然得到一个灵感——我为什么喜欢这话?因为这里头包含着一种人生的经历,意味着文学的代价,流露出一种苍凉感和寂寞感,也包含着一种自嘲。设若君特·格拉斯是德国足球队的守门员,他才没工夫写什么《铁皮鼓》,他要是隆美尔将军,也顾不了那么多文学。写作,就是要献身文学,要付出代价。你以为会写的词儿不少,可没等你成为作家就先失业了——先把信用卡收回去。就跟《月亮与六便士》那篇小说一样,毛姆是说一个画家的故事:一个中年女人,丈夫原本在一家银行里当高管,突然就不回家了。这个女人就请小说中的“我”来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最后说,这男的爱上了艺术。女人就哭了,说:他要是遇上另外一个女人,最多三年我能把她干掉,我觉得我的魅力超过一切;如果他去抢银行、参加黑社会了,我很快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可他迷上艺术了,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所以,我看《叶生》的时候就想到了:越是天才,往往越是容易因科举失范而受挫的。
马瑞芳:刚才王老这一段话,里面有很多的闪光的话,像《叶生》是“天才的命运悲剧”“创造的悲剧”。像《战斗报》提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铁皮鼓》的作者回答“我做不了别的,我只能写小说”?蒲松龄就是做不了别的,只能写小说。
我想起1997年,我到美国访问,回到北京下了飞机后,中国作协就派车把我接到中日作家对话会上,对面是一些日本作家,这边是咱们中国作家。日本作家就跟咱们中国作家提了同一个问题——法国人那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写小说?
第一个回答的是《长江万里图》的作者周而复。因为他去了靖国神社,我当时对他印象特别坏。日本人问他:“你为什么写小说?”他这样回答:“我写《长江万里图》就是要把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真实记载下来。”他的那一句话让我改变了对他“完全坏的”印象,他一说这话,在座的日本作家的头全低下去了。
第二个回答也特别有意思,那是刘恒——《狗日的粮食》的作者,刘恒说:“我写小说是为了在小说里面爱——爱我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爱而不敢爱的人,也是为了在小说里面恨——恨我非常恨但是不敢恨的人。”这和蒲松龄是一样的!
蒲松龄就在他的小说里面恨了他平时不敢恨的人——贪官污吏,爱了他不敢爱的人——他有一个梦中情人,给别人做了小妾,所以他在小说里面经常写“我怎么爱你”“我们两个最后终成眷属了”。所以《铁皮鼓》作者的回答非常好。
王蒙:我最近在阅读《聊斋志异》的过程中,有了一些新想法,有一些和现今通常的观点不尽相同的见解:我觉得蒲松龄写作的故事种类很多,且态度不尽相同。在有的故事中,他表现出鲜明简单的态度,连小学生都能看懂,比如《一员官》,讲述一个官吏顶住了上级的压力,坚持不做违法乱纪的事。他的凛然正气使得上级也有所让步,而且从此对他非常尊重。这个故事的含义就特别清晰。再如一些书写农民起义的故事,含义也一样清晰。与此相对的,另一些故事,可能含义并不如此清晰,仅仅是叙事。比如《田七郎》中的田七郎,他的形象就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田七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是一个被欺骗送了命而又意识到自己被欺骗的人,这样一个人是英雄还是懦夫?《田七郎》的故事与《史记》中吴起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都有“兵士身上化脓,将军用嘴去吸”“兵士的母亲意识到将军对两代兵士做了同样的举动,故而他们也面临着同样死亡的命运”的情节。我认为蒲松龄写下的这个故事引发我们思考:任何“忠”都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什么样的人值得为之牺牲,什么样的人不值得?
《田七郎》中的武承休也是个颇有深意的人物。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他的身份——他是地主,马瑞芳老师认为武承休对田七郎应当只是利用,而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武承休讲义气,故而也要交讲义气的朋友。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现在有这样的观点:对人坏,往往是由于嫉妒与排挤;对人好,便是为了利用和占有你。我认为如果人人都这样立论,对你好或坏都是害你,人与人的关系便会更恶化了。
还有《促织》也是个没有明确含义的故事。我的疑问是:《促织》中的小蟋蟀到底是不是成名的儿子变的?一些人毫无根据地认定他的儿子变成了小蟋蟀,但蒲松龄并未明说,这给了读者相应的期待:读者期待蟋蟀是由儿子变的,这样才替跳了井的孩子出了气。
因此我认为,蒲松龄在很多作品里留下了空间,读者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就如《促织》,可以有各种解读:一些读者可以认为蟋蟀是孩子变的,另一些读者也可以认为不是。我觉得这种多角度的解读非常好,不必有排他的定论。
马瑞芳:王老说的这两个问题都特别有趣。先谈论《田七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开了个专栏《聊斋人物论》,其中就有一篇谈及《田七郎》。我采用了对话的方式来写这篇文章,分为正反两方。正方所持观点,这是朋友之间的义气;反方则说,这是武承休利用田七郎。我持反方的论点。后来这篇文章在国际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甚至有人从美国打电话来反对。
我的论点有两个主要依据,第一个是《聊斋志异》人物的命名规律。像《娇娜》中,“娇娜”的含义本身就是妩媚可爱。而孔雪笠姓孔,是孔夫子的后代,暗指他讲礼仪。他名叫“雪笠”——雪中送了个斗笠,是雪中送炭的意思,孔雪笠果然在娇娜危难的时候救了她。而“田七郎”的名字中有“七”,中国古代以“七”为名的一般都是好人。和他交朋友的“武承休”,其名“承休”指继承优良传统,这是个好名字,但是“武”姓谐音“有无”的“无”,便指他没有继承优良的传统。第二个依据是田七郎母亲的言谈。田七郎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社会经验的老太太。当武承休来巴结田七郎,找他要虎皮,连掉了毛的都要,老太太就看出了端倪。在这一段中,蒲松龄记载了老太太的淄川话“再勿引致我儿”,这句淄川话暗含的意思是武承休“大不怀好意”。然后她告诉田七郎,穷人和富人交朋友,富人拿钱交,穷人得拿命赔。这就是我的两个主要依据,也就是我和国际蒲学家辩论时的观点。
至于《促织》,我早就发现全国统编教材里的《促织》用错了版本。现存《聊斋志异》最早的版本,就是蒲松龄的半部手稿,在辽宁省图书馆。教材没有用这个版本,用的是青柯亭本,而青柯亭本是蒲松龄逝世很久之后的一个刻本。在青柯亭本里,出现了儿子的灵魂化成促织的情节,并且相应地改动了前文。我写过一篇文章,大声疾呼“不要误人子弟”“赶快把中学课本改过来”,喊了二十多年,不起作用。后来我在喜马拉雅讲《聊斋志异》的时候,特别讲了两讲,专门谈《促织》的问题。
王蒙:我在阅读的时候也有一些奇思怪想。蒲松龄的想象中,有一些内容非常美好,让人看的时候十分沉醉。比如说《崂山道士》,几个道士在那儿喝酒施法,一画便成真,一招手嫦娥便从月亮上下来。我看了,觉得美极了,很浪漫主义。《画壁》也非常美,说一个人在寺庙,看了美丽的壁画以后就进入画中,而且和一个小女仙相好——“与之狎”。“狎”这个词儿用得多好,他把性爱说成是一种游戏。世人喜欢游戏,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伟大得不得了。可是英文说的那就是奥林匹克“游戏”(game)。——蒲松龄通过“游戏”写这些东西。
说到浪漫主义,我有一个观点:毛泽东同志提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这两个主义之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讨论、学习和研究。这两个词远远不像“延安讲话”那样影响深远。苏联是只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主席则不仅限于现实主义,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文学就是文学,它不是新闻,不是记录,也不是历史。
同时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蒲松龄不能把美好的浪漫保留到最后。《崂山道士》的美丽景象结束后,剩下那么一个平庸的、不卓越的、低级的一个人物,要学着穿墙越户偷东西,结尾他由于坏心思,不能穿墙越户,自己把脑袋撞了一个大包。那么美丽、那么浪漫的故事结尾,主角的脑袋上撞了一个大包。蒲松龄非常伟大,他完全可以改的,哪怕以一个坏人的事儿结束,你也可以从中抽出一分美好来。故事中当然可以有好人、坏人和雅人、俗人,也有脑袋上撞包的人,但是完全可以写得唯美一点。像王尔德,写一只对一切无能为力的燕子的死也写得那样美。
马瑞芳:王老的这个说法,真令《聊斋志异》研究家瞠目结舌了。因为《聊斋志异》专家的一般论点是:蒲松龄写《崂山道士》的目的,是劝喻读者踏踏实实劳动,想取巧一定会碰壁。王老这个说法,则是一个大作家的观点,很好。
王蒙:能够追求审美,能够养成对美的追求和爱恋,能够看到愚笨和艰难中的美的元素,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不光高级的仙人、神人、天才能追求审美,俗人、傻人、穷人、文化低的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可以追求审美。有时一个蠢人经受挫折失败,碰得头破血流之时,或许就忽然感到了什么,能够想到:“自己虽然做不到穿墙越户,但我亲眼看到‘崂山道士’创造的最美丽的经典,不白活这一辈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所以,唯美主义也有它的存在价值。
马瑞芳:《聊斋志异》中的唯美特别体现在写青岛的作品上,比如《香玉》。《崂山道士》可能叫王老不是很满意,王老应该满意《香玉》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中国古代讲爱情是三世情,香玉和她的恋人王生两个人超过了三世情,而且最后花神还让她复活了,小说中最唯美的意象是在花瓣绽开之后,有一个小美人唯美地跳下来,渐渐地像人一样高。
王蒙:我还有一个怪想法,就是在看中华书局那一版的《王六郎》时,看到注释者说王六郎之伟大,在于他的仁爱之心、体恤之心、不忍之心。本来应该是一个抱孩子的女子死去,他借此就可以重生为人。可是他不忍心为自己一人而死母子二人,故舍弃托生机会,继续当溺鬼,后来因仁心达上天,王六郎当上了城隍。中华书局版说这一篇的关键是“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我觉得“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是本着当代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来解读的,尤其提倡在生死的关头舍己为人。可是舍生取义地拯救妇女这样的事并不给人以深切的真实感。相反,熟悉的人做了官,你就跟他搭不上话了——蒲松龄可能经历过这一类事。
与《聊斋志异》正文的神怪世界不同,蒲松龄在写“异史氏曰”的时候,他在人间。我认为他是有意识地在“异史氏曰”中唱着普通的调子,向世俗妥协。他不能在“异史氏曰”中把话说得太偏激、太超然,或者太愤怒,如果说得太过,就有“文字狱”的危险。所以当他在神仙鬼怪的世界中时,怎么扯都行;然而当他写“异史氏曰”时,他便从《聊斋》的神鬼世界中回到了现实世界。此时,他是一个很正常、理性而普通的人。作为普通人,他说的话也都是符合传统的。
马瑞芳:这只能说是“异史氏曰”的一部分内容。“异史氏曰”更主要是蒲松龄模仿太史公的评论。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相当于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发表意见;蒲松龄个人定位是“写异史的”,于是就写“异史氏曰”,要对异史故事发表意见。所以有一些地方,他并不是完全宽容的、完全平静的。最近非常流行的刀郎的歌《罗刹海市》,人人都知道那出自《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中的“异史氏曰”便说“花面逢迎,世情如鬼”,指社会中每个人都得带着假面才能生存,就像荣格说的“人格面具”。蒲松龄比荣格早二百年提出这一概念,还不止一次强调。他不光在“异史氏曰”当中强调,在故事中也强调。《画皮》便讲述了假面的故事,美女的画皮里边是恶鬼。
“异史氏曰”的研究成果很丰富。有的“异史氏曰”还会再补充个小故事,有时是相反的故事,往往讲得很好玩。王老还是看得很仔细。
王蒙:为什么我对武承休没有反感?因为我一生也经历过各种挫折。我心里想:在逆境中如果有人对你如此之好,你还会怀疑他的动机?他想利用你,太好了!感人泪下!就怕谁也不想利用你了,把你晾到一边去了,把你冻结了。居然还有大人物想利用你,那实在很感谢!必要的时候应该为他死一回!是不是?你自个儿倒霉还倒霉不完,你还怀疑对你好的人?不怀疑!谁对我好,我就该报答谁。知恩不忘,有恩必报,涓滴之恩,涌泉相报,这才是好人。
马瑞芳:这一段非常有说服力。王老体会到“我为他死了都可以”,完全和他自身的坎坷经历有关,太感人了。
我建议同学们都去看一看王老的《这边风景》。在那么多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当中,《这边风景》算是最好的小说之一。人们很难想象到一部写政治斗争的小说可以把每一个人都写得活灵活现,太有意思了。真实的人性被王老挖掘得太棒了!《这边风景》最近不是要改成电视剧吗?我估计会非常好看。
因为王老有如此真实的经历,所以他会发表这样一番议论。这是发自肺腑的,和我这种没怎么受挫折的人感受很不一样。
《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第一个应该提的,就是毛主席非常欣赏的席方平。席方平的父亲受到恶霸的陷害而死,到了阴世,恶霸又买通了阴世的人,对席父严刑拷打。于是席方平到阴世替他父亲复仇告状,从城隍告到郡司,从郡司告到阎王。每一级都受贿了,一升堂,不打被告而打原告,最后把原告推到火床上,几乎要把他烙死,还下令把他锯成两半。但是席方平“忍而不号”,所以这会儿小鬼都同情他了,拿出一条丝带“赠此以报汝孝”,往身上一拴,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毛主席非常欣赏这个情节。毛主席在1942年,对陈荒煤、何其芳等人说:“《聊斋志异》写的是清朝的历史,其中《席方平》就可以做中学课本。”他特别欣赏“小鬼赠丝带”这个情节。席方平就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中国男子。
王蒙:男主人公里头,我觉得《娇娜》的男主人公孔雪笠很不一般。故事名虽然是《娇娜》,但是他与女主角娇娜并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孔生开始被他的学生说成是“少见而多怪”,看到学生老父的婢女香奴就视为佳偶,后来见到能治病的女童娇娜更是神魂颠倒。娇娜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但是年龄太小了,与孔生婚配也是不合适的。对于男子来说,会对各样的女孩子倾心、倾情,会有各式的示好与奉献,会表现出不同的义气与庇护。孔生的爱慕与仗义最后表现为以自身的身体和生命抵御娇娜狐狸家族的雷霆轰击劫难,献出了生命,后又被娇娜救活。“异史氏”的评论,是“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是“‘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这样的爱情故事,比起苏三、杜十娘、《西厢记》、《牡丹亭》等,又更有其别样真情与清新格调。厉害!
好书一定要好好看,千万别光看手机段子。不能让手机段子戕害了我们的青春,戕害了我们的学生时代,戕害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教养,戕害了我们的审美意识。好好看《聊斋志异》,好好看《红楼梦》,好好看世界上的一些经典,这是我的愿望。
马瑞芳:咱们有句古话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心自知”。四大名著、《聊斋志异》、唐传奇……一定要读原著,要好好读原著,而且要挑好的版本,特别是一些大出版社出的一些版本,像王老师说的那样,不要把时间花在看手机段子上。孙犁先生说,能在文学史上留几个字都是不容易的,而现在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章的是《聊斋志异》,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大家都得好好读。当然我还建议,外国作家的作品也要好好读。王蒙老师之所以能成为这么杰出的一个大作家,是因为除了这些经典,他也读了很多的外国作品。所以既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要夜郎自大,世界文学也要好好学,谢谢。
(本文是2024年5月7日王蒙先生、马瑞芳教授在中国海洋大学的对谈,对谈由熊明教授主持。本文由龚雪、陆天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对谈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