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思想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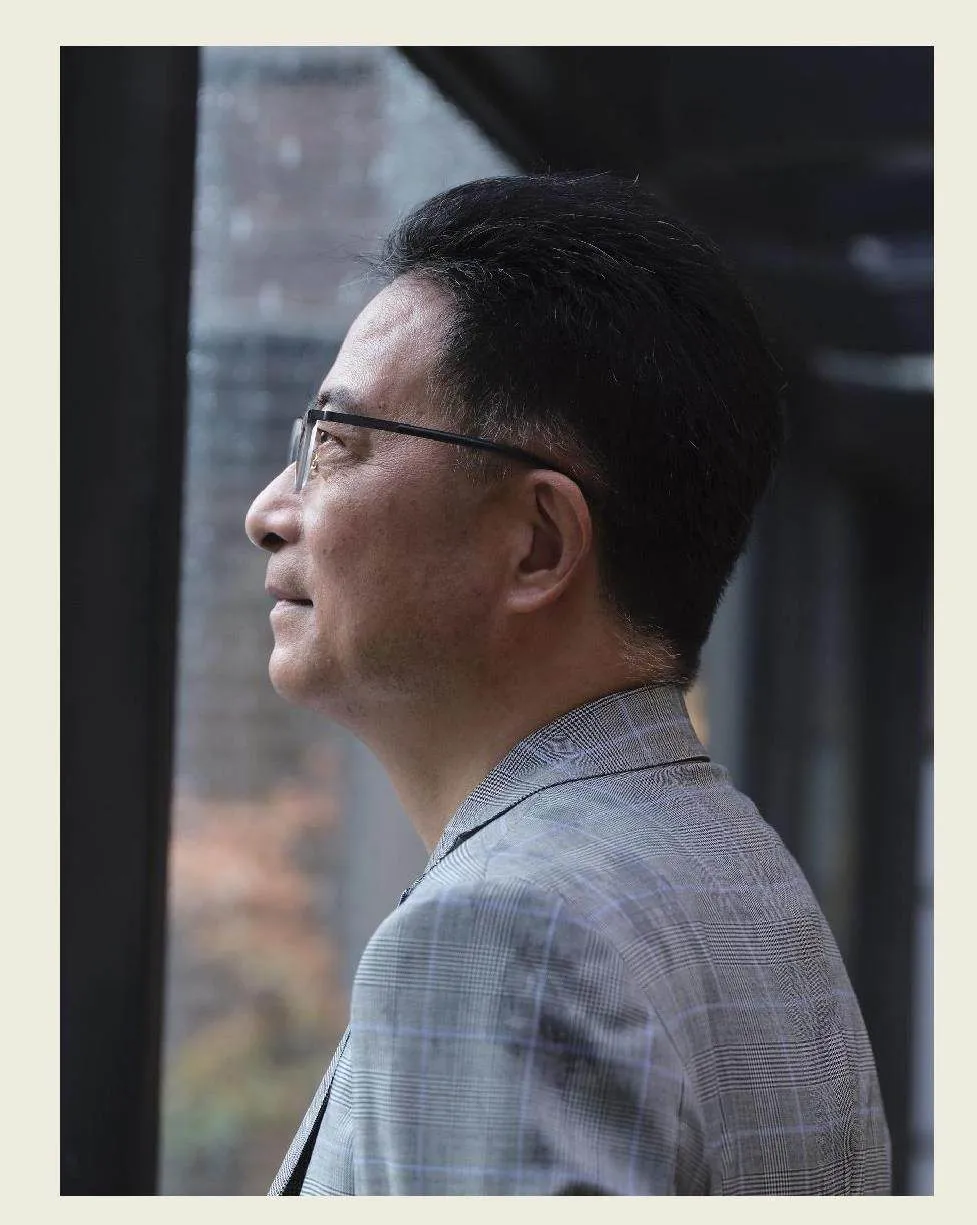



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IPRA学术工作委员会
主任
叁
就像有人留恋上世纪90年代,我则怀念80年代。年初电视剧《繁花》热播,不少朋友问我,上海人是否就是这个腔调?我竟不知如何回答。我虽生在上海,从小在上海长大,当年我家(长乐路)离黄河路最近也就三四公里,但因1979年十八岁北漂上学,后又留北京工作近四十年,期间不乏时常回上海探望老人或出差,却不曾见过上世纪90年代上海黄河路之繁花。受如潮好评的促动,我试着看了几集《繁花》,不知何故,对其中人物的叽叽喳喳、心机过重,甚不适应,也难欣赏,这大概也应了朋友们对我的评价: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春节期间,通过微信读书,看到新世纪这
些年在上海工作生活过的外国人写上海(上海人)的一些
书,如《长乐路:一条上海马路上的大城市梦》(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
(Outsider,一个老外在上海十八年)等,反而感觉既熟
悉又陌生。
长乐路位于上海市中心,东起黄浦江,西至华山路,长约3公里,在地图上是一条很短的波浪线,当年我家就在这波浪线的东端,属卢湾区(2011年与黄埔区合并),系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历史悠久的长乐路,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丰富的文化氛围,以及现如今琳琅满目的餐厅、小店极具小资情调。《长乐路》一书的作者是美国驻华记者史明智(Rob Schmitz),他选择把来上海后十多年一直居住的“长乐路”作为自己了解中国的窗口,记录报道了在长乐路生活、工作的多位中国百姓的日常故事,并于2016年在北美出版了非虚构文学作品英文版《长乐路》,2018年译成中文,被读者评价为“半条马路知中国”。
Outsider,原本是外行人、局外人、旁观者之意,将一个在上海有近二十年经历的外国人称其为上海话里的“洋盘”,在文化交互中可谓神译,不知上海话中的“老克勒”“模子”“捣浆糊”如何译成英文(据说“老克勒”一词被小说版、电视剧版《繁花》都弃用,因其所含的揶揄、暗讽之意)。2005年,24岁的美国人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怀着“冒险”精神,离开老家迈阿密,以年轻厨师的身份去了香港,后又谋得一份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餐厅的工作,由此开始了他近20年的“沪漂”生涯。从厨师到美食专栏作家,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评测52家上海小笼包店家,写出《上海小笼包指南》(The Shanghai Soup Dumpling Index,2015),出圈成了“网红”,被人称为“最懂上海小笼包”的外国人(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华访问,也去上海豫园吃了南翔小笼包)。他几乎游历中国各省,与人聊天,透过食物镜头看中国,探寻背后的中国人世界观,记录正在发生的当下。2023年10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亲身经历中西文化碰撞的写实作品《洋盘》,有评论说,作者是当下“最会讲故事的在华外国人,笑中带泪地讲好了中国故事”。罕见的是,此书只有翻译版,没有英文版。
这几部作品宏观背景下的微观叙事,对近三十年上海和上海人形象的输出传播,有其明显效能和积极意义,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如何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有效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品牌(National branding),凡品牌皆有人的故事。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而非只是GDP硬实力以及诸多超级工程的宏大篇章。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悲欢离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生存境遇所构成的凡人故事,才更富人类普遍命运的基本意义,也更具交流分享的传播效能。
国际传播涉跨文化传播,根据文学作品《繁花》改编的电视剧,虽非国际传播,但也有沪港两种文化的光影折射。香港导演王家卫力图把他心目中的上海人还原在一个大致特定的时空,因为是虚构,真实性有折扣,不可细考,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大多数百姓的生活并非繁花。电视剧《繁花》有甚好的传播效果,更多的是繁花寥落时人们对如真如假梦幻中繁花的追忆甚至是错忆。相比较,非虚构的《长乐路》则被评论为“太真实”,不少美国读者表达喜欢这些中国老百姓故事,因为这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故事”。其实书中的这些人物有不少是“新上海人”(非上海本地人),他们怀揣发财梦(改变命运的梦)来到上海,至于梦是否实现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做梦”。同为非虚构作品的《洋盘》,记载着一位外国人“沪漂”的所见所闻,正如沈恺伟自己所言,每一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在回家后变成“非正式外交官”,他们会向别人介绍这个国家,描述现代化城市和高铁、美食以及种种他们难忘的细节。“中国不再让人感觉太抽象,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地方,甚或是生活过、爱过的地方”。
现如今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其意旨在国家形象塑造或建构,体现了我们要在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上“有所作为”,但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关键在于传播效能如何,否则只会形成“内宣”“内循环”。当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之所以在国内外成为畅销书,清华知名学者秦晖就曾这样评价:“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先生去世,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中国时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即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悼念。崔天凯大使说,傅高义是杰出的中国问题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其一生中,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他称赞傅高义对中国的慧见不仅对研究领域的人而言,乃至对世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国内学术界目前关于国家形象塑造的研究,有“自塑”和“他塑”之说(甚至还有“偏塑”、“合塑”),如何辩证看待这些“塑造”形态,寻求对我有利且适合国际传播的国家形象,很值得研究。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多属“自塑”,国家形象的建构或在外传播则非完全是“自塑”。现今国际传播已超越了对外传播的概念,它应该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指对第三者的影响),而非单向的,如此国家形象自然就会有“他塑”。双向意味着多重声音,有对话有交流,非一种声音,国家形象有意无意的“合塑”,甚至传播过程中“他塑”出现“偏塑”(其中不乏国际舆论斗争的因素),这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自然状态,其呈现的是立体但非我一厢情愿或传统习惯的国家形象,问题是其最终产生的效果是不是均衡,是不是有助交流、促进理解(理解也并不等于接受或全面接受),是不是不至于走向对立冲突。对于“他塑”中的“偏塑”,要做具体分析,属唱衰抹黑、诋毁污蔑的,应坚决斗争予以回击,以降低其负面影响;若属误解误读,则应秉持包容的态度,加强持续对话,逐步建立共识。我们经常强调“和而不同”,其实在国际传播、国际交流、国际对话中尤显重要,多元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真实,强求一律则背离了事物的本性。
沿着跨文化传播的学理,我们再来看看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上面临的挑战。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国际传播中的中国故事,自然不是中文版的,而应是外文版的。在如今的国际话语格局下,英语世界依然是国际传播的主场。据有关统计,在全球的网站中,英文内容占比超过50%,中文内容仅占1.3%,而每一种语言必然伴生着与之适应的叙事方式,中文的叙事方式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未必在说英语的地方就被人们所欣赏。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有一部中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当这个书名译成英文时,聂华苓自己给出的是Far away, a river。设想再把这英文翻成中文,那又是什么?由此可见不同的语言在讲故事时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长乐路》的“半条马路”叙事带给我有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因建造上海南北高架道路,我家那段长乐路的房子因让路被拆,与我家一起消失的还有上海滩二手店的鼻祖(当年的网红店),我家正对面的“淮国旧”(淮海旧货商店)。“淮国旧”店面有1000多平方米,前门对着淮海路,后门就是长乐路,我从小就在它门前长大。在那个资源紧缺、商品匮乏、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从小就听大人说,只要对面商店有人排队,你就排上,一定是卖无需票证的“等外品”,“淮国旧”虽卖旧货,但绝无假货。我家当年有一辆英国兰令牌自行车,就是在“淮国旧”买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曾骑着它去外滩看大字报,很是过瘾。据说,“淮国旧”前些年换址重建,可我一次也没去过。
所有的故事都会带有讲述者个人(文化)记忆的痕迹,随着岁月的流逝,其真实性变得渐渐模糊,难以考证,失真、错忆成为常态,但感情、情绪的成份则日益加重。“戏短情深留神望遍这地方,回头的一刹皆寥落;繁华渐散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留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