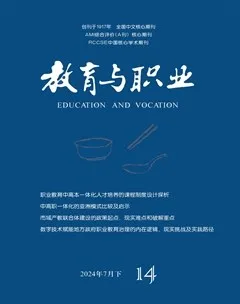中高职一体化的亚洲模式比较及启示
[摘要]促进中高等职业教育之间高质量、一体化衔接,是构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相较于西方教育体系,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体系与我国大陆存在更多共通之处,这些经济体的教育实践有着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通过系统梳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典型的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模式,从中提炼出成功的经验,涵盖招生遴选机制、课程体系设计、过程评价机制以及产教融合机制等多个维度,为促进我国中高职有效衔接、提升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中高职一体化;亚洲模式;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李小文(1992- ),女,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陈鹏(1982- ),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江苏" 徐州" 221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重点研究项目“职业院校课程教材与人才培养质量”(项目编号:JCSZDXM2022013)和2023年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高职教育质量第三方评价改革研究”(项目编号:B/2023/02/09,项目主持人:李小文)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4-0013-09
我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近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教育、科技、产业等领域探索出一系列中国方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蓄了重要力量和发展动能。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经济社会、教育科技、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向亚洲周边其他国家或地区学习。不同于西方,亚洲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体系和我国大陆有一定的相似性,更易于借鉴学习。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教育改革与发展包括中高职一体化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本研究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系统梳理三个亚洲经济体典型的大陆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模式,以期为我国大陆中高职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亚洲经济体中高职一体化的典型模式
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从产生背景、运作过程、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探究三大经济体中高职一体化探索的典型模式及其运作机理,为经验借鉴提供参考方案。
(一)日本中高职衔接的典型模式
日本中等教育包括普通高中、综合高中、技术高中等,毕业生均可选择进入职业院校、专门学校等中等后职业教育机构学习,形成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主要形式有基于高等专门学校的五年一贯制衔接和基于选拔推荐的分段式衔接。
1.基于高等专门学校的五年一贯制衔接。1951年11月,日本政令改正咨询委员会发布“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答申”报告。该报告提出设置一种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初中、高中一贯制职业高中[1],一贯制教育体系有了雏形。在此基础上,日本于1962年建立了一贯制高等专门学校,即包含高中和大学两个阶段在内的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以深入传授专门学艺、培养职业所必要的能力为目的[2]。五年一贯培养学制的建立,打通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学历进阶路径,成为日本中高职衔接的典型模式之一。
高等专门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以高中为职业教育的起点,以工学专业为主,在学制上推行五年一贯教育。根据办学主体的不同,高等专门学校有国立、地方公立和私立之分。2017年日本的57所高等专门学校中,有国立院校51所,公立、私立学院各3所①。高等专门学校的五年学习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学习中职教育的相关内容;后两年为第二阶段,主要学习高职教育的内容。在第一阶段,学生入学后的第一年统一学习基础课程,第二年进行专业划分,正式开始专业课学习。高等专门学校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各学校按照统一标准编制教学大纲,并就教学大纲的各项要求设置相关课程[3]。统一大纲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生在不同学校间流动的障碍。
高等专门学校的课程设计注重实践导向,课程体系包括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在五年制培养模式中,学生往往初期难以明确专业方向;第4~5学年,待学生对专业有更深入了解后,学校才开始开设选修课,便于学生按照实际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选择。以长冈中学高等专门学校2015级机械工程学科为例,五年通识必修学分分别为29、25、17、6、1;专业必修课学分设置分别为6、9、20、25、17;选修课从第四、五学年开始,学分要求分别为1和11②。为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高等专门学校非常重视课程的务实性,尤其重视实践教学和实习环节,实践课程占比较高。此外,高等专门学校也特别关注学生通识能力的培养,努力使学生成为“既拥有广泛基础性的人文知识也在特定领域中具有较高实践性与创造性”的优秀人才[4]。
学年学分制是高等专门学校对学生进行考核的主要依据。在学分制的考核框架下,学生以学年为单位获取学分。如果学生在某一学年获得的学分不足,则不能顺利进入下一级学习。在整个学习进程结束后,学校将对学生的学分进行清算,如果总学分未达到有关要求也难以如期毕业。值得一提的是,达到相应学历和技能要求的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也能够进入技术科技大学继续深造,为毕业生开拓更为广阔的人生道路[5]。这套严格的学分考核体系具有长效的激励作用,促使每位学习者努力学习,以达成学业目标。
2.基于选拔推荐制的分段式衔接。自日本启动“二战”后教育改革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大学的入学考核主要以各大学自主组织的学科学力考试结果为主。各大学自主选拔虽然尊重学校自治的传统,但在加剧升学竞争的同时,也出现中等教育应试化的倾向,甚至影响了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6]。在考试制度改革的呼声下,高等职业学校也积极探索新的入学考试制度,并逐步形成推荐与选拔优秀职业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专门院校的制度,被誉为“社会人员特别选拔制度”。该制度主要针对职业学校毕业生以及具备职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士,以满足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的要求。
尽管推荐选拔制度面向的群体是职业学校毕业生和社会人士,但实际上职业高中和综合高中职业科的毕业生也是该模式的受众主体。职业高中和综合中学在科目设置上具有多样化特点,其中很多科目能与职业类的短期大学和技术大学实现顺利衔接[7]。推荐入学主要有三种形式:指定校推荐、校长推荐和自荐。指定校推荐即高等职业院校指定中学的学生才有报考资格;校长推荐以公开招募的形式进行,由未指定学校的高等职业院校实施,未能获得指定学校推荐名额的学生也可报考;自荐即学生自己撰写申请书。虽然前两种选拔形式由学校或校长负责申请书撰写,但三种形式的考核均由书面审核与面试两大环节构成[8]。高等职业学校通过推荐选拔招收学生的方式具有五大特点:第一,招生数目有一定限制,通过推荐制招收的学生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50%;第二,考核形式有所创新,小论文撰写成为考核依据之一;第三,兼顾笔试与面试的形式,面试成绩占比更大;第四,注重基础知识,为通过选拔的学生提供基础专业课程的学习机会;第五,各高等职业学校进行推荐选拔并无固定时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报名参加考试,增加了升学成功率[9]。
具体而言,推荐制度采用多样化的选拔形式,与职业教育彰显个性特色的改革举措协同增效。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旨在全面评价学生不同层面的发展状况,主要措施包括制订多层次选拔方案、在高等职业院校推行落实推荐制度、适当提升对学生社会实践和文体活动成绩的考核权重等。基于学生综合能力考查的目的,日本的推荐选拔考核除了传统的以知识检测为中心的纸笔测试以外,还包括面试、小论文撰写、调查问卷等多样化方式。不管哪种考核方式,学生的核心素质始终是考核的重心。以木更津高等专门学校为例,毕业生的学业成绩是考核基础,学校对申请者以身心状况为代表的个性特征和以学习动机为代表的能力特征等方面都有明确要求,并且能够具备理工学科学习的潜力③。
(二)韩国中高职衔接典型模式
韩国职业教育体系以学校教育为主体,主要由高中阶段的职业高中、专科层次的专科大学以及本科层次的产业大学构成。韩国中高职衔接主要以专科大学和产业大学为主体,形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衔接模式。
1.面向专科大学的中高职衔接。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擘画了“第三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意欲将以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重化学工业转变,实现经济发展重心的转向。1973年政府出台《加强重化学工业教育方案》,对技术人员的培养提出具体要求。但这一时期,韩国国内承担技术工人培养职能的机构主要有初级大学、专科学校、实业高等专科学校等,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引发相关教育改革。1977年,文教部重新修订《韩国教育法》,将初级大学、专科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统一改编为专科大学。专科大学以教授、研究社会各领域有关的专门知识和理论、锤炼才能、培养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中坚职业人才为目的[10],成为韩国高职教育的重要力量。
韩国专科大学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修业年限为2~3年。从政策偏向性来看,韩国专科大学在招收新生时,职业高中毕业生以及持有专业资格证书者享有优先权,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这两类群体,进而更好推动职业高中与专科大学的衔接[11]。除了优先录取的优惠政策以外,专科大学还对职业高中毕业生、具备国家技术资格体系认证的技术人员以及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保留50%~60%的入学名额。学生入学后,专科大学将按照《国家技术资格法》严格进行学生技能培养工作。若专科大学毕业生不能在技能士一级和二级的国家资格考试中取得及格及以上的成绩,学校将不向用人单位推荐[12]。
专科大学的课程设置紧扣“产学合作”“实际应用”“有效实习”“国家资格技术证书”“英语和计算机教育”等多维度育人导向,增强课程学习对学生技能发展的适切性,解决好“如何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现场实务能力”这一问题[13]。在具体学习过程中,专科大学向学生提供渔业、护理、家政、环卫、农业、社会实践、艺术、体育等丰富的专业技能课程[14]。此外,不同的学生会因学制的长短而有不同的总学分要求,两年制学生需在毕业前取得80学分,而三年制毕业学分要求则比两年制多40学分;专科大学对学生每学期获得的学分上限有相应规定,每生每学期获取的学分不得超过24分[15]。在修业年限期满后,学生也拥有多元的升学选择路径,不仅可以在专科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深化课程”学习;还可以按照个人意愿,升入普通大学和产业大学继续学习深造[16]。
专科大学的入学考查涵盖学生高中整个阶段的综合表现,并规定高中在校成绩占入学考核总成绩的30%。同时,将高考学历考试成绩、实际技术技能考查成绩、面试成绩三项进行累加,分数由高到低录取。考试科目主要有“国语”“英语”“数学Ⅰ/Ⅱ”“国史”“国民伦理”5科[17]。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传统的纸笔测验成绩,专科大学的入学选拔更关注特定职业所对应的综合能力,换言之,学生的适应能力和获得的资格证书在录取过程中相当重要。此外,专科大学的招生入学考试较为灵活,主要体现为考试时间和日程安排并无统一规定,学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有计划地开展招生录取工作。
2.基于产业大学的中高职衔接。为紧跟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以及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韩国于1982年创办第一所开放大学,为延续学校教育者提供继续学习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机会。1997年,韩国重新修订《高等教育法》,将先前实行继续教育的开放大学统称为产业大学,并提供学士学位课程。产业大学对接产业时代向劳动者所提出的理论与技术要求,以产业人才培养为中心任务,进而推动产业社会的发展。在韩国“六三三四制”体系下,产业大学与专科大学共同构成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机构。本科层次的产业大学使得韩国高等职业教育层次不断提升,进一步丰富了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升学路径与选择。
产业大学没有固定的实体校园,从办学形式看,它更偏向于一种开放式大学。在韩国纵横交错的教育体系网络中,职业高中毕业生除了转入专科大学,还可直接升入产业大学。同时,专科大学的毕业生不仅可以升学至普通大学三年级,也可升入产业大学三年级完成更高层次的职业技术学习;产业大学的毕业生可以继续接受普通或职业的研究生教育[18]。以三星电子公司建立的社内大学——三星电子工业大学为例,学校自2001年开设专科课程,2004年增设四年制本科课程,以高中及专科学历的社员为主要招生对象;从2005年起允许学生以三年的年限取得学士学位,在2006年与成均馆大学联合培养硕士、博士[19]。韩国产业大学在提高职业教育层次的同时,实现了“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研究生”教育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打通了职业人才培养更长远的通道。
在课程设置方面,产业大学的课程能够与高中基础教育课程相衔接,主要包括准学士课程和学士课程。准学士课程是将两年职业高中课程和两年产业现场的大学课程相衔接,学士课程则是将两年产业准学士课程和产业现场型大学的第三、四学年的两年课程衔接起来[20]。此外,产业大学的课程编排不再以理论性的普通教育课程为遵照,而是将应用导向与实用价值融入课程体系建设,切合当地的产业结构与经济需求,以必修、选修相结合的方式开设修养课程、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三类主要课程,并加以强制性与义务性的现场学习,拓宽学生的理论知识,强化学生的职业技能。
工作现场是产业大学的主要学习场所,教育对象大多数拥有企业员工与学生双重身份,因此产业大学的入学门槛较低,更强调学生的职业理论知识和技能实践表现。同时,产业大学的学制规定和学习方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主要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通过在线教育方式实施专业课的理论教育与基础课程教育,获得规定学分者方可取得相应学历和学位。相较于普通大学的毕业生,获得产业大学规定学分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享有优先推荐的机会,并在就业后免去职前培训。
(三)我国台湾地区中高职衔接典型模式
我国台湾地区具有较为健全的技职教育体系,其中,实施中等技职教育的机构主要包括高级职业学校和综合高中;高等技职教育包括专科层次和本科层次,专科层次技职教育机构包括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和五年制高等专科学校(简称为“五专”);本科层次技职教育机构包括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学制又分为两年制(简称为“二技”)和四年制(简称为“四技”)。作为高等技职教育的延伸,硕士、博士层次的技职教育主要由技术学院的研究所承担。在完善的技职教育体系支撑下,我国台湾地区中、高等技职教育层次之间相互贯通和衔接,并形成两种主要衔接模式。
1.基于“五专”设计的一贯制衔接。在我国台湾地区,最早的五年制专科学校成立于1949年。而后随着我国台湾地区技职教育向本科层次高移,一些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的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但“五专学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在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中设立的“五专部”。“五专学制”为我国台湾地区产业发展与经济腾飞培养了大批应用型技术人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据统计,我国台湾地区的“五专部”存在于12所专科学校、10所技术学院以及33所科技大学中,2019年在校生人数达到79157人,占整个专科教育在校学生数的94.3%[21]。
“五专”生源主要是国中(初中)毕业生,经过五年制中高职连读获取副学士学位,毕业后可直接就业,或升入二技修读学士学位,属于典型的中高职一贯制衔接。“五专”的入学方案呈现多元化特征,主要有两种类型:免试入学和特色招生入学。其中,免试入学即免除入学测验,依照学生的兴趣与志愿等选择合适的学校就读,并规定学校不得私自订立申请条件。免试入学的名额应占学校总核定招生名额的80%以上,若申请者过多而超出学校核定招生名额,则依照学生国中阶段的健康与体育、综合活动、艺术和科技四个学习领域的成绩按顺序录取,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成绩不予考虑。进行特色招生的“五专”主要是拥有特色课程的专科院校,通过公开选拔,遴选符合志向、兴趣与能力的学生入学,具体包括甄选入学和考试分发入学两种方式,招生名额不能超过学校总核定招生名额的25%[22]。
在专业设置方面,“五专”采取“总量管制”的原则灵活调整,以支援重点产业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如近年来主要针对绿色能源、观光旅游、生物科技、文化创意、精致农业与医疗照护等重点产业领域更新专业与教学计划。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延续我国台湾地区技职教育体系群科课程的特色之外,发挥一贯制培养的优势,将课程结构与逻辑体系按照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地科学设置。随着年级的增长,基础课逐年减少,专业课逐年增加。通识课主要设在第1~3学年,选修专业课主要设在第3~5学年[23]。从学分设置来看,专业课程和实训课程占总学分的60%以上,体现出以专业技能和实习实践为导向的课程规划理念,重视学生实操技能的提升。此外,多样化的选修课程也是我国台湾地区“五专”课程设置的特色。尤其是通识选修课程的开设通常涵盖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活应用、生命伦理与环境关怀等多领域,学生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跨院系和专业进行自由选择,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综合拓展起到重要作用。
2.基于“多元入学”的分段式衔接。我国台湾地区技职教育体系结构的完善、不同层次技职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离不开其以“多元入学”为特征的招考制度设计。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颁布《四技二专多元入学改进方案》,提出逐步试行甄试入学、技优甄选和登记分发等多元化入学方案改革,明确技专院校多元入学方案的合法性地位。2000年以来,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技职院校的招考制度与多元入学方案逐步发展成熟,实行分类招生制度,并制定面向不同生源群体的升学办法,确保生源多元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通道的畅通,进一步提高中高职衔接的灵活性。
我国台湾地区以学制为依托的中高职分段式衔接主要指中等技职教育毕业生(包括高级职业中学、综合高中)升入“二专”和“四技”,毕业后分别授予大专学历、副学士学位,以及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在政策法规的支持下,它们的入学方式多元,但总体来说实行“招考分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赋予高等院校充分的自主权。具体来说,进入“四技二专”有甄选入学、登记分发、技优甄审和保送等多条路径:甄选入学主要面向高级职业中学毕业生和综合高职毕业生,申请者将参加指定科目甄选,考核方式包括资料审查和面试,由各院校自行组织。例如,有参加相关科类的竞赛获奖或资格证书,则另有优待加分;登记分发入学或单独招生,主要面向高级职业中学毕业生和参加“二专”夜间部、“四技”进修部在职专班单独招生的学生,将以统一入学测验成绩为依据申请入学,考试内容为高级职业学校课程内容,以统一入学测验成绩志愿登记分发;技优保送是面向学生中技术优异者的推荐保送,这类学生可以不用参加统一入学测验而免试入学,对“技优”的认证一般以国际性技能竞赛或全国性技能竞赛奖项的前三名为依据。
为保证不同层次技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接续性,21世纪初我国台湾地区启动“技职教育一贯课程改革规划”项目,通过重新调整原有分层设计的课程结构统整各级各类课程资源,实施集群课程,从而实现技职教育系列课程的一体化构建。具体来说,在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统筹下,按照职业群的内涵与专业属性,将原有300多个专业科系整合为17个“群”,如机械群、农业群、食品群、水产群等;并在“群”下设“科”,通过按群规划、以科分类的原则来设计某一个“群”三级层次(中职层次、高职层次和本科层次)的一贯制课程。以机械群为例,中职层次包括机械科、模具科、机电科、制图科等16个类科;高职层次包括机械工程科、模具工程科、自动化工程科、纺织工程科等16个科类;本科层次则包括机械工程系、机械材料工程系、造船工程系、纺织科学系等18个科系[24]。在此基础上,各级技职院校的具体课程方案需由我国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和院校共同制订,其中由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课程占比为20%~60%,一般中职层次的课程比例为50%~60%,高职层次的课程比例为40%~50%,本科层次的课程比例为20%~40%;而剩余课程可由各学校自主设计,以保持校级发展特色和满足当地产业发展需求[25]。总的来说,我国台湾地区中高职课程一体化的设计模式有效实现了不同层次技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质性衔接。
基于“多元入学”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中高职衔接过程中的考核评价也有多种方式。一方面,登记分发、单独招生等方式的中高职衔接,根据学校要求和不同科系的实际需要,仍需要考专业大类的相关科目。以我国台湾地区彰化师范大学商业教育学系(4年制)日间部联合招生应考为例,包括公共科目4门(国文、数学、英语等),总分为350分;专业科目2门,总分为400分[26]。由此可见,在高一层次教育入学测试中更突出对专业能力和素养的考查。另一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衔接考评过程更多秉持“学力比学历更重要”的理念,学生的升学资格并非仅凭一场考试成绩决定,而是综合考虑在专业实务技能如证照、竞赛、专利、论文等方面的表现。学生可以凭借参加技能大赛获奖或取得资格证书来获得一定加分,如以职业证照为例,我国台湾地区职业证照分为丙、乙、甲三级,获得这三级职业证照的学生可在专业科目总分的基础上加上总分的5%、10%和15%[27],由此增加了实践操作能力较强考生的入学机会。同时,职业证照也是学生步入工作岗位后升职加薪的重要凭证,因而受到多数学生的追捧。
二、亚洲中高职一体化的经验与启示
为推进中高职教育一体化,我国教育部2011年印发《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树立系统培养理念,探索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制度,注重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接续培养。基于此,以江苏省为代表的省份开始探索中高职一体化的多元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一批较为典型的衔接模式。为进一步理顺中高职之间的接续关系,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为中高职衔接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并强调要探索“长学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机制。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支持长学制人才培养。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意见》,指出支持五年一贯制办学,鼓励中职与职业本科衔接培养。然而,我国在中高职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还有很多难点和痛点,如招生机制不完善、课程体系衔接不畅、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在借鉴周边经济体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一)优化招生遴选机制,畅通技能人才通道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中高职衔接招生机制方面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招考方式多元灵活,考试流程统一规范,在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和特点进行个性化选拔的同时,也保证了招考公平性;二是考核过程侧重对技能应用能力的评估。这种招生模式不仅体现了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视,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和可能性。鉴于此,我国的中高职衔接招生机制可从两方面改进:一方面,完善分段式招考选拔机制,建立起规范的技能考试体系。这不仅涵盖高中后的专业技能高考,还应包括初中后的技能中考,确保各教育阶段的顺畅衔接。在此过程中,尤应强化技能课程的考核权重,充分参考学生在中学阶段通用技术、信息技术、劳动课程以及综合实践课程的成绩,从而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水平。另一方面,改进贯通制转段考试机制,简化烦琐的考试评价流程,尤其应避免多个院校各自主导的“一对多、多对多”碎片化考试评价体系。为此,可由省级教育部门在统筹公共课考试的基础上组织专业大类考试,确保评价标准的统一性和公正性。此外,还应进一步推广推荐制和保送制,强化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特别是对在技能大赛中表现优异、被认定为技术能手的学生的认可,为他们提供更直接的晋升通道。
(二)强化课程一体设计,弥合教育层次鸿沟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中高职教育衔接上均显著强调课程的一体化设计与无缝对接,因为课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系统培养来说至关重要。一体化的课程设计能够确保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都能平稳过渡,从而提升教育效果。鉴于此,我国应从中得到启示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中高职学校以及企业应共同参与课程的一体化顶层设计。教育部应负责制定统一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教学标准以及教材研发标准,从而为一体化的课程建设提供明确的指导。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的中高职衔接模式,在课程设计上也应有不同侧重。针对分段式的中职和高职教育,应着重加强一体化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从技能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规律出发,对课程体系进行系统性规划和设计;对于贯通式中高职教育模式,应设置起桥梁和过渡作用的衔接课程,以确保学生学习的连贯性和深度;而对于五年一贯制教育模式,则需要形成独立且完整的培养方案、课程大纲以及教材体系,避免课程的简单拼接,确保教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能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这些措施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中高职教育的顺畅衔接,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强化过程评价机制,提高技能人才质量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中高职教育衔接中都特别强调过程性的考核与评价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关注学生的最终成果,也更加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展现的技能提升、态度转变和创新能力,从而确保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和质量。借鉴这些地区的经验,我国中高职教育体系也应强化过程评价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加强对学生常规性和周期性技能的考查,不限于期末或结业考试,要贯穿整个学习过程。通过设定定期的技能测试和项目评估节点,教育者和学校能更精准地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技能习得情况,有助于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短板,为他们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辅导和学业支持。另一方面,引入淘汰机制也很有必要。这种机制能够激励学生持续努力,避免贯通制人才培养模式中可能产生的懈怠心理。淘汰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这种方式促使学生保持对学习的热情和专注,确保他们在中高职教育各个阶段都能达到既定的技能标准,同时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自我管理能力以及持续学习的动力,从而整体提升中高职贯通式人才培养的质量。
(四)完善产教融合机制,增强技能培养适应性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中高职教育衔接中尤为注意与产业的联系,将产业需求渗透到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等方面,强调产教融合。鉴于此,针对我国中高职衔接的现状,可以从两个方面优化:一方面,强化与产业的深度互动与合作,确保中高职技能培养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中高职院校与产业的合作应渗透到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合作进行一体化课程设计等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既确保中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能够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又有效避免教育内容的断层和重复,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加强与行业代表性企业的长期合作,保障实习实训的效果。企业真实环境的实习实训可以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职场环境,锤炼职业素养。通过中高职阶段一体化的实习实训安排,让学生在不同阶段获得持续而系统的技能训练,帮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深化对专业知识的理解,确保学生技能成长的连贯性和有效性,提高技能习得的适应性。通过这样的合作与安排,能更好地培养出既具备理论知识又拥有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从而有效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并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总体而言,中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凸显了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两个层次在培养理念、过程及评价等方面的紧密衔接与协同深化,确保了教育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贯通的职业技能培养路径,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律和学生个体成长的现实需求,对于推动职业教育向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中高职一体化模式的比较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职业教育发展的全球性视角,使我们对中高职一体化的教育内涵与外延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不仅拓宽了教育研究的视野,也为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未来,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中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将成为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我们应继续深化对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构建更为高效、科学且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求的中高职一体化教育体系,不断创新教育模式与方法,推动中高职衔接深入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我国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助力国家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注释]
①参考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方网站。
②参考日本長岡工業高等専門学校官方网站。
③参考日本木更津工业高等专门学校官方网站。
[参考文献]
[1]沈学初.当代日本职业教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14.
[2]胡建华.战后日本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9.
[3][5][9]王力维.日本中高职教育衔接的模式、先进经验及借鉴[J].教育与职业,2019(9):90-96.
[4](日)武尾文雄,岡田益男.八戸高専における学科等改組の概要[J].日本高専学術誌,2016(1):9-14.
[6]日本教育学会入試制度研究会.大学入試制度の教育学的研究[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54.
[7]金盛.涨落中的协同:中高职衔接一体化教育模式研究[D/OL].重庆:西南大学,2013[2024-04-20].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wZretP9BaFu_-Brpq1pgHzSRxIiYIvwA
jMo0bIS_bQGfKWvTHIsK1tIt7B5Sns9gb7wPr8DygcUKYAZ5Hii
L5vOOe7usVjJaJ0C0OKtdkXzBf-S3a0RAptqapRZ89ey8qUn0kEu
hKIHaQAP1Dsdjg==amp;uniplatform=NZKPTamp;language=CHS.
[8]朱秋寒.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的特点及启示[J].职教通讯,2021(3):31-40.
[10]安期成.大学教育史[M].首尔:学知社,2017:450.
[11][16]索丰,孙启林.韩国的专科大学教育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02(5):14-18.
[12]田以麟.今日韩国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27.
[13][17]孙启林.战后韩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146,147.
[14]秦虹.国外中职与高职衔接模式的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16):51-53.
[15]姜大源,吴全全,刘育锋,等.他国动向[J].职业技术教育,2005,26(18):14-34.
[18]王彦力.转变观念:韩国发展职业教育做法与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23):51-53.
[19]刘宝存,庄腾腾.产业大学的世界图景:理念基础、办学模式与未来走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0):57-65.
[20]夏建国.新型产业大学:特色型大学发展的新路径——韩日产业大学办学模式的中国视角[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1):42-45.
[21]兰金林.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的实施现状与改革对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OL].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1[2024-04-20].https://kns.cnki.net/kns8s/defaultresult/index?crossids=YSTT4HG0%2CLSTPFY1C%2CJUP3MUPD%2CMPMFIG1
A%2CWQ0UVIAA%2CBLZOG7CK%2CEMRPGLPA%2CPWFIRAGL%2CNLBO1Z6R%2CNN3FJMUVamp;korder=SUamp;kw=%E5%
85%B0%E9%87%91%E6%9E%97.%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8%B4%AF%E9%80%9A%E5%9F%B9%E5%85%BB%E6%A8%A1%E5%BC%8F%E7%9A%84%E5
%AE%9E%E6%96%BD%E7%8E%B0%E7%8A%B6%E4%B8%8
E%E6%94%B9%E9%9D%A9%E5%AF%B9%E7%AD%96%E7%
A0%94%E7%A9%B6.
[22]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五专多元入学方案[EB/OL].(2021-
08-10)[2023-10-21].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741.
[23]欧剑锋.台湾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及启示[J].职教通讯,2019(23):73-79.
[24]李红卫.台湾跨世纪技职教育一贯课程改革及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06(4):34-37.
[25]黄京钗.海峡两岸中高职教育衔接机制比较研究[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96-100.
[26]左彦鹏.台湾地区职普沟通、中高衔接的运行机制及其对我国大陆地区的启示[J].职教通讯,2003(12):59-60.
[27]周正.台湾技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启示[J].职教论坛,2008(7):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