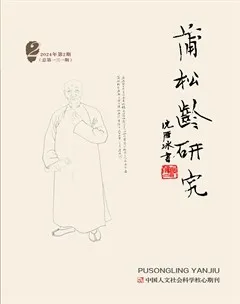从用典看清代花仙文言小说的知识书写倾向
收稿日期:2023-12-05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小说知识学视域下的清代文言小说研究》(2021BS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静(1992- ),女,重庆合川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摘要:清代花仙文言小说好用典故,与前代文言小说侧重叙事的记录方式形成迥异。通过典故叠用、暗用以及反用等方式,实现了知识的重构,使得清代花仙文言小说带有明显的知识书写倾向。这与清代花谱类书的繁荣以及花谱类书侧重事典的体例有关,可以说,花谱类书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支撑。知识书写促使花仙文言小说具有独特的阅读审美效果,知识对位是破译密码的关键。分析清代花仙文言小说的用典情况,可以进一步考察文言小说逐渐脱离“史部”实录、带有明显创作特征的文类演变进程。
关键词:清代;志怪;传奇;用典;知识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清代花仙文言小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明显超越,对于研究文言小说在文言小说史上的演变有着重要价值。以清代单篇传奇《看花述异记》、文言小说集中《聊斋志异·黄英》《耳食录·长春苑主》《耳食录·吴士冠》《里乘·林妃雪》为代表的诸篇花卉志怪故事,其运用典故来生成小说结构、塑造人物形象、构思故事情节等特点,与前代花卉文言小说重记录、重叙事的风格相比,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学界对于花仙文言小说的研究多集中在《聊斋志异》一书,且多从形象、文化、诗意、寄兴等角度讨论 ① ,对于用典特色尚未有专文阐述。典故的使用直接影响到文言小说书写方式向知识的一面靠拢,其背后成因与审美效果也值得深入思考。
一、用典类型与知识重构
清代花仙文言小说的用典颇具特色。从用典方式上看,可以分为典故叠用、典故暗用和典故反用三类。文言小说中用典并不似诗词用典那样,为了在有限的语言中拓宽诗词的寓意和意境,而是通过典故的重组,重新构造文言小说的故事内容,即实现知识的重构。
(一)典故叠用
典故叠用是指在文言小说中罗列叠加多个典故的用典方式,清王晫的传奇小说《看花述异记》及清乐钧《耳食录·长春苑主》即是如此。《看花述异记》讲述“我”夜晚醉酒后游览沈氏园,并与化作花仙的历史美人在园中相遇的故事。小说全篇用典多达十九处,涉及花姑、殷七七、梅妃、花太医、花师、袁宝儿、绿丝醉桃、魏夫人、卢女、太真、薛琼琼、红线、徐月华、弄玉、绿珠、阿纪、念奴、丽娟、绛树等与花卉相关的典故。此篇文言小说运用典故呈现了一个集美人、器乐及歌舞为一体的花国空间,脱离了单个的典故内容,通过杂糅与重组,使之符合故事发展的逻辑。《四库提要》卷一三四中说:“《看花述异记》摹仿牛僧孺《周秦行记》,聚历代妃主,备诸冶荡,尤非所宜。” [1]3430《周秦行记》是一篇带政党攻击目的的虚构故事,原题唐牛僧孺撰,实际是唐韦瓘所撰 [2]580。文中写牛僧孺误入汉文帝之母薄后庙,与高祖戚夫人、薄太后、王昭君、潘妃、杨玉环、绿珠等人相会的故事。王晫的《看花述异记》虽然采取《周秦行记》一样罗列历史典故以重新构建文本的手段,但是两者相较,还是存在较大区别。一是《周秦行记》所列薄太后、王昭君、杨玉环、绿珠等典故,除了共同的女性身份之外,在逻辑上没有任何联系,在一篇行文中将她们拼凑在一起未免牵强,且背景混乱无层次,因而未得称为佳作。而《看花述异记》以花卉为中心,所有人物皆是与花卉相关的典故,比如黄令征为花姑,传为花神,《淮南子》《花木录》《月令广义》等皆有记载。同时,《看花述异记》中人物排列整饬,王恒展认为这种结构颇似近代的意识流小说:“从五代志怪小说《集仙录》中的花姑黄令征(黄灵徽),到《续仙传》中的鹤林寺杜鹃、《梅妃传》中的梅花和梅妃;从花太医苏直、花太师宋仲儒,到《南部烟花记》中的袁宝儿和迎辇花;从唐代李邺侯公子的绿丝、醉桃二妾,到《乐府杂录》等所载的许永新;从晋代的卫夫人、汉末的卢女,到唐代的杨太真、薛琼琼、红线,再到南北朝的徐月华、汉代的王昭君、秦国的弄玉,再到晋代的绿珠、阿纪;从善歌的念奴、丽娟,到善舞的绛树……这些故事和人物表面看来时空颠倒、互不相关,但在本文中却或以花木为媒介,或以音乐为统属,或以歌舞为联络,总而言之是在爱美思想的统摄之下,在作者的梦境当中聚集到了一起,并组成了一支优美和谐的颂歌。” [3]2262可以肯定的是,《看花述异记》并非将各类典故处理成简单的堆砌,而是按照历史、音乐、舞蹈等层次归属叠加,从而前后相互勾连,不至于小说故事在典故内容的影响下断裂,从而将故事整体包裹得更加严实、紧凑。这样的逻辑思维是《周秦行记》所没有的。二是从艺术角度看,《周秦行记》的成就主要在于人物描写较为出色,因为作品突破了六朝小说,在同时代小说的人物描写中,也是少见的。《看花述异记》则更具才情,要想创作出此类小说,须得对历史典故十分熟稔,才能做到信手拈来,且于不经意间化用其中,不着痕迹。如其中运用花太医、花师典故,太医院、太师府皆是宫中司署,王晫巧妙地将其安排在见过帝妃身份的梅妃之后,使得与宫中背景一致,可以看出前后行文思维缜密。
清乐钧《耳食录·长春苑主》同样叠用多达十八处典故来构造小说情节。《耳食录·长春苑主》较之《看花述异记》,有用典重合的地方,比如梅妃、杨妃、徐月华、丽娟、绛树等。但其更突显的是运用僻典,尤其是后半段夫人召众花神为元生饯行时的歌舞场面,卢女弹琴,落花起舞,“于是,崔茝奴理筝,宋伟吹笛,关小红奏琵,徐月华弹箜篌,檀板玉箫,更番迭奏。歌舞纷沓,大都丽娟、绛树、飞鸾、轻凤之俦,尽欢而罢。” [4]39短短几句话,连用数典,且崔茝奴、宋伟、关小红、飞鸾、轻凤等皆为偏僻典故。事实上,僻典更能体现出文言小说的知识特征,其中还显示了作者的知识储备和运典才能。
(二)典故暗用
清代花仙文言小说中的典故暗用较典故叠用的方式更为高明。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黄英》叙菊花仙黄英与弟陶生艺菊致富的故事,全篇小说暗用陶渊明之典故。首先,黄英与马子才讨论安贫乐道和勤劳致富的问题,小说中直接以陶渊明为两人讨论的焦点:“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曰:‘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然贫者愿富为难;富者求贫固亦甚易。床头金任君挥去之,妾不靳也。” [5]1449-1450马子才认为黄英与弟陶生的商人举动与陶渊明的安贫乐道思想背道而驰,从而构成小说人物的矛盾。其二,黄英之弟陶生,醉酒倒地后化作菊花,黄英掐其梗埋在土中,数日后再开花,闻起来有酒香,取名“醉陶”。翻看历代菊花谱录,并没有此品种名,实为蒲松龄杜撰。其实,“醉陶”之名暗用了陶渊明之典故,宋释文珦撰《潜山集》卷十二《秋晓访菊》云:“醉陶为尔早辞官,醒屈曾将当夕餐。我爱露丛深似染,晓寻特地犯清寒。”由于陶渊明与菊有莫大渊源,历史上咏菊之作,基本都会用到陶渊明之典。同时,陶生醉酒之自由不羁的形象与陶渊明如出一辙,陶生“曾烂醉如泥,沉睡座间。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 [5]1451;这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欲醉眠卿可去”等形象十分贴近。在历史的长河中,在知识的海洋里,菊花是陶渊明之化身,已然成为文人心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常识,菊花与陶渊明成为一个固定搭配。可以说,《黄英》是暗用陶渊明之典来构造了黄英与马子才两人的话语冲突,也暗用陶渊明之典来塑造了陶生放浪不羁的形象。可见,用典对于文言小说的书写有着重要作用。
同样,清乐钧《耳食录·吴士冠》亦是暗用典故来设置人物和情节。小说叙吴士冠在沈氏别业遇二女,二女子分别是桃、柳所幻化的花妖,二女争论不休,互相指责对方魅惑吴生,最后一同消失。绿衣女子出场时咏诗:“小院春愁听了规,风残舞断小腰肢。韩郎忽走章台马,烟散红楼月上时。”第三句典出唐许尧佐传奇小说《柳氏传》和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诗人韩翃与姬女柳氏事,韩寄柳一诗:“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吴士冠》中绿衣女子便借此典故暗示自己柳精的身份。如果读者熟悉韩翃的典故,自然会对这位绿衣女子的身份产生一个期待。而桃花精与柳精争风吃醋、相互论争的场景,更是文言小说用典之范:
生犹未信,忽有排闼而入者,乃绿衣也。指绛衣骂曰:“汝本妖妄,乃间我乎?”绛衣亦骂曰:“颠狂婢子,只合向长安道上,牵行人衣袂,何得闯入武林源,诱人渔郎耶?”绿衣曰:“吾先人九烈君,好奖士类,曾以蓝袍赠李秀才,李遂登第。词人学士,往往称之。即清风亮节如陶彭泽,犹心折焉。安所谓颠狂,为汝轻薄随流者口实也!且即有是,于汝何与,而妒若此?岂犹谓阮宣之妇,剑锋不利耶?” [4]88
桃花精指责柳精诱惑吴生,运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武陵人捕鱼为生,桃花落英缤纷的桃花源之典,道出吴生本是自己相公。而柳精用李固之典反驳之,“九烈君”指柳树神,后汉李固行古柳下,闻有弹指声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无疑。”(见《三峰集》)道出自己自祖辈始便高风亮节。自称不是“阮宣之妇”嫉妒桃花,阮宣典出《太平御览》卷九六七引南朝宋虞通之《妒记》:“武阳女嫁阮宣,武妒忌。家有一株桃树,华叶灼耀,宣叹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树,摧折其华。” [6]553桃花精与柳精以一系列机智的知识交锋完成了争论,其典故既符合人物身份,又点出了嫉妒的主题,可谓是知识运用十分恰当。相较于一般的妇女争吵,知识点缀使得情节更加生动有趣。甚至桃花精与柳精两人物的设置,也是暗自用典,桃、柳为韩愈侍妾绛桃、柳枝的合称,宋王谠《唐语林·补遗》:“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可见,典故成为清代文言小说人物设置的一大来源。
(三)典故反用
实际上,上文举例的《聊斋志异·黄英》旨在提倡勤劳致富,已经反用了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典,清乐钧《耳食录·长春苑主》与清许奉恩《里乘·林妃雪》更是反用典故来叙写小说内容。典故反用说明作者在运用知识的时候,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以达到激起读者阅读兴趣的目的。如《耳食录·长春苑主》元生将花神分别定为香品、艳品时,将西施、王嫱等列为“狂艳”,引发西施、王嫱不满:
西施闻之,请见曰:“妾虽鄙陋,君何至以狂艳见目?”元谓:“卿泛湖之役,固当小贬。”西子辩曰:“沼吴之后,妾实从伍相于江流。陶朱何人?妾宁俪之,以负君恩而丧妇节也?”元矍然曰:“微卿言,吾几误矣!”有顷,王嫱亦来泣告曰:“妾以薄命,为画工所误,远嫁沙漠,以君命故,不敢违。未尝一日忘汉也。而佞臣秉笔,诬以聚麀之行,妾饮恨黄沙,未由昭雪,故使冢草独青,以明区区之志。而僧儒《周秦行记》乃敢肆为狂言,深相汗蔑,此妾之所痛心而茹愤者也。君其察之。”元再三引咎。乃列二人之幽香,始悦而去。[4]38
元生因西施与范蠡归去五湖,当作小贬,西施诘问:“以负君恩而丧妇节也?”表明自己坚贞之态度,这与历史上传闻西施私奔范蠡甚至生子之事相反。王昭君嫁塞外,遭画工、佞陷害,还在《周秦行纪》中被污蔑,实非其个人意愿。这里反用西施与昭君之典,暗含了作者对两位女性的历史评判。
又如《里乘·林妃雪》反用典故来刻画人物形象。在众仙宴饮中,熊生与众花仙产生了如下对话:
东坐一美人,着藕色五铢之衣者,笑曰:“夫人曲终奏雅,毫发无憾,惟罗夫人笛声入破,稍滞半板,赖贵主灵心妙腕,巧为偷声,不然,几难合拍。意者心念羊生,神移手涩耶?”上坐者笑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似此吹毛索瘢,得勿令夫人齿冷?”着葱绿者叹曰:“妾当日不过念羊生尚有仙骨,不惜以一粒金丹度其出世,固无他事,一经慧业文人哓哓饶舌,遂不觉轻薄殆尽矣!”西坐一衣青绡褂者笑曰:“姊姊与羊生一段因缘,尚属形迹可疑,尤可笑者赵师雄小子,偶然醉寐,梦中便妄生幻想。若非翠羽唤醒,又要造出几许黑白矣。”东坐一衣紫罗襦者笑曰:“师雄仅托于梦,犹不敢公然唐突。惟有老逋无赖,判将一种清寒骨,老气横秋,硬呼我辈作妻,不尤令人喷饭耶!”满堂大笑。[7]46-47
在这场对话中,小说连用女仙萼绿华夜降羊权家施以金丹、赵师雄醉憩梅花下梦遇梅花仙、林逋隐居杭州孤山以梅为妻三典。但是与历代文人以此为雅事不同,小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梅花仙的角度对三典作了新的评价。这样的逻辑安排,一是符合花仙的仙家身份,仙家一般不会产生人类感情;二是刻画了花仙高傲、清冷的形象,花仙不同于花妖,花妖妖冶多情,而花仙则清冷高洁,不可追攀;三是与旧文本形成反差,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典故在小说中的运用是需要谨慎的,如果只是典故正面的使用和堆砌,只会得不偿失,失去小说的可读性,枯燥无味;而若能将典故反转,推陈出新,则可以在小说中找到典故的乐趣,并且有助于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里乘·林妃雪》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二、花谱类书与知识支撑
清代花仙文言小说的知识书写倾向离不开花谱类书的知识支撑。花仙文言小说在宋前很长一段时间相对沉寂,与此同时,花卉类书与类书花卉门也是自宋代才开始逐渐发展,两者不可谓毫无关联。
宋前花卉知识是很少的,花是作为草木或者果子的附属,植物开花是为了结果或者药用、食用,不是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的观赏性植物。如唐《艺文类聚》将芍药、百合、兰、菊、杜若、蜀葵、蔷薇等归入草部,与兔丝、芣苡、女萝等同属一类。唐《初学记》在宝器类后附花草一类,可见在时人眼中,花草甚至不配专门列一个门类。宋《事物纪原》草木花果类中花卉记载极少,只有牡丹、一捻红两种,并与其他苜蓿、牛尾蒿、何首乌植物归属一起。宋《太平御览》百卉部也多是草、葛、藤诸草木类,花的种类只有菊、芙蕖等,其名虽曰“百卉部”,但“卉”却不是专指花卉,而是草的总称。宋《事类赋》中桃赋、李赋、梅赋、杏赋、梨赋都归属于果部,尽管其所辑内容不少是关于花的,如梅赋中有“陆凯寄江南之春”,“寿阳之妆更新”,柰赋中有“白花兴谣既自于天公织女”,“英半绿而半紫”等,皆是咏梅花、柰花之典实。可见,古时虽有花,但花多从属于草木之类,是从食物、药物、饰物等方面去认识它的。
对花卉知识的认知缺乏独立性和观赏性的眼光,导致宋前关于花卉的志怪小说极少。宋代《太平广记》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型小说总集,其辑录的“花卉怪”一列却只有12条,其中《龙蛇草》《鲜卑女》《蕨蛇》《芥虫》《僧智》《邓珪》《刘早》《田布》等八条皆不是写花卉怪异,如《邓珪》写蒲桃之怪,《刘早》写蓬蔓之怪;只有《崔玄微》(榴花)、《光化寺客》(百合)、《梁生》(梨花)、《苏昌远》(莲花)四篇是花卉志怪,其中《梁生》写梨花冬荣,其后梁生父卒,是从征兆应验来写,不具备小说的叙事、情节等。那么,严格说来,花卉志怪有且仅有三篇,而且《光化寺客》和《苏昌远》在情节上还极为相似,都是书生所赠女子之物现于花房之中;《光化寺客》客赠女子白玉指环在百合花中,《苏昌远》苏生赠女子玉环在莲花中。从小说情节构造来看,除《崔玄微》故事内容充实一些、花仙的人物形象丰满一点,其他都记事简单,交代完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和结果等就结束了。由此可见,由于花卉知识在宋前极少得到整理、辑录和普及,导致小说家们对花卉志怪并不关注。
花卉从草木门中剥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一类是从宋代开始的,并且尤其注重对事类的辑录。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二十二至卷三十九专列“花卉门”,记载了如梅花、琼花、玉蕊、牡丹、芍药、桃花、李花、兰花、萱草花、梨花、杏花诸类,计十八卷共47种花卉。宋祝穆《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二花卉部,计五卷共37种花卉。宋《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七牡丹、芍药、桂、芙蓉等共13种花卉。综上,从数量上看,宋代类书收录花卉数目远远超越前代;从体例上看,这些类书尤其注重花卉事类,如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卷一至卷二十七花部收录花卉102种,从三“祖”来辑录花卉知识,第一是事实祖,内容是有关植物的科学知识、故事、传说等。又如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从格物总论、事类、诗集、乐府四个方面收录花卉知识。其中“事实祖”中的传说故事,《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中的“事类”都被后代类书辑录花卉知识所延续。自宋代后,明清类书对于花卉知识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前代,如明彭大翼辑《山堂肆考》、明郑若庸辑《类隽》、清陈元龙辑《格致镜原》、清华希闵辑《广事类赋》、清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等等,都有专列花卉门类进行知识梳理。这些花卉知识成为明清以来花仙文言小说中情节构造、人物塑造、主题深化的重要来源。
以清代许奉恩的传奇小说《里乘·林妃雪》为例,看历代类书所提供的梅花典故如何成为小说基础。《林妃雪》叙熊生偶然来到众花仙的宴会上,并与梅花仙子林妃雪结为夫妇,最后尸解成仙的故事。小说全篇多处使用梅花典故来构建小说,与历代类书中所载梅花故实叠合颇多。细究来看,在小说情节中,《林妃雪》运用了与梅花相关的典故共15处,这些典故分布在宋代《全芳备祖》《事类备要》《锦绣万花谷》,明代《天中记》《山堂肆考》《类隽》《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格致镜原》《广事类赋》《奁史》《花木鸟兽集类》《渊鉴类函》等类书中。从《林妃雪》所用典故与类书记载的关系来看,唐《龙城录》所记赵师雄于罗浮山中梦遇梅花仙事;北宋诗人林逋隐居西湖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故事;唐代名相宋璟作《梅花赋》,其文“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皮日休《桃花赋序》);宋范成大《范村梅谱》载“绿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绛紫色,惟此纯绿,枝梗亦青,特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绿华。” [8]4《宋书》载宋武帝女寿阳公主卧于含章宫下,落梅花于额间成梅花妆;南朝宋诗人陆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寄友人范晔一枝梅;汉横吹曲《梅花落》本笛中曲,鲍照拟作最佳,此6个为类书中花卉门“梅花”常载之典,属于普及类知识。其中,《尚书·商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诗·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诗·小雅·四月》“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梅妃传》之江妃采蘋,此4典在类书花卉门中所占比例也不小。剩下的羊权、《咏画屏风》、梅柏、边鸾、严陵外姑等5个典故虽然不在花卉门内,但也是与梅有着重要联系,比如庾信《咏画屏风》诗其四“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梅柏姓梅,严陵外姑乃梅福之妻等,皆与梅沾有关系;而羊权事本与梅无关,南朝梁陶弘景《真诰·运象篇》:“萼绿华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许,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晋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是将《真诰》中女仙萼绿华与《范村梅谱》中绿梅比之,两典结合,于是将绿梅与羊权事重新拼凑在一起。可见作者善于将非花卉门类的典故用于梅花仙子写作当中,尤见其知识广博以及运用典故的灵活度。
花谱类书注重事类的体例传统自宋代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代,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像《广群芳谱》这样的大型官修花谱类书,为花仙文言小说的用典打下了知识基础。
三、文本对话与知识对位
文言小说的接受者一般是传统士人,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在阅读文言小说的过程中,由于知识结构的类似,作者可以与读者形成知识层面的对话,了解传奇小说家在构建小说情节中运用的知识,从而破解知识密码,从中产生故事文本以外的阅读乐趣。
对话理论(Dialogism)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苏联著名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M.,M.1895-1975)在文学批评理论和语言学领域提出的。“对话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本中始终存在着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对话才是一切话语与语篇的基本特征,强调将人置于社会群体中加以考察。“‘对话理论还强调了‘不可完成性这一概念,认为对话永远指向‘未来,指向‘他者和‘尚待完成的区域。只要文本作品还存在,还有人阅读,它的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将会永远延续下去,文本意义就具有‘开放性,会无穷延异下去,这就强调了艺术审美活动中的‘动态性。” [9]178
文言小说中的知识因素促使小说不是一个自足的文本,当读者参与进来的时候,读者调动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文学素养,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与其他文学作品的互文功能和对话性质相比,文言小说中的知识因素至少具备两个层面的文学效果:
一是知识因素导致的对话与互文的“靶向性”,也即“定向性”。文言小说尤其是唐宋传奇(明清传奇小说虚构内容增加,表情达意功能明朗,文学创作性质凸显,所以唐宋传奇的记录性的资料性质更为突出),它们作为时代生活文化资料的合集,尤其是历史主题的传奇小说,如《长恨歌传》《周秦行纪》《绿珠传》《杨太真外传》《梅妃传》《赵飞燕别传》《李师师外传》《海山记》等;又如历史真实人物的相关传奇小说,如《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冯燕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王维》《王焕之》《李靖》《虬髯客传》等,读者在阅读这些作为“史馀”的传奇小说,自然要与正史知识联系起来,与正史构成“互文”,其中或有重合叠映,或有离奇出入,都在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生碰撞。同时,这也取决于读者历史知识的丰富与否,拥有不同程度历史知识的读者在阅读同一文本时,其发生的互文又是有所区别的。又如由诗歌内容发挥为传奇故事,如唐代诗人崔护诗“人面桃花相映红”编写成的传奇小说《崔护》,根据唐代刘禹锡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改编的《王榭传》等,读者需要与诗歌知识勾连、想象,看传奇小说文本的故事内容是否与自己阅读诗歌中的联想一致,无论是离是合,都产生一定程度的文学审美效果。清代花仙文言小说同样喜欢用历史知识来填充小说内容,如清王晫《看花述异记》将与花卉相关的历史人物集合起来,敷衍典故,重新组合,与唐宋传奇叙写历史主题的传奇不同,唐宋传奇是叙写当下或发生不久的事件和人物,严格说来还不算真正的历史,但是经过时代的风霜与沉淀后,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在清代传奇中已然成为一种符号、一种知识,存在于作者和读者共有的知识框架之中。清代传奇与唐宋传奇虽然利用了同样的事件与人物,但由于时间的远近,两者书写的性质全然不同:唐宋传奇是记录当下生活的资料,而清代传奇则有运用知识来创作文学的可能,因为这些不是当下发生的事件,不是忠于当下的“记录”,具有炫耀知识和才情的嫌疑。传奇小说中知识因素的靶向性和定向性决定了受众群体的特殊性,为什么文言小说是传统文人的阅读文本,因为需要相似的知识框架来承担起读者与作者的对话,这显然与说唱文学、白话叙事文学乃至戏剧的受众层面不同。白话小说的叙事性、戏剧的表演性、说唱文学的通俗性,普通人也能看懂、听懂这个故事讲了什么,它不需要一个经史子集的传统知识框架,当然缺少这个知识框架,一般人也就体会不到文言小说中破解知识密码的快乐了。传奇小说中知识因素的靶向性要求读者与作者的知识一对一地对接,它较一般的知识介绍功能的阅读文本要求更高。
二是知识因素产生解读的“开放性”与“动态性”。虽说文言小说中的知识因素要求读者与作者的知识对接,但是这只囿于知识存在的客观性(知识存在的这一事实)。如何审视、理解和评判,则见仁见智,这就造成了小说的“开放性”解读。面对同一史实,小说家与接受者与历史学家等不同身份的人物,其认知理解和评价是不尽相同的,多种声音在文本创作中和接受过程中碰撞,传奇小说中的知识因素由此指向了“他文本”“前文本”“他人”“前人”以及“后人”。比如《耳食录》之《长春苑主》中元生将西施、王嫱、卓文君之属定为“狂艳”,相较其他香、艳的定品稍有微词,西施、王嫱由此不满、哭诉的情节,历史上关于西施、王嫱的史料尤多,评论者褒贬不一,有的视其为祸水误国,指摘其负恩忘国、远嫁忘汉;有的反对祸水论,对她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小说借西施、王嫱之口自辩清白,更引用《周秦行纪》中的评价为狂言攀诬,实际上这是与历史评价者的声音构成对话。而接受者在阅读小说文本之际,又结合自身的历史知识和评判标准对此产生或对抗或者融合的声音。在接受者心中,由此又产生众多个新的故事文本,存在于“他者”“前者”与“后者”。知识因素造成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特征在志怪类的文言小说中更为凸显,由于小说文本的故事内容常常颠覆传统认知,所以构成读者与作者对抗性的对话。比如清宣鼎《夜雨秋灯录·九月桃花记》中桃花馆主与天河生就桃花违候九月而开,到底是因为气候原因还是阴阳之说展开议论。按照一般常识,桃花多是春天开放,所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是小说设定为九月,读者的传统认知遭到冲击,会激发阅读的欲望和探索的好奇心理。这种对抗性对话广泛存在于志怪集中,可以说志怪集是小说家与接受者对抗性对话的代表作品类型。而像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这类志怪与释怪结合的志怪小说,则又在对抗性对话的基础上多了一层融合性对话,接受者带着疑惑(对抗性)阅读小说,在小说家阐释怪异现象后,则产生恍然大悟(融合性)的文学效果,这种有层次的文学审美经历和逻辑倒是清代志怪小说的一大特点。
结语
志怪与传奇最初都归属于“史部”,直到宋代才实现从“史部”向“子部”的完全转移,它们的性质介乎于“子”“史”之间。志怪属于笔记小说的一种,笔记小说还包括杂史类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诗话类如《云溪友议》《本事诗》、专题性如《北里志》《教坊记》、考据性如《封氏闻见录》《资暇录》,李剑国指出:“它们的写作——不是创作——主要不是提供寄兴托意供人欣赏的作品,而是提供资料。” [10]3最初的志怪也是属于记录式的写作,而非创作,更不是虚构。传奇的情况要比志怪复杂一些,传奇最初亦是依附于“史部”,指用史家人物传记手法写成的传记小说。尽管历代文人和今天的研究者多从文学角度阐述传奇的特征,但对于最初的传奇来说,其所属“史部”的真实记录性质依然超过其文学性。也就是说志怪和传奇都具有“史部”的资料功能。虽然传奇中虚构等文学因素已经萌芽,但是传奇中具体年代、何人所见、何处所闻等现场感的穿插,终归是意在强调其记录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唐人小说观念里依然秉承“实录”精神,作为审美与娱情的文学创作是被覆盖于实录之下的潜在的层面,并非主体。唐传奇的文学因素自南宋开始,经过元代虞集、明代胡应麟等人的文学性阐释,传奇寓事于情、借事讽喻的功能才被扩大。
在六朝志怪与唐传奇的发轫初期,志怪和传奇都不是文学创作,或者说记录见闻的实录精神要远远压过文学创作的意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言小说本身作用的扩大,它们才承担起寄托和寓情的功能,到了清代,其文学创作才逐渐与实录写作持平。清代文言小说好用典故的特点,恰能说明其创作意图的扩大和知识书写的倾向,是文言小说文类由记录到创作的风向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1][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邓瑞全,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M].合肥:黄山书社,1998.
[3]董乃斌,黄霖.古代小说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4][清]乐钧.耳食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4.
[5][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宋]李昉.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清]许奉恩.里乘[M].济南:齐鲁书社,2004.
[8][宋]范成大.宋元谱录丛编·范村梅谱·外十二种[M].上海:上海书店,2017.
[9]王寅,王天翼.西哲第四转向的后现代思潮:探索世界人文社科之前沿[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19.
[10]李剑国.唐五代文言小说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The Intellectual Writing Tendency of
Fairy Legends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Allusions
Xu Jing
(Chongqing city Management College,Chongqing 400000,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bout fairy tales in the Qing Dynasty often use allusions,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narrative-focused recording methods in the previous dynasties. Through the repeated use,hidden use and reverse use of allusions,the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has been realized,maki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bout fairy tales in the Qing Dynasty have an obvious tendency of knowledge writing. This is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floral dictionari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style of floral dictionaries that focuses on the dictionary. It can be said that floral dictionaries provide necessary knowledge support. Knowledge writing promotes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bout fairy tales to have a unique aesthetic effect,and knowledge counterpoint is the key to decoding the code. Analyzing the citation situ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bout fairy tal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n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that gradually leave the“Ministry of History”and have obvious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 Qing Dynasty;myth;legend;citation;knowledge writing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