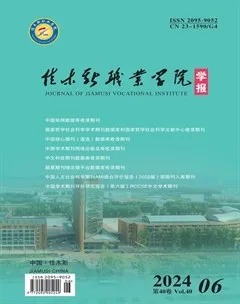《我的父亲》中“父与子”母题的三个维度解析
摘 要: 《我的父亲》(Хороший Сталин)系俄罗斯著名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рофеев)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被誉为“当代《父与子》”的小说反映了当代俄罗斯文学进程中“父与子”母题的别样面貌。儿子对原生家庭的矛盾态度、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思想冲突以及造成上述现象的文化空间贯穿小说始终。借助家庭、思想与文化空间三种维度,《我的父亲》跳出了建构父子冲突情节的范式,摆脱父子母题小说的中心化思考模式,将人格的形成过程同形成人格的文化空间进行整合,并对“父与子”文学母题进行重构,最终得出:“父与子”的文学母题已突破真实与虚构文本之间的界限,在文本之外得以延续。
关键词: 《我的父亲》;“父与子”母题;文化空间;真实与虚构
中图分类号: I207.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5-9052(2024)06-0079-03
引言
俄罗斯作家叶罗菲耶夫所著《我的父亲》通过描写一位外交官以及其子对他的看法,勾勒出一幅别样的“家庭史”。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在这部小说中描写我家庭中很多年一直存在的父与子矛盾,但名称不能叫做《父与子》,因为俄国经典作家屠格涅夫已著有《父与子》”。维克多父子冲突框架的构建撑起了整部小说,然而维克多父子之间的矛盾又不同于屠格涅夫创造的原初模式。首先,作为儿子的维克多既享受着原生家庭带来的种种便利,又对为他带来便利的父母持批判态度。其次,维克多少年时生活在法国,不同的文化空间塑造了其不同于祖国人的特质。而这些影响最终演化成了维克多父子思想上不可调和的冲突。家庭、思想和文化空间是《我的父亲》中的三个重要维度。
一、家庭——“审父叙事”
父辈与子辈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建立的伦理关系,亦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符号,自古以来都是东西方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弗洛伊德将悲剧《俄狄浦斯王》解读为人类基本的戏剧符号,并认为在家庭的框架中父亲作为否定力量的介入(第一阶段为主体和母亲的二元关系),建构了“父亲-母亲-我”的三维结构。吴静在《欲望-生产、配置、反俄狄浦斯:打破装置化的可能性》的一文中指出:“精神分析理论默认了一种预先被构造起来的、连贯的无意识模型,从而完成了对个体的调教和对欲望的压抑。[1]”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的视角下,子辈的能动欲望来源是来自父辈的压抑,是一种“未完成”。显而易见,弗洛伊德的理论总是仰仗着单一的叙事话语,使得分析视角一直禁锢在家庭中。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我的父亲》中塑造了一个家庭空间,包含了父亲、母亲以及我(维克多)。然而,作者借助对父亲和母亲的刻薄分析将这个空间解构了。仔细体察《我的父亲》的情节后,我们不难发现:父亲在维克多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做出任何实质上的压抑行径,甚至维克多在小说中给自己评价是:“娇生惯养”。“审父叙事”就是创作欲望在个人心理层面进行投注的实质。
关于《我的父亲》体裁,评论家们众说纷纭。批评界一说是自传体小说或者是回忆录,也有人称之为自传文学、作者自白或文学随笔。但根据维克多·叶罗菲耶夫本人在《莫斯科新闻》上的说法,可以确认这是一部长篇纪实小说[2],即基于历史和回忆的真实资料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了某些虚构。所以,回忆片段是研究“审父叙事”的重要切入点。第一,回忆片段中透露着主人公家庭与过往。主人公的思想经历,其身上的西方影响连通着他对原生家庭的刻薄评价构成了这部小说“父与子”母题的一副面孔。第二,思考自我存在的“特殊性”体现了法国文化空间和存在主义对作者本人思想上的影响。“回忆录片段”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可以尝试搭建起文本结构与叙事同文学母题之间的联系,用以理解文本与创作思想。小说中维克多进行的最为丰富的心理活动就是对父母近乎刻薄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最原本的样貌是对父亲基本身份的解析:“父亲——外交官”。“我企图在内心自我解释,我不再热爱外交事业,最主要的原因:外交不是别的,而是至今所积累的历史经验把我父亲的行为变成集朴实忠厚行为之大成。[3]”在《我的父亲》中,父亲是一名外交官,为祖国的外交事业鞠躬尽瘁;而维克多是一个受到了法国思想影响的人,自诩“先锋派”,立志于在“停滞”的文艺领域开拓创新[4]。他们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这样就建构了一个别样的冲突框架:“我与父亲都是理想主义者,以相似的方式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这恰恰使我们分道扬镳”。维克多的母亲同父亲一起在高级翻译学校学习,对西方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维克多起初以为母亲同他是战友,然而随着维克多对世界与文化的认识加深,母亲开始有意地管制维克多阅读的书籍,“母子同盟”就这样瓦解,维克多和母亲的文化联盟由于她为父亲的仕途过分担忧而解体。
《我的父亲》的“审父叙事”反映了欲望在个体心理层面上投注的实质,而这种欲望并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受到在家庭中的权威影响而诞生的“被压迫的”欲望,而是一种积极的、生产的欲望,推动维克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德勒兹和迦塔利认为:拉康的结构主义分析导致了“父亲之名”的中心化,让其成为了某种让人信奉之物。从“审父叙事”这一维度来看,对父母进行心理上的分析的实质是打破了父辈与子辈的伦理关系,使得父亲在维克多心目中的形象不再是伟大的、不可撼动的,而是在心理层面同维克多平起平坐[5]。这导致了心理层面上的家庭解体。维克多在心理层面无法同家庭产生共鸣,继而表现出对父母事业的不关心与漠然。值得一提的是,对父母的看法集中于维克多的少年时期,也就是说反叛的种子早已在分析父母的过程中种下。
二、思想冲突与文化空间——新人之困境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重读,将父亲的权威从个体的无意识拓展为语言文化层面的无意识,从而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将能动欲望的生成紧紧限制在了家庭之中。而德勒兹和迦塔利认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理论之局限性就在于它具有结构性和等级制特征。代际冲突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它没有绕过任何一个民族,没有绕过任何一个时代。每次父亲和孩子发生冲突,他们都会找到不尽相同的理由。但这种对抗的本质是什么?在思想观念的斗争中,生活条件的变化意味着思维模式的变化。维克多成长在法国,在法国度过的岁月深深影响着他。而他也显然不具备身边同事对于这片土地的情感,也正是因此维克多认为自己“不珍惜在祖国的生活”,从而导致了悲剧发生。将思想的诞生与更宏大的社会生产活动结合起来,可以探寻思想同另一文化空间碰撞的本质——创造新人。
欲分析新人形成的原因,首先便是分析塑造维克多人格的文化空间[6]。维克多年少跟随父亲驻法国,来自法国和欧洲的影响融入了维克多的成长之中:“实际上我在法国是匆匆过客,我生活在法国的最表层,但是法国却把我整个地、完全地吞没了。”在法国文化环境下成长的维克多人格中逐渐产生了“非祖国性”,文化的“双重国籍属性”成了他身上鲜明的标志。在巴黎的密友甚至调侃他:“你去巴黎比去图拉容易得多” [7]。维克多成长的文化空间造就了他不同于苏联人的特性,而这种特性也会必然影响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
返回苏联参加工作后,维克多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理解同本国现实的冲突日益加剧。在法国生活的岁月造就维克多的志向——在文艺领域开拓创新,于是他打算制造一枚“文学核弹”——文集《大都会》。令人意外的是,这枚炸弹却在不谙文学的父亲手上爆炸了——由于儿子创办刊物未经审查,作为外交官的父亲被停职。在当时,迫使父亲离开外交官的职位就等同于在思想层面上与之了断。李莉在《反俄狄浦斯视域下论郁达夫小说的欲望叙事》一文中指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理论把人的动物性看得太高,反而把人的社会性放低,造就了人对批判外界转向对自我欲望的批判。维克多编撰《大都会》文集是具有法国文化空间印记的“新人”同苏联文化空间碰撞的结果。作者叶罗菲耶夫本人曾在随笔《十年之后》中表示:“《大都会》文集是一次反抗‘停滞的文学创作之尝试”[8]。然而在坚持自己创作理想的过程中,父亲却意外成为了牺牲品。
维克多的行径是在一个文化空间下塑造出的人格与思想与另一个文化空间碰撞出的结果。如果坚持将维克多的行径看做是反抗父亲的话,那么父亲连带受到的压迫便无从解释。思想与文化空间的维度切实反映了“新人”维克多的困境——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他无法平衡法国文化的影响与祖国文化空间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被历史学家称为“停滞”时期,同时在文学上也造就了“停滞”现象。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曾在论文《追悼苏联文学》中严厉地指出:作家们长期以来为了生存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诗学,一石激起千层浪。儿时的维克多同父亲驻派法国,之后回到了那个血统上属于他而文化归属感不强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新人”的维克多的困境与同父亲的思想决裂就是注定的,凸显了“父与子”母题文学悲剧的宿命论感。
三、真实与虚构——再绘“父与子”母题
毋庸置疑,《我的父亲》是一部“父与子”母题小说。它既描写了父亲与儿子之间不可避免的思想冲突,又建构了父亲同儿子的思想决裂。但经过对家庭、思想与文化空间三个维度的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维克多与父亲之间的模式不再是单纯的冲突,而是呈现出了冲突与理解相互并存的样貌。随着来自高层的压力,维克多被开除出苏联作协并面临驱逐出境的威胁,父亲则停职接受审查。在真正的外力面前,维克多才感觉到同父亲是共同体。纵使思想上的冲突多么不可协调,当务之急是将“父子共同体”从来自外部的压力之下解救出来。过去的事实是:父子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某种恒定的品质,而“父与子”母题也相应地保持着恒定的特性。“父”代表权威与秩序,而“子”代表着发展与创新。在这一层面上,维克多同父亲似乎会一直处于对抗模式,永远不可能相互理解和包容。但是把视角放在更宏大的人类社会活动层面上,来自外部的压力会激发父辈与子辈的关系中新元素的诞生,促使父辈与子辈之间形成命运共同体,从而展现出“既相生,又相克”的特点,使得“父辈”与“子辈”既对立,又相互统一。
在“父亲离职”的情节之中,这种“对立与相互统一”展现地更加淋漓尽致。苏联作协要求维克多就《大都会》事件写出书面悔过书。就此,父亲让维克多先反思自己的错误,暂时不要写悔过书。而父亲事实上接受了革职,从而保住了维克多免遭驱逐。甘愿做出牺牲的父亲形象在“父与子”母题的小说中十分少见,同时也颠覆了人们以父亲为权威的看法。而作为儿子,维克多的做法也没有令人失望——或许是出于对父亲的内疚感,他动用了纨绔子弟时期的旧关系,使父亲重返外交比干一份儿闲职,薪水不低。这样的结局可以看做“父子共同体”对抗外部压力的一次胜利,给予了悲剧的故事一点点慰藉。
“父子共同体”是父辈与子辈共同面临外在强力作用下诞生的,而在“父与子”母题之下,父子冲突是必然的。作者叶罗菲耶夫的父亲读过《我的父亲》之后,指责这部小说存在对家庭的不公正描写,要求其作出解释。尽管作者声称《我的父亲》是一部虚构小说,但父子冲突早就超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小说之外延续。“父与子”母题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暗指现实世界中的现象,是虚构文本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点点映射。而在《我的父亲》中维克多与父亲的冲突以“父子共同体”得到了暂时缓解,而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同父亲的冲突还在真实世界中继续,这就搭起了一条连接真实与虚构的线,同时也印证了“父与子”母题的永恒性。在德勒兹的视角下,写作是一个生产的行为,它永远是未完成态的,永远在成形之中,并将超越所有已经存在的质料。“父子共同体”的出现以及父子冲突超越真实与虚构的延续可以看做是一种生成的行为,它超越父子冲突的建构模式并且重构了当代文学中的“父与子”母题。
结语
借助家庭、思想与文化空间三个维度,《我的父亲》中的“父与子”母题不再将分析视角局限于家庭之中,而是通过分析“审父叙事”,探究家庭在心理层面上的解体过程,总结子辈对父辈事业漠然的成因;整合人格形成过程与形成人格的文化空间,发掘同经典文本相同的要素——新人。而20世纪的新人的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可以轻松地跨越不同的文化空间,但无法调和不同文化空间留下的印记,继而同父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三个维度”为“父与子”母题文本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小说拥有别样的建构模式,文学不再看作是“中心化”的慕仿或映射,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作家创作中的“反总体化”与“去中心化”思想。小说虽是虚构文本,但是运用了自传——回忆录性质的语言对父辈进行分析并且探讨了子辈自我认同情结的问题。而“父与子”母题冲突的永恒性又可以反映人类文化进程,是社会文化发展的缩影。在这种意义上,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发展,“父与子”的故事就会继续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 Вик. Ерофеев. Деся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М. Москва: Текст, 1997.
[2]Вик. Ерофеев. Страшный суд: Роман. Рассказы. Маленькие эссе. -М. : Союз фотохудожников России, 1996.
[3]Скоропанова И.С. 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и Наук, 1999.
[4]李莉.反俄狄浦斯视域下论郁达夫小说的欲望叙事[J].宁波开放大学报,2023,21(03):78-82.
[5]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6]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著;陈淑贤译. 我的父亲[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
[7]吴静.欲望-生产、配置、反俄狄浦斯:打破装置化的可能性[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1,(02):216-232.
[8]张建华.家庭、青春、代际鸿沟——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的三个维度[J].中国俄语教学,2019,38(03):37-43.
作者简介:于硕望(2000.05— ),男,汉族,辽宁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2023年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俄罗斯文学中“父与子”母题流变研究——以维克托· 叶罗菲耶夫小说《好的斯大林》为例”(项目编号:SISU2023XK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