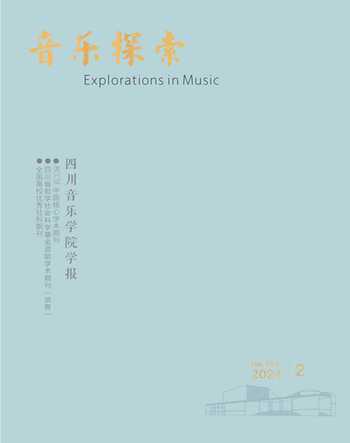历史音乐人类学的基础(上)
乔纳森·麦科勒姆、戴维·G. 赫伯特
摘要:本文为麦科勒姆、赫伯特主编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第一章。在该著中,作者系统地展示了史学新方法的各种方式以及新技术的相关应用,它对于音乐人类学家寻求富有意义且具有代表性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的音乐传统所开展的工作产生了影响。本文以引论性章节开始,直接审核了各项定义、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接下介绍了该著内的各个章节,展示了这些方法和探索在全球范围的音乐传统的创新性历史研究中的应用。这些对于亚美尼亚、伊朗、印度、日本、南部非洲、美国犹太人及美国南部小提琴传统的音乐历史皆具有深入研究,描述了全球音乐史研究的新理论方法和方法论的开端。
关键词:历史音乐人类学;音乐历史学、音乐人类学;麦科勒姆和赫伯特
中图分类号:J60-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2172(2024)02 -0127-06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4.02.011
引 言
有人可能想知道,一本关于历史音乐人类学的书的读者究竟是谁?似乎一本如此主题的,尤其是关注理论和方法的书,只有非常专业的学术领域中的学者才会对此有浓郁兴趣。然而,本书中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对于寻求在一系列音乐专业领域中创造新知识的任何人都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历史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爵士研究、流行音乐研究、早期音乐表演实践和音乐教育史。那么,什么是历史音乐人类学?为什么迫切需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这样一本关于其理论和方法的书?
首先,我们必须简要地思考音乐人类学如何将自己定义为学科,以及是什么使它在音乐学术中与众不同。已经有很多作者对音乐人类学进行了定义,但是从我们务实的观点看来,近年来由音乐人类学协会(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 SEM——译者注)——该领域最大的国际组织——的网站(http://ethnomusicology.org/)中专门提供的题为“什么是音乐人类学?”一文是最有用的定义。根据该文所述,“所有音乐人类学家都在以下的研究方法中分享共同的基础”:
1. 全球性的方法研究音乐的各种事项(无论其原生地、风格或类型);
2. 将音乐理解为社会实践(音乐被视为一种由其文化语境所塑造的人类活动);
3. 从事民族志实地考察(作为表演者或理论家,参与和观察所研究的音乐,并经常在另一种音乐传统中获益)和历史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们上述的解释,第2点表明,音乐被认定为一种“由其文化语境所塑造”的人类活动,但并未提及其历史语境;在第3点中,民族志实地考察有明确的标准,而“历史研究”只是加在最后,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民族志实地考察肯定会出现在音乐人类学协会网站的这里或那里的什么地方,用以强调其假定作为当代音乐实践研究的音乐人类学方法;但是,过去的音乐实践呢?这是否表明历史研究是音乐人类学中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更接近爵士研究、音乐教育史或早期音乐表演实践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样的忧虑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一、具有本质上的非常广泛的历史性
内特尔认为“在我看来,音乐人类学的价值和贡献具有本质上的广泛的历史性”(Nettl 1983, 11)。这句名言此后被一些音乐人类学家引用,诸如斯蒂芬·布鲁姆(Stephen Blum 1993, 20)、邦妮·韦德(Bonnie Wade 1994, 169)等其他学者。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也这样描述,即音乐人类学主要是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如何历史构建、社会维护以及个人创造和体验音乐?”(Rice 1987, 473)我们非常赞赏地注意到,在对音乐人类学领域的描述中,他首次提出了“历史”问题。尽管本学科领域近年来强调对当代音乐实践的民族志研究,以及论证对世界各地音乐传统展开深入的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但是本书的中心目标的确是重申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在音乐人类学领域中应有的地位。在音乐人类学学会(SEM)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特别兴趣小组(SIG[1])担任领导职务时,我们编撰了这本书。SEM的历史音乐人类学SIG是一个为“所有对音乐史研究和历史方法在音乐人类学领域的应用感兴趣的学者”开发的组织(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SIG 2013)。2014年,SEM董事会一致投票通过了SIG为学会的一个正式分支部门。通过深入广泛的研究回顾,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即自1993年以来的20年间,尽管尚未出版过有关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的著作,然而,在此期间,历史研究的实践却跨越了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其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新发展,这对我们的学术领域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历史的忽视与重新发现
上述已经简要地表明了我们的评估,在近来几十年间,音乐人类学越来越强调对当代音乐实践的民族志研究。但是,什么观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又该如何解释以往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忽视呢?民族志无疑很好地作用于音乐人类学领域,民族志方法强调基于实地考察和访谈,在知识和许多深邃思考方面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非常值得庆贺。在过去的20年间,学术期刊和会议议程的许多令人瞩目的内容,以及那些一直得到SEM重要奖项书籍的主题,都清楚地表明当代流行音乐的民族志被广泛认为处于该领域的“前沿”,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音乐人类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重视。然而,本书毫不回避地对民族志方法论提出了警示。因为民族志方法成功而巧妙地削弱了历史研究的意识和价值,从而导致新一代学者追求的兴趣不再关注那些反映过去(近来或相当遥远的)音乐文化中具有许多潜在有价值的研究。显而易见,如果对历史背景不具有丰富认识,就无法完全理解当代的音乐现象,而民族志方法的巨大成功并不能为忽视历史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除此之外,值得我们考虑的是,最近看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学界也对历史进行了“重新发现”,而民族志本身最初就是从文化人类学领域中衍生出来的。近几十年来,所谓“历史转向”的现象已在一系列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讨论,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如何将历史意识更有效地注入那些倾向于强调当代实践考察的领域之中(Abbott 2001;Burke 2005;Calhoun 2003;Hann和Hart 2011)。尽管如此,音乐人类学家露丝·斯通(Ruth Stone 2008)在她的《音乐人类学理论》(Theory for Ethnomusicology)中写道,“从1950到1980年代后期,音乐人类学缺失历史的视角”,并进一步解释说,“音乐人类学对于历史研究的缺失,部分原因是贯穿人类学之中的一种反历史感的影响”,因为人们认为“‘原始人没有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没有书面资料”(Stone 2008, 181)。那么,1980年代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音乐人类学领域的另一些资深学者又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1990 年代初期,丹尼尔·纽曼(Daniel Neuman)确定“音乐人类学视角转向为对于变迁和历史的关注视为自然的和预期的过程,而不是非自然力量作用于毫无异议的非历史社会的异常对话”[Neuman 1993 (1991), 269]。尽管这样的讨论富有洞察力,但在有影响力的学者之间,还是就历史研究在音乐人类学领域的重要作用展开了长期讨论(Bielawsk和Wiewiorkowski 1985;Nettl 1958;Wiora 1965)。
音乐人类学家邦妮·韦德(Bonnie Wade)在她开创性的著作《影像声音:印度莫卧儿音乐、艺术和文化的音乐人类学研究》(Imaging Sound: An Ethnomusicological Study of Music, Art, and Culture in Mughal India)中宣称,“我很高兴地报告历史音乐人类学正在蓬勃发展”(Wade 1998,lvi),并指出“正如我分析的那样,鉴于现有的资料,大多数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著作的探讨必然从现在一直延续到过去,因为学者们通过研究音乐的转变来寻求对于音乐自身发展轨迹的解释”(Wade 1998,lvi)。
尽管在本学科领域的大部分发展历程中,历史研究一直是音乐人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历史研究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似乎都得到了显著认可。同时,该领域显然更加重视当代音乐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内特尔在2005年论述道,“‘历史音乐人类学这个词已经开始出现在会议议程和出版物之中”(Nettl 2005, 274),赖斯在2012年回应了这一观察,他指出“音乐史写作在音乐人类学中越来越被关注”(Ruskin and Rice 2012, 318)。内特尔坚持指出,如果要探讨本领域的更大问题,那么非西方社会音乐史的研究必须纳入音乐人类学。虽然凯·考夫曼·谢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确认,“当今大多数音乐人类学研究在讨论民族志现状时都将历史考虑在内”,她还强调“音乐人类学家对历史理解的贡献比记载所体现的情况要多”(Shelemay 1980, 234)。
三、历史音乐人类学的方法
那么,历史音乐人类学有什么独特之处?其方法如何可以应用于相关领域,诸如爵士研究、音乐教育史和早期音乐表演实践?本书将展示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通过文集中的特约作者们提供的原始数据的具体示例进行说明。书中探讨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在历史音乐人类学中具有核心作用,包括历史学立场和争议、书目研究与策略、历史和传记文献、手稿分析、技术发展和应用(包括声音、图像和视频文件的数字化、存储和分析)以及档案和博物馆藏品的使用(包括录音、图像、音乐手稿、音乐制品等)。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一些中心主题包括口述历史、认知失调和文化记忆、历史写作中的现代主义和叙事模式、重建和重新构想过去的音乐文化、目的论解释的扭曲、音乐学和一般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过去的实践对可能未来的设想。现在,这一介绍性章节将概述历史音乐人类学领域的历史基础。
四、“音乐人类学何去何从”:民族志的首要性
人们普遍认为,对非西方音乐的历史研究预示了现代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如阿米奥(Amiot[2])1979年的《中国音乐回忆录》(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等作品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比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在1950年代的衰落,导致音乐人类学家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音乐,从而将历史研究留给了历史音乐学家;而历史音乐学家直到20世纪末几乎完全专注于西方艺术音乐。世界其他地区的音乐史是怎样的?用什么方法来分析这些“他者”音乐的过去呢?我们认为,音乐人类学家所反映的知识多样性,要求他们包含对于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历史意识及其过程需要有觉醒。因此,本节的目的与其说是追溯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不如说是考察音乐人类学的独特学科条件(相对于音乐学而言)促使民族志方法成为其主要手段。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欧洲和美国发生巨大变化、变革和发明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后半期所创造的条件,为几次大规模前往其他大陆的民族志远征铺平了道路。作为殖民霸权的反映,这些探险活动受益于技术进步,也展示了“异国文化”。音乐人类学思想的德国比较学派(普遍主义)的分支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尽管欧洲将19世纪后期视为政治、文化和科学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但这些进步通常都是损害了世界各地的非欧洲的人民。具体而言,殖民主义对政治、经济和艺术领域造成了极大破坏和转变,几乎影响了世界所有地方,同时也对音乐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样的现代性领域里,全世界的人们开始重新定义与全球力量相关的个人及其文化身份。被殖民的人们在不熟悉的等级结构下被迫适应新的现实,例如法律、财产所有权、欧洲对基督教的解释、教育系统等。在这种情况下,音乐作为一种保存文化知识与历史的方式,其独特的价值得到了强调。
那些研究非欧洲音乐的早期学者们从这种情况中受益。爱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于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使得更详细地研究口述音乐成为可能。低估这一发明和后续发展对于获得世界各地音乐声音的经验和音乐学术技术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已知最早的音乐录音事实上是于1860年在马丁维尔(?douard-Léon Scott de Martinville,1817—1879)发明的留声机(phonautograph[3])上录制的法国民歌《在月光下》(Au Clair de la Lune)的片段,这比爱迪生1888年的蜡筒留声机(phonograph)录音早了28年(Cowen 2009)。
在此之前,只能通过身临其境地近距离接触音乐家才能体验音乐,而且手抄的乐谱是保存音乐以供学术分析的唯一方法。留声机的出现,最终有可能保存大量录音以供分析。根据Nettl所说,在音乐人类学领域,“早期的学术研究始于保存目的,随后迅速成为历史的重建”(Nettl 2010)。
来自不同学科的男男女女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音乐学、民族学、物理学、心理学与声学)中独立地研究非西方音乐。德国普遍主义观点,特别是霍恩博斯特尔(Erich M. von Hornbostel,1877—1935)和斯通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等学者的进化观念,主导了早期思想。他们那种研究“他者”音乐的科学方法被称为“比较音乐学”(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haft),起初被视为音乐学的一个子学科。这些早期的学者收集、分类和储存了一些样本,希望将普遍真理注入于音乐之中。这些学者将音乐的认识概念化限制在他们那个时代共有的假设和期望上;毫不奇怪,由此而证实了欧洲艺术音乐的至高无上。
在北美,乔治·赫尔佐格(George Herzog,1901—1983)追随霍恩博斯特尔的脚步,在哥伦比亚大学为音乐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建立了类似的比较方法。赫尔佐格于1933年与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1886—1979)及其他人一起建立了美国比较音乐学会[4](Frisbie 1991, 250)。语音学家和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埃利斯(Alexander J. Ellis,1814—1890)撰写了开创性成果《现有非和谐音阶的音频观测》[5](Tonometrical Observations on Some Existing Non-harmonic Scales,1884),该研究体现了使用音分系统测量音高来取代试图“以欧洲平均律来表达音程效果”的益处(Ellis 1885, 368)。阿德勒(Guido Alder,1855—1941)于1885年发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Umfang, Methode, und Zeil der Musikwissenschaft)建议音乐学领域无疑与诸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相关(1885;亦见Adler和Mugglestone 1981),而且梅里亚姆(Alan Merriam,1923—1980)指出,“‘比较音乐学本身最早的定义是圭多·阿德勒于1885 年提出的,他强调世界上有各种不同民族的……‘民歌都是出于‘民族志和分类目的。”(引自 Merriam 1977, 191)。西格认为阿德勒首先将“当时新命名的音乐学研究的领域分为两个独立的分支:历史的和体系的”(Seeger 1977, 1)。这一早在1885年所确立的学科划分,对于历史音乐人类学等领域而言,它始终是一个有问题的论题;在理解音乐现象的方法上,其本身既是系统性的,也是历史性的。
阿德勒与其前辈们,例如弗里德里希·克利桑德(Friedrich Chrysander,1826—1901),创办了音乐期刊《音乐学年鉴》(Jahrbücher für musikalische Wissenschaft 1863)和之后的 《音乐学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 1884),它们都强调了阿德勒对于整体音乐学的推动。随着这些音乐期刊的建立,阿德勒和克利桑德为之后成为音乐人类学这样的事物奠定了基础,并阐明了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通过建立音乐学学科,阿德勒与其那时代的其他人一样,试图使音乐研究更加科学,在其案例中,主要是受到恩斯特·哈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的进化生物学的启发。之外,在此期间,许多作曲家从民间音乐中寻找创作灵感,并且收集现场录音的民歌,包括夏普(Cecil Sharp,1859—1924)、瓦尔塔贝德(Komitas Vartabed,1869—1935)、巴托克(Béla Bartók,1881—1945)、柯达伊(Zoltán Kodály,1882—1967)和格雷恩格尔(Percy Grainger,1882—1961);特别是瓦尔塔贝德(参见Poladian 1972)和格雷恩格尔(参见Blacking 1987)二者以对早期音乐人类学理论的贡献而著称。
在北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强调了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在今天,尤其是在北美音乐人类学话语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博厄斯及其学生开创了美洲原住民音乐研究的工作。
本着这种精神,弗朗西丝·丹斯莫尔(Frances Densmore,1867—1957)于1909年发表了《原始音乐中的音阶形成》。文章强调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下观点:“答案必须以原始人的实际演奏为基础,通过对这些与类似问题的回答中,最终可以推断出一些关于音阶逐渐形成的知识”(Densmore 1909, 1)。值得注意的是,丹斯莫尔的主张提出了一种与其前辈不同的方法,例如,艾丽丝·弗莱彻(Alice Fletcher,1834—1923)和约翰·康福特·菲尔莫尔(John Comfort Fillmore,1843—1898)。弗莱彻录制并收集了美洲原住民音乐,而菲尔莫尔(一位音乐教师和教科书作者)则将弗莱彻的录音抄录下来,并在发表的分析中指出,他想象隐藏在音乐中的潜在谐波结构(Fillmore 1899)。
二战后,最初由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提出的文化等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引起了争论,进一步质疑了比较音乐学的科学方法。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可能促进资本主义和竞争环境,但已被用来支持诸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反犹太主义、优生学、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种族和阶级社会歧视等学说。在主要的英美学术期刊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扩大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的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大多数学者都已经“脱离”了运用这一理论概念(Hodgson 2004,447)。随着欧洲从五年的冲突中恢复过来,比较音乐学寻求新的方法,美国学者开始强调人类学的方法论。随着“比较音乐学”及其普遍主义方法的消失,荷兰学者雅普·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创造了一个新术语,“Ethno-musicology”——即后来的“音乐人类学”。正是这种发展,再加上查尔斯·西格等音乐学家的其他影响,音乐人类学由此诞生。
二战之后,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1895—1963)和艾伦·梅里亚姆(Alan Merriam,1923—1980)等学者继承了博厄斯的遗产,特别是在1964年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中,将音乐人类学描述为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之后表述为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梅里亚姆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即“音乐人类学:该领域的讨论和定义”(1960)和“‘比较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定义:在“历史-理论视角”内容中,他讨论了“旧的音乐人类学”(比较音乐学)和“新的音乐人类学”之间的区别,并探讨了超越纯音乐的论题。查尔斯·西格等音乐学家认为,普遍主义观点和文化观点之间的划分过于消极,甚至认为既然所有音乐都在文化之中,那么像“音乐人类学”这样的术语就是多余的。正如威拉德·罗兹(Willard Rhodes,1901—1992)在1956年的《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上所观察到的,“如果要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音乐人类学这个术语,它将包括人类的、不受时间或空间限制的所有音乐”(Rhodes 1956,460)。
威拉德·罗兹是一位早期重要的音乐人类学家。他在1940年就断言美洲原住民音乐“不是死去的、过去的遗物,而是一种重要的、充满活力的力量。”(引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人类学档案,“Rhodes,Willard”)由于他关注的事项是提高对当代美洲原住民文化的认识,罗兹更多地关注生活实践而不是历史研究,但他开创性的声音档案工作对历史音乐人类学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罗兹制作的印第安纳瓦霍族(Navajo)音乐的录音目前正在进入外太空的航海者号宇宙飞船上,希望这些声音最终能被外星的“他者”所欣赏。罗兹最终于196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共创建立了音乐人类学中心。
20世纪中叶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1915—2002)对收集历史音乐唱片的巨大贡献。洛马克斯是一位非常多产、具有高度热情的学者,但他极大规模地研究“歌唱测定体系”(Cantometrics)受到了广泛批评,甚至被描述为他的研究“受阻并具有严重缺陷;因为其未能批判性地挑战机械文化决定论,而且充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人类文化进化论和东方主义思想。”(Averill 2003,24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洛马克斯的一些工作具有明显的理论基础,其深深地致力于“文化公平”的概念;然而,他带有非常激进政治理念的项目,导致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一而再地对此进行调查。洛马克斯令人敬佩地负责在美国建立了许多最重要的录音收集和传播项目,而且像许多早期的音乐人类学家那样,从他非凡成就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Szwed 2010)。
在“音乐人类学何去何从”(1959)小组讨论中,内特尔等学者强调,音乐人类学设定的“文化区域”研究“已证明对人类学是有用的”,而米奇斯瓦夫·科林斯基(Mieczyslaw Kolinski,1901—1981)重申“音乐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心理学、声学和其他学科)”(匿名1959年)。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1918—2005)在其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音乐人类学家》(The Ethnomusicologist,1971)中对比较方法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指出,“在比较对象被理解之前,早期对于比较方法的关注导致了一些富有想象力的理论,但并没有提供多少准确的信息”(Hood 1971, 299)。尽管“比较方法”最终会从音乐人类学中消失,但从全球视角来理解音乐现象仍然是该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
五、缺失的环节:从全球音乐史到历史音乐人类学
通过对民族志首要性的关注,以上部分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进行了传统叙述。然而,关于历史研究作为音乐人类学发展的一种方法的叙述仍然缺乏。长期以来,对音乐实践及其传统的探讨始终包含在对各种文化的一般性历史描述之中。犹如弗兰克·哈里森(Frank Harrison)在其一部重要而不幸并未得到应有的广为人知之作《时间、地点和音乐:民族音乐观察选集(1550年至1800年)》(Time, Place, and Music: An Anthology of Ethnomusicological Observation c. 1550 to c. 1800,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中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在1674年北欧萨米人(Sami)的历史中发现的。具体来说,约翰内斯·谢弗鲁斯(Johannes Schefferus,1674)的《拉普兰历史》(The History of Lapland)中的一则轶事引用了萨满鼓乐的故事:“1671年,拉普兰地区[6]的几位基马(Kiema)居民被逮捕,由于他们所携带的鼓太大了而无法带走,只能在原地被烧毁”(Harrison 1973, 83)。为了最好地说明方法论的重要贡献,本节讨论的是历史音乐人类学中的一些主要数据,它们或早于或避开了上述民族志的趋势。此外,我们还将反思“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的关系,同时讨论这些术语如何人为地划分了音乐“学”(“-ologies”)。
(未完待续)
译者简介:洛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四川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江汉大学特聘教授,浙江音乐学院讲座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1]译者注:原文全称为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Special Interest Group。
[2]译者注:阿米奥(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中国名字为“钱德明”。
[3]译者注:原文为phonautogram,但据查阅似乎应为phonautograph,这是已知最早的录音设备。如文中所述,它由法国人?douard-Léon Scott de Martinville发明,于1857年3月25日获得专利。它将声波转录为在烟熏黑的纸或玻璃上描绘的线条中的起伏或其他偏差,不仅用作声学研究的实验室仪器,还可用于视觉研究和测量语音及其他声音的幅度包络和波形,或通过与同时记录的参考频率比较来确定给定音高的频率。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onautograph,登录时间2022-4-12。
[4]译者注:即American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Musicology。
[5]译者注:此文经修改后重新发表,一年后改名为众人周知的《论诸民族音阶》(On the Musical Scales of Various Nations)。
[6]译者注:拉普兰是芬兰最大和最北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