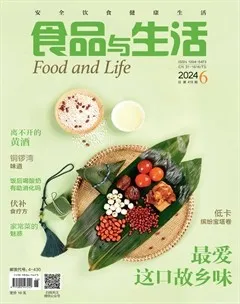离不开的黄酒
乔志远
上海通志馆助理馆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以笔描食,以文述史。
酒是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调剂品,无论是辛辣的白酒、清爽的啤酒、雅柔的葡萄酒,抑或是时下流行的各式果酒,都有着庞大且坚实的拥趸。从古至今,在社会发展、人口迁徙、作物更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地域间也各有其代表性的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的酒文化。如“烧刀子”之于东北,又如“青啤”之于青岛,而与江南地区紧紧捆绑的则非黄酒莫属。
黄酒是我国特有的粮食酒,迄今已有 3 000 余年的历史。江南一带自古便是稻米之乡,每逢丰收时节,酒肆便大量采购稻米、小麦、玉米等做原料,经浸泡、蒸制、冷却等步骤后再与酒曲、酵母混合,并放入缸中静置发酵。待缸中物液分离后,酒匠们便会“开耙”,不断搅拌缸中的醪液,确保上下均可充分发酵。发酵完成后,酒匠们再通过“榨酒”与“煎酒”,将醪液中的酒糟与原浆酒分离开来,原浆酒再经加热、澄清与过滤,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黄酒,其色泽晶莹澄澈,入口甘甜醇厚,香气馥郁芬芳,是舒筋活络、提神解乏的佳品,也是江南人家餐桌上的常客。

上海酿造黄酒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两宋时期,在《宋会要缉稿》一书中,就有关于“上海务”的相关文字记录,而这正是负责酒的酿造、贸易、征税等业务的专职机构 ;此外,南宋名将韩世忠曾在金山一带领兵抗金,其帐下士兵用于饮酒的“韩瓶”也屡有出土,足以反映彼时黄酒在上海一带的风靡程度。
到了元明清时期,黄酒在上海的发展更上一层楼,首屈一指的便是松江。随着华亭府的发展与壮大,松江一带出现了数家远近闻名的酒肆,每年秋收后,酒匠们便选用上好的糯米与泉水酿制黄酒,并根据手法与工艺的不同衍生出迥异的风味,其中雪香酒、刘酒、九峰酒三款较受欢迎,而这三款中又以刘酒为最——相传此酒是泖滨刘氏一族取泖湖水酿制,口味绝佳。清代诗人黄霆在品尝后赞不绝口,在《松江竹枝词》中留下“红市开樽白雪香,沁人心肺带余凉。谁将风味推三白,独让刘郎占醉香”的赞誉之词 ;同为清朝诗人的陈金浩也对其情有独钟,在《松江衢歌》中留下“刘家坊里酒如何,泖水溶溶浚碧波。小醉江乡十月白,茅檐扶出醉人多”的表述,以表达自己对刘酒的推崇与欣赏。
除了松江,金山的白牛镇(现金山枫泾镇)也在这一时期声名鹊起,成为远近闻名的酿酒重镇,其中最知名的便是“三白酒”。相传此酒为当地两家不同风格的酒肆共同酿制的产物,既保留了浙江绍兴黄酒的醇厚风味,也凸显了江苏甜白酒的清冽与甜香,一经推出便成为枫泾人的餐桌至爱。《枫溪竹枝词》中就有“听说新开十月白,打从缸甏让边进”的记载,词中的“十月白”便是指十月份新酿的“三白酒”,口味正佳 ;此外,该书中还有“酿取双燕酒一盏,落花舟清系船宜”的描述,寥寥数字,便将枫泾人饮酒泛舟的惬意情景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酒的流行带动了上海一带酿酒业的大发展,《松江风俗志》中记载,旧时,除了酒肆,许多大户人家也会购置大量粮食在家酿造黄酒,确保全年皆可随意取用。到了冬季,富户们还会雇用专门负责温酒的仆人,在餐前把满壶的黄酒放在热水中温烫。盛极一时的酿酒风潮甚至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康熙年间,康熙帝曾多次传谕,遏止以酿酒之名靡费粮食的恶习,不许黄酒作为商品在市场流通,只允许百姓自酿自用。这条禁酒令贯穿康雍两朝,直到乾隆登基后才有所改变。
随着禁酒令的松动,不少绍兴人把握住商机,他们来到上海开设酒栈,并通过水路将绍兴酒运到上海贩卖。“王恒豫”“王宝和”“王裕和”“永济美”“同宝春”“言茂源”“马上侯”“丰豫泰”“章豫泰”“章东明”“章月明”“全兴康”等诸多酒家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街头扎根,既做堂饮,也做批发,“元红”“加饭”“善酿”“香雪”等各具特色的绍兴酒逐渐打响名号并走进上海寻常百姓家,饮黄酒之风也随之再起。到民国时期,上海市内的黄酒店铺已达数百家,店主们甚至自发组建同业组织,以促进黄酒在上海的良性发展,这股上升的态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阻断。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的爆发虽然对上海黄酒业造成了巨大打击,却也阴差阳错地造就了如今上海黄酒的“金字招牌”。淞沪会战结束后,“萃源”“福记”“康记”三家酒坊为躲避战火侵袭,于 1939 年一同从浦东迁至枫泾。三家酒坊各取自家招牌中的一个字,合并为“萃康福”酒坊对外营业。后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萃康福”屡经改革、重组,最终成为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而其推出的“石库门”系列也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黄酒品牌之一。如此想来,倒也颇有几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感,历史的偶然与巧合,真令人难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