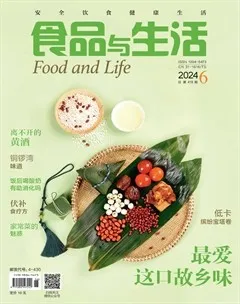食入腹中,化作乡情
郭艳文

北京同事心血来潮,想吃上海菜,在网络上挑了几家饭店,让我推荐哪家的好。我看了,皆是评价极高的餐厅,其中还有上榜“黑珍珠”的。不过说实话,在美国待了四年,来北京也快七年的光景,我还真是一家开在外地的上海菜餐馆都未曾光顾过,给不了她建议,我跟她说 :“若要好吃,这些餐厅应该都不错,但要吃‘上海味道,不如下次来我家,我亲自下厨给你做几道。”
我说的味道自然不是食物本身的口味,而是一座城市反映在菜品上的时间、人情和记忆的积累。所谓一饮一啄,无非是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人在异地漂泊时,对故土食物突如其来的想念总是强烈而坚定的,那一刻,当地再好的家乡风味的餐厅也填补不了内心缺口,唯有自己动手,方能让味蕾和心境获得满足。记得当年刚到美国纽约,有天深夜跟老公回忆起过去校门口卖的糍饭团,第二天我便坐地铁从曼哈顿的中城跑到唐人街的华人超市里买齐所有食材,还拎了一大桶油回来,到家后自习揉面和炸油条,整个过程劳累繁复,但当我俩最终吃上那口记挂已久的味道时,一切努力都变得值得。
某年春节,中学同学陆小姐邀请在纽约的几位上外附中老同学到她家里吃年夜饭,彼时她的父母和外婆正好来美国看望她,那日大家逸兴遄飞,同学们对她外婆做的一锅罗宋汤尤其赞不绝口。纽约飘雪的冬日里,一碗酸甜馥郁的浓汤下肚,那份久违而又遥远的家乡味道瞬间涌上心头。
于我而言,记忆中的上海味道都停留在青春时代以前,深情回顾,皆无过分华美的包装,却处处彰显着亲情的温暖和市井之乐。
儿时我经常陪母亲去南京西路的华安做头发和美容,为了奖励我那漫长的陪伴和等待,结束后她会带我去云南路的“鲜得来”吃一份排骨年糕。
念小学时,我家住在普陀区的石泉路上,马路对面就是“四如春食府”,每到盛夏暑月,胃口不佳,父亲就从那里打包带回些冷面。后来读了《繁花》,发现阿宝心中封神的冷面馆也是这家。

到了寒风凛冽的冬日,父亲则会带我们辗转到真如古镇上的羊肉馆里,给每人点上一碗汤清面滑的阳春面和一客红烧羊腿肉。印象中的羊腿肉带油带皮,按大块红烧肉的方法用细绳四面捆扎住,肉香四溢,上头还包裹着浓郁醇厚的酱汁,丢入碗中,便与汤面浑然天成。
过去我还十分迷恋“光明邨”的葱烤鲫鱼和八宝辣酱,这些年回上海短暂逗留期间,为了满足这难以熄灭的口腹之欲,我依然会排入淮海中路上“光明邨”熟食店门口那条看不到头的长队中。
记 忆 里,“ 杏 花 楼 ”通往二楼的楼梯陡峭逼仄,嘈杂的大厅里充斥着浓油赤酱的菜香和轻盈细腻的沪语;“小杨生煎”铺里的座位总是供不应求,好不容易坐下,却要被迫和陌生人挤在一张桌子前“享用”焦香的生煎包和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粉丝汤,同时不仅要忍受油腻不堪的桌面、邻座奋力擤鼻涕的声音,还有一群站在你旁边、虎视眈眈地用眼神催促你快速吃完让位的人。
过去奶奶家门口卖五香茶叶蛋的年迈阿婆弓着腰,穿着褴褛的布衣和布鞋,每次经过时,都会被那口飘着五香味的锅子吸引过去。很多年后再从那里经过,这个推车卖茶叶蛋的身影却已不在……

读大学那会儿,父亲经常把我从校园里接出来,驱车带我去“德兴馆”,给我点上一碗鳝丝和油焖笋浇头的汤面,他自己则是叫上一份焖肉面外加一块素鸡。也会点那里的糟钵头,清爽不腻,香气醉人,滋味不凡。
还有过去我舅舅做的糖醋小排,在我心中一骑绝尘,他喜欢把汤汁收得很干,如此,小排色泽油亮,入口味更浓郁,肉质也有嚼劲。现在我做糖醋小排也延续着印象里他的做法……
去年整个夏天我都在贵州的贵阳避暑,中秋前夕,一位北京友人去上海出差,特意到“光明邨”排队买了两盒鲜肉月饼给我寄来贵阳,说是解我乡愁。其实朋友的馈赠何止于此?更是中国社会的人情物态,而这也正是美食里最感动人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