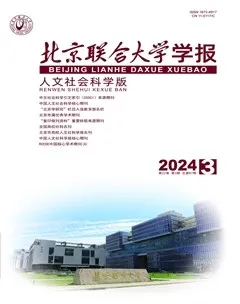《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
[摘 要] 数字时代带来了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从而给刑事诉讼提出了应对这些变化的新需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应当在遵循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需求作出回应。在制度层面上,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实现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修改;数字时代;新兴技术;新兴权利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D925.2;D915.3[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2-4917(2024)03-0049-08
根据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本届人大立法规划,《刑事诉讼法》作为“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即将迎来其第四次修改[1]。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采取开放方式向各界征求意见,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①,其中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即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如何回应数字时代的新需求。
随着人类从工业社会跨向数字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纠纷和争端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相应地,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也需要作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革,刑事诉讼亦不例外。在司法实践中,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各种新兴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刑事诉讼领域,重塑着刑事诉讼的样态,既带来了发现真实、提升效率等方面的裨益,也引发了与传统诉讼原理不适配、导致权利保障难度增加等方面的忧虑。在此种现实下,借由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新需求作出回应,对新兴技术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应用予以必要的肯认和适当的规制,已迫在眉睫。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分析数字时代究竟对刑事诉讼提出何种新需求、应秉持何种回应此种新需求的基本立场与思路、以及如何在制度和规范层面展开对此种新需求的回应这三个问题着手,探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数字时代变革在法治框架内的互动关系。
一、数字时代对刑事诉讼的新需求
数字时代对刑事诉讼提出的新需求,主要体现在要求刑事诉讼应对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三个方面。
(一)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
随着各种新兴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普及,犯罪也不断依托技术进步而进行着迭代更新,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犯罪例如严重暴力犯罪的数量持续下降,而依托网络实施的犯罪数量不断增加。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公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1999年至2023年,我国检察机关起诉的严重暴力犯罪被告人数量从16.2万人下降至6.1万人,案件占比由25.1%下降至3.6%,而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代表的涉网犯罪无论从数量还是占比上都持续走高。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告人51 351人,同比增长66.9%,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等关联犯罪的数量也呈上升态势[2]。
依托网络等新兴技术实施的犯罪,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犯罪的特征。一是逐利性。数字时代下,绝大多数依托网络等新兴技术而实施的犯罪的目的往往十分“单纯”,即在于追求非法的经济利益,无论是网络诈骗、网络勒索、网络洗钱,还是网络非法交易、色情服务等,皆是如此当然,也有部分涉网犯罪是基于其他目的的,例如网络侮辱、诽谤、性侵等犯罪。。这就与传统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的犯罪目的多样性存在明显区别。二是技术“创新”性。基于逐利目的的强烈刺激,犯罪分子不惜“冒绞首的危险”[3],在新兴技术的应用方面自然也是毫无顾忌。从早期简单的钓鱼网站到如今复杂的网络攻击,从区块链、数字货币、元宇宙到人工智能技术,只要有利于他们牟取非法利益,就被他们以“拿来主义”的方式使用。三是跨境性。由于网络世界没有物理世界的国界边境,犯罪分子可以超越国境的限制实施犯罪。例如,针对我国境内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的服务器常架设在东南亚国家,其目的就在于试图利用国际刑事司法协作的不便逃避刑事追诉和惩罚。四是匿名性。犯罪分子往往在网络上以虚拟的身份实施犯罪活动,其真实身份常难以追查。如此一来,一方面使得被害人更容易对其产生信任感,另一方面也给公安司法机关的追踪和打击增加了难度。
第22卷第3期郑 曦:《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5月
数字时代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给以预防和打击犯罪为基本目标的刑事诉讼提出了难题。首先,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技术门槛。犯罪分子运用先进技术实施犯罪,例如使用加密技术隐藏通讯内容、利用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进行诈骗等[4]。这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相应的技术更新,以便有效应对犯罪技术的发展。其次,增加了侦查取证的难度。数字时代的犯罪往往不留下物理痕迹,传统的实物证据收集手段在网络世界中难以应用,使得侦查取证的难度增加。再次,提升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需求。由于数字时代下涉网犯罪具有上文所述的跨境性,犯罪分子以互联网为媒介实施远程犯罪,涉及管辖权、跨境取证等诸多问题,需要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方式予以解决。最后,需考虑打击犯罪与保护隐私的关系。数字时代下,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可能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包括个人隐私数据。于是如何在确保公民隐私权不受非法侵犯的前提下,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刑事诉讼,是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二)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
由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觉醒,可能导致社会关系中“物”的主体性不断被强化[5],因而在刑法学界,关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工具是否能够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开展得如火如荼。持肯定说者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成为犯罪主体以及刑事责任主体的可能。例如,刘宪权教授认为强智能机器人与其他刑事责任主体没有本质差异[6];彭文华教授认为智能代理是人工智能获得犯罪主体资格的条件[7];江溯教授认为现代罪责理论由于逐渐开始排斥“自由意志”这样形而上学的概念,因而完全可以容纳人工智能的罪责[8]。持否定说者则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不过是辅助工具而已,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也无法承担刑事责任。例如,王钢教授认为,唯有能够理解概念和语义、能够领会刑法规范的内容和要求的主体才可能作为适格的规范接受者并被视为刑事责任主体,而人工智能不具有语言使用者的规范主体身份,故而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主体[9];时方博士则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属性,也不具有刑法上的可归责性,因而无法具有刑事主体地位[10]。尽管争论纷纷,但倘若有一日人工智能当真成了刑事犯罪的主体,自然也就将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诉讼主体的地位。
尽管在当前“弱人工智能”的时代,人工智能成为犯罪主体、以至成为刑事诉讼的主体仍然只是一种期待甚至想象,但其以实质上的办案主体身份出现于刑事诉讼实践中,却已然成为现实。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刑事诉讼的程序进展。无论欧洲国家法院使用的案件管理工具如ERP案件管理系统、职位分配和管理系统(OUTILGREF)等[11],还是我国上海法院的“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北京法院的“睿法官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等,都包含案件分配、繁简分流、程序管理、超期警报等功能,使得人工智能对刑事诉讼程序形成一定程度的控制甚至主导。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案件的实际办理者。早在2016年的卢米斯案中,法院使用COMPAS智能量刑辅助系统给被告人定罪,就引发了机器代替人类办理刑事案件的争议[12],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愈发成熟的当下,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办案的实践更具可能性[13]。在人工智能成为刑事案件办案主体的现实可能下,人们不得不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工智能作为办案主体是否对刑事诉讼中人的主体性地位造成冲击?二是人工智能作为办案主体是否有利于实现刑事案件办理的公正,以及社会大众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接受借由人工智能运行而实现的机械、冰冷、去价值判断的公正?
(三)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
我们正处在一个权利得以张扬的时代,而数字时代与权利时代的碰撞交融,使得新兴的数字权利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在法学领域构建起新兴权利的基本理论和规范[14]。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规定,数据主体享有数据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被遗忘权)、限制处理权、可携带权、反对权等权利。我国《民法典》也规定了隐私权、查阅复制权、异议更正权、删除权等权利,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则更为细致地规定了信息主体享有的知情决定权、查阅复制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解释说明权等权利。尽管对这些权利的属性、内涵、外延等还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些新兴权利已经现实地影响了数字时代的人类行为方式,并进一步对刑事诉讼产生辐射影响。新兴权利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隐私保护的思路向数字权利保护的思路拓展。自美国卡兹案[15]以来,隐私保护受到重视。但隐私保护以事后审查和救济为思路,其被动性的特征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在此情形下,新兴权利的兴起为刑事诉讼中的法益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数字权利行使的前置性、主动性、积极进取性,使得主体对于其个人信息和数据的控制得到尊重,对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的制约力度也进一步增强。于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一元化的隐私保护思路逐渐向隐私保护与数字权利保护并行的二元保护思路拓展,给刑事诉讼规则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权利保护的利益向刑事诉讼之外扩张。传统刑事诉讼权利所指向的利益主要聚焦于刑事诉讼本身,例如辩护权、阅卷权、律师取证权等。其目标无非在于获得推动诉讼向有利于本方方向发展的程序利益,以及最终获得定罪量刑等方面的实体利益。但新兴权利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则将保护之利益向刑事诉讼之外延伸,例如知情同意权可能涉及被追诉人、公安机关、数据处理第三方等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删除权(被遗忘权)则可能关系到诉讼参与人在刑事案件办理完成之后的免受参与刑事诉讼影响的生活安宁之利益。
第三,刑事诉讼权利体系受到冲击。新兴权利除了辐射影响刑事诉讼之外,还向刑事诉讼“叩门”。随着刑事诉讼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要求在刑事诉讼领域吸纳部分新兴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学者认为按照“统一纳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思路,《个人信息保护法》创设的一系列全新的权利种类也对执法、司法机关保护个人信息规定了全新的法定义务,进而适用于刑事诉讼[16]。新兴权利的引入,必然使得刑事诉讼既有的权利体系受到冲击,如何合理安排引入的新兴权利与原有诉讼权利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回应新需求的基本立场与思路
对于数字时代对刑事诉讼提出的上述新需求,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有必要予以回应,但此种回应应当遵循以下基本立场与思路。
(一)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
如前所述,数字时代下犯罪分子对新兴技术的运用增加了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难度,面对此种情形,《刑事诉讼法》在公安司法机关应用新兴技术的问题上,应当秉持开放的基本立场,以应对数字时代犯罪形态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应用可能使得公权力得以扩张,给公民权利的保护带来一定的威胁。因此,也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权力的运行与权利的保障作出适当的平衡。
坚持开放的基本立场,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对新兴技术应有包容的态度。新兴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是数字时代新兴技术社会应用的必然,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资源分配方式向着去中心化、扁平化方向发展,重塑了国家权力结构,也使得刑事诉讼必然发生结构性变化,《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对这种变化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宽容态度。此外,新兴技术的应用需要经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除非对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有重大的负面影响,否则《刑事诉讼法》不应对某种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予以直接否定,而是应以包容的态度留待实践取舍。二是在条文表述上应当留有余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立法不可能根据技术的发展进行实时的调整,否则将可能出现“一事一立法”的困境,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为避免此种窘境,《刑事诉讼法》的此次修改在条文表述上应当保留一定的开放空间,以相对概括、留有余地的方式对新兴技术的应用问题作出规定,从而使得《刑事诉讼法》文本有适应技术发展的调适空间。
坚持审慎的基本立场,对《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新兴技术应用应当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目的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则刑事诉讼中新兴技术的应用也应当与上述目的具有同向性。其中尤其应当关注保护人民和保障安全这两项目的,即需要重视新兴技术对人权保障以及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对于不符合此种要求的新兴技术则不应许可其在刑事诉讼中应用。二是应当加强对新兴技术应用的程序规制。即便新兴技术本身具有上文所述的与刑事诉讼基本目的的相适性,也需要防范实践中由于办案人员素质、利益等原因导致偏离的情形。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以程序规制的方式避免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新兴技术,导致对刑事诉讼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带来侵害。针对这一问题,下文将展开详述。
(二)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法治领域的重要法律,对数据安全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问题有较为细致的规定,而数字时代下刑事司法领域也存在数据安全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为实现法律规定的统一协调,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注意与《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衔接。
一方面,《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国家机关处理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规定大体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有专门的第三节“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定”,《数据安全法》第一章第6条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承担数据安全监管职责的规定,第四章第36条有刑事侦查中调取数据的规定,第五章则对国家机关“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做了专门规定。公检法机关属于《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所称之作为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国家机关”,故其在刑事诉讼中处理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行为应当遵守这两部法律的相关规定,尤其应遵守其在处理数据和个人信息时的义务规定。例如,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境内存储、出境需进行安全评估,依法保密或公开等。因此,除非法律有明确的特殊规定,刑事诉讼领域公权力机关处理数据和个人信息时需符合《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对于这一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予以明确。
但是另一方面,刑事诉讼中的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又有一些特殊之处,应当对其有充分认识。首先,刑事诉讼中的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是在处理者与数据或信息主体之间极端的“持续不平等”[17]状态下进行的。公检法机关较之公民个人特别是被追诉人,具有力量上的显著优势,而这种优势可能因为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而进一步拉大。其次,刑事诉讼中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的强制性远远超过合意性。公检法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的包括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在内的诉讼行为,通常无需取得公民的同意,甚至在其反对的情形下亦可强制实施。如此一来,作为数据或个人信息主体的公民的同意权、反对权等,在刑事诉讼场域下的适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几乎没有行使的空间。再次,刑事诉讼中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常是在封闭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刑事诉讼特别是刑事侦查,具有天然的封闭秘密特征,基于诉讼的目的,公检法机关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可以不将数据或个人信息处理的情况告知公民个人,以防止出现阻碍诉讼进行、破坏证据等方面的风险。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公民个人的知情权亦受到较大限制。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在衔接《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问题上,既要关注对这两部法律规定的吸收,也要重视刑事诉讼领域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的特殊性,作出相应的调整规定。
(三)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规定
近年来,针对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的涉及数字时代新兴技术应用、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公检法机关先后出台了各类规范性文件,试图对相关问题予以确认或规制。这些规范性文件,除了最高法“刑诉法解释”、最高检“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类整体性的文件中关于数字时代刑事案件办理的相关内容外,尚有专门性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关于数据处理的。例如2016年“两院一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19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二类是关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的。例如2022年最高法《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第三类是关于数字时代刑事诉讼办案程序创新性规定的。例如2021年最高法《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和2022年“两院两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这些规范性文件就数字时代对刑事诉讼提出的新需求做了积极回应,相关内容可以为《刑事诉讼法》修改所吸收。
将刑事司法领域的规范性文件中的合理规定吸收进《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常见方式。典型的例证就是,2010年“两院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被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所完善吸收。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依然运用此种吸收规范性文件内容、以回应数字时代刑事诉讼新需求的修法方式,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有利于实现法律修改的科学性与高效性。这些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已经历过理论的讨论和实践的检视,将这些内容吸收进《刑事诉讼法》,使得制度和规范的设计具有实践的基础,修法效率也因无需另起炉灶而得以提升。第二,有利于解决不同规范性文件规定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上述规范性文件是由不同主体制定的,难免有难以衔接甚至存在矛盾的问题,而由《刑事诉讼法》予以修订吸收,恰能解决这些规定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规定和适用的统一。第三,有利于消除部门自行立法、自我授权的弊端。各个部门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常常自我授权、自我扩权。例如,公安机关对技术侦查适用案件类型的规定就超出了《刑事诉讼法》许可的范围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为避免此种自我授权的弊端,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就相关问题作出权威的规定,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回应新需求的制度展开
基于以上的基本立场与思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制度规则的修订与完善。
(一)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
如上文所述,数字时代下新兴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是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中应当兼有开放和审慎的态度,既对其应用予以肯认,又需重视对其的规制,以防止技术的滥用。
第一,应当对技术应用的办案场景予以明确。若新兴技术作为取证手段运用于侦查阶段,则其本质上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自然应当遵循技术侦查案件适用类型的规定,即仅应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少数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中使用。若新兴技术作为办案辅助工具用于起诉、审判时,在常规的流程性工作中应许可新兴技术有较大应用空间。但对于涉及被追诉人核心利益的事项,例如提供量刑意见,在应用新兴技术时应有更为严格的限制,例如需规定相关的必要性条件等。
第二,应当对技术应用的程序规则予以规定。对于新兴技术的应用,对其设置细致的程序规则是最有效的规制方式。具体而言,应当对技术应用的批准主体、审批流程、使用期限等予以规定。属于技术侦查手段的,可以直接适用技术侦查的程序规则;其他类型的则应按照正当、必要的原则设计相应的程序规则。
第三,应当对技术应用的救济方式予以确认。技术的应用可能引发争议,例如,审判阶段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裁判即可能引发侵害质证权的疑虑[18]。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就此提供救济途径。例如,设置许可当事人针对技术应用提出疑问、申请技术路径或算法公开、对违法使用技术进行申诉控告的相关制度,防止技术应用恣意损害案件的公正办理。
此外,由于技术的应用如上文所言,将使得工具成为实质上的办案主体,导致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冲击。在此种情况下,《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重视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一方面,应当明确技术工具与办案人员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可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应当仍是刑事案件办理的主体,而技术在此间主要发挥辅助作用。对此我国司法机关已有认识,最高法《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就曾提出人工智能的“辅助审判原则”,要求“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可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对于此项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予以吸收,明确规定“技术作为刑事诉讼的辅助性手段”,进而强化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应当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予以明确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19],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20],进而推进了我国的司法责任制改革。根据司法责任制的要求,既要保证案件办理的最终决定权由办案人员掌握,避免技术工具对案件办理权力的侵蚀,也要确保刑事案件的错案责任由办案人员承担,防止其向技术工具推卸责任。对于这两点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予以明确。
(二)辩方力量的补强
数字时代下刑事诉讼出现结构性变革,无论是新兴技术的应用还是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处理,都显著增强了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办案能力,进而使得本就不对等的控辩力量对比进一步拉大。如此一来,刑事诉讼平等对抗的原则即受减损,程序公正甚至实体公正的价值追求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有鉴于此,《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基于数字时代下刑事诉讼的新需求,有针对性地就控辩力量平衡问题作出调整。除了上文所言以程序性规则等限制控方权力之外,还需对辩方能力予以补强。
首先,应加强对辩方质证权的保障。辩方通过行使质证权,得以针对控方证据进行质疑、辩解和反驳。在我国,质证权的对象既包括言词证据,也包括“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1、120条。,因而以数据形式呈现的证据亦是质证权的对象。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尽管数据化的证据应当作为质证的对象,但辩方却难以有效地对其展开质证。一方面的原因是对数据的质证存在技术门槛,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实际起到追诉作用的数据未必进入“案卷材料”中。针对第一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算法公开和扩大专家辅助人参与范围的方式予以缓解,而针对第二方面的问题,则需要强调数据作为定案依据需以经历质证为前提。例如,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规定“运用新技术收集的数据,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其次,应对算法做有限制的公开。在公权力机关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的场景下,算法的封闭秘密性阻碍了上文所述的质证权的行使,也使得辩方的整体辩护效果大打折扣。因而有学者指出在刑事司法领域,基于公开、开示的要求,有必要促进算法可解释技术的发展、增加算法披露的环节[21],以保障辩方权利。但基于平衡科技企业商业利益与刑事诉讼中辩护利益的关系之考虑,算法公开应有所限制。例如,算法公开应限于对其核心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部分,应通过算法解释寻求特定算法决策结果的原因和理由[22]而实现对被告人的算法公开,可以通过各方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限制公开的范围等。对算法做此种有限制的公开,方不至于对科技企业的研发热情造成过度打击,从而保证经由算法公开的辩方力量补强得以行稳致远。
再次,应扩大专家辅助人的参与范围。如上文所言,数字时代下控辩力量差距进一步被拉大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辩方遭遇技术门槛的阻碍,为此需要加强对辩方在技术方面的外部智力支持,其中较为可行的途径即为扩大专家辅助人的参与范围。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197条已有“有专门知识的人”即专家辅助人参与勘验检查、出庭提供意见的规定。2016年,“两院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亦有专家辅助人操作电子数据展示并作出说明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刑事诉讼法》修改可以拓展专家辅助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运用新技术收集的数据和信息提出意见”,以全面提升辩方应对数字技术门槛的能力,实现有效辩护。
(三)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
如上所述,新兴的数字权利不但在理论和规范的层面得到肯认,亦在向刑事诉讼施加影响。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此不能无动于衷。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所确认的成熟、成型的各项数字权利中,与刑事诉讼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知情权、查阅复制权和删除权。
首先,知情权是前提性权利。数字时代下,新兴技术的运用成为刑事案件办理的重要方式,于是知情权构成了当事人应对新兴技术运用、有效参与刑事诉讼的前提,因而,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可以考虑肯认当事人的知情权。在刑事诉讼中,知情权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当事人有权知悉公权力机关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事实;二是对运用新兴技术处理的事项知情;三是对新兴技术应用的后果,即对其权利义务的影响知情。然而在刑事诉讼的场域下,基于公共职能的行使需要,知情权需有一些限制。例如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5条的规定,在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情形的,或者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即构成知情权之例外。此外,知情权的行使还可能受到案件类型、办案阶段等的影响,使得知情的内容、时间等受到限制。
其次,查阅复制权是保障性权利。为保障辩方充分准备辩护,需令其有权获取控方证据。故我国以阅卷权为途径进行单向的证据开示,然而阅卷权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行使方式受限[23],故需以许可作为数据或信息主体的当事人查阅复制数据或个人信息为内容的查阅复制权作为补充。此项权利在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已有规范基础,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定的数据访问权即包含访问个人数据及获得相关信息的内容[24]。而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已规定查阅复制权,要求在个人请求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提供。在此种情况下,《刑事诉讼法》修改可以在对此项权利设置时间方面的限制、特殊情形下的适用例外的基础上,肯认此种查阅复制权。
再次,删除权是与刑事诉讼脱钩的权利。当事人尤其是被追诉人,一旦与刑事诉讼发生关系,即难以摆脱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被定罪的罪犯,再想回归正常平静的生活十分困难。为实现刑事诉讼的矫正功能,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我国已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等封存犯罪记录的规定。但为进一步实现当事人与刑事诉讼脱钩、彻底摆脱其负面影响的目标,可以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引入删除权制度,实现彻底的“遗忘”。当然删除权的引入可能与公共安全、公众知情等利益产生冲突,因此,应当区分不同类型主体的身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被申请删除数据的性质和内容,并审查该数据被处理后经历的时长,设计出能够协调不同利益、价值的删除权制度,缓解此项权利与刑事诉讼中其他权利和利益的冲突。
结语
数字时代的新需求给刑事诉讼带来了挑战,面对这些新需求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25],《刑事诉讼法》不应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地做“孱头”[26],而应在此次修改中积极回应这些新需求、直面此种新挑战,回答“针对技术和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背景变换(这与确认事实的陈旧方法有冲突),如何在具体案件中明智适用教义”[27]这一问题。如此,刑事诉讼方能在数字时代下依然坚守其捍卫正当程序、保障公民权利的核心价值取向,进而继续有效发挥其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28]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国人大网2023年9月8日,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309/t20230908_431613.html。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2024年3月9日,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2403/t20240309_648173.shtml。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4] 李怀胜:《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事制裁思路——以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为例》,《政法论坛》2020年第4期,第144—154页。
[5] 骆正林:《数字空间、人工智能与社会世界的秩序演化》,《阅江学刊》2023年第6期,第87—95页。
[6] 刘宪权:《对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否定说的回应》,《法学评论》2019年第5期,第113—121页。
[7] 彭文华:《自由意志、道德代理与智能代理——兼论人工智能犯罪主体资格之生成》,《法学》2019年第10期,第18—33页。
[8] 江溯:《人工智能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基于刑法哲学的证立》,《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3期,第111—127页。
[9] 王钢:《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否定论——基于规范与语义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63—79页。
[10] 时方:《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之否定》,《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67—75页。
[11] European Judicial Systems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Justice (CEPEJ STUDIES No.24), Council of Europe, https://rm.coe.int/european-judicial-systems-efficiency-and-quality-of-justice-cepej-stud/1680788229 (last visited on January 31, 2024).
[12] Loomis v. Wisconsin, 881 N.W.2d 749 (2016).
[13] Purvish M. Parikh, Dinesh M. Shah, Kairav P. Parikh: “Judge Juan Manuel Padilla Garcia, ChatGPT, and a Controversial Medicolegal Milestone”,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Vol.75, No.1, 2023,pp.3-8.
[14] 王方玉:《自然、法律与社会:新兴权利证成的三种法哲学路径——兼驳新兴权利否定论》,《求是学刊》2022年第3期,第114—126页。
[15] 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 (1967).
[16] 程雷:《刑事诉讼中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23年第1期,第90—102页。
[17] 丁晓东:《个人信息保护原理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
[18] People v. Belle, 47 Misc. 3d 1218(A), 16 N.Y. S3d 793(N.Y. Sup. Ct. 2015).
[1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2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21] 张凌寒:《权力之治: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规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5页。
[22] 辛巧巧:《算法解释权质疑》,《求是学刊》2021年第3期,第100—109页。
[23] 郑曦:《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重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38—48页。
[24] 京东法律研究院:《欧盟数据宪章:〈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评述及实务指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38—239页。
[25] Niklas Luhmann, Legal Argumentation: An Analysis of its Form, 58 Modern Law Review 285 (1995).
[26] 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27] [美]理查德·波斯纳:《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苏力、邱遥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28]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2版。
Response to New Demands of the Digital Age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has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crime, the potential renewal of litigation subjects, and the realistic impact of emerging rights, thus posing new demands for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address these changes.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esponses to these new demands should be based on a basic stance that emphasizes both openness and caution, to integrate the Data Security Law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nd to absorb provisions from other normative documents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modifications and improvements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hould be made by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the regulation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human subjective status,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defenses strength, and the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digital rights.
Key words: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digital age; new technologies; emerging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