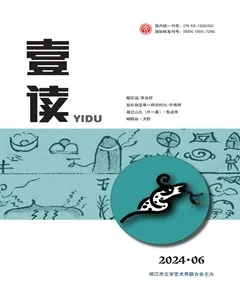鸟的审美
麻雀
极致人性之鸟,我授予麻雀。
有野生的麻雀,但我视野里的麻雀,与乡野的屋宅不离不弃,故此它有了一个别名:瓦雀。高处不胜寒,把飞翔的姿态降至最低,才是安全,也才能讨人疼爱,这浅显的道理,麻雀比任何鸟儿都体悟得深刻,所以,它抛弃了高飞的欲望。在鸟类中,它是最贴近人类情感的,对此,《说文》有释义:“雀,依人小鸟也。”
麻雀相貌平淡,以为难入画家之眼,看见宋人的《竹雀图》《寒雀图》,才傻眼惭愧。前者画者为吴炳中,麻雀侧身,全无遮挡,处在画面的黄金分割处,搔头的瞬间,眼睛半睁,很是舒服的表情。后者为崔白所画,九只姿态神情不同的麻雀,自右至左依次展翅倒挂枝头,倾身欲飞,情态各异,或昂首,或瞰视,或抓痒。
麻雀的心,永远不会惦念遥远的地平线,它寄人篱下却不乏气节,小时曾捉只麻雀关进笼子,不到一天它就在笼里撞死。中国花鸟画,麻雀并不缺席,清人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中说:“麻雀颔嘴皆黑,毛裼有斑,耳有白圈黑印,全身写法俱宜赭入墨,故写麻雀法必先用墨笔写成,斑点浓淡自然,俟墨干然后加赭墨染之,趁湿复加墨点斑纹写是。”宋代有幅《驯禽俯啄图》,一只被人饲养的麻雀,身系红绳,绳端拴圆环,立于浅蓝敞口瓷罐上,罐内有米,麻雀低头欲啄。我注意到,画面中的麻雀神情并不愉快,虽未笼囚,但身上的绳子桎梏了它的天性。明画家边景昭的《三友百禽图》画鸟九十七只,其中二十八只麻雀在画幅下边的缓坡上,悠闲地晒着太阳,叽叽喳喳一片欢闹,传达出欢乐祥和。
阅一幅宋人《斗雀图》,两只麻雀在地上嬉戏争斗,滚作一团。那只占上风的麻雀左爪抓住对方的喙,右爪紧握对方的爪,它的喙却也被对方牢牢地抓住,形成谁也啄不到对方的僵持局面。两雀羽翼大张,动感力度淋漓尽致,仿佛孩童的嬉闹。
西方文人笔下,麻雀并不可爱。格雷《鸟的魅力》第十章写麻雀,“那令人生厌的吱吱喳喳的叫声”,“在众多的嘈杂声中,那种吱吱喳喳的声音非常尖细,引人注意。说它是歌声,真是一种罪过。”布封在《动物素描》里对麻雀也是恶骂,“它懒惰、贪吃”,“尽干蠢事而又一文不值”,在我看来,格雷和布封欠缺的是我的奶奶对麻雀的情感。
奶奶与麻雀厮守一生,太知道它是贴近人性之鸟,就连叫声也含着喜怒哀乐。她把麻雀称呼为雀儿,多了这个“儿”,就是一种情感。她分辨出雀儿“唧唧”“喳喳”两种叫声的不同含义,“唧唧”是肚子饿了,“喳喳”是发现了食物,招呼同伴一起分享。听见“唧唧”声,她说雀儿肚饥了,踮着小脚抓一把谷出来撒在院子地上,喜眉喜眼看着雀儿争抢。偶见几只还在地上磨蹭,她便知它们还没吃饱,就又捏些谷喂给它们。吃完,它们绕着奶奶的头顶,旋转了一圈又一圈。它们以此姿态,感恩奶奶的疼爱。
奶奶说,雀儿如果生气了,吐音是闷声的“喳!喳!”要是高兴了,会“喳喳喳喳”一连串叫个不停,一窝蜂飞来飞去,张狂得像是要去啥地儿看大戏呢。
我家院子的雀儿,一代又一代,繁衍不息。
斑鸠
斑鸠之美在于装饰简朴。对此,曹植也认可,他在《白鸠讴》中赞之:“斑斑者鸠,爰素其质。”
斑鸠喜欢结果子的树,将一颗柔软之心定格于树枝。晨起散步,斑鸠站在柿树枝头咕咕叫着,发音像是汉语里的早安,向我致以春天的问候。在这条林间小道旁,我与它相逢无数,到那棵柿树下,我的步子会习惯性缓慢,等待它的问候,有时我也会主动向它招呼,我的招呼就一个尾韵轻柔的字:嗨——,它露出树叶里的身子,眼里扑闪着善解人意的光芒,用叫声回应我:“咕咕、咕咕,咕——咕——”,轻柔,悦耳,旋回。
秋天的时候,我发现斑鸠喜欢鹐食柿子的落果。
涝河的芦苇丛隐身着许多斑鸠,风在轻摇,芦苇铺排着音乐般的形态,像是从纸页上跳出来的五线谱,斑鸠就在其中闭目陶醉,或曰养神。我下河试图接近它们,它们却瞬间飞出苇丛,惊恐啼鸣。我的出现,也许不是时候,它们正如帕斯卡尔那样思想着,却被我惊扰。不过在我听来,它们的叫声像是风一样抚响松木古琴弦样的羽轴,发出悠扬的颤音。
尽管聆听到了美声,我还是要向它们道歉:对不起,原谅我的莽撞。
天地之间,总是人类必须向无数的生灵说声对不起。
斑鸠形似鸽子,体羽蓝灰,带着一些淡淡的葡萄酒色。它的喉部粉红,若少女之味,温柔可人,北宋诗人梅尧臣诗情赞誉:“颈上玉花碎,臆前檀粉轻。”它的修长之尾,像是大自然的精心修剪,深得乡野之人喜爱。农人认为斑鸠为吉祥鸟,谁家屋进了斑鸠,被视为极佳住宅风水,预兆家人无灾无病。俗语云:“喜鹊欢叫,喜事来到;斑鸠飞舞,家家有福。”
温庭筠之子温宪写的《春鸠》是一幅春和日丽背景下的人鸟和谐,桑树下温暖舒适,斑鸠屋脊闲鸣,诗人与邻居心神愉悦。斑鸠清脆鸣啼,是这首诗的诗眼。
修成爷是村子的老秀才,谁家筹办喜事,会携礼登门。求他作对联,喜棚、院门、新房至少三幅。他从不推辞,铺好红纸,研好墨,那些词语就从他的脑袋里飞出来。院门的对联上,总是少不了“鹊笑鸠舞”的组合。
斑鸠枯草筑巢,坚守稻谷遗风,寄寓农人期盼,在柔软芳香的草屋顶上说着悄悄话,倾听农人的呼吸。
鹌鹑
鹌鹑形似麻雀,纺锤状,头小尾短,尖嘴黑背,羽毛若稻谷。乡下有谚语:吃啥像啥。许多以谷物种子为主要食物的鸟雀身上,都有谷物种子的形状或谷穗的形状。
鹌”字音同“安”;鹑,凤凰类神鸟。在远古,鹌与鹑是两物,《本草纲目》曰:“鹌与鹑两物也,形状相似,俱黑色,但无斑者为鹌也,今人总以鹌鹑名之。”
鹌鹑性格温顺,不像麻雀宁死不被笼囚。它的名字寄寓平安祥和,禾穗之形色意寓岁岁平安,乡人养于家院,以图平安吉利。收秋之后,即为农闲时节,老人聚到一起,地上摆个簸箕,放两只笼养的鹌鹑进去相斗。与蛐蛐脾性一样,鹌鹑碰到一起一定要分出胜负。挑逗鹌鹑相斗,农人借此打发晚秋以至冬日漫长的时光,也有老人把鹌鹑握在手心,称“把鹌鹑”。鹌鹑眉眼微闭,缩身于掌,心神安详。老人的腰带里裹着一个纸包,里面装着小米,估摸着它饿了,捏出几粒塞进它的嘴里。享受张嘴即食的生活,它很幸福,很满足,忘却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翅膀会带它升向高空。
朋友家养了只鹌鹑,挂于石榴树枝,见我进院,在笼里跳来跳去,窄小的笼子难以让它舒展羽毛,瞧着我怜惜的眼神,它似乎心有灵犀,忽然张嘴啼鸣了几声,在我听来声调中满是委屈,还有叹息。它会做梦吗?梦的背景会不会是辽阔的天空和绿色的山野?
这寓意吉祥之鸟,古代文人也喜欢。中国花鸟画以鹌鹑为题材者众多,个性纷呈。南宋赵葵的《鹌鹑图》,一只鹌鹑立于山石上凝视前方,一足立,一足松,毛羽丰满,体质团圆,细节精致。同为南宋画家的李安忠绘有《安居图》《鹌鹑图》册页及《鹌鹑》团扇。明代鹌鹑画注重形象,呈现写意雏形,朱耷的《鹌鹑图》洒脱着墨,着意夸张鹌鹑之眼,眼圈阔大,眼珠顶到眼眶上角,似在昂首问天。
唐玄宗时期,鹌鹑被供养、赏玩于宫廷,《鹌鹑谱》载:“惟唐外史云,西凉厩者进鹌鹑于明皇,能随金鼓节奏争斗,故唐时宫中人咸养之。”明永乐时期,一个叫边文进的画师被召至京师专绘鹌鹑,流传有《鹌鹑图》,两只鹌鹑立于草丛,一只俯首觅食,另一只笔挺而立,显现趾高气扬之态。它也许在想,来到皇宫,岂能如稻谷般卑微猥琐?如此丢弃本性之鹌鹑,我不喜欢。
与斑鸠一样,鹌鹑亦是朴素之鸟。朴,未加工的木头;素,未染色之白绢。布衣陋舍是朴,粗茶淡饭亦是朴。朴是寂的开始,素是在减法中不断体悟明亮与欢喜。
朴素为最高级的审美,如庄子所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穿一袭素衣,赏一轮秋月,守一堆老人,如此的乡野鹌鹑,多好。
鹰
鹰有天鸟之称,为天之骄子,心境在无限高远的境界,如苏东坡所言,“一点浩然气,万里快哉风。”人和动物无法抵达的地方,它都可以光临。与人类相比,它的眺望要宽阔得多,比人类的见识显然要多得多。
秦岭梁顶菜子坪的一面巨石,我瞧是一尊佛,同行友人说是一个慈祥的老者,无需争论,对自然的审美各有角度。突然,我们同时发现那面巨石上站着一只鹰,像是佛或老者的守护神,宛若天书里的一幅插图。在秦岭山间,常见坚硬的峭壁间和悬崖上伫立着一只鹰,翅膀别在身后,如同穿着垫肩大衣的将军,倾听草木颤动和岩石呻吟。那样的地方,人是无法抵达的,但鹰却可以,这样我就只能对它仰望。
与其它鸟类不同,鹰选择遥远的领空和人迹罕至的悬崖为生命背景,为世间万象做着神性的解读。它的窝叫地巢,建在人迹罕至的干燥岩石之间,数尺宽,木棍支撑,中间是柔软的树枝,铺几层灯心草,安全、稳固、舒适。只需一次建巢,便可享用一生。产在空寂险拔崖石间的卵蛋并非所有的都能孵出小鹰,通常只有一两只。鸟研究者甚至认为,幼鹰稍微长大,母鹰就会把最弱的或贪吃的那只杀死,不是绝情,而是它们的生活区域不能供给多余的食物。幼鹰一问世,就在高远而孤绝的起点,一旦强壮会飞,就被父母驱赶出巢,自谋生路。
鹰被誉为百禽之首,在先民眼里为图腾形象。在鸟类中,它属于精神贵族。海涅在《论法国画家》中这样说:“一个展翅高飞的天才,他要飞得安全保险才能令我们感到愉快;我们只有对他的翅膀的力量有信心,才能分享他高飞的喜悦,只有这样,我们的心灵才会跟随他直上艺术的九霄,达到无比纯净的太阳的高度。”
审视鹰眼,颇似原始时代陶器的纹饰,具有巫术礼仪的图腾性质,庄严、恐怖、神秘,称它为神鸟毫不为过。它是富有神性的鸟,有灵性,有使命,有飞翔的缥缈,也有震慑的力量。飞在高处的鹰,人必须以仰望的方式,才能见到它隐约的风姿。天幕绸蓝的底衬上,别着一枚高贵的徽章,谁才配接受这样的颁赠?
《淮南子·人间训》有这样两句:“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间。”此二句,我以为说的是鹰。
天空翱翔的鹰,地上行走的人,各自丈量着天与地的距离。鹰拉开与人类的距离,就是隔绝了世俗。存鹰之心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成大事者,需有鹰一样的活法。
精神贵族,王者风范,这是我对鹰的赞誉。
秃鹫
常人心里,秃鹫是恶鸟,通体黑色,光头,圆鼻,眼睛凸出眼眶,带钩嘴,羽短褐,后颈无羽,爪子短平,浑身上下照应着它的“秃”名。其状凶恶,让我联想起商周青铜器上的神秘图纹,一种神秘的气氛和象征,呈现出李泽厚先生所言之“狞厉的美”。
搭眼看,秃鹫长得有几分像鹰,但两者风范迥异。鹰总是高傲直立,显得盛气凌人,而秃鹫的站姿呈低伏状,低头哈腰,飞行笨拙,仿佛明白自己的相貌丑陋。在美学家眼里,丑的审美价值体现在美丑对照、美丑对立、以丑衬美、化丑为美、形式丑等方面。作为审美范畴,丑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和美学价值,因为“丑”照亮生活中的病态和阴暗。罗森克兰兹《丑的美学》明确了丑在美学中的独立地位,美学大师叶朗认为丑有一种“意义的丰满”,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等。美丑对照原则是雨果在1827年发表的剧本《〈克伦威尔〉序》中提出的,他认为“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如果创作的过程能做到美丑对照,相辅相成,可以使人们对崇高优美产生更强烈的感受。而如果将美与丑割裂,就失去了自然的完整面貌,也就失去了真实。雨果把这种原则贯穿在《巴黎圣母院》创作的全过程。
如此,秃鹫之丑同样具备着审美。世界是以对称的方式设计的,昼与夜,阴与阳,黑与白,雌与雄,美与丑,善与凶……甚至人类品行的每一种高尚,都配对着卑鄙。物种的安排,印证了老子关于自然之道的普遍法则与现代物理学家玻尔的互补性原理。常常,我们会发现丑与美是相对的:鹰和鹫,狗和狼,猫和鼠,龙和蛇,青蛙和蟾蜍……这是怎样奇异的对立?矛盾,对垒,冲突,对比之下彰显出一方的美德。也许,上苍觉得只有在矛盾中才能体现自然界的平衡之美。
秃鹫不会对鹰怀有刻骨仇恨。嫉妒产生的先决条件,是两者之间具有某方面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我无从知道秃鹫对鹰怀有怎样的情感,它从未有过什么明确的表示。
很难见到成群的秃鹫,如老子之言:“我独异于人。”秃鹫的孤独,不是寂寞,而是源于内心的警觉。既然无法赢得美誉,就要警惕猎人的眼睛和猎枪的准星。
秃鹫孤独而不自私,每当发现食物,它在高空旋转身体,告知同伴。
曾在公园凝视笼中一只目光炯炯的秃鹫,心想,这个秃顶又驼背的家伙,难道是《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个敲钟人卡西莫多?
鸟类专家言,秃鹫虽样子凶煞,却从不主动伤人,除非你惹它生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鸟如是,动物大抵也是。
秃鹫是天葬的主体,从来没有人见过它的尸体。它具有人类不具备的第六感官,预知死期将至,它拼命朝着太阳飞冲,直到太阳和气流把它的躯体消溶,其死亡方式颇具神秘意味。藏人视秃鹫为上苍之使者,期盼死者之尸被秃鹫肚腹收留,如此灵魂可以被秃鹫带入天国,就像依壁鸠鲁说的那样:“幸福,就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
孔雀
羽毛上汇集着天地间诸多色彩,将阴暗、冷暖不同的色调融为一体,提炼出瑰丽的光泽,若鲜花鲜艳,如宝石璀璨,像彩虹绚丽,使孔雀成为大自然的杰作。
孔雀的古典特征表现于两个细节:一是头上的羽冠像一把弯曲的镰刀;二是尾上的覆羽呈青铜色。
“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这是唐人张祜的诗句。
温庭筠用笔更妙:“红珠斗帐樱桃熟,金尾屏风孔雀闲。”
带孙子去秦岭动物园,首入眼帘的是一只雄性孔雀,收拢着翅膀,平静地走来走去,远远的一只雌孔雀向它靠近,雄性孔雀摇动着冠毛,伸展开长长的双翅,起伏波动,宛如一棵果实累累的小树。孔雀开屏,着意舒展,若碧纱宫扇,尾羽眼斑反射光彩,仿佛无数面小镜子。
孔雀开屏,虽是自我保护的功能,却被世人视之为吉祥,具有古典美的特征,在希腊神话中,孔雀象征着赫拉女神。古人以为,孔雀有“九德”,依照《逸周书·常训》的解释,即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一言以蔽之,文明之鸟,寓意吉祥如意、白头偕老、前程似锦。
孔雀是传说中凤凰的化身,被誉为百鸟之王,入列吉祥图案之“三台”,鹤为协台、雉为道台、孔雀为府台。以孔雀羽纹饰以古代官服及官帽,明清时为鼎盛。孔雀属阳鸟,百无禁忌,可化煞镇宅,招财引贵,在家宅悬挂孔雀展屏,配以牡丹画,二者遥相呼应,寓意和谐。做官弄商回家,品一盏浓茶,摆一副倦态,瞧一眼孔雀,再看一眼牡丹,自是怡然舒神。
江南诸多水乡的家宅,精细的木雕上少不了孔雀的身影,屏风、门窗、床背,甚至笔筒,富豪之家,竟有大型的孔雀木雕立在客厅。我视力不好,凑近细看,却不敢手摸,怕脏了它的身子。
鹤
巧、细、轻,这是汉代以后艺术家的审美倾向,鹤全部占有。它是鸟类中的模特,是懂得呼应美学的鸟,以喙、颈、腿“三长”著称,身披洁白羽毛,行云流水,裸露着的朱红头顶,似一顶小红帽,脖颈如一根细绳,脖子和尾部为黑色,行走的姿态如踩高跷。十九世纪一位印度鸟类学者如是赞之:“不论以什么姿势站立,它的头、颈和身体的整个轮廓,都呈现出最高雅和匀称的曲线。”
鹤的瘦打破了我们习惯中的平衡比例和审美感觉,具备强烈的个性色彩,契合西方美学注重个性和自我观念的推崇,为鸟类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水中的它仪态万方,奇异地保持着自身均匀的美态。诗经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可看作是对鹤的献辞。头和尾都是黑色的,这是懂得呼应美学的鸟,它的影姿因此也颇宜于在雪中展现,体现出和谐之美。
鹤在求偶时,要进行优美的舞蹈仪式。在它的意念里,动作比语言更适宜于表现内心世界。
在宝鸡陇县白鹤坪见到八渡河畔的一只白鹤,它以悠闲的姿势在一块石头上伫立了十几分钟,之后在我的瞩目下,它翩然冲天,在空中掠过一条白色的弧线,隔空传来鸣声,其音唳嘹,若《诗经》里的句子:“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鹤唳,不及百灵、夜莺婉转,但有着别样的清傲,令人感受到一种苍茫的岁月。淝水之战中,自以为投鞭断江的符坚大败而逃。溃兵失魂落魄,闻听“风声鹤唳”,皆以为追兵来剿。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区。鹤的叫声,其实是那样优雅,让人荡气回肠。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总爱倾听“来自云层上鹤的叫声”,那美妙的天籁,如李商隐所言:“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有了鸟鸣,天地间才有了音乐。
我常想,在这物化的今世,诗肠、佛心、侠胆,还有那美妙的鹤音,真的如历史的烟云,渐行渐远了吗?
鹤迎合着东方童话的推崇,在东方受到的欣赏远胜于西方。鹤的童话境界,成为文人墨客经久不息的表现内容。唐人储光羲《杂咏五首·池边鹤》有句:“舞鹤傍池边,水清毛羽鲜。立如依岸雪,飞似向池泉。”宋朝的林逋,因“梅妻鹤子”而成为《梦溪笔谈》的著名典故。由于它所具备的玄学色彩,神话传说中,鹤是神仙的坐骑。天蓝云白,仙人骑鹤杳杳而去,优雅,浪漫。与“爱屋及乌”同理的“慕仙至鹤”,鹤因神仙的荫护关系,被人们认为享有千年的传奇寿命。古人以“龟鹤遐龄”来为老人祝福,其实鹤龄不过五、六十年,根本不能与龟相提并论,但在鸟类中,鹤应是高寿了。
鹤把窝建在芦苇及沼泽地带,吃的是水生植物的嫩芽、种子、水生昆虫、软体动物和鱼类,临终也要依偎于水的怀抱。水中之鹤仪态万方,性情高雅。《诗经》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可以视为对它的献辞。
白鹭
早晨在涝河边散步,看见河边的白鹭,从来都是孤单一只,未曾见过杜甫诗里“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种盛景,白居易的那句“何故水边双白鹭”也让我纳闷,更有宋朝诗人唐庚,以白鹭为诗题,写出“说与门前白鹭群”此般诗句。是白鹭改变了性格,还是诗人们不甘寂寞?
打开《诗经》,亦有白鹭踪迹,《周颂·振鹭》有此二句:“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手头有本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的《诗经》解读本,二句注解为:成群的白鹭展翅高飞,就在那西边的水泽边。我又皱眉,“振”的本意为“挥动”,怎么可以释为“成群”之意呢?
或者是,古人喜鸟群居?
孤独,是白鹭生命的常态。它的沉默,被我用思想者解读,虽然这比喻有点别扭,也从无人反驳。
伫立,静静的,苍穹间弥漫着安详凝练的静态姿势和内在精神,这是白鹭赋予我的感受。美丽、娴静、优雅,宛若绘画与诗词艺术里的婉约之美。我想和它交朋友,与它并行于河水中,可是,它对我保持着足够的警觉,每当我向它靠近,本来一动不动的它朝着相反的地方走去。我的念想,只能是种奢望。尼采说:人与人之间是应当保持一定距离的,这是每个人的“自我”的必要的生存空间。
白鹭孤身独处,静享流水岁月,我视之为哲学意象。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说:“生命从来不曾离开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成长、相爱,还是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
道家主张清净,推崇“独钓寒江雪”之境,我以为是。心灵的洒脱与浪漫,人格的完满与圆融,皆源于孤独。
人曰:孤独是一味泡久了的中药,浓腥而回甘。
责任编辑:尹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