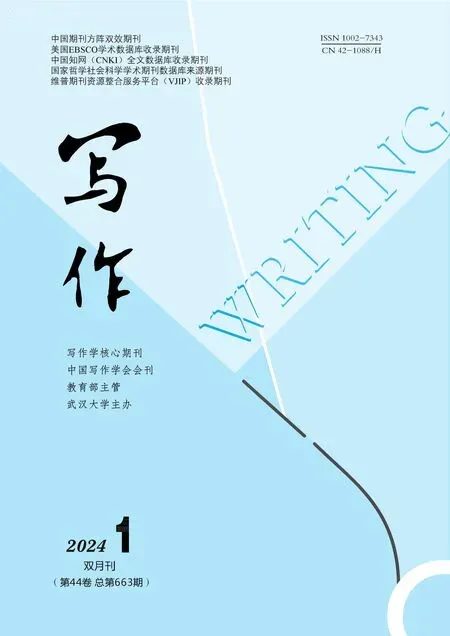从体验到拟剧:创意写作中的戏剧意识
史玥琦
关于《阿Q正传》的戏剧改编问题,鲁迅在对《戏》周刊编辑的回信中写道:“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而后笔锋一转,就未庄是否在绍兴、阿Q 该说何种方言陈述意见,若是绍兴话,有上等人“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下等人“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的特点,而“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并不懂得,其剧本作用便减弱。鲁迅提议可以将此本作为底本,到各地方展演时可以结合当地土话,地方背景和人名也可更换,只为使看客觉得“切实”①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第148-151页。。从家乡社戏到京剧批评,从翻译介绍外国戏剧到对中国学生话剧的观演支持,从《社戏》到阿Q 唱《小孤孀上坟》,再到《伤逝》涓生和子君两次谈易卜生,更有其杂文批评时而引用戏曲故事、传统唱词,鲁迅几次讲述“毫无研究”不可不谓自谦②在《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中也有“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的表述。参见《鲁迅全集》第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其小说不仅大量容纳戏剧元素,也常用现代戏剧手法叙事,长于场景的营造交替,叙述者以冷峻笔调直观呈现人物言行,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被弱化,而是以场景的内在联系构成完整结构③汪晖:《戏剧化、心理分析及其它——鲁迅小说叙事形式》,《文艺研究》1988年第6期。,又以强劲的意象如药、头发、长明灯等作主旨隐喻和象征。若以“文体互渗”为线索考察中国新文学传统,鲁迅作为先行者只是一股前浪,在现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小说的戏剧化或戏剧体小说已是普遍论题④王爱军:《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如郁达夫所说,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⑤郁达夫:《现代小说的渊源》,《小说论》,光华书局1931年版,第13页。。我们也能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至深的契诃夫创作中找到这种写作的当代性——小说和戏剧意识的融合。
一、小说和戏剧的互渗
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课堂上谈到小说的异质性时曾引用卡尔维诺的话:“我们生活在没完没了的倾盆大雨的形象之中……这些形象被剥去了内在的必要性,不能够使每一种形象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内容,不能受到注意,不能成为某种意义的来源。”①[意]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此语指涉视觉形象,道出这些强行进入我们视觉听觉的事物散漫无序。契诃夫的小说素来以“现成的小戏”著称,生活散漫的印象被组织起来,由于个人生活与剧场难解难分,其本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友谊也传为知己佳话。其作品小说和戏剧两种文体是相互纠缠影响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戏剧中的对白和独白可以独立为小说人物的对话和心理独白,而去掉小说中叙述者对人物和环境的描写,抛去细枝末节,小说叙事也可当作剧本旁白。这种转换的便捷帮助其在生前就将多篇小说搬上舞台,如《克尔汉特》被改编为《天鹅之歌》,《无力自卫的人》被改编为《纪念日》等。
托马斯·曼曾撰文评价契诃夫作品:“小型的压缩形式也可以传达真正史诗的内容,就艺术的紧张度而言,这种形式远超其它形式。”②转引自凌建侯:《小说与戏剧意识的融合——论契诃夫的当代性》,《国外文学》2005年第8期。这里的紧张度可理解为戏剧性。不难看出,卡尔维诺和契诃夫在对现实材料的组织上存在某种以“现代”为节点的文学传统流转后的暗合,契诃夫在彼时语境下的“细腻洞察力”过渡为卡尔维诺对文学任务的认知,即文学应赋予现实某种形式,它是组织起来的,可见的,同时也是被场景化了的。戏剧包含时间和空间的限度。人物的直观锚定和勾勒,戏剧总是和舞台挂钩,而王安忆的“小说异质性”正容纳时间、空间和人物三个方面的论述。在创意写作课堂上,这种异质性被阐释为现实进入小说发生的质变,即形式中的生活如何改变形态。王安忆在课堂上举了一个切身例子,她曾在最高检察院旁听一桩死刑案的终审开庭,被告青年男子自河北来沪务工,杀了前妻的现男友,他的行为属于激情杀人还是预谋杀人,这对量刑来说区别很大。公诉方主张预谋,举证其带着刀具、手套、胶带等作案工具专程前往前妻住处,而辩护方则解释说作案人未按期见到雇主,于是绕路见被害人。最后由被告本人陈述,他的一句话颇具意味:假如最后什么都没发生,那身上带着什么,是否是专程去是不是都算不上什么!王安忆进而阐释,这意味着所有事先的行为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但最后的杀人案将一切细节都组织起来。“我们小说要做的,就是要人为制造一个案子,足以将看似漫不经心的人和事结构成形式。”③王安忆:《小说课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137、155页。而这种文本生成的前提无疑是戏剧式的,甚至可以说是戏剧的教育,创意写作的基础训练即是这样合理而符合逻辑的“作案”,即使人有异禀,变成甲虫,这些异人“最后上演的是一出再现实不过的戏剧”④王安忆:《小说课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137、155页。。
在这层意义上,小说作者的使命在于让“自然”或“现实”的人物合乎逻辑和顺序地动作。在复旦创意写作的课堂中,一种怀疑的声音从不中断,即这个人物为何如此?他的情感逻辑是什么?是什么使他这样?课程的写作任务往往以“故事接龙”、命题创作以及非虚构体验的形式呈现,要求写作者编织材料,“提取”故事,并以“探案”般的形式逻辑反复追问。人物和故事的诞生往往在设计之初,而后的工作则是一气呵成,有时命题的选材空间尽管相似,但如何编织、发现欲望仍是创意写作中“创意”的旨要。张怡微就曾在“小说写作实践”课堂上带领同学阅读欣赏福克纳的《烧马棚》、村上春树的《烧仓房》以及李沧东的《燃烧》,以解读同一故事模式下小说及电影文本的内在关联和表现区别。上述的这种扎实的写作策略始终是一条与刚入学的追求灵感突现、火花迸裂的创意写作新生相龃龉的暗流,却让创意写作基础课程“小说写作实践”的作品成果每每“顺产”,学生们在学期末回头,发现自己的写作已在平稳的可见的道路上。
以王安忆、张怡微为代表的作家老师们深植于现实主义理论土壤的发问,既是使小说写作者有迹可循的扎实创作方法,又深切关联着近百年前的俄罗斯戏剧课堂:“请问你自己:‘假如我处在剧中人的规定情境中,我将怎样按照人的方式行动?’”①[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3 卷,郑雪来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 年版,第230页。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文体互渗的深层观照,这种将现实要素组织起来的训练如同一场舞台展演,有意识地描述物的意志、行动和情感,并把它放进规定情境中去理解,以“体验”或同等效能的追问引起情感本身。戏剧是不断流动的已成的事实,而其文体本体在形态发展中的成熟取决于其形成了“观”—“演”之间的审美距离,又合乎规律地使人物“变形”②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6页。。这一意识在小说文体上构成了创意写作基础训练的核心前提之一,即被安放的现实。正是这种展演—观看、现实常态—异质人物的戏剧式双重紧张使小说文体得以在创意写作教育生成中提前确立,并经得起情境、逻辑乃至与生活距离的阅读推敲。
二、超文本戏剧的“围读”与“展演”
自国内第一个创意写作专业在复旦大学“登陆”以来,十余年间各校竞相建设创意写作学科,其重创作而轻研究的特性与表演类、影视制作类艺术学科同质,所授予的学位也属艺术硕士学位(MFA)③关于学科范围论述参见史玥琦:《“登高”与“望远”——创意写作的四种艺术延伸》,张怡微主编:《写作知识的革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233页。。小说写作工坊一直是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和主要活动形式之一。复旦创意写作除“小说写作实践”课程固定设置的开放式研讨外,王安忆、王宏图、张怡微等任课教师也邀请海内外作家、编辑、导演及各类艺术创作者参与学生的小说文本生成及情感、情境构建。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常见的小说研讨会不同,小说写作工坊吸收英美经验,重视反馈和批评,小说文本的实时评价形成模拟社会的“公共舆论”,批评和正在创作的作品同时“在场”④班易文:《创意写作的诗意如何可能——中国高校写作工坊发展方向初探》,《2015 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论文集》,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2015年版,第135-141页。。而基于复旦创意写作展开并辐射至其他各高校的小说工坊,如“猫头鹰小说会”“惊险小说工作坊”“庚子写作计划”等都是以匿名研讨评点的形式展开的。
文学史意义上,一篇小说的经典化,离不开四种身份,即作者、编辑、读者和评论家。大众阅读层面,我们多数看到的是以读者为核心、作者和评论家分别发声的小说发布会,或者小说研讨会,它们在小说结束后不断地呈现意义,以供传播和解读。匿名小说会是以作者为核心、编辑和读者去发声的改稿会,意义在彼此讨论中不断产生。在匿名的状态下,其余作者担任编辑和读者两种身份,两种身份互动参与文本生产的过程,能为作者在叙事策略上增一份力,而这种围坐式的开放文本讨论及实时的修改、反馈,和戏剧展演前演员及编剧、导演坐在一起“围读”剧本极其类似。
以2022 年6 月于线上举办的复旦中文系“猫头鹰小说会”为例,与会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基于《流俗地》的盲人人物创作经验对会上小说文本《夜游神》⑤小说修改后发表于《收获》2023年第4期。中的盲人书写提出修改意见,充分肯定作者的方言运用和隐喻设置,并假设了几种不同的命运情形,来反推该小说如何成立①此次会议举办于2022年6月30日,相关报道见《我对中国大陆文学新人充满希望——复旦大学猫头鹰小说社对话黎紫书》,网易号,网址:www.163.com/dy/article/HBE9OEII0544B8E4.html,发表日期:2022年7月14日。。此处作者的盲人书写经验并非传统写作者的“学习”如何去写,即参照既有的眼障书写,形成单向经验的汲取,如向经典文本《推拿》《民间音乐》“取经”等。相反,工坊形态中由成熟文本的作者提供经验视域,经验出现了双向的交互,即编剧和演员共同完成剧本的“呈现”版本,从单向的“剧本解读”到双向的“剧本共读”,个人的小说在工坊中如经过一场集体“彩排”。这种“围读”将小说的创作视域扩大到工坊全体,并呈现出“超文本”的状态,彼此独立,内在关联。某一类人物创作经验必然涉及其他创作主体的形象意识。如在此次会议上,《流俗地》中的银霞同《夜游神》中的盲人书写形成文本的并置,而其余文本涉及的残障叙事也将在此网状结构中被“观看”和共享。这一超文本形态的目标,正是在“围读”后进行的成品“正式演出”,即工坊内的小说被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当然,这类文本似乎也应在结构式批评中被考量,对于尚“年轻”的本土创意写作学科来说,工坊的建设依然有益于创作主体视野的打开和叙事多样性探索。
戏剧型的“展演”意识在创意写作的非虚构写作训练中同样重要,如在2019年12月光华楼举办的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两校创意写作“上海地铁”非虚构写作比赛中,张怡微邀请校外编辑、作家、记者参与匿名文本评点。在动员现场型的非虚构书写之前,她鼓励同学们亲自乘坐具体的某线,并贯穿整条线地“在场”观察、走访、体验,以现实质料取代故事想象。用王安忆的话说,非虚构写作有一种现成性,它是真实发生的,人们基本顺从它的安排,无条件地接受和承认②王安忆:《小说课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1页。。比赛文本依托现实,以“超文本”式的选取形成情感逻辑线索,构成新的伦理真实。在当时的匿名研讨中,常见的“人物怎样想”“他为何如此”不再是一种文学主体的推敲,而是不容置辩的对现实的再反思。叙述主体固然无法与人物合一,却在非虚构批评场域中有一种完美贴合的期待,其鲜明的叙事意图正如演员对角色的塑造,当“剧本”(现实)已敲定,如何趋近“角色”(主人公)的远景(线性意义)成为非虚构写作的当务之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在舞台表演中,任何表演、动作、思想、言语、情感都不能没有相应的远景和最高任务,演员应掌握充分的心理技术,在每一个表演单元中对角色的过去和未来进行瞬息检查,并在每一个瞬间考虑到这一远景,以估量角色当时所处的单位状态,结合角色的最高任务,合乎逻辑、有顺序、有系统地配置情感,从而达成有惯性的展演③[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3卷,郑雪来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60页。。面对已成现实的材料、故事、人,非虚构写作也应将主体安放在演员位置上,考量被书写角色(真实人物)的“贯穿动作”。以此次比赛中的优胜文本拙作《消失的年轻人》为例,主角地铁站务员小米从兴奋入职到决然离开,经历的是情感递进的“一场场独幕戏”。每幕戏一二主角,如离家出走的小女孩、失约吵架的情侣、精神异常的朱阿姨、躲在楼梯间喝农药的自杀者以及刁蛮的乘客,现实百态构成了小米的角色远景④李北京:《现实的表情——关于〈消失的年轻人〉》,《红豆》2020年第7期。。对现实质料的提取以最终的远景“展演”为前提,我们固然可以将这种非虚构书写简化为从生活材料中提炼戏剧性,但其观察、体验、表演型塑造的叙述肌理更值得重视。
三、戏剧教育与编排
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开设创意写作方向不同,复旦创意写作挂靠“戏剧”硕士学位,在作品的鉴赏与分析中,小说和戏剧隔山望高,常有来回。这一点在南京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课堂上体现得更为鲜明,很多专业课程都是戏剧班与创意写作班同上,所留作业主题相同,只是改写形式不同:戏剧班写剧本,创意写作班写小说。尽管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复旦的课堂仍不乏艺术教育,王宏图所主持的创意写作必修课程“艺术创作方法研究”,即邀请多位从事不同种类艺术工作的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的老师讲授,涉及戏剧、影视、音乐、美术、舞蹈、绘画等。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并长期带领复旦学生排演戏剧的周涛试图围绕“故事”这一核心、以斯宾格勒式的观相审视戏剧艺术,又将罗伯特·麦基等多位炙手可热的西方戏剧理论家的故事线画出,表明现代戏剧的无可逆转的“西方性”,比对中国传统戏剧的单线大团圆或双线闭合的扁平结构,呈现出“戏剧学”的整体讲授。而复旦创意写作戏剧教育的缺位已非一时之谈,较早有16 级创意写作学生伍华星《学徒及其漫长时代》谈及课程中加入的戏剧元素,当学生比较《呼啸山庄》的小说与戏剧时,其文体意识是鲜明的,边界感是清楚的,而他也提出了关键问题,学生的剧本改写不尽人意①伍德摩:《学徒及其漫长年代》,《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第7期。;更早有张怡微《隔膜与创新:谈戏剧教育与创意写作》,以马文·卡尔森《戏剧》为中心,梳理国内外各类戏剧教育经验,注重其对创意写作的方法论提领②张怡微:《隔膜与创新——兼评马文·卡尔森〈戏剧〉》,《通识教育评论》2020年第7期。。周涛反复强调“讲故事”为核心,以及课堂中表现剧本写法的即时表演,他着重于戏剧的展演关系,即“戏”的部分。的确,戏剧的最终呈现是舞台化的,多数文学专业的学生对戏剧的参与往往是写剧本(一次习作,或一篇寒假作业),而忽略最为关键的舞台呈现部分,写戏不看戏,使对话、场景都处于“悬空”状态,更无“好看”的可能。
大学戏剧教育能否有一次完整的“写、练、演”过程?或许我们能从一些关注“成长”的通识课堂获得启发。笔者曾在张怡微教授的“《西游记》导读”这门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课上担任助教,给本科生做过关于戏剧导演的任务的报告,为学生的期末舞台展示提供可参考的方法论,调动大家表演与导演的积极性。这门课的课堂展示要求是对《西游记》进行任何形式的戏剧改编,时长为20分钟以内。要讲一个传统的舞台故事,无论是小品还是更为复杂的话剧,只要立足于现实主义的人性冲突,总会要求导演把控全局,对舞台呈现有全盘的掌握:第一,他要担任一个解释者的身份,导演对剧本做出阐述,根据剧本文本的原有思想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二次创作,确定演出立意,将剧本“舞台化”;第二重身份是镜子,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对演员创作给予回馈和引导,包括演员调度,计划、彩排、舞台情境的浸入;第三重是组织者,表现出对综合流程的把握,包括场景、设计图纸、舞台站位、舞美、灯光、道具等,即“一个不懂表演的好道具不是一个好导演”。而在表情和动作的延伸上,戏剧舞台、现实以及电影特写大概呈十倍递缩的关系,话剧舞台上的演员无论从仪态还是动作都需尽可能地“夸大”,是现实幅度的十倍有余,而电影却要在一颦一笑间将正常情绪“缩小”,以实现镜头外观者情绪的延展,即“戏剧既是听觉的也是视觉的”。如尤内斯库所说:“它并非像电影那样的一连串的图像,而是一种建筑,由舞台图像构成的活动的建筑。在戏剧中一切都是许可的:使一些人物具体化,但也使一些焦虑,一些内在的存在物质化,因此使道具表演,使物体活,使面景有生命,使象征具体化,这不仅仅是被许可的,还是被推荐的。”③转引自[法]米歇尔·普吕讷:《荒诞派戏剧》,陆元昶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223页。而就学生的演出效果来说,在加分制度的激励下,大多数学生表现踊跃,尽管仍显青涩,个别学生已展现出很强的舞台意识。美中不足是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小组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导演机制,叙事节奏也因排练不足而脱轨,但其戏剧训练是整体性的,即编、导、演于一身,同时也照顾到故事的进行。将故事“讲圆”,是任何一台戏成立的前提,学生在短暂排练中重溯自身的观看经验,表现出模仿、叙事的戏剧本能,这或许是“创意”成分在戏剧文体中的最大价值。
复旦创意写作也重视培养学生欣赏戏剧,带领学生走出校园“看戏”,如组织学生观看由专业导师王安忆的《长恨歌》及校外导师金宇澄的《繁花》改编的戏剧。在同题条件下,学生从经典小说接受转向戏剧接受,更有益于对各文体创作的认识。同鲁迅就阿Q的方言问题发表意见类似,当代文学经典的戏剧改编往往都有原作者的加持和“在场”。在大众接受层面,改编的舞台剧是否“忠实”于原著成为某种隐性标准,《繁花》话剧版的编剧温方伊就曾援引理论家琳达·哈钦的《论改编》谈她的创作,认为改编作品并未丧失独立性,但她仍不希望改变小说原作的风格和结构,只因还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法来替换和转化原作极高的文学性和画面感①温方伊:《繁华梦里说书人——舞台剧剧本〈繁花〉创作谈》,南京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该剧自2018年在上海首演以来广受好评,不久即登陆北京,在全国巡演。与原作枝枝蔓蔓、浓稠黏腻、叙事空间交错暧昧不同,舞台剧需有清晰的主线和矛盾,在叙事整体格调上保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繁花》第一季舞台剧只截取小说的一部分,将阿宝和小毛的友谊前后变化作为戏剧前提,人物行动的主线也随着这一前提展开。温方伊为其主题表达“大刀阔斧”地裁减阿宝、沪生和小毛在原著中对沪上人生百态的旁观与参与,隐去诸多情感分支轶事,使三个主角得以中心化,另将小说中阿宝和蓓蒂坐在屋顶俯瞰上海的开场作为引子,添加90 年代的两个孩子坐在屋顶上望景作为收尾。舞台呈现上,《繁花》的最直观特征即遵循原著满纸沪语而采用全程沪语对白,这一选择打破了读者面对小说的阅读区隔,直接将观者抛入彼时情境当中。这对非吴语区观众接受既是鲁迅所提及的“外县人”命题挑战,又是一种对文本中方言叙事的高度还原。该剧舞台设计同样是改编的亮点,在前后、高低景区的分区布置下,时空交错分明有序,中心一个大转台是舞台的中心表演区,其旋转功能全场共使用三次,从常熟饭局的大圆桌构成同心圆,到李李讲述自己受辱,在床垫上翻滚,再到伴随《新鸳鸯蝴蝶梦》的音乐,演员站成一圈谢幕②谷海慧:《话剧〈繁花〉召唤出了原作的“声音”》,《文艺报》2018年7月16日第4版。。改编剧以隐喻型的道具设置重塑了原作的宿命感和轮回表达。金宇澄也在多次访谈中表示舞台剧是独立于小说之外的创作,这种转化依然能“撞击”观众,有意想不到的内容表现。从人物筛选到情节组织,改编剧注重对原作“神韵”的表现,并获得作者的首肯,这在2003年话剧版《长恨歌》中也可见一斑。此剧经一定打磨,于2021 年4 月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再度上演。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进入剧场,得以“重温”《长恨歌》的当代性。王安忆在演出结束后的分享会表示,话剧版是最靠近她的版本,电影电视的改编反而和原著几乎无关。“贴合创作本意”是该剧导演苏乐慈、制作人李胜英的美学意图。直面人的复杂性,更好地塑造人物不仅是戏剧或小说的内核,也是艺术本身的内在表达。王琦瑶的时代将越来越远,这也意味着随着一轮轮演出,“摘掉”形容词变得越来越困难。王安忆引述编剧赵耀民的话:“我们不能把她演成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她要做一个好女人很简单,嫁给程先生就可以了,但她有一种征服的野心,对自己的命运有一种挑战性。”③何晶:《她给予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无限的想象 话剧〈长恨歌〉即将再次上演》,《文艺报》2021年3月26日第4版。这种看似“凌空”的内核把握往往成为剧作改编的要素,而对再创作的观看与解读无疑为经典作品的生成之考察提供了美学空间。改编剧不失原作者的参与,这就给写作的还原提供一个缺口或视角。这种文体跨越的“回看”和“重读”,也为有关创意写作的“作家是可教的”的经典论调提供了一个新的主体诠释。
四、创意写作的戏剧性启示
如前所述,如何“作案”是创意写作学生面对的首要基础问题。在复旦创意写作的学科培养中,一个学生平均要在三学年内完成5—8篇短篇小说及1—2篇中长篇小说,故事的“完成度”通常是先于文学风格、美学取向的首要考量。专业导师严锋就曾多次在毕业答辩中提及对学生作品的期待,要有“内部爆裂”“紧张感”,让人“眼前一亮”的情节。王宏图也表示作品中的人物不应按部就班地按预设情节机械运动,应有生活中“自由意志”的展现。这些对于小说叙事的前置基础要求蕴含着两种戏剧性命题:一是人物间冲突的内在性,二是人物本体与创作主体的距离和人物主体的意志体现。
谭霈生曾试图对戏剧性作出定义:“在假定性的情境中展开直观的动作,而这样的情境又能产生悬念、导致冲突;悬念吸引、诱导着观众,使他们通过因果相承的动作洞察到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本质。”①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动作”是叙事艺术的基本单位,无动作的小说空剩场景和心理的“搁置”,终使情节落入虚空。关于动作的设置和想象,张怡微在“小说写作实践”课堂上常援引诸多戏剧、电影情节举例说明,一方面是因为戏剧和电影时长较短,接受度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浓缩了矛盾,将小说的“暧昧”空间压缩,便于冲突的展现。如何使人物行动是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必经训练,对于一定程度上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作者而言,长于心理抒情常使小说中的动作“疲乏无力”,导致最终的学生作品只有结构而叙事平平。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反复提及演员要坚守三个原则:首先是绝对客观(Super-objective),即客观化台本给出的效应、表演结果,这样在叙事的“反复”中会造成真实差异,比如三打白骨精中玄奘的不同反应;其次是坚持舞台呈现(Stage action),对目标和心理斗争进一步发挥,如哈姆雷特的经典独白“To be or not to be”,表达真实的问题,将其抛给观众;最后是暂停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要相信故事的发展,取消“间离”,设置自身的任务,不再扮演人物,而是“成为”人物。当然除此以外,一些“黄金法则”为普世之演员公用,如热情的真实和情感的逼真;注意规定情境,抓住最高任务;贯穿行动线,动作连贯;注重形体表现,不仅仅是体验以及交流、适应。以我在武汉大学莎士比亚戏剧社的戏剧经验为例,“写”往往是服从于“演”的,这也要求戏剧创作从开始改到最后,直至第一次演出结束,剧本仍需打磨。好的剧本往往是如此“磨”出来的,更不必说对经典的重新排演,要求我们重现原戏的文本节奏。因此,“围读”往往是真正验收戏剧剧本的开端,演员、导演、服化道(舞美呈现)同编剧四种身份的合一讨论将使戏剧从“可读”转向“可看”,这或许是创意写作教育侧重于“创意”时可发展出的制度方向。如何以故事的方式包装一个非故事,如何在非故事的时代继续讲故事,复旦艺术教育中心戏剧教师周涛引用奥斯卡最佳编剧威廉·戈德曼的话,可以作为对于无论希望用哪种方式讲故事的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共勉:“所有故事结局的关键就是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不是通过他们所期望的方式给予。”
而就深层体验来说,创意写作也能从戏剧展演经验中汲取养分。2022年8月俄罗斯迈克尔·契诃夫中心曾就“行动分析与小品工作方法”在中国大陆开展线上戏剧表演公开课。迈克尔·契诃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安东·契诃夫的侄子,他的表演理论影响深广。他主张舞台上的“生活”要大胆,而非生活在舞台上,戏剧应超出真实,演员想象自己头顶“光环”。他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能量的身体”戏剧观,认为演员应以“想象动作”训练,除外部可见的身体之外,还有一种能量身体(Energy body),它虽不可见,但可感可控,不断赋予本体能动性,演员要做的即是将两种身体打通,操纵“能量”。与此同时,他认为外在的身体和内在心理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一个身体动作和姿势都和心理感受相联系,通过清晰、准确而强烈的身体姿势可以唤醒相应的内在感受,是为“心理姿势”。演员不断训练这一高度浓缩和可持续的表演动作,便唤醒其内在生命,想象和制造“心理姿势”成熟后,便慢慢呈现出丰富的下意识的角色动作,其姿态和质感也是属于角色本身的,即进入了角色内部①何雁:《迈克尔·契诃夫方法:“身体——心理”表演训练方法研究》,《电影艺术》2017年第9期。。戏剧公开课的主讲导师拜切尔阐释,好的表演呈现不能去命令情绪,而是使情绪随动作体现,创作者能做的只是完成动作。他在课堂上做了一个实验,让全部学生站起来,把自己房间中的灯关闭。随后他问学生,这个行动困难吗?是不是比让大家哭泣的要求更简单一些?他随后解释,前者是可以百分百地通过意志力实现的,我们可以告诉自己去举手,去蹲下,这些全在我们的意志范围内,是自然而然的“行动”。我们无需强迫自己去产生情感,我们也不用臆想关灯和举手,这些行为由于在意志范围内可控而显得简单。而意志外的行为需要我们调度外部身体去尝试,以此调动内心感受,来找到准确的人物感觉。一个完整完成的“行动”。我们可以用斯氏的话来定义:行动是朝向目的的意志力的体现。不难看出,这种外—内—外的调动身心的行动界定,为我们打开了小说人物何以行动的塑形空间,而这一动作设计在小说书写中的底色,也正是王安忆在早期小说讲稿中提到的“心灵世界”,她将小说形式解释为“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另一种规则、原则、起源和归宿”②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我们可以在这重意义上,将小说中的动作理解为通过其“心理姿势”生发出来,当我们根据心灵姿势去“行动”,小说作者去“训练”人物的直观动作,叙事文本才会“有戏”,小说也得以成立。
诚然,小说的材料总是根植于生活又有所区隔。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作品要么来自外部的“传奇”,要么来自现实经验的“想象”,其基本策略是某种对异质性日常生活的重构。如学者欧文·戈夫曼著名的拟剧理论所述,日常生活中,个体总是在扮演一种角色,他不言而喻地要求观察者认真对待在他们面前建立起来的印象,要求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人物实际拥有他们所看见的品性,也要求他们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有适于他品性的结果。他将积极调动他的行动,当处在他者面前时,用各种标记强化自己的行动,这些标记戏剧地突出和勾勒若干看似确定的事实③[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9页。。这种双重意志的观察和取材当是创意写作专业学生构建人物的现实底本,各类现实生活的自我呈现如一场“深表演”,创意写作抓取的是那一闪而过的本雅明式的“灵韵”。当大幕落下,人物独处,任何成熟叙事文本的生成都当保留一个鲜活的“幕后”,那里安静如初,又热闹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