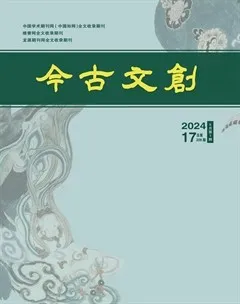美狄亚与霍小玉复仇形象的文化溯因
【摘要】美狄亚与霍小玉是中西文学史中两位为情复仇的女性。在面临“被抛弃”的悲惨境遇时,她们均毅然决然走上复仇之路,实现由弱到强、由依附到独立的个性转变。但由于中西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她们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的愤怒的强度不同、表达愤怒的方式不同。在审美营造上,一个走向激烈的崇高,一个则趋于平和的优美。
【关键词】美狄亚;霍小玉;复仇形象;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4)17-005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17
在男性擁有绝对话语权的父权制社会,女性被动地从属于男性,承受摆布与摧残,她们的声音被湮没,她们的形象消逝于历史烟尘。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成熟,女性的命运及生存状态得以书写,一个个面目清晰、个性鲜明、具有自主意识与抗争精神的女性形象呈现于世人眼前,展现了独属女性的勇气与力量。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和中国唐代小说家蒋防笔下的霍小玉,便是这样的典型。
一、心系理想,却沦为弃妇
美狄亚与霍小玉这两位复仇女性虽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在爱情轨迹上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同样怀揣着炽热的心与所爱之人结合,倾情付出;同样被男性一方无情背叛;痛定思痛过后,她们同样勇敢地站立起来,做出复仇的选择。
少女时期的美狄亚对爱情有着无限向往与憧憬,从被厄洛斯之箭射中后,她便疯狂地爱上了伊阿宋。她将爱情置于首位,视为一切,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与伊阿宋厮守一生,永远幸福。为了铲除爱情道路上的阻碍,她不惜背叛故土、手刃胞弟并残忍分尸、设计杀死珀利阿斯、心甘情愿流落异乡。她的爱太过强烈,以至于失去理性节制而走向泛滥。在她为爱付出的时候,她忘记了全世界,也完全忘记了自己。圣修伯里曾言:“爱并非存于相互的凝视,而是两人一起望向外在的同一个方向。”美狄亚在爱情中,一心一意凝视对方,陷溺在两人建造的小世界,完全依恋于伊阿宋,而忘记去思考自己的退路和未来。当伊阿宋为了现实利益,迎娶公主,联合国王驱逐她时,她才幡然醒悟,痛心疾首于曾经无知的行为,为当下异乡异国的境地而忧虑懊恼。
“不邀财货,但慕风流”“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体现霍小玉超越世俗、重才重情的爱情观。首次见面,她便对风流才子李益一见倾心,一言一行都透露着少女怦然心动时的矜持与娇羞。她将自己交付给李益,从此温顺柔婉,一心一意,矢志不渝。她是痴情的,害怕失去李益,又怕自己的身份耽误李益,于是定下八年之约,将无限之爱倾注于有限之期。她看重的,不是“情”的长度,而是“情”的厚度与质量。所以,当她得知李益瞒着她聘娶卢氏,背叛了她最珍视的情义,她才会如此决绝、如此刚烈。
美好的爱情理想的破灭对两位女性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她们誓要让负心汉接受惩罚、付出代价。美狄亚与霍小玉无疑都是具有智慧的女性,她们复仇的最终目的不是杀之后快,直取其命,而是要让负心汉长久地承受生的折磨。死的痛苦是一时的,难解心头怨恨,而生的痛苦则伴随终生,无法摆脱。
二、“暴力杀子”与“化为厉鬼”
复仇目标一致,但美狄亚与霍小玉的复仇道路却迥然相异:美狄亚杀子,让伊阿宋变成一个无子的人,毁灭了他的全部,让他悲惨一生;霍小玉化作鬼魂,在李益心里埋下猜忌的种子,让他亲手断送他的幸福,在疑心与不安中度过余生。
两者在具体的复仇方式的择定上呈现较大差别:美狄亚手段血腥暴力,霍小玉则相对温和;美狄亚连带报复情敌,霍小玉只惩罚负心汉;美狄亚独自复仇,霍小玉拥有外界的同情与帮助;美狄亚在现实世界中反抗,霍小玉凭借超现实力量进行反抗。
当美狄亚被背叛时,从爱中生出恨。因为她的爱是如此排山倒海,也就使得她的仇恨比火山喷发更有爆发力,比惊涛骇浪更有吞噬力。既然她爱伊阿宋时可以为他摧毁全世界,那么她恨伊阿宋也要摧毁他的全世界。所以,她不仅要惩罚伊阿宋,还要惩罚公主与国王。她在精美的衣饰上投下可怕的毒药,当公主穿戴上袍子与皇冠,毒药发作,公主被活活烧死,死状凄惨恐怖。老国王抱住公主的尸体,也沾染上毒药,最后痛苦死去。为了让伊阿宋绝后,彻底击垮他,她可以做出极端的杀子行为。在美狄亚被抛弃时,没有人主动给她提供帮助,就连埃勾斯也是美狄亚与他达成交易才得到他的庇护,并且整个复仇活动都是依靠美狄亚一己之力独立完成,面对夫权和强大的王权,她勇敢、暴烈,不留任何回旋余地。
霍小玉是死后复仇,她熟悉李生多疑、胆小的性格,于是时时化作鬼魂出现,以陷害的方式离间李益与妻妾的关系,使得李益惶惶度日,不得安宁。霍小玉的复仇手段是温和的、间接的,她没有对李益做出实质性伤害,只是利用他多疑的性格,逐渐攻破他的心理防线,施加心理压力,在精神上慢慢折磨他。同时,霍小玉的复仇也不如美狄亚那样可怕、骇人,她顾念李益对自己尚有情谊,所以她不是以凄厉的鬼魂形象出现,而较温美,所做出的报复行动也只是躲在帷幔后向卢氏招手、抛掷小盒子,而没有故意惊吓。霍小玉的报复对象明确地指向李益一人,虽也不可避免地牵连卢氏、侍婢媵妾,但却并非她有意为之。当霍小玉被李益抛弃时,她的遭遇得到众人同情,公主资助她钱财,崔允明告知她真相,黄衫客促成二人见面,社会舆论也皆是感叹小玉的多情,愤怒李益的薄情,她远不像美狄亚那般孤立无援。
在复仇过程中,美狄亚与霍小玉的形象都发生了变化,且发展变化方向大致相同,均为由弱到强、由依附到独立,但仍有区别:美狄亚的气质近乎女战士、女英雄,而霍小玉依旧带有传统女性柔美底色。
在面对心爱之人的绝情背叛时,美狄亚是悲痛至极的,她折磨自己的身体,悲叹自己的命运,懊悔自己遇人不淑、真心被负,苦痛世上没有识人的良方。但她没有就此沉溺在痛苦的漩涡中自怨自艾。“要是我想出了什么办法、计策去向我的丈夫,向那嫁女的国王和新婚的公主报复冤仇,请替我保守秘密。”在此之前,美狄亚的情绪是低落的,而至此就出现了转折,她已经迈过“怨”的层次,而走向“怒”“恨”。她激发起原始强力,击破权力、道德的框架,像战士一般,发出复仇宣言:“我一定向着勇敢的道路前进,虽然我自己也活不成”。她的“怒”“恨”是暴风骤雨式的,但因有了“理性”的参与,所以她的一切复仇行动都表现出英雄独具的隐忍、清醒。她可以为了报仇,在国王面前奉承、卑躬屈膝;可以忍着愤怒和恶心,假装与伊阿宋和解;可以智慧地施加法术,设下圈套让公主、国王都走向死亡;她还会冷静思考自己报仇完毕后的退路,与埃勾斯达成约定,全身而退;她甚至可以忍痛杀子,只为让伊阿宋永远陷入悔恨与痛苦的泥沼。
她对伊阿宋的爱让她失去独立性,而她对伊阿宋的恨让她重拾自我。杀子标志着美狄亚斩去了母亲与妻子的双重身份,回归为独立个体,完成身份蜕变、自我蜕变。
蒋防所写的霍小玉是典型的在传统社会道德规范下成长的女子,她才貌相兼,知书达理,性格温顺,在爱情中专一执着又甘愿退让。对于李益,她不是自私地长久占有,而是许下八年短愿,为他的前途未来着想。当李益迟迟未归时,她四处奔走探访,期盼用银两换得消息,以致最后钱财散尽,忧思成疾。但此时的霍小玉仍仅有“怨”“恨”的情绪,而尚未产生发泄“怨”“恨”的冲动。崔允明的出现是第一次转折,他将李益的背弃行径告知小玉,文中这样描述:“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一个“恨叹”承载了千钧重的情感:错愕、難以置信、怀疑、委屈、悲痛、怨愤、绝望。确证了李益的背叛,一颗复仇的种子悄然埋下。黄衫客促成二人的见面,他的仗义相助推动了第二次转折。相见后,小玉一反以往娇弱、退让形象,不是嗔怪、哭泣、投入怀抱,而是“含怒凝视,不复有言”。良久,小玉举杯酬地,倾泻愤怒:“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霍小玉勇敢地迈出了复仇、反抗的一步。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有太多女子在爱情中被辜负,但大都敢怒不敢言,或只是简单地表达不满,最后仍与负心汉重归于好。而霍小玉与这类女性不同,她敢爱敢恨、敢怒敢言,不妥协、不让步。死亡不是复仇的终结,而是开端,她借助超自然、超现实力量完成复仇愿望,惩治负心汉。虽说“化为厉鬼”,但后文鬼魂的形象却是姿态温顺美丽,所有的动作也都轻柔,并无恐怖之感。
美狄亚与霍小玉的形象都是逐渐走向刚烈的,美狄亚的复仇表现阳刚美,轰轰烈烈,走向崇高,而霍小玉的复仇呈现出阴柔美,如流水潺潺,走向优美。
三、复仇形象的文化溯因
美狄亚与霍小玉有着相似的爱情经历,在男主人公负心情变后也都走向抗争。但她们的复仇方式却大为不同。为何如此?这就不得不回归两位女性的生存土壤,回归各自生活的时代、国度、社会文化背景,去探求合理的解释。
美狄亚激烈、残暴的复仇之举与古希腊海洋文明特征分不开。一方面,海洋文明崇尚冒险、进取,注重人的价值与现世享乐,强调个人本位。另一方面,海洋文明推崇英雄主义,主张对命运不屈不挠地抗争。这使得他们敢于主动追求幸福,敢于向背叛与不忠进行反抗。但由于过分放大自我感受,缺少理性节制,行为也容易走向极端。
美狄亚在追求爱情时,她抛弃了一切,手足、父母、国家,统统都不要了,眼里只剩下伊阿宋。为了伊阿宋能脱险,她甚至做出杀弟这样违反伦理、违背道德的举动。在被伊阿宋抛弃时,她能鼓起全部力量,释放自己的报复欲,大胆果断地对夫权、王权做出反击,誓要鱼死网破以泄恨。她将个人情感与好恶放在首位,肆无忌惮地发泄愤怒,而毫不受社会规约与伦理道德的约束,不用隐藏情绪、收敛个性。她突出个人力量与意志,根本不需要仰仗外部势力,独立自主地开展复仇计划。她干净利落地杀死情敌,狠下心杀死两个儿子,展现出西方民族赞赏的“英雄本色”。
霍小玉生活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她的性格与行为都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
首先,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与强调冒险、开创、征服的海洋文明不同,农耕文明注重务实、稳定、和谐。它以土地为根本,追求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协调,避免变动与激烈的冲突、争斗,这也造就了自省向善、内敛沉稳的民族性格。霍小玉在得知李益负心后对情绪极力收敛克制以及选择用和缓的方式进行复仇,就体现出这种性格特征。
其次,儒家思想作为古代社会正统思想文化,也支配、影响着霍小玉的言行举止。儒家一个很重要的道德标准是“中庸”,放在个人情感方面, 就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儒家文化要求和谐,要求克制忍受来维持制度的稳定和延续。因此,应当怨而不怒,既怨又能受。《卫风·氓》中的弃妇就是典型:“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包含着隐忍的无限怨恨。后世许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弃妇也延续此类形象特点。霍小玉最后虽既“怨”也“怒”,用生命控诉负心汉的背信弃义,但她的整个情绪的递进过程与发展变化并不如美狄亚那般迅猛、激烈,愤怒的强度也不及美狄亚,由此也可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对她的潜移默化的浸染。
最后,霍小玉化鬼魂复仇的方式与佛家因果报应思想有关。妇道以敬顺为本,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女性必须严守社会强加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深受君权、族权、父权的支配与压迫,社会地位低下,力量弱小,始终处于依附、从属的第二性地位,失去话语权与独立意志。在爱情中被“强势”的男性一方抛弃时,女性很难反击,或反击的效果甚微,无法彻底地反抗,彻底地战胜男权。因此,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但终了还是与莫稽重归于好;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自投江心,但未对负心汉做出实际报复。男尊女卑,力量悬殊,中国古代女性没有社会条件与思想基础,像美狄亚一样在现实中正面挑战并摧毁男权。这就导致负心汉似乎种下了“恶果”,却没有“恶报”,并不需要付出对等的代价,接受相应的惩罚。而中国人信奉“有因必有果”“善恶终有报”的伦理正义,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冲突,人们做出了无奈却智慧的选择——扭头转向另一个世界,跳脱出被种种清规戒律捆绑住的现实,借助超现实、超自然的“鬼神”之力,伸张迟来的正义。李益违背誓言,始乱终弃,凭霍小玉一人之力,无法完成复仇,于是霍小玉终结自己的生命,将死亡作为复仇的开端与契机,让李益承受应有的折磨。窦娥如此,蒲松龄笔下的窦氏亦如此。弱者不该生来逆来顺受,她们也有发声的权利与自由。“鬼魂复仇”的反抗虽有明显的局限性,带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但它使得一个个冤愤的女性得以梦想成真,使善与公平正义最终实现,彰显出女性微弱却不妥协的抗争力量。
参考文献:
[1]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4-18.
[2]李昉等编.太平广记:足本3[M].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4:2356-2358.
[3]林晓彬.不同的悲剧形象 相同的悲剧命运——中希弃妇形象比较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01):85-89.
[4]杨晓莲,罗均丽.美狄亚与窦氏——中西文学中复仇女性形象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06):60-65.
[5]王宝峰.传统儒学中的女性观及其现代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04):23-31.
作者简介:
钟桢楠,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生。
——对古希腊悲剧形象美狄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