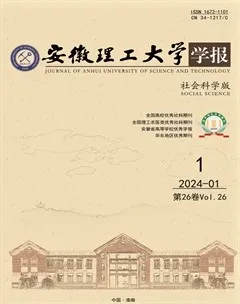中共“二大”代表考证
代先祥 韩玥
摘要:中共“二大”是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相关原始文献资料严重缺失,会议地点频繁更换,以及会议代表未经民主选举产生等原因,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始终难有定论。文章通过史料的比较、鉴别,在分析中共“二大”代表构成的基础上,梳理出包含12名代表的完整名单,并对大会的列席人员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中共“二大”;代表;考证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24)01000907
收稿日期:2023-08-12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gxyqZD2021009);煤炭行业高等教育研究课题(2021MXJG161);安徽省高校“三全育人”试点省建设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研究项目(sztsjh-2022-1-9)
作者简介:代先祥(1982-),男,安徽庐江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列出了出席中共“二大”的11名代表名单,同时注明尚有1人姓名不详。
中共“二大”是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并通过了党史上的第一部党章。目前学界对中共“二大”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一些基本问题,如出席的代表依然成疑,各方说法不一,尚无权威结论①。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史料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辨析,以期对厘清中共“二大”代表名单有所裨益。
一、中共“二大”代表难以确定的原因
中共“二大”代表难以确定的原因有很多。首要的因素是原始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并且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研究者考证中共“二大”代表较有影响力的证据主要来自两份文献:一份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该文献指出,参加中共“二大”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的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1]128。这份材料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提交给共产国际的补充报告,从成文时间看,最接近中共“二大”召开的时间。但这份材料并非原始文件,是由俄文稿翻译过来的,并且文中提到代表分别来自7个地区,却只列了6个。另一份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2]190(以下简称中共“六大”统计表),内中载明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共12人,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施存统、李达、毛泽东、许白昊、罗章龙、王尽美。统计表涉及中共“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是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在与会期间整理出来的。统计表中有毛泽东的名字,但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并没有参加中共“二大”。
首先,当事人的回忆是考证中共“二大”代表的重要依据。目前能找到的有李达、张国焘、包惠僧、罗章龙等人的回忆资料。但因年代久远及政治考量等主客观因素,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彼此之间出入很大,甚至同一当事人的说法也前后不一。如张国焘认为,包惠僧是武汉地区代表[3]233,而包惠僧却否认[4]11参加了中共“二大”。李达在1955年的回忆文章中列出包括自己在内的6位代表[1]587,可几年后又说自己不记得具体名单了[5]449。罗章龙在晚年回忆说自己是中共“二大”代表[6]12,但他早年的回忆录却只字未提参加中共“二大”之事。
其次,中共“二大”出于安全需要,不断更换会议地点。据张国焘回忆,中共“二大”鉴于上海的政治环境,决定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以分组活动为主。每次全体会议都变换会址。1922年7月16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转移到英租界的另一个地方,7月23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再次更换地址。小组活动采取流动开会的形式,分散在党员家中进行,因此部分上海党员也参加了小组活动。为期8天的大会实际只召开了3天,这使得与会代表彼此印象可能不够深刻,时隔多年,参会代表的回忆难免模糊不清。而分组活动的会议形式造成每次参会人员都不固定,一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就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中共“二大”代表。
再次,中共“二大”代表是由中共中央局提名或协商产生,并没有经过民主选举。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7]。因此,地方党组织对中共“二大”代表人选应该有所安排。但据李达回忆,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哪省的人就作为哪省的代表”[1]587。这就导致计划的代表人选与实际参会代表有差异,亲历者事后的回忆也就不尽一致。
最后,中共“二大”前后,相继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921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罗章龙、邓培、毛泽东、王尽美、许白昊、李震瀛、袁达实、冯菊坡等10余人。1921年4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党和青年团的负责干部会议,陈独秀、蔡和森、张國焘、张太雷等20余人到会。1922年5月1日—5月6日,中共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刘少奇、谭平山、李启汉、许白昊等出席了大会。1922年5月5日—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施存统任团中央书记。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出席会议。从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可以看出,与会人员大部分是交叉的。在缺乏文献记载的情况下,亲历者多年后的回忆难免会混淆多个会议的参加者。
二、关于中共“二大”代表人数的争论
中共“二大”代表有多少人?学界有20人、15或16人、13人、12人、9人、7人等多种说法。目前研究者普遍认同的是12人说,依据就是中共“六大”统计表和文献《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前一份文献明确指出中共“二大”代表是12人,后一份文献则指出7个地方党组织有7位代表。有论者认为[8]296,如果加上中央局3人以及工团组织各1人,正好也是12人。那么,这12位代表究竟是哪些人?7个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分别是谁?对于这两个问题,学界尚无统一结论。为便于统计、鉴别,现将亲历者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回忆资料整理如下。
李达在1955年回忆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除陈独秀、张国焘外,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等。”[1]5871959年,在给中央档案馆的信中他又说:“二大代表共有十五、六人。代表的具体名单,我记不得了。我所记得的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我。但确实记得毛泽东、谭平山、杨明斋没有参加。”[5]449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有党员123人,到会的正式代表只有9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党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3]233。
罗章龙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中说,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人数不多,除了自己之外,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等。他还讲到会议期间的一个细节,某天晚上开会,陈独秀因事中途离开,委托他主持会议。在和王尽美互相推让一番后,由他主持会议直至陈独秀回来[6]13。
包惠僧在1953年[4]11、1954年[4]391和1979年[4]433的3篇回忆文章中都说,项英代表武汉地区出席了中共“二大”。中共“二大”共有6个地区代表参加,每个地区1名代表,加上中央3位委员共9个人。
此外,有资料将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等7人视为“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名单”[9]。还有研究者认为,四川党员王右木是中共“二大”代表,并且就是“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的那位代表[8]321。
综合上述各种说法以及中共“六大”统计表,中共“二大”代表名单共涉及21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施存统、罗章龙、杨明斋、陈望道、张太雷、李震瀛、项英、许白昊、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谭平山、包惠僧、向警予、王右木。其中,毛泽东和包惠僧都否认参加了中共“二大”,因此可以排除。王右木的代表身份仅是一家之言,持此论者主要是基于中共“二大”召开时王右木正在上海。有研究者据中共江油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王右木传略以及阳翰生的回忆资料认为,王右木去上海的目的并非是参加中共“二大”,而是忙于请示团中央承认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合法事宜[10]。这样,王右木也可以不予考虑。那么,剩下的18人哪些是中共“二大”代表呢?笔者拟从中共“二大”代表的组成来进行一一验证。
三、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的考证
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由3部分组成:中央局代表、工团组织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作为中央局的成员,肯定是中共“二大”代表,众多的文献资料都能佐证。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参加了中共“二大”,并在“二大”上作了关于青年团问题的报告,那么他是不是“二大”代表呢?尽管张国焘以及中共“六大”统计表都提到施存统是中共“二大”代表,但学界仍然不能确证。2012年,《党的文献》杂志第1期披露了一组存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团中央档案。根据档案记录[11]30,1922年7月15日召开的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13次会议决定,推选施存统代表青年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施存统代表青年团参加中共“二大”也就确凿无疑了。
对于工会组织的代表,目前学界在邓中夏和李震瀛之间争执不下。认为邓中夏代表工会出席中共“二大”的依据有三:一是邓中夏当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二是邓中夏在“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三是李达回忆说邓中夏参加了会议。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12],邓中夏的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并不能证明他是中共“二大”代表,因为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照样能当选中央局书记。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六大”统计名单中并无邓中夏,而邓中夏又是中共“六大”代表,应该参与了中共“六大”代表的集体回忆。一般情况下,作为当事人,在仅仅隔了6年后对自己是否是中共“二大”代表是不会记错的[13]。既然邓中夏不是出席中共“二大”的工会代表,那么同在劳动组合书记部任职的李震瀛则当然是代表。
笔者认为,邓中夏作为工会代表出席中共“二大”的可能性更大。最主要的证据就是,邓中夏是中共“二大”选出的5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如果说缺席会议也能当选中央委员,那么李大钊应该比邓中夏、高君宇、蔡和森等更有资格。邓中夏不在中共“六大”统计表上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觉得,中共“六大”的这份集体回忆名单可以作为参照,但也不能盲目采信,毕竟名单上的部分代表还是有疑问的,如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的毛泽东竟被视为中共“二大”代表。何叔衡出席了中共“六大”,应该也参加了对中共“一大”至“五大”代表的集体回忆,但是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他却不在根据这次集体回忆整理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名单上“六大”统计名单记录了11位中共“一大”代表,分别是: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包惠僧、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佛海、王尽美、陈公博,何叔衡和邓恩铭不在其中。。因此不能就此断定,凡是出席了中共“六大”,但名字不在中共“六大”整理出的中共“二大”代表名单上的,就不是中共“二大”代表。也就是说,尽管邓中夏不在中共“六大”统计名单上,但他仍有可能是中共“二大”代表。这个推断同样适用于后文论及的高君宇和項英。
在明确了中央局和工团组织的5位中共“二大”代表后,接下来就可以确定7个地方党组织的7位代表。这里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中缺少的一个地区究竟是哪个地区。有研究者对照陈独秀于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认为,第7个地区应该是郑州[14]。陈独秀在这份报告中说:“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九十五人。”[1]56郑州有党员8人,在陈独秀所列的这些地区中排第7位,而且陈独秀对郑州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视。李达回忆说:“记得当时派赴郑州作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1]587因此,郑州派代表参加中共“二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这位代表就是中共“六大”统计表中提到的李震瀛。李震瀛是郑州地区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1921年11月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洛阳、郑州等地开展工运工作。蔡和森在1926年回忆说,李汉俊在中共“二大”前给中央写了一封意见书,“托振法同志从河南带至大会”[15]。学者李丹阳认为,“振法”就是李震瀛[16]。这进一步说明李震瀛是出席中共“二大”的郑州代表。
北京地区的中共“二大”代表,学界的争论集中在罗章龙、高君宇和邓中夏3人身上。3人均为北京党组织的重要成员,都有可能是中共“二大”代表,但按照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代表的规定,只能有一人代表北京地区。前文已经述及,邓中夏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的名字因为出现在中共“六大”统计名单上,所以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等权威党史著作所采信。可问题在于,不仅张国焘、李达等当事人的回忆中没有提到罗章龙是中共“二大”代表,而且罗章龙本人在其早年的回忆录《椿园载记》里也无相关记载,只记载了他当时正忙于组织安源工人罢工。尽管罗章龙在1981年接受党史学者肖甡采访时说,自己代表北方区委出席了中共“二大”,并说自己曾受陈独秀委托主持会议。罗章龙可能是想以此来证明自己出席了中共“二大”,但学界却对罗章龙这个细节描绘充满质疑,毕竟罗章龙当时在党内的资历和威望还比不上张国焘、李达等人,陈独秀怎么会让他代替自己主持会议?采访罗章龙的肖甡也对罗章龙回忆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他认为罗章龙可能把1921年9月中央扩大会议同中共“二大”混淆了。这两次会议召开时间接近,与会人员也有重合[6]15。相较于罗章龙,笔者认为,高君宇代表北京地区出席中共“二大”的可能性更大,依据有四:第一,高君宇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张国焘在回忆中说高君宇是中共“二大”代表;第三,高君宇符合李达所说的“从莫斯科回国的是哪省的人就作为哪省的代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发起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国焘、邓培、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冯菊坡、许白昊、林育南等出席了大会。;第四,据前文所引的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13次会议记录,中共“二大”召开前一天(7月15日),高君宇即在上海。
山东代表是王尽美,学界对此异议不大,不过有研究者认为邓恩铭也出席了中共“二大”。按照每个地区只能有1位代表的规定,邓恩铭可能参加了会议,但应该不是中共“二大”代表。
地方代表最难确定的是上海,目前学界有杨明斋、张太雷、陈望道3种说法。杨明斋代表上海党组织出席中共“二大”的最有力证据就是中共“六大”统计表中有他,但杨明斋既非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也未出席远东革命团体大会,所以由他来代表上海党组织出席中共“二大”的可能性不大。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中列出的中共“二大”代表中就没有杨明斋[17]。陈望道曾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工作,与陈独秀关系密切,一度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尽管后来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陈独秀的关系紧张,并因此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不过,陈望道当时并未脱离党组织,中共“一大”后还担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1922年下半年,陈望道提交辞呈,中共“三大”召开后正式脱党。有研究者认为陈望道脱党时间是1922年6月,并据此断定陈望道不可能参加中共“二大”,这显然是将陈望道辞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和脱离党组织混为一谈[18]。陈望道辞职后由张太雷接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中张太雷被视为中共“二大”代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的文献材料能证明这一点。陈望道辞去上海地方委员的时间是1922年下半年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陈望道辞职是在1922年6月。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在《我的父亲陈望道》一文中认为,陈望道是在“二大”后辞职。,也就是在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个时间段。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交辞呈?这也许和中共“二大”的人事矛盾有关。建党之初,以李汉俊、陈望道、李达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员注重理论宣传工作,而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高君宇等人则关注劳工运动。蔡和森在1926年回顧党的历史时,就指出了中共“二大”上的“小组织”问题,“这时中央显然分两派,所以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问题,结果这次委员为独秀、国焘、君宇、和森、中夏等同志,因此望道对中央更加不满意”[1]489。由此可见,中共“二大”上选出的5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4位都是“小组织”的成员,这让陈望道非常不满,也就更加消极。也就是说,陈望道可能出席了中共“二大”,目睹了两派之间的人事纷争之后,最终决定辞去书记一职。
湖北代表涉及项英和许白昊两人。许白昊虽然出现在中共“六大”统计表上,也参加了远东革命团体大会,但他的代表身份不能因此完全确证。包惠僧作为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回忆录中一再指出项英代表湖北地区出席中共“二大”。他还说,由于张国焘小组织捣鬼,中央要求他不要离开武汉,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可另派同志。为了不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出席,他就提名项英,得到多数同志同意。在包惠僧看来,当时武汉区委秘书许白昊就属于小组织分子[4]10-11。从包惠僧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中央是希望湖北方面派许白昊出席中共“二大”,而包惠僧出于对张国焘小组织的不满,指定项英出席了会议。此外,项英在中共“六大”后撰写的《许白昊同志传略》也未提及许白昊出席中共“二大”,说许白昊当时被党派至武汉指导汉阳铁厂工人罢工[19]。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采纳了这一说法,认为项英代表湖北地区出席了中共“二大”,许白昊因领导罢工斗争未能出席[20]。不过,湖北省委组织部编的《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依据《罗章龙谈话记录》(1972)和李书渠著《武汉建党初期情况回忆》指出,项英和许白昊均出席了中共“二大”[21]。罗章龙、李书渠曾和项英一起共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他们的回忆需要正视。可是,按照一个地区一位代表的规定,项英和许白昊只能有一人代表湖北出席中共“二大”。笔者认为,党史专家李良明的解释比较合理。他在《中共“二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中指出:“许白昊应该是中央局与中共武汉区委协商确定的代表,但由于领导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许未能出席,中共武汉区委后改派项英参加。”[22]如此一来,既未违背一地一代表的规定,也验证了项英的回忆记录,同时与包惠僧、罗章龙、李书城的说法也没有矛盾。
湖南代表原本是毛泽东,但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到上海后忘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同志,结果未能与会。在毛泽东缺席又未向大会请假的情况下,蔡和森有没有可能代表湖南党组织出席“二大”呢?蔡和森肯定是出席了中共“二大”,他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7月15日)列席了青年团中央执委会第13次会议,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是蔡和森能代表湖南吗?学界对此存有分歧,认同的一方认为,湖南不可能没有代表出席大会,由于毛泽东未到会,蔡和森代表湖南是可能的。反对的一方则认为,蔡和森1921年10月从法国回到上海后入党,没有参加过湖南党组织的活动,不可能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二大”。根据中共“二大”前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有“留法国二人”的记录,蔡和森应该代表留法支部,而且张国焘也说蔡是“留法中共党支部的代表”[3]233。笔者认为,蔡和森代表湖南的可能性很大,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所列的7个地区,湖南是其中之一,并未提到留法支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形成于1922年6月30日,是在中共“二大”召开前。报告在说明“党员和党费”问题时,提到“留法国二人”,并不涉及中共“二大”代表的构成。而《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则是在1922年冬提交给共产国际的,这时中共“二大”已经闭幕,对于中共“二大”代表的构成非常清楚。如果有留法支部的代表,报告肯定会列出。而报告中只有湖南等7个地区,说明中共“二大”就没有所谓的“留法支部代表”一说,因此蔡和森代表的应该是湖南党组织。至于蔡和森没有参加过湖南党组织的活动,这个说法根本不能成立。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与毛泽东鸿雁往来,就建党理论发表过很多有见地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深切赞同”,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广东代表是谭平山,这点学界没有不同看法。不过,有研究者怀疑,谭平山可能没有出席中共“二大”,因为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广东当时发生了陈炯明叛变,通讯出现困难,谭平山未能赶到上海。张国焘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发生在1922年6月16日,而召开中共“二大”的通知在1921年11月中央局即已下发,不存在通讯困难的问题。张太雷的行踪也可证明这一点。1922年6月30日,张太雷在广州致信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汇报青年团改组情况,并询问中央能否允许他回上海[23]。1922年7月26日,张太雷则出现在上海,列席了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次会议[11]。可见,广东的战乱并没有影响张太雷从广州到上海,自然也不会妨碍谭平山在同一时间段赴上海出席中共“二大”。另据陈公博1943年回忆,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后,上海方面的消息非常消沉,“平山虽然似浪漫无所用心,但聪明却不后人,和我商议要我们举他赴沪探听消息,趁早脱离这个是非之地,我自然听他的话,开了一次会,举他为广州共党的代表赴沪”[1]575。在这篇文章中,陈公博还抱怨谭平山到了上海后没能向陈独秀解释清楚他同陈炯明的关系,导致陈独秀对他误会极深,因此指责谭是“卖友之人,连做寻常朋友都不配”[1]577。这两则史料确凿无疑证明了谭平山不仅是广东地区代表,而且顺利出席了中共“二大”。
四、结论
综上所述,出席中共“二大”的12位代表分别是:陈独秀(中央局)、张国焘(中央局)、李达(中央局)、施存统(青年团)、邓中夏(劳动组合书记部)、高君宇(北京)、陈望道(上海)、王尽美(山东)、项英(湖北)、蔡和森(湖南)、谭平山(广东)、李震瀛(郑州)。由于为期八天的中共“二大”实际上只开了三天,其余时间都是分组召开小型小组会议,这些小组会议多在一些党员家中举行,因此部分在上海的党员如向警予中共 “二大”专门研究了妇女问题,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注重妇女运动的向警予完全有可能参加会议。、张太雷、杨明斋,以及从莫斯科回国的党员如邓恩铭,有可能参加了这些小组活动,但他们并不是会议代表,只能看作中共“二大”的列席人员。
这份代表名单虽然未经民主选举产生,也没有像中共“一大”代表那样经过充分酝酿,但还是考虑到组织均衡,同时也体现了地域均衡。中央、工团和地方均有代表分布,各地党组织也都有1名代表参加,符合李达所说的“从莫斯科回国的是哪省的人就作为哪省的代表”。于是也就出现了陈独秀指定蔡和森作为湖南代表接替临时缺席的毛泽东,以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尽管同为山东党员,但只能有1人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二大”的情况。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190.
[3]張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33.
[4]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刘春鹏.著名思想家书信鉴赏[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6:449.
[6]肖甡.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J].百年潮,2001,21(5):12-19.
[7]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5.
[8]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6.
[10]苗体君.王右木是否是中共“二大”代表的两种说法[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8,35(3):18-23.
[11]佚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J].党的文献,2012(1):3-35.
[12]汪家华.中共二大北京、湖北代表考辨[J].党史文苑,2012(8):68-71.
[13]周霜梅,刘明钢.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辨[J].天津政协,2012(8):45-46.
[14]王志明.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证[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8):7-9.
[15]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57.
[16]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77.
[1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71.
[18]乐基伟.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证与思考[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7):26-29.
[19]中央档案馆.革命烈士传记材料[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22.
[20]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57.
[21]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中国共产党湖北组织史资料[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11.
[22]李良明.中共“二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1):27-30.
[23]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集[M].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82:116.
[责任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