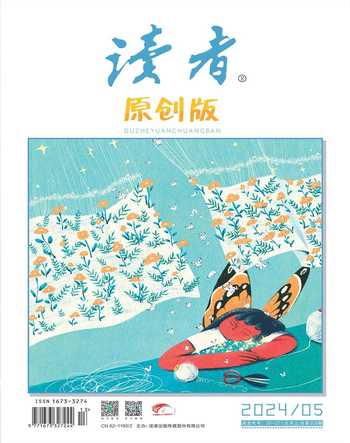我偏爱辛波斯卡
樊北溟

一
仪表盘上的指针向上竖起,指挥棒般,直指前方。
几乎在上车的一瞬间,我就确定自己不会迟到,但大叔还是把车飙到了每小时100千米。车窗外,春天的中欧平原极尽所能地舒展着它的绿意,湿暖的空气凝成绿雾,温柔而缱绻;车窗内,大叔显得比我都着急,一路上都在用波兰语对我说着什么,我拿翻译软件传译。他讲的都是敬语。
从目的地出发,导航把我带往了错误的方向,当我意识到沿途一直没有见到铁轨,准备回头时,已几乎没有可能赶上火车了。距离发车时间还有20分钟,坐电车去火车站?导航软件显示转两次线预计耗时58分钟。走路?抄近道至少也要1小时。我决定不再浪费时间,硬着头皮站在路边拦车。
这不是我第一次搭顺风车,却是最艰难的一次。所有司机都目不斜视地掠过了我,只有一个载着孩子的母亲停下来,听我说完,为难地指了指堆满东西的副驾驶,那意思是:没位置了。作为一个自驾超过7万公里的人,我非常理解司机们的心情,但也依旧可怜自己。对于陌生人,伸出援手是情谊,不是义务。所以尽管心里急得直跺脚,我没打算苛责任何人。
远远看见有一辆车刚启动,我立马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去。起先司机大叔也本能地摇了摇头,但见我执着且急切,便迟疑着摇下了车窗。
我把能想到的词语说了个遍,连同用翻译软件,这位波兰大叔总算搞懂了我此刻的窘境。于是他稍微沉吟了一下,允许我上了车。
“谢谢,谢谢。”仿佛怕大叔反悔似的,我不停地致谢。大叔没和我对视,挂上挡就跑。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变化无常则更加美丽
我偏爱不把一切/都归咎于理性的想法/我偏爱例外
几分钟之前,我还在一边朗读辛波斯卡的诗,一边美滋滋地吃“波兰版”的“海拉尔雪糕”,几分钟之后,我却表现得如此焦灼而局促。天知道我有多不靠谱。
我的鲁莽和自负给自己带来过很多麻烦,但也给我带来了不少奇遇。总之截至目前,我还是得到了世界的款待。
二
我没来得及告诉大叔我只是为一个名字专程而来,这是我来到科尔尼卡的唯一目的。由波兹南市区出发,由电车再转汽车,我终于来到了辛波斯卡的故乡。这位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天才作家、诗人,把一生之中绝大部分的时间留给了老城克拉科夫,最终仍然选择长眠于此。童年生活是一个人永不消磨的底色,因此我想来看一看,看那些妙笔和巧思是如何在坚实的土地上扑扇翅膀,吹出有力的风。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不是气象学家/不用知道云彩如何形成或气流里有什么成分/但我可以用我的眼采集天边的流云/放在心里细品那份最抽象的唯美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也不是动物学家/我不清楚鸟到底靠什么飞翔/我只知道阳光下那对神奇的羽翼/常常让我感应到蓝天白云之间有天使飞过的痕迹
你不能说辛波斯卡古灵精怪,但她笔下的字句的确具有灵动的因子,她让想象力在现实的世界中横行,让尖锐的话题被打磨出圆润的边角,让朴素的事物依旧朴素,卻又非凡。
当我说出”未来”一词/第一个音节便已成为过去
当我说出“寂静”一词/我就立刻打破了这种寂静
当我说出“乌有”一词/我就在创造一种无中生有
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找到了标明“辛波斯卡出生地”的一幢房子,如今这里已挪作他用,但看到上方升起的袅袅炊烟,我还是忍不住推了推门。门当然没开,但我听到了诗人在尘世间嘹亮的哭声,她说:
“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最好简短”,她说“我亏欠那些/我不爱的人甚多/另外有人更爱他们/让我宽心”,她说“长寿是岩石和树木的特权”。
我觉得她用精巧的譬喻幻化出了神奇,用诗歌打败了时间。
除了长椅旁的一尊塑像,镇子里没有更多关于她的纪念碑,然而一切又是这样的亲切、随和。辛波斯卡的塑像目光灵动,正眼含爱意地望着自己的小猫;小猫恃宠而骄,顽皮地压住了描写自己的诗稿。诗人的雕像没那么潇洒,也没那么高大,却丝毫没有减损诗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谁说诗人不能住在隔壁?诗意和智慧应该一直与我们比邻而居。
我坐在长椅上出了会儿神,专注地想念一个名字让我觉得幸福,只可惜这里往来行人太少,没人能为我和雕塑拍张合影。于是我索性决定多坐一会儿,陪辛波斯卡吃顿午餐。天气好得不像话,润泽的空气如约而来,阳光为远处的芦苇勾勒出迷人的金边,林间传来一阵阵密集的鸟鸣,叽叽喳喳。春天真的来了,万物生光辉。

与读小说不同,读诗未必非要一气呵成,闲时、闷时随意捡几篇来读,如同空口含橄榄,咸津津而有回甘。不知道辛波斯卡是如何创作的,但读她的诗总能让我收获巨大的平静,尽管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会被“稀释”,但她关于人类共同的疑问和相似的情绪,却总能冲破层层叠叠的阻碍,直抵我心。我掰了一块波兰黑面包,又夹了几片辛波斯卡的诗,津津有味地咀嚼,深感诗歌如盐如醴酪,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滋养。
在科尔尼卡,当地人同样热爱辛波斯卡。为了庆祝她的100岁诞辰,人们收集了小镇及周边地区居民的100张面孔的照片。拍摄者邀请大家在拍照时审视自己的内心。现在,不同性别、年龄、面容的人物照片被张贴在长椅的周围,仿佛辛波斯卡从未离开,诗意也未曾走远。就连这个活动的创意本身也源于辛波斯卡的一首诗:
在繁忙的街道上萦绕着我的思绪/面孔/世界表面有数十亿张面孔/显然/每一个都与过去和将来的不同
三
一个人和她的故乡有什么关系?
那是她人生的起点和记忆的归途。
文学的故乡和个人的故乡必定重合吗?
未必,在创作者笔下,我们指认出了更多的文学的来处。
现在再想起辛波斯卡的故乡,我总会想起险些错过车的那个下午,想起好心的波兰大叔,想起湖边长长的甬道,想起甬道旁的那条长椅,想起辛波斯卡轻松地笑着。
那笑无比深邃,通向蓝色的记忆的大海。

一个奇怪的星球,上面住着奇怪的人。
他们受制于时间,却不愿意承认。
他们自有表达抗议的独特方式。
他们制作小图画,譬如像这张:
初看,无特别之处。
你看到河水。
以及河的一岸。
还有一条奋力逆流而上的小船。
还有河上的桥,以及桥上的人们。
这些人似乎正在逐渐加快脚步
因为雨水开始从一朵乌云
倾注而下。
此外,什么事也没发生。
云不曾改变颜色或形状。
雨未见增强或停歇。
小船静止不动地前行。
桥上的人们此刻依旧奔跑
于刚才奔跑的地方。
—节选自辛波斯卡《桥上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