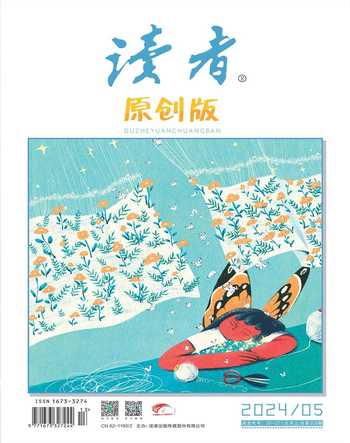印尼四日
韩晗

一
我关于东南亚雨季的记忆,来自2015年的胡志明市与2019年的曼谷。我这次到印尼,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寻访东印度公司的旧址。
近世以还,欧洲人创立的东印度公司有7家,均在亚洲横行霸道、恶名昭彰。其中有三家最为著名,当中就包括位于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初,荷兰人驾驶6艘帆船从巽他格拉巴港登陆,赶走了盘踞于此的葡萄牙人与英国人,建立了印尼第一个现代化城区—巴塔威亚,也就是现在的雅加达。
东印度公司雅加达总部旧址就在巴塔威亚老城的法塔西拉广场上,今天法塔西拉广场与摩伦利维特运河周边的荷式老建筑依然是雅加达的一道盛景,成片的老式坡顶建筑、残留的铁轨、庞大的海港,以及依然矗立的中央车站,明示着这里曾是印尼工业化的开端。昔日的殖民者总部如今成了雅加达历史博物馆,依然透露出当年盘踞于雅加达的东印度公司的阔气,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雅加达乃至印尼的现代化借此地发迹。一言以蔽之:印尼现代化源于雅加达,雅加达的现代化则源于巴塔威亚,而巴塔威亚的现代化从巽他格拉巴港开始。
巽他格拉巴,由“巽他”和“格拉巴”两词拼成,意为“椰子”与“风”,曾有人将其翻译为“椰风港”倒也说得过去。曾经繁盛无比的巽他格拉巴港近年来日渐衰颓,一字排开的工人村比印度斋普尔的工人棚户区有过之而无不及,路边的流浪汉不可计数。叫不出名字的老街尽头,是雅加达的金字招牌海鲜餐厅“玛莲娜”,餐厅由昔日的海水处理厂的老建筑改造而成,算是工业遗产再利用。从远处看,这座建筑庞大、显眼,但想要抵达却需费一番工夫,穿越乞丐云集的棚户区后,还要经过两道岗的盘查才能靠近这栋大楼。
在雅加达,进入所有的大型商场前都要接受安检,所有的酒店都会用探测器把接送客人的出租车排查一番。
在印尼四日,我學会的第一句印尼语是马路警示牌上随时出现的“HATI-HATI”,中文并不流利的华侨老江告诉我,这是“小心”的意思。再问他“要小心什么”,他说,这里人多车多,该小心的都要小心。
二
雅加达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除了生活方式多为舶来品,这里更具特色的就是苏加诺的革命史。
印尼国家美术馆里的油画,但凡苏加诺时代的,我们看着都不陌生。青纱帐里的民兵、车间里的劳动模范、水田里插秧的妇女……这是属于那段岁月的集体印记。
占地庞大的莫迪卡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巨型的民族独立纪念碑,纪念碑的基座是陈列着苏加诺辉煌灿烂革命事迹的展览馆。进入展览馆,电梯里的《游击队员之歌》旋律激昂。升至纪念碑最高处的平台,俯瞰整个雅加达市区,棚户区鳞次栉比,高楼屈指可数……首都如此,其他地区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疆域横跨亚洲与大洋洲的海洋国家,印尼迫切地想走向世界。面对外宾,印尼人热情如火。街头遇见小学生春游,他们的老师竟然拉住我们,现场给学生们开展外语教育。万万没想到,即使远达雅加达,我依然有机会做老师。
三
来了雅加达,当然要去旁边的万隆。
大雨倾盆如注,但遮挡不住万隆与生俱来的文艺气息。事实上,来雅加达的许多中国游客不一定会来万隆。对中国人来说,万隆更多的是与历史课本联系在一起—1955年的万隆会议,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旧址现被改建为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大厅中的第二排右数第二个座位,就是周总理当年所坐的位置。如果有中国游客来访,管理员会邀请游客坐在这把椅子上留影。
巴拉呷街头的咖啡馆和酒店数不胜数,时常能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里仿佛比雅加达更加国际化,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去郊区看火山的。
我们从雅加达去往万隆的路上晴空万里,高速公路休息区里坐满了歇脚的年轻人;回程时却持续暴雨,狂风骤雨中,高速公路上的车纷纷亮起双闪。老江说,印尼的雨季就是这样。我问他雅加达会不会发生城市内涝,他说肯定会。

记得最近一次见识到东南亚城市内涝还是在柬埔寨的金边,已是8年前的事了。但雅加达人认为,金边和雅加达没有可比性。在他们眼里,“雅加达是东南亚的中心”。
四
有文章讲,到了印尼一定要去泗水街,那是古董一条街。这让我来了兴趣,因为东南亚的古董店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据说在那里可以看到一部人类早期全球化的历史。
但当我们抵达泗水街后,却大失所望—街道长度不过500米,沿街的店铺里,一半是售卖劣质行李箱的店铺,另一半才是所谓的古董店,几十家店铺竟然没一件像样的东西。这里所谓的古董多是报废的农具或私家旧货;至于所谓荷兰或中国的文物,基本都是假货。
老江开车带我们跑了大半个雅加达,一再建议我不要去泗水街,他说:“这些东西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是假货,他们都是骗欧美人的。你们来了雅加达,可以去吃鼎泰丰,味道比其他地方的都要好。”
雅加达的鼎泰丰餐厅并不大,位于雅加达海滨新区“PIK”,这里是华侨聚集区,只用了三年便建起一座规模巨大的中国城,令人叹为观止。街前站着持刀镇守的关老爷,街后供着观音像,街中间端坐着笑盈盈的弥勒佛。贡茶、麻辣烫、小龙坎竞相揽客,即使与号称“美食王国”的悉尼唐人街相比也不遑多让。街上的华人反而不多,更多的是本地人,随处可见戴着头巾的印尼姑娘。
老江告诉我,他的朋友经常从中国往印尼代购纸尿裤。我问为何,答曰:“本土品牌不如中国的好。”
五
与其他地方不同,雅加达唐人街分新老,新唐人街如是,老唐人街当然更值得一看。
老唐人街位于巴塔威亚老城旁,中文名叫草埔,英文名叫Glodok。街口有家汲泉茶舍,创立者林宜蓉是生于雅加达的“90后”女孩,店里雇了不少本地人做服务员。
此茶舍的房屋原来是间中药铺,乃是荷兰堡垒式建筑,有300余年的历史,至于更早是用作何事未可知也。荷兰殖民时代与苏加诺时代,印尼建造了比肩曼谷耀华力路、新加坡牛车水和吉隆坡茨厂街的华人旅居区。但时移世易,如今这里许多华侨都是通过短视频学习汉语,比如老江。
汲泉茶舍不远处的诺富特酒店内的新明会旧址,曾是老唐人街上的一处四合院,如今成为酒店中庭的一部分。新旧相生,极有个性,我没查到设计师是谁,但这绝对是一个天才的创意。这里原来的主人是印尼侨领许金安,他因抗日牺牲,但他的经历今日几乎无人知晓;新明会也曾为维护印尼华人的权利做了许多工作,如今这座建筑也几乎无人光顾,冷冷清清。
要找老唐人街的遗风,唯有去旁边的偏僻巷子里去寻。头条侧巷里的“饶咖啡”是百年前潮州饶姓华侨创办的,据说是饶宗颐先生的族人。主干道旁一处不起眼的信谊药店已近百年。老板说生意并不好,因为这些年当地的华人都走向了世界各地。像林宜蓉这样愿意回来的是极少数。
百叶窗、吊扇、竹藤椅、椰子树,以及广府风格的建筑和异常湿闷的雨季,在这短暂的四日旅程中反复出现,勾勒出一个新旧交织,又令我异常熟悉的场景。这里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华文化曾经落地生根的地方。我相信,即使这条老唐人街衰败了,但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依然能够在世界各地生根。
东南亚华人和他们血脉中的中华文化从来就不孤独,它从近代出发,一直延伸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