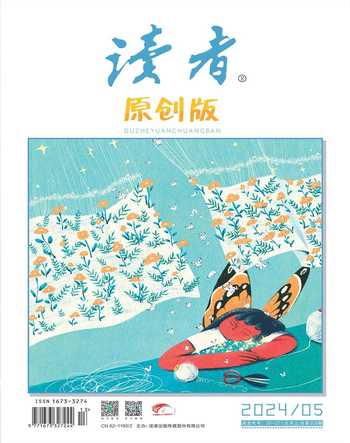大道俱是同行人
毕业几年后,我回到大学校园。
大约是近乡情怯,走在校园熟悉的甬路上,居然还有些不自然,希望遇见中文系的某个老师,又怕真看到了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正嘀咕呢,从身边走过一个人,突然回头叫我:“马德?”
我转过身,脱口一声:“老师!”
几乎是第一时间,我就认出了对方。她是我上学时负责邮件收发的女老师。我上大学时发表的文章的样刊、样报以及稿费单,都是经这位老师的手转交给我的。其时,我常到她的办公室。邮局送来的报刊她总已整理好,见我来,就用手一指,说:“马德,那一摞是你的。”我便满心欢喜地拿走。上了几年学,到过她那儿无数次,却不知道老师叫什么。好在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我来,我取,我走,像一个必然发生的化学过程。
“果然是你。”
我听得出来老师此刻的欣喜。她说:“你毕业之后,陆续又来过一些汇款单,我替你取出来了,一直没法联系上你。这下好了,你跟我去拿一下。”
我以为还是去她原先的那间办公室。老师说,她已经不管收发了。我跟着她去了她家—操场南面的一间平房,屋子不大,收拾得很利索。她从橱柜里扯出一本书,又从书页中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来。信封里装着一个纸包,纸包里包着一小叠钱,10元、20元的居多,合起来有100多元。
老师数了数,报给我一个数。然后说:“马德,你点一点,看对不对。”我赶紧说:“不用数,一定是对的。”“对了,包钱的纸上,我都给你记下来了是哪个报刊的哪篇文章的稿酬。”老师又叮嘱我一句。其实,在她打开那个纸包时,我已经看到了老师的那些记录。
我说:“谢谢老师。”她说:“不必谢,这个钱夹在这本书里有几年了,我真怕再找不到你呢。这下好了,算了了我的心愿。”那一刻,老师的眉宇间,透露着释然的轻松感。
时间线由此回溯。大学毕业后,我在张家口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待了大约一年,后来就调到了平原小城。由于待得时间短,乡镇中学的好多老师还不熟悉,有一位老师很让人难忘。
那是一位身形微胖的老师,姓崔,50多岁。由于眼镜经常从鼻梁上滑下来,他右手的食指时不时会沿着鼻子向上推。他知我是个毛头小伙儿,又不是本地人,常教我一些在这里为人处世的方法。崔老师也不多说,只是偶尔点拨几句,是一个能交心的长者。他曾经几次邀我去家里吃饭,说:“蒸山药鱼儿,来吃吧。”他是真心,然而我总觉得唐突,便都婉拒了。
后来,我在平原小城收到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才又和崔老师关联起来。信是崔老师寄来的。大意是说,我走之后,学校补发了一年的高寒补助,他替我领了,然后根据我走时偶尔谈及的调往单位名称的发音,在地址簿上猜测着找到一个可能对的地方,然后寄出信和款。他在信中说,这种方法不保险,但是比寄丢这笔钱更有意义的是,他寄出了,否则钱放在他那里,心中总是不安。
时间线由此再拉回一点儿,回到我大学刚毕业的那一年秋天。我在某民营企业干过一段时间,说是老板的文秘,其实就是打杂的,干些日常采购、擦桌子扫地,以及不停替人值夜班的活儿。老板出差去国外,我也离开了那家企业。走的时候,留下了封辞职信,辞职理由寥寥,但细细地交代了一笔账。大致是,我从财务支取过300元钱,拿这笔钱购买办公日杂,花去了多少,还剩余多少;花去的每一笔分别是多少,按条目列出来,并把相关发票对应着贴在后面。当然了,剩余的钱,我也一分不少地装进了那个信封里。
之所以写出这些,只是觉得,生而有幸,在人生路上能遇到这些与我做出同样选择的“同行人”。我不知道,是“同行人”更容易有交集,还是如此这般活着的人,更敏感于记住别人的好。总之,我念念不忘这两位老师。他们给予我的,不是那些钱,而是坚定了我对某些人生意义的认同。
人生每有迷茫,我会在心底说:去做吧,與你同行的人,世上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