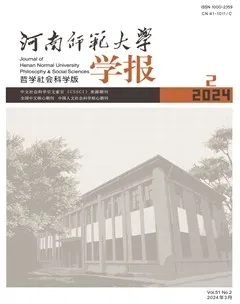传统的赓续:论晚清小说批评中的“味”
晋海学 王晨曦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4.02.19
摘要:“味”是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之一,晚清批评家将其用于对新小说的宣传和阐发之中,充实和丰富了它的内涵。晚清小说批评家对“味”范畴的使用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以“味”品评小说文本,主要集中于故事虚构、情节运思和语言使用等层面;其二,把“味”当作小说的“原质”之一,或者将其看作是区别小说与其他文体的标识,或者将其提升为衡量国外小说翻译水准的标尺。晚清小说批评家对“味”范畴的理解和使用没有脱离古代文论传统,但也能因时而变,表现出兼有汲古与开新的双重特征。
关键词:味;范畴;晚清;小说批评;传统
作者简介:晋海学(1973-),男,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审,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王晨曦(2001-),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项课题重点项目(2023WHZX23)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24)02013707收稿日期:20230717
“味”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的文献中,主要指食物之味,譬如,史伯所说的“味一无果”,孔子所言的“三月不知肉味”等,采用的便是这一语义。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者开始将“味”引入文艺批评领域,以指称文艺作品某种特殊的审美属性,如刘勰《文心雕龙》云:“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钟嵘《诗品》云:“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隋唐之后,“味”便被广泛用于诗歌的品评之中,进而衍生出“趣味”“余味”“意味”“遗味”“异味”“真味”“风味”等诸种内涵。相比之下,“味”在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使用既不广泛,也不成熟,即使偶有用之,也基本上没有多少新意。
上述情况在晚清之后得到了改变。凭借对小说乃“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的认知,批评家不仅将这种能达致“振民智”效果的文学体裁放在了“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而且对它的远景构想进行了颇为积极的倡言和建议。正是在这一时势和人势的裹挟之下,小说批评家开始有意识地将这一常用于诗文领域中的术语频繁地使用于小说批评领域。客观地说,晚清小说批评家的这一做法是对传统文论术语的一次借用,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味”范畴则往往能将小说的文体特点凸显出来,并展示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批评效果。可以说,晚清小说批评界对“味”范畴借用,不仅在促使人们对小说文体意识的觉醒方面起到了促发作用,而且对小说文体身份在近代的转变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一
“味”范畴的内涵比较丰富,人们经常将它用在对诗文的具体品评之中。当晚清小说批评家将其用于小说领域之后,它便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以及语言取得了紧密关联,展现出了与此前不一样的新内涵。
其一,指附会的故事内容。“读《东周列国志》,觉索然无味者,正以全书随事随时,摘录排比,绝无匠心经营于其间,遂不足刺激读者精神,鼓舞读者兴趣。”历史记载以材料的真实性为撰写原则,虽胜在事迹之真,然失在趣味全无。吴趼人对此曾说:“童蒙受学,仅授大略,采其粗范,遗其趣味。”他将趣味性的不足看作是历史书籍无法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东周列国志》的作者蔡元放主动放弃对故事内容的虚构性追求,而用“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的“正史”笔法进行创作,这样的创作思想虽不失其历史合法性,但是在趣味性的营造方面却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批评家正是从此一视角出发表达了对它的批评。在“趣味”之外,还有“意味”之说。如果说“趣味”多是就故事的虚构程度而言,那么,“意味”則多指虚构与事实的统一。“动以附会为能,转使历史真相,隐而不彰。而一般无稽之言,徒乱人耳目。……等而上之者,如《东西汉》《东西晋》等书,似较以上云云者略善矣。顾又失于简略,殊乏意味。”吴趼人在这里道出了历史小说在创作上的两难之境:作者对故事虚构的过分偏爱,有可能会降低故事的真实程度,而一旦表现出对历史事实的刻意推崇,则又可能会限制故事内容的附会程度。吴趼人在此主张“意味”,强调故事附会之“奇”与历史事实之“真”的彼此交融,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趣味”的超越。
其二,指巧妙的情节布置。“将昨夜情事,再补叙一笔,余味曲包。”《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叙述者和袭人都讲述了这段故事,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采用全知视角,叙述得客观、详细;后者使用的是人物视角,叙述得主观、简略。前者主要使用间接引语,其叙述声音均匀而流畅;后者全部使用直接引语,其叙述声音直接而生动。在既有叙述的映衬下,袭人面对平儿的重新叙述,不仅会让读者生发出对“昨夜情事”身临其境般的在场感,而且会有益于袭人性格特征的凸显。除此之外,“余味”也有含蓄之意。“社会小说,愈含蓄而愈有味。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魁魅罔两,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尝落一字褒贬也。” 浴血生:《小说闲评录》,《新小说》,1905年第5期。批评家认为《儒林外史》的“用笔之妙”在于没有对所述的故事加以褒贬,却又能收到“莫遁其形”的叙述效果,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作者将含蓄成功地蕴藏到叙事之中。相反,缺乏含蓄之笔的叙事则有可能会令人感到“毫无余味”。“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实事,未必尽肖其言。即先后绝不矛盾,已觉叠床架屋,毫无余味。” “搀入作者论断”即是小说中的叙述干预,它经常表现为叙述者对故事中人物品格、或者人物所办事件对错的评论。较多地使用叙述干预会有益于主旨的凸显,但同时会减弱叙述的含蓄性。蛮反对在小说中“搀入作者论断”,是对“议论多而事实少”之类直白性叙述的反拨,和浴血生所论“社会小说,愈含蓄愈有味”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三,指优美的遣词造句。“大抵小说一道,言之无文,则事迹虽奇,一览之后,无复余蕴矣。文笔佳胜者,则自能耐人寻味,百读不厌。”新广评吴趼人的小说《胡宝玉》,先言其“文笔亦极雄健简炼,一字不苟”,然后赞其“耐人寻味,百读不厌”,在逻辑上与刘勰论文“左提右挈,精味兼载”有很多相似之处。新广对小说的语言格外重视,他认为没有文采的语言就没有韵味,只有“文笔佳胜”的小说才值得翻阅,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文论中经由优美语言而“寻味”的说法在晚清小说批评领域的再现。觚庵更认为语言具有“领味”功能,“缓读者,就其一章一节一句一字,低徊吟讽,细心领味,使作者当日精神之精神脉络贯注经营,无不若烛照数计,心领神会,即此一章、一节、一句、一字,亦且击节叹赏曰:‘此妙笔也”。与新广在小说《胡宝玉》中“寻味”不同,觚庵是反其道而用之,他先假设小说“有味”,并潜含于文本的词句之中,然后要求读者细读每一个词汇,以及每一个句子。由于“有味”被设置成了逻辑前提,所以,读者要做的主要工作不是去“寻味”,而是去领悟和体会“一句、一字”之中的意蕴,即“领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谈及了“小说家言”这一问题,与上述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在比较的论域中谈论语言,以显示它之于“味”的重要性,或者对这种重要性的推崇。譬如,寅半生批评《地心旅行》“皆科学家言,以小说之眼观之,实不得其趣味云”。周树人辩言《月界旅行》“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吴趼人附记《电术奇谈》“书中间有议论谐谑等,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衍义者拟借此以助阅者之兴味,勿讥为蛇足也” 。在这里,凭借“不得其趣味”“措辞无味”“以助阅者之兴味”等句,批评家们将“趣味”“无味”“兴味”等批评术语与小说语言实现了紧密关联,而正是凭借这种关联持续不断地加强,小说的文体特色才得到了比较明显地凸显。
总而言之,通过对小说文本中故事、情节和语言的品评,晚清小说批评家们表达了他们对于“味”范畴新的理解和阐发,人们正可从“趣味”“意味”“余味”“寻味”“领味”等批评术语中去领会“味”范畴在晚清小说批评中的大致内涵。考虑到宋代已有“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的表述,以及上述批评术语在古代文论中已有较多运用情况的事实,我们应该清楚,晚清小说批评对于“味”范畴的阐发并没有脱离古代的文论传统,而是呈现出了对它的整体性借鉴。可喜的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语言等要素,毕竟与诗歌中的“立格命意用字”等有文体意义上的不同,因此,基于前者而来运用于小说批评领域中的“味”范畴即使“整体性借鉴”了传统文论,也自觉不自觉地彰显出了具有小说文体的一些色彩。
二
晚清的小说批评家认为“味”是小说的“原质”属性,当对具体文本进行评价时,他们常常会将其当作一种有效的文体标识,将小说和其他文体区别开来,也经常会将其当作一种标准的尺度,用于衡量国外小说的翻译水平。
一、作为小说“原质”属性的“味”。陈景韩在论及小说与“味”之间的关系时认为:“有益无味,开通风气之心,固可敬矣,而与小说本义未全也。”所谓“本义”,就是事物所固有的要素或属性,作为小说“原质”之一的“味”,在这里被定义为“小说”的本质要素。以此而论,一篇乏“味”的文本很难被看成合格的小说。梁启超在论及他的《新中国未来记》时,也将“趣味”的有无看成是小说文体能否成立的大问题。“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作为新小说最早的创作实践,《新中国未来记》当属小说无疑。然而,出于凸显“新民”主旨的考慮,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夹杂了较多的“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内容,以至于冲淡了它的趣味性。以此考察这篇文本,作者的担心恐怕已不仅仅是“无以餍读者之望”的问题,而是它还是不是一篇小说的问题了,“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箸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味”之于小说的本质属性在品评国外小说时也依然适用。“吾友徐子敬吾,尝遍读近时新著新译各小说,每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知新主人以“味”来评判中国小说与国外小说之间的不同:中国小说的“味”浅,“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国外小说的“味”厚,“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两者之间的“味”虽有“浅”“厚”之分,但它们各有各的“味”,知新主人在这里以不同之“味”提醒读者,正是从本质的意义上对中外小说做了一次简明扼要的区分。
二、作为区别其他文体标识的“味”。吴趼人认为“趣味”的有无是小说与历史书籍区别的主要标识,“深奥难解之文,不如粗浅趣味之易入也。学童听讲,听经书不如听《左传》之易入也,听《左传》又不如听鼓词之易入也。无他,趣味为之也。是故中外前史,浩如烟海,号称学子者,未必都能记忆之,独至于三国史,则几于尽识字之人皆能言其大略,则《三国衍义》之功,不可泯也”。《三国演义》之所以受人喜欢,是因为它有趣味性,而人们之所以喜欢《三国演义》,则是因为他们偏爱趣味性,“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可以看到,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读者,他们都是将趣味性当作小说的主要标识来看待的。蛮也将“味”的有无看成是历史小说与历史典籍的主要区别,他说:“历史不成历史,小说不成小说。谓将供观者之记忆乎?则不如直览史文之简要也。谓将使观者易解乎?则头绪纷繁,事虽显而意仍晦也。或曰:‘彼所谓演义者耳,毋苛求也。曰:‘演义者,恐其义之晦塞无味,而为之点缀,为之斡旋也。兹则演词而已,演式而已,何演义之足云!”蛮用“晦塞无味”称谓历史典籍,却把“有味”当作历史小说的首要价值。从这层意义上看,他之所以批评那些“演词”“演式”之类的历史小说,是因为它们没有对“有味”给予应有的尊重。所以,他认为历史小说的作者要将“有味”放在创作目标的首要位置,只有在叙述事件的时候,有意识地“为之点缀,为之斡旋”,才有可能做一名合格的“演义者”。
三、作为衡量国外小说翻译水平尺度的“味”。“未到上海者而与之读《海上花》,未到北京者而与之读《品花宝鉴》,虽有趣味,其亦仅矣。故往往有甲国最著名之小说,译入乙国,殊不能觉其妙。如英国的士黎里、法国嚣俄、俄国托尔斯泰,其最精心结撰之作,自中国人视之,皆隔靴搔痒者也。日本之《雪中梅》《花间莺》,当初出时,号称名作,噪动全国,及今已无过问,盖当时议院政治初行,此等书即以匡其弊者也。今中国亦有译之者,则如嚼蜡焉尔。”《雪中梅》《花间莺》是日本近代的小说名著,但是蜕庵却认为国人对它们的翻译工作做得不好。蜕庵从“味”的视角考察不同地理空间的小说创作,以及它们在语际之间的传播交流,认为译者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捕捉到原著小说的“意味”所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或者“不能觉其妙”,或者“隔靴搔痒”,最终都导致了“如嚼蜡焉尔”的阅读效果。蜕庵在这里使用“味”范畴,而不是其他术语来讨论小说的跨语际交流问题,虽不乏笼统、简约,却鲜明地呈现出了“味”之于国外小说翻译水平的衡量作用。寅半生也将“味”范畴引入对国外小说翻译的品评之中,“第一章论理审之学,趣味隽永,不愧侦探唯一,惜乎全书人名多至五六字,易启阅者之厌,苟易以中国体例,当更增趣味不少”。《四名案》里面的人物众多,他们的名字均有独特的书写格式,译者在翻译时显然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寅半生从增加小说趣味性的考虑出发,提出“易以中国体例”的合理建议,当为的论。邱炜萲在品评小说《茶花女遗事》时也提到了“味”的问题,“然余曩曾得见《时务报》译《滑震笔记》《长生术》,皆冗沓无味;而《求是报》《菊花》小说有味矣,惜报中辍,小说亦未完”。一种译文“无味”,一种译文“有味”,批评家用“味”范畴作为衡量翻译水平的标准,直接表达了对两种译文截然不同的态度。
综上所述,晚清的小说批评家将“味”看作是小说的“原质”之一。他们的这一看法不仅使“味”成了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显著标识,而且使“味”成了鉴定国外小说翻译水平的一种尺度。尽管将“味”作为一种品评标准的做法在古代文论中已不少见,但是在它们中间,我们很难找到那些将“味”看作是某种文体本质属性的举例或者表述。从这一点看,晚清的小说批评家们对“味”范畴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考虑到小说改良在其草创时期受挫的现实,这或许是批评家们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在“味”范畴身上所寄寓的另一种厚望吧。
三
晚清小说批评中的“味”范畴既是对传统文论的承继,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它的内涵之中兼有慕古与趋新两重成分。
首先,“味”范畴表现出了“向传统文学的理想范式趋同”的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味”范畴自宋代以后已经积累出比较丰富的内涵,其理想范式大致有二:一种指诗文的含蓄之美,如梅尧臣诗,欧阳修谓之“古硬”且“咀嚼苦难嘬”,终说“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又如《贾谊传赞》,吴子良评之曰:“语简而意含蓄,咀嚼尽有味也”。一种指诗文的意外之旨,如司马光论诗云:“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楼昉评《名二字说》云:“字数不多而宛转折旋,有无限意思。”
与此相反,明清小说批评家则看重小说明白晓畅的叙述特征,袁宏道在论及通俗小说时指出:“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既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无名氏《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亦说:“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许宝善《北史演义序》也说:“独《三国演义》,虽农工商贾妇人女子无不争相传诵。夫岂演义之转出正史上哉?其所论说易晓耳!” “明白晓畅”“明白易晓”,以及“易晓”等相似术语的频繁使用,足见明清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明白晓畅叙述特征的赞同与认可。然而,这一情况在晚清发生了转变。如曼殊论《儿女英雄传》,以为其前半部分最佳,“其书中主人翁之名,至第八回乃出,已难极矣。然所出者犹是其假名也,其真名直至第二十回始发现焉。若此数回中,所叙之事,不及主人之身份焉,则无论矣。或偶及之,然不过如昙花一现,转瞬复藏而不露焉,则无论矣”。二我评《黄绣球》说:“凭空结撰者。则须曲折而赴,取势于前,不可入手发泄尽净。且即叙已有之事迹,入手便说尽者,亦无意味,非必上乘之法也。”可以看到,批评家对小说叙事“转瞬复藏而不露”“不可入手发泄尽净”的强调,与明清小说批评家看重小说明白晓畅的叙述特征已有不同,反而呈现出向含蓄之美这一传统文学主流的回归倾向。此外,晚清小说批评追求“意外之旨”的倾向也非常明显。漱石生认为:“小说之作,不难于详叙事实,难于感发人心;不难于感发人心,难于使感发之人读其书不啻身历其境,亲见夫抑郁不平之事,流离无告之人,而为之掩卷长思,废书浩叹者也。”东海觉我认为:中国小说“事迹繁,格局变,人物则忠奸贤愚并列,事迹则巧绌奇正杂陈,其首尾联络,映带起伏,非有大手笔、大结构,雄于文者,不能为此。盖深明乎具象理想之道,能使人一读再读,即十读百读亦不厌也。” 所谓“掩卷长思,废书浩叹”,所谓“一读再读即十读百读亦不厌”,均是对小说“意外之旨”的另一种言说。如果说明清批评家偏爱于小说的通俗性,那么晚清批评家则钟情于小说的曲折性,尤其在如何达致小说曲折性的思考上面,他们似乎更愿意向传统借鉴经验,从而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理想范式的追慕和靠拢。
其次,“味”范畴表现出了向“新民”主旨开放的态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以其具有吸引读者的魅力而受到晚清批评家的注意,他们一方面以“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唯此小说”的认知,将小说推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另一方面则以“诱掖国民”为创作目标,对小说的内容进行改良。但遗憾的是,新小说的创作实践尽管在内容上取得了进步,可在叙事上却有远离小说文体特征的趋势,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近时之小说,思想可谓有进步矣,然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文人学士鄙之夷之。”而接下来的问题或许更加严重,“如果读者都不去阅读这些小说,那么,即使这些小说全部都是‘觉世之文,它们对于民众又有什么影响和效用呢?”这是事关“小说界革命”能否成功的大問题,也是事关“新民”策略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因此,有批评家提出“有益”与“有味”的统一论,“必有味与益二者兼俱之小说,而后始得谓之开通风气之小说,而后始得谓之与社会有关系之小说”;有批评家提出“理想”与“意味”的结合说,“一则此种小说,要有高尚理想。二则此种小说,要有文学意味”;等等。基于对上述种种与纠正新小说创作偏至有关的考虑,一些批评家们在谈论“味”范畴时便不再将其内涵局限于小说的形式方面,而是有意识地将“新民”的主旨内容融入其中。如曼殊从思想的角度重评明清小说,“《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此论小说者所评为淫书之祖宗者也。余昔读之,尽数卷尤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曼殊对《金瓶梅》评价的前后转变,即当从一般的视角阅读这部书时,他会感到“毫无趣味”;可是换一种阅读视角,把这部书当作社会小说来读时,他又会感到其名“必无虚也”。阅读体验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以第二种视角阅读时,作为读者的曼殊能与“无穷冤抑,无限深痛”的时代内容发生精神上的碰撞和共鸣,而正是凭借这一融入了现实关怀和社会批评的阅读,他收获到了一种“有味”的阅读体验。曼殊在这里通过比较前后不同的阅读感受而让“味”范畴与社会关怀取得关联,这无疑为其理论边界的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梁启超用“时代精神”论“有味”,“中国文学,大率最富于厌世思想,《桃花扇》亦其一也。而所言犹亲切有味,切实动人,盖时代精神使然耳”。定一用“嘲世主义”论“趣味”,“若出自著撰者,则以《自由结婚》及《女娲石》二书,吾尤好之。前者以嘲世为主义,固多趣味” 。寅半生更从“理”字入手论“趣味”,“虽各国风尚容有不同,且此事原属一时游戏,然游戏亦须近理,方有趣味可寻,若此书所述,未免太觉离奇矣”。可以看到,“社会之书”“厌世思想”“嘲世主义”,以及“游戏亦须近理”等词句的使用,与曼殊对“味”范畴的体会形成了明显的呼应之势,它们都展示出了这一范畴的重新理解,这无疑是“味”范畴此前所不曾有过的内容。
整体而言,声势如虹的小说界革命在其初期遭遇挫折,既有的审美“趣味”已受到批判,而主旨高义的新小说又不受读者喜欢。为此,批评家们不得不同时兼顾各种因素,以求小说改良的顺利进行。他们一方面向传统文论靠拢,以期在“味”范畴的传统内涵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则又根据时代特征开放其理论边界,从而让“味”范畴在晚清小说的批评场域中展示出了既汲取传统,又与时俱进,既拥有传统的影响因子,又不拒绝吸纳新知的美学特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
自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后,传统“说部”便开启了它向现代“小说”的转型之路,而随着虚构自由的凸显、叙述视角的调整,以及叙述者语言与人物语言之间的区别等现代叙述要素的开始出现,小说批评也不得不提出它自己在接下来应该如何因应的问题。晚清小说批评家们对于“味”范畴的重新使用即是为回应这一问题而进行的主动尝试。小说批评家们一方面尊重“味”范畴的传统之义,使小说批评的审美品格不脱离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审美精神,另一方面则大胆地开放“味”范畴的内涵边界,使小说批评的文体色彩得到了格外凸显。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批评实践,已被赋予“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 称号的新小说才开始显得名副其实,它不仅借此有效地肩负起了“移易社会之灵魂”,以及“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的“新民”任务,而且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繁衍出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实业小说、写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多种“创例” 小说,呈现出“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这无疑与小说批评家们借用“味”范畴的批评实践有莫大关系。
对于“味”范畴在晚清小说批评领域的出现,我们还应该看到,晚清小说批评家们的选择是在西学侵入的时势之下完成的。他们一方面创造性地采用古代文论中的范畴术语,另一方面则充满自信地沿用将诗文批评移植于小说批评之中的传统做法,极大地表现出了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考察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状况,中国传统批评样式被放弃、被遗忘,以及被忽略的现象已经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已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提出了“我们应如何在面对‘西方的同时返回民族文化精神性泉源”的思考。可以看到,这一思考是在为纠正和改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现状的立场上提出来的,所以,对“民族文化精神性泉源”的“返回”并非一句虛空的话语,它应该包含了如何回到历史现场,以及如何与那些为坚守文化主体而不得不进行顽强抵抗的历史紧张感发生共鸣的思想之力。在这些思考者看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返回”之路并不容易,因为它不仅需要批评主体具有将当下所处困境的现实感与历史中坚守主体性的紧张感进行对接、融通的能力,而且需要找到某个可为这一对接、融通行为提供契机的历史媒介才行。在此意义上,晚清小说批评家们基于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而滋生出的现实感与紧张感,正可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之“返回”所需的“对接、融通”提供有效的历史接洽点。这或许是晚清小说批评给予当代思考的又一重贡献吧。
总之,当我们对西方文艺批评进行质疑,乃至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未来发展忧虑的时候,晚清小说批评家们借以“味”范畴的批评实践,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如何彰显文化自信的成功经验,而且提供了可与其历史紧张感进行“对接、融通”的批评媒介。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应该重新给予它们关注与考量,而不是忽略或者遗忘。
[责任编校张家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