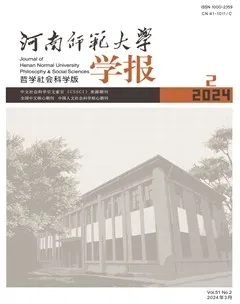汉代生育禁忌习俗中的性别与权力
孙朝阳 焦杰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4.02.15
摘要:两汉社会出现了比先秦时期更为严苛的生育禁忌,人们普遍认为产妇不洁且危险,产孕异常、忌日出生的婴儿会妨害父母。因此,承担生育重任的产妇和某些“特殊婴儿”被当作禁忌对象,产妇在分娩之前必须离开日常生活的居所,到特定地点分娩,产孕异常、忌日出生的新生儿也会被弃之不育。两汉社会流行的生育禁忌观念,不仅是对产妇不洁和“特殊婴儿”妨害父母的担忧,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性别与权力关系。汉代父权制文化深入发展,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力不断增长,夫权不断强化,针对产妇和婴儿的一系列生育禁忌实则是权力压迫和性别歧视在家庭关系中渗透的结果。
关键词:汉代社会;生育禁忌;驱逐产妇;生子不举;性别与权力
作者简介:孙朝阳(1975—),男,河南濮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性别史研究;焦杰(1964—),女,辽宁海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性别史和文化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ZSB047)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24)02010806收稿日期:20230215在汉代,由于医疗水平低下和人们对生育问题认识的局限,生育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出于恋生恶死、趋吉避凶的心理,承担生育重任的产妇和某些“特殊婴儿”在当时被当作禁忌对象对待。产妇在分娩之前必须离开居所,到特定地点分娩;产孕异常、忌日出生的新生儿也会被弃之不育。关于这些问题,不少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方面加以阐释,认为生育禁忌由生殖崇拜转化而来,是图腾崇拜遗存、巫术思想信仰、迷信及生育活动本身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分析虽然各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这些研究仅就生育而谈禁忌,并未将禁忌的产生与流行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也没有关注到生育禁忌与父权制家庭权力框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汉代生育禁忌不仅事关产妇和婴儿,更事关丈夫和父亲。因此,深入探究汉代生育禁忌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可以更好地认识汉代社会的家庭关系和性别文化。
一、驱逐产妇习俗中的性别与权力
在汉代社会,有一种观念非常普遍,即产妇是危险和不洁的。产妇生产之前,或被逐出家门,“丘墓庐道畔”,或出居乳舍,不许回娘家生产,这些习俗表面上显示的是对妇女生产极为厌憎的心理,实质上却是汉代社会性别与权力关系的体现。
(一)“丘墓庐道畔”。汉代社会,产子之家与丧事之家都被视为不祥而受到歧视。据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中原地区对丧家及产乳家都很忌讳,祭祀前“举家毋到丧家及产乳家”。《说文解字》云:“乳,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孕妇生产不但为外人所厌憎,也为自家人厌憎。外人避之唯恐不及,家有吉事,或外出远行、入山林过川泽者,都离产妇远远的,唯恐被其祸及。甚至还有将产妇送到野外,搭個棚子让其在里面待产,满月才能回来的做法。《论衡》记载:“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畔,踰月乃入,恶之甚也。”对这种歧视产妇的做法,李贞德认为主要是由于分娩血水污秽而产生的产乳不吉观念和妇女身份由妻子、媳妇到母亲的转换等李贞德的观点为一家之言,不过尚有拓展的空间。笔者认为汉代驱逐产妇,除了分娩血水导致的产妇污秽观念作祟外,还受到先秦产妇移居侧室礼俗的影响,是先秦礼仪的世俗化发展。
先秦时期,孕妇临近产期,必须移居侧室。据《礼记·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齐,则不入侧室之门。”先秦贵族宫室有燕寝和正寝之别,正寝是男主人祭祀前斋戒和生病时休息的地方,也是举行丧礼的地方;燕寝则是家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孕妇分娩前必须从燕寝迁到侧室去待产。婴儿出生之前,丈夫虽然每天都要两次过来询问情况,但皆止于门外,妻子并不与丈夫见面,而是派保姆与丈夫沟通。等到孩子出生后,丈夫仍然不能与妻子面对面,直到满月,丈夫都不能进入侧室之门。普通百姓当然没有燕寝和正寝,条件不好的家庭甚至没有正室和侧室,孕妇生产时没有多余的房间供其使用,那么则由丈夫回避。《礼记·内则》又曰:“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问之也,与子见父之礼无以异也。”总之,先秦时期,无论是贵族阶层还是普通民众,无论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临产的孕妇都必须与丈夫隔离。尽管礼法要求丈夫持续关注生育过程,但绝不能与妻子见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满月为止。若将先秦产妇与丈夫隔离的礼俗再往前推演,则可以发现,《礼记·内则》所载产妇移居侧室或者丈夫出居群室,其实就是原始时代隔离产妇习俗的礼仪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隔离产妇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这一习俗源自“母权时代的原始秘仪——生育仪式和经期禁忌”,是妇女自我神秘的手段。原始秘仪发展为隔离习俗则变成男子的自我保护措施,并在进入父权制社会后“被男性加以篡夺并利用,成为他们控制女性的仪式,男性由被逐出者变成了逐出者,女性由仪式的实施者变成了被禁锢者”。为了保证男子的安全,临产的妇女必须与丈夫隔离开来。汉代更加严苛的生育禁忌和驱逐产妇行为,就是原始时期男子的自我保护措施的再次呈现。
不过,汉代驱逐产妇现象主要发生在江南地区,中原一带则比较少见。王充《论衡》云:“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无恶也。至于犬乳,置之宅外,此复惑也。江北讳犬不讳人,江南讳人不讳犬,谣俗防恶,各不同也。”彭卫、杨振红认为驱逐产妇的习俗“并非如《论衡·四讳篇》所说的‘江北讳犬不讳人,而是广泛存在于华夏大地,所异者只是程度不同”。这一说法虽然比较客观,但也有可商榷之处。我们认为不论江南江北,产妇生产是不祥的观念普遍存在,但因地域文化不同和条件所限,各地对待产妇的做法是不同的。比如在洛阳,驱逐产妇的现象比较少见,或者说没有,因为王充在洛阳游学多年,对洛阳情况比较了解,“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的话绝不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在北方的上层社会,产妇生产并不移居于外。《史记》记载:“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莨菪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剂,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臣意往”说明菑川王美人生产时并没有移居宫外,而是将淳于意召到王宫里来为她接生。《汉书》也载:“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为世嫡皇孙。”颜师古引应劭之语:“甲观在太子宫甲地,主用乳生也。”则知上层社会的产妇并不逐出家外,因为家中有专门的房间供其生产。
不惟上层产妇生产时不逐出家门,北方普通人家的产妇也多在家产子。《淮南子·本经训》中有“刳谏者,剔孕妇”的记述,高诱在注释中指出:“孕妇,妊身将就草之妇也。”王充《论衡》也记载:“方包曰:‘《淮南子》称妇人产子为就草。北人卧炕,以草藉席,将产则去席就草也。按此,则北方乳子不出室也。”由此可以判断,汉代下层社会妇女生产也不被驱逐,就是在其平时生活的炕上生产,只不过生产前要先去掉炕上铺的席子而已。
(二)出居乳舍。汉代社会,各地文化和风俗发展并不一致,有些地方的确存在驱逐产妇的现象,尤其是下层社会。“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礼记·内则》的礼法只适用于先秦宗法制社会,两汉时代流行一夫一妻个体小家庭,男子娶妻之后往往析门别居,若非富裕之家,自然没有可供丈夫避居的群室。而秦汉以后,随着个体家庭成为主流,董仲舒顺应时代的变化,将阴阳思想与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结合到一起,夫权得以进一步强化。在夫权至尊的原则下,出于趋吉避邪的缘故,只能将产妇驱逐出去。因为在野外待产很危险,有些地方便出现了专门为产妇提供服务的乳舍,很多孕妇到了预产期便离开家,住到了乳舍里,满月方归。《风俗通义》里有两条乳舍的记载,所谓“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皆怀妊,数月,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舍,弟妇生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掾,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得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颍川、汝南在长江以北,其有乳舍的记载与《论衡》有异,但并不意味着王充“江北乳子,不出房舍”的记载有误。我们认为,颍川、汝南有乳舍应该与其地理位置有关。两地虽地处江北,但地理位置偏南,南接荆楚,正处在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之处。而江南地区极少受周礼文化的影响,原始时代驱逐产妇的习俗应该一直存在,也就是《论衡》中所说的“丘墓庐道畔”,故颍川、汝南“讳人”的做法很可能是受了江南的影响。从《风俗通义》的记载来看,颍川富室和汝南周霸都是富裕人家,家中应该不缺房子提供给产妇,她们出居乳舍说明该地“恶”产妇的风气非常浓厚。而王充是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仕之后主要在江南任职,对江南情况比较了解;虽然他曾长期在洛阳游学,但对颍川、汝南的情况并不一定十分了解,他不知道这二地有乳舍是很正常的。
关于乳舍的出现与性质及其分布情况,20世纪80年代,秦建明认为乳舍是汉代“专门接生的妇产院”,“临产孕妇与初生婴儿可以得到较专门的社会保健待遇”。21世纪初,李贞德认为“汝南、颍川均为汉代州郡,而更大一些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设有乳舍,并且住院的产妇有屠夫之妻,说明产院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近年王子今又提出了一种新设想:“乳舍也使人联想到时代条件相近的在复杂文化情境中所出现之‘义舍‘义米肉等社会公共服务设置。”这些说法是否言之成理均须讨论,但在文献匮乏的情况下,这些推测均有益于研究思路的拓展。不过,在两千年前的两汉社会,民间医生或许有不少,但以男医为主体且完全依靠自然分娩的时代,出现以孕妇生产为服务对象的医院则不可能。尽管春秋时代的越国曾经有将分娩者“令医守之”的记载,但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为发展人口所作的特殊安排。所以,乳舍专为产妇服务是没有问题的,但肯定不具有医院性质,当然也不会提供医疗看护。乳舍只是给被逐出的产妇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生产空间,让她们度过所谓的危险期。相较而言,王子今所主张的乳舍类似于“义舍”“义米肉”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乳舍是否免费亦可商榷。而从洛阳“讳狗不讳人”和《淮南子》产妇就炕去席落草而生的记载来看,北方很多地方产妇生产是不出房户的,因而乳舍在北方应该并不普遍。
(三)不宜归生。汉代社会流行的生育禁忌中有“不宜归生”(归娘家生产)一条。相较于驱逐产妇“丘墓庐道畔”,归生显然是一件于婴儿、产妇及夫家都极为有利的事情。但在汉代社会,归生也是产妇必须严格遵守的生育禁忌。据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不宜归生”的原因是“俗云:令人衰”,即产妇归生对娘家人不利。在先秦宗法制社会里,妇女自出嫁之日起便与娘家脱离了血亲关系,非有大故不能回娘家。所谓大故,指的是家有丧事,最大的丧事便是三年之丧。《礼记·杂记下》曰:“妇人非三年之丧,不踰封而吊。”若无大故,一个已婚妇女要回娘家,必须征得丈夫同意,若丈夫已逝,则需要儿子同意。故年轻丧偶的鲁母师,“腊日休作者,岁祀礼事毕”,向儿子们请假回娘家探视,与诸妇约定“夕而反”,“天阴还失早,至闾外而止,夕而入”,故“大夫美之,言于穆公,赐母尊号曰母师”。《列女传》称其“诚知礼经,谒归还反”。两汉社会,个体小家庭占主流,礼法对已婚妇女与娘家关系的限制已不像宗法制社会那样严格,出于自我保护或者关爱女儿的考虑,被驱逐的产妇们可能会回娘家生产,“归生”成为汉代社会一种禁忌,说明产妇回娘家生产的现象曾经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所谓“不宜归生”,是否因为妇女生产是血光之灾而影响娘家的安危呢?当然不是。应邵在《风俗通义》中很明确地指出“令人衰”的说法都是骗人的把戏,真正的原因是“妇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许归”。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社会里,无子为“七出”之首的礼法使得妻子时刻有地位不稳的忧虑。即便有“三不去”礼法保障,但无子或不能生育长子也意味着老年没有或缺乏足够的保障,因此产妇被逐出虽然是悲惨的事情,但却为她提供了一个稳固家庭主妇地位的机會。如果生育的是女儿,她可以在娘家人的帮助下换回一个儿子。根据《风俗通义》里颍川富室长妇偷弟妇之子,周霸妻以金换屠妇之子的记载来推测,汉代产妇归生以女易子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防微杜渐,保证子女血缘的纯正性,“归生令人衰”的话语便被建构起来。
二、生子不举习俗中的性别与权力
生子不举是两汉时代生育禁忌中的重要内容。在某些特殊日子出生的孩子,或出生时身体有异的孩子被视为不祥的征兆,因此会被弃养。从表面上看,生子不举是为父母安危着想,但实质上仍然体现了父权的利益。《风俗通义》所载生子不举的禁忌颇多,所谓“不举并生三子。俗说:生子至于三,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举之也”;“不举寤生子。俗说:儿堕地便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举寤生子,妨父母”;“不举父同月子。俗说:妨父也”;“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婴告其母勿举,且曰‘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不举生鬓须子。俗说:人十四五,乃当生鬓须,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同样的记载也见于《论衡》,“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偶)死,则信而谓之真矣”;“五月子者,长至户,将不利其父母”。
关于汉代生子不举,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李贞德的研究与分析最全面,她将生子不举的情况分为产孕异常、时日禁忌两类,认为“在产孕禁忌下,似乎没有性别之分……但若由于贫困苦役等社会因素,必须以弃子杀婴节制家庭人口时,便可能有性别选择的差异”。不过,学者的研究要么是在陈述生子不举的几种情况,要么就是从趋吉避凶的民俗心理或社会因素来分析其原因,很少有人从性别角度考察生子不举习俗如何产生及发展的,更没有考察其间权力关系的运作。其实,生子不举习俗在汉代的普遍流行,也与战国以来夫权的强化有密切关系。
杀婴习俗产生于原始社会,但彼时杀婴主要出于优生和族群生存的考虑,杀婴对象没有男女之别。进入父权社会以后,男丁受到重视,杀婴才有了性别选择。不过,在婚姻恋爱相对自由的时代,女性贞节观尚未建立,为了保证父系家族继承人血缘的纯洁,上古时代有“首子不举”的习俗 关于上古时期首子不举习俗,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为确保父系血缘的纯洁,也有人认为与原始时代的献祭习俗有关。我认同主流的观点,因为所有的杀首子缘由都指向了一个目标“宜弟”,而所谓“宜弟”实则是“宜父”,只有杀掉首子才能保证父系血缘的纯正。。《史记·夏本纪》所记载“予(辛壬)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讲的便是禹与涂山氏结婚之后不举首子的故事。当然《史记》对此的解释是为了“成水土之功”。商王虽不杀首子,但生子必占卜,卜之不吉,则弃之不养。胡新生认为卜是“贞问此子与商王之间是否有血亲关系”,其说非常精辟。生子而卜的习俗一直到周代立国,实行聘娶婚制,“聘者为妻”“奔者为妾”后才发生改变。《史记·日者列传》载有司马季主与人谈论先秦占卜习俗云:“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不过,春秋时期男女自由婚恋风气较浓,未婚野合现象较多,故周代虽然生子不卜,却有“三月庙见”之礼以防新妇珠胎暗结,扰乱父系血缘的纯洁 。
通过婚姻六礼与严格的内外之分,除非是非婚生子,春秋时代的贵族很少有弃子不养的情况了,即使偶尔有之,弃而不养的也通常为女婴。比如襄公二十六年,“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 。前者因为生下来身体异样被弃,后者仅仅因为是个女婴而被弃。战国时代虽有杀婴现象,但多发生于下层社会,被杀者主要是女婴。《韩非子》记载云:“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一直到近代,下层社会杀女婴的现象都比较普遍,杀男婴几不可见。当然,特殊情况下,比如劳役赋税过重,战乱灾荒,或家庭贫困,为减轻养育负担的考量,也有杀男婴的现象 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38—158页。。在杀首子习俗于中原绝迹的情况下,为什么又出现了生子不举的禁忌呢?是否如俗所说不利父母而杀子呢?最早记载生子不举的文献是《史记·孟尝君列传》:“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常言道:虎毒不食子。田婴为什么要以妨碍父母的名义杀死儿子田文?从整个事件的记载来看,对五月五日生子危害的担忧只是父亲田婴的意思,田文之母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只是在“举”与“不举”问题上她没有发言权,所以只好采取“窃举生之”的方式将儿子养大。
汉代文献中还有两件生子不举的记载,同样也只显示了父亲对忌日生子危害的担忧。《汉书·五行志》载:“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方与女子田无啬生子。先未生二月,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三日,人过闻啼声,母掘收养。” 因胎儿在母腹中便能啼哭,不是孕期常态,故而一生下来便被埋掉了。虽然这条资料并没有说明不举子的决定是谁做出的,但三天以后听说儿子仍然活着,田无啬就跑去把儿子挖出来收养,显然孩子被弃养是山阳方的决定,很可能并未征得田无啬的同意。《西京杂记》载:“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婴敕其母曰:勿举。其母窃举之。后为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详也。遂举之。”王凤是王政君的同母弟,在汉代曾权倾一时。因为出生在五月五日而差点被父亲弃养,幸亏他的叔父坚决反对,他才得以长大成人。在决定王凤生死的问题上,发言权掌握在王凤的父亲和叔父手里,他的母亲是缺席的。
从上述记载来看,汉代社会忌日生子不举通常是父亲的决定,而母亲通常是反对的。因此,《风俗通义》中诸多“俗云妨父母”本质上都是担心“妨父”,都是出于父亲对自家安危的担忧,只是为了争取妻子的同意,便建构了不利父母的一套话语。事实上,春秋时代并没有寤生子不举的禁忌。《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这件事《史记·郑世家》亦载:“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虽然这两条资料关于寤生含义的解释有所不同,但武姜因此而讨厌庄公则是事实,以致她还打算废长立幼,只不过庄公非但没有被弃养,而且后来还做了国君。此外,在春秋时代,出生长相怪异者也不会被遗弃。“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遂不视。”所以寤生子不举与五月五日子不举的禁忌都出现在战国以后,而且很可能出现在上层社会多子女家庭里。对上层社会男子而言,多配偶制使其“奉祖先,继后嗣”的要求能够轻易达到,故生子不举习俗便发生了变化,由考虑血缘纯洁变为考虑自身安危。
两汉时期,父亲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忧,也表现出对生育的禁忌。根据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竹木简《日书》的记载,秦汉时人对生子时日的禁忌非常多,“禁忌日生之子,或为盗,或身残,或早夭,或妨于父母兄弟等,攻解此类不吉的方法之一,乃是弃之不养”。这些禁忌既包含父母对婴儿未来的担忧,也包含父母对自身及其他兄弟的担忧,但《风俗通义》所载两汉之际对忌日生子的担忧都与妨碍父母有关,婴儿本身及婴儿的兄弟则不在考虑范围。另外,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玄戈》中有一条禁忌是“戊午去父母同生,异(简五四正叁)者焦寠,居癃(简五五正叁)”,但在《风俗通义》中却只有“不举父同月子,俗说妨父也”的禁忌。与父同生妨父,与母同生不忌,这种情况表明,生育禁忌的流传过程存在着有目的的选择,而选择权应该掌握在父亲手中。事实上,在父权强大的社会里,产后虚弱的母亲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意愿的,尤其是产妇特殊的身份,比如田文母是妾,田无啬可能连妾的名分都没有,她们连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又怎么有能力维护一个忌日出生的婴儿呢?因此,生子不举习俗流传甚广,忌日出生的孩子被弃者不少。据《世说》记载:“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恶之,乃置之瓮,投于江湖。翁见瓮流下,聞有小儿啼声,往取,因长养之,以为子。登三司,流中庸之号。广后不治其本亲服,云:‘我于本亲已为死人也。世以此为深讥焉。”又据《后汉书·张奂传》记载,东汉河西一带,“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后来张奂任武威太守,“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
结语
两汉社会流行的生育禁忌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性别权力关系。与先秦社会相比,汉代产妇得到的待遇明显低得多。虽然生育的过程在先秦时代也是不洁的、危险的,但是产妇大都会受到良好的待遇,贵族妇女生产移居侧室,庶民妇女生产则丈夫出居群室。为了保护妇女的生育功能,丧服制度对妇女的要求也相对宽松,比如三年之丧期间男子必须倚庐、寝苫以示哀悼,但“妇人不居庐,不寝苫”,以免给妇女身体造成伤害。然而到了汉代社会,由于丈夫过度关心自身的安危,产妇由被照顾保护的对象变成被厌憎的对象,产妇的身体健康也被放到次要位置。当然,由于文化发展不同,周礼的影响不同,驱逐产妇的恶习主要发生在江南地区,北方和中原地区产妇主要在家生产。在某些地方,如颍川和汝南,也许是受江南“恶”产妇之风的影响,出现了“丘墓庐道畔”的变通形式——乳舍。表面上看,这些习俗是先秦乃至原始时期产妇不洁观念和隔离产妇习俗的延续,实质上却是强化的夫权和父权在汉代妇女产孕过程中的体现。不论是“丘墓庐道畔”和“不宜归生”,还是“生子不举”,掌握话语权的都是丈夫和父亲,妻子和母亲的意愿可以忽略不计。毫无疑问,汉代社会生育禁忌背后体现的是汉代家庭中性别与权力的关系。
[责任编校解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