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诃夫的《宝贝儿》看女性的依附性问题
郭欣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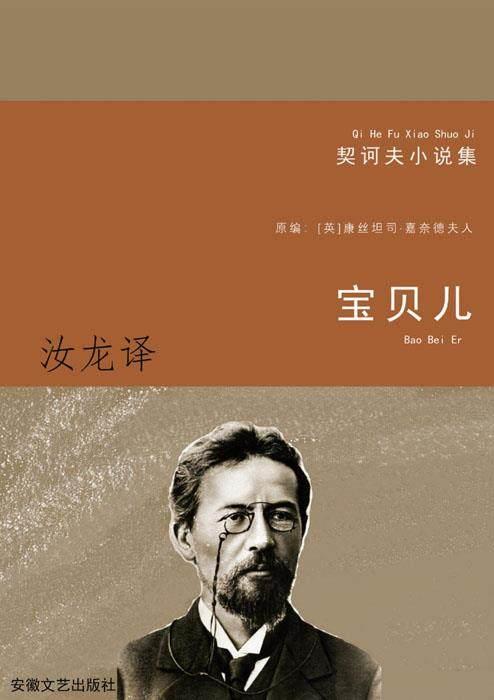


《宝贝儿》是俄国作家契诃夫于1898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俄国外省的一位普通女性奥莲卡一生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经历。奥莲卡温柔体贴、善良且讨人喜欢,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宝贝儿”,她一生中都没有停止爱人,先后与剧团经理库金、木材厂经理普斯托瓦洛夫组成家庭,又因为两任丈夫的离世而孤身一人。后来,她爱上了已婚兽医斯米尔宁,但因军队的离开又重回一人。最后,兽医一家的回归及带来的兽医之子萨沙使她重燃生机与活力,将爱转移到了萨沙身上。
相较于另一位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对于“宝贝儿”奥莲卡的喜爱以及对其细腻情感的赞扬,契诃夫对奥莲卡的塑造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点也可以在其手记中窥得一二。契诃夫借奥莲卡这一女性形象,用幽默嘲讽的笔调温和地批判了这类毫无主见、病态依附他人的女性,这也是对沙皇专制制度下传统女性价值观的抨击。在契诃夫看来,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尊严、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女性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应该具有独立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依附他人。因此,对于《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奥莲卡,他怀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感,开放式的结尾也引人深思。表面上奥莲卡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甚至结尾都还在记挂着萨沙,但实际上她过着完全木偶式的人生,是别人的依附品,既可怜又可悲。
小说中奥莲卡继爸爸、姑妈、法语教师后,又爱上了其貌不扬、刻薄、爱抱怨的剧团经理库金,这种所谓的爱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种为爱而爱的女性本能。奥莲卡总是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将他对天气、对观众品位的抱怨照单全收,会为他流泪,并被他的不幸打动,从而爱上他。但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奥莲卡无法停止爱人的本能体现。比如,婚后当库金生病咳嗽时,她会整夜悉心照料他,对他说“你真是我的心上人,你真招我疼”,后半句不似情人间的甜蜜情话,更像是对孩童的一种亲昵。当奥莲卡收到库金离世的噩耗时,这种本能的爱又显现出其特定诉求,即依附他人。在丈夫离世后,她痛哭道:“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小说中奥莲卡的第二次“爱情”出现在库金离世的三个月后。奥莲卡与木材厂经理普斯托瓦洛夫在做完弥撒回家的路上相遇,普斯托瓦洛夫安慰了她几句并将她送回了家,奥莲卡便喜欢上了他。后来在媒人的介绍下,普斯托瓦洛夫登门拜访,在不到十分钟的聊天中,奥莲卡又爱上了他。婚后,每当普斯托瓦洛夫到外省采办木材时,奥莲卡总是十分想念他,整夜睡不着觉并为此哭泣。普斯托瓦洛夫重病去世后,她又再次表现了对其强烈的依附性,丈夫下葬后,她再次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
奥莲卡所依附的第三个男性是早前便与她有过交集的兽医斯米尔宁。在与兽医的相处中,出于爱的本能,奥莲卡又爱上了已婚的兽医。这种爱同样也不是所谓的爱情,而是小说中所写的“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是一种出于本能的爱。在斯米尔宁生气的时候,她惊讶且惶恐,努力求他消气。但这种于奥莲卡而言幸福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很久,随着军队的离开,奥莲卡又孤单一人。
直到兽医斯米尔宁带着他的一家重新回来,奥莲卡才在其子萨沙身上寄托了她全部的爱,将她的依附性转移到了萨沙身上,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叮嘱他好好学习,操心他的功课问题等。奥莲卡甚至在幻想中担心萨沙离她而去,并为此心悸。
奥莲卡总是很轻易地爱上一个人,但这不是出于任何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她渴求爱、渴望依靠他人的本能在作祟,尤其是最后她将爱倾注在兽医之子萨沙身上,更是对这点的验证,这实际上是一种女性依附性的爱。
“宝贝儿”的称呼
“宝贝儿”一词用作题名和对女主人公奥莲卡的称呼,其实是契诃夫“去名化”叙事策略的一种体现。在契诃夫的另一部作品《谜样的性格》中,同样采用了这种叙事策略,女主人公向往自由,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嫁给了阔绰的老将军,慢慢习惯了这种依附他人的生活,即便在老将军死后,她获得了财产和自由,仍嫁给了第二个阔绰的老头。因为她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把自己看作男人的附庸,这样一只笼中的金丝雀自然也没有姓名。因此,“宝贝儿”这看似宠爱亲昵的称呼实际上也是奥莲卡失去自我、缺乏独立性的一种体现。“宝贝儿”一词属于低级的修辞,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亲昵性特征)。然而,在称呼者与被称呼者之间所体现的是不平等的关系,尤其是这一称呼在原义上多用于孩童这类需要呵护的对象。当这一形容词被用于男性或女性身上时,其意味就明显改变,成了软弱无能的一种礼貌性说法。
与这种称呼有类似内涵的还有中国古代女子出嫁后所冠的夫姓。在古代,女子处于从属地位,出嫁前只有乳名和闺名,出嫁后在自己姓氏前加上丈夫姓氏,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旦男女结婚,女方就脱离了自己的宗族,成为男方宗族的正式成员,要改随男方的姓氏。一方面,这是增强家庭共同体中成员凝聚力的办法;另一方面,它同样加深了女子對夫家的依附性,使其被视为夫家的私有财产,失去了自我,更验证了古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直至现代法律明确规定:“夫妻有各自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才彻底保护了女性的命名权。
但在现代社会中,即便没有这种称呼的枷锁在,女性在婚后也常常失去自己的“姓名”,成为某某人的夫人、某男孩或女孩的妈妈,被称为“张夫人”“李夫人”“张妈妈”“李妈妈”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对女性的“去名化”呢?
思想上的依附
小说中奥莲卡最显著的依附性体现在她对生命中四个男性思想上的依附,她没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是自己的话语,她的一切思想都源于别人,是对他人思想的一种复制,经她之口所说出的话仿佛是他人话语的一种“回声”,而她在其中不过是充当“传声筒”的角色。
奥莲卡先后经历了两任丈夫,又爱上了已婚兽医,对她来说,无论丈夫或情人是剧团经理、木材厂经理还是兽医,他们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他们的事业就是她的事业,奥莲卡模仿他们的神情、复刻他们的话语、盲从他们的观点。
当她爱的人是剧团经理时,甚至结婚前,夜里听到游乐场乐队演奏声和鞭炮声,她就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这时奥莲卡的思想观点已与库金在同一立场上。婚后,她将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剧院和演员身上,将剧院管理得井井有条,仿佛世间没有比她更懂、更爱戏剧的人。但有趣的是,这种对戏剧的热情在她爱上第二任丈夫时好像瞬间消失了,当普斯托瓦洛夫让她在闲暇之余去看戏剧娱乐一下时,奥莲卡一本正经道:“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剧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时她爱上的人不再是剧团经理,而是木材厂经理了。奥莲卡替普斯托瓦洛夫算账、卖货,和熟客抱怨木材贵、运费贵,她的生活重心也随着第二任丈夫转移到木材上。奥莲卡对各种木材的名字倍感亲切,甚至在夜里都能梦见各种木材整齐地堆叠起来,倒下又竖起。这种情况随着第二任丈夫去世,她爱上已婚兽医又有所改变,奥莲卡开始谈论家畜,她重述兽医的想法,谈起牛瘟和家畜的结核病,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又变得和兽医一样了,甚至在兽医因为她的话语可能暴露他们之间的关系而生气责备她时,奥莲卡惶恐地问道:“可是,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可见,除了一味地复制他人思想,奥莲卡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爱人的情绪和思想就是她的情绪和思想。当两任丈夫离世,兽医又离他而去,奥莲卡的思想世界就崩塌了。她看得见、听得到,也明白周遭的一切,但就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她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脑子和心里一样空空荡荡。直到兽医一家归来,她在思想上的依附性又转移到了兽医的儿子萨沙身上,奥莲卡和他一起温习功课,重复萨沙所学的知识、讲过的话,在多年的沉默中,又一次自信地发表了“她的”见解。
情感上的依附
小说全文以“爱”为线索,多次强调了奥莲卡“老得爱一个人”“不爱什么人,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的爱的本能,而她追求“爱”的过程同时是她寻求情感依附的过程。奥莲卡的情绪被她所爱的人牵动,她的全部身心都放在爱人身上,当爱人不在身边时,她会想念到哭泣、心神不宁,甚至幻想所爱之人离开的场景而忧心忡忡。奥莲卡的爱并没有任何固定标准,无论所爱之人是刻薄爱抱怨的剧团经理、沉闷浅薄的木材厂经理、没有担当的兽医情人还是顽劣没有礼貌的兽医之子,在她的眼里,他们都是可爱的、值得爱的,是满足她“爱”的需求和本能的,她不止爱他们,也在情感上绝对依附于他们。如果没有爱,她的精神、她的灵魂将无所寄托,她会感到空虚、迷茫、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灵魂的空壳,活着没有目标、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文中还多次通过对奥莲卡的神态、外貌和心理的描写,对比奥莲卡有人可爱和无人可爱时的两种状态。和爱人在一起时,奥莲卡“那绯红的脸蛋,可爱而天真,像在发光的笑容”,“满面红光”并真诚地祈祷大家能过着像她一样的生活;当奥莲卡孤身一人时,“她瘦了、丑了”,生活于她而言变得“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作者在奥莲卡的两次婚后都提到了“婚后过得很好”,因为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时,奥莲卡是幸福而满足的,她不用費心思去考虑别的什么事或人,只要找到了爱的人,她便找到了情感的依托。即便这在我们看来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和幸福感,但就奥莲卡固有的传统女性价值观来说,她确实是快乐的。
小说中并没有写明奥莲卡这种依附性的由来,对其家庭背景也只是一笔带过,但从已知的信息可知,早在奥莲卡恋爱结婚前,她便陷入了这种依附性爱的漩涡中,难以自拔。因此,原生家庭可能也是造成奥莲卡这种病态依附性爱的重要原因,凡是在她生命中给予她一点点关怀和光的人,出于爱的本能和需求,她都不可抑制地爱上了他们:先是自己的父亲,再是隔一年才见一次面的姑妈,甚至是只负责上课的法语教师。足可见,原生家庭在经济上可能是富足的,但它给予奥莲卡的爱远远不够,无法让奥莲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被爱的满足感,所以她终其一生不断追求爱、渴求爱,将自己的希望、思想以及情感统统寄托在他人身上,却忘了自己也可以给予自己爱。
除了原生家庭,社会环境是造成这种依附性女性观的根本原因。当时的俄国正处于农奴制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新兴势力相互渗透的时期,传统的宗法制家庭虽然受到冲击,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无法掌握自己的幸福,不论是底层劳动女性还是出身显赫的上流社会女性,都只能依附于他人,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契诃夫小说中的奥莲卡这类女性形象是对当时俄国社会广大女性的真实写照,他们大多困守于传统,既不懂得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过的是“木偶般”行尸走肉的生活。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