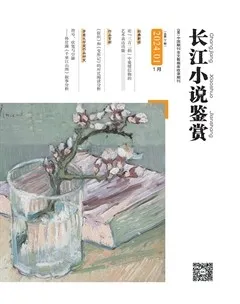库切小说《福》中的音乐叙事研究
张金梅
[摘 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作品一直深受国内外学者关注,但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作品中的殖民书写、流散身份等主题,鲜有研究从音乐叙事入手。其代表作《福》巧妙地将音乐叙事与后现代风格相融合,小说中不仅有诸如“笛声”这样重要的音乐意象,结构上更利用多声部的叙事揭露了殖民语境下边缘化群体的反抗。库切正是借助音乐叙事这一工具向读者进一步展示小说的内涵,即殖民主义下的暴力与沉默的现实以及后现代语境下去殖民化书写的可能性。
[关键词] 库切 《福》 音乐叙事 去殖民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1-0081-04
自1974年发表第一本小说《幽暗之地》后,南非当代小说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就受到各国读者与小说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其小说内容从聚焦南非殖民暴力到探索全球语境下动物伦理、大屠杀、老年残疾人、难民、宗教等新兴议题,丰富的主题内涵及冷峻简练的叙事风格使库切的作品一直深受学者的关注。尽管库切的身份是一名作家,擅长以隽永的文笔来表现复杂的主题,但是从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乐曲以及各种访谈中可以看出,他还是一名音乐爱好者。在库切看来,文字是有局限性的,不同语言文字表达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互通,但是音乐却没有这种局限,受众能够达到普遍的共鸣。纵观库切创作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其从作家生涯初期就开始对作品中内容及形式层面的音乐书写进行探索,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鲜有学者从音乐叙事的角度对库切的作品进行解读。本文以库切中期小说《福》为研究对象,作为对经典殖民文学《鲁滨孙漂流记》的改写,库切不仅将叙事视角转向一位虚构的女性角色,更是将音乐这一意象融入小说的内容以及叙事结构中,从而在后现代语境下再次审视这段殖民历史,探讨音乐叙事实现去殖民化书写的可能性。
一、音乐内容叙事:沉默之笛
作为南非出身的作家,库切自进入文坛以来便被打上“南非作家”这一烙印。在库切创作生涯早期,许多直接以南非为背景的小说如《幽暗之地》等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不难看出,初出茅庐的库切更愿意在熟悉的故土以及南非被殖民的历史中寻找写作灵感。与其他非洲作家不同的是,库切曾在访谈中表示,“南非小说家”的标签对他来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他本人对这个身份多少是有点抗拒的。从其后期作品中可以看出,库切逐渐把目光从南非这片土地转到整个世界,小说《福》就是写于这一时期。不同于早期作品中对南非现实的历史书写,库切此时的创作无论是在主题还是叙事技巧方面,都开始呈现后现代主义特征,多变的叙事手法不仅是对经典的颠覆,也启示读者思考,边缘群体如何通过自我叙事在历史书写中实现去殖民化。
《福》改写了经典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叙述的故事似乎跟非洲毫无关系:一个叫苏珊·巴顿的女人在巴西乘船前往欧洲寻找女儿,不料水手集体叛变,将船长杀死并把他的情妇苏珊扔下大海,最终苏珊流落荒岛被克鲁索和星期五所救。后来一艘路过的商船将三人带回英国,但克鲁索死于途中。回到伦敦后,苏珊一边照顾星期五一边找到作家福,想让他把自己在荒岛的故事写出来。如果仔细研读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可以发现,小说《福》中的星期五来自非洲大陆:“他的皮肤黝黑:一个满头鬈发的黑人,上身赤裸、仅穿着一条粗糙的衬裤。”[1]相比于笛福笔下唯命是从的星期五,与苏珊一起生活的星期五更具有反叛精神,虽然他从一出场就处于失语的状态,被割掉的舌头让他丧失了话语权,但星期五没有就此沉默,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来为“发声”。
星期五是小说中最难理解的人物之一,库切对其形象可谓是精心设计。笛福原著中的星期五被驯化成克鲁索忠诚的奴隶,此外,他还被动接受了宗教观念以及英语的学习,话语成了奴役星期五的工具。库切却别出心裁,将星期五设定为一个被割掉舌头的野人,一个只有沉默、没有话语的“他者”。星期五的舌头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通过“无声”的形式让读者意识到星期五的残缺,意识到“历史和文学中许多无声的人们”[2]。克鲁索作为殖民者的代表,认为星期五只需要学会日常需要的单词就可以,不需要理解太多英文单词,面对苏珊“没有声音的生活有何乐趣可言”[1]这样的疑问,克鲁索却以奴隶主的身份把星期五的失声当作是上帝最好的安排。和星期五一起生活十几年的时间里,克鲁索拒绝教星期五开口说话,对于他来说,星期五像条狗一样,只需要服从自己的命令,他并不关心星期五的想法,对星期五的遭遇也没有怜悯之心。作为殖民者的代表,他不允许作为“他者”的星期五拥有话语自由与权力。
对于星期五来说,这个世界是无声的,除了听懂主人的命令之外,他没有权力去了解这个世界,去叙述自己的故事。从苏珊的转述中读者可以发现,在星期五无声的世界里,音乐构建了他的精神世界。在克鲁索得热病的时候,星期五会用他的芦笛重复吹奏一首只有六个音符的曲子,一首他永远不会感到厌倦的乐曲。在他的世界里,音乐就是可以表达自己的唯一方式,也正是借助这种含蓄的方式,库切赋予星期五为自己发声的机会。正如库切在小说《耻》中借主人公所言:“有声言语的起源在歌唱,而歌唱之起源蓋因人类灵魂涵盖太泛而又空洞无物。”[3]对于库切来说,音乐比语言更接近人类的灵魂。在教授星期五说话未果后,女主人公苏珊尝试用音乐和他交流,她“演奏着星期五的曲调,先是跟他齐奏,后来是等他停止的时候再加进去,最后一直不间断地跟着他演奏”[1]。虽然两人的合奏听起来并不和谐,但苏珊已经感到满足,此时对她而言,“对话本身不就像音乐一样,一个人先演奏一段,然后另一人再接着演奏”[1]。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珊发觉通过演奏同样的曲调无法满足交流的欲望,她最终还是在曲调上做些变化,但是星期五仍然坚持自己的曲调,这就造成了两人合奏时发出极不和谐的刺耳声。苏珊试图通过音乐与星期五进行交流,对她来说音乐只是一种交流工具,而她则化身指挥家,通过吹奏笛子引导星期五与自己交流,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霸凌。但星期五对苏珊的演奏变化无动于衷,他宁愿沉浸在个人世界中,通过吹笛子神游他乡而忘记苏珊的存在,他更不会主动地学习融入白人的世界。
作为被殖民文化的隐喻,星期五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他拒绝融入苏珊的演奏,不仅是对苏珊管教的反叛,也是西方殖民主义之下无声者“正逐渐从西方自我那里要回阐释的主动权”[4]。没有人可以为星期五发声,他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演奏笛子与手舞足蹈来表达自我,他的舞蹈有自己的节奏,他的笛声有自己的音调,这一切都是苏珊无法理解、无法融入其中的。“而沉默,是他抗争的手段。”[5]
二、音乐形式叙事:多重声音
如果说笛声是库切在小说中的显性音乐叙事,那么不同的叙事声音则构成了小说的复调结构。多声部叙事不仅是对音乐曲式的模仿,更是对星期五和苏珊这类边缘群体的“赋权策略”[6]。《托斯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指出了“复调”在文学上的应用:“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7]不难看出,复调小说强调的是众多“独立的意识”,而不是简单的情节与人物的发展,小说中的角色被赋予独立意识,不再成为受作者控制的傀儡。库切本人也认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他曾在论文集里对托斯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对话性的起源展开讨论。在库切看来,作家书写对话真正的意义是“唤醒人物内心相反的声音”[8]。小说《福》中,库切巧妙地利用角色间的对话来扩展叙事模式,不论是苏珊与克鲁索、作家福之间的言语交锋,抑或是他们内心的坦白,不同角色间的意识和表达让小说呈现出乐曲般的流动性。
作为贯穿小说的灵魂人物,苏珊·巴顿的声音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可以说读者正是通过她的叙事来了解小说的全部情节。库切从一开始就让边缘化的女性在叙事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作为女性叙事主体的苏珊的声音却一直遭到来自父权体系的压迫:在荒岛上,作为国王的克鲁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威,当苏珊稍有反抗之意,他就大发雷霆,并且威胁道:“只要你生活在我的屋檐下,你就要听从我的命令!”[1]尽管如此,苏珊依然一心挖掘克鲁索以及星期五的故事,并在获救后希望以自己的视角叙述整个故事,想要“根据自己的希望选择说出自己要讲的故事”[1]。当作家把叙事的权力下放给一直被边缘化的女性角色时,苏珊的声音不仅是对父权压迫的反抗,更在叙事主体上打破了角色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此外,叙事视角的转变也将小说中不同的声音呈现给读者,小说开头便以“我”展开第一人称叙事,与此同时,第二人称叙事也贯穿小说前两章。随着故事的展开,小说中的“你”也向读者袒露真实的声音:作家福先生。作为殖民者的代表,具有作家权威的福先生在话语层面一直彰显着自身的男性权威,而叙事视角的变化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更凸显了苏珊的叙事力量:由于苏珊不相信自己的创作能力,她的声音最初只传达给福,由他加工、删减构成理想的荒岛故事;随着两者交流愈发频繁,苏珊开始质疑福的权威性,在辩论中发现福为了故事的趣味性而虚构出荒岛事实,让她发现她所惧怕的作者权威不过是作者在话语权力之下的随意创作。福的创作历程因随意篡改他者历史到遭受质疑,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殖民文学中作者权威性的解构过程。
小说中多重叙事声音的出现是库切为赋予边缘人物发声的权力所采取的策略,也是对后殖民语境下男性气质解构的再思考。作者通过女性叙事来瓦解殖民霸权体制下男性话语的权威性,不仅呈现了去殖民化的写作形式,还向读者揭示了殖民者历史书写的本质。库切曾在访谈录里谈到,叙事的过程其实是文本作者对事实的删减或篡改,最终呈现的只是一种“十分空洞的真相的观念”[8]。小说中苏珊和福因为如何再现荒岛故事产生了分歧,苏珊只想叙述在荒岛上发生的故事,包括克鲁索和星期五之间的生活片段;然而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福只想围绕苏珊和她的女儿来进行创作,从而完成“找女儿”这个故事的创作。荒岛的故事在他看来过于平淡,需要加入虚构的成分才能引人入胜,而这恰恰违背了苏珊追求真实的原则:她坚决反对通过虚构的历史呈现出虚假的叙事。
小说中不同的声音呈现了角色的自我意识,苏珊代表的女性角色追求故事的真相,而男性作家福却对故事随意地进行篡改,作为他者的女性叙事却贯穿整体,不仅挑战了男性作家所象征的父权权威,更是对殖民文学中随意删减事实而创造出的虚假历史进行了批判。
三、音乐叙事内涵:去殖民化
库切在《什么是经典》一文中谈到巴赫的音乐如何成为经典,他叙述了音乐是如何走进自己的生活:“1955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我十五岁……在那些日子里,无聊是生活的最主要的问题。恰在那时,我听到邻家传来的音乐声。音乐结束前,我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连大气都不敢出。乐声悠扬,似乎在向我诉说些什么,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经历。”[9]此时震撼少年库切的音乐便是巴赫的钢琴曲,这也让他感受到了经典的魅力。对于库切来说,巴赫的音乐并不是晦涩难懂的,他笔下的音符和谐地形成更深层次的音乐,“巴赫在用音乐思考。音乐通过巴赫在思考自身”[9]。那么库切是否也在通过音乐思考自身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巴赫的乐章还是库切的小说,都是让受众通过这个媒介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通过一种普世的视角来延伸主题的表达,音乐叙事的意义便由此构成。
小说的创作源自作者对生活和世界的探究,作为拥有南非成长背景的库切,第三世界所遭遇的惨痛历史是他无法逃避的主题。其南非主题的小说正是库切对殖民主义之下被边缘化的族裔人群的生活的反映,正如《福》中的星期五,一个被克鲁索所救的黑人奴隶,就是被殖民群体的缩影:一个被割掉舌头丧失话语权的人,无法讲述自己的历史,无法提出自己的诉求,只能被殖民者压迫、被边缘化。正如苏珊所说,星期五是被沉默,他的沉默“是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只好日复一日任凭他人肆意地塑造”[1]。星期五的沉默背后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沉默,他们都被殖民者剥夺了为自己正言的权利,而他们只能选择用沉默来反抗殖民者的支配,从被迫失去话语权,到以沉默相抗衡,這正是后现代语境下对于殖民化的解构。
此外,库切在小说里通过音乐赋予边缘人物星期五权利,星期五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但他有一支笛子,通过笛子重复演奏的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苏珊曾试图通过笛子来与星期五沟通,当她演奏出与星期五相同的曲子时,内心感到十分满足,虽然吹出来的音符不够和谐,但作为主导者的她已经认为自己能够和星期五“交谈”,能够理解他的世界。苏珊不仅希望能够走进星期五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让他屈从于自己的话语权力。所以当星期五拒绝跟随苏珊的曲调进行变化时,作为殖民代表的苏珊变得愤怒。此刻的音乐不仅是被殖民者星期五的精神支柱,更是他反抗权威的有力工具。通过星期五无声的反抗,库切展现了殖民语境下边缘化个体的觉醒,他们在历史书写中努力去除殖民化的影响,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片无法被殖民的自留地,这里有他们的文化和灵魂”[10]。星期五的残疾叙事被嵌于殖民背景下,“不仅隐射殖民肌体的残疾,更是对殖民文化进行质疑与批判”[11],而音乐这一意象不仅破坏了这一叙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殖民群体发出反殖民诉求的工具。
同样作为殖民语境下的边缘群体,苏珊通过书写荒岛故事来重新构建白人女性话语权。她与福的声音宛如乐曲中的双声部,始终就故事书写这一主题展开辩论,而苏珊也从默认男性书写权威成长到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可以看出小说中苏珊的话语流露出对殖民语境下父权的反抗,从而完成女性去殖民化的书写。这种音乐叙事不仅打破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多声部叙事恰如乐曲中的合奏,恰好体现了库切重视小说参与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性,借助文字的力量演奏出后现代语境下父权与殖民话语逐渐解构、女性群体和殖民地边缘群体夺取话语权的乐章。
四、结语
文字作为传递情感的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和音乐的功能如出一辙,而音乐和小说的结合早已在小说创作中得以运用。对于库切来说,音乐不仅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也成为其创作过程中的缪斯。在库切的小说中,各种音乐元素或直接或间接地被运用在小说中,这不仅是对音乐简单的借鉴与模仿,更是通过音乐放大小说的内涵意义。小说《福》中呈现的音乐叙事不仅是利用众声喧哗的叙事声音来谱写边缘群体反抗殖民的悲歌,更是利用笛声这一意象为殖民历史中受伤害的残躯发出无声的抗议。音乐成为库切探讨边缘群体如何寻求话语权的工具,也让库切的小说达到文字与音乐的统一。音乐叙事不仅推动了文本叙事的进程,同样是库切赋予边缘群体反抗文化霸权、审视殖民历史的有力武器。
参考文献
[1] 库切.福[M].王敬慧,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2] Hall B.The Mutilated Tongue: Symbols of Communication in J. M. Coetzees Foe[J].Unisa English Studies: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1993(31).
[3] 库切. 耻[M]. 张冲,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 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 张德明. 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J]. 當代外国文学,2010(4).
[6] 张磊.意识形态的“声”战—小说中的音乐书写[J].外国文学,2018(4).
[7]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 Coetzee J.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9] Coetzee J.Strong Short Essays 1986-1999[M].London:Vintage Press,2002.
[10] 高敬,石云龙.试论后殖民语境下库切小说《福》中的话语权[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 (10).
[11] 金怀梅.库切《幽暗之地》对殖民神话的颠覆[J].外国文学研究,2023 (1).
(特约编辑 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