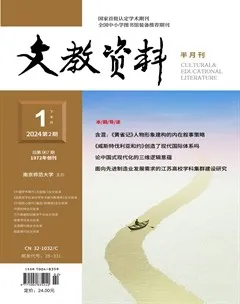从“鄙夷”到“师夷”:朝鲜士人朴趾源的“对清观”及其转变
徐炎红
摘 要:明清更代,深受朱熹华夷观影响的朝鲜士人对清朝并不认同,这种局面至18世纪后期才有所改观。一批具有实学思想的朝鲜士人先后出使北京,在深入观察清朝社会后,对清朝产生了认同感,促使朝鲜“北学派”产生。朴趾源作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热河日记》形象地展示出他在康乾盛世影响下从排斥清朝到以清朝为师的思想转变过程。追根溯源,这反映的是朝鲜士人对中华儒家文化的追求。
关键词:朴趾源;“对清观”;《热河日记》;“康乾盛世”
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朝鲜士人普遍接受朱熹的华夷观,认为“贵贱之位,华夷之判,皆天之所为也……君臣之义,宾服之礼,皆理之常然也”[1]。因此,明亡之后,朝鲜国内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以“小中华”自居,并将自己塑造成“中华正统”的继承者。不过,这种局面在18世纪后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清朝不断对朝鲜施恩抚慰,通过主动裁减贡物、赈济朝鲜、优待朝鲜国王与使臣等[2]举措拉拢人心。另一方面,朝鲜国内实学思潮兴起,一批具有实学思想的士人陆续出使清朝,他们对清朝社会进行了细致观察,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清朝的现实情况,从而使他们的“对清观”发生变化。朴趾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清五个月,曾前往燕京、热河两地考察,所著《热河日记》因内容丰富广为学界关注。
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朴趾源实学思想的研究、对中朝文化交流的史学研究、以日记为切入研究当时社会的思想和社会风貌,以及对日记本身文学价值的分析。仅就朴趾源的“对清观”而言,学界多将《热河日记》与其他燕行录一起研究,而对其个人的思想转变研究略显不足。
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析《热河日记》所体现的朴趾源“对清观”转变过程,进而探究其转变背后的根源。
一、朴趾源固有的“斥清思明”思想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君臣感念明朝“三大恩”:朱元璋赐朝鲜国号之恩,明朝出兵助朝鲜平息“壬辰倭乱”之恩、崇祯帝发兵东援朝鲜抵御清兵之恩。朝鲜国内弥漫着浓厚的“尊周思明”氛围,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孝宗宣扬北伐,肃宗志在崇祀,英祖、正祖时皆崇祭祀、重编史、顾明遗民。[3]在这种背景下,朴趾源的心中始终尊明朝为“上国”:“皇明,吾上国也……何为上国?曰中华也……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者,四百年犹一日,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4]
与之相反,朝鲜与清朝的关系颇为复杂。女真时期,双方已矛盾重重。女真部落长期侵扰朝鲜,纠纷不断,朝鲜甚至曾武力讨伐女真,两方仇怨积攒已深。同时,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朝鲜以传统的“华夷观”为衡量标准,奉明朝为宗主国,视自己为亚宗主国,并将明周边的其他民族如女真等视为有“来朝”“来贡”义务的朝贡国,女真成为朝鲜理念中的“夷狄”。虽然丙子之役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奉清朝为正朔,但朝鲜君臣内心均不承认清朝为“上国”,仅称“大国”,朴趾源也是如此。他说:“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曰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5]
在朝鲜国内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热河日记》中随处可见朴趾源所坚持的“斥清思明”思想。比如他对清太祖名讳使用“奴儿哈赤”,根據该名音译所用汉字之意可知这是一种丑化性、歧视性的称呼。朴趾源采用这种源于明朝的译法,而不称“清太祖”,体现的是对明朝“君父”之邦的延续,对自身文化正统性的标榜以及对清朝的鄙夷之态。又如他在日记中沿用崇祯年号,尊明朝为正朔,甚至直言清人断绝中华正统,转华为胡,反观朝鲜“环东土数千里画(划)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6]。他认为如今胡虏占据中国,唯有朝鲜能继承并发扬中华文化,驱除戎狄,光复昔日中华正统。这是传统华夷观影响下当时朝鲜国内士人的普遍认知。
朴趾源初入清朝时,随时随地感叹明朝的消逝。如途经康世爵隐居之地,联想到其父祖为抗清所做的牺牲,认为康世爵不臣清朝而奔向朝鲜是明智之举。“中原路绝,不如东出朝鲜,犹得免薙发左衽。”[7]自古中原文化中就将“薙发左衽”视为“蛮夷”的文化特征,朴趾源批评清朝强制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不仅与中华正统文化相违背,也是对朝鲜文化的不尊重。清朝戏台上“演剧者蟒袍、象笏、皮笠、棕笠、藤笠、鬃笠、丝笠、纱帽、幞头之属,宛然我国风俗。道袍或有紫色而方领黑缘,此似古唐制也”[8],古代伶人地位低下,如今清朝伶人服饰与朝鲜服饰相似,在朴趾源看来这无疑是对朝鲜的一种耻笑。朝鲜士人自视为传承华夏衣冠,当看到明朝衣冠只能出现在戏台上,成为伶人之服,其内心的感慨可能与此前出使清朝的另一位使臣金昌业相同,即“夷狄乱夏,四海腥膻,中土衣冠之伦,近入于禽兽之域”[9]。
朴趾源所处的时代距离明清更代已有百年之久,其观念中对清朝的排斥却未曾减弱,而对明朝的思念愈加浓厚。但随着朴趾源对清朝社会的深入接触,其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尤其康乾盛世的现实景象对其原有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二、朴趾源对清朝社会的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
朴趾源随使团前往清朝时正值“康乾盛世”,朝鲜国内流传的“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早已不攻自破,并且朴趾源所见之景象与朝鲜国内宣扬的蛮夷形象大为不同,现实带来的巨大震撼促使朴趾源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
(一)政定边宁的政治景象
朴趾源入清是为乾隆祝寿,因此得见一场盛会。既有六世班禅、蒙回王公、四川土司、台湾少数民族首领等人来贺,也有越南、琉球等国的使臣携礼前来,特别是六世班禅万里来朝,乾隆极为重视。朴趾源在沿途已听闻臣民议论,在热河祝寿时又亲见乾隆与班禅“两相搐搦,相视笑语”[10],共同接受满汉蒙臣民、各族首领及外国使臣的庆贺。[11]虽然对黄教缺乏了解,但他深谙中国历史,自汉代以来少数民族一直侵扰中原王朝,而康乾盛世下的民族关系显然比朝鲜尊崇的“中华正统”的明朝更为稳定、和谐。对此,朴趾源肯定了清朝的“制四方之术”,一针见血地提出边防忧患的重点在于北方,领悟到热河行宫的作用:“宿留蒙古之重兵,不烦中国而以胡备胡,如此则兵费省而边防壮,今皇帝身自统御而居守之矣。”[12]同时他也认识到清朝扶持黄教以巩固西部边防:“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迎其法师,盛饰宫室以悦其心,分封名王以析其势。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术也。”[13]这让他感受到清朝强大国力下的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扭转了清朝在他脑海中只知掠夺的蛮夷形象。
(二)富庶康宁的百姓生活
入清之前,朴趾源认为清朝百姓大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他沿途经过的边地市井乡村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热河日记》中这样描绘:酒馆“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豚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皆精丽如画”[14];村落“栅内闾阎皆高起五梁,苫草覆盖,而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术(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15]。百姓的娱乐生活也颇为丰富,“趁上元、中元设此簟台,以演诸戏。尝于古家铺道中,车乘连络不绝,女子共载一车,不下七八,皆凝妆盛饰。阅数百车,皆村妇之观小黑山场戏,日暮罢归者”[16]。此外,还有各种迎神赛会、地方戏曲、游艺等活动。至于京城,则“百货盈庭”,品种繁多、制作精美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珍宝“磊落宛转于履屐之间,令人足踖如也,心怵如也”[17]。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景与朴趾源最初的想象完全不同,这是清朝统治者改善民生所取得的成效。
(三)承袭儒韵的文化风俗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重要体现,是判断某文化是否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朴趾源作为儒家学者,对清朝儒学保持高度关注。入清前,他已知清朝国内大兴科举,士人皆读“四书五经”、习程朱理学,但他认为清朝此举是出于“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18]的目的。入清后,随着与清朝文人广泛交流,他深切体会到清朝所遵行的程朱理学并非徒具虚名,清朝亦多有饱学之士。在热河,他结识了举人王鹄汀,与之笔谈后非常钦佩其才学,“纵横宏肆,扬扢千古,经史子集随手拈来,佳句妙偈顺口辄成,皆有条贯,不乱脉络”[19]。同时他也看到儒家观念依旧主导着民间风俗,如女子出嫁沿袭了明朝的“摄盛”制度,“女子出嫁时有髻无笄,无论贫富。民妇无冠,惟命妇有冠,各随夫职。簪钗有品,如顶帽之制”[20];所见“丧制皆遵朱子”“丧人据椅碧纱窗下,身披一领绵布衣,头发不削,长得数寸,如头陀形,不肯与人酬酌。前置《仪礼》一卷”[21]。这些都表明清朝延续并发展着儒家传统文化,承继历代“故常”。
一个落后的蛮夷文化能否转变为先进文化,朴趾源认为衡量标准在于这个文化能否富民强国。虽然朴趾源没有获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他从亲身体验与观察中看到了清朝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稳。因此他认为康乾之世已比肩汉唐,“今升平百余年,四境无金革战斗之声,桑麻菀然,鸡狗四达。休养生息乃能如是,汉、唐以来所未尝有也”[22]。由此他一改对清朝全面鄙视的态度,萌生了向清朝学习的想法。
三、朴趾源“北学”思想的萌发
朴趾源“北学”思想的萌发始于他对清朝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的关注。作为实学家,朴趾源重点关注了清朝的各类生产工具,并赞叹这些工具的精巧与高效,如灌溉田地的工具有“龙尾车、龙骨车、恒升车、玉衡车”[23],各式车制结构精密、灌溉科学高效;纺织布匹的工具有“机动而轮旋,轮旋而籰转,交牙互齿,不疾不徐,慢慢抽引,不激不浊,任其自然”[24]的缫车,所生产的纱线更加粗细均匀、光洁明润;加工面粉的工具有“大牙轮二层,以铁轴串之,立于屋中,设机而旋之”[25]的转磨,微动却功巨。这些生产工具的构造比朝鲜的工具更显精妙,相较于朝鲜手工劳作更能提高生产效率。为此,他积极探寻并记录这些工具的操作方式和原理,如他将看到的救火水车“略录其制,将归谕我东”[26],并希望朝鲜有识之士能将这些技术在朝鲜推广应用以改善本国民生,即改变“吾东生民之贫瘁欲死,庶几有瘳耳”[27]的现状。
朴趾源对清朝先进生产技术的认可,推动了他“北学”思想的形成,促使他逐渐承认清朝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朴趾源认为,技术不论出处,只要有实用价值就可以吸取。“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28]因此,他提出为促进民生发展而利用“夷狄”之术并不耻辱,并以南朝时期陈庆之之语为理论依据,“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29]。朴趾源与陈庆之两人虽所处时代不同,但思想经历类似,陈庆之自北魏回还后“特重北人”[30],朴趾源此次燕行之后也开始“特重清人”,这代表着他对清朝的观念发生了嬗变。既然北魏之洛阳可被称为“中原”,那么清朝之景象也确实继承了中华传统,“中华之城郭、宫室、人民”“正德、利用、厚生之具”“崔、卢、王、谢之氏族”“周、张、程、朱之学问”“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31]均未消亡。日记中的这些肺腑之言是朴趾源承认清朝保留了“周官旧制”,承袭中华文化的直接证据。
朴趾源的“北学”思想更直观地体现在他为学生朴齐家的《北学议》所做的序言中。首先,他痛心朝鲜对清朝的偏见:“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32]他抨击朝鲜将清朝山川、百姓、语言贬低为腥膻、犬羊、侏离的错误做法,批评朝鲜排斥良法美制的愚蠢行为。之后,他肯定了清朝为汉唐宋明的继承者,指出百姓生于中土是中华遗民,认为“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况其规模之广大,心法之精微,制作之宏远,文章之焕赫,犹存三代以来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33]。最后,他指出向清朝学习的必要性,朝鲜“日趋困穷,此无他,不知学问之过也。如将学问,舍中国而何”[34]?若是舍弃向先进文化学习,故步自封,只会导致国贫民弱。由此而言,朴趾源实现了对清朝从“鄙夷”到“师夷”观念的转化,并进一步主张学习清朝先进的技术文化以利用厚生。
四、结语
明朝、清朝与朝鲜都是典型的宗藩关系,但是受华夷观的影响,朝鲜对明朝保持高度认同,甚至在孝宗时提出过“北伐论”。随着康雍乾三朝的励精图治,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朝鲜对清朝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实现了从“北伐论”到“北学论”的转变。[35]
朴趾源等朝鲜燕行使臣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切感受到清朝的盛世风貌,思考起原有观念与现实的冲突,两者的矛盾促使洪大容等朝鲜实学家进行思想革新,提出“新华夷论”,进行重新定义:天地生养、气血充足为人;能够安邦定国、平定一方者谓君王;“重门深濠,谨守封疆”则是邦国;无论是章甫亦或是委貌均是中华服饰,文身亦或是雕题都是刺青,这些是中华习俗风貌的体现。[36]因此“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37]这是“北学派”对朝鲜传统“尊周攘夷”的质疑和反思的结果,他们认清了传统儒家文化已被清朝继承的事实,强调向清朝学习先进文化和技术。“新华夷论”是对清朝政治、经济、文化认同的现实回归,是朝鲜旧有文化观念对现实的妥协。朴趾源等实学家们为保守的朝鲜社会带来新学术、新思想,期待朝鲜焕发新机,“同时也令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实质上又回到了传统东亚的‘中华世界秩序之下,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38]。
参考文献
[1][朝鲜]权好文.松岩先生文集:第六卷[M]//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五十四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96.
[2]池新宇.宗藩体系下的朝鲜与琉球关系研究(1644—1842)[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21.
[3]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62.
[4][5][6][7][8][10][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1][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M].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87,187,1,7,81,186,219,219,12,10,67,346,219,243,79,104,153,65,66-67,66,65,65,61,61.
[9]劉广铭.《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族人形象——兼与其中的汉族人形象比较[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5-50.
[11]毕国忠.六世班禅热河觐见史略[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34-36.
[29][3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4854-4855,4854.
[32][33][34][朝鲜]朴趾源.燕岩集:第七卷[M]//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二百五十二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89:109,109,109.
[35]刁书仁.从“北伐论”到“北学论”——试论李氏朝鲜对清朝态度的转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4):113-122.
[36][37][朝鲜]洪大容.湛轩书:第四卷[M]//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二百四十八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89:99,99.
[38]杨雨蕾.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8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