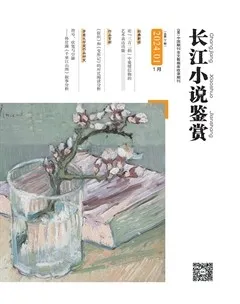《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形象分析
龙佳仪
[摘 要]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明代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中的一篇白话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三巧敢于打破封建社会对女性情感和身体的束缚,正视人的欲望,是极具典型性、反叛性和进步性的女性形象。王三巧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嬗变性可以从两个矛盾来分析,一是从前期人性的压抑、恪守妇道到后期热烈大胆、放纵情欲的矛盾;二是人物形象的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以弗洛伊德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剖析王三巧的内在心理,再结合家庭环境、人际关系等外在因素对王三巧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王三巧 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1-0028-04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珍珠衫是全文的线索,原文围绕蒋兴哥、王三巧、陈商、平氏四人,书写了几段分分合合的情感纠葛,其中珍珠衫作为隐藏的线索贯穿其中,极具戏剧性。蒋兴哥初会和重会珍珠衫是情节发生重大变化的节点,推动情节发展。其中王三巧这一人物占据大量篇幅,她与蒋兴哥、陈商、县令的三段关系,以及她在每段关系里所做出的选择,使这一女性形象鲜活、丰满,极具复杂性和进步性。
王三巧是王公最小的女儿,比两个姐姐出落得更加标致,所以夫妇俩疼爱有加,三巧在父母浓浓的爱意里成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此性格善良体贴、通情达理、浪漫随性。蒋兴哥的父亲早早为儿子定下了与王公女儿的婚事,因此一到适婚年龄,兴哥明媒正娶迎三巧回家。这两位新人郎才女貌、互相尊重、恩爱非常。五年后,蒋兴哥因南方生意尚未处理,又不能坐吃山空,于是启程南下,却因病在广东耽搁。三巧在家中久等不到音讯,经薛婆和陈商的诱骗失去贞洁。丈夫不忍明言,一封休书结束了夫妻关系。后来三巧成了县令妾室,再度与蒋兴哥相逢,舍命救了他,她的深情最终感动县令,成全她和蒋兴哥重归于好。这篇小说以王三巧的情感和婚姻为主线,书写夫妻内部矛盾,“凸显人性与伦理的冲突,人的本能欲求在生活中的压抑和爆发,以及爱的宽容”[1]。王三巧这一人物形象有许多闪光点,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性格具有复杂性和发展性。作者通过王三巧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意义,即对人性、人情的肯定,对男女之间爱和真情的认同,为无数封建礼教压制下的传统妇女发声,亦用男女之间的真挚情感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和吃人本质。
一、外在形象:长相标致、教养极好、恪守礼法
小说中王三巧刚出场时,其外在形象是极其完美的,不仅长相标致,还出身大户人家,婚后恪守礼法。这一完美形象满足了封建社会人们对完美女子的想象。
王三巧长相极为标致,小说中有许多直接描写,如“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2]。也有一些侧面描写,如“陈大郎只在楼下看了一眼,便心心念念:‘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2]。就连薛婆子初次见到王三巧也心想:“真天人也!怪不得陈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浑了。”[2]而王三巧出挑的长相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她与三个男子之间的关系都离不开她的美好姿容。
王三巧的教养极好,善解人意、礼数周到,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出阁前,受过良好的礼法熏陶,且从王公因“孝未期年,于礼有碍”断然辞婚,待“周年已到”“六礼备足”才让女儿出阁,可看出王家是克己守礼的正经人家。而王三巧为人处世也极为周到,从她招待薛婆即可看出:讓丫鬟弄了一桌子的菜,还客气道“见成的,休怪怠慢”,婆子端着菜来她家,请她坐客席,她谦让道“虽然相扰,在寒舍岂有此理”[2]。
王三巧起初是恪守礼法的少妇,同时也过着长期困于楼阁内、与外界隔绝开来的寂寞生活。就连新春佳节阖家团圆热闹非凡的时刻,她也只能在房中寂寞冷清地度过,可见其生活乏味无趣、度日如年。但她依旧听从丈夫临走前的留言,莫在窗前徘徊,以免招惹到不怀好意之人。当陈大郎请薛婆子帮忙时,婆子也推辞称三巧很是贞洁,与丈夫十分恩爱。
二、性格嬗变的内在心理和外在因素
1.内在心理:本我、自我、超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提到个体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人性本质和社会规范之间始终存在的矛盾冲突,这个理论可用于深度剖析王三巧失贞的内在心理原因。王三巧从压抑人性、恪守妇道转为正视人的欲望、热烈大胆这一嬗变过程,反映了她性格的复杂性,读者可以深入地探寻其失去贞洁的原因和心理斗争,深入了解王三巧这一灵动和立体化的女性形象。这一复杂性和前后矛盾揭露了三巧生命里的爱、纠结、痛苦和悲悯,是一种因外界的种种束缚无法实现内心统一的挣扎,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激情燃烧和自我救赎。
超我是良心和道德。王三巧幼承庭训,家教甚严,所以起初她过着孤独寂寞的闺怨生活,“数月之类,目不窥户,足不下楼”[2]。她是遵守伦理道德、贞洁操守的典型。
本我是人的潜意识,代表欲望,是人的生物本能,如饥饿、生气、性欲等。“本我既无组织,也无统一的意志,仅仅有一种冲动为本能需要追求满足。它不容于社会理性,所以压抑在意识之下,但并未被消灭,无时不在暗中活动,要求直接或间接满足,从深层支配着人的整个心理和行动。”[1]王三巧在家苦苦等待了一年,归期已至丈夫却杳无音讯,归家之日遥遥无期,她内心早已被等待和寂寞纠缠至绝望的境地。这时遇上薛婆子几个月的牵引和诱骗,她逐渐沦陷在情欲里。正如文本中所写:“一个是闺中怀春的少妇,一个是客邸慕色的才郎。一个打熬许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个盼望多时,如必正初谐陈女。分明久旱逢甘雨,胜似他乡遇故知。”[2]本我追求唯乐原则,不管价值、善恶和道德,只一味地发泄本能的冲动。事后三巧也有过犹豫:“事已如此,万一我丈夫知觉,怎么好?”[2]婆子便说:“这事包在我身上,你且放心。”[2]于是本我又占了上风,“生理欲望战胜了道德理性原则的召唤,她和陈大郎两人很快就‘恩义深重,各不相舍”[3]。三巧内心的欲望,在许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如火焰般燃烧起来,实际上,封建社会将妇女置于一个极其严苛和变态的环境里,违背了基本的人性需求,三巧的行为是本能的反叛和抗议。
自我扮演着调节者,调节本我和现实。王三巧在事后对自己有过道德和良心的谴责,“看到休书后她想起与蒋兴哥四年来的恩爱,如今因为自己的背叛而致决绝,悔恨羞愧不已”[4]。蒋兴哥又顾及夫妻之情不忍说明,让她更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后悔。超我便惩罚了本我,表现为自卑和罪恶感。三巧潜意识里感到自责和羞愧,甚至想用死亡来惩罚自己,这里超我和本我的斗争达到极致,她陷入极端痛苦的情绪。
这样的心理变化过程让读者先是吃惊,换位思考后又愿意理解她的处境和命运,最后甚至对她心生敬佩之情。小说对贞操观念有了新的理解和假设,不再受困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的爱情和婚姻有了更合乎人性的观念。王三巧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反叛者,她的行为为许多倍受压抑的妇女发声,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2.外在因素:家庭环境、他人诱骗、丈夫宽容
王三巧性格的形成和嬗变也离不开一些外在因素,比如家庭环境、薛婆子的诱骗、丈夫的爱和尊重等,这些外在因素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她是家中的小女儿,从小父母对她就宠爱有加,原生家庭给的安全感也是她性格任性、浪漫自由的根源。父亲看到休书后,气愤地跟到女婿家为女儿讨回公道:“我女儿是清清白白嫁到你家的,如今有何过失你便把她休了?须还我个明白。”[2]随后又对妻子说:“慢慢地偎着女儿,问他个明白。”[2]王三巧想自缢时,母亲急忙拦下来,安慰她说不可寻短见,日后再择良缘。有父母做三巧的坚实后盾,为王三巧性格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对人物的反叛性书写有重要意义。
王三巧的性格由克制压抑到热烈大胆,这与薛婆子的煽动和诱骗有直接关系。薛婆子先是得到了王三巧的信任,顺利地住进了她家里,这是第一突破口。夜里两人一头同睡,薛婆子给王三巧讲了许多“街坊秽亵之谈和年少偷汉的许多情事”[2],这是第二突破口。最后以自取其乐之道为借口,成功引诱王三巧上钩,失去了贞节[2]。
蒋兴哥对王三巧的尊重和理解对她性格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当蒋兴哥在外遇见珍珠衫,并知晓了三巧与陈商的事后,他急忙赶回家中,内心虽愤怒不已,临到家门却落泪悔恨自己不该将三巧留在家中,酿成如此后果。在休书中,他为了维护三巧的尊严,不忍明言其过错,还将十六箱嫁妆送回。即使分开,蒋兴哥对三巧的爱和呵护却始终如一,他的宽容甚至让三巧无地自容,差点寻了短见。
正是这些外在因素和内在心理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王三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形成和发展。她的家庭培养了她知书达理的智慧和浪漫率性的性格,她本着对爱情的追求与丈夫恩爱非常,但又在丈夫迟迟不归的空等后受到他人的引诱而背叛了婚姻,但家庭和丈夫始终对她抱以宽容的态度,因此三巧有机会重新追随内心对情感自由的渴望。
三、进步性和落后性
王三巧的人物形象既有进步性,也有落后性,读者要辩证地看待,从人物的正反两面把握作品的艺术价值,感受作者对人物寄托的理想和价值。
1. 进步性
她的进步性有三点:一是观念进步,她赞同一夫一妻制度;二是突破封建礼教束缚;三是追求情感自由。这三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显示出女性身份和人格的极大进步,超越了现实社会对女性的种种约束,尊重了人性,反映了创作主体对封建社会男女关系不平等、女性深受纲常伦理约束和迫害这一问题的反思,极具进步意义,也反映了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女性地位的理解较宋代有了进步,以更加合乎人性的视角来看待男女关系。
观念进步这一点,从小说中王三巧对薛婆子将小女儿嫁给他人做偏房的态度可以看出。“你老人家女儿多,不把来当事了。本乡本土少什么一夫一妇的,怎舍得与异乡人做小?”[2]三巧主张一夫一妻制,一定程度上是她认同男女平等的表现。王公给女儿操办婚事时,全按照正规的礼数,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看出他对女儿婚姻的重视。这种主张也反映了明代部分地区婚姻观念的进步,婚姻不再是男性对女性的占有,而是一种相互尊重和扶持的关系。
突破封建礼教是指王三巧突破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正视人的欲望。“明代是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后确立统治地位的关键时期,伦理道德意识逐渐加强,妇女贞洁受到空前重视。”[3]同时,明代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人的本体意识得到解放,在封建伦理极端压抑的情况下,人的心理会产生更激烈的反叛。王三巧逐渐突破了内心纲常伦理的束缚,放纵情欲,失去了贞节,虽然在伦理上仍犯了禁忌,坏了规章,但她敢于突破不合理社会规范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作者给予了王三巧充分的自由,用行动展示了女性的爱恨情仇,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和工具,而是鲜活灵动的有着炽热情感的人。她被丈夫休妻后,并没有长期陷入自我谴责中或被外界舆论裹挟,而是坦然接受结局,另择良缘改嫁。这体现了她对感情的尊重,以及自身倔强和果敢的个性。王三巧嫁给蒋兴哥后,两人举案齐眉、恩爱非常,令众人艳羡不已,当蒋兴哥提出要外出经商,三巧在等待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倾注了无尽的思念,盼望着他的归来;当三巧对陈商产生感情后,她甚至愿意为了爱情放弃原本的生活,追随陈商,哪怕嫁给他当妾室,临走前还将珍珠衫作为信物赠予陈商,约定好相见时间;在收到蒋兴哥的休书后,她悔不当初,决心改嫁他人,重新开始。这两段关系都体现了王三巧对情感自由的追求,对平等婚恋关系的渴望。王三巧的爱是十分热烈的,往往不顾一切,为了爱情她可以放弃世俗的规范和自己的原则,这突破了当时人们对于女性的印象,是大胆追求情感自由的典型。这些性格上的进步性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2.落后性
王三巧人物形象的落后性也有两点:一是过度地放纵情欲;二是追求情感自由,但不追求自我的独立。人物的弱点使其形象更加鲜活真實,反衬其闪光点的可贵,这使得人物更加立体。
过度地放纵情欲,所谓“情”即原始欲望,“智”即合规范性的理性。若人只被情欲操控,就成了原始人。在肯定王三巧大胆反叛精神的同时,也要看到她性格中的落后性,她过度放纵情欲,忽视家庭责任。这样无节制的放纵和对基本道德伦理的忽视,必然会导致家庭秩序的混乱。无论男女,都应该合理控制自己的欲望,维护婚姻的尊严。
追求情感自由,但不追求自我独立,这说明三巧并不是彻底的反叛者,具有一定的妥协性。虽然她赞同一夫一妻制度,主张夫妻双方人格平等,但仍然两次妥协做妾,两次放弃了婚姻中女性的独立地位。第一次,改嫁给了南京的吴进士做妾,这是一种顺从和屈服,也是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无奈之举,尚且可以被原谅。结合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伦理规范来看待,封建社会对女子本就更苛刻,女子不仅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还被纲常伦理所约束,这极易使封建社会的女性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像王三巧这种改嫁的女子,难以同时顾全各种因素,只能向现实妥协。而第二次她只因放不下和蒋兴哥往日的旧情,再次嫁给蒋兴哥做妾,一夫二妇共处一室。正如小说结尾所说,“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2]。由此可见,王三巧的行为受情感支配,是极致的情感自由主义者,可以为了情感而放弃平等的夫妻关系和自我的独立性,她对封建规范的反抗具有妥协性。
四、结语
“贞操观念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规范,最初的产生仅限于婚姻之内,是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家庭并生育纯正父系血统的继承人。然而自宋代以来,它却蜕化为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越来越严重地体现着女性是男性私有物的观念。”[5]男性可以娶妻纳妾,却对女性进行单方面的摧残和约束,称其婚姻外的性关系为“失节”,将女性视作一种工具进行操控,这种观念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话语体系里。王三巧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她用行动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规范,敢于正视自己的欲望和情感。在小说里,作者态度鲜明,没有过多刻画封建礼教将如何惩罚三巧,就连蒋兴哥和三巧的父母都给予其同情和理解,作者将这些人物塑造得极其宽容,给予了三巧充分的尊重。而对她自己而言,在内在心理和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她由恪守礼法走向追求情感自由,她的行为也是对思想牢笼的冲破,是其自我个性的飞扬,也是与封建礼法的对抗。这一反叛性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在明代还是当下,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启发人们对于女性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深深的思索,不断探寻女性解放道路,争取平等和自由。
参考文献
[1] 冯梦龙.喻世明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 米舜.至情至性珍珠衫——《蔣兴哥重会珍珠衫》的生命美学之光[J].衡水学院学报,2006(2).
[3] 罗荣.“三言”中的人物形象系列及其文化内涵[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
[4] 黄睿清,于天.走进封建妇女的内心世界——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王三巧之心理人格解剖[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1).
[5] 刘军华.在真情与理性之间徘徊——论“三言”女性形象的矛盾性[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3(3).
(责任编辑 陆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