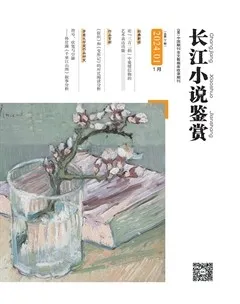《西游记》中罗刹女的形象源流与特性
孙嘉艺
[摘 要] 本文认为罗刹女从最初以恶女的形象传入中国,而后演变成《西游记》中复杂立体的形象是由于世代累积与时代特色双重因素所导致的。罗刹女的独特形象是明代中后期世情小说的广泛传播以及社会所倡导的儒家道德礼教两者交织形成的。本文通过对罗刹女的身份归类,梳理其形象、故事原型在流传中的变化,辨析明代中后期情与欲的解放和礼教规训对罗刹女形象塑造的影响。
[关键词] 罗刹女 鬼子母 世情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1-0014-04
一、罗刹女形象的多重来源
明代吴承恩版《西游记》的故事以师徒四人为中心,而铁扇公主的形象很容易被学者忽略。铁扇公主亦叫罗刹女,是外来文学形象在进入中国后,经过多个朝代的浸润最终形成了《西游记》中复杂多元的女妖。
罗刹二字的梵文名字为raksasa,又写作罗刹娑、罗乞察娑、阿落刹娑,属于印度神话中的恶魔。最早见于《梨俱吠陀》,慧琳《一切经音义》云:“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畏也。”[1]罗刹成为恶人的代名词,即使在后来被佛教纳入后,罗刹二字所代表的依旧是恶魔的形象。在佛教经书中,十罗刹女指的是守护诵持《法华经》者的十位罗刹女,“是十罗刹女,与鬼子母并其子及眷属,俱诣佛所,同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亦欲拥护读诵受持《法华经》者,除其衰患。若有伺求法师短者,令不得便”[2]。其形象具有一定的“佛性”,这便与前者对女罗刹的描述有了区别,形成了善恶交织的特点。
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第十九出《铁扇凶威》中的罗刹女因为与王母发生争执自行生活在铁嵯山,其形象与《西游记》中的铁扇公主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所塑造出的性格都是刚烈狂傲的。《铁扇凶威》中的铁扇女敢在醉酒后与王母争执,展现出其刚烈张狂的性格本色,“妾身铁扇公主是也,乃风部下祖师,但是风神皆属我掌管。为带酒与王母相争,反却天宫,在此铁嵯山居住,到大来是快活也呵”。《西游记》中的罗刹女“手提宝剑怒声高,凶比月婆容貌”[3],不难看出罗刹女是一个气傲心高,敢与男子一拼高下的人物。而在书中她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人性与母性,这一特征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鬼子母。
《西游记》中罗刹女的形象和故事结构都与佛经中鬼子母的内容和传播息息相关。鬼子母,梵文为Hariti,译名为欢喜母、爱子母、暴恶母,早期的佛经中有关鬼子母的描述可以用血腥可怖、暴力邪恶来概括,她们基本没有具体的形象描述,但从文字中依旧能感受到鬼子母是恶鬼、邪祟的代表,如“降鬼诸神王,及降鬼子母。如彼瞰人鬼,取人指作鬉,后复欲害母,然佛取降之”[4]。
鬼子母流入中国后形象逐渐丰富,具有暴力血腥和爱子求子双重性。其爱子的祈福特性在经书中有体现,《增以阿含经》云:“求祷天神,请求日、月、天神、地神、鬼子母、四天王、二十八大神鬼王、释及梵天、山神、树神、五道之神、树木、药草,靡处不周,皆悉归命,见赐一男儿。”[5]到后来,《佛说鬼子母经》:“是母便复行盗人子,来人舍中,不见其子,便舍他人子,不敢复杀。便行索其子,遍舍中不知其子处。便出行至街里遍城中不得,复出城外索不得,便入城行道啼哭。如是十日,母便狂,被发人市,啼哭自扑仰天,大呼为狂梁语,亦不能复饮食。”[6]鬼子母的形象得到第一次深化,在血腥食人子的基础上,细致描述了其形象和内心活动,突出其强烈爱子的母性。
在唐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中,鬼子母的形象进一步完善,其美艳的形象特征被体现出来。鬼子母前世有“药叉女”和“牧牛女”两个来源,使得她拥有美艳、慈爱和残暴这些矛盾冲突的特色。从汉代到隋唐五代时期,鬼子母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原型中那些血腥暴力的因素通过民间的流传与主流思想的规训逐渐被淡化。
直到宋代的部分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将鬼子母形容为悍妇、妒妇的描写,《本事诗·嘲戏》云:“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妻桿妒,谈畏之如严君。尝谓人:妻有可畏三:少妙之时,视之如生菩萨。及男女满前,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妆粉或黑,视之如鸠盘荼,安有人不畏鸠盘荼?”[7]这时的鬼子母身上添加了彪悍、善妒的特点。
至此为止,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罗刹女的形象特点均可以从罗刹和鬼子母中得到考证,由此可见铁扇公主这一形象来源甚是久远,并且由多种因素和个性混合而成,她的形象不再单一而是多元立体的,糅合了罗刹的善恶交织、狂傲不羁和鬼子母的血腥残暴、美艳慈爱、彪悍善妒等特质。因此,《西游记》中的罗刹女蕴含着道性、人性、母性、妖性和佛性多重性质。
二、罗刹女故事的流传
笔者认为对吴承恩版《西游记》中罗刹女故事影响最大的原型是鬼子母相关传说。鬼子母的故事在佛经中屡次见到,在《大唐西域记》和《取经诗话》中也被提及,而到了明代吴承恩版的《西游记》中却不再詳细讲述鬼子母的故事。虽然书中没有完整回目描述其故事内容,但鬼子母故事被拆分到多个回目中,例如第六十五回《妖邪假设雷音寺 四众皆遭大厄难》中就出现了与“鬼母揭钵”相关的内容,第七十八回《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中取众多小儿心脏和满城婴儿的情节。
《西游记杂剧》中,红孩儿将鬼子母与罗刹女联系到了一起,“不知此非妖怪,这妇人我收在座下,作诸天的,缘法未到,谓之鬼子母,他的小孩儿唤做爱奴儿”。这段情节与吴承恩版《西游记》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观音收服红孩儿情节相似。而书中的铁扇公主为爱子复仇与孙悟空大打出手,不肯借出芭蕉扇的情节也符合“鬼子母揭钵”中为解救儿子与佛祖相争的故事特点。《西游记》第五十九回:“罗刹道你这泼猴!既有兄弟之亲,如何坑陷我子?”[3]“你这个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伤性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3]“伸过头来,等我砍上几剑!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与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见阎君。”[3]这里的罗刹女虽然不再主动去和佛祖争斗,但在语言中依旧能看到对失去爱子这件事情的复仇心理。
《西游记》中罗刹女出场三个回目,在形象塑造和故事改编上均有着浓厚的历史因素。在形象上有着深厚的宗教意味,从神女到恶女,从祈福到暴力,从美艳到丑恶,从慈爱到妒妇,从鬼子母故事扩充到多个回目,明代吴承恩版《西游记》的罗刹女也从单一的性格形象特征变为了复杂多元的形象,由于其来源的杂糅多样导致书中的罗刹女比其他妖怪有了更深刻的特性,让她身上蕴含着妖性、母性、佛性与人性,在与牛魔王、红孩儿组成家庭后更体现出明代特有的情感、婚姻和妇女观。
三、明代世情道德对罗刹女的塑造
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随之产生的文化下移也加快了速度。随着人欲的发现与解放,人们对于“情”的描写更加直白大胆,受“心学”的启发,情与性的描写不再是文学中需要避讳的内容,这也赋予了罗刹女在情欲上的释放。但明代仍是一个要求女子三从四德、遵守女德、恪守妇道的社会,文学作品塑造女性形象时依旧体现了社会整体的妇女观。罗刹女在此基础上,也被赋予了贤惠持家、顺从丈夫、恪守夫妻之德烙印。
吴承恩版《西游记》第六十回中写道:
面赤似夭桃,身摇如嫩柳。絮絮叨叨话语多,捻捻掐掐风情有。时见掠云鬟,又见轮尖手。几番常把脚儿跷,数次每将衣袖抖。粉项自然低,蛮腰渐觉扭。合欢言语不曾丢,酥胸半露松金钮。醉来真个玉山颓,饧眼摩娑几弄丑。[3]
小说中对于罗刹女的“投怀送抱”有着较为详尽的描写,与之前罗刹女形象对比,加入了更多的情色方面的叙述,这与明代中后期情性思潮的解放密切相关。受王守仁及其“心学”的影响,人们逐渐从理学的钳制中解放了出来。这时的人们不再对人欲、情欲的表达有过多的忌讳,开始正视人天性中就带有的对欲望的渴求。而书中罗刹女对孙悟空所谓的暧昧行为,体现了对牛魔王的思念与夫妻之间的欲求,能将这种心理和行为描述出来,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人们对于情欲正确表达的需要。
随着元明两朝文学文化的大众化,鬼子母一改之前的美艳、慈爱的形象,而被掺杂了更多有关丑陋、情色的情节。如《续金瓶梅》:“风火来烧,白牙象战败鬼子母”[8],又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面皮靛样,抹上粉犹是乌青;嘴唇铁般,涂尽脂还同深紫。稀稀疏疏,两边蝉翼鬓半黑半黄;歪歪踹踹,双只牵蒲脚不男不女”[9],这与隋唐时期美丽慈爱的鬼子母形成鲜明对比。宋代的《太平广记》中,黑叟因为画壁上鬼子母的面容不够娇美,甚至不如自己的妻子,于是把墙上的面容撬下来,文献中对其妻子的形容“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10],这侧面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鬼子母的想象是娇艳可爱的。吴承恩版《西游记》对罗刹女的外貌、行为、语言等描写也突出了其彪悍、粗犷的特征。
元明两朝对于罗刹女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使得其情欲方面更加突出的原因基于两点:首先,鬼子母在以往的宗教信仰中本身带有多子、求子的含义,这与性关联密切,随着文学的世俗化以及明代对人性的解放,鬼子母以及延伸形象罗刹女也逐渐成为情色欲望的代名词;其次,鬼子母的原型从产生初期就包含着血腥暴力残忍的因素,佛经中的鬼子母本身就以食人子为主要活动,后来的慈爱、求子等祈福功用均是根据人们的需要而衍生出来的,所以元明两代在描述鬼子母及罗刹女时用丑陋、青面、垢发等词属于正常的描述。如小说中“手提宝剑怒声高,凶比月婆容貌”[3]便是罗刹女的第一次亮相。
《西游记》中的罗刹女是封建思想制度下的牺牲者,体现了以父权为核心的社会中女性生存的现状。书中第六十回牛魔王在介绍山妻罗刹女时:“那芭蕉洞虽是僻静,却清幽自在。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个得道的女仙,却是家门严谨,内无一尺之童。”[3]
这表明罗刹女自幼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接受了充足的道德礼教的训导和熏陶。明代常用贤惠敬顺来要求女子,“从”即“顺”,所谓的“三从”不过是强制女性从父、从夫、从子。儒家的礼法将“顺从”作为衡量女子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这一思想在《西游记》中罗刹女身上得到了体现,“男儿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自古道:‘妻者,齐也。夫乃养身之父,讲甚么谢”。
罗刹女在言行中,也认为男子是主导自己一切的根本,自身价值的体现需要通过男子来实现。书中的罗刹女安心修道,拥有自己的府邸,完全是一个在经济物质上可以独立的形象,而其思想依旧被深深钳制在牛魔王以及封建思想之下。书中的牛魔王在外与玉面公主居住,而罗刹女对此却选择忍气吞声,守候徒有其表的婚姻。不得不说,罗刹女是明代女子接受儒家礼教道德驯化后的形象集合,在极度压抑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蜷缩在闺房之中。
《烈女传》中,明代女子的数量是最多的,在礼教和父权的控制下,女子必须严守贞洁,这是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夫死不嫁”是男子对女子节操的控制也是衡量女子是否优秀的标准,它不仅将女性压抑在绝望的空间里,也在精神上阻碍其发展。即便是在明代中后期人性与性欲有所解放,女子依旧无法自由表达自己正常的人性需求。书中孙悟空假扮牛魔王,企圖骗取芭蕉扇,而在罗刹女主动献情后,却对罗刹女的行为嗤之以鼻:“罗刹女!你看看我可是你亲老公!就把我缠了这许多丑勾当!不羞!不羞!”[3]
孙行者调戏罗刹女这一情节早在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就有体现,而在吴承恩版《西游记》中,这一情节被丰富,侧面展现了明代对于女子守节的要求。《西游记》中的牛魔王可以抛下山妻,自寻小妾欢乐自在,而罗刹女却是“家门严谨,内无一尺之童”[3],在无法识破假扮丈夫的孙行者时,由于长时间的思念,她主动献情,却被形容为“丑勾当”。两相对比下,明代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对女性的要求显然更为苛刻。
从汉字产生时,“女”字的形象内涵就被打上了恭顺服从的烙印。在儒家文化的指导下,这一特点随着父权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沉淀逐渐极端化。在这一现实下,明代女子依旧保持着自卑自贱的认知,除了伦理道德对她们的教化作用外,她们对自身的位置判断以及认知也是如此,罗刹女在面对不公平的对待时仍对空壳婚姻抱有幻想,她在迷失自我的同时思想上充满了浓厚的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