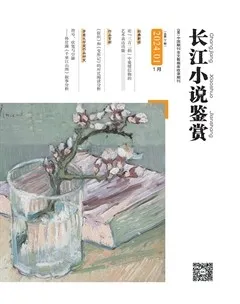贾宝玉的“厌男”言说与现实交往矛盾
严佳丽
[摘 要] 贾宝玉以自我言说的方式阐明“女儿尊贵”的价值理念,将男性作为推尊女儿的参照对象,置于价值尺度的另一极端,表现出“厌男”的倾向。但考察其与男性的交往,却与作为知己、陪伴者、解围人的部分男性保持着或亲密或自然的交往状态,与言说存在明显的矛盾。作者正是以矛盾的文学表达,树立宝玉“护花使者”的人物形象,在阐明个人社会理想的同时展现小说人物自身的精神诉求和现实利害考量,使人物更加立体丰满。
[关键词] 贾宝玉 “厌男” 文学矛盾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1-0009-05
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核心人物,不仅是串联情节的线索,也是解锁小说题旨的关键。自“新红学”产生以来,有关贾宝玉的研究堪称细致入微。其中宝玉对女性的态度作为其性格的突出成分,最早得到学界关注,以“女清男浊”“女儿三变”等观念为核心的“女儿观”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1]。值得注意的是,在宝玉推尊女儿的言论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男性的厌弃。作者似乎有意将男女两性对立,通过贬斥一方的方式抬高另一方的地位,从而使人物在言说上呈现出“厌男”的倾向。然而,考察其现实交往情况,却不难发现,宝玉在理论言说与实际交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贾宝玉“厌男”之“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本文试图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阐明贾宝玉的“厌男”实质,并进一步阐述人物言行矛盾所具备的文学意义。
一、宝玉“厌男”的自我言说
贾宝玉“厌男”倾向来源于人物的自我言说。《红楼梦》中,宝玉每一次关于女儿神圣的言论几乎都以男儿污浊为对比,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始终成为其推尊女儿的参照对象。可以说,从宝玉的自我言说来看,他已然将男女两性完全对立,并置于价值评判的两极,使得男女两性形成不可调和的天然矛盾。
1.总体评价:“泥”与“须眉浊物”
“水、泥”论是贾宝玉关于两性认知的核心理论,也是决定其两性态度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并非由宝玉直接阐发,而是出自旁人的转述。第二回中,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2]
这是宝玉对于两性的论断。在其判断中,男女两性的“浊”“清”源于先天差异,是先在的、自然的,且不可后天弥补。其言外之意是,对于男儿来说,即使作为个体,后天如何修饰自身都无法突破先天的缺陷。先在的价值判断似乎决定了宝玉的“厌男”应当是无差别地、普遍性地厌弃男性整体。况且,宝玉的这些言论能够被贾府的外人——周瑞家的女婿知晓,排除“水、泥”论本身新鲜、惊骇的成分外,也可以想见宝玉言说的频率之高。
“须眉浊物”是贾宝玉在“水、泥论”的基础上引申出的对一切男性的通称。“须眉”二字本出自《汉书·张良传》:
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3]
古时男子以胡须眉毛之稠密为美,“须眉”二字于是被用以指称男性,考察其源出语境,不难发现,称男子为“须眉”具有鲜明的褒义色彩。宝玉却无视传统文化语境,以“水、泥”论为基准,将“须眉”与带有明显贬义的“浊物”二字相结合,用来指称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男子。全书中关于“须眉浊物”的言说情景如下:
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豎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
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
宝玉听说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说:“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2]
“须眉浊物”在小说中共出现了四次,其中三次都出自宝玉的自我言说。考察词语运用的语境,不难发现,第一处和第二处的语意都偏向于热衷功名、求取进仕的读书人,而第三处宝玉的自称则直接将语意扩大,不仅指向来厌恶的士大夫诸男人,也包括以自身为代表的厌弃功名、无意仕途的“混世魔王”或“离经叛道”者。可见,宝玉语境下的“须眉浊物”一词,摆脱了传统文化语境中“须眉”的褒义色彩,以“水、泥”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为基准,侧重于强调“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之“浊”,“须眉浊物”已然成为宝玉指称全体男性的总代名。
2.特定评价:“禄蠹”
除“须眉浊物”的总体评价外,宝玉还对于部分男性做出了特定的价值评判,即“禄蠹”。小说首先通过宝玉的身边人——袭人的转述提出了“禄蠹”的概念: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2]
此事发生在第十九回,袭人假意离开贾府,借机规劝宝玉三件事。第二件便提及“禄蠹”,袭人既然郑重其事地以此劝告,可见宝玉是常将这一评价挂在嘴边的。从袭人的描述来看,宝玉认为的“禄蠹”实际上就是“读书上进的人”,更准确地说,是读书上进以此谋取功名前程之人,这与宝玉排斥仕途经济之路的行为相一致。
书中另外两处提及“禄蠹”均出自甄宝玉、贾宝玉见面一回:
贾宝玉听这话头又近了碌蠹的旧套。
宝玉道:“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
宝玉道:“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2]
“禄蠹”主要作为贾宝玉对甄宝玉的特定评价。此处将“禄蠹”的语义具象化,再次明确了在贾宝玉的评价体系中,思想重于外貌,而专营仕途经济、功名利禄的读书人更是一众“须眉浊物”中尤为可厌可弃的。
小说通过宝玉的一次次自我言说,呈现人物的价值判断。总的来看,在其价值评判思想中,以“水、泥”论为核心,男女两性作为二元对立的矛盾因素,存在着先天固有的“清浊”差异,女儿尊贵的对立面必然是男儿污浊,两者位列于价值尺度的两端。在贬斥男性的整体语境下,对于热衷仕途经济的“禄蠹”则更为厌恶。而这本应当成为其行动的理论指导。
二、现实情况下的男性交往与“厌男”实质
考察小说中宝玉的现实交往,就男性人物而言,除了对以贾雨村为代表的“禄蠹”之人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外,与其他男性似乎并未因其“须眉浊物”的先天缺陷而刻意疏远。反而,与男性交往时,宝玉有时表现出或亲近或自然的状态。这些男子或如秦钟等人具有女性化的特征,或如茗烟等小厮是日常的陪伴者,或如詹光等清客相公作为宝玉面对贾政时的解围人。
1.女性化
小说中,宝玉与四位男性有过惺惺相惜的挚友之情,分别为秦钟、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四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差异甚大,却都能与宝玉成为知己之交。考察其中的缘由,便不难发现四人身上都具备宝玉所推尊的女性化特征。
第一,在外貌上,四人均面容秀丽、风流潇洒,如秦钟之“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北静王之“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柳湘莲之“生得又美”;蒋玉菡之“鲜润如出水芙蕖,飘扬似临风玉树”。小说对四人外貌举止的描述,都并非传统意义上对男子阳刚正气的赞赏,而具有典型的阴柔之美,表现出女性化的特征,与宝玉推尊女儿的价值观相符。
第二,在思想性格上,四人并不以世俗男子的人生追求为目标,表现出有别于一般男子的心性品格。秦钟实为“情种”,不为礼法束缚,尚情重情;北静王虽出身高贵,却“不以官俗国体所缚”,自觉远离朝政喧嚣;柳湘莲则纵情任性、放荡不羁,却于漂泊浪迹时仍不忘旧友;蒋玉菡“情赠茜罗香”,与宝玉的知己之交亦建立在一个“情”字之上。正是由于四人在心性品格上重情重义、至情至性,不以利益为尚,才能与宝玉成为知己之交。进一步来说,宝玉与四人之间身份地位虽差异巨大,但相同的品性却展示着“异地则同”的人生选择,这也是彼此能够惺惺相惜、成为挚友的关键[4]。
2.陪伴者
宝玉作为贵族公子,虽常爱在内帷厮混,但在外也少不了小厮的陪伴跟随,其中即以宝玉的贴身书童茗烟为代表。作为在外的陪伴者,宝玉对同为男子的茗烟亦表现出亲近维护的态度。
第九回中,茗烟大展身手,与金荣厮斗。事后,宝玉出言维护茗烟:“茗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打伙儿打了茗烟,连秦钟的头也打破了。”茗烟作为跟随者,实际上是宝玉权力的延伸,与宝玉处于同一个阵营,茗烟自然是时刻维护主子。而作为权力的赋予者,宝玉对茗烟的出言相助也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同时,由于身份的限制,宝玉不得不面对出行不便的问题。此时,茗烟便作为在外的打探者与执行者,成为宝玉耳目的延伸,两人自然表现出亲近的交往关系。如秦钟之死是茗烟前来告知,刘姥姥胡诌的茗玉小姐之庙是茗烟前去打听,宝玉祭拜金钏儿之事是茗烟受命准备,等等。可以说,茗烟作为宝玉的小厮,是其想法的落实者,茗烟的行动已然成为宝玉行动的一部分。何况茗烟不时有意做出讨好宝玉的言行,如将“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脚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替其解闷;如在宝玉祭拜金钏儿时,见宝玉伤心,说出“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再不可又托生这須眉浊物”等有意迎合宝玉的话。总之,无论宝玉是否从心底认同茗烟,但就实际情况来看,茗烟作为贴身书童,不仅对宝玉言听计从,而且刻意讨好。正因如此,宝玉确实将一些不为礼法认可的事情交付茗烟,十分信赖,并对其表现出亲近的友善态度[5]。
此外,在宝玉摆脱父亲考学时,众小厮能够“拦腰抱住”,讨要彩头,不由分说地“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扇囊”“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也可见宝玉与小厮间的亲近。
3.解围人
如果说与秦钟等具有女性特征的男性交友,是宝玉推尊女儿的价值观使然,那么与以茗烟为代表的小厮亲近则出于现实的自然。另外,贾府中还有一群围绕在贾政身边的清客相公,他们为谋生不仅对贾政卑躬屈膝,而且成为权势的帮凶[6]。就宝玉的人生价值观而言,这类人本应成为其厌弃的对象,但小说在行文过程中,却并未刻意展现宝玉与他们交往时的嫉恶如仇,反而带有应酬交往的世故意味。
第八回,宝玉为避免遇着贾政,刻意绕路,却不想遇见贾政的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小说对三人相遇时的表现做了详细描述:
二人走来,一见了宝玉,便都笑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说着,请了安,又问好,劳叨半日,方才走开……二人点头道:“老爷在梦坡斋小书房里歇中觉呢,不妨事的。”一面说,一面走了。说的宝玉也笑了。[2]
这里首次描写了宝玉与贾府清客相公的私下交往。《红楼梦》的作者向来偏好于用人名谐音来暗示人物品格,此处“詹光”谐音“沾光”,“单聘仁”谐音“善骗人”,对二人之类的清客相公充满蔑视与鄙夷[7]。但是,作为小说理想人物的宝玉在与此类阿谀奉承之人相遇时,其反应却并没有表现出“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时的厌弃。反而是任由此种“须眉浊物”“抱住腰”“携着手”,还听了他们的半日唠叨。最后,当二人传递出贾政午睡的讯息时,宝玉甚至还笑了。试想,向来“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的宝玉,能够听任两人的刻意亲近与无意义的唠叨,大概是为了探听贾政的消息,从而使得自己免于被父亲责备。不得不说,与此类清客相公的交往应酬,是宝玉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有意选择。
第十七回将众清客对宝玉的相助展现得淋漓尽致:
原来众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功业进益如何,只将些俗套来敷衍。
众人听了,都赞道:“是极!二世兄天分高,才情远,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
众人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
众客道:“议论的极是,其奈他何。”
众人都哄然叫妙。
众人不知其意,只当他受了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尽词穷了,再要考难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来,倒不便。[2]
一众清客相公对宝玉所题“对额”,无不表现出赞赏的态度,而且在贾政面前察言观色,多次出言替宝玉解围。其中,自然有阿谀奉承讨好贾政的成分,但客观上众人的行为确实使宝玉脱离窘境、免于责打。正是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考量,或为方便探听消息,或为危急关头解围,宝玉与贾政身边的清客相公保持着自然的交往状态。
总的来看,即使在价值取向上,宝玉持有“男子污浊”的观念,但在现实情况中,却与作为知己、陪伴者、解围人的部分男性保持着或亲密或自然的交往状态。与作为知己的秦钟等人的交往,偏向于精神诉求的实现,而与作为陪伴者、解围人的小厮以及清客相公等人的往来,则更倾向于现实利害的考虑。考察宝玉价值阐述与现实交往之间的矛盾,“厌男”的实质并非对性别之“男”的偏见而是对男性气质的厌弃,更准确地来说,是对社会期待下追求功名、热衷仕途的男性期待的厌弃。小说有意突出性别上的男女对立,强调宝玉的“女儿情结”,最终指向的是对社会规训的批判。所以说,与其将宝玉称为一个“性别的叛逆者”,不如称之为“社会的反叛者”更接近于这一人物的内在价值。
三、矛盾表达的文学意义
《红楼梦》是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呕心沥血之作,如此明显的人物言行矛盾不可能不引起关注,作者的有意保留,使得这一矛盾具有内在的文学意义。与女儿态度的坚定不移相比,宝玉现实的男性态度显得更为柔和执中,表现出作为小说理想人物的世故一面。
1.确立人物核心:护花使者
贾宝玉的“女儿观”作为其典型性格,不仅是“护花”行为的价值指南,也是树立人物特殊性的核心理论。宝玉的“厌男”言说是作者为凸显人物核心有意设置的艺术对照,从而提升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作者早在宝玉正式出场之前便安排冷子兴通过转述的方式传达其价值理念,从而使宝玉的“水、泥”论具有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不得不承认,一味强调女儿尊贵的言论不如有意设置男女两性的矛盾对立来得惊世骇俗。作者一开始便有意将男女两性对立,为强调主人公宝玉“护花”的典型性格,以男子为参照对象,在推尊女儿的同时,不得不将男子置于价值衡量尺度的另一端,从而使得宝玉在自我言说上呈现出“厌男”倾向。
同时,小说在行文过程中通过宝玉的言行不断强化其核心性格。无论是对宝黛等姐妹的体贴关照,还是对袭人、晴雯、龄官等人的关心,都是其“女儿观”的行为实践。而诸如秦钟等具有女性化特征的男性人物,则是作者更进一步的有意设置,目的是强调宝玉作为“护花使者”的核心品格。小說通过性别的错置,有意模糊男女性别界限,进一步凸显宝玉作为小说理想人物的重“情”思想。表面上人物理论言说与行为实践之间产生矛盾,实际上,原先简单的性别对立被提升为一种社会气质的对立,即宝玉之“厌男”并非简单的性别偏见,而是对社会规训下男性气质的批判,使得小说展现出更深意义上的社会批判。
2.丰满人物形象:自我矛盾
矛盾使得小说文本具备更大的艺术张力,人物的自我矛盾则使得其获得现实意义上的鲜活生命力。作者正是通过宝玉在核心问题上的言行矛盾,凸显理想人物的世俗一面。如果说,勇于宣扬“水、泥”论以及“女儿尊贵”论的贾宝玉是大胆的叛逆者,那么基于现实、迫于利害不得不与“须眉浊物”往来的宝玉则是现实的生活者。
关于宝玉在男女两性价值上的叛逆之举,无须赘言。正因为如此,才有冷子兴言说荣国府的讥笑,才有王夫人“混世魔王”的告诫,才有金钏儿投井以及之后的种种祸端,此类不为世俗认可的言行举止展现着宝玉典型的叛逆性格,凸显着这一人物敢于反叛、追求理想的艺术魅力,其中寄托着作者个人的思想价值,宝玉一次次关于男女两性的价值言说,也正是作者对社会理想的一次次呼号。
然而,完全意义上的理想人物将成为作者的“传声筒”,从而失去自身的真实性,宝玉“厌男”的言行矛盾正体现着这一人物的生命力。如果说大胆的言说是宝玉反叛自身的挑战,那么基于现实、迫于利害的男性交往则是其回归生存现实的妥协。与茗烟等小厮的自然交往是身为贵族公子的成长环境使然,身份局限所导致的不自由,使得宝玉不得不通过茗烟等小厮获得权力的延伸;与各清客相公的交往,则是为探听贾政消息、免于责打的有意之举,体现出理想主义者迫于现实利害的世故一面。小说正是通过宝玉言行的内在矛盾,展现着人物的生存现实,使得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宝玉始终能够立足现实,表现出人物自身的真实与鲜活。
贾宝玉作为《红楼梦》“女儿国”的守护者,其自我言说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物通过男女两性天然对立的言论,强调女儿尊贵的同时,不免表现出一定的“厌男”倾向。然而,考察人物的现实交往,却与作为知己、陪伴者、解围人的部分男性保持着或亲近或自然的状态,呈现出价值宣言与实际行动的矛盾。如果说,宝玉推尊女性的“女儿观”是作者社会理想的自我宣言,那么,现实中的男性交往则显示着小说人物的精神诉求与现实考量,展现着人物自身的鲜活。作者正是通过宝玉激烈的言说表明其行动的价值指南,在树立人物核心的同时,传达个人社会理想,但在行文的过程中,又通过宝玉言行的内在矛盾,展现其生存现实以及对种种利害关系的妥协,显示出理想主义者的世俗一面,使小说人物更加立体丰满。
参考文献
[1] 温婧.近十年贾宝玉研究综述[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赵宗来.贾宝玉的厌男情结[J].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5] 高时阔.精明的小厮宝玉的知音——略论茗烟的“贼”[J].南都学坛,2004(6).
[6] 徐永斌.治生视域下《红楼梦》中的文人生态[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7] 孔昭琪.《红楼梦》的谐音双关[J].泰山学院学报,2004(5).
(责任编辑 夏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