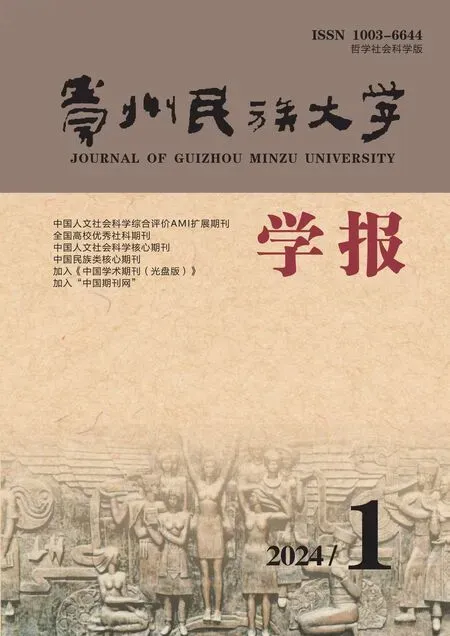非洲语言的声调研究
李 倩
随着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以及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持续开展,对于非洲各国语言的深入研究成为一项重要战略需求。但对于中国大陆学者来说,除了从语言学教科书中了解到的个别语言案例外,非洲语言几乎是陌生的,专门针对非洲语言进行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1)章培智编:《斯瓦希里语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年;程汝祥编著:《简明豪萨语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莱昂:《龚语(Gungbe)声调实验研究——兼论龚语与汉语声调的差别》,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大学,2019年;莱昂、曹文:《龚语的声调及其抑调辅音实验研究》,《第七届世界汉学大会》2021年;莱昂、曹文:《龚语(Gungbe)双音节词中的声调变化》,《中国语音学报》2022年第2期;吴桐:《非洲语言类型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相比之下,由于历史、地缘等原因,西方语言学者对于非洲语言的研究不仅起步早、研究力量集中,而且非洲语言研究在西方主流语言学体系内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许多著名语言学理论或分析框架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以非洲语言中的现象为基础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便是声调。
声调是一种通过音高变化来区分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的现象。结构主义学者以及早期生成音系学(2)Noam Chomsky and Morris Halle,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New York:Harper &Row,1968.的主流观点认为,声调是音段(主要是元音)的固有区别特征之一,并通过将高低特征(即“[+/-高调]”)或者调型曲拱特征(如“[+升调]”“[+降调]”等)加入音段特征矩阵的方式,将声调解析为元音音系表征的维度之一,如一个负载降调的后高元音[u]可以用以下特征矩阵来表征:
这种声调特征的表征形式主要借鉴的是王士元基于汉语中的声调现象所提出的声调特征系统。(3)William S.-Y.Wang,“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vol.33,no.2,1967.但汉语(包括普通话和方言)与非洲语言一般认为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前者为曲拱型声调语言(contour tone language),而后者属于高低型声调语言(register tone language),曲拱的形状一般不认为是高低型声调的主要特征。(4)Kenneth L.Pike,Tone Languag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48.因此,类似“[+降调]”这样的曲拱形状特征也就无法对高低型声调进行准确的音系表征。此外,由于非洲语言中存在大量声调的语境变异(contextual variation)现象,这种整体表征声调特征的做法无法体现由于譬如前后声调环境影响带来的变调现象,因而在非洲语言声调的实际分析操作中显得捉襟见肘。(5)Larry M.Hyman,“Issues in African Language Phonology”,UC Berkeley PhonLab Annual Report, vol.4,2008.但如果将“[+降调]”拆解成“[+高调][-高调]”,就又打破了区别特征单列呈现的统一形式。
为解决以上问题,戈德史密斯(Goldsmith)提出“自主音段”的概念,即将声调层(tonal tier)视作是与音段层(segmental tier)平行独立表征的“半自主”特征层,与音段层之间只存在某种抽象连接。在此框架下,由各种音系规则导致某个声调特征发生变化的情况将不会对音段层的特征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这就是自主音段音系学(Autosegmental Phonology)提出的由来。(6)John Goldsmith,Autosegmental Phonology,Ph.D.dissertation,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76.自主音段音系学提出的声调表征方式在解释非洲语言中的许多声调现象时体现出了一定优势(7)②⑦Moira Yip,To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自主音段音系学也自此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时至今日,有关非洲语言声调的研究大部分仍是在自主音段音系学的框架下开展的。
对中国学者来说,声调现象并不陌生。但由于汉语与非洲语言在声调类型方面的差异,又或许是由于研究视角与传统的不同,汉语(包括普通话与方言)及相关语言(如泰语、越南语)的声调研究与非洲语言声调研究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自20世纪初刘复、赵元任等前辈将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汉语声调研究领域以来,有关汉语及相关语言声调的研究已得出了大量有关声调(至少是针对曲拱型声调)普遍规律和机制的结论,形成了“大波浪小波浪”理论(8)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页。、Fujisaki模型(9)Hiroya Fujisaki and S.Nagashima,“A Model for the Synthesis of Pitch Contours of Connected Speech”,Annual Report of th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University of Tokyo, vol.28,1969.、Stem-ML模型(10)Chi-Lin Shih and Greg P.Konchanski,“Chinese Tone Modeling with Stem-ML”,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2000.、PENTA模型(11)Yi Xu and Q.Emily Wang,“Pitch Targets and Their Realization:Evidence from Mandarin Chinese”,Speech Communication, vol.33,no.4,2001.等诸多声调相关的重要理论和模型框架。这些基于实证研究数据的理论和模型已逐渐成为理解声调这一人类语言普遍现象的基础,并在前沿的认知神经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产生重要影响。
相比之下,有关非洲语言声调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大多数关于非洲语言声调的研究主要依靠研究者的主观听感。因此,非洲语言声调研究中的许多结论都有待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同时,由于世界上60%—70%的语言都有声调,而非洲声调语言又占了声调语言的大部分,因此汉语声调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相关理论以及现有对于声调现象的认识是否能够普遍适用于人类语言中不同类型的声调现象,还有待通过非洲语言中的证据来检验。对于汉语声调研究者来说,想要全面理解人类语言的声调现象,就不可避免要对非洲语言中的声调现象有所了解和研究。
本文旨在以一个汉语声调研究者的视角,对西方学者有关非洲语言声调现象的研究进行简要介绍,并通过对现有非洲语言声调相关研究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反思,探讨未来进行非洲语言声调研究的可能方向。
一、非洲语言声调现象概况
在非洲大陆使用的2,000余种类型各异的语言中,已知声调语言占了绝大多数(12)Joseph H.Greenberg,The Languages of Af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3; B.Heine and D.Nurse,African Languages:An Introd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这些声调语言大部分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13)②⑤Constance Kutsch Lojenga,“Tone and Tonology in African Languages”,in A.Agwuele and A.Bodomo,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London:Routledge,2018,pp.72-92.。由于非洲语言内部多样性程度较高,目前学界普遍将非洲语言分为四大语系(phyla)(14)Joseph H.Greenberg,The Languages of Af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3.:亚非(Afro-Asiatic)语系、尼罗-撒哈拉(Nilo-Saharan)语系、尼日尔-刚果(Niger-Congo)语系以及科伊桑(Khoisan)语系(15)该类语言是否能统一成一语系学界尚存争论。。根据洛简嘉(Lojenga)的归纳,尼罗-撒哈拉语系以及科伊桑语系几乎全部都是声调语言;尼日尔-刚果语系中除了部分语言——如西大西洋(West-Atlantic)语支——其余大部分也都是声调语言;此外,亚非语系也有部分语言有声调。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某种语言是否被称为声调语言取决于研究者对于声调现象的定义,因此部分语言是否属于声调语言仍有争论的空间。比如亚非语系的一部分语言据称只有一个声调,且并非每个语素上都有声调,(16)Zygmunt Frajzyngier,“Typological Outline of the Afroasiatic Phylum”,in Z.Frajzyngier and E.Shay,eds.,The Afroasiatic Langua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505-624.部分语言中声调对于词汇的区别意义也较为有限(17)Maarten Mous,“Cushitic”,in Z.Frajzyngier and E.Shay,eds.,The Afroasiatic Langua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342-422.,因此也有人认为这些语言实际上属于音高重音型语言(pitch-accent language),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声调语言(18)吴桐:《非洲语言类型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事实上,非洲语言多处于音高重音型语言与典型声调语言之间连续谱的不同位置中(19)Moira Yip,To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4.,音高重音语言有时也被认为是广义声调语言的一个子集(20)Larry M.Hyman,“Tone Systems”,in M.Haspelmath,E.König,W.Oesterreicher and W.Raible,eds.,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vol.2,Berlin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1,pp.1367-1380.。
从声调在语言中的功能来看,在汉语中,声调全部用于区别词汇意义,因此也称为词汇声调(lexical tone),对于声调现象的观察可以局限在词汇的层面。而非洲语言的声调除了能够区别词汇意义之外,还存在大量不区别词汇意义只标记语法功能的语法声调(grammatical tone)(21)G.Tucker Childs,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Languag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03.,例如不少语言都可以仅通过一个高调来标记领属关系(22)Cory R.C.Sheedy,“Grammatical Tones in dó:An Optimality Theoretic Account”,in S.Gessner,S.Oh and K.Shiobara,eds.,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Vancouver: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01,pp.67-74;K.Williamson,“Igbo Associative and Specific Constructions”,in K.Bogers,H.van der Hulst and M.Mous,eds.,The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Suprasegmentals,Dordrecht:Foris,1986,pp.195-208.。此外,非洲语言的声调还与形态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例如尼日尔-刚果语系班图(Bantu)语族和古尔(Gur)语族的不同语言中都广泛存在词缀部分与相邻词根部分声调相反的“反向性”(polarity)现象(23)Douglas Pulleyblank,“Extratonality and Polarity”,Proceedings of the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Volume 2,Stanford:Stanfor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1983,pp.204-216; Michael Cahill,Aspects of the Morphonology and Phonology of Konni,Dallas:SIL International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2007; Arto Anttila and Adams Bodomo,“Tonal Polarity in Dagaare”,in V.Carstens and F.Parkinson,eds.,Advanc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Trend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4,Trenton:Africa World Press,2000,pp.119-134.。
从声调库藏(inventory)来看,典型的非洲声调语言都存在两个或以上可以形成词汇或者语法(包括形态和句法)对立的音高模式。根据各语言描写的相关研究来看,这类语言一定都存在高调和低调两个平调(register tone),许多语言还存在中调,比如尼日尔-刚果语系的Yoruba语就是三声调系统的代表(24)Karen Courtenay,“Yoruba:A ‘Terrace-Level’ Language with Three Tonemes”,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vol.2,no.3,1971; Bruce Connell and D.Robert Ladd,“Aspects of Pitch Realization in Yoruba”,Phonology,vol.7,no.1,1990.。极少数语言存在三个以上的平调,比如尼日尔-刚果语系的Mambila语有四个平调(25)Bruce Connell,“Tone and Intonation in Mambila”,in L.J.Downing and A.Rialland,eds.,Intonation in African Tone Languages,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7,pp.131-166.,曼德(Mande)语族中Dan语的部分方言甚至有五个平调(26)Eva Flik,“Tone Glides and Registers in Five Dan Dialects”,Linguistics,vol.15,no.201,1977.。除此之外,不同语言还选择性地存在由高调、低调或者中调组合而成的曲拱调。
曲拱调的类型和数量在不同非洲语言中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任意性,即不同语言出现的曲拱调类型和数量差异较大,且不同语言对于某种曲拱声调的选择受具体音系系统的制约,比如班图语族的Digo语中曲拱声调只能出现在词的最后一个音步,且只能是升调或降调,不可能出现更复杂的调型(27)Moira Yip,To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2-143.。非洲语言学界主流的观点一般认为,只有高低型声调才是具有音系学地位的底层声调(underlying tone),而不同语言中观察到的大部分曲拱型声调都属于表层声调(surface tone),不具有音系学意义,因此都必须分解为底层声调的组合形式,才能进入后续的音系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非洲语言都符合这一类型,也有语言据称存在底层的曲拱声调(28)Paul Newman,“Contour Tones as Phonemic Primes in Grebo”,in K.Bogers,H.van der Hulst and M.Mous,eds.,The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Suprasegmentals,Berlin:De Gruyter Mouton,1986,pp.175-194.。
由此可见,与同是声调语言的汉语或相关声调语言相比,非洲语言声调的研究难点并不在于其声调音高对立的数量或者声调空间的复杂程度。相反,根据现有关于非洲语言声调的描写来看,非洲语言的声调系统在这个维度上比东亚、东南亚语言中的声调系统更为简明。这使得非洲语言声调研究对于声调现象的关注重点与汉语及相关语言的声调研究存在较大差异。
二、非洲语言声调研究主要议题
由于大部分非洲语言声调库藏较小,且声调一般只在调域(即高低)这个维度形成对立(至少对于非洲语言中的高低型声调语言来说),因此研究者一般对于单个声调具体的语音实现情况较少关注。此外,由于非洲语言在形态学上多属于综合型语言,声调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面临大量语境变异,因此也很难界定何为“本调”(citation tone),这一点与汉语声调研究传统极为不同。
相比之下,由于非洲语言声调与载调单元(tone-bearing unit)之间的对应性相对较弱,非洲语言声调的位置通常较为灵活。不同语言中广泛存在声调从某个语素扩展或移动到另一个语素的“声调扩展”(tone spreading)现象、曲拱型声调简化成高低型声调的“声调简化”(tone simplification)现象,以及声调不固定依附于音段而独立实现语法功能的“浮游调”(floating tone)等现象。自1974年海曼(Hyman)和舒尔(Schuh)对非洲西部诸语言声调系统进行调查以来的几十年间,已有大量研究从语言描写的需要出发,试图在理论音系层面采用不同分析框架理解非洲语言中发现的这些声调规则。(29)Larry M.Hyman,“Universals of Tone Rules:30 Years Later”,in T.Riad and C.Gussenhoven,eds.,Tones and Tunes Volume 1:Typological Studies in Word and Sentence Prosody,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07,pp.1-34; Larry M.Hyman,“Tone:Is It Different?”,in J.Goldsmith,J.Riggle and A.C.L.Yu,eds.,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New York:Wiley-Blackwell,2011,pp.197-239.此外,基于非洲语言声调与句法形态之间存在错综复杂交互关系的语言事实,声调也常常作为语法研究的重要方面。(30)Moira Yip,To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05-129.
这些关于非洲语言声调的理论分析研究,报告了不同非洲语言中类型各异的声调现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从非洲语言声调现象出发的声调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声调学界的研究传统,如在汉语声调研究中引入自主音段音系学的分析框架等(31)林茂灿:《汉语语调实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研究大多只是基于对声调现象的印象式描写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音系归纳,难免存在研究者个人的印象偏差。某种声调现象在进行音系归纳以及进入理论分析之前,首先要确保对于现象的观察准确客观。
由于词汇层面的声调交互以及后词汇(postlexical)层面的语调影响,声调在连续语流中一般呈现较高的变异性(variability)。该部分内容一直是不同非洲声调语言的研究者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非洲语言声调相关实验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该领域一个受关注较多的现象就是所谓“音高下行”( downtrends)的现象(32)Laura J.Downing and Annie Rialland,“Introduction”,in L.J.Downing and A.Rialland,eds.,Intonation in African Tone Languages,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7,pp.1-18.,可进一步细分为“下倾”(declination)、“降阶”(downstep)及“下移”(downdrift)等具体机制。
“下倾”是指短语或句子(尤其是陈述句)范围内音高缓慢下降的语音现象,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声调语言(如汉语(33)Chilin Shih,“A Declination Model of Mandarin Chinese”,in A.Botinis,ed.,Intonation:Analysis,Modelling and Technology,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pp.243-268.、Hausa语(34)Mona Lindau,“Testing A Model of Intonation in A Tone Language”,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vol.80,no.3,1986.)和非声调语言(如荷兰语(35)A.Cohen and J.′t Hart,“On the Anatomy of Intonation”,Lingua,vol.19,no.1-2, 1967.)的普遍现象。在声调语言中,下倾现象一般与具体的声调组合无关,但一个考察单元中如果所有声调都一致——如一句话中全是高调——将会明显观察到“下倾”现象的存在。
“降阶”现象是指在“高-低-高”这样的音高序列中,后一个高调会因为中间的低调发生音高整体下降的现象,又称“自动降阶”(automatic downstep)(36)William.E.Welmers,“Tonemics,Morphotonemics,and Tonal Morphemes”,General Linguistics,vol.4,no.1,1959; F.D.D.Winston,“The ‘Mid’ Tone in Efik”,in M.Guthrie,ed.,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I,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60,pp.185-192.。此外,即使两个高调中间不存在低调,即“高-高”的组合,也有可能发生后一个高调降低的现象(标作“高!高”),称为“非自动降阶”(non-automatic downstep)(37)John Massie Stewart,The Typology of the Twi Tone System,Accra: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Ghana,1964.。对于“降阶”现象属于音系现象还是语音现象目前还存在争议。
“下移”的概念则稍显模糊,在不同研究中常与“下倾”和“降阶”混用。(38)Jean Marie M.Hombert,“Universals of Downdrift:Their Phonetic Basis and Significance for A Theory of Tone”,in W.R.Leben,ed.,Papers from the Fifth Conference on African Linguistics,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Supplement 5,Los Angeles: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74; Keith Snider and Harry van der Hulst,“Issu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onal Register”, in K.Snider and H.van der Hulst,eds.,The Phonology of Tone-The Representation of Tonal Register,Berlin:De Gruyter Mouton,1993,pp.1-28; Larry M.Hyman,“Tone Systems”,in M.Haspelmath,E.König,W.Oesterreicher and W.Reible,eds.,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1,pp.1367-1380.在大部分文献里,“下移”常对应“自动降阶”的现象,而“降阶”则特指“非自动降阶”。(39)Laura J.Downing and Annie Rialland,“Introduction”,in L.J.Downing and A.Rialland,eds.,Intonation in African Tone Languages,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7,pp.1-18.
这种术语混淆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洲语言声调学者对于“音高下行”这一笼统现象下具体机制的理解还有继续深化的空间。不少研究因此试图通过不同非洲语言中的声调现象为例,来厘清这三种机制之间——尤其是“降阶”和“下移”之间的异同,发现“降阶”和“下移”至少从下降幅度上来看较为相似,或没有特别区分的必要,都属于局部(local)的声调变异现象,因而与全局(global)的“下倾”现象存在明显区别。(40)Bruce Connell,“Downdrift,Downstep,and Declination”,Proceedings of Typology of African Prosodic Systems Workshop,2001; Susanne Genzel and Frank Kügler,“Phonetic Realization of Automatic (Downdrift) and Non-Automatic Downstep in Akan”,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2011,pp.735-738.
厘清概念(至少是部分厘清)的一个良性结果就是对于某种音高现象的观察不再平面地归因于特定难以解释的音系规则,而是以分层的视角剥离出不同因素。比如,在较长的句子里,往往会同时出现局部的“降阶”或“下移”以及全局的“下倾”现象。此外,除了三种常见的“音高下行”机制外,还有一种低调前的高调抬升现象也常伴随总体音高下行的现象出现,类似汉语(如普通话(41)Yi Xu,“Contextual Tonal Variations in Mandarin”,Journal of Phonetics,vol.25,no.1,1997.和天津话(42)Qian Li and Yiya Chen,“An Acoustic Study of Contextual Tonal Variation in Tianjin Mandarin”,Journal of Phonetics,vol.54,2016.)中的逆向协同发音现象。这种机制并不在“音高下行”的常规讨论范畴,但常与“(非自动)降阶”现象并存。如在一个“高-低-高”的声调序列里,中间的低调在造成后一个高调发生“降阶”的同时,也对前一个高调形成抬升。在这两种看似冲突的机制共同作用下,声调具体会如何实现?拉尼兰(Laniran)和克莱门茨(Clements)(43)Yetunde O.Laniran and G.N.Clements,“Downstep and High Raising:Interacting Factors in Yoruba Tone Production”,Journal of Phonetics,vol.31,no.2,2003.通过Yoruba语中的案例发现,所有母语者都会采用对后出现的高调进行音高重置的方式,但也有部分母语者可以通过提前预判后面要出现的音高序列将第一个高调抬升为超高调。此外,除了逆向的抬升,顺向的声调协同发音现象也会与这些因素发生交互。
尽管文献中的术语混淆时有发生,但研究者都共同注意到了局部声调变异与各种全局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试图在更大的语言单元内探讨声调语言中如何实现全局韵律的问题。除了前文提到的“下倾”与“降阶”的交互,还有“降阶”/“下移”现象与韵律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44)Sabine Zerbian and Frank Kügler,“Sequences of High Tones across Word Boundaries in Tswan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vol.53,no.2,2023.此外,唐宁(Downing)和里亚兰(Rialland)(45)Laura J.Downing and Annie Rialland,eds.,Intonation in African Tone Languages,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7.所编《非洲声调语言的语调》(IntonationinAfricanToneLanguages)一书集中展示了非洲大陆11种声调语言中的语调现象,并以实证研究为主(或至少能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着重探讨了不同语言中声调在不同韵律结构、信息结构、句法结构、语气语调以及边界调等现象影响下的具体音高实现。
这些实验研究的开展充分说明,某种能观察到的声调音高现象往往都是不同机制相互叠加或者制衡的结果,而这些效应往往很难由印象式的归纳所揭示,因此实验研究应当也必将成为未来非洲语言声调研究的主流。
三、非洲语言声调研究存在的问题
几十年来,西方语言学界已有大量研究对不同非洲语言的语音系统尤其是声调系统进行了基本的描写。由于非洲语言总量巨大,已有文献数量惊人。但细看之下,除了少部分语言的声调现象研究得较为深入外,大部分非洲声调语言都只存在零星的报告,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学界对于非洲语言声调现象的研究又极不充分。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绝大多数非洲语言声调研究是以印象式描写为主,并以此为基础在自主音段音系学为代表的理论框架内,采用一系列合乎形式合法性的规约和排序,对不同语言的声调现象进行理论解释。虽然这种模式能够一定程度上总结出不同语言中声调现象的规律,但音系形式分析往往无法揭示某种声调现象产生的生理心理基础,对于理解声调的普遍机制作用有限。尽管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非洲语言声调及语调的研究,但相对于汉语(包括普通话和方言)数量庞大的声调实验研究来说,有关非洲语言声调的实验证据太过稀少。此外,目前为止未见任何有关非洲语言声调感知及与认知神经科学交叉的研究发表。
从研究视角上来说,由于非洲语言研究仍是一个完全受西方学者垄断的领域,无论理论分析的体系还是对具体语言声调现象的研究视角,都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影响。针对非洲语言声调现象的探讨,西方学者往往会局限于从欧洲非声调语言中的现象出发,如用重音(stress)来类比声调,而不是从其他声调语言中的现象出发。一旦切换视角,许多对非洲语言的既定认知或值得重新思考。
1.关于非洲语言声调特征问题
由于大部分非洲语言已被先验地归入“高低型声调语言”,因此一般认为只有声调的高低才具有底层音系地位,而曲拱形状只属于表层语音形式,不对声调对立起决定性作用。(46)Kenneth L.Pike,Tone Languag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48.有关“高低型声调语言”的所有声调研究几乎都不会对这一前提提出疑问。甚至有学者认为派克(Pike)早年提出的基于声调实际音高的研究方法属于“前生成时代”的落后做法。(47)Constance Kutsch Lojenga,“Tone and Tonology in African Languages”,in A.Agwuele and A.Bodomo,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London:Routledge,2018,pp.72-92.这种普遍认知使得声调的具体音高实现方式从来都不是非洲语言声调研究关注的重点。
但即便从为数不多的声学研究中也不难发现,许多语言中所谓的平调,其实并非实现为平直的音高曲线。比如莱昂(48)莱昂:《龚语(Gungbe)声调实验研究——兼论龚语与汉语声调的差别》,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大学,2019年。对Gungbe语单音节声调进行的声学研究发现,该语言中所谓高低两个平调的实际声学表现是高升和低降的调型。尽管从声调空间来看,两个声调确实在高低调域这个维度形成了对立,但也绝非平调。
将曲折调用高低平调组合的方式来表征这一处理方式虽然适应了以自主音段音系学为代表的理论框架对于声调抽象表征形式的要求,但同时也丢失了实际基频信号里的其他声学线索。有关汉语声调认知的研究发现,汉语母语者能够利用声调中的细节声学线索,实时地对听到的语音信号进行声调类型的辨认,并能利用声调信息实时地从音段相同的诸多候选项中筛选出目标。(49)Jeffrey G.Malins and Marc F.Joanisse,“The Roles of Tonal and Segmental Information in Mandarin Spoken Word Recognition:An Eyetracking Study”,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vol.62,no.4,2010; Qian Li,“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Online Processing of Anticipatory Tonal Coarticulation-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Frontiers in Psychology,vol.14,2023.那么“高低型声调语言”的母语者是否表现出与汉语母语者完全不同的声调感知方式,从而完全忽略声调曲拱的变化?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一个与此相矛盾的点就在于:那些由平调组合而成但具有一定对立功能的曲折调又是如何起到区别意义作用的?非洲声调语言母语者是如何做到选择性地忽略声调曲拱信息的?
2.关于声调灵活性问题
长期以来,非洲语言的研究传统认为非洲语言声调相对汉语等东亚、东南亚有声调的语言来说体现出较高的灵活性(mobility),具体表现为声调常不以所在音段为条件,因而某种声调常常可以出现横跨不同的音段甚至移动至别的音段等现象。(50)Moira Yip,To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这些现象为非洲语言的声调现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挑战了我们基于东亚、东南亚有声调的语言中的现象得出的有关声调现象本质的既定理解。
在以汉语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的声调语言中,载调单元多为音节,一个音节上只能有一个声调,也必须有一个声调。胡方以藏语拉萨话为例,考察了音节产出过程中辅音、元音以及声调发音动作的时间序列关系,论证了声调与载调单元之间存在某种稳定的对齐关系。(51)胡方:《音节时间结构与拉萨藏语的声调起源》,《民族语文》2022年第3期。许毅对汉语普通话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52)Yi Xu,“Consistency of Tone-Syllable Alignment across Different Syllable Structures and Speaking Rates”,Phonetica,vol.55,no.4,1998; Yi Xu,“Effects of Tone and Focus on the Formation and Alignment of F0 Contours”,Journal of Phonetics,vol.27,no.1,1999; Yi Xu,“Speech Melody as Articulatorily Implemented Communicative Functions”,Speech Communication,vol.46,no.3-4,2005.这说明至少对于汉语、藏语等声调语言来说,声调并不是完全独立于载调单元存在的“自主”成分。非洲语言的声调是否在这一本质上有别于汉语、藏语等语言,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验证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从前对于汉语声调的分析也一度有研究试图论证类似非洲语言中“浮游调”“声调扩展”等现象的存在。比如汉语普通话中单念或停顿前的上声音节常实现为降升的曲折调(如果按照非洲语言声调研究传统应表征为“高-低-高”),但不处于停顿前的上声却会丢失末尾的“高”音高,实现为降调(“高-低”)。且如果上声后面出现轻声音节,这个“高”音高还会向后“扩展”,成为轻声的音高,因此认为上声末尾的“高”音高属于“浮游调”现象,而轻声则由于声调模式不固定、容易受到周围声调的影响,被认为属于“无调”(toneless)音节。然而,随着近二十年来声学实验的大量开展,这些汉语中的现象尤其是有关语境变异的各种声调现象已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比如陈轶亚和许毅通过控制连续出现的轻声音节数量(0—3个轻声音节),发现汉语普通话中的轻声并非“无调”,而是存在其固有的“中”音高目标,但由于轻声音节时长较短(仅为重读音节的一半),因此音高目标往往无法在一个轻声音节的时长内得到实现,从而在前字重读音节声调的影响下表现出较为多样的轻声音高表现。(53)Yiya Chen and Yi Xu,“Production of Weak Elements in Speech-Evidence from F0 Patterns of Neutral Tone in Standard Chinese”,Phonetica,vol.63,no.1,2006.这一发现也在之后的不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54)Qian Li and Yiya Chen,“Prosodically Conditioned Neutral-Tone Realization in Tianjin Mandarin”,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vol.28,no.3,2019; Aijun Li and Zhiqiang Li,“Prosodic Realization of Tonal Target and F0 Peak Alignment in Mandarin Neutral Tone”,Language and Linguistics,vol.23,no.1,2022.可以推测,非洲语言中的相关现象是否也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有待未来类似实证研究的开展。
3.关于语境中的声调变异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语言事实的限制,非洲语言的声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很难遵循汉语声调研究那样以单字调为基础,逐渐将考察范围扩大至更大声调组合单元乃至句子层面的研究传统。对于某种语言声调的现象,几乎全部是在语境中考察的。
而从汉语声调研究的实践中可以总结得出,声调——尤其是非孤立形式下的声调,存在着大量由不同层次来源造成的变异现象(即便是对于汉语这种典型的曲拱型声调语言)。有的变异是来源于音段对声调的影响,有的变异是来源于局部的相邻声调互动(比如连读变调和声调协同发音现象),有的变异是受整体的韵律切分、信息结构组织以及言语产出规划等因素所制约(55)Yiya Chen,“Tonal Variation”,in A.C.Cohn,C.Fougeron and M.K.Huff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boratory Phon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03-114.,非洲语言的声调也不例外(如前文所述)。但大量关注语流中声调现象的非洲语言声调研究,由于较少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很难厘清不同机制导致的声调语境变异,因而试图将所有观察到的声调变异现象音系化(当然,汉语声调研究中有一部分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但如果将不同层面的声调变异机制考虑在内,就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语境变异都需要进入音系表征,而且这种做法有时也并不具操作的便利性。例如音系表征中对声调的表征形式只能是类型化(范畴化)的音高对立,比如“高”“中”“低”等,但往往音高变异并不总是从一个调类变为另一调类,因此,这种做法常常除了增加声调描写和规则归纳的困难之外,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变异现象发生的机制。
除了前文提到的各种声调交互或声调-语调交互现象,另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就是非洲语言中的所谓“抑调辅音”(depressor consonants)现象。“抑调辅音”一般是指浊阻塞音后出现高调时,声调起始部分的音高会被前面的浊音拉低,使得高调变升调(56)Constance Kutsch Lojenga,“Tone and Tonology in African Languages”,in A.Agwuele and A.Bodomo,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London:Routledge,2018,pp.72-92.(但具体到不同语言中“抑调辅音”现象的具体情况又存在一定的多样性(57)Yiya Chen and Laura J.Downing,“All Depressors Are Not Alike:A Comparison of Shanghai Chinese and Zulu”,in S.Frota,G.Elordieta and P.Prieto,eds.,Prosodic Categories:Production,Perception and Comprehension,Dordrecht:Springer,2010,pp.243-265.)。辅音对于后接元音起始部分的基频扰动,是不同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清辅音后元音的起始音高要高于浊辅音后元音的起始音高。(58)Jean-Marie Humbert,“Consonant Type,Vowel Quality,and Tone”,in V.A.Fromkin,ed.,Tone:A Linguistic Surve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pp.77-111; Mary Bradshaw,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Consonant-Tone Interaction,Ph.D.dissertation,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1999; Katrina E.Tang,The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of Consonant-Tone Interaction,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8; Seunghun Lee,Consonant-Tone Interaction in Optimality Theory,Ph.D.dissertation,Rutgers University,2008.这种现象常被认为与声调起源(tonogenesis)有关,主要发生在辅音本身的清浊对立线索(比如嗓音起始时间;VOT)消失时,通过保留基频部分的差异——也就是形成声调的对立——来保持两组声音的对立性。(59)Andries W.Coetzee,Patrice Speeter Beddor,Kerby Shedden,Will Styler and Daan Wissing,“Plosive Voicing in Afrikaans:Differential Cue Weighting and Tonogenesis”,Journal of Phonetics,vol.66,2018.但是,当辅音部分的对立仍然存在时,如非洲语言中“抑调辅音”的情况,基频作为VOT之外清浊对立的次要声学线索(secondary acoustic cue)对于区别清浊辅音所扮演的作用还是否具有音系学意义,是值得重新考察的。“抑调辅音”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音系现象,决定了声调系统的复杂程度。同时,通过对不同语言中“抑调辅音”现象多样性的考察,也可能从一个侧面观察到非洲各语言声调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
四、未来研究展望
想要全面理解人类语言中的声调现象,应当转变西方学界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研究视角,从对声调语言的已有认识——尤其是从近年来基于汉语声调现象所形成的有关人类语言声调现象普遍机制和规律的认识出发,探究声调现象的普遍本质。中国声调学者在这一点上有巨大优势。但同时需要警惕的是,无论“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完全照搬汉语声调研究的经验和结论,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合理地观察非洲语言中的声调现象,实证研究因此显得尤为关键。
非洲语言的声调现象之所以显得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实证研究的不充分导致不同层面的机制都被当作音系规则来处理。而复杂的音系规则就意味着交际双方在语言产出和语言感知的过程中可能需要付出较大的认知精力(cognitive effort),尤其许多非洲语言甚至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更加不利于语言的习得。因此,未来非洲语言声调的产出研究可适当借鉴汉语声调研究的范式,开展严格控制的声学实验,或基于语音语料库的数据,挖掘可能影响声调实现的不同因素。
截至目前,由于完全没有非洲语言声调感知方面的研究发表,因此我们对于非洲语言母语者如何感知和理解声调基本一无所知。未来可研究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对于“音高型声调语言”的母语者来说,声调感知的声学线索究竟是什么?所谓的“抑调辅音”和基频信息在声调感知中的线索权重(cue weighting)是什么?从语言加工的层面来说,非洲语言的声调是否像汉语声调一样在听觉词汇识别(spoken word recognition)的过程中扮演同等重要的作用?在声调变异如此丰富的情况下,母语者是如何在实时语言理解的过程中加工那些声调变异乃至所谓“声调移动”的现象?不同声调系统的母语者如何感知另外一种类型的声调(例如非洲语言母语者与汉语母语者感知对方语言声调或不同类型非洲语言母语者感知对方语言声调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非洲语言并不是一个具有内部同质性的整体,不同语言/方言中的声调现象多样性极高,这为不断完善对声调现象的全面理解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挑战。且非洲语言常常互相接触,影响频繁,使得不同语言的声调系统本身也正处于历时的发展变化中,同一语言中的同一现象常常会在母语人群中观察到完全不同的表现,因此语言使用者的个体差异也应作为未来非洲语言声调研究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