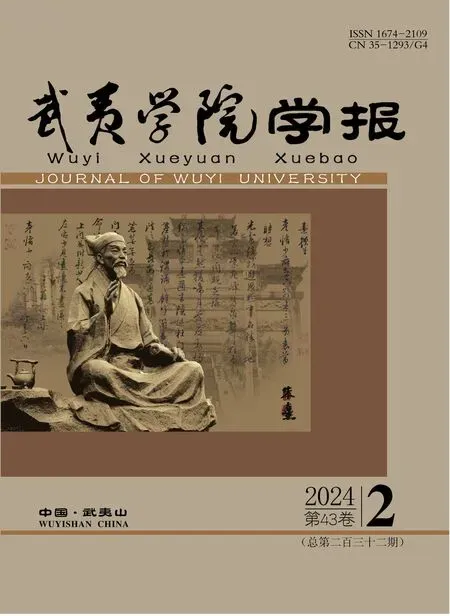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
——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赵项飞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1)
朱子对“格物”的注解非常丰富,但是往往分布在辞章语录之间,散落于寻常谈论之中。有鉴于此,后世学者对朱子“格物”工夫的理解往往陷于一端,看不到不同诠释之间的统一性,从而不明其核心要旨。乐爱国等则认为“朱熹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1]。唐君毅亦主张从内外两面来理解“格物”,他说:“若格物致知只为向物求理,而非自显其心体中所原具之理之事,则此吾心之‘全体’与‘大用’,何以皆可由此格物致知而‘无不明’,即全无法加以了解矣”[2]。从原文来看,朱子讲“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3],“致知、格物,便是择善”[3],“致知、格物,只是一个”[3]。以上定义从逻辑上可以看出,“穷理”“择善”“致知”三者均涵盖了“格物”工夫的全部内涵。换句话说,当将“格物”诠释为“穷理”的时候,就已经兼有“择善”“致知”的意思了,并非是有几种不同的“格物”工夫在,而是其诠释的角度各有所侧重。因此,这些定义既可以分说,体现出“格物”工夫的普遍性,又可以会通,彼此之间互为印证,呈现出“格物”工夫的统一性。本文通过对这三种诠释方式的分说与会通,发现朱子所讲的“格物”工夫立足于“理”“性”“心”上,既是一种修德的工夫,又是一种求知的实践。
一、“穷理”以明事物之理
“穷理”一词原出自《易传·说卦传》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4]一句。在朱子注解《大学》时,释《大学》中的“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7],即通过“穷理”来明事物之理。有鉴于此,后世学者往往从认识论上来理解“穷理”。但是细究可以发现,“穷理”的目的不仅在于求知,还在于根据这些知识来指导人的行为实践。正如朱子所说“不明其物之理,则无以顺性命之正而处事物之当”[8]。“明其物之理”只是工具和方法,“顺性命之正”和“处事物之当”才是“穷理”的目的,而求其“正”“当”便是一种道德修养。
朱子强调在具体事物上“穷理”,这主要与当时批判佛老的风气有关。陈来认为,“朱熹是继承了‘二程’,用穷理来把握格物的主要精神,同时强调‘至物’(‘即物’),不离开事物,以区别于佛教的思想”[5]。但是朱子所讲的这种在“物”上求索的方式只是为了使工夫不至于落空,不至于流于虚寂,其最终目的是仍然是指向“我”的。同样,作为“穷理”所指向的对象,所格之“物”虽然包含天地万物,但是其关键还是在“切己”之物上。
朱子所理解的“物”,既包括具体存在之“物”,又包括与人相关之“事”。从范围上看,朱子引程颐所言“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3]。意思是广大如天地,精细如一具体存在物,均是“物”。从时间上看,朱子又从人生的角度来讨论“物”,他说“人之生也,固不能无是物矣”[8],说明“物”总是贯穿人生的始终。此外,朱子更重视人的行为实践,认为“事”也是“物”。他说:“言学者之穷理,无一物而在所遗也。至于言‘讲明经义,论古今人物及应接事物’,则上所言亦在其中矣。”[3]虽然“物”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应该以“切己”之物为重。朱子在注解《论语》“君子之道贵有三”章时认为,笾豆之事“也须著晓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3],“三事”指曾子所言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皆是“切己”之物。同时,他也认为笾豆之事也需晓得,否则“若不晓,如何解任那有司”[3],其目的还是在于“切己”上。
由此可知,朱子以“切己”之物作为“穷理”的入手处,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自身道德行为实践上,并非单纯以形成对事物的认识为目的的。
“穷理”的目标有两个,一为明事物之“所以然”,一为明事物之“所当然”。朱子认为:“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3]此句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当如此”和“当如彼”是指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此事物,指的是规范、仪则。其二,这些规范、仪则必有其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根据。倘若是从先知先觉的圣贤言语中学得这些节文的,尚可说不明其背后之理。倘若是通过自身“格物穷理”的方式得到这些节文的,那必不可能不明其背后之理。朱子所讲的“当如此”“当如彼”就是指事物之“所当然”。何以“当如此”,何以“当如彼”就是指事物之“所以然”。所以他说:“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3]
朱子在论述“所以然”和“所当然”时说:
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8]
朱子用“不可易”来描述“所以然”,用“不容已”来描述“所当然”,说明二者都具有客观性。“所以然”是指一事物之所以如此的本质规定性,所以又用“理”字来表示,称之为“所以然之理”。“理”是纯粹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此理不可更改,是本然如此的,此即是“不可易”。“所当然”也具有客观性。一方面,“所当然”被“所以然”必然的决定着,不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它所呈现出来的仪则、规范亦如天理一般不容改变,此即是“不容已”。另一方面,“所当然”的客观性也能够从主体的角度得到说明。当我们说一事物不是客观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此事会因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朱子看来,每个主体皆是禀赋同一天理,然后有了善性,愚人和圣人皆如此。但是由于不同的主体所受到的“气禀所拘,人欲所蔽”[7]不同,造成了认知上的差异。倘若人人都能克私去蔽,则不同的主体在认知上就没有差异了。朱子常引用“人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3]来说明“所当然”不会因人而异。
朱子又常把“所当然”就着“事”来讲,而非就着“物”来讲,他在回答弟子的疑问时说“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3]。所有的“事”都是有行为主体的,这意味着明“事”之“所当然”,不仅是为了形成对“事”之“所以然”的正确认识,还是为了给主体的道德实践提供指导。所以朱子认为“穷理”的目的在于“顺性命之正”和“处事物之当”。“顺性命”和“处事物”都是“事”,对“性命”“事物”自身的认识不是目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与事物的关系——如何“顺”、如何“处”上,即人应该如何对待事物。例如,砍树造梁即为一“事”,欲明此“事”之“所当然”,首先要认识到草木春生秋死的自然规律,即“所以然”,然后才能认识到“斧斤以时入山林”的“所当然”。
从“所以然”和“所当然”的关系来看。“所以然”在逻辑上更为根本,“所当然”在目的上更为根本。
一方面,“所当然”以“所以然”为依据。朱子说“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层”[3],这里所说的“更上面一层”是指更本质的意思。同样,“所以然之故”的“故”字表原因,即“所以然”是“所当然”的内在原因。例如,以“读书明理”为例。尽管通过圣贤言语,可以直接认识到事物的“所当然”。但是,如果不明背后的“所以然”,那么“所当然”就只能流于口耳之间。因此,在逻辑上,先有“所以然”,后有“所当然”。另一方面,对“所以然”的认识只是一种工具、手段,势必要走向“所当然”。在朱子看来,所格之物虽遍及天下万物,然而又应以“切己”之物为重;“格物”之功又须在物物上格到尽处,方能始得,然而其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处物”“应物”上。因此,明草木器用的“所以然”并非是最终目的,而是以此为基础,明得其“所当然”,从而使得人能够应物得宜、处物得当。吴婕说:“‘所当然而不容已’应为朱子论述道理的核心与关键,须由‘不容已’处,以见‘不可易’者分明”[6]。
二、“择善”以复天赋善性
“择善”一词出自《中庸》,原文为“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朱子对此句注解为“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7],说明“择善”是“明善”的工夫。所明之“善”即为禀赋于天的善性,又可称为“明德”“仁义礼智”之性等①。“择善”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诠释“格物”,朱子说:“‘择善而固执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择善”[3],将“格物”与“择善”等同起来。所以,有时他又说“大学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3]“仁”便是善的,“求仁”的过程便是在“择善”。因此,“格物”除了可以从外在的层面——“穷理” 上理解外,还可以从内在的层面——“择善”上理解。此并不是说,“穷理”和“择善”表示存在两种不同的“格物”工夫,而是说,“穷理”的过程便是“择善”的过程,二者是同一的。朱子说“物格后,他内外自然合”[3],说明并非是有个内在的工夫,又有一个外在的工夫,而是“格物”工夫,本身就兼有内外了。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切己”之物来入手,还是明事物之“所当然”,整个“格物”工夫所彰显出来的就是对善的追求。“顺性命之正”是善的,“处事物之当”亦是善的。人只有通过“格物”,才能够复自己本有的“仁义礼智”之性,才能够参赞到天地万物的生化流行中去,这种使命便是大德、大善。朱子以“择善”来诠释“格物”,其目的在于明“仁义礼智”之善性。以“穷理”来诠释“格物”,其目的在于明物“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而物之“所以然”和“所当然”能够被认识,又必须依靠人的“仁义礼智”之善性。朱子说:“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3]在朱子看来,草木的“春生秋杀”,禽兽的“好生恶死”是事物的“所以然”,“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是事物的“所当然”。万物自身本有的规律,皆是天理在其中的发用流行,对于人而言,是无所谓善恶的。但是,在一“事”之中,“物”成为“我”的行为对象,“物”与“我”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善恶之别。如“顺性命之正”和“处事物之当”,便是善的。反之不顺其正、不处其当,便是恶的。因此,要想明事物之“所当然”,除需明事物之“所以然”以外,仍需要人依靠自己的善性对如何“顺”,如何“处”来考察。如此,才能使事物各当其理。朱子曾说:“如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如虎狼,便只可陷而杀之,驱而远之。”[3]意思是,认识到马的凶悍之理,虎狼的残暴之理,这只是认识到事物的“所以然”,并不是“格物”工夫的结束。仍需要通过自己的善性对此“所以然”进行考察,形成对“悍马”“虎狼”的对待之理,如“鞭策”“陷杀”,这种善性的彰显,才是“格物”工夫的结束。
分而言之,“择善”的过程又体现在“穷理”的两种方式之中。一为从“所当然”到“所以然”,即为现有的仪则、规范,寻找背后根据,如读圣贤之书。一为从“所以然”到“所当然”,即通过对背后依据的认识,来认识外在的仪则、规范,如在具体存在物上“穷理”。这两条路径均能够明“仁义礼智”之善性。
其一,从“所当然”到“所以然”的过程中,“所当然”需要由人的善性来体认。朱子所讲的“格物”工夫,最终落脚点在于明事物之“所当然”上。他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3]。同时,他又认为“所当然”不是在“皮壳上做工夫,却于理之所以然全无是处”[3]。“所当然”如果没有经过人的善性的体认,那么就只会流转于口耳之间,凭空做个样子给人看。朱子说:“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即从“所当然”到“所以然”的过程,亦需要在自家推究,将圣人如此这般的道理与自身本有的“仁义礼智”之性相合。如孝顺父母便不是做个孝的样子,而是需要从自身上体会到这种孝的情感,才是知孝。他又说:“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3]意思是圣贤言语不能仅仅流转于口耳之间,必须要将其在自家心中体认出来。自家能够能体认的原因,就在于“所当然”是由人的天赋善性所体认出来的,不会因人而异。既然自家的善性与圣人并无区别,那么所体认出的“当然之理”亦无区别。
其二,从“所以然”到“所当然”的过程中,“所以然”需要由人的善性来彰显。在朱子看来,对于没有现成的仪则、规范的事物,也需要“格物”。例如,草木鸟兽。此过程便是“择善”的过程。首先,要想明草木鸟兽的“所当然”,必须先认识它自身本有的规律,即“所以然”。对“所以然”的认识,便是人的“智”的呈现,朱子认同弟子所说“知其所以然便是智”[3]。“智”是一种认知能力。在此认识过程中,“智”是最先彰显出来的。朱子说:“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3]其次,在明得事物之“所以然”以后,便要依据自己的善性来明事物之“所当然”。“仁”便是能明的根本。如春天是草木生长的季节,便会“斧斤以时入山林”。虎狼天性凶残,对待它们就要陷杀、驱赶。如果没有一个“仁”做根本,那么对待凶残的虎狼,该采用何种举措,就无的放矢了。再次,“所当然”是人对事物进行的合宜的宰制,如伐木以时,陷杀虎狼。这种合宜的宰制表面上是由人决定的,实际上这种宰制来源于人心中的“义”。“义”不会因人而异,是对事物最合宜的处置方式,朱子引程子之言“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即是此意。最后,每一物皆有其“所当然”,这些仪则、规范,又必须依靠人心中的“礼”才能呈现出来。如果没有“礼”,对“所当然”的认识便会粗犷很多,不能井井有条,层次分明。因此,在认识事物的“所以然”到“所当然”的过程中,“仁义礼智”之善性便能够彰显出来。
三、“致知”以立主宰之心
“致知”与“格物”并列在《大学》八条目之中,所谓“致知在格物”(《大学》),“致知”原为“格物”之后的工夫。但是朱子在注解《大学》时,将“致知”和“格物”视为一种工夫,并用“致知”来诠释“格物”。所以他说:“致知、格物,只是一个”[3],又说:“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3],二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徐复观亦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身家国天下即是物,修齐治平之效即是格物,修齐治平之道即是致知;在修齐治平之道以外无所谓致知,在修齐治平之效以外无所谓格物。”[9]“致知”与“择善”的诠释角度又有所不同,“致知”一词中的“知”字,在朱子看来,指的心的“知”,所以他常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7]、“致知乃本心之知”[3]等语。心原本是“虚灵不昧”的,但是却由于受到气禀、人欲的遮蔽,使本有之善性不能正常显发。“致知”的工夫便是克私去蔽,从而使本心之知的作用能够没有遮蔽的显发出来。说到“致知”工夫的目标时,他又说“得知至时,却已自有个主宰,会去分别取舍”[3]。意思是“致知”的目标,便在“心”上确立一个能够“分别取舍”的“主宰”。
朱子尤为重视心的“主宰”义,并用“主宰”来释“心”,他说:“心,主宰之谓也。”[3]在论及“心”与“性”的区别时,朱子同样以“主宰”来辨析此二者。在他看来,性只是“未发”,是必然如此的这般道理。心则兼统摄了“已发”,是在应事对物的过程中对此般道理的顺应与感通,所以他说:“盖主宰运用底便是心,性便是会恁地做底理。‘性’则一定在这里,到主宰运用却在心。”[3]
在道德实践上,朱子把此心的主宰能力作为修养工夫的根基和前提。他认为,若无此心的主宰能力,工夫便昏昏地失去了头脑,所以他说:“才出门,便千岐万辙,若不是自家有个主宰,如何得是。”[3]因此,在工夫上确立此主宰之心便要使得此心虚灵不昧,不要昏浊了他,不要使他随物而去。朱子说:“今人无事时,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时,则又随事逐物而去,都无一个主宰。这须是常加省察,真如见一个物事在里,不要昏浊了他,则无事时自然凝定,有事时随理而处,无有不当。”[3]
“择善”和“致知”两种诠释方式均是对人而言的,但是各有侧重。“择善”是以“性”而言,讲的是本体,即明自身所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的善性。“致知”是以“心”而言,兼讲发用,确立自身主宰的虚灵不昧之心。
“致知”的“知”字历来有诸多不同的理解。既然朱子将“格物”和“致知”视为同一个工夫。那么,便可以借助朱子对“格物”的诠释来理解“致知”之“知”。以下对“知”进行详细分析。
一方面,可以从内外的角度来理解“知”。“格物”工夫既可以明事物之“所以然”,又可以明事物之“所当然”。“所以然”指的是事物自身规律,如草木“春生秋杀”之理,鸟兽“好生恶死”之理。对事物“所以然”的认识,即是对外在知识的积累,是属于认识论上的认知。“所当然”则指的是“事”,既包括人自身的行为规范,又包括人对待事物的方式、法则。客观上来说,事物之“所当然”的仪则,其根源是外在于人的。人只是通过自身本有的“仁义礼智”将这些仪则、规范彰显出来而已。因此,对事物“所当然”的认识,又是对人所固有的内在善性的澄明,又属于修养论上的认知。
另一方面,可以从动静的角度来理解“知”。无论是事物之“所以然”,还是事物之“所当然”,亦或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仁义礼智”,都是静态的“知识”。但是在朱子看来,更重要的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知”。他说:“物理皆尽,则吾之知识廓然贯通,无有蔽碍,而意无不诚、心无不正矣。”[8]静态的知识是不能够用“廓然贯通”来形容的,只有动态的认知能力才能以此来形容。所以,朱子在“格物致知”章补传中说:“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7]由此可见,将朱子所理解的“知”视为一种认知能力、觉悟能力更为贴切。
“致知”作为一种工夫,此工夫的结果就是“知至”的状态。朱子又把“知至”的状态视为在心上确立一个能够“分别取舍”的“主宰”。“分别取舍”是从两个角度来说,“分别”意思是说,万物皆分殊同一理而形成众理,通过“穷理”的工夫,使得众理能够为一心所具有。在“应接事物”的过程中,心便能够依据自身所具有之众理,对事物进行区分、辨别,使之各符其“当然之理”。“取舍”意思是说,“仁义礼智”之性为一心所本有,通过“择善”的工夫,使得善性能够依托于心,“无有蔽碍”的发用出来。在“应接事物”的过程中,心便能够依据此善性之发用,来对事物进行宰制,使之得宜。
朱子又用“豁然贯通”来诠释此心的“主宰”作用。他说:“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焉。”[7]对此可以从“一”和“多”的视角来看待。在豁然贯通以前,是对“多”的积累。在豁然贯通以后,是对“一”的把握。把握了这个提纲挈领的“一”,便能够应对无限的“多”了。这个“一”就是朱子所讲的能够“分别取舍”的“主宰”。这个“多”就是朱子所讲的事物之“所当然”。此“主宰”的确立,使心“无有蔽碍”,而“无有蔽碍”是指心物之间没有分隔。此种分隔,在朱子看来是“气禀”“人欲”对心的遮蔽。去掉这种遮蔽以后,心中的明德(“仁义礼智”)就能够呈现出来,在“应接事物”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分别取舍”的主宰能力,内在之“性”和外在之“理”就达到了贯通。统而言之,即是张岱年所说:“心本有知,而欲致心之知,必即物而求物之理。如不即物而求物之理,则心虽具众理而不能自明;必至穷尽万物之理以后,心中所具之理方能显出。”[10]
此“主宰”之心的确立,便能够会通朱子所讲的“理”和“性”。他讲“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7]“众物”和“吾心”虽是分内外两个方面而言,但是,在“物”上做工夫——“格物”的同时,也是在“心”上做工夫——“致知”,所以朱子又说“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3]此二者是合一的。王磊认为:“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11]分而言之,“众物之表里精粗” 是以“理”而言,朱子说:“理固自有表里精粗,人见得亦自有高低浅深。有人之理会得下面许多,都不见得上面一截,这唤作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体,都不就中间细下功夫,这唤作知得里,知得精。二者都是偏。”[3]所谓的“知得表,知得粗”是指明事物之“所当然”,所谓的“知得里,知得精”是指明事物之“所以然”,二者不可偏废。“吾心之全体大用”是以“性”“心” 合而言之,“心之全体大用” 包含体用,“仁义礼智”是心之体,使众物各符其理是心之用。此“主宰”之心确立以后,便能够“无有蔽碍”,而“仁义礼智”之性能够随事物彰显,“应接事物”便能够使“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四、结语
在朱子看来,“格物”的目的在于“顺性命之正”和“处事物之当”。其一,这种“正”和“当”的依据在于事物,而不在于人,并且是由事物之“所以然”来决定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仪则、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格物”便是“穷理”,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其二,这种“正”和“当”又必须依靠人的善性加以体认,被气禀、人欲遮蔽的人,其认识必然“过”或“不及”,不能准确的明得这些仪则、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格物”便是“择善”,目的在于明自身被遮蔽的“仁义礼智”之善性。其三,“格物”工夫“一旦豁然贯通”,则于外,明物之理,于内,明我之性。物之理和我之性又分殊于同一“天理”。这种在心上的内外贯通,“无有蔽碍”的境界,便是《大学》所讲的“物格而后知至”。从这个角度看,“格物”便是“致知”,目的在于确立自身的主宰之心。
注释:
①或问:“所谓明德便是仁义礼智之性否?” 朱熹答曰:“便是”。引自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