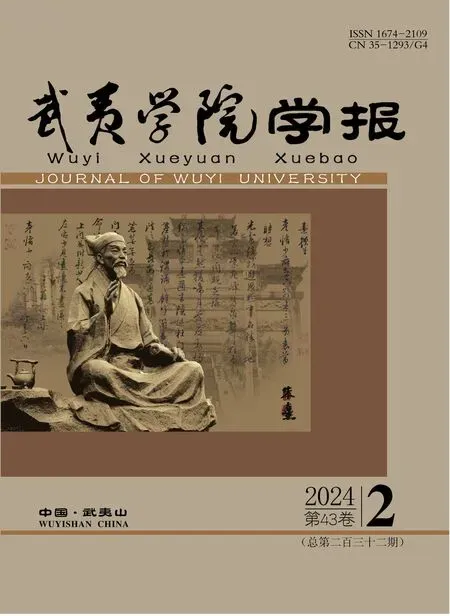苏轼《水调歌头》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与受容
李梦琦
(福建教育学院 语文研修部,福建 福州 350001)
熙宁九年丙辰(1076)中秋,苏轼与友人聚饮于密州(治今山东诸城)超然台,醉中有感而发,遂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表达出世、入世的思想矛盾,寄托对胞弟苏辙的思念之情。此词一经问世,好评如潮,饮誉一时,甚至声名远播,流传至朝鲜、日本,深受当地文人喜爱。此词在朝鲜的传播情况受学界关注,柳基荣《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1]、杨焄《韩国历代和东坡词论》[2]聚焦李齐贤、赵冕镐等人的次韵之作,惜论述较为简略。此词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尚未见文章论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细梳理此词在朝鲜、日本的传播与受容,以期深化苏词研究、苏轼的域外接受研究。
一、《水调歌头》在朝鲜的传播与受容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依、海陆相通,有“千里同风,一衣带水”之说。中、朝两国交流历史悠久。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载:“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3]范晔《后汉书·三韩传》简述当时三韩的基本状况。[4]唐朝时期,金云卿、崔致远等人慕名赴唐留学,有意了解、学习中国文化。苏轼作为名噪一时的大文学家,其人、其文远近闻名。高丽中期文人金富轼、金富辙兄弟之名,流露出对苏轼、苏辙二人的仰慕之情,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八云:“尝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所慕云。”[5]苏轼作品传入朝鲜,最早约在元丰初年。据吴熊和《苏轼奉使高丽一事考略》,苏颂《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闻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诗四篇,以为异日相遇一噱之资耳》诗歌自注:“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6]时元丰二年(1079),苏轼正因“乌台诗案”身陷囹圄。[7]
《水调歌头》作为苏词经典,备受朝鲜文人推崇。李齐贤(1287—1367),字仲思,号益斋,高丽(918—1392)庆州文人。二十八岁时,奉召入元,与姚燧、赵孟頫等人往来密切,著有《益斋集》十卷。李齐贤心慕苏轼,其《苏东坡真赞》云:“金门非荣,瘴海何惧。野服黄冠,长啸千古。”[8]传神描绘苏轼精神风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奉苏词为圭臬,进行模仿创作。《水调歌头·望华山》承苏轼豪迈之风,全词瑰丽雄壮,余味悠长,“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烟霞深处,幽绝使人愁”明显化用“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句式相同,稍异字词,却毫无生搬硬套、机械呆滞之感。他以“烟霞深处”之“幽绝”替换“琼楼玉宇”之“高寒”,同样是为表达出世、入世的思想矛盾。不同的是,在壮丽奇特的华山面前,李齐贤顿生隐逸之思,“一啸蹇驴背,潘阆亦风流”[9],倒比苏轼多出几分清狂之意。李齐贤词追摹苏轼,成就斐然,夏承焘赞扬他“在韩国词人中应推巨擘矣”[10]。
除袭用《水调歌头》词句,朝鲜文人还喜欢步韵此词。李瀷(1681—1763),字子新,号星湖,李朝(1392—1910)后期杰出思想家,倡导“经世致用”,著有《星湖先生全集》七十卷。其《水调歌头·寄洪古阜叙一相朝,次东坡〈水调歌头〉》云:
山川正修阻,异地本洞天。白云何处飞绕,黄菊怨残年。夜梦蘧然来去,随意枫丹露白,无处不清寒。祸福有常命,夷险转头间。倚沧海,瞻斗极,悄孤眠。达人远瞩,不信觚破即成圆。众道攀援枝叶,我独推寻行墨,毕竟孰亏全?缅忆曾欢会,江汉杂花娟。[9]
此词为寄赠之作。首句寄寓对友人的思念之情,感慨二人相距遥远,山川阻隔,嘉会难再,只能在梦中缓解相思之苦。词人受老子思想影响,“祸福有常命,夷险转头间”,饱含哲理情思,与《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1],意义上一脉相承。末句追忆二人昔日欢会,再次表达对友人的想念。
赵冕镐(1803—1887),字明史,号怡堂,李朝末期著名词人,著有《玉垂集》。其《水调歌头·白牡丹》云:
南院石兰在,可是懒阴天。□□玉杯承露,谁记桂宫年。初卷锦帷香海,又呼锁烟笼雨,琼浆沁髓寒。夙世侬和你,那梦到人间。朝来笑,暮也困,欲成眠。何日归去,天上有月几回圆。倾国倾城堪唾,魏紫姚黄无数,雪操玉同全。白发怕堂叟,相对一婵娟。[9]
虽未提及苏轼,但通过比对可以确定此词为追和之作。两首词题材不同,苏轼中秋月夜怀念亲人,表达进退行藏的思想矛盾,赵词则以拟人手法歌咏白牡丹高尚纯洁的情操。与倾国倾城的“魏紫姚黄”相比,词人忠爱白牡丹的素雅、高洁,借此象征个人情操志趣。二词亦有关联,与苏词相同,赵词亦咏及月,且词人想象瑰丽奇特,词中亦出现谪落人间、想要乘风归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此外,字句上亦相承接,“谁记桂宫年”脱化自“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何日归去,天上有月几回圆”融合“我欲乘风归去”“何事长向别时圆”“月有阴晴圆缺”数句。“朝来笑,暮也困,欲成眠”刻意与原作“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形成对比。
高圣谦(1810—1886),字穉希,号甪里,李朝末期文人,晚年隐居,潜心著述,著有《甪里文集》十四卷。其《江南好·咏月,和赠黄声汝》云:
问尔杯中月,何术到长天。爱看清影孤坐,遥夜抵过年。若使明光长照,更有情亲同赏,胜似玉楼寒。方死方生理,天宇似人间。歌声亮,舞影乱,未成眠。畴千磨汝,冰如清莹镜中圆。怊怅江南远别,寂寞回廊独转,造化苦无全。多是有情物,随处向人娟。[9]
题目虽作《江南好》,但句式、韵律与《水调歌头》实为一体。词调往往一调多名,除了常用名,还有许多别名,可称之为“同调异名”。《水调歌头》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12]万树《词律》卷十四《水调歌头》注:“梦窗名《江南好》、白石名《花犯念奴》。”[13]清末民初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二十六亦云:“梦窗名《江南好》,白石名《花犯念奴》,名虽别,体实一也。”[14]此言承袭万树,但旧说多有讹误。秦巘《词系》卷六云:“《草堂》注姜夔词,名《花犯念奴》,吴文英词名《江南好》。今考《草堂诗余》有杨慎《花犯念奴》一调,而白石歌曲旁谱《水调歌头》二阙,并无《花犯念奴》之名。吴文英《江南好》实《满庭芳》之别名。”[15]王鹏运校注吴文英《江南好》亦云:“按此调即《满庭芳》,殆以坡词有‘江南好’句易名。《词律》于《水调歌头》注云‘梦窗名《江南好》’,《词律拾遗》谓‘与《凤凰台上忆吹箫》相近’,均误。”[16]可知吴文英《江南好》其实是因苏轼《满庭芳》(蜗角虚名)有“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17]之句而得名。笔者检吴文英《江南好》,确与《水调歌头》句法全异,而与《满庭芳》同,可证王鹏运之说。或许这种错误记载,亦传入朝鲜,误导了朝鲜文人对《水调歌头》词调的认知。从题序中“和赠”看来,友人黄声汝亦作同题之词。与苏词题材相同,此词亦抒发词人月下之思。苏词首句向天发问,尽显豪迈之气。高词首句便向月发问,何等奇思妙想。词人虽喜清影孤坐,月下独酌,但亦乐于亲友相伴,以抵“玉宇之寒”。词人亦主张顺应自然,正如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18],蕴含哲理情思,何尝不是一种达观。
此词不局限于词体,更“跨体”传播,对朝鲜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沈象奎(1766—1838),字可权,号斗室,李朝后期文臣兼学者,自幼即有才名,所作诗文得到众多文人肯定。其《寄叔度》曰:
东坡《水调歌头》,题以“丙辰中秋,欢饮达朝,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辛卯仲秋,病余独卧,离怀别感,岁不能自胜,遂绎坡词为长句以寄。
东坡先生曾大醉,水调歌城留替人。我亦把酒欲问天,天幸无语无可陈。琼楼玉宇最高处,又恐寒宵未易曙。虽有清影在人间,便欲起舞乘风去。转檐低户何皎洁,照人不眠增愁绝。为别销魂本恨人,月亦何恨兼怜别。不时偏向别时圆,倒是圆时偏觉别愁牵。一年明月阴晴外,能得团圆无几番。人生百年强半,忧患疾病相缠绵。又此离别劝经年,莫谓此事古难全。如此长久又可怜,不如无别亦无月,二身兄弟长得甘眠在一室。[19]
此诗作于晚年时期,诗人借演绎苏轼《水调歌头》,哀叹年华逝去,感慨身体之衰,抒发离别愁绪。此外,其《夜既深,又成近体》诗句“明月几时有,清光万里遥”“怅怅今何夕”亦直接脱化苏轼《水调歌头》词句而来。
南宋鲖阳居士首次解读苏轼《水调歌头》饱含“爱君”之思,其《复雅歌词》记载:
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20]
这种解说有附会之嫌,论词合于“风雅”之旨,正是《复雅歌词》一书的指归。但这种“误读”堪称“片面的深刻”,丰富、拓展了此词内涵,极大提升了此词的地位。这种记载亦流传至朝鲜,在诗话中多次出现,表现出苏轼《水调歌头》在朝鲜的影响力。如佚名《诗话类聚》“东坡爱君”云:
熙宁丙辰中秋,东坡居士欢饮达朝,大醉,作《水调歌头》兼怀子由。元丰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因得上尘乙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21]
此外,佚名《诗文清话》、南羲采《龟磵诗话》基本原封不动重复鲖阳居士之语,集中表现对苏轼“爱君”思想的推崇。宋神宗与苏轼之间的君臣和洽传为美谈,苏轼忠君爱国的完美形象在朝鲜文人心中根深蒂固,他们乐于对这种文人轶事加以载录,推动苏轼其人、其词在朝鲜的广泛流传。
二、《水调歌头》在日本的传播与受容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关系密切。中国文学传入日本之后,众多文人濡笔作诗,留下大量汉诗诗集。这些诗集屡被注释、解说,至今依旧被复刻、再刻。词这种文体在日本虽然没有受到如诗一般的待遇,亦没有诗那样的知名度[22],但即便如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苏轼词依旧通过各种方式流传到日本,对当地文学发展起着直接的启迪、借鉴作用。
据王水照 《苏轼作品初传日本考略》,平安朝(794—1185)后期左大臣藤原赖长《宇槐记抄》“仁平元年(1151)九月二十四日”条云:去年(1150)宋商刘文冲将《东坡先生指掌图》二帖等书赠给藤原。王水照认为此书可能是假托苏轼之名,但无论如何,这是东坡名字首次在日本出现。[23]此时距苏轼去世(1101 年)不到五十年。可知苏轼其人为日本文人所晓,约在1150 年。
《水调歌头》作为苏词经典,在日本广为流传且传播方式多样。首先,它借助词集得以传播。据日本现有文字资料记载,《东坡词》至迟在日本嘉祯元年(1235)由出使宋朝的僧侣带回日本。[24]普门院开祖圣一国师于1240 年从宋朝带回《注坡词》两册、《东坡长短句》一册。这些汉籍传入势必推动苏词在日本的传播。此外,还通过词选、词谱等书传播。元好问编《中州乐府》有五山翻刻本,金代“苏学行于北”[25],金人作词多受苏轼影响。《中州乐府》收录之作,多慷慨豪壮之音,词调也常袭用苏轼《念奴娇》《水调歌头》诸作,间接推动苏轼《水调歌头》在日本流传。[26]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林罗山手校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068)《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刊本,读耕斋词序云:“了的一日阅书肆,买得《草堂诗余》一本,想有意于唱腔,慢而如此乎。因任口赋三首寄之。”[22]江户后期浅野长祚《寒檠锁缀》云:“与诗余有关,有《历代诗余》《昭代诗余》、朱竹垞的《词综》、万红友的《词律》等,都是便利于填词之书。”[22]可知当时在日本,《草堂诗余》《历代诗余》 以及万树《词律》等皆是易于购得或日本文人为填词而学习、模仿的书目,苏轼《水调歌头》被收录其中,必然为众人所知。
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中国进入晚清阶段,虽受中日战争影响,且日本转向西方开放,但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学仍保持浓厚兴趣。这一时期,日本填词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森槐南、高野竹隐、森川竹磎等杰出词人,他们在日本填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森槐南(1863—1911),名大来,字公泰,号槐南小史,日本尾张(爱知县)人,诗才敏捷,著有《槐南集》。他十五岁开始填词,对作词充满热情,《百字令》自述:“仆心如水,住如烟如梦,如秋诗国……不知何苦,嗜诗仍甚于色。”[27]黄遵宪《续怀人诗》自注称赞森槐南“真京东才子也”[28],《补天石传奇题词》 叹曰:“后有观风之使,采东瀛词者,必应为君首屈一指也。”[29]评价颇高。森槐南醉心苏轼,《酹江月·题髯苏大江东去词后》“我思坡老,铁绰板歌是、森然芒角”表现出对苏轼的思念与崇敬之情,“便把大江东去意,试问南飞乌鹊”“君岂灰飞烟灭去”[27],化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词有苏词之风,夏承焘《域外词选·前言》赞曰:“日本词人为苏、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10]
明治十五年(1882),森槐南二十岁,作《水调歌头》云:
文章固小技,歌哭亦无端。非借他人杯酒,何以沥胸肝。毕竟其微焉者,稍觉可怜而已,到此急长叹。精神空费破,心血自摧残。论填词,板敲断,笛吹酸。声裂哀怨第四,犹道动人难。摩垒晓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谱就烛将灺,泪影蚀乌阑。[27]继《满江红》发表之后,森槐南便停止填词,转而创作散曲、传奇等文体,这首《水调歌头》是他再度填词的第一首作品。读此词,足以窥见词人的创作欲望不减反增。森槐南借这首词阐述词学观,他认为词虽“小技”,却是“借他人酒杯”“沥自己胸肝”的极好途径。填词亦难,即使费心费力,“板敲断,笛吹酸”,也很难写出打动人心的词作。词应表现词人“精神费破”“心血摧残”之“声裂哀怨”,所以他的词总体上充满感伤主义情调。正当风华之年,词人对填词心怀抱负,“摩垒晓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表明其对柳永、苏轼的企慕追随之心。
森槐南亦作《水调歌头》云:
皓月照人代,知阅几千年。既然盈者应缺,早自恨团圆。况个真销魂事,传作绝伤心史,谱入断肠弦。清泪忽如雨,飘散绿尊前。借君盏,浇我酒,有谁怜。闲情一赋,不妨信手粉脂拈。纵使牧之期误,肯学微之过补,逮道我无缘。但愿墙花影,永拂玉人边。[22]
首句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30]有异曲同工之妙,神思飞跃,探索人生哲理与宇宙奥秘。苏轼云“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森槐南却云“既然盈者应缺,早自恨团圆”,心中忧愁唯有借酒才能得到片刻缓解,缺少了几分达观。苏词结句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森槐南词云“但愿墙花影,永拂玉人边”,模仿苏词创作,表达美好祝愿,却不及苏轼眼界开阔。
高野竹隐(1861—1921),名清雄,号竹隐,别号修箫仙侣,与森槐南交情深厚,二人时有唱和,齐名于一时。森槐南作《贺新凉》二首寄赠竹隐,竹隐便唱和回赠,收到竹隐唱和词后,森槐南评价:“君以天才夙悟,能唱金玉之音。如读顾贞观寄吴汉槎词,凄惋独绝,一字动移不得。所愧原唱粗率,深有负于知己。”[22]自谦原作粗鄙,赞扬竹隐填词颇有造诣。高野竹隐喜爱苏词,明治二十年(1887)三月,他偶染微恙,闭门休养,模拟厉鹗《论词绝句》,创作十六首论词绝句,其一“江湖载酒吊英雄,六代青山六扇篷。铁板一声天欲裂,大江东去月明中”[22],是为歌咏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所作。其《水龙吟》“料琼楼玉宇,高寒空共,月明千里”[27],化用苏轼《水调歌头》词句,表明“江湖之意”。明治二十二年(1889)秋,竹隐作《水调歌头》寄赠槐南,词云:
天风吹散发,倚剑啸清秋。功名一念消尽,况又古今愁。漫学宋悲潘恨,休效郊寒岛瘦,恐白少年头。我欲乘槎去,招手海边鸥。吹铁笛,龙起舞,笑相酬。大呼李白何处,天姥梦游否。杯浸琉璃千顷,月照山河一片,万古此沧州。何似控黄鹤,飞过汉阳楼。[27]
颇得苏词风神,气宇阔大,风度超迈。“我欲乘槎去,招手海边鸥”,化用“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表达“功名一念消尽”之后对于超脱旷达境界的向往,与东坡词在情感上相互契合。“琼楼玉宇”是月宫景致,轻盈飘渺,“海边鸥”则给人以旷达悠远之感。
森川竹蹊(1869—1918),名键藏,字云卿,别号鬓丝禅侣,词作600 余首,是日本填词作品最多之人。其《得闲集》便是取苏轼《病中游祖塔院》“因病得闲殊不恶”句得名。他曾作《水调歌头》,词并序云:
病余未有一词,中秋之夜,月明如霜,夜色玲珑,恨如此良夜不得与故人共杯酒。独坐小楼,感怀无数,便赋商调一曲,拍牙吟诵,殆自不堪情也。
碧落听鸾啸,今夜最清寒。银河无影,冰壶濯魄露娟娟。云外桂枝香散,井上梧桐影转,秋气又阑珊。独自感情切,欢会记当年。思往事,默无语,倚栏干。良辰美景,恨无故旧共留连。皎皎月明千里,漠漠暗愁万斛,深夜奈难眠。何况玉箫响,吹泪更涟涟。[22]
森川竹蹊长期受病痛折磨、身心俱疲,《得闲集·自序》云:“予性多病,终年与药炉相亲。”[22]此词是词人疾病趋向好转、身体稍觉轻快之后的第一首作品,充满哀愁之情。与苏词相同,此词亦表达词人在中秋明月下对故人的思念之情。夜色朦胧、桂枝飘香、树影斑驳,如此良辰美景却只能独赏,词人心怀感伤,只能以笔自慰。如霜般的月光倾洒满地,照得孤独之人辗转难眠,追忆往昔与故人团聚欢会的美好情景,恰逢远处玉箫声起,更是触动了这无眠之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词人不禁声泪俱下。
铃木虎雄(1878—1963),字子文,号豹轩,日本杰出汉学家。其《水调歌头·对月怀人》云:
今夕是何夕,明月照关山。碧空烟断尘散,万里镜光寒。问汝何心相瞰,不省燕山客子,寂寞思怀酸。记玉钩高揭,笑语倚阑干。鹊惊起,星灭没,夜漫漫。汝如有意,须向他日照团栾。天上仙娥孤冷,地上幽人悬隔,别易会常难。清景虽云好,到底不堪看。[22]
选择《水调歌头》词调来写月下怀人题材,无疑受到苏轼影响。词句上亦相承接,处处可见苏词的影子。虽同样是“对月怀人”,以词来表达对远方亲友的思念之情,铃木豹轩却缺少苏轼宽广的胸襟与乐观旷达的精神境界。
除上述外,苏轼《水调歌头》对其它词调创作亦产生影响,森川竹蹊《好事近》“那更清风明月,问今宵何夕”、《桂枝香·中秋望月》“念天上人间倏忽,便今夜全盈,明日还缺”、《望汉月》“天上团圆镇如许,怎照遍人间离别”,细野燕台《人月圆》“碧天如水良宵永,玉宇自清寒”“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自古难全”等词句,皆出自对苏轼词句的模仿。
三、结语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经历了不断被传播、解读、接受的过程。正如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提出“5W”传播模式[31],作者、作品、读者、传播媒介在这一过程中缺一不可。苏轼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为其作品传播奠定了基础。《水调歌头》由于情感体验的普遍性、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的典范性,能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读者的心理需求,为其经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引用、化用、模仿、唱和等多种“再创造”形式,成为其主要传播方式。《水调歌头》在朝鲜、日本的“跨国”传播,使其在新“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命,这正彰显出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强大影响力。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探究经典作品的域外传播,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启示。学界应深入挖掘古典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充分了解读者的接受心理和阅读需求,努力创造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推进文化交流互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