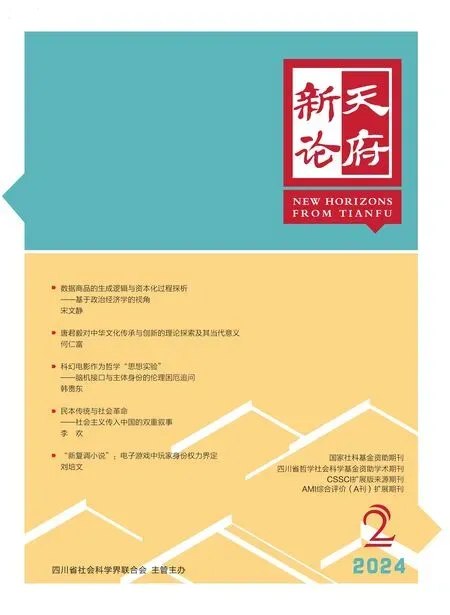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双重叙事
李 欢
民本传统是理解现代中国政治的重要路径(1)任锋、杨光斌、姚中秋、田飞龙:《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也是历史政治学阐释“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面。杨光斌曾提出社会主义与民本主义的内在连续性(2)杨光斌:《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表述问题》,《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叙事方式,这种内在连续性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来。 事实上,一些西方研究者早已注意到民本传统对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影响,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施乐伯(Robert A. Scalapino)等人通过考察梁启超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现,十月革命之前中国许多革命者将传统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论述,并本能地倾向于社会主义。(3)Robert A. Scalapino,Harold Schiffrin,“Early Socialist Current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un Yat-sen versus Liang Ch`i-ch`a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18,No.3,1959.而民本传统与中国革命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关系要更加深远,如法国著名中国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通过文人的乌托邦传统和农民阶层的平等主义抗争运动,论证传统中国与现代社会主义之间的“跨时代”的联系;(4)Jean Chesneaux,“Egalitarian and Utopian Traditions in the East,” Diogenes,Vol.16,Iss.62,1968.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现代中国革命仍然是朝着传统“大同”和“太平”理想前进的一个关键步骤;(5)Joseph Needham,“Social Devolution and Revolution:Ta Thung and Thai Phing”,in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eds.),Revolution i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61-73.沟口雄三则更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机制当作中国土生土长之物,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网络、生活伦理和政治理念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6)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24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1年,第120页。关于社会主义在清末民初的传播问题,过去一些学者以反传统的思维来理解,倾向于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否定传统思维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8)王进:《试论我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化,逐渐出现了一批正视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早期传播影响的研究,并以“民本”的概念对这一时期的传统思维进行总结。(9)孙代尧、路宽:《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付粉鸽、李强:《民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文化基因》,《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王刚、范琳:《正面与负面:民本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邱华宇:《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始阶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马藏〉第1部第1—8卷为考察对象》,《理论学刊》2022年第4期;吴增礼、胡鹏:《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关注社会主义早期传播时期的革命认知,亦未深入解释“传统—革命”的内在关联。传统与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传播的两种话语方式,在清末民初主要展现为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本文将考察两者既对立又融通的历史过程,以期厘清两者之间复杂的内在纠葛,这应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何种意义及何种程度上形塑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
一、民本传统与清末民初的社会主义叙事
“民本”作为一个概念产生于近代,内涵较为宽泛。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先总结为民本主义,并列举《尚书》 《国语》 《左传》中与之相关的语句证之。(1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8—45页。金耀基认为民本并非一家一派之言,也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思想概念:“凡为生民立命,凡为天下着想之精神,即是地道的民本思想。讲民本思想,若仅从‘民本’二字的字面去把捉、衡量,未免失之皮相了。”(11)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6页。广义言之,传统中国政治的许多内容都可冠以民本之名。民本最初与天命紧密相连,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秦誓》)。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民本才逐渐摆脱天命色彩,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12)《五子之歌》古有伪书之争,但今人考证对古文《尚书》真伪多有辩驳,不能一概否认。详见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贾学鸿:《清华简的文章体式与传世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江汉论坛》2019年第2期;刘光胜:《〈古文尚书〉真伪公案再议》,《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内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民本自始便与中国政治关系密切,并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完善。
若将民本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理论,可以说民本既是古代中国政治理论与政治合法性的源头,也是中国政治最具根本性的实践准则,中国古代政治在价值、逻辑和事实层面都笼罩在民本的规范和约束之下。在几千年的历史脉络中,中国发展出了一系列基于民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并使民本的关怀深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中。因此,当晚清民生凋敝、触目惊心之时,兼具西方智识的思想家们自然地转向一个与民本政治传统极具亲和性的外来概念——社会主义。面对清末的社会政治困境,思想家们一方面立足传统民本理想寻求出路,另一方面以传统资源理解西方先进思潮,社会主义开始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生长。
民本的逻辑起点是“生民”,是“足食”,因而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91年向中国介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时,开篇即说“夫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13)金竺山农、李提摩太:《保民新法论》,《万国公报(上海)》1891年第34期。。由于早期农业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匮乏,只有尽量做到均平,才能够维系“足食”的要求,故而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因此,1899年《万国公报》翻译《社会演化》时,第一章即说“民为邦本,古有明训,乃不能糊口者,偏屡见于民之中”,进而介绍西方为解决社会“不均”而奋斗革命的“百工领袖”马克思,并为马克思主义取了一个极具民本色彩的名字——“安民之学”。(14)本杰明·颉德:《大同学·第一章》,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万国公报(上海)》1899年第121期。在梁启超引进日本翻译的“社会主义”概念之前,西方的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经常将Socialism和Communism翻译成“人群之说”和“均产之说”。(15)伯纳尔:《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事实上,无论是“安民之学”还是“均产之说”,都体现着民本传统与社会主义之间极强的亲和性。
民本传统与社会主义的亲和性使得当时许多学人认为中国自古的民本传统即是社会主义。例如,严复在1906年翻译《法意》的时候,将老庄的民本理想与欧美社会主义对照说:“贫富之差数愈遥。而民之为奸。有万世所未尝梦见者。此宗教之士。所以有言。而社会主义。所以日盛也。此等流极。吾土惟老庄知之最明。故其言为浅人所不识。不知彼于四千余年之前。夫已烛照无遗矣。”(16)译者严复自注。参见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325页。老庄道家的民本理想固然追求均平,但较少付诸政治实践,因而更多人以儒家比附社会主义。如江亢虎在1911年写道:“社会主义,非西人新创之学说也,我中国夙有之,顾无能倡道之成一教宗,组织之成一科学者。”(17)江亢虎:《〈社会主义述古〉绪言》,载汪佩伟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江亢虎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蔡元培在1920年也以孔子和周制为例,说“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又说“中国本又有一种社会政策”。(18)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期。以传统认知解释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固然与时人知识背景有关,却也道出了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的一种内生的、历史的动力。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民本的大同理想、民本的平等主义和民本的土地意识。
“大同”是《礼记·礼运》中儒家民本政治的理想形态,在晚清时期被康有为重新唤起,成为维新者与革命者重要的思想资源。康有为立基于“公羊三世说”的《大同书》开启了民本政治传统向现代西方政治的艰难转向,这种转向之所以在理论上是合法的,是因为两者殊途同归:“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19)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梁启超于1901年12月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说道:“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20)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 951页。康有为的思维有着明晰的旧学理路,而梁启超称之为社会主义,看起来是本能地拿传统的民本理想对应他在日本接触到的西方社会主义。美国小说家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百年一觉》在1894年翻译出版之后,谭嗣同称《百年一觉》的西方理想世界“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21)谭嗣同:《仁学》,《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93页。。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意味着封建等级制的逐渐崩溃,当维系周礼的天命变得无常,平等主义思维也就勃发起来。(22)余英时引用《庄子·人间世》“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认为“庄子之说将‘天’‘人’关系推到了个人化的极致。不但如此,人人都是‘天之所子’,则地上人王独称‘天子’并垄断与‘天’的关系便完全失去了根据,而最初巫师所建构的‘天命’系统也不得不随之崩解了”。详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第38页。先秦民本政治的平等主义更多着眼于生活生产资料的均平,而这也成为学人介绍社会主义的关键内容。晚清学者宦懋庸注解《论语》时就说:“‘均无贫’即今日民生社会主义之意,由是而和而安则天下大同矣。”(23)宦懋庸注:《论语稽》,维新印书馆,1913年,第257页。1919年杭辛斋又以《周易》中《谦卦》之“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与社会主义相对:“皆今世社会主义之所主张,而《易》象已著明于数千年以前矣。”(24)杭辛斋:《学易笔谈》,岳麓书社,2010年,第230页。民本传统对生产资料平等的追求恰与西方社会主义的论述相照应。1903年杜士珍翻译日人所著《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认为产业的不平等要甚于政治不平等。在他看来,即使有“兵威刑戮”“暴君悍吏”,也不过“被困于一时”,而且难逃“当世之公论”和“后人之清议”,产业的不平等将导致贫困的不可逆转,“其受制之惨,有什倍其于政体专制者矣”。他进而回顾中国旧学说:“我中国唯列战大儒多有发明此意,末学流传,辗失师旨,而井田均产之法且见迂阔于后世,此亦足见中国学术之衰矣。”(25)译者杜士珍自评。参见久松义典:《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杜士珍译,《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5期。主张经济的平等,在传统的农业中国自然走向类似于“均田”的平均地权。
民本的土地意识在社会主义传入之初就被格外地标明出来,甚至贯穿了整个社会主义传播的历史过程。这种土地意识最初是农业社会的均田,而后又接受彼时美国社会主义“单税制”理论追求土地国有。章太炎在介绍社会主义的时候,始终观照旧学中对土地兼并的贬抑,其在初版于1900年的《訄书》中谈到:“是故有均田,无均富;有均地箸,无均智慧。今夏民并兼,视他国为最杀,又以商工百技方兴,因势调度,其均则易。后王以是正社会主义者也。”(26)章炳麟:《訄书:初刻本、重订本》,朱维铮编校,中西书局,2012年,第210页。严复则颇有民本的复古思维,认为西方社会主义的出现正是机器时代民生困顿所导致,因此将罗马田制的变迁与中国均田相连:“今之持社会主义。即古之求均国田者也。”(27)译者严复自注。参见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565页。1901年国人翻译《近世政治史》,在译序中谈到:“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社会云者,盖谓统筹全局,非为一人一家计也。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在将社会主义与均田制对照之后,又介绍德国社会党“麦克司与拉司来”二派,即马克思与拉萨尔。(28)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译书汇编》1901年第2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倾向于以土地国有来阐释其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理论,如1906年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三部分讲社会民主主义(国产主义):“惟土地国有,则三代井田之制,已见其规模。以吾种智所固有者,行之于改革政治之时代,必所不难。”(29)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1906年第3号。胡汉民等人宣扬的土地国有及在此基础上的“单税制”,事实上是吸收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将现代经济理论与民本传统进行简单比附。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无一不有民本政治的关切,无一不与中国传统相连。大同理想,孔子“均无贫”的平均主义,孟子“井田制”的土地意识,在晚清民族危机加深的时候“异乎寻常地急剧发展起来,从而迅速地为社会主义平等理想传入中国创造了重要的舆论基础”(30)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二、从社会革命看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特点
民本传统的一个重要困境,即是其复古主义倾向。虽然传统知识分子经常以这种“回向三代”的复古主义批判现实甚至改造现实,但其复古倾向仍然约束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方向选择。与这种复古相对,变革时代的另一思潮即进化论也沛然兴起。当社会进化的思想深入人心之后,西方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就有了传播的土壤。在进化论的熏陶下,民本的大同理想一变而为革命的社会主义。
经由严复介绍,《天演论》的社会进化思想对晚清时期追求救亡图存的中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进化的最后阶段自然备受推崇。1903年马君武从进化论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相与有密切之关系”,进而批评一些思想家将传统的“大同”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是“不知竞争不息之旨”。(31)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1903年第11期。而推崇佛家的章太炎,也认为社会主义与世界“随顺进化”最为切近:“亦惟择其最合者而倡行之,此则社会主义,其法近于平等,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32)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3页。以进化逻辑理解社会主义的思路影响深远,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创办的《民国日报》仍然以此来宣扬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之阶级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嬗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中极乐世界也。”(33)《社会主义教育机关》,《民国日报》1917年1月3日。
虽然社会进化思维有批判“大同”复古倾向的理论潜质,但同时也有人将作为理想的“大同”本身与其实现路径分割开来,并嫁接到“帝国—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的进化理路之中。1903年三合会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发行机关报《大同日报》,《新民丛报》转载《大同日报缘起》一文,称“今列国由帝国主义而升为民族主义,渐由民族主义而变为社会主义,似亦去大同世不远矣”。他们提倡以立宪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并说:“以中国贤圣所传天下学、大同学之种子,久经灌溉,岂忧其不繁生耶?”(34)《秘密结社之机关报纸》,《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号合本。复古的“大同”摇身一变,成了社会进化的顶点。事实上,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对于进化论、社会主义、大同理想的认知是较为模糊的,大多数人的论述方向更多取决于现实的政治需要。
随着现实的政治矛盾愈演愈烈,社会进化论开始走向以社会革命为路径的社会主义。在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看来,社会革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进化的逻辑延展:“凡吾辈今日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昔皆曾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此二主义非相反,惟今之主义较昔之主义为进化耳。”(35)《与友人书论新世纪(来稿)》,《新世纪》1907年第3号。对于一些接受日本社会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伴随社会革命的暴力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采取政治“暗杀”等活动。与之相反,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必将到来,但是否定暴力的社会革命,认为社会革命是野心家煽动乞丐流氓以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在他看来,“辨理的社会主义”不需要暴力也能实现,“盖辨理的社会主义与感情的社会革命,决非同物,非必由人民暴动举行社会革命,乃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36)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 453页。梁启超极力反对暴力的社会革命,并在1906年掀起了一场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但最终以革命话语的胜利而告终。(37)汪越:《从20世纪初两场社会主义论争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
在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看来,社会革命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也有着先天的优势。这一思路被同盟会的《民报》大力宣扬,如冯自由在解释同盟会的“民生主义”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弱小,社会革命的阻力就小,更适宜在政治革命之初即实行社会主义:“横览世界列国,其受资本家之害未深者,惟我中国;其能实施民生主义而为列国之模范者,惟我中国。”(38)冯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1906年第4号。朱执信在1906年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进行概念上的区分,认为“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并列举了汉代以来抑制兼并、尊农贱商的历史,认为传统中国政治就重视“细民”,“抑豪者而利细民者,中国自来政策者之所尚者也”。(39)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载谷小水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朱执信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第44页。朱执信以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论证了社会革命在中国的历史正当性。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仍以社会革命为重中之重,他在1912年的演讲中说:“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想要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事实上还是站在“细民”的角度谈问题,并以传统中国的社会特征立论,认为中国更容易实行社会革命:“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40)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319页。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经由社会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有了现实的榜样。1918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首先在《劳动》上声援俄国:“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正大光明的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41)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1918年第1卷第2号。这一时期的论述在表面上仍然延续着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思路,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呼唤后者,如北大的罗家伦认为“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但其对社会革命的理解已经有了不同,他认为社会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42)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通过社会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开始被学生们大张旗鼓地传扬,如孟真直接宣称:“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43)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社会革命的概念影响如此之大,俨然成了标明中国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主流话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社会革命在早期领导者的著作和党的官方文件中也频繁出现,并被视作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途径。(44)李永杰:《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概念的中国化理解与运用》,《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1期。
在社会主义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看似形成了各自的话语体系并且相互对立,实则有着内在的关联。然而,当我们指出这种内在关联的同时也要警惕对这种关联的过分夸大。正如张灏先生所说:“过分强调传统在现代文化的断层固然是错误的,过分强调传统在现代文化的延续性也同样是错误的。重要的是:断层与延续,脱节与承袭,不是有此无彼,互相排斥的文化现象,而常常是多少并存的。”(45)张灏:《传统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185页。梳理并澄清这种“并存”是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的应有之义。
三、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的内在关联
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的内在关联不仅体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线索之中,也体现在现实革命路径的选择之中。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纷纷在半传统半现代的中国发起了面向未来的革命探索。所谓的半传统半现代,不仅是指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是指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知识分子从历史中搜罗出一切传统的优势因素,期望以此理解吸纳最先进的西方思想。这种建立在社会性质基础之上的思想激荡,就表现为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的对立统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正是社会主义与民本传统的结合,使得中国革命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使得革命者的视角转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使得中国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时期(工人阶级占据少数)仍然服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政治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培育创造了独特的土壤。
传统的民本政治本身就包含着革命思维,如《周易》所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这一革命逻辑根本上还是以民为出发点,即《左传》中所讲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当政治的合法性从“天” “神”转向“民”的时候,民本政治就内在地包含了革命的合法性。因此,《礼记》在讲民本的大同理想之后,也提出如果政治家没有依循民本的规章制度,则会“在执者去,众以为殃”(《礼记·礼运》)。孟子、荀子也都基于同样的逻辑提出“诛独夫”的合法性。(46)《孟子·梁惠王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议兵》:“诛桀、纣若诛独夫。”传统社会中的一些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也是民本的政治逻辑使然。正如金耀基所说:“民本思想与革命思想实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一刀之两面,凡言民本思想者,必同时亦讲革命哲学。”(47)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2页。当然,传统革命与现代革命有着本质差异,但其出发点和话语的一致性毫无疑问有助于现代革命的宣传和发展。
民本与革命的密切关联为晚清之后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强有力的合法性支持。当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强政治批判开始显露出民本传统的时代锋芒,西学激越下的革命的热血随之澎湃。孙中山以“民生主义”指称“社会主义”(48)冯自由曾明确说明:“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详见冯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1906年第4号。,并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他既传统又现代的革命号召:“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49)孙中山:《发刊词》,《民报》1905年第1号。孙中山认识到“吾国治民生主义,发达最先”,却将政治革命置于社会革命的优先地位。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人们的革命思维开始转向,以陈独秀、李大钊主阵的《新青年》杂志为代表,“他们崇尚‘以民为本’的‘人心变动’,即所谓社会改造运动。因此,他们明显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改造方法,极大地看重平民及其劳动阶级的历史作用。”(50)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年轻一辈的革命家仍然笃信着民本,并向劳动阶层靠拢,逐渐认识到社会革命的优先性。
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都有着深刻的底层关怀,这也是两者能够产生辩证联结的根本出发点。在墨子刻看来,近代思想家接受西方的一个基本逻辑即是民生:“欢迎西方物质进步之前景的,不是那些怀有提高生活水平这一普通愿望的人,而是那些认为‘人的生计’这一问题是有最重要哲学意认的人。”(51)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从“人的生计”出发,民本的“民”就不仅仅是政治革命所要求的“人民”,更是社会革命所对应的“细民”。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同时意识到了这两者的重要性,一方面抨击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追求西方的政治革命;另一方面站在“细民”的立场以传统民本政治接引社会主义,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革命。当西方的社会革命宣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抗争时,中国则将“细民”与“豪右”的阶级对立扩大到农民与土豪劣绅的对立。民本传统和社会革命都要求关注底层,基于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底层就不仅是工人,还有农民。传统民本思想的阶层关怀在科学社会主义逐渐清晰的时候自然转变为阶级意识。李大钊实际上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种联系。在迈斯纳看来,李大钊与陈独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认识,即“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力量,无论其阶级构成如何,天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甚至认为中国有“中华民族固有的无产阶级意识”。(52)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49页、第250页。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天然倾向”和“固有的”无产阶级意识,无疑都与民本政治传统有着内在关联。也正是这种关联,使得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目光最终投向了底层的农民。
民本传统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与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革命内涵具有类似性。长期浸淫民本思维的知识分子赞赏平等主义的政策,如蒙文通评论经学家心目中的制度建构时说:“今学家的思想是一个万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井田制度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群众学校是在受教育和作官吏机会上的平等,封禅是在出任国家元首上的权利的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国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议政是在议论政治上的平等。”(53)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载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孔子讨论文集》(第一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15页。这种平等主义的根源当然是经济的平等,这也是民本传统接引社会主义的反资本倾向的重要内涵。吕思勉评龚自珍《平均篇》,认为经济平等是国情需要:“此篇大意,以贫富不齐为致乱之原。而以操其本原,随时调剂,责诸人主……故藉国家之权力,以均贫富,实最合于我国之国情者也。”(54)吕思勉:《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6页。以国家力量调节贫富,不仅是自汉代以来反“兼并”的历代政策实践,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潜在认知。
对传统民本实践和民本制度的历史认知,使得知识分子毫不费力地转向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冯自由认为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滥觞于中国”,又举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太平天国设立公仓等例子,进一步阐述道:“民生主义实为中国数千年前固有之出产物,诚能发其幽光,而参以欧美最近发明之新理,则方之欧美,何多让耶!”(55)冯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1906年第4号。而刘师培更是认为两千年来中国的共产制度一直存在:“共产制度,中国古代诚见施行;中古以还,仍存遗制。至于近代,共产之制犹有存者。”(56)刘师培:《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载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43页。对民本传统的历史追溯与对社会主义的先进追求混融在一起,这构成了当时人们的社会主义认知。孙中山在1912年的《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谈道:“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57)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507页。离开民本传统的思维链条,这种对社会主义的乐观追求就会变得难以理喻。
民本政治传统所塑造的思维本性,成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迈斯纳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得益于中国对商业的传统的敌对情绪和几乎是天生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那些反映中国特定环境的因素,则使从西方民主信仰到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比在其他情况下要容易得多。”(58)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第133页。若说上层知识分子因其理智的选择而接受外来思想改造社会,何以连那些底层乡绅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社会主义?事实上,虽然底层社会并不能十分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但我们却仍能在民本传统中找到其社会主义信仰的思想依据。在1923年河南新乡县的县志中,地方士绅将社会主义看作从家族亲睦向外推演的过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族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即国家主义,天下一家也。”(59)韩邦孚等监修,田芸生总编:《(民国)新乡县续志》卷三,1923年刊本,第72页。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底层士绅只是将民本的伦理理想与社会主义简单附会,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其平等内涵也逐渐凸显出来。1935年甘肃省镇原县的县志将社会主义追溯到三代理想:“前人所谓圣君贤主,平时必与民并耕于田野,自为饮食,自供饔飧以治民事,为天下任其劳,此殆今日欧洲社会主义之源泉也。惜其学说于孟子而外无有流传之者。”(60)钱史彤、邹介民监修,焦国理、慕寿祺总纂:《(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十九,俊华印书馆,1935年,第40页。甘肃虽然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较远,却仍能以民本传统对社会主义进行解释。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已经逐渐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事趋同。1936年河南光山县的县志谈道:“夫今日之世界,一社会主义之世界也。社会主义以能摇动人民者,为贫民争平均地权也。”(61)《(民国)光山县志约稿·财政志》,谦记商务印刷所,1936年,第14页。从简单附会到平均地权,底层社会依托着民本的传统思维,最终转向了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的信仰认知。
四、结论:民本传统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
在五四运动与传统决裂的背后,有一条传统与社会主义认知融合的“暗线”,正是这一蜿蜒强劲的“暗线”,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孙代尧、路宽谈道:“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话语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具备中国话语体系的 ‘外衣’,而且具备了融合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思考方式的复合‘身躯’,成为真正‘入籍’中国的具有强大亲和力的本土文化的一分子。”(62)孙代尧、路宽:《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传统与革命话语系统的差异被现实的革命问题消弭,最终走向了民本传统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
如果把1921年作为一个临界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一方面,民本的传统理解仍在论证中国施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完成于1921年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对比清朝与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时说,“中国自古行社会主义,政治家皆以防贫富悬隔为目的,故财产略均,富豪不出”(63)刘锦藻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8 252页。;另一方面,社会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两者正是在这同一时空下达成了辩证统一,民本理想作为反传统的传统,社会革命作为反西方的西方,两者逐渐交会融合于一个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65)王汎森曾以“反西化的西方主义,反传统的传统主义”解释刘师培的思想倾向。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244页。
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辩证统一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都立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这种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处于传统和现代交汇处,而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被动地、或隐晦地吸收了民本政治传统,并不期然而然地走向了两者共同的目的地——“中国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内含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即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唤起的中国自古存在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讲,早期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既是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同时由于民本传统塑造了中国社会革命所立基的社会原貌,因而本身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那样一个新旧之交的社会结构下,“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民本政治传统的根据,在于中国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而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根据,也在于中国的经济基础。正如杨奎松所说:“不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具有多少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立脚点,并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这无疑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与文化条件相适应的。”(66)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容纳民本政治而超越民本政治,在社会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上充分考虑中国的旧根基与新方向。其中,旧根基是小农,新方向是工人阶级。在旧根基上进行革命,需要动员小农;使旧根基具有新方向,需要无产阶级意识的普及,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归根结底需要工人阶级的教化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