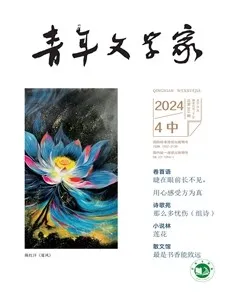《一句顶一万句》中“延津”的多重隐喻
林逸凡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上下两部分,利用地点的变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在提及的诸多地点之中,“延津”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全文共提到了一百二十多次。故事正是围绕着“延津”一“进”一“回”展开的,可以说是本书的起点与终点。据此,本文分为三部分对“延津”的隐喻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是上部内容,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探究杨百顺选择离开的原因;其次,是下部内容,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梦境中的延津和真实的延津有什么不同的意义;最后,是结语,总结了延津在本书中的中心位置。
所谓隐喻,即“一种隐含的类比,它以想象的方式将某物等同于另一物,并将前者的特性施加于后者或将后者的相关情感与想象因素赋予前者”(欧阳禾子《图形的设计隐喻分析》)。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格,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方式,而且还是一种语篇建构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文学语篇中更是如此。其中利用地点进行隐喻也是常见的手法,正如西塞罗所说“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一句顶一万句》叙事时间跨度大,故事情节平铺直叙,人物关系松散。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本书中有很多重复的语言和情节,给人以循环之感,而循环的支点就是“延津”。七十年前的杨百顺从杨家庄一步步走到了延津县城又最终离开,七十年后他的孙子又从山西沁源一步步回到了延津,这个巨大的时空循环中,“延津”發挥着不可或缺的力量,围绕着它呈现了一幅中国底层人民艰难求生的浮世绘。
一、精神困境的创伤之地
(一)“庄子”:传统家庭关系的破碎
《一句顶一万句》上部时间大致约在“民国”时期,但作者没有介绍当时风云激荡的社会大背景,而是选取了河南一个小县城,讲述底层人民的琐碎生活。故事的开篇是生活在杨家庄的少儿杨百顺,继而又引出了董家庄、魏家庄、马家庄等村落。在村庄的内部人物活动很简单:卖豆腐的、赶车的、剃头的,等等,众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彼此通婚形成了一个“熟人世界”,像是一张无形的网将彼此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人物关系众多的集体。就像阿莱达·阿斯曼认为的那样,“赋予某些地点一种特殊记忆力的,首先是它们与家庭历史的固定和长期的联系。这一现象我们想称之为‘家庭之地或者‘代际之地……在这样的代际之地上,一个家庭的成员像一个不断的链条一样生生灭灭”(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但是,杨百顺在此地的关系却并不亲密。首先是父子关系,父亲不喜杨百顺以“喊丧”作为梦想,他十三岁的时候为了去看“喊丧”间接导致家里的羊跑丢了,父亲不顾杨百顺正发着烧将他捆在院子里用鞭子抽打了一顿,又将其赶出家门。“又瞪大眼珠看着众人:‘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可以说,在这个家庭权力场中父亲是绝对的权威,是难以沟通的。但恶劣的不仅仅是父子关系,还有兄弟关系,当杨百顺被捆在树上抽打的时候,他的兄弟们在旁边偷笑,幸灾乐祸;当哥哥杨百业结婚的时候,杨百顺却只能站在茅房里填土。可以认为,杨百顺在出生地杨家庄中并没有感受到亲人间的温情与关怀,相反充满了压抑的痛苦,最终导致他选择离开家庭。这与人们印象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氛围不同。这个小小的“庄子”之中,不仅杨百顺一家是这样紧张、冷漠,其他人家中如老裴家、老曾家等也是充满了争吵和痛苦的。作者构建了这样一个关系扭曲的地方,其实也是在隐喻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破碎。《一句顶一万句》虽然没有提及当时的社会变迁,但是正值新思想传播的年代,西方文明对于传统乡土中国伦理本位的思想产生了冲击,所以“庄”里的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异变。而作者将人物的活动限定在各个庄子之中,更加剧了这份痛苦,最终唯有逃离才得以解脱。所以说,“庄”并非静谧的桃花源,而更像是终年下雨的马孔多。
(二)“县城”:欲望交织的失序之地
离开庄子的杨百顺只好来到了延津县城谋生,阴差阳错成功进入县政府里种菜过活。在这一时期,入赘吴香香家,杨百顺改名为吴摩西。这桩婚事办得仓促,因为两人各自有心中盘算。吴香香想要利用吴摩西“县政府”的牌子作为庇护,吴摩西则希望通过婚姻获得立足之地。因此,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感情结合的产物,也没有父母亲族的祝福,在后期不出所料地走向了崩坏。
有的学者认为吴摩西这次失败的婚姻暗含着夫妻人伦感情的失序,但是这种说法有些片面肤浅,真正造成两人婚姻破裂的不仅仅是人伦失序,更是因为人欲的滋生。首先是情欲,老高和吴香香两人均已有婚姻,但是也都和自己的爱人“说不着”,于是选择了私通甚至最后私奔。这种违反道德的情感却显得格外坚定,导致吴摩西在火车站看到了两人相互依偎在一起的画面放弃了杀人。其次是权力欲,由于吴摩西是入赘,吴香香在这段婚姻关系中占上风,总是将吴摩西说得一无是处。他自己也感叹“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说,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压着,怕是永无出头之日”。而家庭的权力场更是社会的权力场,当吴摩西没有被县政府开除时,人人敬他三分。但是当他被开除之后,他先是被倪三揍了一顿,又被孩童们戏弄,他与妻子的裂痕也越来越大。最后是暴力欲,吴摩西决定来到姜家讨个说法,作者详细描写了他砍杀狼狗的动作和狗血溅起了一身的模样,甚至让“吴摩西大闹延津城”流传了几十年。
但是,当杨百顺来到延津县城之后,最明显的还是生存欲。可以认为,杨百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摆脱生存困境,不再过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甚至会为此放下尊严。与严格意义上的欲望化叙事不同,刘震云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描写受到欲望支配的众生相,也没有直白地让欲望作为叙事的动力,而是让欲望在热闹的延津城中暗自涌动。
二、记忆深处的朝圣之旅
(一)虚构的延津:梦境与幻想之地
《一句顶一万句》的下部《回延津记》从七十年后的山西沁源展开。当年吴摩西的养女巧玲被拐卖到山西沁源后,被曹家夫妻买入改名为曹青娥,在这里彻底失去了和延津的联系。对一个遭受拐卖的孩子来说,延津代表着养父吴摩西的所在地,也意味着安全、温暖和理解,所以在曹青娥的记忆深处总是闪烁着对延津的思念。“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有趣的是,曹青娥总是将延津挂在嘴边,但是真正促使她动身前往的却是一个梦,在梦中失去头的生父让她想起养父吴摩西。“曹青娥突然下定决心要去一趟河南延津,看看另一个爹是也死了。不管是死是活,都想找到他。”梦境是虚幻的,但也是人内心的反映,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意念性。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梦境中的场景是一定具有某种能指和所指,梦者是经验世界或者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但梦境不是真的,由此说明梦的叙事是有象征特色的。而这里的梦境不仅推动情节的发展,而且表明了曹青娥对于延津的思念就是源自对父爱的思念。于是,当她站在没有吴摩西的延津街头时她只觉得陌生,“到了延津,发现延津跟别的没有去过的生地方没有区别。她小时候记得的延津,和三十三年后的延津,是两个地方……比这些重要的是,她没有找到巧玲时的爹爹吴摩西”。
“延津”这个地方在下部作品中总是出现在回忆里,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更不是仅代表着曹青娥一人的出生地,它更是在隐喻着无數漂泊在外的异乡人魂牵梦萦的精神港湾。似乎很容易到达,只需要买一张火车票;但是那里又是难以到达的,失去了理解自己的亲人,家乡也不再是家乡,归去也只会让人失望。就像十四岁的曹青娥一样迷茫,“但她脑子里是吵架的延津,实在的延津在哪里,千里茫茫,并不知道”,于是只好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庇护所。然而,很多人最终也没有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延津”。
(二)真实的延津:永恒的记忆之乡
牛爱国从来没有见过延津县城的样子,只是偶尔在母亲曹青娥的口中听说这个遥远的地名,更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延津。但当他母亲去世、妻子私奔,并且生活陷入了孤独迷茫后还是阴差阳错来到了延津。“昨晚进了滑县,除了觉得心不乱,还对这里感到亲切;原来以为亲切的是滑县,谁知不是滑县,而是滑县跟延津离得近。他一辈子没去过延津,没想到跟延津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在延津他找到了杨百顺留下的教堂图纸。“头一排是蝇头小楷:恶魔的私语;第二排是钢笔字:不杀人,我就放火。”关于这句话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放火”就是追求精神世界的理解,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因果报应。如今看来,这句话的隐喻应该从老詹、杨百顺和牛爱国三人的整体遭遇来解。
老詹,一个在延津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丰乳肥臀》中高大俊美的瑞典牧师马洛亚不同,老詹从外形上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延津老汉,传教一生不过八个信徒,甚至连传教地都失去了。这琐屑灰暗的人生境遇,老詹将它们概括为“恶魔的私语”,他抵抗着这些窃窃私语坚持不懈走在自己的道路。而七十年后物质条件快速发展,与之对应的却依旧是虚无的精神世界,这份空虚和不信任与七十年前是一样的,人伦秩序失序之后一直没能重建。因此,与其说牛爱国在寻找妻子不如说他在寻找自己,他和当年的祖辈一样面对生活的困境,只不过当年的杨百顺是肉体的生存之难,而如今的牛爱国更多的是精神的困顿。老詹和杨百顺的留言一体两面,像是牛爱国精神世界的两个部分。老詹构想中的教堂神圣和谐,隐喻着社会关系中超然世俗的精神品质,是摆脱了欲望控制的伊甸园;而吴摩西的那句狠话则象征着当今社会中存在的精神危机,信仰缺失后的孤独与苦难只好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出来。牛爱国兜兜转转终于在自己的记忆之乡深处找到了答案,延津作为从未去过的故乡为他指引了方向—去寻找真正说得上话的人。故事的结尾那一句“不,得找”,他向着老詹的方向走去了。
当莫言构建了自己文学世界“高密乡”同时,刘震云则选择依托故乡“延津城”作为文章叙事的暗线。对于上部来说,它是主人公生长活动的空间,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对于下部来说,它是活在回忆与记忆中的永无乡,为主人公构建了一个精神归宿。《一句顶一万句》全书出场人物众多,涉及了各行各业;跨越时间之久,长达半个多世纪;所写地域广泛,各个省份均有出现。内容如此琐屑,自然需要创作者合理安排。因此,作者选择了让主人公“出走”再“归来”,通过一个关键人物曹青娥将两条线连成了一个圈,而这个循环的圆心就是延津。著名评论家摩罗说过:“刘震云正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和精神探索者。他像鲁迅一样,他在我们最习以为常、最迷妄不疑的地方,看出了生活的丑恶和悲惨。”(吴义勤《刘震云研究资料》)刘震云本人曾经评价本书:“是我写作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部书。是我自个儿愿意送人的一本书。”回顾刘震云的以往作品,从《塔铺》到《我叫刘跃进》,本书的写作艺术是最成熟的,也是把“延津”塑造得最鲜活的,这也揭橥了刘震云以“延津”为中心的文学王国终将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