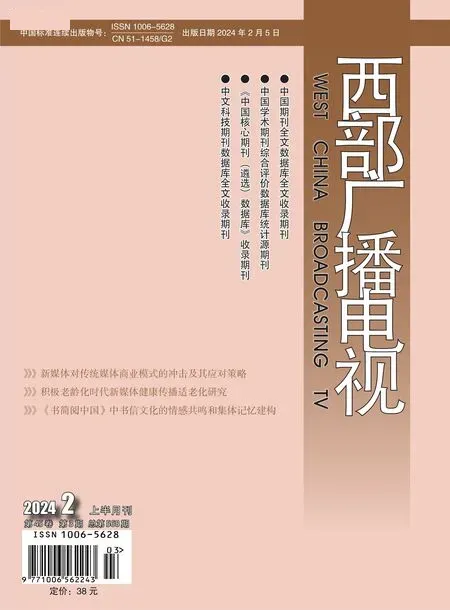福柯权力理论视域下对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仿生人“主体性”的分析
徐思涵 刘 端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观点“我思故我在”,将主体看作一个有着充分意识的思想着的行为者。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要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将运用自身理性和有进行抉择的自由能力作为主体性的两个核心特征。20世纪以来,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概念不断遭到质疑,如拉康提出主体性的建构必须经过“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连续过程,福柯则直接以“人之死”瓦解了主体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构建的赛博世界正是对主体性概念的一次巨大冲击,随着科技进步,当传统哲学中主体所具备的思维和理性同样出现在仿生人身上,人类和仿生人的边界变得模糊,“主体性应如何界定”成为赛博世界中人类面临的一大新难题。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的仿生人是否具备主体性?对于这个问题,廖明一在《后人类主义视角下对〈银翼杀手2049〉“主体性”的分析》中,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对赛博世界中的主体性进行新的界定[1];殷乐希在《拉康三界视域下的仿生人主体性建构——以〈银翼杀手2049〉中K为例》运用拉康的“主体三界”理论分析主角K建立“主体性”的过程[2]。基于以上研究,笔者选取福柯的权力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对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仿生人的“主体性”进行新一轮辨析。
1 技术与控制:赛博空间中主体性的变异
在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的赛博世界,人类在镇压旧型仿生人的革命反叛后重整旗鼓,大批量生产新型仿生人并借助他们对旧型仿生人进行处理,新型仿生人K在完成一次捕杀任务时,意外发现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在追查谜底的过程中,他的身上开始展现出人性的影子。以主角K为代表的仿生人是典型的“赛博格”,“赛博格”一词是由“控制论”与“有机生物体”构成的组合词,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被理解为人与机器的共同体。就生理上而言,仿生人在外观上与人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就心理上而言,K和露芙等高级仿生人有着鲜明的主观意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细腻的童年记忆。“赛博格”作为拥有生理实体和心理意识情感的存在物,与人类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传统哲学中诸如“我思故我在”关于主体性的界定已然失效,在赛博世界中,主体性的定义发生了新的转变。
“‘cyber’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舵手’、‘驾驶者’,在现代被运用于自动控制、信息通讯和计算机技术领域中。”[3]273“赛博”这个词语自出现伊始即被赋予了“技术控制”的内涵。知识与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技术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控制则和权力密切相关,“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这些基本的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4]30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权力是构建主体性的重要维度。影片中,人类正是由于掌握了生产制造仿生人的最高技术,才得以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阶层,并借助一系列权力程序,使得仿生人技术及其衍生出的统治制度占据赛博世界中的支配地位,从而进一步巩固人类的权力统治。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网络关系,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影片中,人类权力的网络关系以秩序的形式对仿生人进行全方位的统治。这种秩序体现在诸多方面:仿生人无法自然分娩,无须经历成长的过程;仿生人的记忆是后天植入的,尽管清晰且逼真但并不真实;仿生人的程序设计规定他们不能反抗上级命令,只能被动接受任务;仿生人不具备真正的情感,情感是程序设定的参数。从生理到心理,工作空间到生活空间,这些秩序无不标志着人类和仿生人之间的鲜明界限,权力通过这一系列严密的秩序弥漫在赛博空间中的所有场域。这种秩序并非稳定不变:旧型仿生人在见证了自然分娩的“奇迹”后发起了联合起义,试图对现有的人类权力进行反叛和革命。然而,这种努力最终导致了技术新一轮的优化,人类借助新型仿生人对旧型仿生人进行绞杀,以此对权力秩序进行重建和维护,仿生人为建构主体性作出的努力最终成为对主体性的倒戈。
在人类和“赛博格”界限愈加模糊的赛博空间中,人类作为知识技术的掌握者成为该空间中的权力阶层,一方面将仿生人设计成与人类极为相似的产品以充分发挥其工具效用,一方面通过秩序的形式对仿生人进行全方位控制,禁锢仿生人的“主体性”。由此可见,权力已然代替传统哲学中的理性思维等维度,成为《银翼杀手2049》中赛博世界里建构主体性的最关键因素。
2 权力与话语:仿生人“主体性”建构的核心
同处于权力阶层的人类相对应,《银翼杀手2049》中的仿生人可以看作是属下阶层,即从属的、缺少自主性的、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层。斯皮瓦克在《底层人能说话吗?》这一文章中强调了底层人“不能说话”的特征,她认为“能够认识和表达自身的而无法再现的底层主体是没有的”[5],底层人阶层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论断,在他看来,权力不仅仅局限于最高统治阶级,那些能够让别人听见自己声音的人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而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是权力的组成部分。人类针对仿生人设计了一套新型话语,首先体现在“去名化”的手段,名字是身份和话语的象征,名字的缺失即意味着话语权的缺席。影片多次提及名字:初见露芙的K对同为仿生人的露芙拥有名字这一事实表示惊讶,称“他给你取了名字,你一定很特别”;当K探寻身世之谜时,女友乔伊激动地为K取了一个名字Joe,理由是特别的仿生人理应拥有一个名字;当戴克问及“你有名字吗”,K报出了自己的代号,戴克立刻打断他说“这不是名字,这是序列号”。在相对宽松的生活场景中,警局里和K擦肩而过的人类警察毫不客气地把K叫作“人皮鬼”,人类老妇人用怪异的声音将回家路上的K戏称为“铁皮战士”。这些强制和非强制的一系列语言符号都试图达成一个结果,即泯灭仿生人的生理和社会属性以及强调其被生产出来的作为人类奴隶的工具属性。在各种调侃、戏谑和嘲讽的话语中,仿生人的尊严被一步步践踏,他们无法开口反驳,只能默默接受被看低和奴役的事实。语言作为一套符号系统,被人类用作驯化仿生人的权力武器,潜移默化地使仿生人日益接受了这套话语体系的规训。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福柯认为,权力创造了反权力,有权力必有反抗存在。阶级的不平等使得仿生人产生了极强的自卑心理,他们被规训的同时内心深处对话语亦有着极强的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仿生人反叛的前提。因此,无所不在的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也是建设的力量。这种反叛在主角K对自己身世之谜的勘察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K为了确认那个神秘失踪的小男孩是否就是自己,他违背命令四处探查,在新一轮的基线测试中显示出严重的偏离,不惜被追杀找到戴克探寻究竟。更甚者,K在与戴克交手时不经意透露出自己看过《金银岛》的事实。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知识和权力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权力制造知识(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4]29。K作为警官的主要任务是捕杀旧型号复制人,文学作品的阅读并非他的工作所需,反而文学的非功利性与仿生人的工具属性背道而驰。戴克和K作为人类科学技术的产物,难以对科学知识形成新的超越,却可以转而汲取文学的力量,通过知识的探索建构权力关系。
K并非单打独斗,影片中,仿生人成立了新的反叛组织,并邀请K加入他们共同反抗人类政权。组织首领向K揭示了所有秘密,她说:“我看见奇迹的诞生,一张完美的小脸朝我啼哭,哭声震天响……孩子意味着我们不只是奴隶,如果能生孩子就意味着我们能自己做主。”仿生人反叛军将自然生育视作权力的最显要象征,并将全部生命都奉献于这一事业,正如影片中仿生人所说,“跟即将到来的风暴相比,我们的命不值一提,为正确的事业牺牲,这是我们能做的最有人性的事”。福柯认为,“主体是通过种种被奴役的实践构成的,或者以一种更自主的方式,就像在古代那样,通过种种解放和自由的实践被构成的”[3]501。反叛军队的成立意味着仿生人不仅拒绝被奴役的命运,还将这种强烈的主观意志转化为群体性的革命行为。组建起反叛军的新型仿生人开始脱离失语、无意识的底层,进而朝着权力阶层进击,在集体意义上作出构建其“主体性”的突破性尝试。
3 监视与规训:仿生人“主体性”建构的悖论
尽管K和戴克等仿生人在个体或集体层面上作出了获取权力的一系列尝试,然而从旧型号被镇压的结局以及K和戴克在寻找真相中遭遇的诸多打击来看,仿生人脱离属下阶层的过程依旧十分艰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权力机制,“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4]226。如果将赛博空间看作监狱,那么掌握最高技术的人类就是监狱中的监管者和最高统治者,仿生人则是监狱中低级的、失语的、被囚禁的犯人。每一个仿生人都有着特定的编号,以便人类对其运行状态和行动轨迹进行持续追踪;仿生人的眼睛和耳朵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感觉器官,而是行车记录仪一般的监视系统,正是这种监管使得仿生人难以摆脱人类的控制。然而,由于仿生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强化,这种程度的监视已然无法满足人类的控制需求,他们随后吸取了旧型复制人发动起义的教训,设计了一套“创伤后基准测试”用以对仿生人进行更深层次的驯化。基线测试的本质是检查,“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4]208。该测试通过对仿生人的及时反应进行观察,判定其面部表情、语音语调是否由于任务内容出现异样的变化,进一步对仿生人进行规训。通过上述一系列技术手段,人类作为权力阶层对仿生人进行了透明、持续的全景式监控,全景敞视主义的赛博空间使得人类从一开始就取得了“避免任何物理冲撞的永久性胜利”[4]228。
在监视的基础上,人类为赛博空间这一新型监狱划分了“标示出差距,划分出品质、技巧和能力的等级”[4]204。这使得囚禁者在接受奖励和惩罚过程中主动接受既有等级体系,成为等级体系的忠实服从者,从而弱化其反抗意志。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的赛博世界并非简单将人类和仿生人划分为高低位的两个阶层,在仿生人内部同样有着森严的等级规定:位于最高位的是以露芙和K为代表的高等仿生人,他们拥有可以自由地进行空间移动的实体存在以及可观的工作、薪酬和生活环境。与之相对应的是乔伊等人所代表的低等仿生人。乔伊低等地位的最直接的表现在于,K的代码是AGCT四个字母,而乔伊的代码却只有0和1,作为低级程序的她需要借助特定设备才能从二维空间有限度地成为三维空间中的实体存在。影片中,K在露芙面前对乔伊的评价是“她很逼真”,可见乔伊于K而言仅仅是一种服务伴侣性质的产品,“乔伊”这个符号指代的是一切批量生产的女性仿生人伴侣。处于最低等级的是曾发动革命的旧型仿生人,他们由于具备移情能力和生育能力被人类视作权力的威胁者而被通缉和追杀。影片开头,面对莫顿对自己屠杀同类罪行的指控,K回答“我们不需要逃跑”,新旧型仿生人的区别在“追捕—逃亡”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转变为等级地位的差异。综上,《银翼杀手2049》中大致形成了“人类—新型高级仿生人—新型低级仿生人—旧型仿生人”的等级秩序。在赛博空间中的等级秩序中,权力阶层和属下阶层是相对的,K和露芙等人在接受人类的统治时,也对他们的属下阶层进行着有意或无意的剥削和压榨。
仿生人在这种森严的等级秩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来自人类的规训。影片中,K试图证明自己是自然出生,以此实现由新型高级仿生人向人类的跨越;乔伊努力地把自己“进化”为能与K有亲密接触的实体,实现由新型低级仿生人到新型高级仿生人的跨越。影片中这些仿生人跨越等级的努力正如反叛军首领所言,“我们都希望那孩子是自己”,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所谓“特殊性”来源于人类制定的等级标准,这种对证明特殊性的尝试本身就是对既有等级秩序的认同和服从,他们看似作出了构建“主体性”的努力,却并没能从根本上颠覆人类构造的权力话语体系。因而,在这种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视与规训下,赛博空间中仿生人“主体性”的建构成为悖论。
4 结语
影片结尾,得知真相的K终于意识到这种证明特殊性的尝试是无效的,他选择把珍藏的木马玩具交给戴克,微笑着目送戴克前去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相认。K最终脱离了既有权力话语体系的约束,他形成了同情心和自由意志,成功建构起了主体性。然而,人类仍旧通过权力话语体系对高智能的“赛博格”群体进行监视和规训。这或许是赛博世界里权力阶层的人类的一种成功,然而人类也应当意识到他们在后人类主义时代面临的新型危机:一旦权力体系丧失效用,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又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