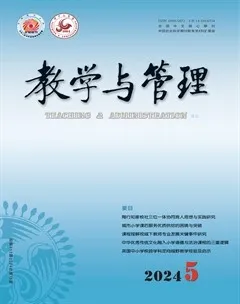新时代青少年政治认同的红色记忆路径研究
傅金兰 姬祥文
*该文为2023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重点项目“新时代青少年政治认同建构的红色记忆路径研究”(DEA2303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面对媒介记忆背景下红色记忆式微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集体记忆的时间化与空间化将青少年个体对国家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链接起来,从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红色记忆是增强新时代青少年政治认同的重要建构方式。教育者在尊重青少年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符号、仪式和实践活动等方式促进红色记忆对他们的积极影响,同时借力红色记忆媒介可以激发青少年的政治认知,通过话语沟通记忆增进他们的政治情感,使青少年真正产生一种“我们感”,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实践行动。
政治认同;红色记忆;媒介记忆;集体记忆
傅金兰,姬祥文.新时代青少年政治认同的红色记忆路径研究[J].教学与管理,2024(15):72-76.
每个国家都会以其所需要的政治理想培养青少年一代,以使他们能够积极认同现有的国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各个国家会采取与其历史发展相一致的教育措施,并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教育理想或设计运用到实践中去,以达致个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作为教育者需要找到能够把国家和新一代青少年联结在一起的记忆符号或实践活动,而整个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流集体记忆就成为这些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来源。
一、青少年政治认同的时空链接
信息传递的一般形态是时空结合的,即集体记忆的传播与传承既有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也有时间上的纵向传承。把红色历史记忆嵌入青少年内在精神世界的教育活动是一个提供积极社会记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分享了某一群体集体记忆的青少年个体可以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理清自己为什么会归属于这一群体,且为归属于这一群体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而回忆过去的重要历史节点需要人们主动提供特定的空间以使集体记忆被符号化、意义化,也需要提供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一个国家在过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的集体记忆不仅在空间与时间上是需要可视化的,它在青少年认同的内容上也应该是可感知的、有深度的。只有达到这些条件,其集体记忆才能在思想上触及青少年心灵,也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空间与时间上的集体记忆对塑造青少年的政治认同作用不同,发挥好这些处于不同时空中主流集体记忆的积极作用,对青少年群体的自我认识和政治认同都意义非凡。
1.集体记忆时间化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集体记忆,一个有深度的社会是一个有着自己集体记忆的社会。新时代的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有推动其发展的主流集体记忆。涂尔干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同一体,他认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需要基于一个共同的集体意识,我们在自己身上必须体现出来的全部人类意识,也只不过是我们所属群体的集体意识。”[1]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的集体记忆才使得人们能够凝聚在一起,也正是由于这些主流集体意识的存在,才保证了社会能够不断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
集体记忆的时间化主要是指集体记忆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延续与传承,它们能使年轻的群体成员时时忆起历史,以保持一种对过去的强烈认同,并使青少年在获得集体记忆信息和价值认同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成长。集体记忆时间化,表现为象征性记忆,它可以借助各类教育仪式来呈现。集体记忆正是借助于现今的媒介载体使个体形成对过去的理解和未来的规划。也就是说,集体记忆提供了一种链接,通过这一链接,社会构建了群体认同,实现了代际之间的文化记忆传递。例如,节假日日历所反映的就是一种在集体中被经历的特殊时间点,在各种红色记忆纪念性活动和各节日的庆祝活动中集体记忆得以不断复现。群体成员共同回顾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回忆过程中这种基于共同记忆的情感会被不断激发出来。集体记忆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就是通过大型节日庆典来复现或纪念这些重要历史事件,当这些重要事件再一次被回忆起,这些事件深层的意义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升华。这样青少年通过不断地亲身体验、学史明理,从而获取前行的方向和动力。
2.集体记忆空间化
集体记忆还与物质化的空间记忆场域关系密切。集体记忆的传播主要是指“集体记忆在空间维度上被更多的群体成员更深入地共享”[2]。通过记忆空间的再次展现,庞大而遥远的历史不再与我们相距甚远,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世界的历史都成为每个个体的记忆内容。集体记忆空间化具体可表现为物质性记忆或载体性记忆,它们承载于实在的物质之上并将记忆空间化或恒定化。通过这种空间化所塑造的社会典范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掌握历史发展与当下新时代的密切关联,并引导青少年去相信和遵循这些社会典范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首先,在纪念性空间中,空间是被主动赋予特定意义的。在此各种积极的、赋予深厚历史意义的红色记忆得以被寄放,并成为记忆传播的特有场域。红色记忆通过纪念空间的设置,形成具有符号意义与价值的红色记忆媒介。它唤醒了群体对重大事件的回忆与认同,从而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书写和传承[3]。在这种具象化的空间中,“政治仪式的时空要素为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历史记忆资源”[4]。这样积极向上的集体记忆就被有意识地刻画于外在的物质空间中。每一个纪念性空间也被赋予属于它自己的、区别于其他场域的内在精神价值和传承意义。纪念性空间中的传播内容就是这些纪念场域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是设计者设计思想的有意識表达或推送。这些被精心设计的集体记忆内容所传播的是一种可以被纪念、被回忆的情感和体验,能够凝练纪念空间的精神主题,实现正向价值的呼吁与传播。
其次,客观上空间化的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媒介记忆载体,携带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与价值浸润于个体和群体的精神和行动之中,推动了人们对权威典范的信仰与学习。集体记忆空间化传递着人类的生存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正是通过这个特殊媒介,特有的精神价值观、生活目标或信念态度得以被动态地保存和传承。纪念性空间通过时空叙事所呈现出来的象征意义,具有影响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内在力量,因为纪念性空间不仅被设置了具体的外在显现意义,更被赋予了抽象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实质上是时空叙事下的记忆再生产,并在对青少年的政治认同中发挥着体验这些经验和意义的作用。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情感与体验来塑造青少年政治认同所需要的价值观,可以产生更好的渗透力和教育效果。
二、红色记忆之于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图式场景
任何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都需要基于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红色记忆是集体记忆对红色文化的一种选择性建构,设计良好的红色记忆教育活动是新时代青少年形成政治认同的重要建构方式。
1.媒介记忆背景下红色记忆式微所带来的挑战
媒介记忆以各种符号作为记忆的载体。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自己沉浸于网络虚拟空间时,以纸张为代表的传统记忆载体就开始慢慢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退,数字记忆也就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媒介记忆的空间是自由而宽松的,也是零散而琐碎的。而且媒介记忆对青少年的影响渗透缓慢、不易察觉,其不良后果常常让人始料不及。青少年生活在基于电子媒介形成的文化环境中,需要依赖电子媒介获取信息,且这种依赖越来越强。而教育的使命就是要使学生不必在杂乱无章的媒介记忆中被动接受信息,而是要让他们可以主动选择,学会判断应该选择哪些信息、抛弃哪些信息。
由于我们的许多行动都被记录在媒介记忆中,并且可以通过存储器进行不断的访问,这样通过媒介记忆,个体随时随地可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5]。在借用媒介实现集体记忆延伸的同时,个体面临着被媒介记忆所“绑架”,甚至会出现主体性被削弱的风险。另一方面,集体记忆在媒介空间中不断地被置换,这样的改写最终导致的不仅仅是真实集体记忆的被遗忘,而且可能出现虛假集体记忆的盛行与蔓延。
在媒介记忆盛行的背景下,青少年更乐意将繁重的记忆任务交付于外部存储设备,不愿主动记忆和重温红色历史。这些浅层化的信息减弱了红色记忆对青少年的积极影响,而且红色记忆式微现象也日趋弥漫化。红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革命时代重要事件的积极建构与实践呈现。它们展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富强、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征程,赋予了新时代的青少年对厚重历史的正确理解。从对集体记忆的呈现到青少年内化这些价值与理念的过程是红色记忆发挥功能的重要体现。而目前由于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完全建立,可变性极强,他们很容易被庞杂的媒介信息所蒙蔽,因此还存在着青少年对红色记忆漠视甚至可能产生误读的现象。这直接导致了青少年对红色记忆的学习呈现式微与消解的趋势,而红色记忆式微则会使青少年群体难以形成与共同体身份息息相关的政治身份定位,而且现实中不是所有的记忆活动都会有效地激发起他们的政治认同情感。因此,将个体对国家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链接起来,并借助红色记忆来培育和建构青少年的政治认同,需要教育者在红色记忆教育活动中充分考虑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和发展需求。
2.通过红色记忆教育活动涵育青少年政治认同
认同是内化外在价值观念的过程。政治认同是一种感性的认知活动,是一种感情上和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它涉及对外在客观事物或符号的内在理解。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认同涉及个体对组织规范、约束等外在体制或符号的理解。红色记忆教育活动作为一种外在的实践活动可以增强人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理解,也为个体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能使他们体验到归属于一个更大共同体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将个体嵌入到特定的文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内,从而把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6]。
记忆本质上是一种已经完成的历史活动,红色集体记忆反映的是前人所创造的积极的过去,它能帮助我们建构对过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塑造新的身份,产生新的身份认同。但是红色记忆作为已经发生的过去与今人今事并不能自动建立起直接而有机的联系。将政治认同教育与青少年的思想和生活联系起来,是解决青少年政治认同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重拾所积累和共享的丰富的红色记忆故事。通过有效的红色记忆教育活动,青少年会对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与记忆产生更为鲜活的认识与理解,特别是在政治情感方面产生共鸣与深省,从而形成积极而稳定的政治认同行为。
红色文化是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汇聚起来的集体记忆表征,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家国情怀,具有极强的感召力。集体记忆为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成长背景或语境,同时他们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强化或重构集体记忆,这就尤其需要教育者的及时引导与帮助。学校组织积极主动而非放任自流的集体记忆教育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家国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有利于使个体更好地认识和处理自己的群体归属问题,寻找积极而正向的生活价值和生命意义[7],这样通过学校组织的红色记忆教育活动就能将以集体观念为背景的群体认同情感延伸下去。
三、借助红色记忆媒介创新青少年政治认同路径
在寻找红色记忆教育活动的创新路径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深入挖掘并遵循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心理发展规律,循着青少年政治认同发展脉络,从政治认知经由政治情感,最终实现新时代青少年所需要的政治认同行为。
1.打造隐性仪式场域,激发青少年政治认知
记忆不能仅止于一种知识性的记忆,更应该达致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即记忆的目的不止于知道或了解,而是要感同身受,但这种感同身受需要个体建立在对已知事件持续关注与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体验记忆,即个体的在场记忆,需要通过与纪念空间的在场互动而发生。个体通过一系列具身行为去体验、感受空间化的集体记忆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与意义,与纪念空间的时空叙事形成交互关系[8]。青少年群体借助仪式场域中的显性语言重温历史,并对未来的可能行为作出思考与判断,以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作为记忆的物质基础,身体的直接体验感知可能来得更清晰、更深刻,来自身体体验获得的具身记忆是一种客观实在,这是以身体体验为聚集、以世界作为“他者”而构成的记忆获得。在具体的红色记忆仪式场域中,仪式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它体现了很高的表达性,这种体现社会主流价值的象征或符号化行为对社会记忆中正确认知的唤醒起着弥足珍贵的作用,并能够引发在场个体产生思考与情感的共鸣,创建和强化共同体意识。
空间感比较强的仪式能够给个体提供一种亲身到场才能获得的体验,这是一种显性的仪式表现。隐性的仪式场域则能给青少年提供一个形成政治认同的氛围与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由内而发地唤起对国家认同的共鸣。由集体记忆空间化衍生出的纪念仪式更能突出其隐性功能,它将有关纪念事件和人物的价值导向渗透进个人和群体的思维模式中,成为影响大众情感和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空间化的集体记忆通过特定时空模拟、再现、唤醒历史记忆,这时隐性的仪式场域需要注意在追忆中激发个体的集体归属感,从而塑造国家发展所需要的青少年政治身份认同。隐性的仪式场域需要呈现一种富有感染力和认同感的符号意义,在这种主流价值形态的积极引领下,红色文化精神才能得以传承,并为青少年提供一种正确的社会价值秩序,从而为构建良好的社会价值导向贡献其应有的力量。
康纳顿指出,我们可以在各种纪念仪式中去寻找社会记忆及其踪迹。他认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社会记忆,很大部分是通过仪式活动的重复操演来传递和维持的。”[9]如此,红色集体记忆能够以各种典礼或仪式活动重复显现,使文化得以传承,价值得以展现。学校组织的红色仪式教育活动是表达政治信仰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影响青少年的政治认知方面,仪式表达的教育效果更佳。作为传播社会记忆的重要手段,组织良好的仪式教育活动能够将我们所期望表达的意义传递给青少年群体。通过仪式教育活动的反复操演,青少年群体可以深刻体验到活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庄严感与神圣感,从而内在地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认同,这是来自身体记忆,也是对文化记忆的深层体验,是一种真正内化了的红色记忆教育活动。要实现青少年群体的政治认同教育目标,学校组织教育活动更需要突出隐性仪式场域的作用,以多样化的仪式活动展现红色记忆的价值与内涵,使仪式真正激发青少年的政治情感,巩固政治认知,从而形塑政治行为。当然,在活动组织过程中,我们应该关注仪式所承载的内容,而不是外显的形式,特别需要把握仪式教育的隐性象征内容。打造仪式场域红色主题,激发青少年政治认知,就需要让青少年群体获得一种“在场感”:或体验到热血沸腾,或感动到泪流满面,或震撼到奋发向上,让这些红色记忆直达青少年的心灵,从而实现红色记忆价值的传承。
2.强化话语沟通记忆,增进青少年政治情感
虽然集体并不具备主动记忆的功能,但它决定了内部成员拥有什么样的记忆,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情感体验。群体成员之间的回忆也会通过不断的交流与互动得以深化。个体成员所记住的,并不只是他们从其他地方间接了解到的信息,还包括别人主动分享给他们的內容信息,这就需要话语沟通来促进信息的交流。“我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以他人为参照物,是在一个既定的、关于什么重要和什么不重要的社会框架中获取的,因为没有感知也就没有回忆。”[10]且这种感知也需要在话语沟通中不断增强其深度。客观的外在事物本身不会自动记忆,但它们作为特殊的表意或象征符号,通过话语传递,可以营造让人产生真实情感体验的氛围,从而成为激发个体进行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这些特殊的话语所营造的氛围,个体愿意使自己融入当下的情境中,并产生情感的共鸣。
首先,强化话语沟通记忆,需要把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考虑在内,因为个体积极的意识和记忆只有在参与这种互动时才能形成。具体来说,可以让英烈英模家属宣讲团通过“亲人”视角、“身边”教材,将真实故事真情讲述;让革命后代通过亲身叙说,以更生动的方式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青少年听,激励他们不断把自己融入家国情怀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红色记忆教育活动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把家国记忆与个人的真实情感联结起来,可以产生较好的教育效果。这些话语沟通记忆活动使青少年从英雄英模家属们的视角了解到那些勋章背后的感人事迹,受到触动。通过这些红色记忆教育活动可以使青少年在共情共鸣中收获精神力量。可以说,每一个纪念先辈事迹的日子,都是一次家国情怀的唤醒,都是一次还原真实记忆的历程,也是一次经历伟大精神的重要旅程。
其次,在话语沟通过程中,红色记忆教育活动需要锚定历史长卷中政治认同教育的闪亮坐标。通过与历史的对话,使那些定格在历史画卷中的面容熠熠发光,那些呐喊在历史长空中的誓言雄浑嘹亮。他们以或壮烈或深情的方式树起的一座座精神灯塔不断照亮一代代新青年前行的道路。学校需要组织青少年群体走进英雄,在实地探访中挖掘感人故事,把英雄的故事与青少年切身感受到的巨大变化融合在一起。在仪式教育活动中,可以让青少年感受到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英雄的光芒就隐藏在一封家书、一本日记、一句嘱托、一件小事当中。学校依托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清明祭英烈”等具有深度对话感、仪式感的活动,缅怀致敬革命先烈、礼赞歌颂革命英雄、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发广大青少年群体的爱党心、报国志,激励他们作为接班人勇敢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坚毅笃定地向着新征程阔步前行,这是对新时代青少年进行的一种比较普遍而有效的政治认同教育。
3.发挥场域复归功能,形塑青少年政治行为
集体记忆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并不能自发地对个体产生其应有的影响。纪念空间具有场域复归功能,但必须附之以丰富的体验化实践教育活动。缺少了对集体记忆的亲身体验,青少年就难以产生较强的政治认同行为,也难以形成精神凝聚力。设计良好的集体记忆空间能够提供有效的视觉具象体验,如以博物馆、纪念馆为代表的物理空间的记忆场域是需要精心打造的,也是红色记忆得以展现的主要场域。这些纪念空间的共同特征是必须存在纪念性的主体,即要有纪念的对象。通过空间纪念场域的打造,这些抽象物具备了政治认同教育所需要的崇高的、永恒的纪念特性,使青少年群体进入一个价值凸显的空间,实现人才培养锚定到具体化的目标。
记忆不是沉默的,建筑也不是无声的,那么,它们该如何发挥场域复归的功能呢?首先,要充分发挥场域的符号表征功能所具有的潜在力量。如纪念碑作为记忆空间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它可以延续或重塑人们的集体记忆,以潜在地影响人们作为参观者或学习者的个体记忆和政治认同。发挥符号表征功能的红色记忆纪念碑能够引导后人独立思考,激发他们对生活的反思。这些纪念性空间作为红色记忆的媒介,为个体在同一空间中提供了另一个不同世界的感知与体验资源,能够实现他们对民族与国家的政治认同。纪念碑让青少年不仅记住牺牲了的英雄,也让他们通过思考人的生命意义来反观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这方面看,“纪念性空间中对英雄主义的赞美是基于集体或群体观念的个人化超越,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引下,个体生命获得一种新的伦理意义”[11]。
其次,学校应在多样化实践活动中落实红色记忆的政治认同教育功能。如可以通过体悟活动来建构共享的集体记忆,提升青少年个体对于集体记忆中的人类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在亲身参与红色记忆教育活动的过程中能获得更直观的具身体验和思想震动,他们通过场域体悟活动来形成“我们是谁”的认识,领悟“我们应该怎样做”的行动纲领,最终形成一种“我们”的共同体意识。纪念空间的价值就在于它赋予人们的精神意义,且重在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群体成员通过亲身参与红色记忆教育活动,了解其意义与价值并获知其他成员也获得了相同的信息,从而产生“共同感”,形成或强化集体记忆,这样的体验化实践才能成为红色记忆教育活动的有效活动范式。
参考文献
[1]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54.
[2] 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31.
[3] 高月,翟光勇.纪念空间的转型对红色记忆的书写与传承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20(06):131-136.
[4] 杨惠,戴海波.政治仪式推进政治认同的逻辑与路径[J].现代传播,2019(10):30-35.
[5] 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8.
[6] 傅金兰.儿童政治身份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2.
[7] 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5.
[8] 邹润琪,孙佼佼,陈盛伟,等.红色博物馆的时空叙事与记忆场域建构——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J].旅游学刊,2023(07):36-51 .
[9] 保罗·唐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0.
[10] 阿斯曼,金寿福.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
[11] 赵海翔.人造的路标:纪念性空间研究[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1:74.
[作者:傅金兰(1974-),女,山东日照人,枣庄学院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姬祥文(2000-),男,山东枣庄人,新加坡斯坦福特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郑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