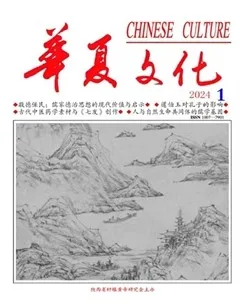对儒学核心之解读
袁泽宇
作为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庸》,历代思想家对其多有讨论,由此形成了《中庸》学史。儒家形而上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根本保障。然学界对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少有专著。以此而言,郑熊教授著的《(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6月)这本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此书对于想要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来说是值得关注的学术专著。
一、主要内容
在本书之中,作者确立的研究主线为:“具体探讨《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考察《中庸》学是如何带动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同时也考察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是如何推动《中庸》学的发展”(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页)围绕这条主线,书中的正文共有五章,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围绕前《中庸》时代的儒家形而上学思想进行论述,主要探讨《诗经》《易经》《尚书》《论语》以及郭店楚简等当中的零散概念,如中、庸、中庸、道、天等所蕴含的形而上思想。第=节分析《中庸》的形而上学,包括天道与人道以及联系二者的工夫论,还有天道与人道相结合所体现出来的天人合一思想。第三节是对孟子、荀子及《易传》中的《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进行论述。第二章是对汉唐《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延续与深化的论述。此章中,作者分为两节进行讨论。作者区分两节的标准不是简单地以汉代、唐代这样的时代为标准进行区分,而是以《中庸》学与形而上学的内容为标准进行区分。展开来说,作者在第一部分以汉代的董仲舒、郑玄,唐代的王通、孔颖达等人为中心,分析这些儒家学者对于“道”“中道”“中和”等概念的诠释。通过这些研究,作者认为此时的儒家形而上学并没有超越先秦儒家形而上学的内容。之后,作者认为中国的佛道两家对儒家的影响开始加深。也正是因为有了佛道两家的刺激,儒家的形而上学逐渐深化。在此背景下,此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韩愈、李翱等人对儒家形而上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包括第三、四、五章的内容。这一部分的主题是围绕“儒家本体论”来讨论儒家形而上学与儒家《中庸》学之间的关系。作者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儒家形而上学”的核心:“儒家本体论”。“儒家本体论”是在与《中庸》学的交互中逐渐确立。展开来说。书中第三章是讨论北宋理学的《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关系。作者主要通过对周敦颐、张载、二程及其后学分析此时《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关系。通过对这些人的分析,作者认为“儒家本体论产生于北宋,是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通过对儒家经典特别是《中庸》的阐发来建构的”(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196页)。第四章主要论南宋理学《中庸》学与儒家本体论的关系。作者通过对朱熹、张栻、陆九渊这三位理学大家的《中庸》学研究,凸显了儒家形而上学在这一时期的深化。更具体言,“儒家本体论”的深化就是指“儒家本体论与心性论的结合”(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196页)。此时,儒家形而上学在与《中庸》学的交织中逐渐呈现出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之境。第五章主要阐述的明清《中庸》学与儒家本体论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作者认为陈献章、湛甘泉、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等人通过“对《中庸》学达阐发实现对本体特点的深层阐释,涉及内外关系、体用观念等、同时则是对整个万物特点进行归纳,用实有来统括”(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271页)。
整体来看,整本书中通过对历史上各个时期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对《中庸》的阐释中呈现出《中庸》学对儒家形而上学发展的影响。《(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所反映出整个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是儒家继承三代思想文化,又吸收佛道两家思想精华后,逐渐确立“儒家本体论”的过程。
二、重要概念
要完成对“儒家形而上学与《中庸》学的关系”考察,就必须对此问题中的重要概念作出界定。从作者对此问题所涉及的重要概念的界定中,亦可看出作者写作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特点。首先,作者对儒家形而上学和儒家本体论做出了界定:“儒家形而上学就是指儒家围绕抽象的‘道进行研究而产生的学问……如果说儒家形而上学实现了从现实到抽象,把视角从有形有象的世界转向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那么儒家本体论则是在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天地万物的产生、发展追寻根据、根源”(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12页)。作者对于这两项概念的定义是在其充分总结学界对于中西方从古至今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反映出作者以中国哲学为本,以西方哲学为参考,以突出区别于西方哲学独属于中国哲学自身之问题的研究特点。这一特点还体现在书中一直都是以中国传统中的概念范畴为核心,如“中”“和”“体用”“本末”等,并在中国古代文献的语言背景下研究問题,而不是随意地使用西方的哲学词汇以解释古人对概念的理解。
其次,作者对儒家本体论的建构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两种方式:“天道伦理化为人性、人性本体化为天道,而且前者体现为下行路线,后者体现为上行路线,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天道与人性的同一”(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121页)。作者对于儒家本体论建构方式的研究,反映出作者秉持的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去面对研究对象。在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问题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研究者通过史料将自己代人古人的思路之中以了解古代哲人思想,可称为“走进去”;另一方面则需要研究者以第三者的身份态度分析古人的哲学问题,可称为“走出来”。如果只有“走进去”,则容易以古人为准,陷入“厚古薄今”之中。如果只有“走出来”,则容易苛责古人,陷入“厚今薄古”之中。只有将“走进去”与“走出来”结合起来,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
再次,在“儒家本体论”建构方式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种“天人合一”模式。作者提出:“《中庸》的天人合一关系来说其中的天-人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论语》等的延续,体现的是天命赋予人性,另一种则是天道之诚被赋予人道之诚。在这两种情况中,第二种就蕴含着天道转化为具体人性的思维模式在里面。”(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22页)这句话主要注意两个词:“赋予”和“转化”。用准确的词语以让读者理解所表达的相应意义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的关键。作者用“赋予”和“转化”,清晰地表明了“天人合一”是有“外在”和“內在”这两种模式。以“外在”来说,就是“天命赋予人性”。此日寸,“人性”来源于“天命”,说明“人”是从属于“天”。“人”与“天”虽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人”与“天”终究是两种不同的存在。以“内在”来说,“天道转化为人性”。此时,“人性”不再来源于“天道”,“人”不再是从属于“天”,“人道”与“天道”不过是某一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某一存在”就是书中所提出的“儒家本体”。以此来看,作者认为在“天人合一”两种模式的区分中,是以“儒家本体”为标志的。没有“本体”思维,没有“本体”,就是外在的“天人合一”。形成“本体”思维,确立“本体”,就是内在的“天人合一”。
三、意义所在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引文详实,概念明确,逻辑清晰,兼具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
从学术上讲,作者通过对《中庸》学和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揭示出以下五点内容。第一,揭示出《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互动性。《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二者互为主体、互为受动者。此外,毫无疑问的是,《中庸》学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思想本身就是儒家形而上学的表现。第二,《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是通过对道的相关内容的阐述凸显出来。第三,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是分时期、分阶段的。第四,这二者与儒学与佛老的关系相联系。第五,《中庸》学相比于易学,对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352-357页)
从理论上讲,从21世纪开始,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向世界,更加全面深入地吸收、了解外国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所一直强调的“海纳百川”,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但在这种中西交汇的背景之下,中国仍然应该坚持自己的文化自信。要做到如此,就需要学界在研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时在借鉴西方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用更为科学的,符合当今时代的方式予以研究。此时,在思想史的研究中,研究就需要回归古籍文本,以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概念、范畴、命题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要借助西方哲学的优点。毫无意外,《(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一书做到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