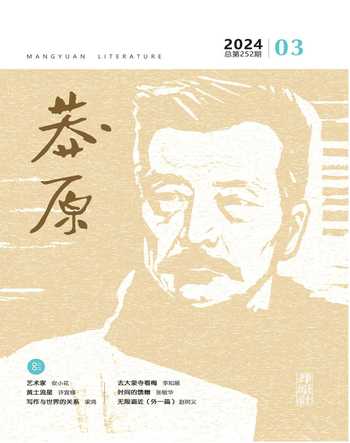黄土流星(小说)
许宜修
祖父归来那天,是我第一次对父亲动手。我打肿了父亲的脸,父亲的两颗牙齿也在我的拳头下摇摇欲坠。像儿时父亲拎起我那样,我拎起了父亲。我等待着祖父的下一道指令,所以我仍五指紧握。想不到祖父却跟个顽童似的,溜到父亲身后,狠狠地踹了他儿子两脚。
那是傍晚,我记得太阳沉得很快。我每吃一粒枣,天空就挂起一颗星。我看到有颗星似乎被黄土地上一只看不见的手拽住,起先带着不情愿的抵抗,缓慢地滑行着,但很快就架不住大地之手的蛮横,或是得到感召,闪烁间急速坠下,在天空撕出一道滚烫浓烈的白痕。
我说,流星!父亲闷声抽着烟,还没来得及抬头,祖父已站在了他面前。
现在回想起来,当我们看到祖父时,都吓坏了,说是魂飞魄散都不为过。三个月前,父亲埋葬了祖父,可这位本已入土为安的老人此时又站在了我们面前,双手背后,像看秋收时的庄稼一样看着他的儿孙。祖父的脸上是平静的疲态,晚霞一寸一寸从祖父身上褪去,衣裤外粘着的一圈肉眼可见的尘土也在夜幕中走向暗淡。祖父仿佛不是在黄土里沉睡了三个月,而是照常去田间忙活,像黄土高原上所有的庄稼人一样,满身风尘,披星而归。
祖父没有理睬我们呆在原地的傻样儿,只是绕着窑院走了一圈又一圈。看得出来,祖父对这三孔新箍的窑洞很满意。尽管祖父活着时半辈子奔波劳碌,一辈子寄居他处,但他儿子在这片他从生到死的黄土地上完成了他的遗愿。祖父去世后,父亲不顾众人反对,冲破一切阻碍,硬是用最短的时间箍起了三孔亮堂堂的窑洞。打地基、修拱顶、铺防水、盘炕灶、刷窑顶、装门窗……挖掘机、推土机和压路机在黄土地上持续轰鸣、颤抖,这方高原的角落焕然一新。工程队用三个月时间走完了祖父准备了一生的箍窑路。三孔窑洞箍好后,父亲在硷畔上放了数不清的鞭炮。满地红色炮屑像山丹丹花瓣,洒在黄土地上。鞭炮炸响后冒出团团蓝雾,随风远逝,炮音缠绕我们的身体,回旋不绝。不知是不是浓烈的硫硝味太刺鼻,呛得父亲流下了眼泪。
父亲常提起祖父曾对他说的一句话:不蒸馒头争口气。父亲就是靠这句话撑到了新窑箍好。哪怕我们早已在城里安家,除了一次暖窑仪式,再没住过新窑,但三孔窑洞像三个壮实的后生,立在院前,立在村里,板板正正的,父亲就觉得值得。我曾不止一次听到父亲喃喃自语,这下好了,我们有根了。但父亲怎么会想到祖父还能亲眼看到这三孔窑洞呢?父亲怎么会想到他只是烧了新窑的照片给祖父,以此告慰他在天之灵,祖父就像受到召唤般归来了呢?所以父亲僵在原地,像一块烈日晒干的泥巴,在思索天地间的隐秘,任凭祖父绕着窑院转圈儿,扬起细微的黄尘,化作闪着亮光的情绪粉末环绕他,使他鼻子发酸。
起風了,月亮轻移,山影颤动,月光掠过黄土地,在高原的沟壑间游走。祖父停到父亲脚边,踩住了父亲的影子。他看着父亲,说,有几件事没弄清楚。祖父的嗓音变了,不再是那种常年吸烟袋锅熏出的混着痰音的粗犷,而是像石头滚落崖底发出的那种模糊而低沉的闷哑。祖父见父亲没有反应,继续说,我回来有几件事想弄清楚。祖父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儿石头滚进父亲的胸腔,从四面八方围剿他的心脏,堵得他喘不过气来。后来父亲对我说,其实那时他很想开口说话,也想好了要说什么,可是祖父的声音压住了他的嘴唇、舌头和喉咙,不要说开口了,父亲甚至都不敢拿正眼瞧一瞧归来的祖父,只是盯着祖父的黑布鞋头,和影子一块儿默不作声。
祖父叫我的名字,小宝,小宝!祖父用手指戳着父亲的额头说,打,打他。替我好好教训这个不孝子。
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冲动,二话不说就替祖父教训了他的儿子。祖父的声音遥远、苍茫,带着雾气般的混沌,像电波穿透我的肉体,震荡我的神经,向我发出紧握双拳的信号。我以为父亲的身体会和我儿时他揍我的拳头一样坚硬,想不到父亲的骨头早已被岁月侵蚀得像面团一样松软。我的拳头让父亲去镇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父亲的腰受到了损伤,还换了两颗牙齿。此后每年我们去给祖父烧纸,父亲磕完头,都要我扶他,他才能艰难地起身。我还记得父亲躺在病床上,又好气又好笑地摇着头对我说,你是个好孙子,但不是个好儿子。
我原以为祖父归来,要对父亲箍窑一事予以赞赏,或对父亲为他举行隆重的丧仪表示满意,却没想到祖父首先指责了父亲对婚姻的失败经营。祖父踹了父亲两脚,父亲往后退了三步。祖父的脚力带着棺木的沉重,使父亲和他的影子在月光下左摆右荡。祖父站在硷畔上说,畜生!多好的儿媳妇,让你这样糟蹋!父亲听罢,脸色和月光一道儿发白,黄土高原的夏夜温和凉爽,他整个人却像在结霜。
在我印象里,父母吵架几乎像他们的血液流淌在我血管里一样不足为奇,可以说,我生下来还没跟父母学会说话,就先听懂了他们吵架。三个月前,母亲离开了我们。母亲离家和祖父去世只隔了一天。父亲看着母亲脱下丧服,摔门下坡,却不挽留,只是大口嘬烟。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砸盘撂碗的阵仗,搞得父亲的脸面和灶台一样狼藉;也没想到母亲会甩出早已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把我们父子俩晾在硷畔上。盘子的碎片割破了母亲的手指,有块儿碎渣在锅内弹起,戳红了父亲的鼻头。母亲本想用带血的手在父亲脸上狠狠砍一巴掌,但她看了看我,神情复杂地收回了手掌,转而用滴血的手轻轻抚摸了我的脸颊,在我脸上留下了一道血痕,然后猛地掀起窑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跑下坡去追母亲,才发现母亲走得那样迅速,那样坚决,我连她离去的方向都没搞明白,连她远去的背影都没看清楚,只有脸上的那道暗红还在我皮肤上跳动。那天,父亲和我圪蹴在硷畔上,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们都憋着话不说。他不说,我也不说。父亲总是这样,一遇到事儿,就把话都放在尼古丁里吞吐。祖父归来前,我们一直在寻找母亲,但每次都无功而返。我们能想到的地方都去了,能想到的人也都问了,但母亲就像黄土高原上夏天的雨水一样,落到地上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那天傍晚,我们在窑院前乘凉,像往常那样一言不发。不知过了多久,我抬头看到流星破空,父亲第二次看到了祖父。
我们祖孙三代挤在窑洞里,抽烟、拉话和吃饭。我们都饿坏了,连菜带汤呼噜噜喝了个干净。祖父一口气吃了三个馒头,又掰下一角馒头蘸菜汤。祖父说,春琴蒸的馒头还是那么好吃。春琴是我母亲的名字。祖父弥留之际,想吃馒头,母亲蒸了一锅又一锅。馒头白得发亮,连水蒸气都变得异常松软,祖父却吃不动了。也许那时母亲就已经决定要离开了,所以才把馒头一个一个摞在寒窑里,任凭它们在时间的积淀中越来越坚硬。祖父生前跟我讲过,我母亲蒸的馒头是前村后庄最白、最圆也最暄软的。祖父当时拧着父亲的耳朵,翻过一座山,蹚过一条河,去外祖父家提亲。母亲的手艺征服了祖父和父亲的胃。喝酒划拳间,两位老人已成亲家。此后,祖父每月都找他的亲家喝酒拉话,直到外祖父两年前病重离世。一开始,母亲并不愿嫁给父亲,甚至想违背父命,跟着她的相好一道儿走西口。可外祖父警告母亲,你如果不愿意,老子就打断你的腿!外祖父并未真的打断母亲的腿,但母亲的强烈反抗却换来了外祖父的数顿打骂。外祖父的病可能就是那时候气出来的,他不能接受一个不听他话的女儿,更不能失去一个能喝酒喝到一块儿的亲家。母亲是外祖父找人硬抬上轿子的。母亲下轿后一瘸一拐的样子在喜庆的人群中并未引起注意,鞭炮、唢呐和孩子们的欢闹使人们忽略了新娘脸上的泪痕。新婚第二夜,母亲偷偷跑回娘家,却被外祖父的巴掌和外祖母的笤帚打出了家门。外祖父把母亲绑在一头毛驴背上,翻山过河,押还给祖父。后来,母亲随父亲离开村子,进城,打工,持家,吵架,又生下了我。随着我越长越高,母亲对人和事的失望也越筑越高。在时间的长河里,母亲亲手溺死了真正的自己,一个陌生女人取代了她。母亲活成了众人口中的贤妻良母,一晃二十五年有余。
毕竟三个多月没吃没喝了,祖父饿得厉害,我和父亲已经放下碗筷,打起饱嗝,祖父还在拿铁勺刮锅底的菜汤。因为吃得太急,我看到祖父咬断了一截筷子。祖父“噗”的一声吐出筷子头,又继续埋头喝汤。在熟悉的陕北烩菜的滋养下,祖父原本风尘仆仆的脸庞,变得油光满面,身上那股旧衣服的霉味和潮冷的棺木释放的土腥气,也被迅速蒸发掉了。祖父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圆润起来,皮肤又黑又亮,在灯光的反射下,像紧绷的鼓面。祖父抹抹嘴,摸摸肚子,看看儿子,又看看孙子,心满意足地笑了。
父亲在做饭、吃饭和洗碗的过程中渐渐接受了祖父归来这一事实,他原本的震惊和恐惧在祖孙三人吃菜、掰馒头和喝汤的声音中消解了,甚至祖父抓起第二个馒头的时候,父亲多看了祖父一眼,神色中是难以置信的欣喜。父亲后来跟我说,他一开始真的以为遇到鬼了,完全是汗毛直竖的惊惶,整个人像被祖父棺材板上锈蚀的铁钉牢牢钉在原地,但是猪肉、油辣子和小麦的香气,还有祖父对着窑洞内的灶镬、炕围画和各样家具问这问那的好奇样子,让父亲卸下了被恐惧支配的担子。父亲说,那是谁?那是我爹呀!就算是鬼,也是我爹,我有什么可怕的?父亲还对我说,那三孔窑洞我是为他箍的,也是为自己箍的,更是为你箍的。人穷不能志短,人死不能复生。谁都知道我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想不到他还能回来亲眼看看这三孔窑洞,想不到他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的儿子把他的儿子揍了一顿。
祖父打了个饱嗝,盘腿坐到炕头,靠着铺盖,还在重复他说了很多次的话,有几件事没弄清楚……我回来有几件事想弄清楚。我想父亲和我一样,不知道祖父到底要弄清楚哪些事,而且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祖父到底弄清楚了哪些事。祖父归来以后,我们才发现他生前身后都是个谜。父亲和我静静地等着祖父的下一句话,我们竖起耳朵,连鼻息都轻了。可没想到父亲听完祖父的话,眼眶瞬间红了,只是张了张嘴,却没有回答。
其实父亲那时无论做出什么反应,我都是完全理解的。我知道父亲那时欲言又止,如鲠在喉,不是出于对祖父归来的恐惧,因为恐惧已消散;也不是刻意有所隐瞒,本就没什么好骗祖父的。父亲只是不想回答,或是没想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刚过去三个月的悲痛仍皱在心间没有熨平,又或是祖父的突然去世掐断了父亲在外地经营数年的事业线,更重要的是,父亲没想到再次问起这件事的人,竟会是祖父自己。父亲没有说话,他还能说什么呢?从小到大,父亲在祖父面前不知撒了多少次谎,但死而复生的祖父就是为真相归来,你让父亲怎么说谎?于是父亲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祖父掰开盘腿,撑着膝盖,从炕上站起来,看着父亲哭,神情难辨。祖父的脑袋和肩膀遮住了窑顶灯泡发出的光,窑内猛地暗了下去,窑壁上投出祖父又黑又长的影子。祖父没有再让我动手教训父亲,我也没有办法止住父亲的眼泪。祖父冲父亲说,你哭什么?这窑里谁都能哭,只有你不能哭。你嫑哭了!父亲没有因为祖父的话而停止哭泣,祖父又冲他喊,哪个受苦人像你,说哭就哭呀?哪个出门人像你,光哭不说呀?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哭什么?
父亲已经哭成泪人了,他的嘴唇像是被眼泪粘住了。他像个孩子似的在哭,也像个孩子似的看着祖父。父亲泣不成声的样子,也让我眼眶湿润了。我知道父亲是不可能回答祖父的问题了,而祖父因他儿子莫名其妙的眼泪,正陷入烦躁与愤怒的旋涡。于是我回答了祖父的问题。我知道这是我该做的。父亲的眼泪让我明白,我必须更迅速地扛起家族的一部分旗帜,直到父亲将它全部交给我,正如祖父曾对他所做的那样。而那一刻,将是我为下一代摇旗呐喊的开始。
我和祖父一直拉话到天亮。祖父听得很认真,几乎没有打断我。只是在我讲述的关键处补上一声“嗯”,或把目光从我的嘴巴移到父亲的脸上,像在思索着什么。父亲在后半夜完全成了一个孩子,不听话,不说话,只是哭,哭着哭着,打起了哈欠,而后很快就睡着了。我的话音和祖父的鼻音非但没有吵醒父亲,反而成了父亲的助眠曲。父亲蜷在被窝里,鼾声连绵,似在做梦。恍惚间,我竟觉得父亲正在收筋缩骨,重回孩子般大小。我的讲述就在那时中断了,没有再继续下去。祖父仍在思索,他的目光定在了父亲脸上。黎明第一束光射透窗纸的时候,祖父发出了他归来后的第一串笑声。祖父喃喃自语,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我就是这么死的?我看着熟睡的父亲,点点头。于是祖父平躺在炕上,盖上被子,闭上眼睛,对我说,是这样吗?我说,左手还差个酒瓶。祖父睁眼,招呼我,快去帮我拿瓶酒。祖父一口气喝掉了半瓶白酒。在瓶口离开嘴唇的那一刻,他的脸就红起来了,五官似乎各自晃荡开来,酒气渗出肌肤,窜入空气,呈灰丝状游移不止。晨光通过酒瓶折射出炫彩,我看见酒气满溢,氤氲在门窗上,似要重新发酵。我们仿佛不是身处窑洞,而是置身于一孔明晃晃的酒窖。
在我記忆里,祖父永远是这样一副醉态。他喝酒上脸,但贪杯。爱红火,爱拉话。无论喝多喝少,他都能和人划两拳,或吼几嗓子信天游。我的童年是由祖父弥漫酒糟气味的硬胡须蹭我脸蛋的画面和祖父挪着步子从各处酒局晃晃悠悠回家时喊我名字的声音构成的。再次归来的祖父对酒的情感依旧,他豪饮半瓶,仍意犹未尽,又捧起酒瓶,咂了两口,然后很满足地躺回原样。酒瓶倾倒,酒液流出,在瓶嘴处洇出一摊酒渍。祖父撩起上衣,露出肚皮消热,又在肚皮上挠痒,接着,他的两条腿、两只手都很无力地瘫在炕上,腹部不再起伏,脑袋也歪向一边。我突然想起,三个月前,父亲对匆匆赶回来参加祖父葬礼的我只说了一句话,你爷喝酒喝没了。三个月后,祖父不是躺在棺材里,而是躺在我面前,让我的耳畔重新响起唢呐高亢、嘹亮的丧音。
等祖父坐起来,脸上已褪去醉红,透着一种平静的苍白。仿佛他刚才并没有狂饮白酒,倒像是噩梦初醒。祖父扶正酒瓶,看着酒渍,愣了很久。白酒的辣味和透过窗棂的阳光让父亲皱起了眉头,他翻了个身,鼾声变弱。
后来我想,祖父和我那时候都很担心父亲会醒过来。祖父说,我这辈子就这点儿爱好,喝酒解乏呀。去山里受一天苦,回来喝点儿酒,出身汗,能睡个好觉。我谁也不怪,我能喝醉了死在炕上,值啦。祖父看了看父亲,说,这有什么不好给我说的,你爹怎么就哭得像个娃娃?你爹埋我的时候也像这样哭吗?我摇摇头,说,他只是抽烟,一个礼拜没讲一句话。我想起那几天父亲终日笼罩在烟雾里,指头和鼻尖都熏黄了,眼眶却只是泛红,没有滴泪。祖父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你爹年轻的时候,鸡毛蒜皮的事就能和你娘吵起来,真碰到了大事,却是个包,只会像牛一样,拿两个鼻孔出气。祖父滴尽瓶底的酒,面色又红润起来,他用大拇指蘸蘸那片酒渍,凑到舌尖舔,见我看着父亲,又说,你不要管他。他马上就会醒了。他可能早就醒了,只是不愿睁眼。他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管他。
——我的好乖孙,你能帮我再拿瓶酒吗?
祖父归来的季节,已到夏天的尾巴。只是过了一夜,黄土高原的夏日似乎就结束了。我不知道祖父化作流星归来,是不是裹挟着宇宙的冷冽,让我们村比其他地方更早入了秋。我们走在路上,路旁的树木都在扑簌簌地抖叶,风里已经没有夏天的那种干燥,多了些秋天的潮湿。秋风卷起枯叶、断枝和碎石,尘沙漫天,空气中凝出细线样的黄褐色气流,使我眼角发凉、鼻痒难耐,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我们在去洋芋地的路上。
祖父走在前头,双手有力地挥着,每走一步,都在黄土地上踩出一个结实的轮廓。我跟在祖父后头,踩着他的脚印前行。祖父踩过的地方,古老厚重的黄土地变得柔韧而富有弹性,似无数绳索结成网,在秋风中晃动,我必须双脚精准地嵌在祖父的脚印中,才不至于摔倒。
祖父却越走越快了。我看到他脚下的黄土地如明亮的鼓面,他不是在走而是在颠。他左看看,右看看,显得如孩童般兴奋。高山、沟壑、河滩、地洞;灌木、荆棘、泥沙、滚石;梨树、桃树、杏树、枣树;玉米、糜子、谷子、洋芋……祖父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似乎在重新认识他生活了七十五年的黄土地。
其实,祖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不下地了。他老了,除了喝酒,其实什么也不干了。我们要接他到城里住,他差点儿一酒瓶砸断父亲的鼻梁。祖父说,孽子,你要把咱家从黄土地连根拔走呀!祖父说,我生在这儿,就得死在这儿。哪怕死在别人家窑里,我也不会去城里住。那是一片长不出庄稼的土地,只能长出一茬茬没有根的人!祖父和父亲吵得很凶,几乎就要动手了。父亲被祖父的粗嗓门儿压着声音,驳不了几句话,只是挨祖父的骂,一张脸也跟喝了酒似的,气得脸红涨涨的。
后来还是母亲让他们父子俩停止了争吵。母亲既没有帮着她丈夫,也没有顺着她公公。她其实就没说什么话,只是喊他们到院前吃晚饭。母亲说,今天吃羊肉饸饹,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母亲就是在他们父子俩吸溜吸溜吃面的时候,把理儿给他们说清楚的。吃罢,父亲递给祖父一根烟,两个人吞云吐雾,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句,我一句,有了商量的意味。父亲那阵子正在外地忙生意,和祖父闹僵之后,也就任由祖父住在老家了。能有什么办法呢?人老了,脾气就成了一块硬石头,别人是撬不动的。
父亲早有在老家箍窑的想法了。只是祖父到了晚年,固执如铁,不听他人言。你们谁都不能帮,我自己能行,我能把窑箍起来!他在前村捡一块砖瓦,后村拾一截木头,去赶集时,用驴车拉回一袋袋沙子。所有材料都分好类,整整齐齐码放在父亲后来箍新窑的地基处。那时那块地还未推平,还是一片油绿的玉米地。祖父逢人就说,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在这儿箍窑哩!可是祖父没有等到他亲手摞第一块砖的那天,没有迎来亲朋好友欢聚暖新窑的那天,也没有能够在自家窑院前搭起自己的灵堂。祖父的葬礼是在别人家窑院前办的。那户人家在我儿时便搬到了城里,村里的窑洞长期借给我们住。我儿时的很多记忆原本在那两孔窑洞里清晰可辨,直到父亲把我接到城里念书才日渐模糊,等到祖父上山入土,关于窑洞的一切似乎都从我脑海中凭空消失了。
我们到了洋芋地。
洋芋地明明就在村东头儿,我儿时还去帮祖父追过肥料,拔过杂草,到那儿不过祖父一袋煙的工夫罢了,这次却走了很久,才看到那块地的灰色地皮。我忘记了时间,只记得太阳升了又落,落了又升,风越来越凉,地上的枯枝败叶不断冒出来。我只是不断提醒自己,要踩在祖父的脚印里。我们饿了就吃山上的红富士、红香酥梨和红枣,渴了就下到河滩,以手作瓢,痛饮溪泉。
走了那么久,祖父仍然精神矍铄,毫无倦态。他步履不停,时不时回头对我说,我们快到了。夜深时,天地浓黑如墨,星星在黄土高原的头顶发白。月光如镰,收割一切声色。世界愈暗,阒然无声。我又累又困,几乎看不清祖父的身形,却感到祖父的影子在领着我继续向前。月光下的祖父融入了天地,仿佛无处不在。他一直在对我说,走呀,别停。
祖父的声音让我想起他和祖母临别前的最后一刻。那也是一个无声无色的秋夜,我们一大家子挤在窑内,灯泡昏黄,窑壁上映叠出一个个拱形人影。窑内的悲伤也在无声无息地延长。祖父坐在炕头,陪伴病重的祖母度过了死亡前的平静时光。祖母看着他的老伴儿和子孙们,欣慰地笑着,离开了人世。祖父轻轻托起祖母垂下的手,抵住自己的额头,似乎想给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温暖。祖父说,别走呀,等等我吧。祖父的叹息和哭泣让我们一大家子的心潮湿了整夜,直到黎明破窗,将一缕明晃晃的阳光打在祖父的身上,泪眼蒙眬中,我们才发现祖父已经不再哭泣,而是和祖母一样在笑。祖父就在祖母最后的微笑中等待了十年零三个月,也驾鹤西去了。
黄土地上躺满了洋芋的枯秧,都是秋风中迟暮的模样。祖父踩过,干瘪的叶蔓发出虚弱的脆响。一抬脚,脚底粘上一层碎叶子;落脚后,碎叶又盖在泥土上。我们没有带农具,祖父和我也不是要下地干活的打扮。事实上,这块洋芋地也并非祖父种植了几十年的土地。祖父去世后,他的洋芋地无人打理,早已荒弃,如今只有裸露的干燥的黄土块儿,大的、小的,卧在地里,似乎知道不会有人再为播种而打散它们。
祖父站在这块洋芋地的地垄上,双手叉腰,微笑着对我说,今年也是好收成呀!你看那叶子多宽,洋芋也不会小!不远处有人在刨洋芋,埋着头,弯着腰,身影在阳光下移动。我不能像祖父那样一眼就认出村里的老朋友,只看出那是一位像祖父般年迈的老人。祖父对我说,你应该认识他,你小时候没少在他家吃炸糕和饺子,还好几次把尿撒在他脖子上呢。
祖父带我来的不是我们家的洋芋地,而是他老朋友的洋芋地。我对这位老人的记忆并没有因为祖父的提醒而复苏,只是在祖父和他交谈的时候,发现他瞎了一只眼。大概因为常年劳作,他的脑袋像糜籽般低垂着,经年累月风沙的侵蚀,使他整张脸爬满了蜈蚣般的皱纹。老人在和祖父说话,但另一只眼不是看着祖父,也不是在看我,而是看着远山的某处。那座山上埋着祖父。
老人说,我另一只眼也快瞎啦……
祖父说,今年也是好收成呀!
是啊,你看叶子多宽,洋芋也不会小!
祖父摆开架势,以手为镰,以脚为锄,开始在洋芋地忙活。他拨开枯秧,拔出芋根,刨出洋芋,揣进口袋。一颗,又一颗。祖父不像是在挖洋芋,而像是在寻找埋在黄土地里的某种宝藏。每一颗洋芋都光滑完整,不会遭遇被锄头误削成两半的命运。祖父抹去湿泥,吹掉杂质,掐掉新芽,用手掌轻轻摩挲。洋芋在祖父的掌纹中变得更浑圆,像颗颗饱满的蛋,散发着淡淡的青黄色光芒。祖父将洋芋放进口袋,似乎怕它破碎,手伸进去,在袋中小心翼翼地调整着洋芋的位置。我听到祖父的口袋里传出洋芋表皮相互摩擦的声响。“沙沙”“沙沙”……祖父的口袋明明很小,却装了一颗又一颗洋芋。口袋既没有肿胀凸起,也没有让他身体失衡,无法行动。甚至只轻轻一跃,祖父就从沟渠这头儿跳到了那头儿。祖父的口袋仿佛是永远装不满洋芋的洋芋窖,贪婪地吞掉一颗颗黄土高原生长出的粮食。从清晨到傍晚,我们都在洋芋地里忙活。老人就在田垄上静静地看着我和祖父。我不知道老人的那只眼是看着祖父,还是看着我,抑或远方。
老人离开前,父亲出现在洋芋地旁的槐树下。父亲变了,西装革履,头发油亮,身上重新散发出城市商人的气息。父亲向我招手,我跑到他跟前。父亲打量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父亲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明白父亲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感到眩晕,脚下的土地似乎轰然塌陷,整个人仿佛坠入梦境。我看到父亲开始和那老人交谈,他们在说些什么,我竟听不清楚,只觉得风变大了,变冷了,像流水堵住我的耳朵。这时祖父也走了过来,他光着脚,浑身裹满泥土,面色灰黄,简直像一颗刚从黄土地里钻出来的洋芋。祖父每走一步,都震落他身上的一层薄土,薄土像蛇蜕皮一样,一层又一层脱落。祖父两只手按着口袋,口袋里是数不清的高原果实。而他身后的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晰而完整的厚脚印。
祖父扇了父亲一记耳光,父亲的脸上长出了五根手指印。指印是黄土地的颜色:一根黄,一根褐,一根黑,一根红,一根灰,像某种胎记,隐于皮肤之下多年,终于出现。父亲瞪着祖父,说,打得好!老人站在中间,拦住了紧握双拳的父亲。老人对我叫着,小宝,小宝!我们都开始后退。我扶着祖父退回了洋芋地,老人拉着父亲退到了马路上。我们中间隔着祖父的那一串脚印,在暮色中越来越暗,先是轮廓,然后渐渐全都看不见了。只有风经过,被绊了一下又一下,发出似愤怒又似无奈的不规则的呜咽声。
我已记不清祖父收获了多少颗洋芋。一行行秧苗、叶蔓东倒西歪地耷拉着,它们完成了结洋芋的使命后,终于等到了枯萎,心满意足地躺在黄土地上,和我一样看着祖父不知疲倦地继续刨挖。祖父挥汗如雨,身上冒出的汗水在黄昏的光线下散发出热烈蓬勃的气息。祖父仿佛不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而是一个在黄土地滋养下重新年轻、重新健壮起来的男子,穿梭在洋芋地的这头儿和那头儿,里头和外头。
夏天已经过去了很久,时间似乎是深秋。午夜的黄土高原,漫山遍野落满了银色的霜,像星河的灰烬倾泄于此。这已经是不知第几遍翻地了,祖父在搜寻可能漏掉的洋芋。他找得很仔细,尚未现身的洋芋也很迫切地呼唤着祖父,希望能被收进那只无底的口袋。
祖父发现了一颗漏收的洋芋,硕大如瓜,他对我不无炫耀地说,真是好收成啊!一如我十歲那年祖父带我收洋芋时说话的语气,喜悦而满足。十一岁那年,父亲把我从老家接到城里念书。十一岁之前的那些美好、纯粹的日子却常常出现在我梦中,使我不至于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寸步难行。离开村子前,祖父喊住了我,他抓了一把黄土,放在我手心,高兴地说,这片黄土地要出一个大学生哩!一些黄土钻出指缝,在风中轻扬,余下的则聚成一座小塔,光滑而纯净,在我手心升温。
祖父把洋芋放在我手心里,亲切地说,走吧,我们一起把它挂到天上去。
我手中的洋芋开始变得滚烫,似乎正在燃烧,又像有无数萤火虫在它的内部飞行。洋芋越来越亮,变成一颗发光的球体。我想起当年那把黄土在父亲的摩托后座上越漏越少的情形。无论我怎么保护那把黄土,它们仍然迅速地流失,眨眼间便回归大地了。那时我真想也变成一把土,这样就不必离开故乡。我感到我的身体自手心开始冰凉,只有眼泪滑过脸庞,滴在父亲的后背上,烫出一片深色的洞。
洋芋悬空,越升越高,越过我的嘴巴、鼻子和眼睛,越过我的头顶,越过树木,越过群山,越过云层,继续向上,向上,向上。我看到祖父朝远方走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颗发光的洋芋,每一颗洋芋的外表都散发着青黄色的光芒。光芒在跳动,似迫不及待的姿态。祖父一伸手,洋芋就跳了出去,挂在无边的夜幕上。他每掏出一颗洋芋,夜空就多了一颗星星。月亮出来的时候,祖父还在调整星星的位置。祖父把那颗最大的洋芋指给我看,我看到一颗星悬在夜空,像夜晚的太阳。星光灿烂,照得大地亮如白昼,黄土高原一片白茫茫,如铺了一张雪毯。祖父又将两只口袋翻出来,大地上洒落了很多不知是洋芋还是星星的碎屑,泛着银黄色的光,一闪一闪的。祖父的口袋空了,他整个人也瘦了一圈儿,简直像是一副骨架站在那儿。好像他不是掏出来那么多洋芋,而是掏出了他的血肉。祖父似乎对星星的布局很满意,欣慰地笑着。我看到数不清的星星在跳动,天地正在变成一颗巨大的心脏。我想喊一声祖父,我想跪在他面前,哭或者笑,可祖父已经朝远方走去。
这时我听到了父亲的喘息声。父亲在奔跑。他脚步急促,踩乱了祖父留下的一个个脚印。不知道父亲去了趟哪里,他变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连鞋袜都丢了。父亲双手撑膝,气喘吁吁,像一棵在秋风中战栗的树。他呵出团团白气,用一种疑惑的眼神打量着哭泣的我。这不能怪他,父亲没有看到祖父远去的背影,所以才不哭泣。父亲抬头看着漫天的流星,久久不语,直到夜尽破晓,才开了口。父亲告诉我,祖母回来了。祖母从远方带来了雪。冬天几乎是和祖母同时抵达黄土高原的。在父亲箍的三孔窑洞前,祖母拍落了身上的白雪,掀起门帘,走进窑洞,脱鞋,上炕,垫枕,盖紧了被子。睡前,祖母对父亲说,希望能帮她换一口棺材。那口棺材太窄,她睡得不踏实。
责任编辑 刘淑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