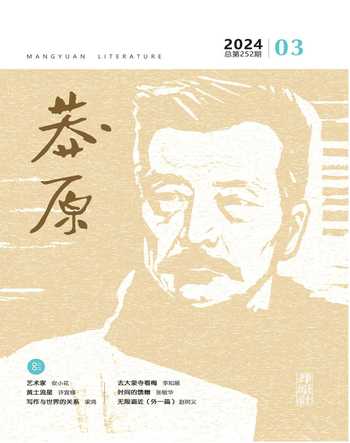苹果蛋糕
(美)阿丽嘉·古德曼/著 杨伟莉/译
珍妮是姐妹三个中最小的,今年七十四岁了,她形容枯槁,病得很厉害,大姐海伦和二姐西尔维娅对此感到非常恐惧,谁会想到……她们不肯说出口。大姐海伦八十岁,二姐西尔维亚七十八岁,她们比珍妮岁数大,比她早结婚、早生孩子,她们觉得应该是自己更脆弱,珍妮怎么可能比她们先走呢?
一岁生日的照片里,珍妮穿着网眼花边的衣服靠着软枕坐在婴儿椅里,面前的盘子里放着一块蛋糕,两个姐姐陪伴在她的左右。照片里的珍妮眼睛大大的、圆圆的、蓝蓝的,一头金色卷发,像极了姐姐们的玩具娃娃。那时候,熟透了的苹果从树上掉落到草地上,姐姐们用小车推着她,一路上快乐地颠簸着玩耍。
现在,姐姐们觉得和珍妮在一起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珍妮的头发只剩几缕了,说话的声音游丝般微弱,并且不断被剧烈的咳嗽打断。恐惧、怜悯、羞耻的感觉同时折磨着姐姐们,她们看着珍妮现在的样子,不由地回忆起她以前的美丽,伤心的同时却又为自己活得好好的而十分欣慰。她们穿着低跟的鞋子,步履稳健!她们呼吸自如,身体健康!但无论怎样也不能坦言她们的身体有多么好、命有多么好,还有心中的内疚感,她们谁也不会说出来的。
“亲爱的,你好吗?”大姐海伦问道。
珍妮沒有回答。
“你看见理查德送的兰花了吗?”二姐西尔维亚把一枝长长的白色的兰花转向珍妮坐的椅子,那是她的儿子理查德送给珍妮姨妈的。
珍妮因为不能走楼梯了,住在一楼她的音乐工作室里。珍妮看了一眼外甥送的兰花,工作室里到处都是鲜花,有外甥理查德送的兰花,二儿媳梅兰妮送的向日葵,隔壁邻居奥尔巴克送的玫瑰花。她视线所及之处,都能看到邻居们、外甥们、孙子孙女们送来的各种礼物,钢琴调音师送的一篮菊花开始凋零,花瓣飘落四处。还有一些暖心的卡片,上面大都写着:“给我们的最爱”“想念你”,其中一张是大姐海伦的女儿温迪送的,温迪是一名音乐治疗师,卡片上面写道:“治愈之光!”
“看这些花多美啊。”二姐西尔维亚说,她想对珍妮说的是,你看,大家都很爱你。
珍妮脸上的表情怪怪的,看到花儿只会让她更难受,特别是那些枯萎的花,当她看着凋谢的菊花时,她希望死神早些降临。
姐姐们坐着聊着炎热的天气、交通状况和下不下雨。她们害怕珍妮一个人会孤单,尽管珍妮已经寡居了十五年之久。珍妮的丈夫活着的时候是个很难相处的人,珍妮之所以一个人过日子,是因为喜欢这种独居的生活。
珍妮住的房子属于都铎王朝建筑风格,儿子们认为房子太大了,二十岁的孙女菲芘说,住这么大的房子太浪费能源。好多年了,大家一直劝她搬家,现在,没有人再提搬家的事儿了。珍妮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护理有一定优势,可以不用给房子装保温层,没有人建议进行延长生命治疗、没有人来指责碳排放,说实话,几个礼拜之后,甚至是几天之后,珍妮离开人世,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碳排放了。另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能来探望珍妮,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珍妮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她十分不屑于这些迷信思想,但却身染肺癌这种绝症,这让她在信仰上帝的家人眼里成了现身说法的范例,他们相信从珍妮身上能获得一种驱邪的能量,姐姐们总是紧握她冰凉的手不愿意松开。
大姐海伦告诉珍妮说:“我的女儿们帕姆和温迪这个礼拜日就来陪你。”
珍妮点点头。
“我的儿子理查德也要来呢。”二姐西尔维亚说道,她这个独生子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没有固定的工作,还离了婚,能想起来探望姨妈,理应得到赞扬。
大姐海伦有两个女儿——帕姆和温迪,帕姆住在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温迪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都离珍妮很近,而二姐西尔维娅的儿子理查德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过来则需要开好长时间的车。
珍妮闭着眼睛听姐姐们唠叨,姐姐们轮番地重复着那些话,她感觉很累,精疲力竭,她真的需要休息了,她任凭阳光照在自己的脸上,享受着眼前红彤彤的光亮。
秋日的阳光和煦明亮,但她更喜欢夜晚,因为大家都走了,只有夜班护士肖恩看护她。珍妮还没有睡意,她躺在从医院租的病床上,听交响乐、合唱、四重奏、波士顿经典无线广播电台WGBH的协奏曲,当听到小提琴独奏,她左手手指条件反射地弯曲着,就像她从前拉小提琴的样子。
为了方便肖恩护士,珍妮的儿子们把工作室里的乐谱架和钢琴都搬走了。珍妮看着肖恩靠在椅背上打盹,猜他白天还有一份工作。她发现他很用功,没事的时候总在看课本。这时,天快要亮了,他刚想打个盹儿,书就从他的腿上滑落到地板上。
肖恩护士一下子站起来,看见珍妮正在床上凝视着他,“对不起,对不起,夫人……”他弯腰去捡书。
“你睡吧。”珍妮说。
“不,您需要什么,我就在您身边。”
“睡觉!”
他睁大眼睛,他绝不会继续去睡觉,这样做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会告诉你的。”珍妮说。
每天下午,儿子儿媳们都会来陪珍妮。这一天下午,大儿子史蒂夫和大儿媳安德利亚先到了,他俩坐在她身旁,安德利亚拿着手机让她看两个孙子扎克和内特的视频。扎克和内特年龄相差十八个月,都是高中足球队主力队员,等到地区比赛一结束,安德利亚就开车直接把他俩从球场上接来,衣服、鞋子也不用换就来看望奶奶。
接着,二儿子丹和二儿媳梅兰妮也到了,他们只有一个女儿菲芘,梅兰妮怀菲芘的时候,体重增加了五十磅,之后体重再没有减下来,也没有再怀上孩子。
“菲芘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二儿媳梅兰妮说。
二儿子丹接着解释说:“她想来看您的,可她不愿意坐飞机。”
珍妮想象着学习生态专业的孙女从密歇根州安阿伯市一路骑脚踏车奔驰而来的画面,她好像看到了菲芘戴的头盔下瀑布般长长的金发。
“学校的功课比我重要。”
“事实上她这学期休学了。”二儿媳梅兰妮说。
“为什么要休学?”
听妻子提起这事,丹皱紧眉头,烦闷地说:“她说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
“她很可能要去农场里工作,”二儿媳梅兰妮说,“她想当农民,想写诗。”
珍妮憋不住笑起来,这让她呼吸急促,喘不过气,眼前发黑,白班护士劳瑞恩连忙过来帮她坐了起来,擦了擦她眼里的泪。
“休学没什么好笑的。”二儿子丹说。
“菲芘不是休学,”二儿媳梅兰妮说,“她只是需要调整一段时间。”
珍妮声音低哑地说:“她想做什么就做好了。”
二儿子丹和二儿媳梅兰妮都苦着脸,珍妮心里也为他们难过,但是没人有理由让她也为此烦恼。
得了肺癌的珍妮没有变得更加依恋家人。起初,她很感激家人们来探望,只要她还有一口气,他们一定会陪伴她的。但是,姐姐们不断地带她们已届中年的孩子们来是为了什么呢?是向她道别呢?是拿她警示别人呢?还是最后的祝福呢?
“你劝劝我的儿子理查德,让他戒烟吧。”二姐西尔维亚请求说。
珍妮心想,你们真是把我当不好的例证了。珍妮仔细看着气色红润的理查德,离婚以后,他的前妻获得了孩子们的抚养权,就连养的狗也归了前妻。
“我喜欢抽烟,”珍妮对理查德说,“你妈也喜欢抽烟。”
二姐西尔维亚听了,把身体直向后缩,仿佛珍妮打了她似的,她不知说什么,这时候再反驳也没用了。
珍妮的儿子们来了,他们的身体状况看上去都不好,二儿子丹戴着金属边的眼镜,肚子肥大,头发几乎掉光了,珍妮看到他,又好笑,又有些伤感,他长得很像他的父亲。大儿子史蒂夫的背不好,只能不时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踱步,珍妮看得头直发晕。
珍妮的儿媳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悲伤,二儿媳梅兰妮更是伤心,虽然她是个医生。珍妮想,你们快别这样了,我像你们一半年龄大的时候就没了父母,可现在你们都已年过五十了,和我一样也老了。珍妮假装睡了,很快就睡着了。
珍妮醒来的时候,看到姐姐们都在身边,她想,我们姐妹三个是不是有人活得太长了,突然,她的心沉了一下,不是吧,我就是那个人,那个人应该就是我。
曾经幽默风趣的珍妮,如今却好似一副空壳,珍妮想到自己的生命即将逝去,想到自己会失去意识,想到会失去自己的音乐,想到自己有待整修的房子,想到自己再也见不到阳光,一种油然而生的恐惧令她的身体不可抑制地颤栗。癌细胞吞噬着她的肉体,药物使她的思维麻木,即便如此,珍妮仍坚持着,她吃不下,没有气力说话,但她一息犹存。外甥女和外甥们都坐在她的身边,大姐海伦的女儿温迪边唱边轻轻拨弄着她的旧吉他,两个高中足球队员的孙子扎克和内特也来了,扎克指关节骨折了,内特不时地抖动着右腿,两个大男孩儿从头到脚活像一对长耳大野兔。
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们说珍妮的时间最多这一两天了,但是四天过去后,又是一天,事情开始变得很棘手,儿子们必须得请假,孙子们会耽误好几天的课,到底是留下?还是回去?回去之后,等到葬礼的时候再赶回来是不是明智一点呢?
“我们需要安排一下。”大姐海伦说,她是家里的大姐,她觉得自己担得起家里的重任。她对珍妮说:“跟我们说说你的愿望吧。”
“我要从床上起来。”珍妮立刻回答道。
之后,在大客厅里,二姐西尔维亚埋怨大姐海伦说:“你怎么跟她說那种话。”
大姐海伦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我们总不能直接问她何时闭眼吧?”
二姐西尔维亚听了哭出声来。
“别这么情绪化了。”大姐海伦责备地说。
“我不是情绪化,我是伤心,你应该理解我。”
“我很理解你,”大姐海伦说,“我是在帮珍妮,希望以后我像珍妮这样的时候,有人也能帮我做这样的事。”
二姐西尔维亚抽泣着回餐厅找丈夫卢抱怨去了。
下午,大姐海伦在珍妮的床边对当税务律师的女儿帕姆郑重地说:“你珍妮姨妈没有安排任何后事。”
大姐海伦刚说到“后事”,珍妮突然睁开眼睛,珍妮觉得尴尬的是,大姐海伦刚说完那句话,她就醒了。大家一下子围到她身边,儿子和儿媳们注视着她脸上的表情。
“梅兰妮,”珍妮低低地叫道。
“什么?”二儿媳梅兰妮流着泪问,她的眼泪好像从未干过。
“想吃半个面包圈。”
儿子和儿媳们立刻奔赴罗森菲尔德面包店,他们坐着丹的沃尔沃车子来到牛顿中心,互相说着珍妮的要求太离谱了。
当医生的二儿媳梅兰妮说:“妈妈根本吃不了半个。”
“那有什么关系!”二儿子丹边开车边说。
“没关系,”二儿媳梅兰妮说,“当然没关系。”
“如果我妈想吃半个的话,就吃好了。”
二儿媳梅兰妮说:“不要买带罂粟籽的,万一呛着就麻烦了。”
“买个鸡蛋面包圈吧。”坐在后座的大儿子史蒂夫说。
大儿媳安德利亚纠正道:“她不喜欢带鸡蛋的,她喜欢什么都不加的面包。”
他们买了十二个面包圈、两大罐子鲜奶油奶酪 、半扇熏三文鱼片和一块巴布卡巧克力,回来时,珍妮已睡着了。
护士们不再预告珍妮离开的时间,他们说只有珍妮自己知道。劳瑞恩护士建议家人们坐在一起讨论一下,是不是家里存在未解决的矛盾?有时候,人们需要互相原谅才能安心离开这个世界。
天性善良敏感的二姐西尔维亚对大姐海伦说:“我原谅你了。”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大姐海伦说,她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西尔维亚原谅的。她们姐妹两人有很大的不同,大姐海伦素来说话直接,而二姐西尔维亚则喜欢避重就轻。
“大姐海伦从不听我说话。”二姐西尔维亚跟围在珍妮床边的家人们抱怨,“我在她眼里就像空气一样,她心里根本没有我。”
大姐海伦听了觉得十分可笑,说道:“我心里肯定有你。”
珍妮的二儿子丹赶紧说:“我们还是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吧。”
“阿门。”劳瑞恩护士赞赏地说,这让每一个人嫉妒起来,因为劳瑞恩护士更喜欢丹多一些。
你们这些人啊,珍妮想,都争着让别人去关注自己!但她原谅了他们,晚安!她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再见!她希望她能说服他们心安理得离开,她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珍妮感觉身体状况稍微好了点儿,她喝了些果汁、吃了一口面包,她让人给她拿小提琴,她拉不了琴,连打开琴盒的力气也没有,可她要求把它放在挨着自己病床的窗台上,让它留在自己的视线之内。
珍妮像猫一样,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醒着的时候,精神状态却好了很多。大姐的女儿帕姆第二次从普罗维登斯赶回来时,珍妮就问她为什么还不结婚,二儿媳梅兰妮哭泣的时候,珍妮会说:“别为你自己伤心了。”珍妮认为二儿媳梅兰妮是对自己有一天也会面对死神而害怕,珍妮看着她的眼睛时判断的。珍妮的姐姐们更是恐惧,她们看着珍妮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珍妮这个想法不只是可恶、错误的,简直是残忍的!姐姐们并不只在意自己,二姐西尔维亚在回马萨诸塞州威斯顿家的路上一直拿丈夫卢撒气;大姐海伦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家里,熬夜做了各种甜点,有柠檬饼干、果仁巧克力饼干、杏仁饼干、山核桃棒、苹果蛋糕。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把做好的甜点都用油纸包好,装进保鲜盒里,然后放入冰箱冷冻起来。她的丈夫查尔斯体贴地劝她:“你休息一下吧。”怎么能说这种话?家人们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休息?珍妮是音乐老师,西尔维亚结了三次婚,三任老公都是有成就的人。她是个全职家庭主妇,现在家人们需要准备吃的,她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做。所以,每样甜点她都做了两份,然后把其中的一份冷冻起来, 为将要举行的葬礼以及葬礼后七天的悼念做准备。
大姐海伦的脑子里已经在想象珍妮的学生和家长们到来的场面。因为二姐西尔维亚的丈夫卢患有糖尿病,西尔维亚好多年不做甜点了。至于珍妮的两个儿媳梅兰妮和安德利亚,谁知道她们会拿来什么吃的呢?一盒子炸甜甜圈?那可不行!大姐海伦作为家里的烘焙能手,她觉得买来的东西表达不出她的亲情,她的心里埋藏着浓浓的悲伤。
珍妮在与病魔纠缠着,姐姐们夜里守着她,珍妮的儿子们周末来陪她。家人们在厨房里一点点啃着吃大姐海伦拿来的柠檬饼干,二儿媳梅兰妮招呼护士们吃果仁巧克力饼干。“吃吧,”她对劳瑞恩护士说,“我们吃不了,海伦姨妈非得要做。”
“她真是贴心,”劳瑞恩护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哀伤的方式。”
大姐海伦为珍妮无比的心痛,她每天来的时候都拎着好几个食品袋,带来的蛋糕松软新鲜,里面还有苹果片,可是,她做的杏仁饼干一碰就碎,山核桃棒又甜又黏,而且硬邦邦的非常硌牙,大家都不愿意吃,大姐海伦不喜欢把好好的食物丢掉,所以它们原封不动地在厨房里放着。
珍妮犯糊涂的时候会奇怪地问大家为什么在这儿,等到清醒的时候就开始指派人,她让二儿媳梅兰妮把所有的鲜花和绿植送到牛顿·韦尔斯利医院,让大姐海伦的女儿温迪把她的吉他放到一边,最后,她要求跟她的儿子们单独说话。她在病床上躺着,注视着二儿子丹和大儿子史蒂夫来到身边,丹和史蒂夫心里想着是到了时候了。
“我们说说吧。”珍妮说。
“什么?”大儿子史蒂夫紧张地问。
“我的遺愿是……”珍妮说。
二儿子丹拉了把椅子坐下,大儿子史蒂夫开始来回踱步。
“史蒂夫,不要那样来回走了。”
“您的愿望是什么?”二儿子丹问母亲。
“第一,”珍妮看向大儿子史蒂夫,“不要那样来回走了。第二……不要举行葬礼。”
“只有家人参加的土葬仪式行吗?”二儿子丹小心地问。
“不要土葬。”
大儿子史蒂夫惊讶地说:“您想好了?”他的下一句话“我们把墓地的费用都交了”被咽进了肚子里。
“我不要土葬。”
大儿子史蒂夫不满地说:“您的墓地是挨着父亲的。”
“是,我知道这个。”
二儿子丹的眼镜起了一层雾气,他摘下眼镜,用穿的毛衣擦拭着说:“您跟父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八年呢。”
“是的。”珍妮心里另有打算,她不会跟儿子们说的;她能说出的他们父亲的优点,她也不会跟儿子们说的。他们说土葬,她对此十分抵制,她不需要别人悼念,她要努力活下去。
随着生命一天天的延续,珍妮说话渐渐变得有力量了。窗外,树叶的颜色在悄悄改变,窗户和房子排水管道都到了清洁的时间,虽然她为此而焦虑,但她选择忍受这种焦虑。
家人们都离开了,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珍妮的孙子们回校学习,珍妮的儿子儿媳们开始上班,连二儿媳梅兰妮也不再动不动就掉眼泪了,她认为婆婆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婆婆定会长命百岁,会比子女们活的时间都长。
护士们照顾着珍妮,劳瑞恩护士说老人如果有心愿未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生命之灯难以熄灭的情况,比如说期盼着晚辈们的婚礼,或是毕业典礼。大家谁也想不出家里会有什么特殊的典礼,离了婚的理查德或者会有再举行婚礼的机会,其他重要典礼现在还不会有。大家把家里每个人都想了一遍,外甥、外甥女、孙子孙女……对了!他们想到了珍妮的孙女菲芘,她还在密歇根的农场写诗、劳动,她不肯坐飞机来陪伴奶奶!
二儿媳梅兰妮和二儿子丹在珍妮家里跟女儿菲芘通了电话,之后,梅兰妮又在跟丹开车回家的路上跟菲芘通了一次电话,她劝导菲芘要懂得尊敬奶奶,要怜悯奶奶,要想想奶奶的感受,而不是只关心地球环境。
大姐海伦和二姐西尔维亚坚持每天都来陪伴珍妮,她们各自有各自的心事,同时还包含对自己人生的恐惧和伤感。
大姐海伦提出把自己的拉比 (犹太教中意为“老师、有学问的学者”,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及主持宗教仪式) 带来。“不要让拉比来,”珍妮说,“不要让神职人员来。”
“那你说该怎么办?”大姐海伦用严厉的口气问。
二姐西尔维亚哭着说:“你怎么能冲她嚷嚷?”
“咱俩到底是谁嚷嚷来着?”大姐海伦反驳道。
二姐西尔维亚生着气离开了珍妮的家,她想有时候她跟大姐说话是急了点儿,她的情绪是有些失控,可是珍妮现在的病情让人困惑,珍妮的生命什么时候走到尽头?现在看似会有无限延续下去的可能,这时候应该不需要做什么事情,然而大姐海伦却总要跟以前一样掌控一切、发号施令。
二姐西尔维亚一夜未眠,伤心欲绝。“都怪大姐海伦,”她跟丈夫卢说,“都怪她的自作主张、她的拉比、她做的那些变味儿的山核桃棒。”
十月十二日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家人们聚集在珍妮的家里,二姐西尔维亚带来了刚烤好的苹果蛋糕,放在锅里还热乎乎的,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珍妮的两个大孙子闻到苹果蛋糕的香气,立刻来了精神,扬起头争着问:“我可以吃一块吗?”“我也吃点儿,行吗?”
二姐西尔维亚来到厨房,把苹果蛋糕放在盘子里,切了几大块儿给男孩子们吃,珍妮的二儿子丹和二儿媳梅兰妮,还有大儿子史蒂夫和大儿媳安德利亚都来吃了几片。
餐厅里,大姐海伦拿的刚解冻的果仁巧克力饼干、山核桃棒、杏仁饼干却无人问津,她的丈夫查尔斯为了不让妻子难堪,吃了一块果仁巧克力饼干,然后趁人不备,溜进厨房去吃二姐西尔维亚做的苹果蛋糕。
“我闻到烤苹果蛋糕的味儿了。”珍妮耳语般地说,她那瘦小枯干的身体躺着,看上去似乎被病床吞没了。
“西尔维亚是按照我的配方做的,”大姐海伦说,“二十年前,是我给了她烤苹果蛋糕的配方。”
“是的,我记得,”珍妮说,“西尔维亚做的苹果蛋糕很好吃。”
“我也做了苹果蛋糕!上礼拜我给你带了!”大姐海伦说。
“我知道,可我更爱吃西尔维亚做的苹果蛋糕。”
大姐海伦冲进厨房,眼睛盯着二姐西尔维亚做的苹果蛋糕剩下的碎屑。珍妮的两个孙子扎克和内特站着吃着,珍妮的二儿媳梅兰妮和二儿子丹,大儿子史蒂夫和大儿媳安德利亚坐在桌子旁吃着,海伦一眼扫见自己的丈夫查尔斯,他心虚地把手里的一次性盘子扔掉了。
“你也吃了,查尔斯。”二姐西尔维亚的丈夫卢幸灾乐祸地说。
“你用的是我的烤苹果蛋糕配方。”大姐海伦對二姐西尔维亚说。
“对,我用了。”二姐西尔维亚答道,连珍妮的两个孙子扎克和内特都听出了她的语气——你又能怎样?
第二天,二姐西尔维亚带来了她在家做的蛋糕卷儿,松软的蛋糕里加了香味扑鼻的杏仁,上面还撒了椰片,她已经十五年没有做过蛋糕卷儿了。一家人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二姐西尔维亚的丈夫卢平时严格控制糖分,这时候也不管不顾地吃了一小块。只有大姐海伦和珍妮没有吃,大姐海伦不愿意吃,珍妮是吃不下东西。
珍妮对家人的陪伴已感到厌倦,但她还是打起精神跟每个人说上几句话。她建议二儿子丹试一下生发治疗,劝二儿媳梅兰妮服用一些抗抑郁的药,服用这些药还会对她减肥有所帮助。大儿子史蒂夫和大儿媳安德利亚对音乐都不感兴趣,他们的两个儿子也从未学过任何乐器,珍妮告诉大儿媳安德利亚,既然两个孙子都那么喜爱运动,可以让他们参加军乐队试试,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参加青年合唱团,这样的话,他们能学会唱歌。
大儿媳安德利亚沉默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我明白音乐对您有多么重要。”
“它是我的生命。”珍妮喃喃地说。
“您想见您的学生吗?”大儿子史蒂夫问。
珍妮想起了她年轻的小提琴手们,乔治拉琴音色很美,但有些急躁;苏菲老是忘拍子;怀亚特很有天赋,却不很用功;爱玛在演奏颤音部分时总放松不下来。
大儿媳安德利亚说:“想让学生们来为您演奏吗?”
“上帝,不要。”珍妮说。
姐姐们、儿子们、儿媳们总在试探地问能做什么,珍妮盯着窗外的枫树,心想既然他们想做,那就随时告诉他们好了。他们推着她来到花园,这里能看见好多的树。她坐在轮椅里,系着安全带,随身带着氧气罐,她仰起脸望着火红的枫树、金黄的栎树,微风拂面,天空高远,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清香怡人,随处可见的青草新鲜而滋润。她靠着轮椅坐着,脸上带着微笑。家人们想她在静养,但他们想错了,她不是在静养,相反,她满心欢喜,她已经为自己做好了打算。
她告诉大姐海伦她想见拉比,想跟拉比面谈。
“谢谢你。”大姐海伦说。
第二天,利伯曼拉比来了,他看上去像是只有十二岁的少年,像是来上音乐课的学生,虽然他穿着正式,但在珍妮眼里仍旧是个孩子。
“珍妮想跟您谈谈。”大姐海伦对利伯曼拉比说。
珍妮对利伯曼拉比说:“您知道我是个无神论者。”
利伯曼拉比点点头说:“是,我知道。”
珍妮又说:“我也没有时间去加入教会了……”
“有很多人跟您一样。”利伯曼拉比说。
珍妮皱了下眉头,她觉得利伯曼拉比的话让她难以信服,难道拉比可以不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吗?
“可是您信上帝。”珍妮说。
“是的,我信上帝。”
珍妮看着海伦说:“这样就安心了。”
“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吧?”大姐海伦对珍妮说,她想珍妮明白了以上帝的名义能让人们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信仰是一种个人意愿。”利伯曼拉比说。
“我同意,”珍妮说,“所以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权。”
利伯曼拉比微笑地听着。
“我家人想把我土葬。”
大姐海伦插嘴说:“你知道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他们想把我挨着我的已过世丈夫土葬,”珍妮说,“可我想换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利伯曼拉比问道。
“我想把骨灰撒入大海。”珍妮说。
“您是说火葬吗?”利伯曼拉比提问的措辞特别精准。
“犹太人从不火葬。”大姐海伦声明说。
珍妮看着利伯曼拉比,他脸上一副为难的表情。
“火葬不符合我们的传统。”利伯曼拉比最终开口说。
“好吧。”
“要是把你的骨灰撒入大海,我们该怎么祭奠你呢?”海伦发问道。
珍妮说:“你怎么知道我想让你们祭奠我呢?”
大姐海伦的泪水让珍妮吓了一跳,她以前从未见大姐海伦哭过。
“我会祭奠你。”大姐海伦说。
“哦,好吧,”珍妮说,“把我土葬好了,我不介意。”
“谢谢你。”大姐海伦喃喃地说。
珍妮想死后万事皆空,“按你的想法办吧。”她跟姐姐说,“把我土葬好了。”
家人们轮流着进来陪伴珍妮,一大家子的人让她觉得好累。珍妮闭着眼睛,凝神听着房子里的各种声响,她听着房门关闭的声音、水流动的声音、吸尘器工作的声音、争吵的声音和怒气冲冲的话语。
大姐海伦照着母亲的配方做了曼德尔布罗特蛋糕 ,二姐西尔维亚也按母亲的配方做了蜂蜜蛋糕向她示威。这两种蛋糕珍妮一口都吃不下。此时,家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她——她睡了多长时间?她什么时候醒着?
每天早晨珍妮醒来后,和家人一样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活着。她一睁开眼睛,大家仿佛拜见圣人似的来到她面前,她尽自己所能地给他们找事做。“你回家休息一天,做你的事情吧。”她对大姐海伦说。然后转向二姐西尔维亚,“你再给我做苹果蛋糕吃。”
大姐海伦对珍妮说:“你在生我的气。”这时,房间里只有她们两人,珍妮摇了摇头,海伦继续说:“因为我信上帝,你才生我的气。”
珍妮说:“我不会因为你信上帝生气。”她嘴里这样说,心里却说,我才不在意你呢。
“西尔维亚的苹果蛋糕里用了红糖,”大姐海伦说,“她做什么都爱用糖。”
“她当然喜欢糖。”珍妮说。人人都喜欢甜的东西,那些苦涩、复杂、黑暗的东西怎么能比得上甜蜜、愉悦的东西呢?之前她总会痛苦于这种矛盾,但现在她开始享受这种不公,她望着窗外火红的枫树的时候,心中一半是愉悦,一半是恐惧,这是一个美丽灿烂的世界,却偏偏又是如此的陌生。
一會儿,珍妮听见了门口的动静,看见一个漂亮姑娘,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她的孙女菲芘终于来了,金色长发瀑布般披在背后,菲芘从密歇根坐公交车来的,还带来了个年轻男人,他是个猎手,穿着一件粗糙的皮衣。
珍妮紧紧抓着孙女的手,可菲芘却往后躲,珍妮惨白的脸把她吓坏了。
珍妮心里想,哦,你怕我呀,你看奶奶的眼睛变得好大,脸变得好瘦……
“指甲好尖利呀。”菲芘低头看着珍妮干瘪的手喃喃地说。
珍妮想到了狼外婆用尖利的爪子抓小红帽的故事,然后说:“介绍一下吧。”
菲芘没有听懂,珍妮转向年轻的猎手问:“叫什么名字?”
“我叫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是基督教徒的称呼)。”珍妮听到他的名字,屏住呼吸,控制不住地笑起来,虚弱的病体随着抽搐起来,手抓着菲芘不放。
二儿子丹和二儿媳梅兰妮并不觉得女儿菲芘的男朋友可笑,他们也不会笑话他的名字。他今年二十八岁,没有固定的工作,他说过想种蓝莓。丹和梅兰妮不想这时候见他,他们根本也不愿见他。他坐在沙发上,两只胳膊搂着菲芘,仿佛她只属于他一个人,他们甚至不能跟自己的女儿说上话,他为此饱受白眼和抵制。他的脸紧贴在他们独生女儿脸上,毫不客气地吃掉大姐海伦做的山核桃棒,又狼吞虎咽地吃光二姐西尔维亚做的苹果蛋糕。
孙女菲芘已经来陪奶奶了,大家认为珍妮的时间也到了,可是珍妮恋恋不舍地盯着菲芘美丽的脸庞问:“你的小提琴呢?”菲芘低头看着脚上的登山靴不吭声。
“你把琴卖了,是不是?”
菲芘哭了起来。
“不要紧,不过是早晚的事……”
菲芘在等着奶奶说下去,等了一会儿,她才问奶奶:“您说什么?”
珍妮想,谁记得呢?自己或许是在睡梦中,她分不清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在说梦话,“你的琴拉得好,可别人比你拉得更好。”
“谢谢奶奶。”菲芘说。
珍妮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菲芘小时候的样子,满头金发的小菲芘坐在海滩上,游泳衣上沾满沙子,深蓝的海浪溅着白色的泡沫,一波一波地向她涌过来。
第二天,珍妮陷入了昏迷,她的儿子丹和史蒂夫亲吻了母亲的额头,每个人都再一次来做最后告别。但是,珍妮又熬过了一天,然后是第三天,第三天的夜里,家人们都走了,只剩下肖恩护士在,珍妮突然大声哭起来。
“罗宾斯特恩夫人!”肖恩护士一边呼唤她的名字一边尽可能地帮助她不那么痛苦,可她却打发他走,她不需要帮助。她想睁开眼睛,她想从床上起来,她需要音乐,她想吃苹果,她想去沙滩上,她想感受夏天的酷热,现在她多么需要这一切,可她再也不能享受这一切了,此刻,她已经窒息而死。
早上,珍妮的儿子们来了开始商量安排后事,大家都坐在餐厅里,大姐海伦坚持让她的拉比来领诵祷文。
二姐西尔维亚看着她说:“珍妮说不举行悼念仪式,你知道的,她不接受宗教仪式。”
“你不要跟我嚷嚷,”大姐海伦说,“我们要悼念的是珍妮,不是你。”
珍妮的二儿子丹插进来说:“举行一个简单土葬仪式就行。”
“妈妈说不要宗教仪式。”珍妮的大儿子史蒂夫补充说。
“可是你们的妈妈不愿意土葬。”二姐西尔维亚提醒他们。
大姐海伦提高了嗓音说:“珍妮跟我说了要土葬。”
“那是你强迫她的。”二姐西尔维亚犀利地说。
“我不会强迫任何人。”大姐海伦说。
“噢!真的吗?”二姐西尔维亚讽刺地说。
“珍妮亲口对我说的。”大姐海伦毫不示弱。
“我们没有听到她说愿意土葬。”二姐西尔维亚语气坚定。
“拉比听过。”大姐海伦说得很有底气。
“那是你们两个强迫她同意的。”二姐西尔维亚针锋相对。
“我最后说一次,她不是被强迫的,是她自己说愿意土葬的。”大姐海伦咄咄逼人。
“因为她快要死了,所以才同意的。”二姐西尔维亚毫不退缩。
她们在餐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租赁公司的人来取珍妮用过的氧气罐,还有人打来电话说要来搬走医院的病床,很快,房间里变得空荡荡的。
“珍妮说火葬后把骨灰撒入大海。”二姐西尔维亚说。
“她说把她埋了,她亲口告诉利伯曼拉比的。”大姐海伦说。
“她从不信拉比的。”二姐西尔维亚说。
“难道说你没有见过拉比吗?”海伦反击道,“难道他和珍妮没有见面谈过话?”
“别吵了,”珍妮的二儿子丹请求说,可是两个姨妈谁也不听。
“既然你说起这个,”二姐西尔维亚说,“那么只有你跟珍妮有过要她土葬的谈话。”
大姐海伦怒不可遏地说:“我是让她考虑后事了,你却责备我冷漠无情!我说要安排后事,是因为必须得这样做。”
“珍妮千万次说过她的想法,”二姐西尔维亚坚定地说,“她说把她的骨灰撒入大海。”
“她是这样说的。”珍妮的二儿子丹承认说。
“她从没有改变过。”二姐西尔维亚对大姐海伦说。
“她改变主意了!”大姐海伦哭着说。
可没有人相信大姐海伦的话,理性沉稳的大姐海伦现在仿佛变成了一个有妄想症状的神经病。这几个礼拜以来,二姐西尔维亚总和她针锋相对。
大姐海伦尽管很想得到家人们的支持,但还是控制不住地提高嗓门说:“珍妮跟拉比谈过话,她说把她土葬,这是真的。”
二姐西尔维亚盯着大姐海伦说:“别歇斯底里了!”
当然她们做不了最终决定,珍妮的儿子丹和史蒂夫已经做好了母亲后事安排,他们把母亲的心愿向大家讲明:不举行土葬仪式,而是要举办一个颂扬母亲生平事迹的典礼。
私下里,珍妮的二儿媳梅兰妮和大儿媳安德里亚告诉西尔维亚姨妈和海伦姨妈,颂扬珍妮生平事迹的典礼结束以后,将举行宴会招待所有来宾,所以不用家人做甜点了。为了家庭的和睦,她们特地要姨妈们保证不再带自己在家里做的甜点,像饼干、山核桃棒什么的,尤其是蛋糕。
“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大姐海伦傲慢地说。
“我也是。”二姐西尔维亚说。
大姐海伦又插了一句说:“我决不会在这个时候出风头的。”
在颂扬珍妮生平事迹典礼上没有拉比发言。先是珍妮的学生爱玛演奏了巴赫的乐曲,然后,珍妮的二儿子丹夸赞了母亲生前在这个房子里演奏的美妙的琴音,珍妮的大儿子史蒂夫讲了母亲临终前对他的教导:“不要放弃,不要顾影自怜,不要无所事事,大胆去做。”这些话让他受益匪浅,但他心里知道母亲临终前对他说的是:“不要那样来回走了。”
二姐西尔维亚戴着彩色眼镜坐在前排,她觉得自己不擅长在大众场合讲话的,可是,当她站在发言席的时候,竟然很流畅地按照提前写好的稿子讲起来:“自打珍妮出生,我的朋友们非常嫉妒,我不允许别人碰她一根手指头,她非常可爱,像天使一样,从她出生的那时起,我就很用心地照顾她,我给她换衣服,陪她玩儿,我们在门廊上玩儿上学游戏,我会扮做她的老师,这就是为什么我难以……难以……”
二姐西尔维亚痛哭起来,她的儿子理查德赶忙跑上去安慰她,却惹得她哭得更厉害了,她想不通经历了这段不幸的时光,他怎么还不戒烟?他的前妻,也是他大学时期的恋人,怎么会跟他离婚?她的丈夫卢站在一边,然后带她回到她的位置,她坐在她的丈夫和儿子中间,眼泪仍止不住地流,直到大姐海伦上台发言。
“我是家里最年长的,所以我最后发言。”大姐海伦讲道,“我没让珍妮只听我一个人的话,像所有的人一样,她属于很多人,不是专属于某一个人的,她有父母,”海伦说到这儿,眼睛直直地看着二姐西尔维亚,“她有两个姐姐,作为女儿、妹妹、母亲、朋友,她得到了所有家人们的喜爱,她是个音乐家,她还是个老师,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学生们,她不是敏感、很情绪化的那种人,她非常乐于奉献。”
听到这儿,二姐西尔维亚摘下眼镜,擦干眼泪。
“她不喜欢遵照传统去生活,”大姐海伦讲道,“可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谈到了上帝。”
“撒谎!”二姐西尔维亚跟丈夫卢耳语道。
“她谈到了信仰的事情。”大姐海伦讲道。
二姐西尔维亚在她丈夫的耳边提高了声音:“她在撒谎!”
大姐海伦在上面讲着,二姐西尔维亚却把手里的稿纸翻得哗哗响,她的发言还没有说完,她想站起来讲完她的发言稿,她想让大家了解珍妮生命中的闪光点、一个真实的珍妮,可是来不及了,大姐海伦已经说到了教义中永生和来世部分,已经开始背诵祈祷文了。
二姐西尔维亚快要崩溃了,她想大喊来阻止大姐海伦背诵,可她只能用身边的人能听见的声音说:“珍妮不会同意她说的那
些!”然后默默忍受着,她不愿搅乱典礼,她从不在大庭广众跟人争吵。
在典礼的结尾部分,珍妮的十二岁学生乔治演奏了深沉静穆的小提琴曲《泰伊思冥想曲》,从头到尾都熟练流畅,如果珍妮在的话,她肯定会说,乔治天生就是小提琴演奏家的料。
典礼结束后,家人们开始在珍妮的房子里第一天守丧,按照习俗,应守满七日的丧期,但谁都不能再请一个礼拜的假了。大姐海伦默不作声,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宴席服务人员用亮闪闪的银盘端来蛋奶馅饼、生菜、甜布丁,餐桌上的大水果盘子盛放着工厂机器制作的饼干和味道很淡的咖啡。
客厅里都是珍妮的朋友和邻居,他们对珍妮突然去世感到震惊,珍妮的儿媳梅兰妮和安德利亚安慰着大家,有人感叹着说应该抓住机会享受人生。邻居奥尔巴克夫妇决定先动身去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旅游,然后再去看看北极光,并做了详细的旅行规划。
珍妮的兒子丹和史蒂夫,还有他们的表亲帕姆、温迪、理查德在一楼的工作间里说话,回忆小时候一起在后院里玩球的情景,还让大姨妈海伦去找一找相册,可她怔怔地坐着不肯动,然后,哪里也找不见二姨妈西尔维亚。
天色已晚,客人们开始陆续离开,二姐西尔维亚悄悄回来了,脸上一副沉静的表情,她的丈夫卢跟在后面,手里端着一口锅。
“卢,”珍妮的大儿媳安德利亚警惕地问,“这是什么?”
卢没有停下脚步,他知道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他觉得自己有罪,但他爱自己的妻子。
二姐西尔维亚来到餐厅,把锅里刚做好的苹果蛋糕切成片,顿时,整个房子里飘散着苹果蛋糕的香味。此刻,宴席服务人员正在收拾着冷冰冰的银盘子。
珍妮的两个孙子闻着香味径直跑过来,克里斯蒂安紧跟着也到了,后面还有菲芘。
大姐海伦闻到苹果蛋糕的香味清醒过来,她直奔餐厅,看见家人都在吃着二姐西尔维亚做的苹果蛋糕,她眼中冒着怒火,愤怒使她全身的肌肉紧绷,她和妹妹决裂了。
珍妮的二儿媳梅兰妮劝了,每一个人也都劝了,可是大姐海伦和二姐西尔维亚拒绝和解。她们的孩子们劝着说是个误会,还请求她们别太固执。珍妮的大儿媳安德利亚说现在剩下她们姐妹两个了,可是她们不听。珍妮的二儿子丹说生命太短暂,可是她们不在乎,她们觉得自己还能活很长时间。
劳瑞恩护士说得很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纪念的方式,珍妮的孙女菲芘创作了一首诗;珍妮的二儿媳梅兰妮开始治疗自己的抑郁症;二姐西尔维亚的儿子理查德开始跟在酒吧认识的一个女人约会;大姐海伦的女儿帕姆收养了一只流浪狗;但是,大姐海伦和二姐西尔维亚不肯和解。
春天来了,到了把珍妮的骨灰撒入大海的时间,一家人相聚在马萨诸塞州曼彻斯特海滩,大姐海伦的女儿温迪以悼念珍妮姨妈的名义,劝说母亲和西尔维亚姨妈拥抱和解,她们拒绝了。
责任编辑 刘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