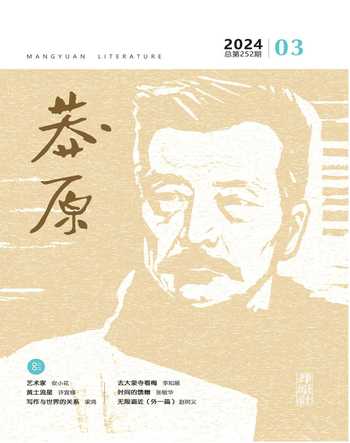瓦屋
赵敏
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才三岁。三岁,记不住事儿。后来六岁了,就记住了。故事不是一次就能记忆深刻的,是一点一点听来记在心里的,像河水轻轻流淌滋养了我半个世纪。在姥姥家族的族谱里,我相信我的姥姥是马湾村李家门族里最幸福的女人,从她结婚的那天起,姥爷对她至死不渝的承诺,让她感动了近一个世纪,也让她终身为这个承诺守护着爱与家,小心翼翼地走过了一辈子。
这是姥爷和姥姥的故事。随着我的年龄逐渐增长,故事也长在了我的心里,经年累月成了一部经典,一部一个旧时代要强女人一辈子与瓦屋相伴的悲情故事,那种蚀骨的磨砺,让她的心疼痛着,也幸福着。这个故事姥姥是主角,瓦屋是她生命的望舒,在她心中的分量有千斤重。
三岁那年,姥姥带着我回到了她的家乡,水河畔南岸的邓襄寨马弯村。水河是沙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支流,最后流进淮水,流过姥姥家瓦屋门前。那清澈见底的流水,多少年多少次我回到它的怀抱里,捧起一捧就能喝下去。脱了袜子把脚伸进水里是很惬意的,水暖暖的,流过脚心、脚背,流到了心底,流到心底就爱得不行。
爱这水,爱这浅山丘陵,爱这姥爷亲手烧制的一片片小灰瓦盖成的瓦屋。瓦屋一排排在村子的土埂上排着,与李家的祠堂斜对着门,通常只要是祠堂里有事儿,在瓦屋的门口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于是,经年累月的瓦屋记载着经年累月的旧事儿,记载着姥爷和姥姥留在乡邻们心中的往事。
姥姥的家就是我的家,从三岁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儿。姥姥常跟她的那群老姊妹带着炫耀的口气说:这小闺女儿在水河里快玩儿疯了。
其实,我没有玩儿疯,我就是喜欢姥姥家门前这条不宽的水河。春季里河水是温温的,青草葳蕤鲜花盛开的时候,河流湍湍东去;夏季河水是热热的,晚上脱了衣裳跳进河里洗的是热水澡,洗完上岸,舒服得让人直打哈欠;秋季里河水日照长,晒好的水不凉不热浇在身上,水流过皮肤,就流到了心窝去;冬季里河水慢了,这条河在我的记忆里是不结冰的。我问过姥姥,它怎么不像咱家左边的坑塘里冬天会结着满池子的冰。姥姥说它和坑塘不一样,河里流的是活水,河水到了冬天只会很慢,天太冷了,水也会变得更凉,它就流得缓了。
有一年秋天,下雨,天一个月都没有晴。河水浑了,汤汤的黄水流过去,流得很急。我站在河边看水流向远处,远处看不到水流去了哪儿,一直到天边。我急得直掉眼泪,心想,这河水为啥浑成这样,往后还咋在河里洗脚洗头。那一年我六岁了。想着想着泪珠子“扑嗒扑嗒”滚落一脸,直到姥姥做好了饭喊我。姥姥扭着小脚来到河边,把我揽在怀里说,哭个啥呀!天一晴,这满河的水清得可快了。不信你看西边,天上晚霞一大片,明儿个准是个大晴天。第二天没有等来大晴天,天却黑云一层,雷声滚滚,下了一天的大雨。我伸着腿被姥姥塞进被窝里坐在床上,吃着她给我煮的嫩玉米,早把天阴天晴的事儿忘脑后去了。
姥爷和姥姥没有儿子,只有母亲一个女儿。姥爷还没有等姥姥给他生出儿子,就死了。那一年母亲五岁,姥姥二十九。就是那个黑云一层,雷鸣电闪的大雨天,姥姥搂着六岁的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姥爷不等她给他生儿子就走了,她那么年轻,她想嫁,但为了她的闺女,她不敢嫁。柴湾张湾有好几个长相俊、家里又富裕的男人常年围着她转,她不敢和他们说话,不敢给那些男人一个微笑……
姥姥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一塌糊涂,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我瞪着一双迷糊的大眼,怔怔地看着姥姥悲凄的脸,举起小手抹去她脸上流下的泪水。姥爷死那年姥姥二十九,到五十岁,她守寡已守了二十一年。姥爷的家族族谱里有五千多人,我相信在这个庞大的门族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姥爷去世之后还那么年轻的姥姥却没有再嫁。旧时代的妇女,丈夫死了守着婆家没有再嫁,那是“烈女”,门族里是要给立牌坊的,可姥姥说她不要那个东西,那东西会把她压死的。当年姥姥反抗家族给她立牌坊在那一带也是出了大名的。她没有文化,可她知道立了牌坊,就得守着那些陈规陋习在人们的口舌中艰难地活着。她找到族长说,牌坊我不要,我也不会再嫁,我会好好抚养我的闺女长大成人。族长说,你还那么年轻,长得又好看,咱们门族里贞女少,你就为咱李家做个榜样吧!姥姥说你非要立,我也没有办法,但你今儿立上,我明儿个就嫁,要不,我拉着我闺女跳河去。族长迫于她的威胁,到底没有敢立牌坊。
她坐在床沿上,拉着我的手说,赶明儿个我带你去住你姥爷给咱盖的瓦屋,那屋子可大可敞亮了。有天窗,還有小窗,排场得很呢!她说你呀,你得快点儿长大,长大了上学了,你得给姥姥说说啥叫“生死契阔,与子成说”!六岁的我在那个时候不可能给她解释“生死契阔,与子成说”的深意,她不懂,我也根本听不懂哦!
姥爷读过两年私塾,很精明,手还很巧,成年之后就传承了李家做小瓦窑技的本领。李家的小瓦烧得在整个豫东南一带都很有名气,十八世纪末已名声远扬,订瓦盖房的络绎不绝,而且知道李家第九代小瓦传承人李山的捏瓦窑技是顶流的。姥爷捏的小瓦烧出来比普通的小瓦要小上一号,角角棱棱完美无缺,拿在手里精致得像个艺术品。
姥姥说姥爷给她说过,一间屋上用多少瓦,那是算出来的,瓦扣着瓦上了屋顶,严丝合缝整齐干净。姥爷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搬着高高的云梯从上往下看盖好的瓦屋,那是他的杰作,他怎么能不欣赏呢?姥爷说从房顶往下看,瓦屋就是一幅百鹊儿图,层层叠叠的小瓦,像鹊儿翅膀上的羽子,一层压着一层。站在房底朝上看,屋角立体出檐,瓦屋简捷明快。在远处看,俨然一座宫殿,虽是灰色,却大气庄重,也常令人驻足欣赏。
姥爷说,“瓦”上了屋顶,它的使命才开始,过路的人会仰起脸来看小瓦的外观和品质。姥爷捏的小瓦,烧出来的颜色也比普通的蓝色略微深一些。他为了把坯泥拉到位,整日里用两条胳膊对着大堆的坯泥拍打,再用木槌使劲儿地夯打。在我的记忆里,姥姥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姥爷烧的小瓦,过程里有手工拍泥,木槌打泥这一关。有关这方面的历史传承,我了解过不少地方民间遗留下来的说法,东南有地方叫“踩泥”,中原的禹州做钧瓷,钧窑也有这一关,叫“练泥”。我国幅员辽阔,江河纵横,坊间制作小瓦的技术无论拍泥、打泥、踩泥、练泥……其内在含义基本都是一样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说法而已。中原土厚,养育了这一民间传承。
烧瓦的窑是柴窑,全是用树桩劈开来烧的,莹蓝色的瓦烧好后像涂了一层洋油,亮亮的锃光起明,顶级的漂亮,还结实。三里五村,十里八乡,远道而来的有钱人家去姥爷的窑上订瓦,都是订三间屋、六间屋、十间屋上用的瓦,姥爷一年里从年头忙到年尾,没有歇下来的空闲。
姥姥说,她和姥爷成亲的那一年,她十七,姥爷二十七,比她整整大了十岁。可她一点儿也不嫌姥爺比她大。
一盏盏灯在瓦屋的周围亮起来了,屋外也灯火璀璨,烟花四起。加上姥爷在十里八乡的声誉,来祝福他成亲的人挤破了瓦屋的门。姥姥是这一带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儿。在娘家长到十七岁,爹娘娇惯她,从没有让她下地干过活儿,姥爷名声远扬,嫁给姥爷是她做姑娘时心里最想的一件事儿。就在那个晚上,姥爷牵着她的手,从拜堂的正厅走进了婚房。
瓦屋是姥爷一只小瓦一只小瓦烧出来后自己盖起来的。专门为迎娶姥姥盖的。瓦屋的墙底下九层蓝砖,上面包墙,外熟里生。外熟里生指的是外墙是砖,屋里用泥坯。在那个时代,农村娶媳妇这是最气派的房子。在大红的绣帐中,姥爷把姥姥白晳柔嫩的手和自己的手合在一起说:妮,往后,后半辈子吧,我们“生死契阔,与子成说”!
姥姥说,她想破了头也不知道姥爷在洞房里握着她的手给她说那八个字是啥意思。她小心翼翼地问姥爷,姥爷只对她宠溺地笑笑。她二十九岁那年姥爷死了,她后半辈子就守着那八个字。姥爷对她的承诺在她二十九岁之后变成了她对姥爷的承诺。
我长大以后,在寒冷的冬夜里,和她一个被窝睡觉,出溜到她的腿底下,使劲儿地用手捏她的小脚。我一个字一个字给她说:“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我问她,我给你讲的你明白是啥意思吗?我说姥爷对你说的“生死契阔,与子成说”就是这意思!她说:是不是字里的女人对她的男人忠贞不渝的决心?我点头说:是!就像姥爷对你那样的亲,那样的爱,你们俩互相承诺的决心一样。她懵懵地似乎是懂了,说,你讲的字里的女人是不是“我”?一瞬间,她把我搂进怀里泪如泉涌,用被子捂着嘴呜咽,对我说:妮啊,你姥爷他给我的承诺是一辈子的,我也给他一辈子的承诺,我守着瓦屋,一辈子守着他。我从被窝里坐起来,把她搂进我的怀里,像小时候那样伸出手抹掉她脸上的泪珠。
岁月走,她也走,她越来越老了,这种思念蚀骨的痛却并未减少一分。
瓦屋外的烟花笼罩了整个马湾村的上空,闪耀的烟花如瀑布飞流而下,马湾村的小瓦烧匠李山和田妮的婚礼热闹了足足三天,壮观到让整个马湾人瞠目结舌。
母亲是姥姥在解放初期送到速成班学过文化的人,也很喜欢读书写字,在我十五岁时曾经对我说:能让父母牵着手,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儿!母亲说,她就希望她的娘和她的爹一辈子都牵着手。
可是,姥爷和姥姥只有十二年牵手的时光。姥姥和姥爷在十二年的岁月里,过成了神仙都羡慕的眷侣。他们结婚七年才有了母亲,那一年,姥姥二十四岁。母亲两岁时,她又怀孕了。她说这一次怀孕和怀母亲时不一样。她的儿子心疼她,她没有任何孕吐,该吃该喝如从前一样。姥爷喜欢得天天干着活儿哼小戏儿:“……曲尽今宵之乐,这才是:欲求真富贵,唯有帝王家……”
说着说着就到年下了,天冷得出不了屋。长长的冰凌挂在屋檐上。姥姥已怀孕仨月整了,要说胎儿也已在肚子里坐实落了,谁承想,家里鸡下了蛋围着院子“咯嗒,咯嗒”叫个不停,像是催她下床去收鸡蛋。她真的就从床上下来了,穿上鞋出了屋去拿鸡蛋。一块冰从房檐上落下,掉在她的脚边,她一脚踏上滑出去八丈远,肚子与院墙碰撞又弹回来,平身子仰面倒下来摔在地上,棉裤腿里大股的血流出来。姥爷去外村收瓦租天擦黑才回来,姥姥躺在坚硬冰冷的院子里昏死已几个时辰了。姥爷回来,吓得腿都软了,他来不及套车,脱下棉袍裹住姥姥冰冷的身体,抱着她就往柴湾柴郎中家里跑。
那个年过不去了,把姥爷姥姥隔在了年的这边。姥爷已几个月没去他的瓦间干活了。终日抱着姥姥的一双小脚给她暖,姥姥只要醒来就哭着喊她的儿子。姥爷说:妮,只要你好好的,还愁咱没有儿子吗?
此后三年,一直到姥爷死,姥姥再没有怀过孕。柴郎中对姥爷说,你媳妇寒邪入了体,这辈子也不会再生养了。
三年之后,姥爷郁结得病而死。姥姥说孩子流掉后的那三年里,她整日以泪洗面。姥爷什么也干不成了,全身心都在她的身上。白天给她变着法做吃的,晚上给她暖脚。带她到济南府逛了十几天。姥姥说,她一直陷在儿子流掉的那种哀伤的氛围里走不出。每每在梦中听到鸡“咯嗒咯嗒”催她起来收鸡蛋,惊醒之后,就整夜再也不能入睡。
姥姥说,真正要姥爷命的是柴郎中给他说姥姥再也不能生养的事,那是一副毒药,生生将姥爷毒死了。
姥爷的右胳膊窝里长了个毒疖子,姥姥说要在平时,也不算啥,喝点儿去火的汤药,很快就会痊愈。可这回不行了,脓疮越长越大,郁结的旺火一下子把毒疮供养大了,姥爷疼得整夜里呻吟。
姥姥说,那一年深秋的夜怎么那样长啊!长得她守着姥爷睁着眼到天明。疼得不停呻吟的姥爷只要歇一会儿,看姥姥的眼神就是炙热的。温润的眸子里像有细流涓涓而淌。姥姥强忍着泪水,依偎着姥爷的身子对他说:我在呢,一会儿柴郎中就来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你跟前看着你。姥爷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柔软的亮光,嘴角往上翘一下,有安慰的笑意在眼角流出。姥姥说她的那颗心呀钻心疼,很多年之后,还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只要提起姥爷,提起姥爷这一段往事,她的泪水就会止不住地流下来。
姥姥说姥爷是个大气沉稳的人,喜怒不形于色。他知道他躲不过这一劫了,到死都没有歇斯底里地让姥姥难过。他被姥姥的爱意包裹着,陪伴着。四十一岁的姥爷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走了。姥姥说她再也感受不到那种沉沉的爱意,在安静的夜里把她搂进怀里的温暖。她把手指放在姥爷的胸口上,就感受到有力跳动的心脏,在她的手底下起起伏伏的愉悦。
她成了寡妇。村里最年轻的寡妇。此刻夕阳西下,大片橙黄的光透过瓦屋的天窗、小窗,铺满了整个空间。在斑驳粗粝的堂屋地面上,像铺了一地黄金。姥爷临死前,放在姥姥手里一个红铜色的小盒,上面有一把小锁锁着,他撕开粗布白夹祅的领口,拿出一把明晃晃的铜钥匙,轻轻地放在姥姥的手里,小声对姥姥说,你打开看看。铜盒里是一摞账单,买小瓦的人家签字画押的欠账单。他对姥姥说:妮,往后你省着点儿花,够你二十年的开销了。他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一直看着姥姥,眼底就像月光铺满了湖面,荡起阵阵的涟漪。姥姥的心瞬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一般,泪水沿着脸颊无声地流下来,她捧起姥爷的脸亲上去说:山哥,你别把我丢下呀!
姥姥说,现在回过头去想,婚后十二年,她和姥爷的相处中藏着很多细节,都是姥爷没有明说的对她的爱意。
姥姥说,姥爷待她好,好得就像她是姥爷的女儿一样。她的发丝垂下来,姥爷给她撩到耳后去;她的额头有汗水,姥爷就用温厚的手掌轻轻给她擦干凈。她的眼尾泛红,二十几岁啊!说不尽的柔情万种。姥姥身体娇弱,吃不了太咸的饭食,姥爷做的饭菜几乎都成了淡的。在吃的上面,家里也没有辛辣刺激的食物,就是因为姥姥不吃这些东西。姥爷是干重活的人,不吃咸食怎么能行。在他的瓦间坊里,茶壶边一直放着一碗食盐水,他喝一次茶水,就把盐水兑开水里一点儿。姥姥怀母亲的时候,五个月了还孕吐得厉害,想吃酸枣。姥爷忙完瓦间的活,就去林子里给姥姥摘酸枣,每次摘枣回来,都被枣树上的尖刺扎得一手的血。摘一小捧枣子,宝贝似的把腰上的汗巾取下来包着,回到家里,再一个个洗擦干净,递到姥姥手里。
姥爷走的那个黄昏,她一直头枕着姥爷的大腿躺在姥爷的怀里,姥爷的右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疼痛折磨得他痛苦不堪。姥姥把泪水咽在了肚里,看着黄昏最后一抹流影快要熄灭了。她仰起头,姥爷的手最后滑过她曲线优美的颈,如同潋滟的水波流泻,如同姥爷在捏小瓦时飞速在瓦沿上捏成的一排美丽的小流印子。姥姥说在那个空间里,她与姥爷的灵魂契合在一起飞进了天堂。
多少年之后,我还记起她眼中的泪光,细碎的泪光,若流星落进碧泉。旧时代的秀女们除了在家里学习女红,家庭富裕允许外出的女子们,还会聚在一起打一种纸牌。纸牌叫“洋画”。柴湾村的柴景元是个心气极高的男人,他读过书,长得也高大英俊。他喜欢姥姥。每每打纸牌,他看着“洋画”中的“七”是个古典大美人,说,这画儿上画的就是田妮,好看着呢!又说,妮呀,李山死了,你就跟我过吧,我会比李山对你更好!
姥姥说:元哥,我是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呀,以后这话就不要再说了。我哪儿都不会去,一辈子就在李山给我盖的瓦屋里住。柴景元撵了姥姥十二年,也没有撵上。最后罢了,也娶妻生子了。
姥姥喜欢穿自己织的瓦蓝色的土布长裙,大摆的。春秋天是碎花的夹祅,冬天是碎花深色小棉祅,黑色的棉裤,外面是大摆瓦蓝色的老土布长裙。长发在脑后绾着,露出修长的天鹅颈。五官纯净而柔美,唇角始终带着恬淡的笑。有时候长发松散,红唇美艳,妩媚的气韵如河水一般清澈,温暖的气息像十月里阳光的线条一样,撒开在野地野花里。柴景元说,她不能与其他女人走在一起,会把其他女人比成渣渣儿!
姥姥喜欢在晴朗的日子里沿着坡地到岗上看瓦屋,许多年一直都是如此。十五岁后我懂得了她一次次回老家看瓦屋的心灵执念。瓦屋的小瓦是瓦蓝色的,她的长裙是瓦蓝色的,瓦屋是姥爷盖的,长裙是姥爷喜爱看的。房子里有姥爷的魂灵在,裙摆上有姥爷的目光在,她说她怎么能改嫁呀!
我跟着她,从三岁去岗子上看瓦屋,一看就是十几年。有一年秋里,下着雾蒙蒙的小雨,她举着伞抬头看向瓦屋,看着看着笑了,看着看着又哭了。她后来对我说,她在细雨里看见了姥爷温暖的笑容,如同阳光一样穿透厚厚的雨帘望着她。
夜很长。她说不知从何年起,她已不再惧怕黑夜的到来,身心皆投进姥爷的怀抱。情感及肉体皆畅快淋漓。即使后来她跟随母亲住进了城市,这种感觉依然包围在她的周身。每隔一段就要回老家去看一次瓦屋,这已成了她生命中的约定,不能更改!
刚刚解放的时候,大舅找到乡里——大舅不是姥姥的儿子,是她婆家的侄子——后来又找到县里,反映姥爷的瓦屋,让懂这方面的专家去鉴定瓦屋的价值。后来省里也来了人,再后来人又走了。给大舅的回音是瓦屋属于普通民居,虽有些年头,但仿古艺术价值还不足以列入国家下拨经费修缮、保护的行列。但可以在李家传承下去,作为教育后人立志、认真读书学习的典范,建立一个教育基地,让大家来参观学习李山同志刻苦努力创新制作的精神!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一个初春,是个倒春寒。三月初,雪花飘得又稠又密,一夜之间,天地换了银装。姥爷的瓦屋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那场风雪之夜里坍塌了。那一年,姥姥八十九岁了。
那一年的深秋来得特别早,姥姥大病,被大舅接回了老家。夜里,我陪在姥姥的病榻前给她暖脚。午夜到来,我对着姥姥的耳朵小声说,“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是姥爷与你生死相依,不离不弃,发誓要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白头到老,永不分离!
姥姥久病的面容上泛起了红晕,说,你妈是真的笨哪,我送她去上学就是想让她给我说说这几个字是啥意思,可半辈子了,她硬是不知道,瞎搭让她上了五年学。还是我的小妞懂我的心呐!然后,她闭上了眼睛,安详地睡着了!
责任编辑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