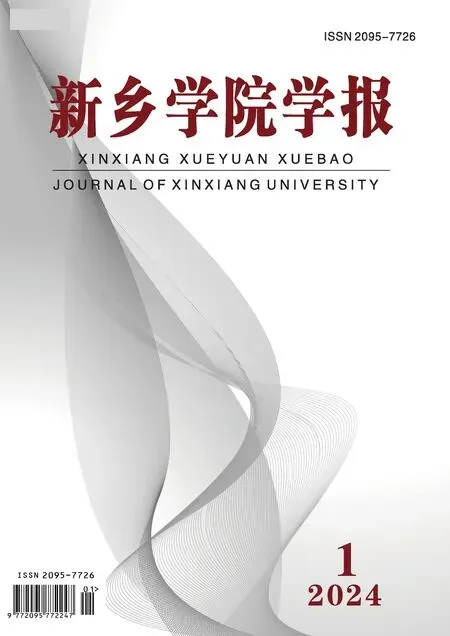“逍遥”与庄屈文化人格
邵文彬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说文解字》对“逍遥”的解释为:“逍遥犹翱翔也。”[1]可知逍遥是翱翔游戏之意。文学与人学有着一体性关系,而相同的文字在不同人的文学作品中,表达不同的情感,因此庄子与屈原笔下的“逍遥”一词,有着不同的精神意蕴。文人的性格与其作品在历史发展中对后人产生诸多影响,成为一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化人格。庄屈二人皆身处乱世,对社会的顺应、反抗或逃避的选择便构成了不同的自由观。“逍遥”在庄子笔下多表现为超脱外物、悠然自适之意,包含着庄子“无为自然”的哲学思想。在屈骚中,“逍遥”多为翱翔游戏之意,包含着屈原“不愿去国”的爱国情怀。后世对《庄子》与《楚辞》的不同注释版本对于“逍遥”一词的理解,因庄屈二人不同的创作背景与创作心态而有所不同。同时,它们承载了后人对庄屈二人不同文化人格的接受。
一、逍遥与无为之学
《庄子》有四篇出现“逍遥”一词。《逍遥游》:“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2]40《大宗师》:“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2]268《天运》:“古之至人,假到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墟,食于苟简之田。”[2]519《让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2]966“逍遥”一词包含着庄子“无为自然”的哲学思想,因而不再单纯地表达为“翱翔”之意。后人对该词的解释也加入了对庄子文化人格的接受。对“逍遥”一词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三种,即自得、忘形与无为。
(一)自得
《礼记·中庸》有言:“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3]无入即无处,自得即自足。言君子不管身处何种环境之中,均能悠然自足地生活。在后人对《庄子》的注解中,许多人将“逍遥”与自得关联。而如果达到自得逍遥的生活境界,则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德理内足。穆夜云:“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2]31唐释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引王瞀夜云:“消摇者,调畅逸豫之意。夫至理内足,无时不适;止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消摇。”[2]2这两种注解将“逍遥”解释为“自得”。若要达到这种状态,需要“德”与“理”内足。德为品德正道,理为事理方法,拥有这种才能,则可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在自己的内德达到完善状态时,面对外在的变化才能以逍遥心态应对。
其二,各当其分。郭象在注释《逍遥游》时认为“逍遥”为“自得”之意:“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4]1《逍遥游》中有很长的篇幅来描写小大之辨,郭象认为尽管鹏可以飞至九万里之外,蜩、学鸠只能“抢榆枋而止”,但万物之间并没有固定统一的评判标准,因此事物之间也没有相互比较的必要。小与大的区别是生来就有的,大鹏与蜩、学鸠只是在各自“性”的范围之内,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因此没有胜负之分,也没有相互比较的必要。郭象认为,自得便是要对自身的自足性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在“分”的范围内,依照其“性”自然发展。只要持守自己的本然状态,实现自身的“性”与“分”的和谐,各当其分,便可以达到自得逍遥的精神境界。
其三,顺时不用。成玄英的观点与郭象相似,除了各当其分,他认为“顺应自然、应物不用”是达到逍遥的方法。如其《逍遥游》疏曰:“彷徨,纵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称。”[4]21《天运》疏曰:“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机而行博爱,应物而用人群,何异乎假借涂路,寄托宿止?暂时游寓,盖非真实。而动不伤寂,应不离真,故恒逍遥乎自得之场,彷徨乎无为之境。”[4]281《让王》疏曰:“姓善名卷,隐者也。处于六合,顺于四时,自得天地之间,逍遥尘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4]504“应物”即面对外物的态度。成玄英在这几处对郭象注的疏中,都体现出其“顺应”观点。认为耽溺于外物只会为其所累,进仕而用也只是暂时游寓于世间。只有不背离真实的本我,身处六合之中,顺应四时变化,身心达到适当的状态,才能体会其中的道而达到自得逍遥之境。
(二)忘形
对外物的态度一直是庄子想要传达的重要思想,也是“逍遥”一词集中体现的文化内核。“自得”重在表达内心的满足,“忘形”则重在表达灭除贪念、摆脱俗物。逍遥是一种超脱肉体的精神状态和不为世俗桎梏的理想人生境界。
支遁在《逍遥论》中云:“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常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2]1支遁是杂糅老释的僧人,对老庄的理解常与佛教相联系。支遁否定了郭象所说的“各当其分”便是逍遥状态的观点,认为“物任其性”只是满足于所得到的,快意天真并不是真正的逍遥之境。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不会因为一次满足而消失。此言“不物于物”是不被外物所奴役,即忘形之意。佛经言:“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5]对外界可欲之物的迷恋则为“贪”,忘却外物,足于所足,方为至足之境。不为外物努力,不为贪念控制,方能达逍遥之境,乘天而游无穷。支遁在解释“逍遥”的时候,不否认凡尘世界,将心看作是达到逍遥之境的核心,加入了自己的人生体悟,赋予其佛教理趣,用庄子玄学来解释佛教道理,对“逍遥”的解释达到了玄佛融合的精神状态。
王夫之《庄子解》言:“逍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脗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6]王夫之在这里将逍遥赋予了认识万物的重要意义,认为要达到庄子所讲“逍遥”之境,必须忘却自己外在的物质形态,不局限于心灵,不执迷于功名。只有忘记外物,摆脱凡尘的束缚,才能达到远游的心灵状态。朱得之在《庄子通义》中指出:“大观而不见世,顺天而不存我,此逍遥之游之旨也。所以相吹举而莫足为之类,动容周旋无入而不自得,所以为逍遥游也。”[7]“逍遥”即忘却外在形体,不拘于心,显现真实本我。
(三)无为
无为是庄子哲学的重要范畴。若论及“无为”,“有为”也是重要的讨论对象。顾桐柏云:“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2]30顾桐柏认为“有为”即是人生的烦累,“逍遥”便是要消除有为的烦累,摆脱凡尘,以无为而游。
刘武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也提出对郭象“自得逍遥”观点的反对。他认为:“逍遥,无为也。是欲心意之逍遥自得,重在无为也……本篇之旨在凝神,而神之能凝,在心意之逍遥,欲心意之逍遥,则在无为。人之不能逍遥者,有为也。其所为者,名也,功也,己也。”[8]刘武并不同意郭象的说法。他认为“逍遥”一词并不能解释为自得本真,若这样解释,不能很好地解释《逍遥游》全篇,失去了庄子创作的旨意。刘武认为《逍遥游》的意旨就在于凝神。“逍遥”之意在于心意,只有心意逍遥才能凝神。而若要心意逍遥则需要无为。人之所以不能达到逍遥之境,是因为总是有为的。人的“功、名、用”便是“有为”,这是牵绊人走入无为逍遥之境的因素。人们被功名凡尘所束缚,不能走入真正的逍遥之境。鹏虽然可以乘风到达南冥,但它仍需有所凭借,而只有达到无己状态,才是真正的逍遥。达到无名、无功、无己、无用人,才是无为的逍遥状态,这也就解释了“逍遥”在《庄子》中的含意。
除了“自得”,郭象、成玄英二人也将“逍遥”解释为“无为”。郭象认为庄子所写“逍遥”有无为之意,在《天运》与《大宗师》篇的注解中提出自己对于“无为”的理解:“有为则非仁义。”“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4]148即只有无为才是仁义之举,是寻求真我的唯一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郭象认为庄子所言“无为”并不是沉默、隐藏于山林之中的无所作为,而是应该各司其职,“各当其分”。强调顺应事物的本性而为,才可达逍遥之境。成玄英曰:“彷徨逍遥,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尘埃,色声等有为之物也。前既遗于形骸,此又忘于心智,是以放任于尘累之表,逸豫于清旷之乡,以此无为而为事业也。”[4]148成玄英认为尘埃便是色、声等入世的欲望,这些“有为”的外物会阻碍事物的本真发展状态。将“逍遥”的自得之意上升到丢弃形骸之中的声色,可达到无为状态。
二、逍遥与高洁之心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9]。《离骚》等赋是屈原因奸臣进谗言被贬他乡后所作,作者渴望报国而无门,愿进忠言而被君王周围的污浊之人所排挤,在文字中表达了自身的愤懑和伤悼之情。屈原诸赋中,《离骚》《湘君》《湘夫人》《哀郢》《悲回风》《远游》篇中出现“逍遥”一词。如《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10]28《湘夫人》:“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10]68总体而言,与庄子的潇洒自然不同,屈原笔下的“逍遥”是以忧愁为情感基调的。后人在对其赋进行注解之时,也会受这种情感基调以及屈原文化人格的影响。后人对“逍遥”的注解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游戏
第一种注解为“翱翔、游戏”。这种注解是词语表层含意。王逸注:“逍遥、相羊,皆游也。”[10]28洪兴祖注:“逍遥,犹翱翔也。”[10]28汪瑗注:“逍遥容与,皆从容游戏之貌。”[11]118“逍遥,犹翱翔也。”[11]73“浮游逍遥,皆优游自适之意。”[11]81朱熹注:“逍遥、相羊,皆游也。”[10]19“逍遥、容与,皆游戏闲暇之意也。”[12]36屈原因奸臣进谗言而被贬,远离君王,流离他乡。屈原无官无职,不能参与国事,只能被迫翱翔游戏。这几个注解都是从“逍遥”的字面含意出发进行解释,尚未与其生活环境、心态背景相联系。
(二)无所之
屈原之“游”,并非字面的逍遥闲适,而是被迫去国。这种对“逍遥”的注释便有了被迫和无所适从的情感背景,超出了词语的原本含意。言贪浊者大盛,屈原欲异行去国,远离贪浊之人却无处可去。戴震对“逍遥”注言:“为聊须臾以相羊。”“托言欲求淑女以自广,故历往贤妃所产之地,冀或一遇于今日而无良媒以通己志。因言世之浑浊,无所往而可者。”[13]朝中浑浊之人当道,屈原因不愿与贪浊者同趣,为保自身高洁而被迫去国。此处“逍遥”包含作者不知自己该去何处的彷徨以及怎样能保全自己高洁之身的疑惑。
汪瑗云:“终古之居,谓先人自古居于此土,而子孙百世不迁者也。今则失之,漂摇而来东矣。”[11]175此处的“逍遥”意为“漂摇”。屈原述自己祖先百年以来一直居于此地,而今自己被贬,不得已远离故土。洪兴祖云:“言己既求简狄,复后高辛,欲远集它方,又无所之,故且游戏观望以忘忧,用以自适也。”[10]34屈原想要去远方,想要离开国家和君王远去,又没有可去的地方,只能游戏,使自己忘却忧愁,蕴含着屈原无处可去的苦恼,以及对浑浊奸臣无法根除的无奈。
(三)待君
在“被迫”的情感之上,对君王的期待便是其第三层释义。屈原在被迫远离故土之后,仍留存着想要回归朝廷拯救国家的想法。“逍遥”一词便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心情。屈原待君,此处所待既有君王又有天命。
洪兴祖云:“言己总结日辔,恐不能制,年时卒过,故复转之西极,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10]28五臣注:“自言忧愁,欲以决死,死不再生,何由复遇。逍遥容与,待君之命,冀得尽其诚心焉。”[10]64屈原想要以死诀别,但仍然期冀着君王的命令,希望可以将自己的诚心表达出来。此处的“逍遥”代表屈原欲远离朝政又待君主唤其回归之心,这样矛盾心情的描写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诚心:即便至死,也一心报国;虽远在他乡,但待君之心昭昭。
汪瑗注曰:“己迎湘君之不来,遂弭节北渚之间,而复捐玦遗佩,并采杜若以贻下女,而转致之于湘夫人,以达己殷勤之意,思望之心,而且贻其行乐之言也。”[11]118自己迎湘君而不来,采杜若希望能转达给湘夫人,以转达自己的殷勤之意和思盼之心,望能与之行乐,逍遥而游。此处以写对湘夫人之情来表达对君王的眷恋。
三、自由观与文化人格接受
社会、文化的兴衰对文化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文人对社会或顺应,或逃避,或反抗的方式,对后人产生诸多影响,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人格。庄屈笔下的“逍遥”代表的是二人不同的文化人格。
(一)庄子之潇洒脱俗
《逍遥游》集中体现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在《逍遥游》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潇洒恣肆的生活状态和超凡脱俗的人生姿态,而“逍遥”一词代表了庄子追求身体和心灵双重自由的理想。庄子所认为的“逍遥”,是自由的心灵状态,是在纷纷扰扰的世间不被俗尘束缚,无拘无束遨游,展现出超越现实、摆脱俗世的精神世界。庄子要人们恬淡自然,不争不抢,面对复杂的社会,做真实的自我,守护本真,减少私心杂念。道家的“出世”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
庄子所要表达的自由是与他的生活背景有关的。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庄子不愿融入积极入世的浪潮中,却创造了向往本真、自然原始的自由观。庄子是在混乱的社会现实中被迫保存自己,无用无为、潇洒恣肆是应对混乱社会产生的理想生存状态,也是对一些贪欲过盛的君王的劝诫。
(二)屈原之苦闷无奈
屈骚中有着浓郁的个人思想与情怀,充满着奇异浪漫的色彩。屈原被奸佞构陷,放逐他乡,报国之心无法实现。屈原笔下的“逍遥”和庄子是不同的。屈原不是悠然自适的状态,而是对回归故土的极度渴望。他笔下的自由充满了消极情绪,流露了仁人志士报国无门的苦闷,反映了强烈的爱国和忠君思想。
四、结语
龚自珍言:“庄、屈实二,不可以并。”[14]二人处于同一时代,面对繁复错杂的社会现象,对“自由”有着不同的选择。二人的“逍遥”观及其对后人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别。统而言之,有如下三点。
其一,外在与本心。屈原的逍遥与自由是表面的,尽管身体处于去国远游的状态,但内心之中仍待君赏识,渴望回归故土。庄子追求心灵真正的逍遥自由,哪怕居于乱世,其心灵仍处于超脱俗世的本我状态。
其二,被动与主动。屈原的自由是被迫的选择,因此其笔下的逍遥充满了消极情绪,是报国无门的哀怨与苦闷与对奸佞小人的反抗态度。庄子则主动选择自由,其笔下的逍遥充满调畅轻快的情绪,是逃避奸佞、崇尚自然的顺应态度。
其三,有为与无为。面对凡尘俗世、奸佞小人,屈原选择与其抗争,甚至以死进谏。庄子认为凡尘俗世会阻碍人进入逍遥境界,因而选择了消除有为的苦累,顺应自然,在凡尘中保存自己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