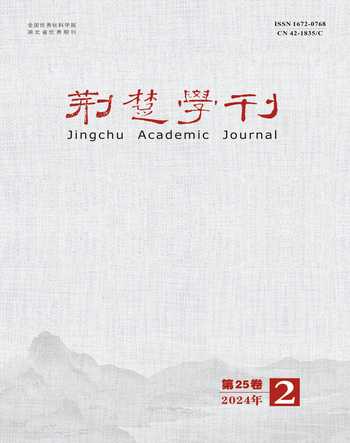阳明后学陈九叙历史地位考
摘要:围绕晚明名宦陈九叙的学派归属、生卒年、交游、著述,通过文献考证与田野考察发现,陈九叙本是曾汝檀高弟,曾汝檀去世后,远赴仪真,改投王襞门下。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根据康熙《漳平县志》所载,将陈九叙列入曾汝檀学派。陈九叙的阳明学研究成果,深得沈宠、耿定向的赞许。陈九叙的阳明学著作《途次论学漫记》,请其学友杨起元品评,获得称道。陈九叙以王守仁再传弟子的身份,撰有《重刻传习录引》。陈九叙与许孚远交往,促成蒋时馨师从李材。陈九叙墓志铭及其故里地方志未载其师从王襞,只记载了他早年曾师从曾汝檀。分析其缘由,有选择性处理的原因,文章还由此提出应重点进行文本分析的建议。
关键词:陈九叙;王襞;阳明后学;泰州学派;明代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4)02-0013-11
陈九叙(1530—1611),字尔缵,号文溪,福建漳州府漳平县人,嘉靖四十年(1561)中举,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处州知府、两浙运同、桂林府同知。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只身前往仪真师从王襞,又于隆庆五年辛未(1571)与其漳州同乡友人蔡国宾远赴王襞故里泰州追随其师。著有《途次论学漫记》《觉订漫记》《心源录》等,曾为朱文启、朱文教重刻王守仁《传习录》并作序,其门人李之藻将其著作刊行于世,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有传。
目前,学术界关于陈九叙的研究,从以往鲜为人知,到根据王襞文集记载而得知其曾师从王襞,再到分析陈九叙所作重刻王守仁著作序文,生平事迹渐显,但仍存在文献搜集不够、文本分析不足的问题,以及出现误读文献,误识陈九叙其名、未考证陈九叙生平与家世及交游,未还原陈九叙应有的学术地位等。黄文树未认真查阅王襞的著作,不曾提陈九叙是王襞的门人[ 1 ] 375。钱明据王襞年谱所载而述及王襞门人陈九叙,却因未仔细查看原文而将陈九叙的“叙”字误作“叔”字,又误认为陈九叙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前往泰州师从王襞[ 2 ]。张树骏亦将陈九叙误作“陈九叔”,且未述及陈九叙所作王襞祭文记载的陈九叙于隆庆五年辛未(1571)与其友人前往泰州师从王襞之事,未将陈九叙视为王襞的突出门人[ 3 ];未述及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將陈九叙划入曾汝檀学派,未就此考证其史实[ 4 ];认为泰州学派“消亡于万历三十到三十二年间(1602—1604)”[ 5 ],实则有误,泰州学派消亡时间应在陈九叙去世的万历三十九年(1611)之际。汪学群未据陈九叙万历二十一年(1593)所撰《重刻传习录引》落款“万历癸巳阳月既望,漳平后学陈九叙撰”,结合王襞著作所载陈九叙的王襞门人身份,来揭示陈九叙的王守仁再传弟子身份[ 6 ]。当前漳州阳明学者张山梁大多重述晚近地方志记载[ 7 ],其与林晓峰[ 8 ]的漳州阳明后学论述,均未将陈九叙视为阳明后学。源于漳平县自清雍正十二年(1734)由漳州府析出,改隶龙岩直隶州,乾隆《漳州府志》与光绪《漳州府志》由此未为陈九叙立传。
基于学术界对陈九叙的学派归属尚无考证,陈九叙在阳明后学的历史地位未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鉴于此,本文围绕陈九叙的学派归属问题,搜集《明实录》、科举文献、地方志、文集、族谱、碑铭等史料,通过再现陈九叙由曾汝檀高足改师王襞的历史情境,考证陈九叙师承关系变迁,分析陈九叙改师王襞的原因;还原陈九叙与王襞的交往过程,揭示陈九叙与王襞的师生关系程度;考察陈九叙与阳明后学的交游情况,分析陈九叙与阳明后学的渊源关系。以期解决陈九叙学派归属问题,还原陈九叙应有的历史地位,为当前阳明后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一、陈九叙改师王襞的历史情境
地方志明确记载陈九叙师从湛若水的再传弟子曾汝檀,并声称陈九叙得其真传,俨然是曾汝檀的高足。地方志陈九叙传提及陈九叙曾向王襞请教,似乎王襞仅是陈九叙请教的前辈,二人并无师生关系。陈九叙的长子陈钟会所撰《明赐进士中顺大夫处州郡守理学陈先生文溪翁圹志》只字不提王襞,仅云陈九叙师从于曾汝檀。尤其是清初理学家李光地之孙李清馥,将陈九叙列为曾汝檀学派传人,似乎陈九叙归属曾汝檀学派之说已成定论。然而,王襞著作中却述及陈九叙师从王襞的具体时间,重刻的王守仁著作亦收录陈九叙所作序文,亟需深入考察陈九叙与王襞的关系。可是,王襞著作仅载陈九叙嘉靖四十五年(1566)师从王襞,却未提陈九叙求学时的身份及其处境。还原陈九叙改师王襞的历史情境,将有助于了解甘泉学派与阳明学派之间的互动过程,揭示王襞学说产生的历史影响,分析陈九叙由曾汝檀高足改师王襞的原因以及遇到的困难。下文通过搜集地方志、族谱、碑铭等史料,考察陈九叙生平与家世,考证陈九叙师承关系的变迁。
漳平县及其先后所属的漳州府、龙岩直隶州所修地方志,记载陈九叙的师承关系,仅提陈九叙师从曾汝檀。万历癸丑《漳州府志》称陈九叙曾师从曾汝檀,陈九叙“尝受学于曾廓斋先生”[ 9 ] 1582,“曾廓斋先生”指曾汝檀,号“廓斋”[ 10 ] 923。该志虽载陈九叙深得沈宠、王襞、耿定向的垂青,却未指出陈九叙师从王襞。“沈古林、王东厓、耿楚侗诸先辈,咸印可其学,以为正脉”[ 9 ] 1583,“沈古林”指沈宠,号古林,分属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王东厓”指王襞,号东厓,“耿楚侗”指耿定向,号楚侗,二人同属泰州学派。根据漳州军府长泰县籍进士戴燿为该志所撰《漳州府志序》落款,为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九月,该志刊于此时[ 11 ]。康熙《漳平县志》[ 12 ] 卷七,34b-35b沿此说,康熙《福建通志》仅称陈九叙师从曾汝檀,而未提陈九叙曾向沈宠、王襞、耿定向请教[ 13 ]。康熙《漳州府志》[ 14 ] 卷二十三,19a-b虽沿此说,却将王襞别号“东厓”的“厓”字误作“里”[ 12 ] 卷二十三,19b字。乾隆《龙岩州志》改称陈九叙师从曾汝檀,使人误以为陈九叙仅师从于曾汝檀,陈九叙“受学”曾汝檀[ 15 ],亦误作王襞别号“厓”字为“里”[ 15 ]字。何乔远、何九云父子述及陈九叙。何乔远《闽书》称陈九叙早年师从于曾汝檀,但将王襞别号“厓”字误作“涯”字,陈九叙“少学曾汝檀之门”“沈古林、王东涯、耿楚侗诸先辈咸推重之”[ 16 ]。何九云于崇祯年间漳平县儒学教谕任上,所作《平先辈诗》其七《陈太守九叙》称陈九叙师从曾汝檀,陈九叙“师事曾运使,教人必曰:廓翁、廓翁云。廓堂,运使精舍也”[ 12 ] 卷八,6b,“平”指漳平县,“曾运使”“廓翁”指曾汝檀,“运使精舍”指曾汝檀创办的心源精舍。何九云崇祯己卯(1639)为明代理学家陈真晟倡建漳平陈布衣祠,在其所撰《新建陈布衣祠记》又云陈九叙深受陈真晟“过化”漳平的影响,“然平之先辈之用心正学者,若曾公汝檀、陈公九叙、蒋公时馨,岂非闻先生之风而兴起者哉”[ 12 ] 卷八,25a。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列“运使曾惟馨先生汝檀学派”[ 17 ] 842传人一人“同知陈先生九叙”[ 17 ] 843,“运使曾惟馨先生汝檀”指“曾汝檀,字惟馨”[ 17 ] 842,“同知陈先生九叙”指陈九叙,亦将王襞别号“厓”字误作“里”[ 17 ] 783字。陈钟会陈九叙圹志仅称其是曾汝檀高足,陈九叙“多解悟师廓斋曾先生学、白沙学,得其传”,却未提陈九叙改师王襞及其与阳明后学交游。事实果然如此?答案是否定的。
陈九叙“字尔缵”[ 9] 1582,“号文溪”[ 18 ] 712,其圹志称:陈九叙“生于嘉靖己丑年十二月十三日丑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三日巳时终正寝”“嘉靖辛酉以《诗经》魁闽省”,即生于嘉靖八年己丑十二月十三日(1530年1月12日),卒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十月十三日(1611年11月17日),中举于嘉靖“四十年辛酉”[ 19 ] 1079,该圹志作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即1614年12月1日。陈九叙出身军籍,《明万历二年进士题名碑录(甲戌科)》载:“陈九叙,福建漳州府漳平县军籍”[ 20 ] 938,其“初为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守括苍”“左迁醝司”“起补桂林府同知”[ 9 ] 1582-1583。
陈九叙早年师从曾汝檀,成为湛若水的再传弟子。陈九叙在曾汝檀去世后,从故里远赴仪真师从王襞,又成为王守仁及其高足、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陈九叙师从王襞的时间与地点。陈九叙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从漳平县出发,前往仪真师从王襞。其时,王襞应仪真县主簿林华的邀请,在当地讲学。王襞年谱载:“(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仪真主政李皋华公聘主讲席。是年,闽漳州陈九叙……来学”[ 18 ] 648,“仪真主政李皋华”疑是仪真县主簿林华,其是“莆田人”“嘉靖任”[ 21 ]。
陈九叙当时有两个身份:
其一,曾汝檀的高足,对曾氏学术推崇备至,并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陈九叙“以易简中正为宗,由人伦日用穷探原本,一切异说、眇论辞而辟之”[ 9 ] 1582。
其二,举人。陈九叙于嘉靖四十年(1561)中举。
陈九叙中举后,未在翌年联捷进士,亦未在中举三年后考中进士,促使其反思,决定放弃举子业,转而潜心钻研学问。
陈九叙选择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改师王襞的原因有二:
其一,曾汝檀生前曾述及阳明学说。漳州知府罗青霄在万历元年(1573)修成《漳州府志》述及曾汝檀“尝以《中庸》戒惧谨独教人,曰: ‘《中庸》揭此独知,为后学开一个门路,多少紧切。譬如种植,必有真种子落地,然后培植,日加畅茂。阳明先生专以致良知为言,盖亦有见于此尔。”[ 19 ] 1083“阳明先生”即王守仁,号阳明。该志“编纂”“谢彬”[ 19 ] 5称该志曾汝檀传采自陈九叙所撰曾汝檀行状:“先生既殁,复得与先生之嗣子思鲁及门人陈九叙者游。而九叙又能状先生之行略以告于余,因得叙次之如此云”[ 19 ] 1084,“先生”指曾汝檀,陈九叙于曾汝檀生前对阳明心学有所知。
其二,曾汝檀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去世,陈九叙选择在三年后改投王襞门下,显然已按子为父守孝三年礼节处理。
陈九叙改师王襞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来自陈九叙的宗族成员压力。明代中叶,漳平形成宗族社会,陈九叙作为宗族成员而深受其宗族影响。陈九叙的堂叔祖陈辅是曾汝檀的岳父,陈九叙的堂兄陈茂楠曾与曾汝檀同修漳平县首部县志——嘉靖《漳平县志》、陈九叙的堂弟陈茂葵是曾汝檀的妹夫。陈九叙在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参与为其五世祖陈志仁竖立墓碑“敕赠户部主事志仁陈公墓”,该碑落款“嘉靖四十年辛酉冬,七世孙九叙……立石”,右刻“男阳泰、雍奉祀”,“雍”即陈九叙的高祖陈雍,“阳泰”是陈九叙的高伯祖陈阳泰,其后裔与曾汝檀的渊源深厚,促使陈九叙顾及此层关系。陈阳泰之孙陈辅“长女适睦里曾元清知县子汝檀”[ 22 ] 81,“睦里”是漳平县和睦里的简称。陈阳泰的五世孙陈茂楠“常与曾廓斋先生汝檀同修县志”[ 22 ] 85,此“县志”指嘉靖《漳平县志》[ 10 ] 957;陈茂葵“配曾氏,和睦里曾汝檀之妹也”[ 22 ] 114。陈九叙改师王襞,将引发其宗族成员的反弹,对陈九叙施加压力。尤其是陈九叙的堂弟陈九仞,曾与之一道师从曾汝檀,又是陈九叙的同科举人[ 19 ] 1079。陈九叙改师王襞,势必遭到陈九仞的反对,导致陈九叙只能独自远赴仪真改师王襞。
其二,来自漳平地方社会的舆论压力。曾汝檀是漳平置县后首位漳平籍进士[ 10 ] 1115,深得漳平地方社会的推崇。曾汝檀创修嘉靖《漳平县志》,掌握地方社会的话语权,湛若水为该志作序。陈九叙作为曾汝檀的高足,其动向因此备受漳平地方社会的关注。
陈九叙之所以决定改师王襞,原因有二:
其一,与其时闽籍士子师从王襞,以及王襞入闽讲学有关。王襞的福建活动影响深远。嘉靖二十九年(1550),福州人朱孔阳前往泰州师从王襞,“(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是年闽朱卦洲……来学”[ 18 ] 647,徐渭《徐文长自著畸谱》所载《纪知》作“朱子,号卦州,孔阳”[ 23 ],“朱卦洲”的“洲”字应改作“州”字,即“朱孔阳,号卦州”[ 18 ] 712。王襞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起,入闽讲学半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襞应其同门师弟、王艮门人、时任建宁府同知董燧的邀请,前往建宁府讲学,为期半年。王襞年谱载:王襞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春二月,講学于闽建宁府……时乐安蓉山董公,署府事……于是留半年始归”[ 18 ] 647,“蓉山董公”指董燧,号蓉山。钱明引用邹守益《武夷第一曲精舍记》所载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郡丞董子燧”谋划在建宁府崇安县武夷山兴建王文成祠,认为董燧时任建宁府通判,却未提及《建宁府志》所载建宁府通判名单并无董燧、建宁府同知名单则载有董燧[ 24 ]。董燧实则担任建宁府同知,而非建宁府通判。康熙《建宁府志》载:同知“董燧,临川人,举人”“嘉靖间任”[ 25 ],董燧实则乐安县籍,从其祖父董时望的户籍即可得知,《明成化二十年进士题名碑录(甲辰科)》载:“董时望,江西抚州府乐安县民籍”[ 26 ]。
其二,与王襞、陈九叙对朱子理学的认知有关。王襞建宁府追寻朱熹足迹,陈九叙于故里探讨朱熹学说,促使他关注王襞。王襞建宁府讲学期间,探访朱熹故居,凭吊朱熹“过化”事功。王襞建宁府讲学期间,“谒紫阳公故庐”[ 18 ] 647,“紫阳公”指朱熹,“故庐”指朱熹位于建宁府的故居。朱熹“本贯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父为户”[ 27 ]。朱熹曾“过化”漳州,陈九叙对朱熹“过化”有所知,早年曾在漳平故里与乡人探讨朱熹学说。陈九叙曾在漳平故里与杨豫的门人蒋时馨、叶时新探讨朱熹“穷理致知”学说。叶时新“素与陈文溪、蒋兰居二先生善,益相讲明穷理致知之学”[ 12 ] 卷七,38a,杨豫“蒋兰居、叶泰窝二先生出其门”[ 12 ] 卷七,13b,杨豫与陈九叙的堂弟陈茂葵是儿女亲家,陈茂葵“生二女”“次适睦里教谕谢畲豫之子”[ 22 ] 114,杨豫是漳平县和睦里“卢溪社谢畲”[ 12 ] 卷一,7a人,曾任“遂溪教谕”[ 12 ] 卷七,13b;“蒋兰居”指蒋时馨,号兰居;“叶泰窝”指叶时新,学者“称为泰窝先生”[ 12 ] 卷七,38a。
陈九叙认识阳明心学的途径,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阳明后学在漳州的活动。王守仁漳南平乱,王守仁高足黄直自嘉靖三年到七年(1524—1528)担任漳州府推官,宦绩突出。王守仁高弟邹守益在嘉靖十九年(1540)应其门人侯一元之邀,为漳南道侯庭训主修《漳南道志》所撰《叙漳南道志》,述及其时漳南道仍沿用王守仁诸令[ 28 ],而漳州时属漳南道管辖。
其二,泰州学派成员宦游漳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守仁与王艮的门人徐樾于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到访漳州,与漳州军府龙溪县籍进士杨表交游、蔡烈论道,参与为漳州望族节妇曾氏竖立牌坊。王艮与徐樾的门人朱锡自嘉靖三十年到三十一年(1551—1552)任漳州府儒学教授,参与竖立漳州籍进士王昇牌坊,同王慎中交游论道[ 29 ]。
陈九叙认识阳明后学,从其个人经历来看,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陈九叙的同五世祖堂兄、曾汝檀的师弟陈茂芝先后师从湛若水与蒋信。陈茂芝(1506—1589),“生于大明正德元年丙寅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大明万历十七年己丑七月十三日”[ 22 ] 107,其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曾请汝檀为其父撰写行状,“以曾廓斋之状”[ 22 ] 97,请陈让、王慎中分别为之撰写墓志铭、墓表。蔡清的再传弟子、陈琛的堂弟陈让《广东德庆州学正南川陈府君墓铭》称陈茂芝“从湛甘泉、蒋道林体认天理内外合一之学”[ 22 ] 94,蔡清的再传弟子王慎中《广东德庆州学正南川陈公墓表》称陈茂芝“幼年向道,常学于湛甘泉公之门”[ 22 ] 99,其时为“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孟夏之吉”[ 22 ] 100,“湛甘泉”指湛若水。“蒋道林”指蒋信。蒋信最初师从王守仁,后改投湛若水门下,蒋信此特殊身份,促使陈九叙对阳明后学有所了解。
其二,陈九叙早年恩师曾汝檀获得阳明后学姜宝的推荐,入祀乡贤祠。曾汝檀去世后,“督學姜公宝访求八闽人物,独推重公,祀之乡贤祠”[ 19 ] 1084,“姜公宝”指姜宝。姜宝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之前担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嘉靖四十四年九月“癸丑,升福建按察司副使姜宝为南京太常寺少卿”[ 30 ]。姜宝师从唐顺之,唐顺之师从王畿,王畿师从王守仁,姜宝是王守仁的三传弟子,属于浙中王门。姜宝不因曾汝檀为湛若水的高足,而区别对待曾汝檀,促使陈九叙改变对阳明后学与阳明心学的印象。
再现陈九叙由曾汝檀高足改师王襞的历史情境,有助于了解陈九叙的思想演变过程,是陈九叙划归阳明后学立论的基础。陈九叙改师王襞之前,即从曾汝檀的言传身教中,对阳明心学有所认识。曾汝檀去世后,陈九叙失去精神支柱,加之身为其宗族较早考取举人却苦于久困场屋,促使陈九叙决定改师王襞。陈九叙并非仅读王襞著作而遥尊之,亦非只与王襞诗文往来而结成文字交,却选择背井离乡远赴陌生的江南他乡改师王襞。陈九叙深知改师王襞,势必引起甘泉学派的攻讦,将其视为辜负师恩的离经叛道之徒;亦必将遭到与曾汝檀数代联姻的宗族成员的发难,认为其薄情寡义。然而,陈九叙出于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体现了其大无畏的精神。不能停留在重述文献记载的层面,而是要揭示文献记载背后的历史情境。应回到当事者所处的历史现场,对当事者抱之以同情与理解,探索其思路演变历程。如此方能更好地认识陈九叙,深入了解王襞学说及其产生的影响,管窥明代学人的思想变迁。
二、陈九叙与王襞的交往过程
还原陈九叙与王襞的交往过程,是再现陈九叙改师王襞的历史情境之后的必然,对考察陈九叙的学派归属将起到关键的作用。王襞年谱仅载陈九叙于嘉靖四十五年庚寅(1566)师从王襞,陈九叙所作王襞祭文却云陈九叙于隆庆五年辛未年(1571)与其友人远赴千里之外师从王襞,此二说孰是孰非?此陈九叙学友又是何人?陈九叙与之同往何地师从王襞?陈九叙两次师从王襞的身份有无变化?陈九叙缘何两次师从王襞?为何是陈九叙友人与之同往,而非陈九叙同科举人的堂弟陈九仞?陈九叙缘何多次离开王襞?陈九叙如此“反复无常”是否遭到王襞的冷遇?从而影响陈九叙与王襞的师生关系,以至于地方志仅载陈九叙师从曾汝檀,而未提陈九叙改师王襞?陈九叙改师王襞是否有诗文为证?由于陈九叙著作已佚,陈九叙与王襞的诗文为孤证,所载是否可信?陈九叙与王襞是否曾探讨泰州学派思想以及阳明心学?对此,下文梳理王襞著作与地方志记载,考证陈九叙师从王襞的起止时间,揭示陈九叙与王襞的关系程度。
还原陈九叙与王襞之间的师生交往过程,这就要对陈九叙所作王襞祭文详加考证。王襞于万历十五年丁亥十月十一日(1587年11月10日)去世,陈九叙写下祭文,因故无法前往祭奠,只能安排专人于万历十八年庚寅四月二十六日丁酉(1590年5月29日)代为祭奠。其祭文云:
万历庚寅四月壬申朔越二十六日丁酉,门生陈九叙自□□遣人斋香帛众羞,告奠于东厓老师王先生之灵,曰:呜呼!圣贤既殁,道术湮沦。不有先觉,孰起而振翳。我心斋先生,天挺独复,拔萃离伦。演会稽之学,而自得其真。其要归于格物,其道极于尊身。乐学一歌,濂洛遗绪。大成有作,出处一致。凡厥同门,儋荷其最。乃生厓师,道遵庭趋,克承先志,四方求友,订其所至。凡东郭、龙溪、绪山诸先生,莫不折简,爰询抠趋。其□□是,深造浑成,倡道海濒,而响动金陵。凡我同方,莫不愿见其颜色,而侧听其指陈。粤自辛未,乃□吾友,千里问学,厕迹师门,谆谆汲引,春风座生。或指导其所闻,或联群而浩吟。感教益之良多,忻色笑之可亲。独惜夫为日之浅,乃靳止于再旬,言别参辰,已一官之系缚,欲侍侧而莫能。岁惟辛巳,奉命江而,始获一通刺于司阍。诵师翰诲,德音犹存。惟是致良知于日用,以求自慊。信中渡之一瓠,而剖眼之金银也。又孰意夫曾阅岁之几何,奄忽逝此哲人,恨云山之阻深。乃寥廓夫讣闻,嗟余生之寡昧,将卒业而奚从。哀铎响之既湮,谁与振后学之沉沦?岂大运之弗辰,抑彼苍之无意于斯文。嗟贤嗣之我顾兮,欷歔相与概述夫生平。幸遗言之未泯兮,犹可以想像其仪刑。傥神灵之可通兮,将阴佑不敏小子于冥冥。[ 18 ] 711
“东厓老师王先生”“厓师”指王襞,号东厓。“心斋先生”指王艮,号心斋。“会稽之学”指阳明心学,源于王守仁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绍兴府古为会稽郡。“东郭”的“郭”字应改作“廓”字,即“东廓”,指邹守益,号东廓。“龙溪”指王畿,号龙溪。“绪山”指钱德洪,号绪山。邹守益、王畿、钱德洪三人均是王守仁的高足,邹守益属于江右王门,王畿与钱德洪属于浙中王门。“辛未”指隆庆五年辛未,“辛巳”指万历九年辛巳。王襞年谱所载王襞“(穆宗隆庆)五年辛未”[ 18 ] 648记事,未提其外出讲学,王襞其时在泰州故里。陈九叙于隆庆五年辛未(1571)与其友人从漳平出发前往泰州,向王襞学习,此为陈九叙再次接受王襞的耳提面命。而后,由于陈九叙在外为官,无法继续接受王襞的耳提在命,但仍在万历九年辛巳(1581)与之书信往来。
陈九叙以王襞“门生”的身份,回顾泰州学派的学术渊源,追溯王守仁、王艮、王襞在学术上一脉相承,认为王艮得到王守仁的真传,王襞又遍访王守仁高足,采众家之所长,将泰州学派学说与阳明心学发扬光大。陈九叙虽在王襞身边的时间较短,却与王襞的师生情谊深厚。陈九叙对王襞当年的言传身教记忆犹新,对王襞的和蔼可亲形象历历在目。陈九叙接受王襞耳提面授时间的仅一年。陈九叙的堂弟陈九仞于隆庆二年(1568)考中进士,陈九叙却仅是“贡士”[ 31 ]。陈九叙此前已返回故里,重操举子业。但不久,陈九叙于隆庆五年辛未(1571)与友人远赴王襞故里泰州师从王襞。直至万历二年(1574),陈九叙因参加殿试,而再度离开王襞身边。
王襞未提与之同往泰州师从王襞的友人名讳,考证陈九叙此友人,这就要从王襞的闽籍门人说起。该书仅载王襞的四位闽籍门人,却漏载泉州李贽,实则选择性失忆处理李贽。究其原因,与李贽和耿定向之间的关系变化有关。该书述及“(万历)二年甲戌”“耿公定向”“聘先生主会金陵”[ 18 ] 648,王襞在万历二年(1574)应耿定向的邀请,前往南京讲学,李贽于此师从王襞。陈九叙在王襞的五位闽籍门人中,并非最早师从王襞。王襞闽籍门人的求学时间有明确记载仅四人,依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40)的福州人朱孔阳、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陈九叙、隆庆六年(1572)的莆田人林讷、万历二年(1574)的泉州人李贽;该书未载“福建漳州人”[ 18 ] 712蔡国宾的求学时间,根据蔡国宾与陈九叙同为漳州人,应是与陈九叙于隆庆五年辛未(1571)一同师从王襞的友人。王襞年谱未提蔡国宾师从王襞的经过,实则漏载所致,源于未考证陈九叙所作王襞祭文。
陈九叙两次离开王襞,返乡重操举子业、参加科举考试,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与陈九叙是其宗族较早考中的举人有关。与陈九叙一同考中举人的堂弟陈九仞先于隆庆二年(1568)考中进士,且陈九仞固守白沙学说,对身为堂兄、改投王襞门下的陈九叙产生了较大的压力。
其二,与陈九叙的户籍出身有关。陈九叙出身军籍,明代卫所军户社会地位较低,军户子弟选择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提高社会地位、避免服兵役。
其三,与陈九叙故里的社会风气有关。陈九叙故里漳平是小农社会,耕读传家盛行,崇尚“学而优则仕”之风,迫使来自名门望族、军籍出身的陈九叙暂时放弃学术研究。
陈九叙所作王襞祭文述及其与王襞书信往来,回首当年王襞与陈九叙师生二人探讨王守仁“致良知”学说、王艮“百姓日用即道”学说的情形,王襞此回信即《答秋曹漳州陈文溪书》,其时为万历九年辛巳(1581)。王襞《答秋曹陈文溪书》述及其时任职刑部的陈九叙与之书信往来,“秋曹”指刑部,王襞于此自谦:“不肖早服先训,虽窃有所闻,实反身而未诚也。往年谬辱伯裳诸君,推信大过,以致受知于左右,而僭妄之罪不可追也”[ 18 ] 661,源于陈九叙对王襞的推崇备至。王襞长期关注陈九叙,追忆其“时别往宣城,犹冀归棹,借一程之送,书所请教而莫之遂,歉甚歉甚。继闻受职京师,书惠远及,注念山林,足征大雅”[ 18 ] 661,陈九叙考中进士后,担任京官,王襞为此欣慰不已。陈九叙不忘其恩师王襞,虚心向其请教。碍于王襞四处讲学,而未能收到陈九叙的来信。直至“前岁冬,始获具小启,讬敝乡袁春元少致谢意”[ 18 ] 661,却因“兼候台祉,又未获达上,而返其所寄。悬仰之情,与日俱积”[ 18 ] 661。王襞收到陈九叙的来信,喜不自禁:“迩时坐老穷庐,忽尊差赉到书翰,并厚仪见惠。故人之爱如奉颜面,曷胜为喜”[ 18 ] 661。
王襞与陈九叙探讨王守仁与王艮学说,王襞追溯泰州学派的学术渊源,对陈九叙寄予厚望。王襞忆及王守仁的教诲,阐发王守仁“致良知”、王艮“百姓日用之道”。王襞云:
昔见阳明师翁与学者书曰:讲学一事,虽犯时讳,老婆心切,遂能缄口结舌乎?仁者爱物之诚,又自有不容己者,要在默而识之,不言而信耳。非今日之谓欤。教言所谓灵明一点,正指良知一脉之传也。实致其良知于日用间,以求自慊,何乐如之。此左右极切语,更何言哉。第此旨时时向人提掇,最易令人醒悟,特欠与人痛加发挥,终至淹晦。使天下有志之士,切希圣之怀而无其径,遂网迷途莫知所适。左右交袂海内豪贤,得无与之一披彻而究竟之耶?鄙人老于丘壑,拭目以观天下,不大赖于左右恳切之力耶。如何如何?[ 18 ] 661
“陽明师翁”指王守仁,王守仁是王襞及其父王艮的恩师。
王襞至少两次到访陈九叙家中,在王襞的闽籍门人中较为罕见,反映了王襞与陈九叙关系极其密切。王襞《再集陈文溪宅》云:
绿杨风煖共登楼,楼上高歌兴更优。
适意不须投足远,合情应自结缘留。
满林莺诉花无筭,小圃疄排蔬正柔。
为语尊前诸侣道,莫教虚负此交游。[ 18 ] 693
“陈文溪”指陈九叙。“再集”指王襞再次于陈九叙家中欢聚一堂。陈九叙以《诗经》考中会试贡士,对《诗经》有深入研究,陈九叙圹志载其“有诗集《觉订漫记》传于世”,陈九叙于此应赋诗与之唱和。
陈九叙出仕后,仍钻研阳明心学,最终成为王襞门人中的翘楚。《新镌东厓王先生遗集》将陈九叙列为王襞“各省直”[ 18 ] 712门人之首,既与陈九叙在王襞门人中官阶较高有关,又同陈九叙较深的学术造诣有一定关联。《新镌东厓王先生遗集》所载《凡例》落款“万历辛亥春上丁日”[ 18 ] 643,该书刊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春,其时陈九叙健在,但已年迈,不便参加编纂其恩师王襞遗稿。参与王襞遗稿校对的王襞闽籍门人林讷与陈九叙是福建同乡,林讷认同陈九叙名列王襞南直隶故里以外的门人之首,陈九叙于王襞门人确具较高的地位。但该书亦有纰漏,如将陈九叙官职误作“杭州知府”[ 18 ] 712,陈九叙生平所任知府实则仅“处州”,应改作“处州知府”。
王襞的佛教情结[ 32 ],对陈九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九叙曾为其故里漳平县居仁里华寮社小都乡西湖岩赋诗二首。陈九叙《游小都凤岩》(在城南二十里,即西湖岩),“凤岩”即“西湖岩”。陈九叙于此感触良深,有“偶来岩壑称予心”[ 33 ] 47b之感,称西湖岩为“天开胜地”[ 33 ] 47b,西湖岩地处“名山”[ 33 ] 47b。陈九叙云及“此生到处须寻乐,莫问祇园与竹林”[ 33 ] 47b,表面上看是陈九叙提倡及时行乐,实则不然。陈九叙又云:“吾侪自有华胥乐,天下岂无尧舜心”[ 33 ] 47b-48a,其“欲说说来谁信得”[ 33 ] 48a的诗句实则反映了陈九叙的真实心境,是陈九叙有感于“只为世情横绁缚”[ 33 ] 47b的体现。
还原陈九叙与王襞的交往过程,有助于揭示陈九叙与王襞的关系程度,是陈九叙划归阳明后学立论的重要依据。陈九叙自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改师王襞,到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王襞去世,交往二十二载。陈九叙两次远赴千里之外师从王襞,源于陈九叙深思熟虑,反映了陈九叙刻苦好学、敢为人先、勇于抗争。陈九叙改师王襞,在其故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使其漳州同乡蔡国宾随之师从王襞。陈九叙两次接受王襞的耳提面命,对陈九叙而言可谓刻骨铭心。陈九叙两次接受王襞的耳提面命,更加坚定了其坚守泰州学派阵营,坚持研究泰州学派思想与阳明心学。陈九叙早年师从曾汝檀是陈九叙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陈九叙两次师从王襞实则陈九叙学术生涯的中期阶段,陈九叙出仕后著书立说则是陈九叙学术生涯的后期阶段。陈九叙先后为其恩师曾汝檀、王襞撰写行状、祭文,有助于陈九叙加深甘泉学说与阳明学说的认知,有利于陈九叙成为王襞的高足。所谓陈九叙是曾汝檀学派传人之说,实则有失偏颇,未能全面反映陈九敘的学术生涯。陈九叙应划归泰州学派,此划分既是从陈九叙的学术生涯而论,又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体现。
三、陈九叙与阳明后学交游
地方志述及陈九叙师从曾汝檀后,提及陈九叙先后获得沈宠、王襞、耿定向等前辈的认可,似乎陈九叙研究湛若水学说心得,竟获阳明后学沈宠、王襞、耿定向的赏识?陈九叙俨然成为沟通曾汝檀学派与阳明学派之间的重要桥梁,陈九叙与沈宠、王襞、耿定向之交仿佛是曾汝檀门人与阳明后学之间的学术交流,陈九叙似乎始终是曾汝檀高足?然而,通过深入考察陈九叙相关诗文,从中发现陈九叙于阳明后学谱系中,除师从王襞外,又获得沈宠与耿定向的认可,又与阳明后学杨起元探讨泰州学派著作,还与曾经同为甘泉学派门人、后与阳明后学渊源深厚的许孚远有交,陈九叙于许孚远赠诗中述及许孚远礼遇的止修王门创始人李材讲学福建镇海卫,促使早年崇尚白沙学说的漳平同乡蒋时馨最终改旗易帜而师从李材。为此,有必要深入考察陈九叙的交游情况,为陈九叙学派归属问题提供依据。下文通过搜集地方志、科举文献、文集、圹志等史料,深入考察陈九叙与阳明后学之间的交往。
陈九叙备受阳明后学沈宠、王襞、耿定向称道,实则获得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的认可。陈九叙所“学”,于此并非指湛若水的甘泉学说,而是指阳明心学。沈宠的师承关系,应以万士和《广西布政司左参议沈君宠墓表》所载“君师受轩,因同至南都参南野……已而得见王龙溪、钱绪山二公”[ 34 ]为是,“受轩”指贡安国,号受轩,“南野”指欧阳德,号南野,即沈宠实则师从贡安国、欧阳德、王畿、钱德洪,并非黄文树所云仅师从于王畿、欧阳德[ 1 ],贡安国又师从于王畿、欧阳德[ 1 ]。陈九叙与沈宠交往。沈宠宦游福建时,曾取王守仁《传习录》手订付梓[ 6 ],促使陈九叙关注王守仁《传习录》,陈九叙由此撰有《重刻传习录引》。
陈九叙与耿定向交往。耿定向于万历六年戊寅(1578)出任福建巡抚,陈九叙率先为其出谋划策,解决其治理难题。万历六年七月甲寅,“以原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耿定向,以原职巡抚福建地方”[ 35 ]。耿定向自述其初到福建,“闽在远徼,朝廷诏令难暨”[ 36 ] 812,“赖漳州陈文溪九叙者,同志友也,先是为我条画颇悉”[ 36 ] 813,漳平县时属漳州府,“陈文溪九叙”指陈九叙,号文溪。耿定向称陈九叙为“同志友”,源于耿定向与陈九叙为志同道合的阳明后学。实则陈九叙于阳明后学谱系中,辈分比耿定向高。耿定向师从何心隐,何心隐师从颜钧,颜钧师从王艮[ 1 ],耿定向为王艮的三传弟子、王守仁的四传弟子。而陈九叙师从王襞,王襞师从其父王艮以及王艮的恩师王守仁,为王艮及其恩师王守仁的再传弟子。地方志所谓耿定向为陈九叙的“先辈”,实则与耿定向时任福建巡抚有关。耿定向其时是陈九叙故里的父母官,福建地方志自然将耿定向视为陈九叙的前辈。然而,陈九叙与耿定向以友人相称,并未以学派谱系而论。陈九叙其时已师从王襞十余载,王襞与耿定向交往密切。由于王襞的缘故,加深了陈九叙与耿定向之间的情谊。促使陈九叙不顾其时在外为官,于此紧要关头,能够挺身而出悉心协助。陈九叙当仁不让率先向宦游其故里的耿定向献计献策,从而获得耿定向的交口称赞,还与陈九叙和耿定向同为军籍进士有关。《明嘉靖三十五年题名碑录(丙辰科)》载:“耿定向,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军籍”[ 20 ] 833。陈九叙与耿定向同为卫所军户,均具家国情怀,促使二人相互砥砺。
陈九叙与许孚远交往。陈九叙有诗《上许敬庵开府》,“许敬庵”指许孚远,号敬庵,“开府”指许孚远出任福建巡抚。陈九叙与许孚远原本皆服膺湛若水学说,陈九叙此前恩师曾汝檀与许孚远的恩师唐枢同为湛若水的门人,陈九叙与许孚远同是湛若水的再传弟子,只是后来陈九叙直接改师王襞,许孚远则与阳明后学关系密切。陈九叙与许孚远是故交,由于王襞的缘故,加深了陈九叙与许孚远之间的情谊。王襞《上敬庵许司马书》述及思念之情,“别后仰念我公”[ 18 ] 654。陈九叙此诗述及孔子儒学、濂洛之学、道南学派,反映了陈九叙对闽学脉络的深刻认识。首先,陈九叙于此远溯孔子开创儒家学说,北宋濂洛之学一脉相承,“衰周一堙塞,孔氏辟其芜。日月揭重光,乃还天地初。源源一脉线,濂洛奕来兹”[ 33 ] 47a。继而,陈九叙提及杨时开创的闽学,“七闽道南乡,倡率响来稀”[ 33 ] 47a。陈九叙此诗述及阳明后学李材。许孚远于万历二十年(1592)出任福建巡抚,李材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被谪戍福建镇海卫,许孚远此间延请李材在当地讲学。陈九叙诗云“师表李罗翁,偶来共绛帷”[ 33 ] 47a,“李罗翁”指李材,号见罗,师从邹守益,邹守益师从王守仁,李材为王守仁的三传弟子,属于江右王门,开创止修王门。陈九叙对李材谪戍福建镇海卫的遭遇、与许孚远的关系程度、在福建镇海卫讲学的情况均有关注。陈九叙关注福建镇海卫,源于陈九叙是军籍进士,为漳州卫所军户出身。福建镇海卫部分军队曾与漳州卫换防,理学家陈真晟因此随福建镇海卫后所军队迁往漳平,署任漳平县儒学教谕而“过化”漳平[ 37 ]。
陈九叙与杨起元交往。杨起元与陈九叙有书信往来。杨起元“《与陈文溪(二首)》”[ 38 ] 182一作“《陈文溪》”[ 38 ] 320,最初应作《陈文溪》。《陈文溪》其一述及杨起元与陈九叙交游十载:“同志之友十载,一晤又别经年”[ 38 ] 320。杨起元称陈九叙为“同志之友”,既与杨起元、陈九叙是志同道合的阳明后学有关,又是杨起元与陈九叙同为泰州学派传人的反映。杨起元师从罗汝芳,罗汝芳师从颜钧,颜钧师从徐樾,徐樾师从王艮;罗汝芳又师从李贽,李贽师从王襞[ 1 ] 。杨起元是王襞的三传弟子,陈九叙早于李贽师从王襞,杨起元应称陈九叙为师伯,杨起元因此尊称陈九叙为“丈”[ 38 ] 320。陈九叙与杨起元最初皆仰慕白沙学说,而后改习阳明心学,加深了二人认识。陈九叙与杨起元久未联系,很大程度与李贽和耿定向的关系变迁有关。虽然,杨起元为李贽的再传弟子,陈九叙却备受耿定向的称道;但是,与陈九叙久未联系的杨起元,收到陈九叙来信,仍欣喜不已。杨起元与陈九叙之间的交往推心置腹,陈九叙曾将其著作寄呈杨起元请其批评指正,杨起元对此提出中肯的评价。
《途次漫记》再三捧诵,知此事已被丈觑破。格物致知,大学第一。重钱关也,古今多少英杰,攻之不过。其说道理者,皆邪说;其做工夫者,皆乱做耳。丈今幸过此关,当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矣。[ 38 ] 320
杨起元所云陈九叙著作“《途次漫记》”,《新镌东厓王先生遗集》称陈九叙“著《途次论学漫记》行于世”[ 18 ] 712,相差“论学”二字,应以《新镌东厓王先生遗集》所载为是,即陈九叙所著实名《途次论学漫记》,杨起元所云“《途次漫记》”为该书简称。陈九叙此著作未见地方志记载,根据该书见载于《新镌东厓王先生遗集》,述及王守仁“致良知”、王艮“百姓日用即道”,实则泰州学派著作。杨起元对该书称道不已,认为是解决其时社会问题的良方,具有较高的价值。
陈九叙所著《途次论学漫记》在其生前未刊行于世。万历癸丑《漳州府志》称陈九叙“卒于家”[ 9 ] 1583。后,所著“《心源录》及诗文数卷,门人李之藻为之梓行”[ 9 ] 1583,陈九叙门人李之藻刊行的陈九叙著作不仅包括《心源录》,还包括《途次论学漫记》。李之藻既在陈九叙去世后,为之刊行遗稿,其时陈九叙为阳明后学,李之藻自然亦是阳明后学。《新镌东厓王先生遗集》称陈九叙所著《途次论学漫记》刊行于世,应关注李之藻之举,李之藻实则泰州学派传人。陈钟会于陈九叙圹志所云陈九叙有诗集《觉订漫记》行于世,亦得益于李之藻为之刊行,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与陈钟会均选择性失忆处理陈九叙阳明学著作《途次论学漫记》。
陈九叙与蒋时馨交往。蒋时馨其人,黄文树未查阅蒋时馨故里漳州与漳平地方志记载,未发现蒋时馨是李材的门人,未将蒋时馨视为阳明后学[ 1 ] 376。郑晨寅根据晚近的光绪《漳州府志》记载,述及李材的漳州籍门人,虽引用道光《漳平县志》所载,却未提蒋时馨曾师从于李材[ 39 ]。张山梁根据光绪《漳州府志》及《镇海卫志》等晚近地方志史料,述及李材的漳州籍门人,却未查阅万历癸丑《漳州府志》蒋时馨传,未能揭示蒋时馨曾师从于李材[ 7 ]。蒋时馨实则陈九叙的漳平同乡、又同为卫所军户出身,均是军籍进士。《明万历五年进士题名碑录(丁丑科)》载:“蒋时馨,福建漳州府漳平县军籍”[ 20 ] 957,是科状元沈懋学是曾经赏识陈九叙的沈宠之子,亦是阳明后学,陈九叙应向蒋时馨提及此渊源。蒋时馨在万历乙未(1595)师从李材,其时已过中年,属江右王门,为止修学派门人,王守仁的三传弟子。蒋时馨于“乙未”之后,“以选郎谢病行矣”[ 9 ] 1585,其时“豫章李公材寓漳唱道海滨,时馨师事之,讲修身为本,终日不倦”[ 9 ] 1585,“寓漳”指李材谪戍福建镇海卫。李材于福建镇海卫讲学,蒋时馨师从李材,究其原因与陈九叙关系密切。蒋时馨之弟蒋时芬与陈九叙有交,蒋时芬在蒋时馨万历丁丑(1577)中进士后隐居讲学,仍奉白沙学说为圭臬。蒋时芬“兄贵,遂隐居讲学”“构伭石洞于里之长潭上,其石壁镌‘江门倒影四字。盖慕陈江门(白沙故里)之风而私淑云。尝偕陈文溪、石洲二先生谈学于此”[ 12 ] 卷七,41a-b,“陈江门”“白沙”指陈献章,学者称白沙先生;“陈文溪”指陈九叙,号文溪,曾师从曾汝檀,曾汝檀师从湛若水,湛若水师从陈献章,陈九叙是陈献章的三传弟子。万历五年(1577),陈九叙已是王襞的弟子。陈九叙与蒋时芬的交游,实则泰州学派与白沙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蒋时馨出仕后,倾向阳明学说,与陈九叙密不可分。蒋时馨历任新喻知县与嘉鱼知县后,“稍迁南廷评。江右邹元标、新安潘士藻同宦留都,相与讲解磨勘,有《体仁篇》传于同志,道望日起”[ 9 ] 1584,邹元标师从胡直,胡直师从欧阳德,属于江右王门[ 1 ] 376,垂青陈九叙的沈宠亦曾师从欧阳德,邹元标曾自称是“王心斋先生”及其子东厓先生”[ 18 ] 644的“后学”[ 18 ] 645,即王襞的“后学”,蒋时馨与邹元标交往勢必提及陈九叙;潘士藻是李贽与耿定向的门人[ 1 ] 375,与陈九叙同属泰州学派,蒋时馨与潘士藻交往势必提及陈九叙。蒋时馨与阳明后学邹元标、潘士藻深交,促使其加深对阳明心学的理解,最终写就阳明学心得《体仁篇》,并在与之志同道合的阳明后学中流传。杨起元曾与蒋时馨相互砥砺。杨起元有诗《赠蒋兰居年兄之留都》[ 38 ] 370,杨起元称其同科进士蒋时馨为“年兄”,其时陈九叙与杨起元同为阳明后学,蒋时馨与杨起元交往亦提陈九叙。陈九叙与归休漳平故里的蒋时馨诗文唱和。蒋时馨《陈石洲陈文溪同登尊生楼玩月即事》(尊生楼在桂林坝尾,为蒋铨郎所筑归休之地)[ 12 ] 卷八,1b-2a,“蒋铨郎”指蒋时馨,“桂林坝尾”指漳平县居仁里桂林社坂尾乡。陈九叙《登蒋兰居尊生楼玩月赋谢》[ 12 ] 卷八,2a-b,做客蒋时馨家中,与之诗文唱和。蒋时馨的恩师李材因受知于许孚远得以在福建镇海卫讲学,李材“于巡抚敬庵许公……称师友”[ 9 ] 1699,陈九叙又与许孚远有交。陈九叙与蒋时馨晚年交往实则泰州学派与止修王门之间的交流,促使二人结成儿女亲家,陈九叙长子陈钟会成为蒋时馨的长女婿。陈钟会于陈九叙圹志自述“娶邑吏部铨郎蒋时馨翁长女”,“邑”指漳平县,“蒋时馨翁”指蒋时馨。
考证陈九叙与阳明后学之间的交往,有助于管窥陈九叙与阳明后学的关系程度,是陈九叙划归阳明后学的补充证据。陈九叙早年虽是曾汝檀高足,其后半生应划归阳明后学,否则陈九叙如何长期与阳明后学密切交往?陈九叙获得沈宠、耿定向认可,实因三人同属阳明后学。陈九叙虽是王襞的高足,属于泰州学派,却与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的止修王门成员密切交往。由于陈九叙虚怀若谷,导致其与耿定向不论所处阳明后学谱系的辈分,而敬奉耿定向为地方父母官。陈九叙与许孚远、杨起元早年均慕白沙学说,而后又与阳明心学结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蒋时馨、蒋时芬兄弟与陈九叙交往,既因陈九叙是其信奉的白沙学说的传人,又因陈九叙改师王襞。陈九叙早在隆庆末年即已影响其漳州同乡蔡国宾,成为蔡国宾师从王襞的领路人,对蒋时馨亦可产生积极的影响。陈九叙由曾汝檀门人改投王襞门下,导致其无门第观念,而以豁达的胸襟广交名贤。亦因陈九叙遍交名贤,对其学术研究大有裨益,最终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不能因为陈九叙曾是曾汝檀的高足,而忽视陈九叙在阳明后学的重要地位。正因为陈九叙曾是曾汝檀的高足,促使陈九叙改投王襞门下后,加倍努力,学有所成。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地方志存在选择性失忆处理陈九叙师从王襞问题,源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对后世地方志、理学著作、陈九叙故里地方官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钟会为其父陈九叙所撰墓志铭,因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为官修地方志,而不便与之记载相左。何乔远《闽书》因其漳州籍挚友戴燝、张燮参与修纂万历癸丑《漳州府志》[ 40 ],而沿用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所载。何九云受其父何乔远的影响,碍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对陈九叙盖棺论定,沿用该志记载。康熙《福建通志》因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未载陈九叙改师王襞,认为沈宠、王襞、耿定向仅是历史名人,从而省略陈九叙请教阳明后学史事。康熙《漳平县志》因漳平县晚明未修志,而采用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所载。康熙《漳州府志》因循修纂府志体例,而采用此前所修府志万历癸丑《漳州府志》记载,却误作王襞别号。乾隆《龙岩州志》因龙岩直隶州前身龙岩县与漳平县同属漳州府,而采用康熙《漳州府志》所载,导致以讹传讹王襞别号。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参考康熙《漳州府志》所载,以讹传讹王襞别号,未揭示沈宠、王襞、耿定向的学派归属。
第二,地方志采取选择性失忆处理陈九叙师从王襞问题,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所处的历史情境有关。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为李材立传,对阳明后学有所了解,不可能不知沈宠、王襞、耿定向、邹元标、潘士藻的阳明后学身份。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之所以未指出陈九叙师从王襞,源于陈九叙的早年恩师曾汝檀在漳平地方社会长期备受尊崇,由于甘泉学说与阳明学说相左,导致该志不便提及陈九叙改师王襞。万历癸丑《漳州府志》由“漳平知县傅文勋”“仝修”[ 9 ] 72,顾及漳平地情,导致该志仅载陈九叙是曾汝檀的高足,而未提陈九叙改师王襞。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同情阳明后学李材遭遇,而将王襞置身于陈九叙请教的前辈当中,欲为后来考证陈九叙学术渊源埋下伏笔。康熙《漳平县志》采用万历癸丑《漳州府志》记载,源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所载陈九叙师从曾汝檀,与漳平地方社会推崇曾汝檀之风相契合。康熙《漳州府志》肯定陈九叙著作《心源录》[ 14 ] 卷二十九,6a的学术价值,将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列入“列贤传”[ 9 ] 1537的陈九叙调整到“儒林”[ 14 ] 卷二十三,8b之列,却未搜全陳九叙著作,无法还原陈九叙应有的学术地位。
第三,陈九叙故里漳平及其曾经隶属的漳州地方社会集体失忆陈九叙师从王襞,源于与曾汝檀对漳平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地方志由于官修性质而产生的影响、同漳平毗邻的泉州府安溪县籍李清馥所撰理学著作产生的影响、漳平与泰州两地的交往情况有关。漳平地方社会对陈九叙改师曾汝檀最初是路人皆知,却苦于无重要人物光大曾汝檀学派,从而仍将陈九叙视为曾汝檀学派传人。漳平地方社会此意愿,获得陈九叙后人的支持。陈钟会身为陈九叙长子、蒋时馨的长女婿,深知万历癸丑《漳州府志》述及蒋时馨师从李材,焉能不知陈九叙与蒋时馨同为阳明后学?陈钟会于陈九叙圹志秉笔直书陈九叙“谪两浙运同,复谪桂林府同知”,却屈服于漳平地方社会,只字未提其改师王襞以及与阳明后学交游。陈钟会深知陈九叙圹志虽将随葬墓中,却因陈九叙改师王襞,其圹志书写仍备受漳平地方社会的关注。陈钟会深知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为漳州知府所修,可不必完全响应漳平地方社会的意愿,仍可留下一定空间而提及王襞。陈九叙圹志则不同,陈钟会只能于此选择性记忆处理陈九叙师从曾汝檀,而选择性失忆阳明后学相关人物。陈钟会之所以完全向漳平地方社会妥协,既因其父与岳父同为阳明后学,又与此二人均遭仕途折戟有关。陈钟会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依傍曾汝檀这一文化符号,以廓斋后学自居。其时,泰州学派消亡,陈钟会亦不便提及陈九叙的阳明后学身份。漳平与泰州两地地理位置相距较远,古时交通不便,两地长期以来交往较少,王襞著作未获漳平地方社会关注,最终对陈九叙改师王襞史实茫然不知。何九云宣称陈九叙与曾汝檀、蒋时馨受到陈真晟“过化”漳平的影响,实与何九云出于地方教化的需要,根据陈九叙与曾汝檀、蒋时馨为漳平同乡而阐发。
第四,当前阳明后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应重点进行文本分析,方能重建史实,重写历史。不能停留在重述文献记载层面,而是要揭示文献记载背后的历史情境,并分析其成因。应还原文本的书写过程,考辨采用选择性记忆处理与选择性失忆处理的内容,并分析其原因与目的。既要回到历史现场深入考察,又要置身于广阔的时空深入考察。对地方志书写的阳明后学,应抱之以同情与理解,揭示阳明后学的思想演变过程,尊重其人生各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探索地方志书写阳明后学的思路,既要从地方志的阅读对象出发,分析地方志的书写用意;又要从地方志的书写结果入手,分析地方志书写产生的影响;并从地方志书写所处的历史情境切入,分析地方志如此书写的缘由。
参考文献:
[1]黄文树.阳明后学的成员分析[J].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0(17):371-388.
[2]钱明.闽中王门考略[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J].2007(1):60-66.
[3]张树骏.论王襞的思想渊源及其对王学的贡献[J].毕节学院学报,2009(1):67-74.
[4]张树俊.王襞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3):111-115.
[5]张树骏.韩贞与王襞的交往[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6-9.
[6]汪学群.明儒刊刻《传习录》的旨趣[J].船山学刊,2015(1):66-72.
[7]张山梁.漳州阳明学发展阶段探析[J].教育文化论坛,2021(1):48-54.
[8]林晓峰,张山梁.传承阳明心学,弘扬漳州文化[J].闽台文化研究,2019(3):50-57.
[9]闵梦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州市委员会.(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下册[M].影印本.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10]曾汝檀,朱召.(嘉靖)漳平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8册.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0.
[11]刘涛.屈大均、陈恭尹与高维桧交往背后的故事——岭南印学在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地位及其影响[J]//张伟.中国文化论衡:2020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94.
[12]查继纯.(康熙)漳平县志[M].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92(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13]金鋐,郑开极,陈轼.(康熙)福建通志:第2册[M]//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福建:第2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486.
[14]魏荔彤.(康熙)漳州府志[M].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715(清康熙乙未).
[15]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岩州志(清乾隆三年镌)[M].点校本.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271.
[16]何乔远.闽书:第4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3621.
[17]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M]//徐公喜.理学渊源考辩丛刊.点校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18]王襞.新镌东厓王先生遗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19]罗青霄,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府志:下册[M].点校本.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20]李周望.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M].影印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21]申嘉瑞.(隆庆)仪真县志:卷九《先举考》[M].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963:7a.
[22]陈得堃.陈太常户世系族谱:上册[Z].抄本复印件.漳州:政协漳州市委员会海峡文史资料馆藏, 1938(民国二十七年).
[23]徐渭.徐渭集[M]//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1334.
[24]钱明.阳明学传入福建的路径、时间及影响[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38(1):1-6.
[25]张琦.(康熙)建宁府志:卷十八《职官二》[M].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93(清康熙三十二年):16a.
[26]李周望.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M].影印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411.
[27]佚名.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M].明刻本清代何桂清跋.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1368-1644)刻本:70a.
[28]刘涛.嘉靖《漳南道志》考述[J]//重庆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长江文明:2021年第3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21:54-57.
[29]刘涛.徐樾、朱锡在闽南漳州的活动及其意义[J].贵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20-26.
[30]徐阶,等.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第56册(卷五百五十)[M].抄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代.
[31]台湾学生书局.明代登科录汇编:第17册[M]//屈万里.明代史籍丛刊.影印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8883.
[32]张树骏.论王襞的佛道情结[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3):53-59.
[33]蔡世钹.(道光)漳平县志:卷九《藝文志下》[M].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830(清道光十年).
[34]焦竑.国朝献征录:第6册[M]//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26册.影印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224.
[35]佚名.明神宗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第11册.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651.
[36]耿定向,傅秋涛.耿定向集:下册(附编二:《观生纪》)[M]//明代别集丛刊.点校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7]刘涛.福建镇海卫扬州籍军户与陈真晟学派渊源考[J]//周新国.淮扬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50-51.
[38]杨起元.续刻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7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39]郑晨寅.从“正学堂碑”看明末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播[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59-64.
[40]刘涛.明代东南文坛名家戴燝年谱[J].闽台文化研究,2018(1):93-107.
[责任编辑:黄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