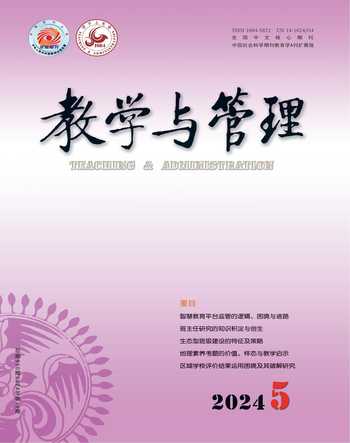现代学校制度功利化的正义审视与建构
学校制度伦理的价值意蕴在于使学生过一种良善互惠的学校生活。制度伦理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假设,从根本上决定着制度安排的正当与否。好的制度伦理不仅能保证学校生活不走向非正义一面,还能够引导学校生活向善向好发展。然而,现代学校因受制于非正义的制度安排,呈现出一种高度功利化的不义倾向,使得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陷入危险的境地。面对此困境,有必要从正义伦理的视角审视当前制度伦理的价值理念、结构安排以及程序运行。好的制度伦理决定了学校生活的善制与善治。基于正义伦理的学校生活力求在理性统一方面做必要的权宜,实现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合理化资源分配,在承认差异中保护每个人的尊严,寻求转向合作互惠的良善学校生活。
制度伦理;学校生活;功利化;制度正义;正义伦理
马雯.现代学校制度功利化的正义审视与建构[J].教学与管理,2024(13):12-16.
在学校中,选择了什么样的制度伦理,就决定了学生大体过什么样的学校生活,同时也塑造着相应的道德品格。学校制度伦理的价值意蕴在于使学生过一种良善互惠的学校生活,好的制度伦理意味着学校生活善制与善治的可能与必要。这就需要从制度正义的视角,审视当前学校制度功利化的倾向,从而建构合乎正义的良善学校生活。
一、制度正义:良善学校生活的前提保障
制度作为一种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结构安排,依据不同的伦理价值,支配着人们的生活选择,塑造着人们的道德养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制度都内在着特定的伦理价值,只不过有着“好”与“坏”,“善”与“恶”的分别,判断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因此,在学校生活中,“好的”制度伦理建设的根本标准和方向也应该是能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依此制度伦理构建的学校制度注重正义的优先性,在促进学生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制度优势。那么,制度正义的伦理意蕴有何价值呢?
其一,制度正义作为一种底线伦理,保证学校生活不走向非正义的局面。一方面,从律己的意义上来说,道德教化的弱力量需要制度正义的强约束加持,从而阻止人性中恶的一面。“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3]在现代学校制度中,由于资源稀缺和人性自私两个前提始终存在,所以不可避免会发生人们为了一己之利互相争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的情况,学校生活也因此容易沦为一个坏的生活世界。面对这种不好的生活世界,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发展出某种制度以保证可以接受的生活[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指望通过道德教化从而达到对人性恶的约束,显然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另一方面,从律他的意义上来说,相互性关系形成的条件性构成了正义的脆弱性,正义本身的脆弱性呼唤制度予以保护。人与人的相互性关系以人与规范的关系为基础,同时,人与规范的关系也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他人普遍遵守正义规范是每个人遵守正义规范的前提”[5],即相互性形成的条件是他人也必须这么做,只要他人不遵守正义规范,就意味着相互性制约的解除。换言之,如果学校生活中有一部分学生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规范,那么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感的学生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他人的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由此导致“非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6]。这就需要借助制度规范的力量,约束他人也不要做惡事。在律己与律他两方面最起码保证学校是一个不坏的生活世界。
其二,制度正义作为一种相互有利的安排,保障学校生活的良序善治。在学校生活中,学生之间不免会存在利益或不一致的相互冲突情况,制度正义有助于在利益冲突的情境下指导学生签署相互有利的协议,从而引导学生向善向好发展。“任何公正理论都必须将制度的作用置于重要地位”[7],因而一个“好”的制度对于构建正义的学校生活具有安排上的优先性。“好”的制度不仅仅指制度本身的合理合法,更要关涉此制度引导下的行为是否正义。一方面,完善的制度安排有助于“促进学生自由发展”的目标实现。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从制度分配的方面定义其“公正原则”,这只是实现制度正义程序中的第一个环节,正义的教育制度还应该考虑制度生活中的非分配领域。此外,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应指向正义。退一步讲,若一项制度形式上正义,但实质上不正义,若其程序完备,将会发挥更坏的价值效用。另一方面,好的制度为人们合乎正义的行动提供了框架结构。作为生活在制度结构中的人们,其行动免不了受制度的影响,这是无争的事实。正如罗尔斯所说,我们不能离开制度来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8]。换言之,在一个不好的制度中,即使学生本人的行为动机无意破坏正义,但也有可能犯下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在此意义上,好的制度是在为好人做好事营造良好的学校环境,有助于引导学生的行为走向规范与善意。
二、制度不义:现代学校制度的功利化倾向
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审视学校制度设计的正当与否,是在伦理学的维度上关注制度,对现有学校制度进行的价值分析。以正义伦理的立场剖析现代学校制度表现出的功利化倾向发现,程序运行中的同一性逻辑造成了对个体差异化的限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原则破坏了制度结构中的正义环境的供给,过度追求工具理性的实质非理性造成了对人性的僭越。
1.价值的失衡: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僭越
从现代学校制度内嵌的功利化价值理念来看,这是一种非人性化的工具理性主导的教育制度。当工具理性以压倒性的方式占据学校生活的主导,长此以往,生活在其中的人容易失去主体性、意志自由和创造性,进而导致人们长久地被置于工具理性砌筑的“铁的牢笼”中。
第一,在制度的伦理价值方面,工具理性主导的制度伦理追求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学校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都与可计算性紧密相关,学生日益被训练出计较得失的功利心理。在这套价值理念的渗透下,出于对行动结果的最大程度收益的考虑,学生会不自觉地参与到竞争中保全自己的利益,最终竞争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学生们为了竞争而竞争。正如韦伯所说:“合理性的计算把每个人变成了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对于生活在这种境遇中的人来说,他关注的是如何从一个小齿轮变成一个更大的齿轮,促使人们追逐权力,产生向上爬的发迹思想。”[9]此外,工具理性主导的制度伦理倾向于把一切教育关系异化为由目的——手段支配的物化关系。第二,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为了追求效率的高度精细化控制容易造成实质的不自由。从工具理性来看,这种高度精细化的控制虽然将学校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学校像一个庞大的机器高效率地运转,各项指标都在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实际上,这种工具理性发展得越彻底,实质上的行动就越偏向非理性,因为它奴役了学生的主体性,剥夺了学生的自由,最终个人压倒集体,冲向泰勒所说的一种社会原子主义[10]。第三,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平衡中,根深蒂固的二元思想将两者视为不可调和的两端,以至于形成韦伯所说的“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每一个过分的理性化要求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非理性和不合理的现象的产生;非理性与合理性共存,前者与后者相对立并表现为后者的结果”[11]。由此可见,制度伦理越偏向工具理性,就越导致结果的非理性,学生在这两者的相互抵牾中不可避免地被非人化。
2.结构的不义:利益最大化对正义供给的破坏
随着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面對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现实情况,就越需要基于正义原则的制度结构保证资源供给免受利益最大化的破坏。首先,在分配领域,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教育正义的第一维度,也是基础性维度[12]。外部性资源的公正分配是教育正义的前提,然而现代教育制度的分配却是以竞争为逻辑的。正如罗萨所说:“现代社会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都是竞争逻辑。”[13]基于竞争逻辑的分配原则容易造成少部分人对优质资源的占有,激起大多数人的不满与怨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理应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化制度伦理进行纠偏。正如艾丽斯·M·杨所说:“如果某种分配的结果抑制了某些人的生存和健康,或者赋予了某些人资源来压迫他人,那么无论这种分配的结果是如何造成的,都必须对其提出质疑。”[14]其次,在非分配领域,结构性的压迫与宰制导致弱势群体的尊严陷入制度性的贬损与僵化的境地。制度规定了一个人能对另外一个人做什么的合法边界。在功利化学校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充斥着种种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等,导致一部分强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造成了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伤害,而本就偏爱少数强者的制度却为强者的野蛮行为做了合法性辩护,弱势群体陷入被当前制度排斥的不利境地。最后,无论是分配领域,还是非分配领域,都不具有达成相互合作的正义环境,这就导致过度追求利益的功利化行为愈发泛滥,当前过度竞争的内卷行为即是明证。正所谓“一部分人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而不得休止”[15]。
3.程序的标准化:同一性逻辑对差异的限制
寻求最大化掌控的制度程序倾向于将那些个性的、不确定的、流变的经验纳入到一个标准化的秩序当中,从而导致冷冰冰的同一性逻辑对个体差异的限制。首先,在制度的运行中,治理的同一性逻辑否认或压制差异。以单一性考试制度为主导的同一性逻辑渗透在学生的学校生活中,隐性地通过价值赋予与价值加权,制造了教育生产的标准化。“这种逻辑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它将我们原先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追求目标全部简化成为数字形式的单一价值,然后把目标的门槛不断越提越高,使得现代社会所有人都被迫卷入以提升数值为单一价值的漩涡中——被迫不断内卷。”[16]学生受制于学校预先设定的制度框架,每个人毫无例外地被卷入到标准化的赛道中。其次,同一性逻辑倾向于构建稳定的制度环境,拒斥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异质的个体经验。在同质化的制度管理中,不同于集体特质的他者被视为变动的异数,效率主导的最大化原则以消灭而不是承认否定他者的存在。“通过同一性逻辑,思想想要掌控所有事物,消除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将那些对超越主体范畴以外的世界进行直接感受的身体性势必加以精神化,去消灭他者。”[17]最后,同一性逻辑反映在程序的运行中,是将个别的差异转换为绝对的他者,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好学校”与“差学校”,“好学生”与“差学生”之间的区分,从而造成更大的差异。“教育原本应关注孩子们的内在禀赋的开发,而不是摧残任何不符合‘应试教育体制的内在禀赋。”[18]在这种力求同一、排斥差异的努力下,不符合主流的差异实体只能被迫承认自己的失败,压制自己的内在禀赋。
三、善制与善治:合乎正义的学校生活构建
合乎正义的学校生活离不开好的制度引导,好的制度不仅指制度本身内蕴的伦理价值是向善的,还包括制度治理过程的正当合理。构建合乎正义的学校生活,需要制度合理引导人们的实践行为,自觉从“非理性竞争”的敌我关系转向合作互惠的结盟关系,在资源分配方面实现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合理化配置,在承认差异中保护每个人的尊严,在必要的权宜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最大化促进学生的发展。
1.必要的权宜: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对形成合乎正义的学校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制度管理的要义就在于善于调适两者的比重。首先,从理性发展的历史背景看,西方遵照逻各斯规定的形式逻辑的规则,以排中律反对矛盾的存在,从而导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极端对立,以至于两者陷入完全不可协调的二元对立桎梏。不同于西方二分的思想源流,我国自古以来所说的“理”就包含着从整体视角出发的统一原则。其基本的意思是纹理、条理,依照事物发展规律,调和事物的矛盾,使其相互平衡[19]。“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之理就是任何事物都包含了两种相对或者相反的力量、原则或者具体的构成要素。”[2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性本就是整体的、平衡的,不是二分的、对立的。其次,权宜的前提是要正确地认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工具理性在制度发挥最大化功效方面的确值得肯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并把效率原则运用到极致时,人就面临着被制度宰制的危险。因此,面对当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支配情况,我们不应当采取“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的极端苛求态度,而是应该在竭力缩小前者的负面影响与扩大后者价值引导之间做出权宜。最后,权宜的程序是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理性协商过程。面对制度生活中个体保存与群体制约之间的矛盾,基于“互为主体性”的理性协商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缓解群己关系对立的有效手段,应当引导人们自愿走出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主动融入群体生活中,自觉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理性协商的过程是一个主体性得到充分解放的最佳手段。在理性协商的过程中个人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每个人的主体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最终成长为韦伯所说的“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 ,避免成为哈贝马斯笔下“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2.合理分配: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教育资源配置
合理分配教育资源是制度正义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也是其他方面正义实现的条件性保障。如果最起码的资源均衡配置都不能满足,其他方面的正义恐怕就更难实现。第一,正义的教育制度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而自由地享有教育基本的权利与机会。《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了受教育权是一项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一人权视角要求教育必须面向所有人,无分收入、性别、种族或民族……或其他任何可能被用来歧视和排斥的特征。”[21]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入学考试制度中,指标到校、名额划分都应保证人人都能无条件享受到教育这一基本益品。正如沃尔泽所说:“对正义理论惟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学习不能够成为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少部分人的排他性特权。”[22]
第二,教育资源的分配要尽可能地均衡,这种划分要满足使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的愿望。当前学校之间的资源分配是基于绩效原则的竞争性分配模式,是一套有着先后次序的等级化分配程序,其背后是市场的利润机制在起支配作用,这就需要政府出于保障教育公共性的责任来治理教育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罗尔斯说:“如果足够多的公民发现公共利益的边际利益比通过市场可获得的边际利益大时,政府寻找一些方式来提供它们便是恰当的。”[23]如今大多数人因为教育资源的有限,纷纷做出抢占资源的内卷化行为,从而进一步导致教育获得的边际效益递减与努力的通货膨胀,一部分原因就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平等,没有满足人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第三,教育资源的分配要考虑教育这一基本善事物的特殊性。一方面,区别于社会其他资源的分配,教育资源的的特殊性体现在不仅关乎学生现在的发展,对学生未来及其发展可能性有着深远影响。教学职位、学生位子以及各种知识的分配模式不能简单地照搬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模式[24]。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种善事物的特殊性还决定了其分配程序也应当是独立的。由于学校、教师以及制度的运行构成了一套有别于社会体系的新的有益品,因而其分配模式也应当是独立的。
第四,教育资源的分配要适当倾斜于处境不利群体。“对于不利者而言,如若没有行使权利的能力,所谓的权利只能是‘空头支票”[25],这就要求资源的配置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打破形式上的平等,从而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因为对事实上不平等的个体使用平等的分配原则进行资源分配必定会造成更大的差异。正如罗尔斯所期望的那样,事实上的平等需要以一种不平等为前提,“即对先天不利者和有利者使用并非同等的而是不同等的尺度”[26]。
3.正当逻辑:在承认差异中保护每个人的尊严
“好的教育制度”离不开对人的价值的关涉,尊严作为人成为人的根基性价值标准,应当受到教育制度的首要保护和关照。首先,承认差异意味着尊重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一方面,制度要保护每个学生的尊严不被侵犯,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个性、能力、兴趣和价值观,承认差异意味着认可每个学生的禀赋,并提供相应的制度空间,促进每个学生实现最大化发展。另一方面,制度要规范引导学生之间进行相互承认,在相互承认中尊重他人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承认差异的教育制度中,每个人都应该被当作目的,受到同等对待。其次,承认差异意味着看到不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与潜力。人类最具独特的地方在于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每个人的能力和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27]。因此,任何无视个体间差异而进行的单一化、同质化与整体性的制度安排,根本上都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正如哈耶克所言:“如果忽视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重要性,那么自由的重要性就会丧失,个人价值的理念也就更不重要了。”[28]此外,个体能力与潜力的激发有助于不同个体积极参与学校的公共事务,欣赏学校的文化,反过来,这又会促进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最后,承认差异是对同一性逻辑的反对,承认人们身上那些不能被计数、被衡量与被辨识的特质。同一性逻辑以一种普遍的、整体化、原子化的冰冷思维力求掌控所有事物,消除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消灭他者中否认或压制差异[29]。然而,人的行动是复数性的,即人的活动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有着不同的形态。正如阿伦特所说,人的差异源于人的复数性[30]。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人类行动的条件,在行动中彼此需要、互通有無。
4.良善生活:转向合作互惠的相互有利安排
人是政治性的动物[31],注定要过政治性的生活,这就注定人要与他人进行合作。在一个增进共同利益、促进他人福利的制度生活中,个人才能收获最大的善。在这种制度结构中,地位较好者的利益改善着地位最差者的条件。首先,合作互惠的制度安排具有现实向度的可能与必要。一方面,由于人们都有大致相近的需求和利益,这为相互有利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处于一个“中等匮乏”的资源状况之中,即资源不足以丰富到使得合作显得多余,同时也不是匮乏到使合作成为一种被拒绝的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合作就显得及其必要。其次,相互有利的合作旨在于形成一个良善有序的学校生活。比较各种不同的制度选择,相互合作带来的效益要远远高于竞争式的个人奋斗。“由于社会合作使所有人都能过一种比他们各自努力、单独生存所能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32]在一个相互有利的制度环境中,每个人都以增进共同利益为最终追求,相应地人与人之间更加宽容与友爱,良好有序的学校生活得以实现。反之,“在一个相互畏惧的环境中,甚至正义的人也可能陷入一种长期敌对的状态”[33]。最后,在一个良序的学校生活中,相互有利得以进一步发展为相互善意。良序的学校生活使得相互有利的利益关系获得了充分的保障,以至于人们不再过分关注利益获取的多寡,而是自发地、无条件地心生对彼此的同情与善意。久而久之,相互有利激发的善意逐渐转变为内心自发的善意,相互善意逐渐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引起一种假使没有外在条件存在的情况下,个人依然能自发地关心彼此、爱护彼此的“错觉”,“而这种‘错觉又会反过来维持和巩固貌似自发的相互善意”[34]。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赖于“联合体”的制度条件。这种“联合体”的制度条件离不开“好”制度的伦理价值引导。良序善意的学校生活离不开合乎人性、符合教育正义及指向于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设计。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1997(03),54-66.
[2][8][23][26][32][33]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22,283,25,126,336.
[3] 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532.
[4]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3.
[5][6][15][34] 慈继伟.正义的两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5,1,7,147.
[7] 阿马蒂亚·森.正義的理念[M].王磊,李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74.
[9][11][19]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233,234,116.
[10] 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M].陈炼,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66-67.
[12] 胡金木.教育正义的多维审视:资源分配、文化承认抑或自由发展[J].教育学报,2022,18(01):3-13.
[13] 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31-32.
[14][17][29] 杨.正义与差异政治[M].李诚予,刘靖子,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34,118,118.
[16] 罗萨.不受掌控[M].郑作彧,马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13.
[18] 汪丁丁.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9.
[20] 唐士其.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117.
[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12.
[22][24] 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M].褚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277,262.
[25] 程天君.新教育公平引论——基于我国教育公平模式变迁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02):1-11.
[27][28]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103,103.
[30] 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06.
[3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8.
【责任编辑 武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