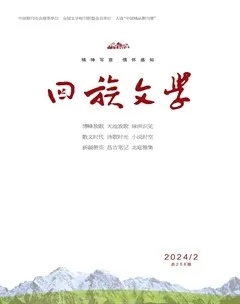菜籽沟无名山上听雨亭
王莉
那是5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们顺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终于站在了菜籽沟无名山的山脊上。
带领我们上山的是木垒书院刘亮程老师的爱人,我叫她金姐。金姐指着蜿蜒上行的栈道说,走,顺着这条栈道走上去,看看山上那座听雨亭吧。
听雨亭?听雨亭在江南,在雨水丰沛的地方随处可见。公园里有,景区山地上有,而且都在亭子上毫无例外地书有“听雨亭”三个字。
在安徽滁州古城南湖公园北岸,有一座八柱四角长亭,名为听雨亭。据说是取意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一诗:“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岸边亭下站着一人,眼望水中残荷,听雨滴落在水中,滴落在枯黄的残荷上的声音。因为周遭再无别人,独有的宁静中,那人一定听得出雨声与以往蓊蓊郁郁草青叶翠的荷塘之上曾经的雨声是多么地不同。
有朋友去苏州游玩,归来后我曾经特意问,去拙政园听雨轩了吗?
友人不解,到那儿做什么?我答,听听雨打芭蕉的声音呀。
那里墙脚下、花窗外,随处可见芭蕉绿色舒展的身影。下雨的时候,雨水滴落在芭蕉油绿的叶子上,淅淅沥沥的声音,构成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境。
而这,在古时候是文人雅客的清玩。“蕉叶题诗”“雨打芭蕉”便成了古诗词中的经典意象。
友人听我这一番解释,连连摆手,那是闲人做的事情呀,我们大多数人哪里有那闲情逸致,忙得跟头绊子的。那你出去游玩又是做什么呢,赶个时髦?当然,这话我并没有说出口。我怕伤了友人。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滁州的听雨亭、苏州的听雨轩,我还没有亲见过,对它们所有的经验,均来自生活在当地的文友的描述介绍。眼下可以亲见一下这菜籽沟无名山上的听雨亭,心情不免有些激动。
我三步并作两步,顺着栈道向上赶。远远地看见一个飞檐尖顶的亭子,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亭下空无一人。
走近之后,只见飞檐正面有一长方形匾牌,上书:听雨亭。六根圓柱,六道飞檐,六角形亭下周遭设有围栏,围栏连着座椅。
我仰着头,围着亭子转了三圈,然后驻足在亭下。
山风吹拂着脸颊,我一遍遍环视山野里的一切。我很贪婪,总想把它们统统拢进我的视野,刻印在记忆里,以便于日后能够端坐在桌旁,拿起笔,一点点讲述这里的山水草木,这里的麦田,这里古老村落曾经的故事。
正值夕阳缓缓滑向远处的山边边,余晖不怎么强烈了,以至于在我的手机镜头里,太阳就像一个刚刚出了馕坑,散发着热气,氤氲着香气的馕饼。
真是一览众山小。山坡坡上青绿的地方,是麦田,绿色略深,凸起的是树木,还间有大大小小的浅褐色块。近处低矮的灌木丛中不时有鸟儿或飞或落,起落之间,流泻串串清脆的鸣叫。久居喧闹的街市,很少听到这样的鸟鸣了。也许有,只是步履匆匆的我,心事沉沉的我,自然屏蔽了它们吧。
我俯瞰着一山山一坡坡似波浪般涌动起伏的麦田,惊讶得发不出声音来。
我在另一篇名为《我是一缕吹过菜籽沟的风》的散文里,曾描述过我看见麦田的感觉:山坡上成行的麦苗,由高到低,铺展开来,给我的感觉,是流动的,是画家不小心把调好的颜料打翻了,绿色便淌下来,漫溢开来,填满菜籽沟所有山坡坡的缝隙。
金姐说,今年菜籽沟比往年雨水少了很多,否则你们看到漫山遍野都是一码子深深浅浅的绿。那些浅褐色的色块,就是因为缺雨水,草长不起来,即使是长起来一点,也被牛羊啃吃得差不多了。
金姐的话,让我陷入沉思。
新疆离潮润的海洋实在太远,本身就少雨,山区由于地势地形的缘故,能略略多点雨。菜籽沟就是这样一个所在,但也不至于在这山脊之上修建一座号称听雨亭的亭子吧?
听雨亭,听雨亭,多雨的江南,多有叫听雨亭的亭子,不就是为了人们能在雨来的时候,能躲在下面赏景、听雨吗?新疆少雨,连雨伞、斗笠之类的遮雨用具都很少用得着。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估计叫听雨亭的亭子,也少有吧?
这座听雨亭,是为了应景、造景?我不得而知。
本想就这个问题和书院的刘亮程老师探讨交流一下,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是从无名山观完听雨亭后下来的第三天,我坐在书院的阳光房里,听到一场久违的雨声,忽有所悟。
这阳光房,房间除了房基是砖砌的之外,墙和房顶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雨点滴落在屋顶,似有人不小心翻掉了盛豆的盆,豆子丁零当啷砸落着,滚动着的雨声敲击耳膜。雨声反衬着山中的寂静。寂静里,我脑海里闪演着几天来在书院里的一幕:
我在书院听到了久违的燕鸣。在这里的每一个早晨,我都在它的歌声中醒来。我坐在书院客房后边的阳光玻璃房中开始晨读。
阳光玻璃房后是一大片草木。成熟的榆钱儿撒满窗外的小路。榆钱儿在等风吹起,等吹起的风,把它们带到菜籽沟其他的角落。我的智慧囿于我的见识,我不能够像刘亮程老师那样,把目光伸向更远更辽阔的地方。他说,菜籽沟的榆钱儿,可以在风中飞很远,飞到哈密,飞过嘉峪关,飞到河西走廊。然后在那里长成一棵大榆树。
望着他把一粒榆钱儿捏在指尖,对着阳光透视榆钱儿种子,如数家珍地叙说,我就知道,他的智慧、他的辽阔,来自自然,来自大地,来自家乡站立在风中的村庄。他熟稔村庄里的一草一木。
忙碌了一夜的风,累坏了,清亮的燕鸣,没能吵醒它们。那棵刘老师手植的沙枣树很安静,那些榆树很安静,那些草很安静。
我暗喜。这样我可以从容地记住它们的模样,起风的时候,它们被风摇晃得太厉害,我无法看清它们。
刘老师笔下那些给我们带来无限新鲜、无限想象的草木和动物,一定是他在起风之前就潜入它们内部,被它们接纳,才那么灵动吧?
燕子在林间鸣叫着,我看不见它的身姿,也看不见它的表情,不知道它是愁,还是高兴。只能聆听它的一声一声的鸣叫。其实,看不见燕子的身姿,看不见它的表情,无关紧要。我可以通过它的声音,感知到它的想法。燕子的心情似乎与天气有关系。
阳光明媚的时候,它的叫声略略宽泛些,声音柔韧,在其他鸟鸣的声音里,燕子的鸣叫就显得尤为突出。燕子成了林中众鸟音乐会中的主唱。
山雨欲来的时候,风吹刮的时候,燕子顾不上那么姿态优雅地在林间鸣叫了,它会急促贴着地面或者贴着草丛飞行。在这样的飞行间歇中发出短促的鸣叫,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爆破出来的。
来菜籽沟之前,我预想了各种遇见,唯独没有想到久违的鸟鸣,更没有想到每天不用出门,坐在房中读书时,就能听见燕鸣。我很羡慕能够在菜籽沟安家的这些鸟儿们。树林里的鸟,是树们的贵客。树用绿叶及其带动的风声,馈赠给客人。
很多年了,树林没有走进过人们的视线。最多有风来串一下门。但现在,鸟的鸣叫,把树林推介到人们的眼前,尤其是燕鸣,让我记住了菜籽沟的树林,记住了掩映在菜籽沟树林里的木垒书院。
夜幕降临整个书院之后,燕子把声音藏匿起来了。它知道自己需要退场了,它知道它不属于黑夜。属于黑夜的是猫头鹰。蛰伏了一个白昼的猫头鹰,站在黑暗处,用独特的叫声,明亮自己的形象。
雨声,燕鸣;燕鸣,雨声,交织轰击着我的思维。
诗人戴望舒在《寂寞》中道:“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
我觉得,留守在菜籽沟的村民们,心中都有一座听雨亭。他们在这里的沟沟坡坡上播撒下麦子。麦子绿了,麦子抽穗了,麦子扬花灌浆了。年成好丰收了,年成不好歉收了,眉宇间是淡然,心底也是淡然——祖辈就是这么过的。
我也觉得,刘亮程老师在炙手可热的文学创作鼎盛时期,抽身隐入菜籽沟,在木垒书院耕读写作,也是寻到了自己的听雨亭吧。
那无名山上的听雨亭,何尝不是我等所有寻觅生命中另一场雨的人,最好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