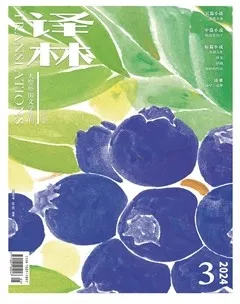另面人生
〔韩国〕金劲旭
爸爸临终时,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不,应该说临终时,他才更像是我这个小说家的爸爸。
听到噩耗的亲戚都不由得问:“你确定不是你妈妈病危吗?”妈妈患有慢性肾衰竭和老年痴呆症,爸爸也有病,但不严重。爸爸此前因急性肺炎住院,现在正在康复。“蛮像你爸的风格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走得干净利落。”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正如他们所说,爸爸活得很认真。他的人生就如他经常挂在脖子上的皮尺一样准确无误,犹如一条没有岔路、笔直到让人犯困的高速路。
“小说写得精准,就像用尺子量了似的。”
某次,在看到某位评论家对我作品的评论的瞬间,我领悟到了一点:我那死板的小说风格就来源于爸爸!这对我的打击持续了很多年。我在任何一篇文章中,甚至私下里都没提起过爸爸是做西服的裁缝。本以为自己已经费尽力气跑到了另一条路上,却还是在与爸爸并肩奔跑。是我的错觉吗?写出“超凡脱俗的篇章”的竟然不是我,而是爸爸。
“医生说把患者的子女都叫过来。”
手机屏幕上出现“白班护工”的瞬间,我变得烦躁不已,我做梦也没想到护工那儿忽然就传来了噩耗。昨晚,我一整夜都蜷缩在陪护床上,和这位护工换班才两个小时。
刚开始,我不懂这一切是什么意思。爸爸病情好转后,已经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两天了。虽然经常去卫生间,但他的呼吸已经不再那么困难。新雇的夜间护工说今晚才能开始工作,所以昨晚只能由我来陪护。因为在我们三兄妹及配偶中,第二天早晨不用上班的就只有我。
“你确定吗?”是因为每个月末的周一银行业务都最忙吧,妹妹的声音疲惫不堪。
“当然。难道等爸爸去世后再给你打电话?”我的声音不知不觉中变得尖锐,但实际上我也质问过护工:“爸爸早上的粥都喝完了,你有没有搞错啊?”
“快要去世的人大概都这样,像僧人一样吃完饭还把钵盂刮得干干净净。可能是想见孩子们吧,乱蓬蓬的胡子都刮得很利索。”护工们像说秘密似的窃窃私语。实际上,是我把剃須刀递给爸爸的。
昨夜大约00:30,本以为已经睡着了的爸爸悄悄起床,要找剃须刀。我劝他:“半夜刮什么胡子啊!等天亮吧。”但他不听。搬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我拿了加湿器,热敷贴,甚至连木枕都拿到了病房,难道竟忘了拿剃须刀?爸爸的电动剃须刀怎么都找不到。
我实在受不了他不停地抽拉抽屉,便放下手头的诗歌译稿走出了病房。医院小卖店打烊了,我便去附近的便利店。
“商店不卖三层刀片的剃须刀吗?”爸爸被我搀扶着去卫生间的时候,还没忘记问一句。每件事他都是这样细心,像给西服上衣缝扣子一样。
“西服上衣即便不扣纽扣,也得有板型。哪怕穿上几百次,也得有线条。用缝纫机就做不到这一点。”
手工缝制的西服要经过照灯程序,只要扣眼有一点光透出来,爸爸就会把缝好的线全部拆开,重新缝。
弟弟一直不接电话,我只能发短信留言。
——爸爸病危。
本来想发送,但删掉后重新写了。
——爸爸快不行了,速归。
我慌慌张张地和弟弟妹妹联系,却把母亲忘在脑后。
“他俩毕竟做了半辈子的夫妻。我陪她一起去吧。”还是妻子想起因为痴呆症去疗养院住院已经三个月的妈妈。妻子刚好下课,打电话时她提醒了我。
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爸爸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脸色如尸体一样苍白,身体也明显萎缩了。鲜血从脖子上流出,绕过人工心肺机一圈进入胳膊,只有这一点证明他还活着。我感觉从爸爸体内流出的不是血,而是他的灵魂。
“老爷子,睁睁眼睛!您大儿子来了!”护工摇动爸爸的肩膀。
“爸,是我,道京,大儿子道京!”
听到我的声音,爸爸的眼皮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斜眼看着我。那是过去弟弟妹妹做错事的时候,不管是非曲直,先罚我跪的那种眼神。不一会儿,爸爸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我俯下身,耳朵贴近爸爸。
“哥呢,你哥呢?”爸爸呼吸越来越急促,艰难地说出了这么一句。
那是爸爸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在我这个长子的耳边,他就是这么问的。弟弟没到,短信也没回。
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爸爸误以为我是弟弟道蓥。我和弟弟的名字只是声母不同。加上我俩连声音都很相像,所以打电话的时间一长,他经常会叫错名字。尽管如此,每当有陌生中年男性进入灵堂的时候,我都会留心察看。爸爸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我是不敢想的,但看到那张陌生的脸时,我还是想到了爸爸的临终遗言。
那个男人是在我独守灵堂的时候出现的。弟弟和妹妹忙于接待前来吊唁的同事,所以只有我守灵堂。那个男人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的服装很显眼——带着白色条纹的藏青色西装,这可是上世纪的旧款式。那是一件肩垫非常夸张的三排纽西服,领子非常宽。这是为了遮住上半身矮小的弊端而设计的款式。
“真正的西装裁缝,并不只是制作西服,而是使人和衣服相得益彰。”爸爸一谈到自己的本行,就会一改平时谨慎、木讷的本色,充满自豪。就像一个阐释自己作品的艺术家!
无论是年纪还是衣着,那个男人都不像弟弟妹妹的熟人。难道是没有什么来往的远房亲戚?但是看他点香后盯着遗像看的样子,也不像是外婆那边的亲戚。难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强忍着巨大悲痛?他系着黑色的领带,规规矩矩地把点着的香画了两圈后再插上,却只行了一次跪拜礼。他与我互相行完跪拜礼后,就远远地站着,丝毫没有要靠近我的迹象。
“您是……”当我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只是跟我行了个礼,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小说家的本能驱使我跟在男人的后面。我心想:没人守灵堂合适吗?就犹豫了一下。再出去一看,那个男人早已不知去向。
他穿的会不会是在米拉波拉制作的西服?
“米拉波拉社是我取的名字。美拉!宝拉!莎拉!虽然不敢肯定,但慕名而来的客人应该也不少。即便把这个牌子挂在首尔的明洞繁华街,也毫不逊色!如果当初按照你爸的意愿叫‘伦敦西装店,恐怕你爸都没法供你们上大学啊。幸亏我早年当过远洋渔船船员,见多识广……”
我原以为这个西服店的招牌充满了沧桑,但鳄鱼堂叔却跟我说了这么一通话。一旦被堂叔缠住就很难摆脱,只能乖乖地听他长篇大论。在葬礼上也是如此。以前,弟弟和妹妹总是偷偷地溜掉,唯我一人留在酒桌上听他侃侃而谈。当然,尽管我当时年纪小,但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因为堂叔一旦开心,就会掏出棕色的皮夹,拿零用钱给我。据说这是用在尼罗河捕获的鳄鱼皮做的钱包。
鳄鱼堂叔的话,很难分清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吹牛。
“秀吉虽然手笨,但手艺还是很好的。要是参加国际技能奥运会的话,金牌是十拿九稳的。”
“秀吉吗?不是秀容吗?”
“难道你不知道你爸改名了吗?原名叫秀吉。优秀的秀,吉祥的吉。他做裁缝店学徒的时候,也不知道抽什么风,一到法定的成人年龄就改名字了。把‘吉字辈的‘吉改成了容貌的‘容,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成了脸赞(用来形容脸蛋最漂亮的人,源于韩国。——译注)。还有一次,你爸爸脱下假人模特身上的双层夹克,穿上后去了忠武路,说是要当演员。”
爸爸还有这样的故事?他可是一听到我要当小说家,就大声呵斥我“你要饿死你的妻儿!”的人啊。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辈分字不能动的。如果你爸爸把吉字留下,不仅事业有成,还能多活十年呢!”
“他为什么没参加国际技能奥运会?”
“他有恐高症,不敢坐飞机。”
怪不得爸爸从来没出过国。连去济州岛旅行,他都摇头说讨厌大海。紧接着,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这样一段记忆:每到儿童节,爸爸就带着我们三兄妹去公园坐摩天轮,自己却不坐。四人一组的座舱每次都会空出一个位置,难道他真的有恐高症?
“在爸爸上面,有早逝的兄长吗?”我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又在写小说?对了,你的小说不是获得什么艺术家奖了吗,叫什么来着?”
鳄鱼堂叔又问这个已经问过十几遍的问题。我说过很多遍:不是获奖作品,而是候选作品!但是,对他没有什么用。
我也知道,爸爸当时清楚地说了“你”哥,而不是“我”哥。虽然很想问问爸爸有没有私生子,但由于堂叔的高谈阔论,便没有了机会。当然,就算真有,堂叔也不会告诉我的。
其实,这应该直接问爸爸。四十多年前,他把一个光头中学生带回家时,我就应该问他是谁;或者一听到谜一样的遗言,我就应该马上问:你指的是那个哥哥吗?或许自从听到“哥哥”的那一刻起,我就摸索着遥远的记忆,想起了那个中学生哥哥。
当时爸爸是怎么介绍他的?说是同宗亲戚,还是含糊其词地说是受老乡嘱托?爸爸出生于离大陆只有半小时船程的岛上,是七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所以我家的来客络绎不绝。这就是即便父母从未教我怎么叫他,我也自然而然地叫他哥哥的原因。而如今也无法期盼二老能给出答复了。
真正被问到的人是前来吊唁的洗剑亭(今位于首尔市景福宫后面的亭名。亦指那一带。——译注)姨妈,虽然她只比母亲大了五岁,但我父母举行婚礼的时候,是她代替早早去世的外婆,坐在了婚宴的主宾席上。她还是三个姨妈中唯一一个居住在首尔的。“这里是洗剑亭。”接电话时,她总是先报小区的名字,有一种生活在繁华地方的人独有的优越感。
“不是哥哥,而是姐姐。你知道这事吗?”洗剑亭姨妈微微摇了摇头,直视着我。
“姐姐?”
“你姐没活过三天。幸亏我们从你妈结婚起就常去看她!她怎么会连自己怀没怀孕都不知道呢?你爸让你妈一辈子受苦,如今却丢下生病的她先走了。”
“为什么妈妈从来没提过那件事……”
洗剑亭姨妈突然面色剧变,打断了我。“那是什么时候来着?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为什么洗剑亭有三个黑色(“洗剑亭”的韩文谐音。——译注),是因为夜晚有三倍黑吗?,那时我就知道你能成为作家。你肯定是继承了外婆家的基因!我上女子高中的时候,也经常作为学校代表参加现场写作比赛呢。”
姨妈虽然依然与我对视,但又似乎在透过我的脸看着别处。
我突然想起从姨妈那里收到的结婚礼物——用华丽的金箔包裹著的派克钢笔。虽然用礼物代替礼金的行为很特别,但让我难以忘怀的原因不是这个,而是钢笔笔杆上印着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姨妈的名字!
或许应该得到那支钢笔的不是我,因为说出“三个黑色”的话的是四十多年前来我家住过几天的小孩,不,是那个中学生哥哥。
“你还记得那个哥哥吗?”吊唁快要结束时,我和弟弟一人拿着一罐啤酒面对面坐下来。我跟他提起了那件事。“就是小时候,在咱家住了一个星期,还是十来天的那个中学生哥哥。”
“这个嘛。在咱家住过几天的何止一两个?咱家简直就是米拉波拉旅馆。”
如弟弟所说,从堂兄妹到不太熟悉的朋友,在我家短暂住过的所谓“哥哥”的确不少,但那位哥哥住在我家时,家里的氛围很不一样。母亲就像老师来家访一样,干什么都很上心。比如,为了好看,她竟在鸡蛋皮里夹上一层紫菜做成鸡蛋卷,还把以前直接用铜锅端出来的泡菜汤给每人单独盛一碗。哥哥的校服裤子都被熨出笔挺的褶。最大的变化是爸爸的眼神,原本很严肃,竟温和了不少。
“你就是那个未来的法官?看上去很会耍锤子啊!”是因为他总是斜戴着的校服帽子?还是因为他那微笑时扬起一边嘴角的特有表情?初次见面时他大大方方伸出手的动作及握手时的触感,我至今记忆犹新,但他的长相却模糊不清。深深刻印在我九岁记忆中的并不是那个哥哥的名字,也不是面孔,而是一种感觉,就是那种显得成熟稳重,却给人一种桀骜不驯、自由奔放的感觉。
“你还记不记得把各种颜料混在一起,变成黑色的事情?”我喝了一口啤酒后,问弟弟。
“哥哥你做的吧?说这是变魔术。”
弟弟的回答令我感到惊诧。
说出“物体的颜色是因为物体反射了特定波长的光,黑色吸收了所有波长,所以才像黑洞般阴暗”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哥哥。
“物体的颜色是由反射光决定的。”他很酷地说。
看样子弟弟对那个哥哥没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告诉弟弟那个哥哥是第一个教会我抽烟的人。当然,也没必要告诉他那几天尽情享受的解脱感。那时,九岁的我在剧烈的干咳中脸色通红,吐出了烟。那不是烟,而是一种希望。那个哥哥如果是我亲哥该多好,能从爸爸那充满期望、严厉无比的目光中解脱出来该多好啊!
爸爸希望我成为那种打着领带上班的人,所以他执意把西装店搬到法院门口,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是爸爸的风格——不用言语来表达,而是用尺子精心测量似的安排我们的前程,让我们动弹不得。
“只要我把尺子拿出来,就算是法院院长也得站直。他脱掉法官服还像不像法官,可是取决于我的手艺。”
虽然爸爸从未说过要让我上法学院,但我每次都会在“未来志愿”栏中填上爸爸想要的职业。俗话说“有压迫就有反抗”,我成为小说家,或许就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吧。
上初中时,我跟爸爸说美术老师劝我进美术社团,爸爸就在上美术课的那天不让我上学。旷课一次就足以让我放弃画画的念头。
“爸爸临走时是什么样子的?”弟弟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安静地走了,蛮像他一贯的行事风格。”我一边起身,一边说道,并试图努力抹去头脑里盘旋的这句话——“你哥呢?”
爸爸肯定是把我错认成弟弟了!即使我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爸爸是一个藏有这种秘密的人。他的一生就像翻手就能看到的掌纹一样,又像米拉波拉橱窗一样,显而易见、一目了然。当年,爸爸年仅十五岁,整天修补渔网,逃离家乡来到了这座港口城市。在这里,吸引爸爸的是一个系着领带工作的裁缝。在他眼里,领带是成功的象征。
我记忆中的爸爸是一个像领带结一样死板的人。顾客一旦不来试穿假缝的衣服,他就不会继续下一步工序。即使别人来代取做好的衣服,他也会以“需要确认本人穿的样子”为由,把人打发走。这样的爸爸怎么会有私生子?这就如同爸爸偷穿橱窗西装到首尔去当电影演员的逸事一样,荒唐至极。
第二天上午,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因为是周六,一大早就有人来吊唁。我把高中同学带到接待室时,就看到那个熟悉的背影在角落里自斟自饮。不会又来了吧?单看那厚重的西服垫肩,就知道是那个男人。
在与高中同学寒暄的过程中,我总是不住地往那边看。他那花白但浓密的后脑勺,看上去很像爸爸。他就坐在姑妈们围坐的桌子旁边。从没人跟他打招呼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既不是本家人,也不是老乡。
到底是什么样的交情,要来吊唁两次呢?我正琢磨该怎么坐到他对面搭话,起身的一刹那,接待处的小舅子来找我了。我看到灵堂门口站着一个好几年没见面的大学同学。
“外交部公务员考试也不错。”
爸爸只希望我考上法学院,但当我考上第二志愿——英语专业时,他也爽快地给了学费,像发善心似的说出了上面的话。但我不喜欢英语,心里只装着文学。即使我后来成了小说家,爸爸也仍然不放弃。有一次回老家过节,看到书桌上有一本我高中时读过的书——《如此人生》,我翻了几页,看到勒口上的作者简介——小说家兼外交官下面画着一条红线。当时,我很好奇,爸爸知不知道书中的内容呢?因为小说讲的是一个儿子否定爸爸的故事。
当我领着大学同学回到接待室的时候,那个男人不见了。桌面很干净,连他垫着的坐垫也摆放得很整齐。
“刚刚坐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坐到了刚才那个男人的位置,问旁边桌上的小姑。
“谁啊?”
“那个自己喝酒的人。”
“那里刚才有人吗?”小姑问对面的二姑。
“是不是你爸回来过?”不知道是哭了,还是酒劲的缘故,二姑眼圈发红。在六个姑妈当中,她是跟爸爸最亲的一个妹妹。二姑递给我一杯烧酒。
“你爸为了照顾我们,差点儿打了光棍。你爸非要把我们全都嫁出去,才娶媳妇。算命先生说如果你爸四十岁以前没有孩子,妹妹们就会遭殃,他这才改变了主意。否则,就没有你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我觉得自己在听一个陌生人的經历。难道人生的真貌,只有在生命结束后才会被看到?难道爸爸谜一样的遗言,到了临终才会说出来?
“真的没看到吗?他穿着一件垫肩很厚的西服!”我又问姑妈们。
“你姑父穿着你结婚时做的西服来了。他说那件陈旧的西服是你爸做的。他一大早就自己喝酒,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小姑帮我往上拉了拉滑下来的袖章说道。
昨天那个男人似乎也打量过我的袖章。
葬礼第一天,我从灵堂的内室换上丧服出来时,葬礼司仪便拿着麻布袖章和麻布孝带来问谁是长子。他说:“死者是男士,所以袖章要挂在左臂。长子戴两道黑杠的,次子戴一道黑杠的,女婿戴没有杠的。”
虽然我很想问他为什么必须让别人区分出长子和次子,但我还是忍住了,只是点了点头。难道那个男人就不知道袖章上的黑杠所代表的含义吗?难道他是在那里寻找四十多年前与自己短暂相处过的九岁小孩的影子吗?如果他看出我是长子,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也许,他认为我已经不记得他了,就像弟弟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一样。
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真正坐过那个位置。不,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强烈地意识到那个男人的存在。他再次让我觉得自己胳膊上的袖章有多么沉重。
我们硬把妈妈从疗养院接过来参加入棺仪式。昨天,妹妹去了,妈妈大喊“什么葬礼要办两次啊!”,妹妹便只能灰溜溜地回来。大家商量了一下,一致决定把妈妈接过来,让他俩见最后一面。
这次是我去接妈妈。我没提葬礼,只是哄她说去约会。听到约会,妈妈的眼睛闪闪发光。那是一种特别的眼神,跟不善于表达的丈夫一起生活的妈妈,只会将这种眼神投给我。像往常一样,我装作没看见,收拾行李。
回到灵堂,我看到十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正在做追思礼拜。别说是逝者,其实丧主中也没人信教,谁把他们叫来的?我很困惑。
妈妈瞥了一眼爸爸的遗像,转身就要离开。我拽住穿上我的皮鞋要逃走的妈妈,把她搀扶到灵堂内屋。
“衣服黑乎乎的,不想穿。”妹妹想在妈妈裤子上面围上丧服裙,但是妈妈粗暴地甩开了妹妹的手。我冲着妹妹摇了摇头。妈妈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背對着灵堂呆呆地坐着。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爸爸已经去世的事实。
“那比太阳更明亮的天堂,我要带着虔诚的心前去。那依偎的宝地,我的主已经准备好。几天后、几天后渡过约旦河来相见。几天后、几天后渡过约旦河来相见。”这是从墙的那边传来的歌声,副歌很刺耳。妈妈看上去很正常,这让我更揪心。觉得不跟她搭话,我就要撑不住了。
“米拉波大桥。就是电影《魂断蓝桥》里的桥。你爸看完电影后,就向我求婚了,就在大使酒店餐厅。后来裁缝店的招牌也取自那部电影。虽然开着裁缝店,但你爸每月一到别人领工资的二十五号,就会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崭新的钞票。之前我拒绝了你爸,嫌生意人收入不稳定。结果,你爸一辈子都在那天给我钱。”当我问妈妈为什么取名叫“米拉波拉”时,她打开了充满回忆的相册,看上去像是在做梦。
“啊,这样啊。”那家酒店不是在首尔吗?你不是一到亲戚们发工资的日子就去借钱吗?我强忍着疑问,附和着她,是因为妈妈精神不正常,我才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直萦绕在嘴边的问题。“那个哥哥是谁?就是那个我九岁时爸爸带过来跟我们一起住过十多天的中学生哥哥。”
妈妈突然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上去很惊慌,又好像很生气。“在我生下第一个儿子后,你爸给我做了套西装。量得好仔细啊。量得好像要再做出一个我似的。只要我穿上那件衣服走在大街上,回头率那个高啊。但是,生下老二和老幺后,他就再也不给我做新衣服了。”妈妈一把抓住我的手。一只手托着我的掌心,另一只手盖住我的手背,两只手完全裹住我的手。结婚后听妻子说,妈妈只对我才这样。
“看来礼拜结束了。”我悄悄地抽出手,站起身来。
“你爸爸是我们教堂的信徒。”从做完追思礼拜的人们那里,我才得知爸爸常去离家不远处的教堂。两年前开始去的?那时爸爸为了让妈妈接受门诊治疗,关掉店铺,刚刚搬到首尔。定制西服被时代淘汰后,爸爸做起了服装修补工作。但他还是把卷尺挂在脖子上,坚决不换“米拉波拉社”的招牌。这样的爸爸也需要新的精神寄托,竟然会去教会?那么,在我去首尔上大学的火车上发现的爸爸的信又是怎么回事呢?
去首尔后须遵守的事项:
——不要参加示威游行。
——不要和信教的女生淡恋爱。
用这笔钱在路上买一碗乌冬面吃吧。
我清晰地记得,在装着十张面值万元新纸币的信纸上,写着这样几行字。我还记得自己眯着眼盯着那个夹杂着错别字的第二条看了好久。“不要参加示威游行”也就算了,“信教的女生”之类的话令人发笑。即便如此,我还是会不经意间问相亲女孩的宗教信仰。
那天晚上,爸爸也在祈祷吧?当晚,他说自己还有力气刮胡子,硬要让我在洗手间外面等着。那时我就感觉有点怪。过了半天也没动静,我打开门看了看。爸爸跪在瓷砖地上,双手紧贴着洗漱台,额头放在双手上。他是体力不支,还是在祈祷?难道他鼻子和下巴下面的胡子只刮了一半,就开始祷告了?难道他在祈祷自己离开人世前要见一见之前无法相认的真长孙?
那个男人第三次露面,是在入殓仪式快结束的时候。爸爸的脸上被涂得煞白,套上了麻布寿衣。我对这样的爸爸非常陌生,连准备好的告别词都没说出来。与爸爸告别后,我后退了几步。这时,我透过玻璃看到了站在送殡席上的那个男人。他伸长脖子越过念诵祈祷文的教徒,望向爸爸躺着的地方,似乎有话要说似的。
我不敢把目光从那个男人的身上离开,哪怕是片刻,生怕他又消失了。当我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向那个男子的时候,葬礼司仪叫住了我。“长子,你得封棺了。”
大家都把手放在棺材盖上,就等着我。虽然我始终也没有回头看,但在封棺的整个过程中,我都能感受到那个男人的目光。他的眼神让我感到很别扭,却无法摆脱。或许,他看的不是爸爸,而是我正站着的位置吧。
爸爸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人活着,难免会经历这样的夜晚:明知道彼此都醒着,却只能闭着眼睛煎熬的夜晚!就是那种不是因为睡不着,而是由于无法睁开眼睛而精疲力竭的夜晚。那天晚上,我们从洗手间回到病房,直到天亮都没说一句话。像睡着了似的没有一点动静。四人中间,我俩齐躺在黑暗的角落里,仿佛在展开一场奇异的心理战。病房里只有其他患者的咳嗽和鼻鼾声,我们格格不入。
爸爸说不刮剩下的一半胡子了,对此我为什么发火了呢?不管做什么事,爸爸不做到底就不罢休。我无法忍受“出格”的他。我侧躺在狭窄的陪护床上,努力回想刚才没校对完的译诗。这是我为了能和爸爸单独度过一夜,特意带去的活儿,因为对我来说,英语诗歌是与爸爸的卷尺距离最远的世界。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
他们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棺材板慢慢遮住了爸爸的脸,他苍白眼皮上的白光完全消逝了,脸上没有任何“怒斥”。
我拿着校样,一直冥思苦想的是这首诗的最后一段。
您啊,我的爸爸。在那悲伤的山坡,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我在考虑,文中把the sad height译成“悲伤的山坡”,是不是应该译成“悲哀的山坡”呢?与爸爸的最后一夜,我这样熬了过来。
入殓仪式结束,我回头一看,那个男人不见了。我急忙跑出去找他,但在通往出口的走廊里却没发现任何踪迹。我感觉被什么勾住了魂。如果不是汗水从耳根流下,我也许会认为自己做了一场梦,因连续熬了两个晚上,精神恍惚而做的梦。
我去洗手间往脸上泼了把冷水。上次刮胡子是什么时候来着?我的鼻子下方和下颌线黑乎乎的,头发乱蓬蓬的,眼里布满红血丝,怒气冲冲的。
突然,镜子里出现了熟悉的西服。搭在隔板门上的旧上衣露出了半截,西服的双肩完全舒展开来。那个中学生哥哥洗脸或出汗时,会很讲究地把校服上衣脱去。正常放进西服盒里的西服是竖着叠的,而他却横着叠校服。爸爸做的西服,定会在内兜纽扣正下方用紫色的草书绣上“米拉波”三个字,所以,只要掀开衣角,就能确定是不是爸爸做的。我盯着镜子里的西服,突然打了个冷战。爸爸的脸出现在那里!那是一张既抗拒出现又无法彻底释怀的面孔。
我赶紧关掉水龙头,离开那里。隔板上高高挂着的西服令我产生恐惧,我得趁那西服主人推开门出来之前离开那里。
我并不是真的害怕爸爸有秘密。我倒真不希望他如我了解的那样毫无隐私。
后来,我偶然查到电影《魂断蓝桥》中出现的桥是滑铁卢桥。那是在整理爸爸遗物时,在网上搜索后才知道的。为什么取名为米拉波拉社?我再次陷入迷茫。虽然我后悔不该揭底,而应该把它当作《魂断蓝桥》中的米拉波桥。但是,当意识到爸爸的人生是需要我趴在地上填写的纵横填字谜的那一刹那,我就不后悔了。当然,一想起现在除了我,谁也不记得那个中学生哥哥,就更是如此。
哥哥在我家里住了一周还是十天?记不清了。就在哥哥住在我家的某一天,我发现他在用打火机熏黑信纸边儿。我问他在干什么,哥哥翘起嘴角答道:“我准备写一个爸爸为了让我好好学习,要烧掉我精心书写的情书,我从火中取出这篇情书的故事,把它放在背面。”
起初,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是写给午夜广播节目的信。看到哥哥在正面写上公开求爱的内容、背面写上这篇文章差点儿成为灰烬时,我才明白了,就点了点头。
“这样,肯定会被播音员选中朗读的。”哥哥像揭示魔术一样,冲着我挤了挤眼睛。当我被人问及成为小说家的原因时,虽然嘴上说是初恋失败,但现在看来,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那若无其事地编造故事的哥哥迷住了!
哥哥浑身散发出一种独有的气质,那是我所不具备的。每当回顾那个场景,我就会产生一种偷取别人的人生的感觉。而且,在烧毁一半的信纸正面写的情书是用诗来开头的,但我不知道他引用了哪首诗。
米拉波桥下的塞纳河在流淌着,
我们的爱情也随之流走了。
应当追忆吗?
总在痛苦之后的快乐。
黑夜降临,钟声响彻。
时光消逝,独留我。
插上一个跟爸爸的死无关的话题。我最终将斟酌许久的诗句从“悲伤的山坡”改为“悲哀的高度”。虽然应该避免重复使用抽象名词,但不知怎的,觉得“悲哀的高度”似乎更好。
“您啊,我的爸爸。在那悲哀的高度,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
顺便再坦白一件事情:是我剃光了爸爸的胡子。不管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把爸爸那只剩一半的胡子从眼前挥去。剃净胡子后露出来的脸,不正是我嗎!不是儿子像爸爸,而是爸爸像儿子。
爸爸,这次换你来做我的儿子,我来好好照顾您!
刮胡子的时候,爸爸静静地闭着眼睛。儿子只是感到好奇:爸爸无力地让我刮自己下巴胡子的那几秒,爸爸是在诅咒儿子,还是在祝福儿子?或者是两者兼具?
(石建国 邓茜予 朴春燮: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